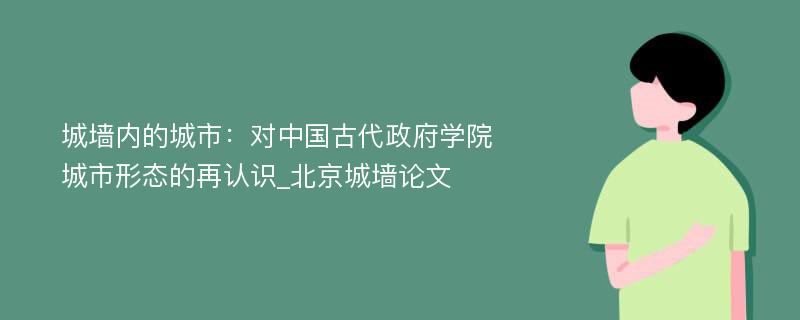
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城市论文,城墙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9)02-0007-10
一、问题之提出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城市大都围绕着城墙。章生道说:“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①陈正祥也说:“城(walled town or walled city)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很突出的标志,构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②因此,在众多研究者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城市一般被描述为四周用夯筑或砖砌的高大城墙环绕着(一些城市还筑有二至三道城墙),城墙的四方开着三、四至七、八个城门(较少的城有少于三个或多于八个乃至多达十二个城门),城墙外通常有护城河(并不一定环绕城墙,往往借助自然河流作为城壕,靠山的部分或多未掘壕)。城郭的形状通常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个别呈圆形;城的规模(通常用城墙的周长来衡量)虽然因城的行政等级而异,但一般较大,“城内土地面积到达一两方公里是很平常的事”,“远较欧洲及日本的城堡为大”。城内不仅包括各种官署衙门、民居、店铺,还有大片的空地(包括园圃、山林、川泉,甚至农田)。城内的格局则受到其行政职能与城门数量的制约:官署衙门等公共权力建筑物一般位于城的中北部,谯楼则常位于正中央;城门的数量与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内的街道布局③。
无庸置疑,上述认识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实地观察与研究基础之上的,揭示了历史事实的重要方面。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认识,我们注意到,其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1)以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官方文献。几乎每一种地方志都有关于城池、公署廨舍、坛庙、桥梁以及城内街衢的详细记载,这是我们认识治所城市空间形态与内部结构的主要依据。然而,出于对权力机构的重视以及这些权力与信仰设施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城池、公署等权力设施的地位、作用乃至其空间形态都被明显地夸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各种明清地方志所附地图中城池在舆地图上以及官廨衙署在城池图上所占据的完全不成比例的空间位置,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④。这种文字记载与古地图对城池的强调与夸大强化了中国古代城市“为城墙所环绕”的特征及其作为军政中心的政治控制功能,相应地,也就引导人们忽视了某些细节,比如城墙外街区的存在以及城市的其商业经济功能。(2)早期来华传教士及其它西方人士有关中国城市的记述,这是西方学者认识并描述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依据。这些主要出自目击者的记述,感性色彩随处可见:当这些西方人来到一座繁荣富庶的城市里,显然更易于被宏伟壮丽的城垣及宽敞高大的廨舍所吸引,而对欧洲城市中同样具有的熙熙攘攘的市场和拥挤的居民区则较为忽视⑤。无需引述马可·波罗那些颇有争议的夸张性描写,即使是最为直接可靠的西方目击者留下的记录,对城垣、道路及廨舍的描述也占据着突出的优势地位。这与中国传统文献中对城池、官署的重视相互印证,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表现为“城墙内的城市”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还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一些总概性的描述和典型城市的个案研究,前者以观察资料为基础,后者则主要集中在一些历史上的重要城市(特别是都城)的研究上。事实上,虽然中国城市史与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一直较受学术界关注,但有关地方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的薄弱也是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感性阶段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乃是“城墙内的城市”这一论点,并未得到切实而全面的实证性证明,而只是以一些直观认识与典型个案研究为基础的,其中还存在若干疑点:(1)在中国古代,具体地说,从秦汉以迄于清代,大部分治所城市由城墙所围绕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即是否在大部分时段里,大部分治所城市均筑有城垣,而且这些城垣确实在发挥作用?(2)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是否占据全部治所城市的大多数?(3)古代治所城市的街区与居民是否全部或大部分均包括在城墙所围绕的范围内,换言之,是否全部或大部分城区均由城墙所包围?
显然,要切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最可靠的途径乃是进行更多的、细致的个案研究,通过大量个案研究的积累,逐步形成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的总体性认识。斯波义信曾经指出:“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方面,通常总是以长安、洛阳或北京之类的模式,千篇一律地概括中国的城市,而且满足于这种研究的思想非常根深蒂固,因此很难作出,诸如一般的和正规的城市论、城市形态论或城市生态论之类的研究。”他认为,只有通过对诸多个别城市的研究和比较,找出普遍性与特殊性,才能提炼出有关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正确论述⑥。遵循这一研究理路,我们对古代汉水流治所城市的城郭形成与演变、外缘形态及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开展了尽可能细致的考察。本文即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地区的城市个案及有关研究,对上述问题作些探讨。
二、城墙之有无
在中国古代史上,历代王朝是否一直奉行修筑城垣的政策?如果王朝奉行这一政策的话,那么,它是否在各地均得到普遍执行,即事实上地方城市是否普遍修筑起城墙?对此,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并得出了一些初步认识,认为“至少在中国王朝后期的宋、元两朝以及明代的前中期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很多地方城市长期处于城垣颓圮、甚至无城墙的状态”⑦。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研究以及对其它地区城市的认识,我们认为,可以将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城墙的修筑、存废情形,大致区分为四个时期:
(1)汉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普遍奉行筑城政策,事实上各地城市也普遍兴筑起城垣。
《汉书·高帝纪下》记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颜师古注云:“县之与邑,皆令筑城。”论者多据此认为汉代奉行筑城政策。从今见史料看,这一政策也确实得到较普遍的执行,大多数郡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沿用先秦特别是战国时期所筑之旧城),而且经常得到维护、修缮⑧。在汉水流域,南阳郡治台宛(在今河南南阳)、汉中郡治西城(西汉,在今陕西安康)与南郑(东汉)、江夏郡治西陵(在今湖北云梦县城关镇)及宜城、冠军、博望、育阳、西鄂、棘阳、比阳、堵阳、湖阳、郦、安众、新都、邓、襄乡、舂陵、朝阳、临沮等县均筑有城郭,且已得到考古勘查或发掘之证明⑨,从而进一步说明汉代郡县治所较普遍地筑有城垣,没有城垣的县治当不会太多⑩。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中国古代史上的“城居时代”:一方面,自汉末三国以迄于隋唐之际,中原板荡,变乱频仍,“百姓流亡,所在屯聚”(11)——“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12);西迁、北徙、南来的移民,亦大多据城壁以自保,从而形成以城邑、坞堡、戍垒为中心的聚居状态。另一方面,各政权对于地方的统治,或藉豪族所筑之坞堡,因其地而立州郡县,遂使坞堡成为州郡县治所;或由地方长吏“敛民保城郭”,选择险要处另立城郭,以为据守之资。于是,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兴筑了很多城郭。据刘淑芬统计,这一时期魏晋北朝所筑城郭见于记载者共有137座(13);而章生道的统计则表明,自西晋以迄于隋统一(265-289年),南北方新筑的城郭共有169座,其中位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区者有121座。显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新筑的城郭要比北方地区多得多(14)。因此,虽然很难估计此一时期所筑城郭的总数,但认为此一时期各地均普遍兴筑各种类型的城壁坞堡、著籍户口多居于其中或附城而居,当无大误。
(2)隋唐五代时期,王朝虽然提倡筑城,但各地往往因地制宜,或沿用旧城垣,或新筑、增筑城垣,或根本没有城垣。
《隋书·炀帝纪下》记大业十一年(615年)二月庚午诏称:“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于是,“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15)则隋炀帝时尝奉行筑城政策。然其时大乱之势已成,欲“令人悉城居”以强化其统治,实无可能,故虽天下郡县悉皆筑城,而成者则甚鲜。
唐初,至少在北方诸边,曾颇提倡筑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16)武德九年春正月《修缘边障塞诏》称:“其北道诸州所置诚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其城塞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为成功。”(17)诏命“所司具有条式”,则筑城或已成为制度。《唐律疏议》卷8《卫禁》“越州镇戍城垣”条云:“诸越州、镇、戍城及武库垣,徒一年;县城,杖九十。(原注:皆谓有门禁者。)[疏]议曰:诸州及镇、戍之所,各自有城。若越城及武库垣者,各合徒一年。越县城,杖九十。纵无城垣,篱栅亦是”(18)。则按照制度规定,诸州镇戍县皆当“各自有城”,“纵无城垣,篱栅亦是。”
然而,这些制度规定并不意味着唐代州(府)县治所即皆普遍筑有城郭。在爱宕元所列的《唐代州县城郭一览》表中,共有164个州县城郭注明了筑城年代,其中有90个是唐天宝以后(不含天宝年间)所筑,占全部已知筑城年代之州县城的55%(19)。注明筑城年代在唐天宝以前(含天宝年间)的74座州县城中,注明其筑城年代在先秦时期者实颇为可疑,不足凭信(20);几个注为后汉或三国孙吴所筑的城郭,也须详加考定(21)。那么,唐天宝以后所筑城郭在全部已知筑城年代的州县城郭中所占的比例,只能更大;更遑论未注明筑城年代的那些州县城郭,也有相当部分为天宝以后所筑。换言之,这些天宝以后方修筑城郭的州县治所,在天宝以前,也就是唐前中期100多年里,并未修筑城垣;而在唐前中期,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州县治所,并未修筑城垣。
当然,文献中未见有关筑城的记载,并不说明州县治所本身即无城垣,而很可能沿用汉魏以来旧有城郭,只是在唐前中期未加维修而已。研究表明,在唐前中期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治所城市中,隋及唐初新筑或重修的城郭只有2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3.4%;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旧城垣有40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69%;其余16座州县治所在唐前期很可能并无城垣,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7.6%。显然,沿用旧城与基本可断定没有城郭的州县城,占据了全部治所城市的绝大多数。唐代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城,虽然仅占唐帝国1500余座州(府)县城的4%弱,其城郭之有无、沿用与修筑情形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然结合爱宕元对331座唐代州县城郭的细致考察,基本可以断定:在隋以至唐前中期,绝大部分州县治所均沿用前代遗留下来的城垣,或者根本没有城郭,只有极少部分州县治所新筑或改筑了城垣。
因此,只是到“安史之乱”后,各地才普遍地兴筑、增修或扩修城垣,特别是很多州府治所城市,普遍修筑了罗城,这就是爱宕元曾充分论证过的“唐末五代州县城郭规模的扩大化”(22)。后世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的唐代城郭,大部分都是晚唐五代兴筑、扩修或重修的。换言之,只是在晚唐五代,大部分州县治所才渐次筑起城郭。
(3)宋元时期,王朝基本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亦普遍不筑城,只在边地城市和部分重要城市,才兴筑或注意维护城垣。
宋初,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淮南、荆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四川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事实上,两宋时代的内地(虽然南北宋间“内地”的含义并不相同)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基本上处于无城状态(23)。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水流域49个州(府)县治所中,北宋中期可以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11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2%稍强;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重修或新修城垣的,只有7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14%;到了元中后期,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有襄州、郢州和均州3座了。换言之,自北宋以迄于元,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现出逐步减少之势。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内地的普遍趋势。
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确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比较重视边地的筑城,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也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筑城(24);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建、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25)。但是,对边地州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熙宁十年(1077年),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说:“看详天下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郭处。”则即便是沿边的河北东、西路及河东、秦凤、永兴军等五路也只有州、军城得到定期修护,五路县城及其它地区的州、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有的州县治所并“无城郭”(26)。
一般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别是在蒙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襄汉、荆湖、两淮地区,平毁了大量的城郭(27)。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28)。因此,虽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但总的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基本上可视作“毁城”时代。
(4)明清时期,王朝比较提倡筑城,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存在很大的阶段性与区域性差别;实际上,大部分州县治所城市只是到明中叶以后,才普遍修筑起城郭;清代主要是维修明代旧城,只是在清后期兴筑了少数新城。
一般说来,明清两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策,州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修筑、维护城垣濠池,如有疏失,要被追究责任(29)。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因时因地各有不同。概言之,明代有两个筑城高潮期:一是明初洪武、永乐朝(1368-1424年),不仅在山东、南直隶、两浙、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部分内地修筑了大量的卫所城市(30),而且大部分府、州(包括散州)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了城郭(31);二是明中后期,特别是景泰至万历初(1450-1573年)的100余年间,不仅重修了大多数府州城郭(主要是甃以砖、石),而且兴筑、改筑了多数县城,到明后期,估计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均筑有城垣(32)。显然,明代府州县治所筑城之先后与其军事、行政地位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
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大部分府(州)县城郭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故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各地均普遍修葺了残毁倾圯的旧城郭。清朝前期的修城主要是在明代旧城基础上培土、甃砖、加高以及修理楼堞,特别注意城门、城楼的维修,但较少有新的创制,也很少兴筑新城。直到嘉庆以后,为因应社会动乱加剧而引发的治安、防守问题以及火器使用越来越普遍对于城池攻守所带来的影响,才又兴起了一场修治城郭的高潮:主要是加固城垣,增高马面,添设炮台,疏浚濠池等;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一直没有城郭的一些山区县治也兴筑了城垣。因此,到清朝末年,绝大部分府(州)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而且得到不同程度的维护。各地今存城郭残迹,大多即为清代城郭的遗存。
综上可知: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既历有变化,其政策在各地的实施又往往因时因地乃至因人(地方官)而各有不同,故州县治所城垣之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所谓“城墙内的城市”。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有超过一半的州(郡)县治所筑有城郭、而且这些城郭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是得到经常性维修的,方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筑城时代”。然则,概括地说,两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06年-公元589年)、中晚唐五代(755年-960年)、明中期至清末(1450年-1911年)这三个时段或可得称为“筑城时代”;其余的隋唐前中期(589年-755年)、宋元至明前期(960年-1450年),则基本可以断言,其筑有城郭的州(郡)县城在全部州县治所城市中不会超过50%,或可称之为“非筑城时代”。虽然“筑城时代”占据了1500余年,而“非筑城时代”只有600多年,但这已足以说明: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特征,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它既不能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段,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治所城市。
三、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将中国古代城市概括为“城墙内的城市”的观点,不仅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大部分时段里、大多数城市都有城垣所环绕,而且认为几乎全部的城市人口都集中在城里,绝大部分城区都包括在城墙围绕的范围内;只是到了晚唐特别是南宋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城市管理也开始放松,许多城市才在城门口形成附郭的街区;而“出于对附郭安全的关心,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构筑了新的城墙”,从而又把附郭街区围进城里(33)。换言之,“城墙内的城市”,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城市人口、街区都应当包括在城墙之内,城外附郭部分即使形成居住和商业街区,也较晚,且规模不大,不影响对中国古代城市特征的概括。
我们认为,这一认识同样至少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
早在汉代,就有不少城市在城下形成了居住街区。东汉时洛阳城上西门与津城门外都有居民,很可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街区(34)。《续汉书·五行志二·灾火》记光武帝建武中,“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杀人。”显然,城外的街区当与城内紧密相连,否则大火无以延烧。汉宜城县治在今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之“金城”内;先秦时楚国所筑之大城至汉时已废弃,然大城内仍有居民住宅,且形成街区,然则,大城遗址中的居住街区实际上就处于汉宜城县城(金城)之外,也是城外的街区(35)。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遍布城壁坞堡,著籍户口多居于城壁之内,但也有不少城市的城下存在居民、商业区。南朝萧梁天监初(502年),曹景宗为郢州刺史,“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36)郢州城下的街区,在长堤以东、夏口(夏水入江之口)以北,显然靠近码头,属河街性质。南北朝后期所筑城郭多属戍城,规模很小,城内除官署外,大抵就是以军兵及其家属为主体的所谓“城民”(37),普通民众大多居于城外,形成附郭居住。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地方长吏才会考虑附郭居民的安全而另立土垣以为保护。如北周丰州(唐均州)刺史令狐整在移治延岑城、营筑新州城时,曾因“丰州旧治,不居人民”而广事抚纳,并在治城外另立罗城,作为民、吏之居所(38);西魏末年营建安州时,曾“迁江夏民二千余户以实安州”,其中也当有部分民户居于州城之外(39)。
唐前中期,在许多沿用旧城垣的州县治所城市里,也有部分居民附郭居住。如江南东道的睦州城濒临新安江,“江皋硗确,崎岖不平,展拓无地,置州筑城,东西南北,纵横才百余步。城内惟有仓库、刺史宅、曹司官宇,自司马以下及百姓,并沿江居住,城内更无营立之所。”(40)睦州城的主要居住街区,显然是在城外沿江地带。这些附郭的城下街区,大抵皆存在规模不等的商业活动。早在唐前中期,襄州城外东北面、汉水岸边的大堤上即酒楼林立、车马驰突、伎乐繁盛,显然是以码头、渡口为中心形成的市场(41);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亦在城外无疑(42)。以情理论,在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南方城市,竹木、米粮之类大宗商品的贸易地点当以码头、渡口为便,而不太可能位于城中,更不太可能居于封闭的市坊里。晚唐五代文献中所见许多南方城市在城外码头、桥渡的“鱼市”、“桥市”,虽然见于文献记载的时间较晚,但其渊源当甚早,很可能早在唐前期即已存在(43)。在一些北方城市的城门外,特别是交通要道所经的城门外,也很可能形成市场。《通典》卷7《食货七·天下盛衰户口》记开元中之太平景象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44)这些店肆虽然“夹路”而列,但必以城门外的通途两旁最为集中,从而形成店肆密集的附郭商业区。“因为城门沟通城市与腹地扇形区域间来来往往的全部交通,所以紧靠城门外的地区是为乡村居民服务的集市和商业最有利的地方。客栈和迎合客商需要的其它服务设施设置在通远距离商路的几座特定的城门之外。”(45)
附郭街区的发展,至晚唐五代以至于宋元,更趋于普遍。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在《乞罢宿州修城状》中说:“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46)照苏轼所说,则象宿州这样居民多在城外的治所城市相当普遍,而且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关于此点,论者已多(47),兹不再赘。
在基本上可称为“筑城时代”的明清时期,附郭街区的发展也相当普遍。在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12座治所城市中,均存在着规模不等的城外街区,其中在明后期至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汉阳府城、沔阳州城、随州城、京山县城、天门(景陵)县城的城外街区在面积与人口方面,基本上可以肯定比其城内还要大一些、多一些;安陆府城城外街区的规模大致接近城内,在清后期可能也超过城内;而德安府城、荆门州城及潜江、汉川、应城、云梦等4个县城的城外街区则比较小(48)。鄂西北山区郧阳府属的7座治所城市,至迟到明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也都已形成了城外街区(49)。显然,无论其规模如何,大部分治所城市都存在着附郭街区。
对于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一般均将其归因于城市居民数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但是,“在许多(如果不说大多数的话)出入最频繁的城门外的附郭,早在城内空间全部变成建成区之前就发展了起来”(50)。实际上,城外街区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而引发的对城垣的突破,毋宁说是一种原始的趋向:城外街区较之于城内,更便于体现城市的另一方面(也是必要的方面)功能:生产(手工业生产)与交流(包括物资、人力乃至文化交流)功能,具备实现这些功能更有利的条件。正因为此,即使城内还有大片的空地,人们依然还是会选择城外建立自己的商铺、作坊及住宅,只是在动乱开始时,才会被迫搬进城内,或避往乡下(又以后者为主)。《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尝释“草市”云:“时天下兵争,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价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伤财以害其生也。”(51)胡三省释“草市”为“草屋所聚而成之市里”,未必确当,然其谓城外(城郭下)之居住成本低廉,当是事实。因此,我们认为,附郭街区及其商业活动的发展,也很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倾向”,因为它比较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居住成本也较为低廉(相对于城内而言)。
这里涉及城内与城外街区的功能分野。《说文》云:“城,以盛民也。”这一解释在诸多地方志所见的“筑城记”中多次被重复。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了一定规模城外街区的城市来说,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盛官”——诸色官署公廨、营房及官员、士绅(官员侯选人)、衙吏住宅与园囿占据了城内最优越、最重要的位置,并构成城内街区的主体。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城内并不是最佳的居住选择,因为它所提供的谋生机会较少,而生活费用(以住宅支出为主体)又较高。城外则不然,相对低廉的地价、便利的交通、较低的捐税以及与乡村的广泛联系,都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机会。因此,如果存在选择可能的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最佳选择显然是在城外。这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内与城外的功能分野:城内主要是行政、文教与士绅住宅区,而城外则是商业、手工业与普通民众聚居区。当然,这种分野仅是就宏观方面而言的,它既时常被频繁发生的社会动乱所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战乱发生时,普通民众大量涌入城内,而部分士绅则避到乡下),又以较为发展的城外街区为前提;而且即便在平常状态下,城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服务于官吏士绅的各种店铺及店铺主与贫民的住宅。由此,我们注意到城内零售店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内的官吏、士绅及其它诸色人等,而城外零售店铺则面向乡村,批发商业则主要面向远距离贸易。这种服务对象的不同揭示了城内商业与城外商业的不同功用:前者是城市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主要是乡村生活与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城外附郭街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确有一些重要城市,主要“出于对附郭安全的关心”,构筑了新城墙,从而将原先的附郭街区包括在城墙之内。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普遍。晚唐五代州府治所城市普遍修筑或扩修罗城,的确将大部分原来的附郭街区围进了罗城,但罗城的修筑主要集中在州、府治所城市,而且不少城市很快又在罗城之外形成了新的附郭街区(52)。明清时期扩建城郭以包括附郭街区的例证,在章生道所列的20个主要首府城市中,也只有北京、广州、兰州、济南4例;所举的另两个例证大同府城与汾州府城则都是北方城市(53)。在我们研究的汉水流域59座明清州(府)县治所城市中,虽然均普遍存在附郭街区,但并无一例曾增筑城墙以包围附郭街区。
据上所论,我们认为:在州县治所城市筑有城墙的情况下,城下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乃是一种“原始的趋向”,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事实上,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甚至数倍于城内。因此,即使在所谓“筑城时代”,城墙也未能完全限制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街区的扩展,“城墙内的城市”不能涵盖大部分城市的形态与功能特征。
注释:
①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第8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5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1。
③参阅前揭章生道、陈正祥文,以及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分别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7-83、112-175页);Sen-Dou Chang."Some Aspects of the Urba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Hsien Capital",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51,No.1,Mar.,1961,pp.23 -45; Sen-Dou Chang."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53,No.2,Jun.,1963,pp.109-143; Sen-Dou Chang."Some Observation on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Walled Citie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60,No.1,Mar.,1970,pp.63-91);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51-8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④参阅范德(Edward L.Farmer):《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第1-1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⑤当然,这种忽视是相对的。事实上,西人文献中有关市场、居民区(包括城外街区)的记载较之中国文献中的记载要丰富得多。如伯来拉关于梧州的报道中,就曾谈到城内的贵族住宅区、市集、街头流动的小贩以及居住在郊区的商人,并解释说:因为每晚都要关闭城门,商人为更好照顾他们的生意,宁愿住在郊区(C·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第27-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⑥斯波义信:《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胡德芬译,见唐晓峰、黄义军编:《历史地理学读本》,第413-432页,引文见第4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⑦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见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第145-183页,引文见第1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⑧参阅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演变》,黄金山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第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第3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第28-9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⑨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下册,第212-21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531、566-567、572、558、543、457、572、543、539、549、559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叶植主编:《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第2、183-184、74-76、319-320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第258-27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⑩也有不少县邑治所可能未筑城垣,如东莱郡不夜县(在今山东荣成县)、犍为郡汉阳县(在今贵州赫章县)即基本可断定没有城垣。见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荣成梁南庄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2期,第1077页;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赫章可乐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199-242页。
(11)《晋书》卷100《苏峻传》,第26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刘淑芬:《魏晋北朝的筑城运动》,见《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353-407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14)Sen-Dou Chang."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53,No.2,Jun.,1963,pp.109-143,esp.Fig.12 and Fig.14,pp.124-127.
(15)《隋书》卷22《五行上》,“旱”,大业十三年下记事,第6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16)《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第116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17)《唐大诏令集》卷107,第5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8)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8,第632-6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19)爱宕元:《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规模化——华中、华南の场合》,附《唐代州县城郭一览》,见《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第451-488页,日本京都,同朋舍,1997。
(20)如项城、南顿、内乡三县城,爱宕元注为先秦楚国所筑;襄城县城,注为楚灵王所筑,即未必可信。
(21)如江州城,爱宕元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定为汉初所筑,亦不可信靠。
(22)爱宕元:《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规模化——华中、华南の场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第415-488页。
(23)成一农细致地讨论了宋代的毁城与不修城政策(《宋、元以及明代前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第一部分,“宋代毁城和不修城的政策”,第146-160页),其结论大致可以信从,故本文不再赘论。需要略作补充的是:成一农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全国的总体情形,其出发点是有宋一代存在一个基本适用于全国的不提倡或不鼓励筑城的倾向或政策,认为“在两宋时期,无论面对何等艰巨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两宋政府都一再坚持不修城的政策。”这在表达上多少有些“绝对”。事实上,成一农也论述了很多地区筑城的事例,从而与上述“绝对”的结论不甚相符。我们认为,合理的分析途径是区分宋王朝的“内地政策”与“边地政策”: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在边地提倡甚至要求筑城。
(24)《宋史》卷5《太宗纪二》载:雍熙四年(987年)二月丁酉,“缮治河北诸州、军城隍。”(第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朝,亦多次诏令河北、陕西诸路州军修浚城隍,详见《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一”至“方域八之六”,第7441-74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庚子,“朝廷惩岭表无备,命完城。”(第41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关于广南东西、福建、湖南诸路的筑城情形,请参阅斯波义信:《宋代的城市城郭》,见《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第291-32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附表一,宋代地方城市修城统计表”,第180-182页。
(26)《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五”,第7443页。
(27)《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九月丁未,“命有司隳沿淮城垒”;十一月庚申,“隳襄汉、荆湖诸城”;十四年二月壬午,“隳吉、抚二州城,隆兴滨西江,姑存之。”同书卷10《世祖纪六》:至正十五年三月丁酉,“命塔海毁夔府城壁”;八月甲戌,“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第185、186、188、199、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参阅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第二部分,“元代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第160-173页。
(28)《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59《工部二·造作》“修城子无体例”条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月,江州路申称,“目今草寇生发,合无于江淮一带城池,西至峡州,东至(杨)[扬]州,二十二处,聊复修理,斟酌缓急,差调军马守御,似为官民两便。”江西行省将此咨目移告上都枢密院,枢密院与中书省一同上奏世祖,得圣旨谓:“待修城子里,无体例。”(第214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据此,则元世祖以“无体例”为由拒绝了地方官修复城壁的请求。在今见史料看,元朝主要是禁止中原汉地和南宋旧地(所谓“南人”区域)修复城壁,毁城政策也是在这些地区实行得较为彻底。考另详。
(29)《明会典》卷187《工部七·营造五·城垣》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若在外藩镇府州城隍,但有损坏,系干紧要去处者,随即度量彼处军民工料多少,入奏修理;如系腹里去处,于农隙之时兴工。”(第9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关于清代州县官员在修护城垣方面的职责,请参阅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第261-26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0)参阅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第三部分,“明代前中期城墙政策的演变”,第173-180页。
(31)以湖广行省为例:明代湖广布政使司所属15府、2直隶州,除成化中方设置的郧阳府外,洪武中全部兴筑或重修了府(州)城;14个散州中,有12个为洪武中筑城,1个(均州)永乐中筑,1个(兴国州)正德中筑。而在91个县(不包括府州附郭县)中,只有11个在洪武、永乐时修筑了城垣。此外,大部分卫所也均在这一时期修筑了城垣。因此,洪武、永乐朝的筑城主要集中于府州(包括散州)治所、卫所及部分军事政治地位较重要的县治。据万历《湖广总志》卷14《建置志·城郭》部分统计(《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94册,第529-54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
(32)仍以湖广行省为例:到万历初年,在91个县中,没有城郭的县治只剩下13个。如果加上17个府(州)与14散州城,则筑有城郭的府、州、县城占全部治所城市的89%。换言之,只剩下约十分之一的治所未筑城垣。
(33)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8页;陈正祥:《中国的城》,见《中国文化地理》,第74页;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81-84页。
(34)参阅Hans Bielenstein(毕汉斯),"Lo-Yang in Late Han Times",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48(1976),pp.5-142.毕汉斯认为这些居民区都位于洛阳城外的“郭”内,并推测洛阳郭的面积比城内面积还要大。张歆海赞同毕汉斯的推断,认为“‘郭’可能是当地居民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指城墙外不太远的环城地带,而以某些自然景观如河流、湖沼或山丘等作为郭的外侧标志”,并进一步推论,“‘郭’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城墙的局限与城内人口增长不能协调的产物……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张歆海:《汉代城市社会》,第47-52页)这里涉及对“郭”之形态、性质的认识问题,不能具论,但认为汉代许多城市的城外,已形成了规模不等的街区,应无疑问。
(35)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28《沔水中》“夷水”条,第2396-239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另请参阅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第265-26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36)《梁书》卷9《曹景宗传》,第1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37)关于北魏中后期的“城人”(“城民”)及其城居情形,请参阅唐长孺:《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见《山居存稿》,第96-1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谷川道雄:《北魏末的内乱与城民》,见《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第132-1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8)《周书》卷36《令狐整传》,第6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1。
(39)《周书》卷25《李贤传》,第416页。
(40)沈成福:《议移睦州治所疏略》,见《全唐文》卷200,第20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41)参阅严耕望:《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第1039-10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177-18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42)《太平广记》卷374“八阵图”(第29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条所记。
(43)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列举了南方城市外鱼市、桥市以及夜市的情形,把这些市场的出现作为唐中叶以后地方城市中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逐步突破“市”的约束的表现之一(第284-285页)。有关鱼市、桥市的文献记载确实均出自中晚唐及五代,但这很可能是由于唐前中期文献记载较为缺失的缘故。
(44)《通典》卷7,《食货七》“天下盛衰户口”,第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45)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8页。
(46)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见《苏轼全集》,中册,《文集》卷35,第1317页,上海,上道古籍出版社,2000。
(47)参阅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239-277、310-336页,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第152-157页;程郁:《宋代城郊发展的原因与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29-36页;杨果:《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第80-84页。
(48)鲁西奇:《城墙内外: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州、县城的形态与结构》,见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第228-29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9)鲁西奇:《山城及其河街:明清时期郧阳府、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见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第538-5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0)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8页。
(51)《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二》天福二年六月甲午,胡三省注,第9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52)如常州在杨吴时曾两次展拓,入宋以后,仍继续突破罗城城垣的限制,在朝京、通吴门外夹运河形成新的市街和民坊区。参阅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见《环境变迁研究》第4辑,第156-179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
(53)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