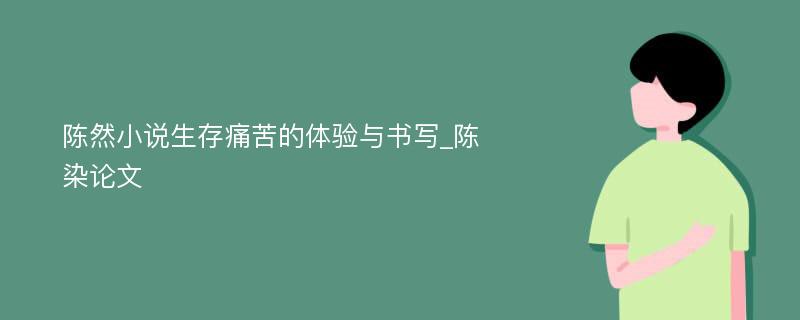
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陈染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痛论文,小说论文,陈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早已惯于在生活之外,倾听
我总是听到你,听到你,
从我沉实静寂的骨中闪过。
一个斜穿心脏的声音消逝了,
在双重的哭泣的门里。
只有悒郁的阳光独步,于
平台花园之上
和死者交谈。
——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染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言说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她所呈现的与九十年代的总体文化语境大相径庭的一部部小说文本之中,而且更直接的从她卓尔不群的小说写作姿态上标示出来。陈染对于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写作天然而然地带上了某种极端的意味,并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文化潮头所无法回避的一种尖锐存在。而对我来说,陈染在九十年代的无限风光则无疑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当代新潮文学的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判断。我不同意评论界不绝于耳的那种关于新潮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就早已死亡和终结的断语,而是认为新潮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正进入一个新复兴发展阶段。
与时下商业大潮中的各种欲望化的狂欢景观不同,陈染的小说呈示的却是一幕幕带有终极意味的人类悲剧性生存景象。她把自己孤立于欢乐的人群之外,以一种思想者的姿态体验和言说着掩盖于生存表象背后的那种生存之痛。我不知道,当代还有没有哪位作家会如陈染这样专注于对生存痛苦的发掘和书写,但我敢肯定,在“生存之痛”的表现上陈染无疑是把文本主题融入生命体验的最真诚最绝对的一个。陈染是透明的,她勇敢地暴露和敞开了她所体验和感觉的全部生命之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努力做到的就是“让那些应该属于我的一个三十岁女人的血血肉肉真实起来,把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等一切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陈染又是隐晦的,她在我们当下的世俗文化谱系之外又重建了一套超世俗的具有形而上彩色的精神文化谱系,她对存在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又让我们重温了那种在我们时代已久违了的对于“生存”问题的哲学和神性关怀,显而易见,她的这种声音和话语方式与流行的大众话语系统是格格不入、无法共鸣的。作为一个独语者和孤独者,陈染对于自我的极端坚守总给人一种无以释怀的沉痛,而同时她以瘦弱的女性之躯去独自面对和承担那巨大的生存之痛的生命勇气又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她的微弱的、私语性的声音也许没有洪钟大吕那般震聋发聩,但却也绝不是可以充耳不闻、忽略不计的。我惊讶于年轻的陈染对于“生存”这个过于沉重的大话题的执着,更钦佩作为女性的陈染书写“生存”时的那种真正哲学化的思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陈染应是我们当下的一把难得的精神标尺,她对于“生存之痛”的出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从混浊、黑暗的生存之地突围而出并迸入敞开和澄明境界的崭新可能。而一旦进入陈染小说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所谓“生存之痛”在她这里也不是纯粹形而上和哲学化的,它有着立体的多重的丰富层面和表现形态,我们可从下述几个层次进行具体的考察。
其一,孤独之痛。
读陈染的小说,我们首先遭遇的就是在她的文本世界里绵延不绝的那个庞大的孤独者家族。无论是耆耆老者,还是妙龄少女,无论是在偏僻的小镇,还是在繁华的闹市,“孤独”都是主人公们在不同时空中的共同体验。而对陈染来说,“孤独”显然正是作家用以探寻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一个特殊的艺术视角。某种意义上,对于“孤独”的反复言说也正是她所有小说的一个贯穿主题。青年评论家汪政和晓华就曾准确地用“习惯孤独”来概括陈染小说的精神线索,并把“孤独”命名为陈染小说的第一“主题词”。而从陈染的创作自叙中我们还发现,“孤独”也并不仅是指她小说的文本状态而且也正是她当下的写作和人生方式的直接体现。陈染是一个对孤独十分敏感并常常耽于孤独的特殊个体,她自称:“按照常情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孤独而闭塞的人了”“我极少外出,深居而简出。到别人家里去作客,常常使我慌乱不堪,无所适从……平日我在自己家中,在自己的房间里胡思乱想,清理太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也是习惯拴上自己的房门,任何一种哪怕是柔和温情的闯入(闯入房间或闯入心灵),都会使我产生紧张感。”在这种情况下,陈染和她笔下的孤独者就具有了特定的亲和性、同构性与互文性。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陈染与文本世界中的那些陈染的创造物在“孤独”的语境中就具有了互为阐释的生命关系。正因为此,“孤独”这个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印痕的哲学“话语”呈现在陈染的文学本文中就有了中国此前的各种“现代主义”文本所未曾有过的那种体验性与生命意味。
在陈染的小说中,“孤独”首先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弥漫性的生存氛围。主人公们活动其中的文本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孤独者的世界,隔绝的空气阻碍着人们自由的呼吸。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主人公们都时时刻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不仅生存个体彼此之间无法沟通、无法交流,而且甚至还彼此提防、窥视、诅咒着。我觉得在陈染的全部小说中都一直存在着一个贯穿性的抒情主体。从她早期的《归,来路》、《小镇的一段传说》、《塔巴老人》,到近年来的《空的窗》、《时光与牢笼》、《站在无人的窗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潜性逸事》、《无处告别》、《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等小说,主人公以自我倾诉的方式呈现也好,命名为“罗莉”、“水水”、“雨子”、“寂旖”、“黛二”也好,尽管他们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少女,有着不同的语符代码,但“孤独”无疑是他们共同的生存体验和生命表征。一方面,孤独是现实的生存世界对个体生命施加压迫的产物。个体与社会和他人的对抗乃至敌视某种程度上正是孤独感的深刻源头。主人公们的许多怪癖和生存恐惧事实上只有在一个适宜“孤独”滋生和繁殖的特定氛围中才会萌生。这方面,《无处告别》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本。黛二与朋友、与现代文明、与母亲、与世界的那种紧张关系既带来了她生存的那种巨大的“压力感”,同时又直接用一次次的背叛、失望、阴谋、受骗、堕落等等的生存挫折创造了黛二的“无处告别”的沉重孤独,而《小镇的传说》是更是一个寓言性的文本,罗古河北岸的神秘传说和小镇人心照不宣的现实文化状态天衣无缝地交织成了一张覆盖主人公精神生命的灰暗大网,罗莉陷入其中左冲右突并在极度的孤独中走向疯狂成为小镇历史“传说”的新一面可以说正是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在“小镇”这样一种封闭性的生存“版图”中主人公走向遮蔽、走向自我封闭、走向孤独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结局。陈染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尼姑庵”、“破庙”、“破损的家庭”、“空洞之宅”、“牢笼”等等意象其实也正如“小镇”一样只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孤独氛围来理解才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主人公的“孤独”又强化了生存世界的非本真性和黑暗性。无论是《小镇的传说》对于罗莉孤独和死亡的描写,还是《塔巴老人》、《站在无人的风口》对尼姑庵中塔巴老人和老女人孤独生命的极端表现,亦或《空的窗》对盲女和老人两重孤独世界的探寻,都为我们揭示了“世界”对于人的荒诞和可怖的一面,并进而使主人公们的孤独体验获得了一种支撑性的广阔世俗“背景”。这方面,《麦穗女和守寡人》就相当典型,守寡人在深夜出行时对于“钉子”、“门”、“陷阱”等恐怖性场景的幻觉化想象就把世界对于人的压迫、威胁和扭曲以及在这种压迫中人的巨大精神恐惧进行了充分的渲染。置身于小说的情境中,我们就会在一种总体的悲剧性氛围中获得对于“存在”的新的理解。
其次,孤独在陈染的小说中还是一种生存态度,一种主动的对于世界、对于他人的对峙态度。世俗世界的灰暗固然制造和繁衍着孤独,但对于生存个体来说孤独也并不就是一种“负生存”,孤独是一种孤立,同时也是一种逃离,是远离遮蔽走向澄明之所的心灵突围。孤独是一种关系的丧失,但也是一种自由的获得。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阅读陈染的小说,主人公们对于孤独的珍爱和偏嗜总会让我们怦然心动。《归,来路》中“我”喜欢孤独,怕开会,想辞职,“关上门独自一个脱得一丝不挂”并沉迷于幻想和回忆是“我”的独特爱好;《小镇的传说》中罗莉正是借助于离群索居开“记忆收藏店”的孤独一度变得生机勃勃、青春焕发;《空的窗》则通过退休老教师对于“孤独”的恐惧绝望和盲女对于“孤独”的升华的对比让读者目睹了现代人两种不同的“孤独”心态。在作者眼中盲女的孤独其实正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境界,她对于世界的远离和无视给了她阐释这个世界的充分而绝对的自由。……我们看到,陈染一方面对于现代人的孤独之痛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书写并很大程度上把它与人的生存困境联系在了一起,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愿现代人在这种生存痛苦中被轻易压垮,因而她的主人公面对“孤独”时往往在体味痛苦之际也同时获得了生存的勇气。此情此景中的“孤独”也就不仅给人以悲剧感而且更充满了一种生存的悲壮了。
其二,家园之痛。
如果说孤独之痛在陈染小说中是一种弥漫性的存在的话,那么家园之痛则又是和孤独相随相依的一种更本质的生存痛楚。当然,所谓“家园”在陈染的小说中也是有双重所指的。一方面,它对应于主人公当下的现实家园,另一方面,它又更指向人类的精神家园。走进陈染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她所营构和表现的“现实之家”几乎全部都是残缺和破损的,“家”的丧失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主人公们生存悲剧性的直接注解和显在表征。一群无“家”的个体在寂寞如沙漠的世界上徒劳挣扎着,孤独、苦闷、徘徊、变态乃至仇恨和死亡交织成了一曲人生的悲剧旋律,陈染的小说也由此覆盖上了一层灰暗、清冷的色调。而具体考察陈染的小说,我发现她对“家园”失落之痛的表现又是沿着两个特定的层面来展开的,一是父母之家的丧失。陈染的大部分小说都是表现父母离异或父母远离人世的“孤儿”的生存感受。作为一些“无父”的个体,“家”对于他人的保护和温暖随着父亲的远离而成了一种不着边际的梦想。他们面对社会和世界时再也没有了依靠和退路,“家”和世界一样成了一种共同的压迫他们生存和心灵的灰暗之所。正因为如此,对“现实之家”的逃离、恐惧乃至仇恨就成了主人公们经年累月的一种最日常的情绪与心态。《小镇的传说》、《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等小说把“父母之家”解体的破败景象以及这种“家庭”碎片对于主人公现实生存的巨大压力描绘得淋漓尽致。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这部小说中陈染甚至隐喻地昭示我们:主人公“秃头女”被父亲打出家门的不幸其实正是她的大幸,相比于父母之家而言“尼姑庵”其实才更具有“家园”的性质”。一扇家门的关闭,正是另一扇家门开启的前提。没有父亲的将她逐出家门,也就没有“尼姑庵”向她的敞开。一是“自我”之家的破碎。陈染的小说世界内总是行走着一对对同床异梦的爱人、情人和友人。她的主人公不是寡妇、离婚者(或即将离婚者),就是妓女、同性恋、变态者。他们或者本就无家可言,或者是家的破坏者,现实之家在他们的冲撞、挤兑和拆解之下几乎无一能免分崩离析的可悲结局。在这里陈染表现了她对于爱情、友谊、亲情等的悲观和怀疑态度,并根本上否定了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如果说在《时光与牢笼》中水水与丈夫的爱情之家虽已经摇摇欲坠但却仍还维持着一种世俗的形态的话,那么,在《潜性逸事》中我们则和主人公雨子一道在现实之家灰飞烟灭的缕缕尘埃中目睹了爱情和友谊的双重覆灭。雨子对于丈夫的粗俗日益不能忍受因而萌生了离婚的想法,并告诉了自己心灵的“知音”李眉。然而,实际上李眉却是她“心灵相通的敌人”,正是超凡脱俗的李眉最终要嫁给雨子的丈夫。生存荒诞和生命的尴尬就是这样轰毁了人类的爱情之家。同样的家园破灭景象在《饥饿的口袋》中也清晰可见,剧作家麦弋女士因为离婚而把她的现实之家改造成了一座“空洞之宅”。女友的同住和男女的短暂回归不但未能给她丝毫“家”的回忆,相反却从他们的双重背叛中再次体味了“家园”人去楼空的凄凉与辛酸。
而与“现实家园”的失落相对应,对“精神家园”流逝的悲悼也是陈染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层面。对于现代人来说,“无家可归”的生存焦虑既根源于现实之家的破败,同时又更来源于内心和精神上的无助与无奈。而根本上说,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绝望心绪的突出表征就是精神之家的无处着落和无从寻觅。陈染的小说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主人公们精神之爱流逝后的幻灭、痛楚、绝望、焦灼等等心态的解剖、呈示出逼进了横亘在人类面前的这道永恒的生存难题。活跃在陈染小说中的生命都是那些精神之家的弃儿和放逐者。他们以自己决绝甚至变态的方式对抗着世界对抗着他人也对抗着自我。《归,来路》中的“我”一方面固然因现实之家的丧失而有着在姐姐家做寄寓者的现实痛苦,另一方面更有着对于精神家园的焦虑和困惑。她对天才孤独的偏爱、对于回忆及怪想的执迷、对于世俗生活的厌倦都是寻找精神家园之旅受阻后茫然失落心态的一种典型表征。《空的窗》中失去老伴的退休教师和失去光明与恋人的“我”都处在一种对“精神之家”的寻找与祈求之中。老教师对于送死信的虔诚一方面是他抵抗孤独和绝望的精神良药,另一方面也是他试图在现实之家的废墟上重建精神之家的生存梦想的一种实现。而盲人少女“我”在失去光明远离现世沉入彻底的黑暗之后却反而获得了生命的澄明与敞亮,在她没有失明之前所无法找寻的“生命与光亮”在她成为盲人之后一下子就照彻了她的心灵,以致她每天清晨都能矗立窗前眺望“太阳的升起”;《塔巴老人》中的塔巴和黑丫虽然是两代无家的孤独者,但在“尼姑庵”内他们的交流与相通又何尝没有为她们构筑起暂时的“精神之家”呢?在此意义上我们似乎能对陈染小说主人公的“尼姑庵情结”和向往“幽僻之所”的怪癖获得一种精神理解。一方面,对于尼姑庵以及各种“幽僻之所”的崇拜和呵护是他们悲剧性地失去现实之家后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另一方面,这种举措又是他们试图超越世俗生存重建精神家园的主动而决绝的生命姿态的一种生动写照。而毫无疑问,陈染对这样一种精神努力是充满感动和敬意的。
其三,失语之痛。
然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孤独之痛还是家园之痛,其本质仍是一种语言之痛。对于世界、对于“他者”的无法言说和失语实际上才是现代人生存痛楚和生存困境的最本质的表现形态。而陈染的小说对于人类失语之痛的表现可以说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她小说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些独语者和准独语者,他们对于世界和他人无从进入也无法对话,无一例外的都只有面对内心和自我一途,仅凭梦想、幻觉般的自言自语在生存的泥淖中沉沦、挣扎。“无人倾诉”的失语之痛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主人公们共同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而某种意义上,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孤独之痛也正是这种失语之痛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失语之痛孕育并催生孤独之痛,孤独之痛反过来又更强化和加剧了失语之痛,两者共同把主人公们带入了生存之夜的黑暗和混沌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陈染小说对于失语之痛的表现同样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层次。一方面,失语首先表现为世俗层面“对话”的艰难。在陈染的小说世界中每个生命个体相对于“他者”来说无疑都是孤独而封闭的,沟通和对话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实际也是不可能和被否定的。在陈染所营构的世界里不仅父母和儿女之间存在深深的敌意无从对话,而且夫妻、情人和密友之间也都无不是些在本质上并没有共同语言的陌路人。陈染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些倾诉者,但他们倾诉的对象都只能是他们。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一个能听懂他们倾诉之声的“他人”,这是陈染对于主人公生存悲剧性的一个基本阐释。我个人觉得,在对于失语之痛的书写上陈染最出色和最深刻之处还在于其对人类“伪对话”状态的发现和揭示。这方面的典型文本是几部描写朋友间的亲密友情之虚幻的小说,如《饥饿的口袋》、《麦穗女与守寡人》、《无处告别》等,其中《潜性逸事》最具代表性。在这部小说中雨子是把“不喜欢说话,习惯说半句话”的充满神秘的李眉作为自己的心灵知音的。她自认最能听懂李眉的沉默和“半句话”,也只有李眉才理解她自己的心语。作为亲密的朋友,两人也似乎确实做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雨子要跟丈夫离婚的想法也只告诉了李眉一人。然而,随着小说的向前推进我们却和雨子一道辛酸地发现李眉是如此的陌生和无法理解。而当丈夫向雨子宣布李眉要嫁给他时,两位朋友过去的相互倾诉立即就变得那么的虚幻和不真实起来,所谓的语言和心灵契约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另一方面,“失语”又表现为哲学层面上神性和精神话语的缺失,这种缺失作用于陈染小说文本就是对于“现实”的悬搁与放逐以及对于“过去”和“回忆”的迷恋。阅读陈染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她对“现实话语”的舍弃是一贯而绝对的,她全部小说的话语指向几乎全都是针对“过去”的,“向过去倾诉”我觉得正是她小说的一种最基本的话语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固然使“失语之痛”和“时间之痛”结合在一起深化了作家对于存在之痛的表现,同时也赋予了她文本一种抽象的形而上意味,进而较好地凸现了陈染对于“存在”问题的现代主义态度。而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才是陈染对于“失语”问题思考的核心所在。在《归,来路》中陈染最先表达了拒绝现实话语的焦灼和寻求超现实精神话语的渴望。“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本是人人羡慕的事,但“我”却充满了压抑和孤独感。无论是对于学校里的各式人等还是姐姐和姐夫,“我”都没有共同语言,即使与H 女的同性恋行为也丝毫不能唤起“我”丁点话语欲望,而只想把自己封闭在往事、回忆和怪想里虚构精神上的对话者。一夜不归之后“我”与二千五百岁老者的交谈和对话无疑是精神幻象发挥到极致后的产物。虽说二千五百岁的老者也很难说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神性话语的发出者,他对于“自我”、“人”等等的言说事实上也并未超越现代主义的话语范畴,但对“我”来说一个倾听和对话对象的获得至少在某些精神层面上“我”的生存焦虑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后《小镇的一段传说》、《塔巴老人》、《空的窗》、《站在无人的风口》等小说也都把主人公追示神性话语的心态历程真实地坦露了出来。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对于神性的祈祷首先就表现在对于“时间”的敏感上。小说叙述都向着“过去”飞奔,“现实”是一种缺席的存在,“回忆”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方式和小说方式。《小镇的传说》中罗莉就是凭借对于“记忆收藏店”内神秘往事的发现与沉迷而获得摆脱现实生存困境的精神力量的。遗憾的是她在过去岁月中的风尘仆仆和喁喁私语并未使她真正接近救赎现代人的神性之光,相反却被厚重的与“现实”同谋的“过去”吞没、毁灭了。而《塔巴老人》中的老人和《空的窗》中的盲女则也都是在对于“往事”和时间的执着中接近心灵和精神之中的神明的,老人话语中的神是过去的一段爱情,盲女话语中的神则是现实中永不存在的光明。尽管与虚幻的过往之爱的对话只是把老人孤独地送入了坟墓、对心中光明的眺望也并未把盲女人生存的黑夜中拯救出来,但是在那微弱的神性之声里我们是能感受到主人公精神的巨大震颤的。同样的生存景象中《站在无人的风口》这篇小说中也有很好的表现,老尼姑谜一般的一生其实正是浸泡在一段无法诉说辛酸往事里,作为“一个靠回忆活着的人”,她与两套玫瑰外衣的窃窃私语正是她悲剧人生的形象写照。本质上,她并未能进行一次走向“神”的真正对话,而是在她的“漫无边际的心灵黑夜”里演绎了“世界的悲剧性结构“并”在永久的沙漠里终于被干旱与酷热变得枯萎”了。其次,陈染小说对于神性精神话语的祈求还表现在主人公总是坚守沉默并以写作和文字对存在与虚无本身的发问。陈染笔下的人物通常都是作家、诗人或文字工作者,他们往往能在无人对话的境遇中以文字的方式与自己对话、与存在对话、与虚无对话。陈染热衷于对于冥想、梦境、幻象等等的书写而这正是虚构神性对话者的一种特殊想象方式。《潜性逸事》中雨子就自认“热爱文字是她的性情与思维使然”,并在梦境和预言般的心灵氛围中把自我的生存之痛演绎得尽态极妍。《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黛二的一方面“记录她所看到的行为怪异者与精神混乱者的言行”,一方面也在这种梦游般的写作中与文字本身建立了一种对话关系。《饥饿的口袋》中的剧作家麦弋女士更是把现实的生存和电脑文字对应、混淆为一体,在她与电脑的对话里真实与虚构已经泯灭、生命的荒诞和生存的沉重都只是在幻象里浮沉。而《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则更通过主人公与照片上的情人的幻觉对话,以及现实中与钢琴师的无从对话,把现代人寻求神性对话者的幻灭之痛渲染、刻划得入木三分。陈染昭示我们,现代人既然失去了现实的对话者,那么他也就不可能找到精神上的真正对话者,无法言说的“失语状态”将是现代人的一种宿命。而一旦人的生存与语言脱离了,那么重返语言之途就更是充满了悲剧性。在此意义上,上文所说的陈染小说主人公向往“幽僻之所”的“尼姑庵情结”也同样是与他们的失语之痛互为因果、互为阐释的。
在对陈染小说中的生存之痛做了如上分析之后,我觉得对陈染小说进行一种总体概括似乎是迫在眉捷的。因为,作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风格独特的写作者,陈染的小说形态无疑具有多种形态和多种言说可能性。在陈染的艺术世界里,对于“存在”的追问是她小说的总主题,对存在的遮蔽状态的表现与书写是她的基本艺术视角,对于女性孤独者变态的生存心理和人格形象的塑造是她对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