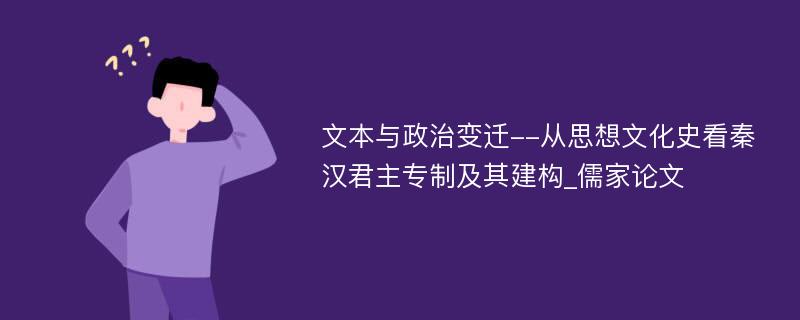
文本与政治变迁——思想文化史视域中的秦汉君主专制及其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君主专制论文,视域论文,文化史论文,秦汉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汉时期的君主专制及其建构问题,既是了解二千年来君主专制体制发育和成形的关键,也是探究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之故,学术界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甚为丰硕。笔者不揣浅陋,通过研究《吕氏春秋》①、《新语》②、《新书》③、《淮南子》④、《春秋繁露》⑤、《盐铁论》⑥、《白虎通义》⑦诸文本与秦汉政治变迁的内在关系,研探这一时期中央集权体制形成的过程、特点及影响。 通过对特定文本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的解析来了解该文本的思想特质,是思想文化史领域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而对特定时期具有某种共性的数个文本的线性解析,则可以展示一个时代的思想兴味。《吕氏春秋》、《淮南子》、《新书》、《新语》、《春秋繁露》、《盐铁论》和《白虎通义》这七个文本都与秦汉意识形态学说史关系密切,而对它们的线性分析,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秦汉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路径及其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以家族为单位、以家族长为核心的各级各类贵族把持着国家大权⑧,无论是与夏王有盟誓关系的部族首领,还是在“复合式国家结构”⑨中臣服于商王的方国首领,抑或是获得分封的西周诸侯,他们在地方上都拥有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权,在与王权长期共存的历史进程中,贵族阶层在政治特权的护佑下形成了适合自身存续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的政治诉求和文化传统与百家争鸣的时代潮流相交并,借此来延续其影响。就儒、道二家而言,其思想视域中无论是关于夏代部族联盟和商代方国联盟的历史记忆,还是对西周封建礼乐制度的美化或批判,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都是他们形成思想主张的历史资源。换言之,儒、道二家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表现和延续。儒家承续西周礼乐传统,他们或以恢复周天子权威为宗旨,或试图以“仁义”规范新兴势力,目的都在于重新确立上下有序的封建秩序,从而使贵族阶层重新获得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准确定位;道家则预感到集权统治不可避免及贵族势力崩溃的历史必然,他们或提倡“无为”之治,或力行避世哲学,形成独特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 战国末年,享有世卿世禄之特权的旧贵族势力逐步被瓦解,军功贵族为代表的新兴贵族势力迅速成长,吕不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吕不韦得势时,曾领有众多食邑,起初,他“食蓝田十二县”⑩,后又“食河南洛阳十万户”(11),燕、赵二国发生冲突,燕国为拉拢秦国,送河间十城为吕不韦封邑。吕不韦不仅封邑广大,且“家僮万人”(12),俨然堪比西周时期的诸侯王。实际上,七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和吕不韦类似的新兴贵族为数众多,即使在秦国,王翦、李斯等人的势力也可与吕不韦比肩,不仅如此,嬴氏统治集团拥有悠久的封建渊源,其所创立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兼有辨贵贱和褒功勋的功能,且在“爵重于官”这一点上显示了封建贵族身份制的传统影响(13),而二十等军功爵制则为新兴贵族势力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 吕不韦为代表的新兴贵族势力一方面借助君权来扩充、巩固权势,另一方面深怕专制君权随时抑制、瓦解其合法性,进而对法家思想主导下的中央集权产生抗拒心理,并试图定义他们理想中的中央集权体制。庄襄王在位时,吕不韦为秦国相邦,嬴政继位后,被尊为“仲父”,权倾朝野,这都为他提供了定义、限制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而《吕氏春秋》则是他实施这一理念的一个文本表征。 《吕氏春秋·不二》云:“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主张“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因此,尽管认为“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责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但其思想主旨绝非是诸子观念的简单叠加和拼凑,而是通过尽可能详尽地集合、重构诸子思想文献,整合出一套自成体系的治国方案。 《吕氏春秋》力倡儒家民本思想,主张“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14),认为统治者须先得民心而得天下,“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心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15)。要得天下,统治者须先“修身”,因此主张“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16)。同时也须礼贤下士,认为“贤者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17)。《吕氏春秋》力倡孝道,认为“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重视移孝作忠的社会管理与控制功能,主张“知之盛者莫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18)。当然,这一文本中也渗入儒家的仁爱理念,《吕氏春秋·精通》云:“德也者,万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形德乎己,而四方咸饬乎仁。”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的批判思想也为《吕氏春秋》所吸纳,主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19)。《吕氏春秋·恃君》亦云“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这种被郭沫若称为“具有一种钢铁的声音”(20)的批判理念,显然与子思“恒尔(称)其君之亚(恶),可胃(谓)忠臣矣”(21)的思想如出一辙。《吕氏春秋》对道家思想的承续方面主要是吸纳了道家的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分职》云“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该文本主张“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22)。如果“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23),其结果定会导致国家衰亡,因此,《吕氏春秋》认为合格的君主应当“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24)。显然,《吕氏春秋》是在借助儒、道二家的思想,试图形成定义、限制君主专制的理论体系。 《吕氏春秋》一书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25)的整合之作,其中,渗入《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主张多与该文本的具体施政主张相关,而道家的无为思想则是其试图定义和规范集权体制及其边界的理论基石,显然,《吕氏春秋》是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在新时代延续的一个文本表征。杨宽先生认为《吕氏春秋》试图用儒家“德”、“义”来纠法家“严罚厚赏”(26)之偏颇,而吕不韦与秦始皇在政治上的矛盾和思想上的分歧最终使《吕氏春秋》的治国理论没能得以实施。(27)杨先生的分析是中肯的,不过,从里耶秦简J1(16)6所载“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28),岳麓书院藏第1541秦简“为人君则惠,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为人友则不争”(29)等出土文献看,儒家提倡的“不违农时”及其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也是秦施政措施的组成部分,这从一个侧面能够说明《吕氏春秋》一书所吸收的儒家思想的确对秦政产生过一定影响。然而,《吕氏春秋》《分职》、《审应》、《当染》诸篇章中提倡君主“处虚”、“无智、无能、无为”,“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等的道家政治哲学,则与秦的集权体制格格不入。战国以来,法家理念盛行秦国,秦人对“厚赏”趋之若鹜,而对“严罚”避之不及,遂有“虎狼”之称,(30)秦的历代君主多以积极有为著称于世,秦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深化,以至“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31)。在新的中央集权体制面前,试图让君主“无智、无能、无为”,并借此来规范这一体制在社会诸领域的边界,显然是在与虎谋皮。嬴政亲政后,吕不韦受嫪毐叛乱牵累被贬,后饮鸩自裁。吕不韦作为新兴贵族势力的代言者,尽管试图借自身实力及既有的封建传统,用儒家仁义、道家无为等传统思想资源来规范、抵制新兴集权体制的“惨磝少恩”(32)及其对贵族政治文化传统的威胁,但最终也难抵君主专制体制本身的历史步伐。从吕不韦的个人命运反观秦的君主专制及其建构方式,它显然是以法家化的政治结构为基础的,从中也蕴含着这一新兴政治体制的建构方式,即以消解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中的离心倾向为其施政宗旨。 西汉前期,诸子之学重又兴起。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刘安的《淮南子》皆试图以儒、道思想或一己之学整合诸子百家,这些文本的思想立意和政治诉求虽各有不同,但或多或少都受到《吕氏春秋》一书的影响(33),先秦贵族政治传统借助诸子思想的传播仍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从文本与政治变迁的内在关系看,对汉初政治产生影响的文本首推《新语》,其著者陆贾以《诗》、《书》进谏刘邦,终获信用,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34)。陆贾为一介书生,他著述立旨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借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而是试图利用旧有文化传统中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 《新语》一书首先剖析了秦速亡的原因,认为“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35)。秦之速亡的主因是“举措太众、刑罚太极”,当新兴的中央集权体制以严刑峻法将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试图用集权统治将天下一切事务归拢于皇权的管辖之下时,导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的结果。 秦因“尚刑而亡”,说明“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36),为避免重蹈秦的覆辙,陆贾认为必须借助儒、道二家的政治智慧来解决汉初的各种社会问题。首先,陆贾试图以儒家仁义思想来重构君主专制的施政性格,他认为“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37)。只有施德政者才能得民心,行仁义者才能得天下,主张“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38)。其次,在立国之道方面,陆贾极力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而天下大治”(39)。《新语》一书提倡道家无为思想,有其深刻的政治基础,因为布衣出身的刘姓皇室在因袭旧有传统方面显然比秦代更为彻底,其表现之一即为大规模恢复分封制。战国时,为实行中央集权制,秦国曾以都官之制拉拢宗室贵戚,在其所封邑之地设立都官,后又为了褒奖军功在军功贵族封邑也实施都官之制。战国末年,都官与县几乎是同等的地方行政机构(40)。秦统一六国后,废止了都官制,导致宗室贵戚与皇权疏离。秦末乱局中,皇权没有了宗亲贵族势力的依凭,一败涂地。西汉初年吸取前朝教训,废止异姓分封后,广泛实行同姓分封,使用宗族势力填充地方政治之空白,以求屏卫皇室的政治功效,正所谓“广疆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41)。《新语》一书将分封同姓的政治基础与先秦道家的政治哲理结合起来,既达到了利用先秦政治智慧解决当下问题的目的,也为刘邦的施政作了很好的注解。 《新语》一书将儒家的仁义和道家的无为熔为一炉,希望统治者能“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42)。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设计与汉高祖的施政方略多有相合之处,史称陆贾奉旨作《新语》,“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43),可见陆贾推崇的“无为”是汉初实行同姓分封的思想基石,也是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吸取亡秦教训,试图以宗藩势力护卫君权的政治实践,而陆贾力倡的儒家仁义则帮助汉初的统治者有效地冲淡了法治的严苛,收拢了民心。从《新语》一书与汉初的政治关系来看,汉初的君主专制体制借助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巩固并完善着自身的社会政治基础,这也使得新兴君主专制体制消解旧有文化传统的步伐暂时得以放缓,与此同时,陆贾利用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试图限制、规范君主专制,并定义皇权在社会诸领域产生影响的边界与范围的努力也暂时得以实现。因此,《新语》一书可看作是新旧政治势力暂时达成妥协的一个文本见证。 贾谊的《新书》也是一部通过反思、批判秦之苛政,试图影响西汉前期君主专制体制建构进程的重要思想文本。与陆贾糅合儒、道的思路不同,贾谊主张以儒家礼乐精神来改革时政,认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他把儒家礼乐精神视为治国之根本,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44)。正唯如此,贾谊曾向汉文帝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45),借此彻底摒弃秦政之残余,以儒治国。贾谊反对分封,认为即使是同姓诸侯,其势力一旦坐大,定会反叛,这是形势所至,并非因骨肉亲情而有所不同,他主张“夫树国必审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凶饥数动,彼必将有怪者生焉。祸之所杂,岂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46)。为解决宗藩势力坐大、皇权削弱的问题,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47),即“其有子以国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须之”(48)的策略,来加强中央集权。 西汉前中期离战国及秦未远,君主专制的建构基础及其面对的社会情状与战国及秦相类似,虽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致力于消弭传统政治结构中的离心倾向,但在实际的国家管理过程中仍然会因袭前制,以求因利就便的统治效果。如汉代的官僚体系中,除有禄秩系统外,也有“公卿大夫士”的爵位系统(49),虽然二十等爵在汉代不断贬值,但列侯与关内侯的封授仍是对官僚权益的重要补偿,官僚一旦封侯,其地位比拟于先秦贵族,这是一种身份的升格,是官僚拥有特权的象征(50),即使是禄秩也往往包含着政府授予官僚的特权,六百石以上官员拥有免役权、“先请”权和子弟入学权,二千石以上的则有任子权,这说明汉代官员的禄秩也体现着官僚的贵族性,而使官僚普遍拥有贵族性则体现了汉代君主专制建构的具体特点。针对列侯势力庞大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状况,贾谊曾上书汉文帝,让“列侯就国”(51),因此得罪权贵,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这说明新旧政治势力所达成的暂时的妥协与平衡,并非能被一介书生所能撼动。 陆贾、贾谊皆为书生,他们对诸子之学的承续是本着以亡秦为鉴,且为统治者提供施政方略的意图,并非是为自身利益作注解。所不同的是,陆贾以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中的共性因素为其主张立据,而贾谊则试图在黄老之术盛行的时代,让皇权改换统治方略,达到以儒治国之目的。因此,在他们的思想视域中,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病皆与严刑苛法有关。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各有不同,而从儒、道杂糅到以儒治国的思想变迁,则预示着西汉君主专制及其建构方式的变化。 西汉前中期,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对君主专制的离心倾向,以及君主专制政体对这一离心倾向的改造、消解,还集中反映在《淮南子》这一思想文本中。如前所述,对刘室子孙进行分封,也是汉政权因袭前制的一个典范。汉初的分封的确为该政权的稳固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但是汉室分封是构建大一统政治的一种手段,与西周初年的分封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导致的政治后果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正如贾谊所指出的那样,郡国之于中央所形成的离心倾向在文、景之时已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史称“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分封诸国“小者荒淫越法,大者睽孤横逆”,“可谓矫枉过其正矣”(52)。秦以法家之治疏远宗室,最终落得玉石俱焚,但汉代皇室在面对郡国势力分化、瓦解中央集权的各种苗头时,则采取了有效措施,全方位、有系统地消解了宗室成员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威胁。淮南王刘安之父刘长就曾遭文帝猜忌,构陷冤死。 据史书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53)。可见,尽管受到过皇权的打压和裁抑,刘安家族的权势、财力仍然炽盛,否则不可能招揽“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武帝即位,刘安入朝献《淮南内篇》,并奉旨作《离骚传》。刘安献书,其目的固然是为汉室的千秋鸿业着想,也有曲意配合武帝施政的想法,但其真正用意则是试图用这个以“无为”为思想主核的文本向武帝宣示诸侯王集团的政治主张,并为同姓诸侯的存续提供基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合法性。刘安对黄老道家“无为”思想的标榜,不仅是通过《要旨》一篇来反复审说,他的门客们在表述儒家礼乐思想时,也明示“仁义礼乐者”,是“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54)的衰世之策,只有“无为”才是理想的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手段。 《淮南子》一书的作者认为,“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稟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55)。“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世界的本原,而“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56),“无为”既然合乎“道”,就有着本然的合理性,“无为而治”则是这一宇宙规律在社会现实中的投影,因此,该书主张“夫圣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终始,是故其寐不梦,其觉不忧……当此之时,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沉沉,是谓大治。于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而难以算计举也”(57)。既然无为之治的好处“难以算计举”,那么统治者自然应当尊奉之,所谓“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敎,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58)。显然,集体创作形成的儒、道思想分野只是《淮南子》一书的表象,刘安和他的门客们在呈示不同治国方案的思想表达中刻意向皇权兜售“无为”之治。《淮南子》一书的作者还敢于批评操持生杀予夺之大权的皇权,“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59)。可见,所谓让统治者“自得”的立论依据仍是合于“道”的“无为”,他们试图将皇权限定在既有的政治与思想边界中,进而“与天下相得”,借此来限制、规范中央集权体制。 在对待同姓诸侯势力方面,汉武帝下推恩之令,以削弱藩国,《新书》中《藩强》、《藩伤》等篇力倡的削藩之策在这一时期得以落实。汉武帝还以左官律、附益法限制封国势力,以解除封国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淮南子》以“无为”来限制皇权,为诸侯王争取生存空间的企图亦无异于与虎谋皮。元狩元年(前122),刘安被冠以“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叛宗庙,妄作妖言”的罪名,被迫自杀。他死后,“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60)。刘安与吕不韦皆以自裁归终,《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地位与作用也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刘安和他的门客们可能比吕不韦及其门客更具生存上的紧张感,因为西汉中期以来,君主专制的建构模式比秦代更为完善、具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旧有政治遗产的存续空间。刘安在政治上的破产宣告了《淮南子》一书试图利用旧有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特别是道家无为思想来抑制皇权,为同姓诸侯谋求生存空间的努力最终落空,同时也昭示新旧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妥协与平衡业已打破,中央集权体制谋求的“大一统”时代业已到来。 秦及西汉中期,君主专制及其建构历程总体上是以中央集权体制代替旧有的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但其建构历程本身则表现得更为复杂,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利用旧有政治遗产是君主专制建构自身合法性的一个共性,同时,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特点,君主专制体制或因势利导,或锐意进取,其结果都对先秦以来的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打击和消解。从文本与政治变迁的关系来看,上述文本背后的政治势力及士人群体或试图以旧有文化传统抑制专制因素的成长,或试图定义集权体制在政治及思想领域的边界与范围,但最终都难抵新旧交替的历史必然。 源自先秦的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成为秦汉君主专制政体打压、消解的对象,同样始自先秦的一些文化观念则成为建构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春秋以来,周礼崩坏,王官典籍流散民间,诸子之学因此勃兴,思想争鸣也成为时代潮流。诸子在宣传自身思想理念时,往往以嘲讽、攻击其他各派为能事,即便是同一学派内部,也有水火不容的思想交锋。如孟子将战国时期的“显学”墨家和杨朱之学斥为“禽兽”(61),而他的学术思想却被同为儒门中人的荀子贬为“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62)。此外,庄子黜孔、墨子退儒皆有贬斥他学、标榜己意的目的。诸子间的思想争鸣的确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思想争鸣并不代表当时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诸子都想以自身的思想主张和政治蓝图来压倒对方,进而使自己的学派获得王权青睐。诸子间的思想交锋固然造就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但诸子间相互轻薄、贬损所造成的思想内耗,和为争夺权力体系的认可与赏识而形成的功利主义学风,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延续也曾作用于秦汉君主专制及其建构过程。 从文本与政治变迁的角度看,《春秋繁露》是典型地利用了上述文化传统,进而对汉代意识形态学说史形成重要影响的一个文本。“汉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63)。诸子之学复出后,立于学官的不仅有《五经》及儒家传记作品,也包括其他诸子之书,特别是《老子》等道家文本甚受重视,《五经》在当时并不具有特殊地位。实际上,汉初黄老之术盛行,“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64),不仅如此,在学术层面上,黄老哲学往往被视为“王道”之本,而儒家礼乐思想则被看成是退而求其次的治国之术,这一点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不仅在政治上汉初的儒生们没有获得特殊的宠信、优渥,其思想主张也甚难见信于君王,在学术领域内,儒学也并不占优势。正唯如此,当儒生们终于迎来武帝时期统治方略转型的时代契机时,便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借皇权贬低、打压诸子之学,借此使儒学获得独尊地位,董仲舒就曾建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5)。董仲舒以学术上的整齐功夫,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斥为“邪辟之说”,建议汉武帝“绝其道”。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66),除其他诸子之书,《论语》、《孝经》、《尔雅》等儒家传记作品也被罢博士。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献《天人三策》,其中,“罢黜百家,表章六经”(67)的建议显然与武帝之前的施政相呼应,为儒学的正统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儒生与皇权互为利用的关系中,以争鸣之名实施学术上的整齐之功夫成为皇权建构专制统治的一种资源,而《春秋繁露》就是在这样的政治与学术背景下形成的颇具影响力的一个思想文本。 《春秋繁露》一书以“天人合一”鼓吹君权神授,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包装皇权,并以“奉天而法古”、“张三世”、“存三统”等治经之法来确立儒家经学的基本框架,通过收摄诸子之学使学术思想定于一尊,并由此来配合现实政治的大一统。在“天人感应”方面,董仲舒提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68)。正唯“天人感应”,所以有阴阳、五行,所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69)。董仲舒将宇宙的运行看做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和道德的体现,借此为“君权神授”立论。同时,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中,“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70)。董仲舒借阴阳、五行学说,将人伦物理神秘化、理论化,其目的则是借此论证“天子”对人世间的一切拥有主宰权,“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71)。 在政治观上,董仲舒极力标榜《公羊春秋》之“大一统”思想,主张“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72)。为夯实“大一统”的合法性基础,董仲舒还将孔子塑造成提出“大一统”思想的圣人,把《春秋》视为孔子的治国大纲,“《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73)则是孔子的政治主张。董仲舒提出,“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74)。显然,《春秋繁露》一书是董仲舒借诸子之学来统摄纲纪、彰明法度的再创作,其目的是为汉武帝加强皇权、转变统治策略提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论参照,而他生拉硬扯、强词夺理的整合功夫和功利主义的解经策略则对后世经学和传统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75),《春秋繁露》一书利用诸子思想包装、夯实“大一统”的意旨则集中地反映了集权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独占性和排他性。 为皇权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同时,《春秋繁露》也试图将儒家仁爱思想纳入他所设计的政治蓝图中,主张“《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76)。他还试图以异灾、谴告之说约束皇权,声称“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77)。然而,在君主专制及其建构理念中,董仲舒塑造的孔子形象只不过是一个招牌,统治者决不会因此就真的会践行仁爱思想,相反,大一统理念一旦渗入思想文化领域,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人类的良知往往会被利用、歪曲,统治者就曾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78)不仅如此,面对强大的皇权,灾异、谴告之说的约束力更是微乎其微,董仲舒本人就曾“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而获罪,不敢“复言灾异”(79),《春秋繁露》一书中的整齐功夫和解经策略最终都被收摄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这说明当时的士人观念已受到皇权更为严格的控制和管束。 《春秋繁露》意味着以整合诸子之学来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阶段已基本告终,自此后,皇权对学术思想的干预也不再仅仅满足于整齐、收摄的表面功夫,而是通过设定思想议题、调和内部纷争等手段,来进一步强化大一统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地位与作用。在这方面,《盐铁论》和《白虎通义》是颇具代表性的两个文本。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朝廷从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辩论国事,史称“盐铁会议”。《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赞》云:“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可见,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武帝大一统施政得当与否进行辩论。事过30年后,桓宽整理相关记录,并增广条目,写成《盐铁论》。 在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乃至屯田戍边、对匈奴战和等问题,展开诘难、论争。昭帝“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80)。贤良文学之士认为,“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81)。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武帝的经济政策,认为盐铁官营之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82)的道德准则,引诱人民背义趋利。他们还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83),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84),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 桑弘羊则认为“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85)在他们眼里,贤良文学之士贫穷羸弱,连为孝资格都不具备,更遑论国事,且他们尊奉的孔子、孟轲等,虽“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或“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而“鲁国之削滋甚”、“(齐)湣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这足以说明“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86)。他们还认为,贤良文学之士“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87),是一些保守固执的不合时务者,没有资格与御史共论政事。御史极力维护武帝施政,认为盐铁官营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借此加强了政治控制,“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88)。可见,在他们看来,盐铁官营是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强化皇权的明智之策。 刘姓皇权标榜以孝治天下,儒家也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89)的警语,昭帝想要改弦易辙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较为沉重,他以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的大辩论为借口,来修正乃父之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压力。这次会议后,政府废除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说明昭帝借盐铁会议补救武帝施政之偏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盐铁会议的举行还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大将军霍光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把持财经大权,试图借盐铁会议削弱桑弘羊及丞相车千秋的实力,以扩张自己的权势。从文本内容来看,《盐铁论》一书时常引用《春秋繁露》,以为立论依据,贤良文学的主张也基本承袭了董仲舒的思想。不过,《盐铁论》的记录者桓宽曾“治《公羊春秋》”(90),由他整理而成的文本与原始记录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用今文经家的眼光来择别材料,由此夸大了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间的分歧,强化了今文经学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在该文本中的主导地位。 总之,《盐铁论》是君主专制政权自我调适的一个文本表征,具有政治斗争的内涵,同时也是王朝国家控制、规范思想议题和政治观念的一个文本见证。盐铁会议的辩论双方不能被简单地看做是两种思想传统或治国之术的代言人(91),贤良文学标榜的儒家思想和御史大夫的执政理念都是表达自身立场或维护自身利益的口实,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通过某个议题或某场辩论,来为调整施政纲领作舆论先导,并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则是大一统政权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的具体建构方式。 西汉武帝至东汉章帝时期,被刘氏皇权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呈分化趋势,今、古文经学从儒经著录上的文字分歧,逐步发展成为经学研究中截然对立的文化流派,政治主张上的分野也日趋明显。总体上看,今文经学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有优势,但古文经学也颇受皇权青睐,西汉末年及新莽执政时期,古文经就曾一度得势。光武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92)。今、古文经学的论争,以学术分歧为口实,其实质是儒生以经学攀附皇权,来铺就他们的“禄利之路”(93)。 经学内部的纷争虽然在客观上活跃了学术,但显然不利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确立。为平息今、古文之争,控制经学思想的解释权,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在洛阳北宫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94)。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由皇帝亲自裁决经义,来弥合今、古经学异同,实现经学的统一。这次会议的记录由班固整理成为《白虎通义》一书。 综观《白虎通义》,该书显然是以今文经学思想为主核,通过收摄古文经学的一些思想理念和西汉末年泛滥风行的谶纬思想,对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伦理原则等方面做出规定。《白虎通义》在承袭《春秋繁露》“天人合一”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颇具神学色彩的宇宙观。《白虎通义·天地》云:“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宇宙起源于太初,经太始到太素才形成天地,而“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95)。在这一宇宙观的思想体系中,天地是至高无上的,决定着人世间的一切,“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师……天有三光,然后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于三,有始,有中,有终。明天道而终之也”(96)。《白虎通义》还以五行思想比附人事,“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97)。可见,《白虎通义》以今文经学设定的宇宙秩序来比附人类社会,并以天道、阴阳、五行学说来阐释皇权纲纪的合法性。 《白虎通义·五行》云:“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世间的人伦物理也须遵照天地、阴阳、五行的法则。《白虎通义》鼓吹帝王就是天之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有权力决定人世间的一切,“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98)。即便是儒家的孝道观也要服从于忠君理念,“不以父命废王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99);“诛不避亲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干弱枝,明善善恶恶之义也”(100)。为强化忠君理念,专制皇权在利用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基础上,把持了相关范畴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进而使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面发展(101),最终达成“移孝作忠”之目的,使今、古文经师们的论争收摄于君主专制的威权,从而使之成为中央集权体制建构自身合法性的一种方式。 此外,《白虎通义》折中今古文经学的经典体系,把《诗》、《书》、《礼》、《易》、《乐》定为《五经》,“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102)。在统一经学所依据的文本体系的同时,《白虎通义》一书还以爵、号、谥,规定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社会各阶层的等级;以三纲、六纪,确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等社会关系的纲常伦纪;以礼乐、乡射、辟雍,制定文化教育礼仪制度;以崩薨、丧服,规定丧葬制度;以衣裳、绋冕,厘定衣冠制度;以三军、诛伐、五刑,明确国家管理的具体手段。显然,该书虽属经学范畴,因其含有“圣谕广训”,故而具有法典的意义和作用(103),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意志。 通过分析文本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演变轨迹,可对秦汉时期君主专制建构的历程、方式及特点做出如下总结: 从君主专制建构的历程看,秦及西汉前中期,如果说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是新生事物的话,在其形成过程中,旧有的政治结构及其文化传统伴随着这一新生事物,二者间的角力也是新旧政治结构相生相克的过程,而君主专制及其建构历程实质上是对旧有政治结构及其文化传统的消解过程。西汉中期以来,集权体制仍在利用旧有文化传统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独占性与排他性因素逐步增强,这一时期,《春秋繁露》、《盐铁论》及《白虎通》等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意旨与政治观念也日趋受到君主专制体制的规范与控制。 从秦汉君主专制的建构方式看,尽管皇权专制主要是通过官僚制度得以实现的,但借助思想文化观念来形塑、完善这一制度,也是其重要的建构方式,这一点在西汉中期以来的施政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鉴于亡秦之教训,两汉专制体制的建构者和维护者都希望能有长治久安的施政效果,因此,通过调整统治方略,与社会各种势力,尤其是与士人集团达成妥协,也是其强化君权的建构方式。因此,秦汉君主专制的建构方式中蕴含着某种双重性:在君权的引导、鼓励或规范下,士人群体通过整合诸子之学来为君主专制体制提供适合其存续的统治蓝图和思想体系,进而形成了体系较为完备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结构;逐步完善的意识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君权在这一领域内的作用与影响,从中也可以看出君主专制体制及其权力性格的多种表现,也可窥见帝王治术的演进。 从秦汉君主专制的特点看,秦及西汉前期,士人群体或特定思想文本背后的政治势力利用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试图定义、规范君主专制体系,以抑制专制因素的成长,这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专制的垄断性、暴力性,但思想文本能够发挥作用与否都取决于君权本身。西汉中期以来,在君权基于宇宙论意义上的权力合法性建构中,皇权至高无上,其合法性的维度不能为任何政治势力、士人群体或宗教团体所干预或控制,正唯如此,对君主权力的制约或对这一权力的分配,往往与其官僚制度的运行法则有关,而与思想观念中的限制皇权理论基本无涉。由此可见,皇权的垄断性是君主专制体制建构的本质特点。 严耕望先生曾说:“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104)对于君主专制体制而言,其坚实统治基础的构建历程也是一个上下联贯的历史过程,如若结合特定时期的思想文本来反观这一建构历程,或许可能更深入地体察到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及其复杂性。 ①本文所引《吕氏春秋》均为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②本文所引《新语》均为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本文所引《新书》均为阎振兴、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④本文所引《淮南子》均为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⑤本文所引《春秋繁露》均为[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⑥本文所引《盐铁论》均为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⑦本文所引《白虎通义》均为[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⑧沈长云:《先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178页。 ⑨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⑩[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七《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1页。 (11)《史记》卷八五《吕不韦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9页。 (12)《史记》卷八五《吕不韦传》,第2510页。 (13)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8页。 (14)《吕氏春秋》卷一三《务本》,第298页。 (15)《吕氏春秋》卷九《顺民》,第199—200页。 (16)《吕氏春秋》卷一七《执一》,第469页。 (17)《吕氏春秋》卷二三《贵直论》,第620页。 (18)《吕氏春秋》卷四《尊师》,第95—96页。 (19)《吕氏春秋》卷一《贵公》,第25页。 (20)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437页。 (21)《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22)《吕氏春秋》卷一七《君守》,第440页。 (23)《吕氏春秋》卷一七《任数》,第443—444页。 (24)《吕氏春秋》卷一二《士节》,第262页。 (25)[汉]高诱:《吕氏春秋序》,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3页。 (26)《吕氏春秋》卷一九《上德》,第518页。 (27)杨宽:《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 (2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秦简——秦代古城一号并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29)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30)何晋:《秦称“虎狼”考》,《文博》1999年第5期。 (3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32)《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56页。 (3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48页。 (34)《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9页。 (35)《新语》卷上《无为》第四,第63页。 (36)《新语》卷上《道基》第一,第29页。 (37)《新语》卷下《至德》第八,第117页。 (38)《新语》卷上《道基》第一,第30页。 (39)《新语》卷上《无为》第四,第59页。 (40)〔日〕工滕元男著,〔日〕广濑薰雄、曹峰译:《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0—69页。 (41)《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2页。 (42)《新语》卷上《道基》第一,第28页。 (43)《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9页。 (44)《新书》卷六《礼》,阎振兴、钟夏:《新书校注》,第214—215页。 (45)《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22页。 (46)《新书》卷一《藩伤》,第36—39页。 (47)《新书》卷一《藩强》,第39—40页。 (48)《新书》卷一《藩伤》,第37页。 (49)杨振红:《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文史哲》2008年第5期。 (50)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3页。 (51)《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22页。 (52)《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394、395页。 (53)《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刘安传》,第2145页。 (54)《淮南子》卷八《本经训》,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250页。 (55)《淮南子》卷一《原道训》,第1页。 (56)《淮南子》卷一《原道训》,第2页。 (57)《淮南子》卷二《俶直训》,第48—50页。 (58)《淮南子》卷九《主术训》,第269页。 (59)《淮南子》卷一《原道训》,第36页。 (60)《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刘安传》,第2152页。 (61)《孟子·滕文公下》,[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6页。 (62)《荀子·非十二子》,[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4页。 (63)《汉书》卷三六《刘歆传》所载《移太常博士书》,第1968—1969页。 (64)《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592页。 (65)《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66)《汉书》卷六《武帝本纪》,第159页。 (67)《汉书》卷六《武帝本纪》,第212页。 (68)《春秋繁露》卷一三《同类相动》,第447页。 (69)《春秋繁露》卷一三《五行相生》,第457—458页。 (70)《春秋繁露》卷一二《基义》,第432—433页。 (71)《春秋繁露》卷一一《为人者天》,第386页。 (72)《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第15页。 (73)《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236页。 (74)《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质文》,第17—18页。 (75)赵伯雄:《从〈春秋繁露〉看董氏〈春秋〉学》,《南开学报》1995年第1期。 (76)《春秋繁露》卷六《俞序》,第201—202页。 (77)《春秋繁露》卷一七《威德所生》,第591页。 (78)《汉书》卷八《元帝纪》,第277页。 (79)《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4页。 (80)《盐铁论》卷一《本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1页。 (81)《盐铁论》卷一《本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1页。 (82)《盐铁论》卷一《错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56页。 (83)《盐铁论》卷一《本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3页。 (84)《盐铁论》卷三《园池》,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172页。 (85)《盐铁论》卷四《地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第209页。 (86)《盐铁论》卷二《论儒》,第149页。 (87)《盐铁论》卷二《刺复》,第130页。 (88)《盐铁论》卷一《复古》,第78—79页。 (89)《论语·学而》,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页。 (90)《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赞》,第2903页。 (91)王利器:《桑弘羊与〈盐铁论〉》,《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92)《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1208页。 (9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20页。 (94)《后汉书》卷三《章帝本纪》,第138页。 (95)《白虎通义》卷九《天地》,第420页。 (96)《白虎通义》卷四《封公侯》,第131页。 (97)《白虎通义》卷四《五行》,第116页。 (98)《白虎通义》卷七《圣人》,第334页。 (99)《白虎通义》卷四《五行》,第197页。 (100)《白虎通义》卷五《诛伐》,第211页。 (101)方光华:《思想与皇权的协调——论孝观念从孔孟到〈白虎通〉的转变》,《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 (102)《白虎通义》卷九《五经》,第447页。 (10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4、494页。 (104)严耕望:《治史三书·治史经验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标签:儒家论文; 吕不韦论文; 吕氏春秋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中央集权制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君主专制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淮南子论文; 春秋繁露论文; 新书论文; 文化史论文; 国学论文; 新语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