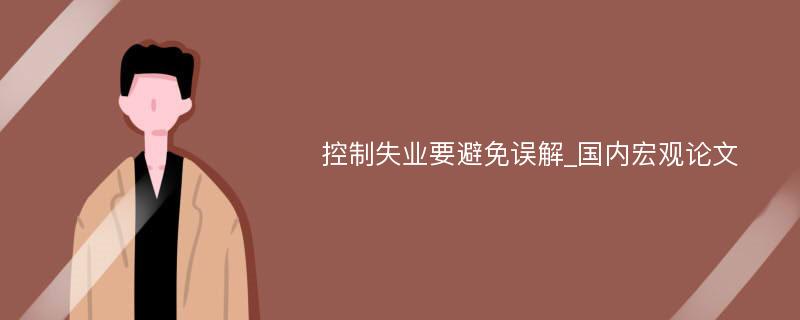
治理失业要避开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一些政策建议的看法
一种政策建议是为城镇失业率确定一个政策控制线。确定一个可以为目前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所承受的失业率控制线,是以失业率平均分摊到职工或居民身上为前提的。然而,这种平均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失业概率并不是平均分摊在所有的就业者身上,而是全部后果都集中于真正失业者身上。所以,社会可以接受多高的失业率,取决于平均收入的提高水平、分配的均等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等一系列因素。
有人建议在近中期内把下岗现象与失业并轨。事实上下岗现象的存在意味着企业为社会承担着一部分失业救济责任。设想如果现在所有的下岗职工都转变为社会上的失业者,国家并不能保障他们的再就业和失业保险,社会不稳定性必然会高于目前。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假以时日,所以放弃下岗这种做法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许多人认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扩大就业的潜力是有限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我国目前确实处于实际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时期,另一方面不同的增长方式和不同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就业弹性。如果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得以消除,劳动力丰富的资源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产业结构将趋向于劳动密集型,从而扩大就业的潜力将会很大。
还有人认为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是不受劳动力市场调节的,这也是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对于非正规部门的定义恰恰是其更加具有市场调节的性质。而由于我国第三产业相对不发达,城镇非正规部门更加符合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具有巨大的就业潜力,不容忽视。
二、失业和下岗现象是多因素造成的
我国当前出现的严重失业和下岗问题,不是某种单一的因素造成的,而是几个原因同时促成的。而只有把握住这种多因性质,才能针对不同区域、有重点和区别对待地选准治理对策,并按照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次序予以实施。
无庸讳言,导致当前失业和下岗的首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处于相对低沉的时期,社会总需求不足,市场萧条从而生产能力未能充分开工。从职工工资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商品零售价格等年度增长指数看,1994年以后均呈明显的降低趋势。这种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必然影响就业的增长,因而同样地,1994年以后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年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一部分丧失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部门排挤出大量劳动者。国有企业长期执行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产业结构具有资金密集程度高、调整速度缓慢的特征。面对国际市场的不断变化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竞争,其产业结构的调整迫在眉睫。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一部分职工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而一旦这些失业者的劳动技能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这种失业就可能是长期的。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来以冗员形式存在的隐性失业变为公开的失业或下岗。国有企业严重冗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也是其与迅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竞争中的一大弱势。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落实、企业改制的加快和“减员增效”口号的推动下,富余职工开始下岗,其中一部分被推向社会。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因素造成的失业和下岗,仍然与宏观经济形势及产业结构状况紧密相关。因为事实上企业早就获得劳动用工自主权,但经理人员并未运用这种权力,直至经济效益滑坡、经营难以为继,才被迫让职工下岗。
三、当前失业治理中的几点误区
误区之一。许多地方政府把外来劳动力看作是城镇职工的竞争对手,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排斥和歧视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例如,通过各种收费渠道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明确规定出诸多的岗位不允许雇佣外地劳动力;以“再就业工程”的名义,通过奖罚手段诱导企业用本地失业工人替代外来劳动力。而事实上外来劳动力与城镇劳动者的就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合,所以这种政策倾向不仅不利于劳动力市场发育,也并无助于减轻城市的失业率。
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大约1/3,就业不足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清退农民工不仅不会减轻整体的就业压力,还会因为农民收入下降而对市场需求产生不利影响,反过来增加城市失业。
实际上,农民收入的提高本来可以通过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从而启动相对冷却的宏观经济。此外,由于同样的岗位雇佣城市职工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所以,这样做的结果还会提高整体工资水平,降低我国经济的竞争能力,与反失业政策的初衷是相悖的。
误区之二。许多人主张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程度来减轻就业压力。首先,其实那些有条件不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我们现在急迫要解决的是那些家庭负担重、夫妻同时下岗因而生活困难的失业问题。对于这些人来说,并不在于愿意不愿意再就业,而在于怎样维持基本生活。其次,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中包含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缩减工时、过早退休等减少劳动供给的方法,实际上仅仅减少了企业对劳动力可变成本的支出,而长期积累的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则已由企业在以前支出了。让有经验的职工回家,腾出岗位雇佣新工人,反而会提高企业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最后的结果并不鼓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误区之三。许多人建议迅速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替代传统就业体制的这种职能,并在这种新的安全机制保障之下完成就业体制的转换。从长期看,显然这是一种正确的思路。但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以其替代旧体制需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在选择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需要特别防止走向我们目前根本承受不起的福利体制。例如,失业保险是在常规条件下的保险机制,而一方面我国这种保险体制刚刚建立,另一方面当前的失业和下岗现象具有超常规的特点,因而保险能力不足是必然的。让企业承担保障就业职能尽管可以解燃眉之急,但与正确的方向南辕北辙,对将来的改革不利。所以,我们急需寻找一种既可以较快建立起来并奏效,又不会对今后的改革设置障碍的办法。
四、关于治理失业的一些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当前失业是由宏观经济景气、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共同造成的,则应该区分轻重缓急,分阶段长短结合地实施政府的失业治理对策。为了避免失业和下岗问题的严重化影响到社会安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适当地调整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
近期内,刺激社会总需求,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应为当务之急。在选择有效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时,需要把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带动作用当作首要的标准。防止赶超思想特别是用产业保护的办法发展所谓支柱产业。以家庭轿车业为例,实际上这个产业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可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此外,该产业资金密集程度比较高,就业推动作用不显著。用保护的办法发展这种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仅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妨碍国内统一市场的发育,还会在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受到冲击。
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应率先在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失业且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的失业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一制度不仅具有迫切性,由于其属于民政、救济的性质,还可以相对独立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其他方面,具有率先出台的可行性。事实上各级政府本身以及通过企业,已经为维持无效率的就业支付了大量的资金。把这笔资金转用于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不改变使用目的的同时,还可以提高效率。
从长期来看,失业问题的解决仍然有赖于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条件下,生产方向的选择和产业结构的形成,才能符合劳动力丰富这一资源比较优势。在较长的时期内,充分发挥这种优势,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届时形成的劳动力市场调节机制,将主要关注因常规性的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自然失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