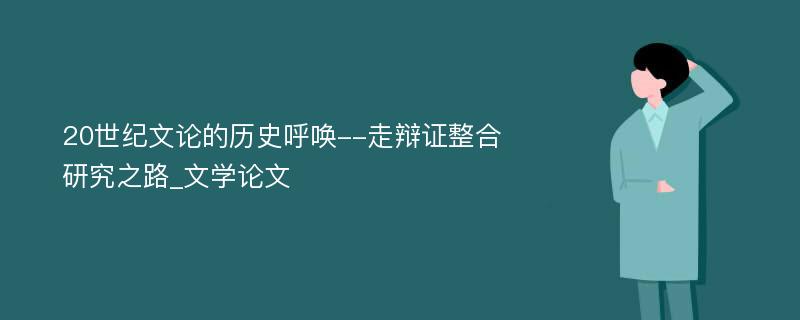
20世纪文论的历史呼唤——走辩证整合研究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之路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文论一方面学派纷呈,蔚为壮观:一方面花开花落,变化急剧,呈现出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从这个角度看,有人称20世纪为批评的时代,这不无道理。
20世纪文论地图尽管斑斓驳杂,20世纪文化历程尽管坎坷不平,但仍可窥见其变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和难忘的经验。回眸百年来中国文论,它同样经历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其主要特点之一是不断地引进和吸纳外国文论特别是同西方文论和俄苏文论息息相关。我们在介绍和吸收外国文论方面也积累了各种经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总结。总之,依我看来,在20世纪文论的种种经验中,最重要的是:走辩证整合之路,这是20世纪文论的历史呼唤。
20世纪文论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历史走来,特别是从19世纪文论演变而来。更确切地说,是对19世纪文论的碰撞和反拔。
自19世纪下半期起,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斯达尔夫人、泰纳、格罗塞等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派和朗松、维谢洛夫斯基、布兰兑斯等为代表的文化史派,在确立文学同民族意识、社会历史和文化等的关系方面做了巨大工作,成就卓著,如洋洋大观的《剑桥英国文学史》,朗松的《法国文学史》,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潮》等,至今仍旧被我们称颂、参考。问题是,它们往往忽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仅仅把它看成是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材料,而且不去探讨研究语言和形式的审美特征,这是它们的严重偏颇和缺陷。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20世纪文论的重要一级——唯科学主义的各个学派便蜂拥而起,如俄苏形式学派(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和以雅科勃逊为代表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如不同于19世纪那种“旧”批评的英美“新批评”,而“新批评”在美国竟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失去其主导地位;如以列维一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而参与其形成的尚有索绪尔及其学生的“日内瓦语言学派”、俄苏形式学派、布拉格结构学派、哥本哈根和纽约的语言学小组,彼尔斯和莫里斯的美国符号学派等;如一些新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派诸如“比利时文学社会学派”(戈德曼等)。可以说,是19世纪文论的严重偏颇和缺陷,促使它们反其道而行之: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把语言和形式绝对化,把文学作品本体化,而置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于不顾。于是,俄国未来派提出“艺术是形式的艺术”;什克洛夫斯基宣称文学研究是“内部规律”研究、“艺术即手法”;雅科勃逊认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文学性”;兰色姆断言文学作品是独立自主的;温萨特和比厄兹利声称“外部因素”研究是“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罗兰·巴特主张文学研究“是文本结构的准确描述”;托多洛夫指出文学研究“应该阐述的不是‘起源’问题,不是文本可以从非文本产生的问题”等等。一句话,他们力图创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并赋予它以精确科学的形式。但实际上这是矫枉过正。虽然他们在形式、结构、手法、韵律、修辞等诸多方面有不少精彩的开拓和建树,但终究走向了另一片面,另一极端,而未能走向全面,走向真理。
在20世纪上半期,与“非人格化”的准科学主义文论对垒的,是人文主义文论,属于这一理论建构的有现代阐释学、存在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美学、意识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它们主张描述作者和读者的意识状态;认为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只能通过体验和感受。在它们看来,文学即主体意识,即直觉,即表现,即原型,即接受。它们所理解的内容成分是一种具有意向性的东西,是一种意识的表现。如果说准科学主义把客体绝对化,把文学作品体论化;那末,人文主义则把主体绝对化,把作者和读者的意识本体化。尽管人文主义文论在意识、主体、原型、接受等诸多方面颇有开拓和成就,但它终究是以偏概全,把它们推向极致,从而陷入了极大的局限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20世纪文论中,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虽各执一端,针锋相对,但在文学与民族、社会、历史、世界等关系方面,在对待19世纪文论的主潮方面,又殊途同归,采取否定立场,仅从认识论,角度看,它们的致命伤或在于把一种局部性质的东西变成一种普遍性质的东西;或把一点、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一个视角变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东西。尽管它们对某一点、某一片断、某一个侧面、某一视角的阐述,不无精采、深刻、合理和独到之外,可是从整体和全局来审视,它们都是生长在“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凡是走过头的东西,总得走回来。在20世纪文论的历史行程中,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大对立的潮流,便受到了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的质疑和挑战。
首先,形成于60年代末的叙术学,便在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之间,采取了一种中间立场。其著名代表者有热奈特、托多洛夫、马尔、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在结构主义那里,文学作品被看成是不依赖于作者和读者的自主客体;在现象学等那里,文学作品被溶化在读者的意识之中。叙述学则力图避免这两种极端立场,既不抛弃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但却把重点放在作者和读者的积极对话之中。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多数结构主义者便转到叙述学一边。这是20世纪文论格局发生的一次明显变化。
其次,20世纪80年代,准科学主义文论和人文主义文论的对立,由于解构主义的蜚声文坛而被拉平。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左右开弓,既尖锐批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也激烈抨击阐释学和现象学,并经常声称自己的解构理论为“后结构主义”或“后现象学”。在他看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是自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至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据点;而阐释学和现象学将主体的反应能力同关于中心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则被德里达谴责为企图复活形而上学的一种努力。这因为,按解构主义的主张,中心应该是绝对的缺席,而文学批评不能追求文学作品的本来意义,其本质是一种再创造活动,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阐释,并且永无止境。其实,解构主义本身是矛盾的,它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反对别人的中心,是以自己的形而上学来反对别人的形而上学。此外,它提出的世界即文本、任何阅读都必然是错误的等论点,这不能不引起其他学派的代表者诸如伽达默尔等的非议。
果然好景不长,尽管解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名噪一时,在美国和西欧许多大学占有优势地位,出版的著述比任何学派都多,领导了多个专业团体,在物质上得到了众多机构的资助,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终于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研究,并占据了文论的主导地位。
曾经是解构主义及“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希利斯·米勒,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对解构主义的衰落及其之后的文论状况作了发人深省的描述: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转为文学研究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和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或者说,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无异于说:20世纪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起,它在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之后,已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与过去所不同的是,这次的返回并不抛弃它的对立面:语言和形式。这是20世纪文论的历史进步。米勒在文中还说了一段富有意味和有分量的话:那些外部关系本身即为文本所固有,包含在文本内部。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正如大多数这类二项对立一样,结果都被证明是人为的和骗人的。其实,我以为,过去和现在的优秀文论无不是“出乎其外”和“入乎其内”的。如何科学地对待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或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相互关系,这是文学理论的永恒试金石。
80年代是20世纪文论进程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也是它的反思时期。
就在美国学者米勒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几年,苏联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和法国学者托多洛夫,当然还有其他文论家,在涉及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的相互关系这一世纪性的问题和论争时,也作了意义深远的反思。这三个不同国家和三个不同学派的学者,几乎在同一时候,以自己不同的学术生涯和生活经历关注这同一问题,这决非偶然和巧合,而是20世纪文论内在发展之使然。
作为俄苏形式学派的领袖人物,什克洛夫斯基1925年在其《散文理论》的“序言”中,明确宣布: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这是他和他的学派的共同纲领,也是20世纪许多学派的宣言,包括韦纳克和沃伦那本著名的《文学理论》(1949)在内。在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1982年他已90高龄,在逝世前两年他写了一本新《散文理论》(除收进过去写的两篇文章外,其余均为新作),作了系统而集中的反思。这是他的学术遗嘱,书中写道:“我在写一本关于散文理论的新书”;“就我而言,写这本书并非易事。我比同辈中的许多人活得更长久……善于重新思考的人剩下不多了。”1925年“那本关于散文理论的书,应该作为这本更厚的书的注解。要知道一切事物诞生时都很小,后来才得到发展。”什克洛夫斯基对许多问题做了反思:
第一,关于词语与文本。他说:“我曾有过错误,因为曾认为,词语仅仅是词语而已”;但“以为文本仅仅是文本,那首先就不是艺术家,不是武士”,因此“诗语研究会”的“建树并不精确,并不完全”。
第二,关于文艺与生活。他写道:“我曾把生活之流和艺术之流分离开来,这是不对的。脱离世界历史,不分析历史的种种病痛,不解决人类经历的全部艰难困苦的遭遇,而要理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作品与作家。他指出:“我曾经写过,艺术无恻隐之心,此话激烈,但并不正确。艺术是怜悯与残忍的代言人,是重新审视人类生存法则的法官,我限制了运用艺术的范围,重踏了老欧美学派的覆辙”。
第四,关于艺术目的。他说:“艺术作品的目的曾为我所排斥。但是艺术,甚至从屋顶上的猫叫开始,它也有目的。这不仅要擦净向我们展现世界的玻璃,而且教导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
另一位有影响的法国结构主义者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1985)一书中,作了同样的反思。该著出版不久,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兼批评家便发表评论说:这是从形式返回内容、从精神的科学主义返回真理的人文主义的一次转折。托多洛夫认为,他发现作品中的历史构想和结构构想,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分辨;过去以为是中性方法及纯描述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某种明确的历史选择的结果。因此,他指出:需要在广泛的语境中理解语言的意义。首先是作品的语境,是作品、作者、时代、文学传统构筑了不同层次的语境;文学如果不有助于认识生活就分文不值。批评和作品一样,也应探求真理和价值。托多洛夫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构主义的过失,要由意识形态来补偿。我想,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走辩证整台之路,势在必行。
与这些反思相联系的,或者说,与这一文论进程相联系的,是20世纪70和80年代之交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巴赫金热”。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他自称为“社会诗学”)和对话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1965年他发表关于拉伯雷和“狂欢化”的论著。这时之所以产生“巴赫金热”,显然同20世纪文论的重点转移有关,同文化研究被提上20世纪文论的“议事日程”有关。一句话,巴赫金是文论进程和文论时代的需要。
——这就是我关于走辩证整合之路的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