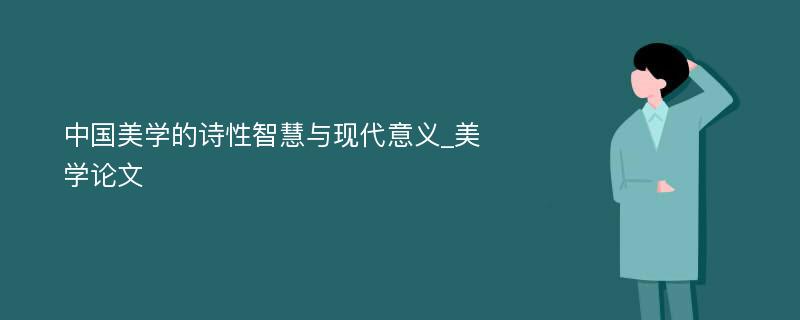
中国美学的诗性智慧及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诗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与西方古典美学偏重理论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倾向相比,中国传统美学在表述方式、内容与内在精神的构成方面,则更多呈现出诗性的气质与禀性。诗性智慧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根基,其内涵与功能是十分特殊的,它铸造了中国美学的感性超越精神,形成了中国美学特殊的价值内涵和人文智慧。时至今日,在美学的发展日益被符号、形式和概念不断遮蔽与割裂,美学创造的浮泛之风与技术化倾向日益严重的状态下,努力发掘和总结中国美学的诗学精神和诗性智慧,对当代美学本体理论的建设来说,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诗性智慧”是由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依维柯的理解,人类社会最初的智慧就是一种“诗性智慧”。由于原始人处在人类发展的儿童时期,其智力是混饨不分的,理性的抽象能力尚不发达,但却富于感觉力和想象力。这种感觉力和想象力被维柯称为“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注:维柯:《新科学》,161~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在维柯看来,诗性智慧就是一种以感觉和想象为内容的创造能力——即诗性的玄学,由此派生出的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文化创造行为,全是诗性的物质(注:维柯:《新科学》,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显然,维柯所讲的诗性智慧只是对人类感官特有的创造性功能的一种肯定,它代表了人类认识的初级形态,是诗的原始想象力与原始方式的体现。中国美学的诗性智慧并非是这种原始的感觉型智慧,它是在中国传统的诗学精神与诗性文化的熏染下,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一种艺术型的创造性灵智,或整体的直觉型智慧。这种智慧融充盈完整的生命体验与感性直观的创造性领悟为一体,把中国哲学“思”的意蕴与中国艺术“诗”的方式巧妙结合,展示出一种超越逻辑和知识的灵性。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内在精神与价值指向,在于维护人的自然感性和生命力量,保持和肯定人的最本真的存在状态,以实现审美的生存境界。中国美学的诗性智慧主要不是展示美的现象域的规律、构成与特征,而是展示与美的存在域有关的人学依据,展示关于生命的诗化性或诗化的人生的理论,展示中国古人实现审美生存超越与从事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则与奥秘。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产生和形成,根源于中国的诗学精神、诗性文化和特殊的思维方式。
中国是一个最富有诗学精神和诗学传统的国度,以中国诗性为核心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是中国美学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训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与诗就有着特别的亲缘关系。在这诗的国度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论便充满着诗性智慧,是地地道道的诗学。“诗者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古代的诗是至情至性的自然流露,是诗人内在品格的充盈外溢,而中国古代文论则是对这种生命现象的直观的理解、阐述与把握,同样包含了充盈的生命力的智慧。因而,中国古代的诗学精神就是诗的气质、诗的灵魂、诗的思维与诗的体验方式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浸淫和渗透,它是诗人的情致、理念和生命型态的外化。中国文论把诗的理论与人的感性生命形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特有的诗性智慧风貌,即中国古代文论所呈现的感性生命结构型态。这种结构型态生长于“言志”与“缘情”的诗学传统,至魏晋时期“气”的概念的提出,便开始了古代文论与感性生命型态的同质同构,如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谢赫的“气韵生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养气》篇,以及气力、气韵、神气等概念的提出,皆与人的感性生命力相关;唐宋以来,“文以韵为主”,由象而境、境生于象外,以及“离形得似”等诗创作观念的形成,皆追求主体“心象”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本自心源、想成形迹”,心即境也,心性为本,无不体现了中国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源于人的心理和精神结构的显著特点;而到明清之际,性情、性灵、童心、境界等概念的提出与完善,已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与人的精神、心灵等生命整体系统要素的内在统一与同构。它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及其内容的演化,也体现了中国美学的诗性智慧独有的内涵,即它的深层根源和精神是人的感性生命结构型态的艺术性外化及其展开,所以说它是关于生命诗化的理论。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整体构架中,中国哲学所体现的诗性气质与诗化倾向,也从内在精神的构成方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特征的成熟,是铸造诗性智慧内核和精神的重要基因与资源。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在人类思维领域,只有诗的语言才可以表达一个人的世界或境界。诗具有独特性、一次性,境界可以通过诗意或审美意识一次性地体验到、把握到。海氏所讲的“诗意的说”与“诗化”,其实正言中了中国哲学所充溢的诗意境界与诗意的语言这种特点。中国哲学大多数是以“诗”的方式表达“思”的内容,在诗与思的结合上尤为突出。中国哲学之所以不以宗教而以审美为中国哲学最高目标,正是对既具有理性内容又保持感性形式的诗化哲学气质的肯定。中国哲学的诗性特点,不仅指孔孟、庄禅、陆王哲学中的诗意的东西,孔子趋慕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庄子“逍遥游”的飘思,禅宗“雁过深潭、影沉寒水”的化境,陆王的性灵发露、良知显现、仁德流行、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的天人合一之境,也是指中国诗文中的哲学感受和思考,屈子之思、陶潜之思、王维之思、寒山之思、东坡之思……(注:刘小枫:《诗化哲学》,273~27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诗所以成为中国哲学特殊的表达方式,成为中国哲人的生存境界和人生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确立与基本精神和内容的嬗变,始终以人生价值目标和意义的阐明及其实践为核心,以心性修养为重点,所以非常重视诗化的内在体验方式及其功能;另一方面,自周以来所形成的以诗为精神本体的传统文化心理,不仅没有受到来自神学和理性的挑战,没有受到知性的改造,反而由华夏民族以异样的热情肯定下来,这就是中国古代对诗的创造的超乎一切的重视和崇尚。可以说,诗的情结已成为华夏民族古老的集体无意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和哲学禀性,必然为中国美学诗性气质的形成打上深深的印记。
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形成,也源于传统思维方式的特殊作用。李泽厚曾指出,中国哲学的审美型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性逻辑的清晰”(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311页,人民出版社,1986。)。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虽然缺少以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使它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神秘性,但这恰恰是形成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重要的思维基础。诸如“体”、“体证”、“体认”、“顿悟”、“禅定”、“觉”、“意会”、“诚明之知”、“清思之知”等概念的提出,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直觉的涵义,或者说与直觉思维有关。而道家哲学、魏晋玄学、中国佛学及宋明理学都颇重视直觉性思维,追求思维内涵的直观体验性、超越性、非逻辑性、突发性、整体性、意向性和内倾性。这些特征的相互协调与融合,导致传统直觉思维产生出一种独特作用,使得思维对象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无限整体和无限本体,思维主体不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认知主体进入思维过程,而且作为一个理智、意志、感情的统一体而发生作用,从而获得对真的认识、对善的体验和对美的感受。“主体的知、情、意对象化为真、善、美,所得到的是一个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整体性精神境界”(注: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14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其优越性在于以自由性、能动性和体验性的发挥,突破有限达到无限,从而实现精神的超越,这正是中国古代诗的思维和艺术的思维所具有的内涵。中国古代的艺术创造、艺术欣赏和审美理论,大都强调“神似”,反对“形似”,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重视含蓄、隐而不露,反对一览无余,形成了重内心体验、重描述、重表现、重直观领悟的审美传统和艺术传统,这与直觉思维有直接的关系。直觉思维是诗的思维,是以诗的精神把握对象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它也是形成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关键。
二
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形成,既然与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和诗性文化精神密切相关,那么,要理解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性质和特点,就不能不深入分析传统诗学理论与诗性文化精神的价值意向和基本内涵。概括地讲,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和诗性文化是本于人心、本于精神境界的,其重心并不在于单纯地探究和阐释诗的创造技巧与原则,而在于感发意志、陶冶性情;在于表现和抒发主体真实的生命感受,引导主体进入艺术化(即诗化)的生存境界。作为一种美学智慧的表达,它充分显示对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维护,并尽可能地完善和提升诗人的生命活动的质量和意义,使主体获得生命活动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因而,所谓中国美学的诗性智慧,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智慧或生命智慧。审美活动主体通过创作或感受大量的诗性符号与艺术对象,以特殊的时间性体验去扩张生命活动的无限空间和范围,把一种现实的日常时间转化为特殊的审美时间,从而获得生命的自由与和谐。生命的诗化或诗的生命化,正是这种智慧的核心所在,它体现了中国美学内在的人文智慧和精神气质,并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的诗化倾向。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习惯中,入诗与作诗,不单是一种艺术创造的问题,其实也是人的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所谓“诗学”概念或诗性文化,其实也属于生命本体范畴的命题,它是本于人的心性、情感和内在的精神。以中国古代对诗的阐释为例,先秦《尚书》曰“诗言志”;汉代《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刘歆在《七略》中讲“诗人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六朝人陆机曰“诗缘情而绮靡”;挚虞曰:“诗……以情志为本,成声为节”(注:《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唐代孔颖达则更加强调诗对维护人性的纯洁所具有的作用,“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数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注:《毛诗正义》卷一)。除此之外,陈子昂论诗重“风骨”,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注:《陈伯玉文集》卷一);刘禹锡论诗重“意境”,即“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注:《刘禹锡集》卷二十九)。白居易论诗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以及严羽所谓“诗之极至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注:《沧浪诗话校释》,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以及所谓“童心”说、“性灵”说等……这种种关于诗的规定和解释,虽然繁复芜杂,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诗是心智的果实,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精神灌注的结果。诗与诗性文化动人的奥秘正在于对真诚与良知的直接表达,在于主体生命力的激扬。
有学者在解释中国传统的诗学观念和诗性本体时指出:诗是“本于心”的精神产品,由此而形成的诗学观念也理所当然地具有“本于心’的特征。中国传统的诗学本体是一个“心物交融”,以能动的精神创造不断包容和建构外在世界的过程。它发端于“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象”,注意了感性显现;完成于“境”,提高于“神”,使表现内心与感性显现都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所以,以诗美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美学,始终强调“本于心”的创造,以及这种创造所爆发的生机与生命活力(注:陈良运:《论中国诗学发展规律、体系建构与当代效应》,见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489~49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本于心”作为诗性智慧的基本内涵,它形成了中国美学的本体性征:在展现方式上,即偏重审美主体的内在体验和真情抒发,不仅致力于人的生命本真状态和源泉的探索,致力于生命最高活力的追求,并把审美对象和宇宙中一切非生命的存在都视作生机勃勃的活体。因此,与人的生命型态相关联的气、情、神、韵,才构成中国美学的智慧之源与存在之本;而从内在构成与价值向度方面看,“本于心”的诗性智慧,则意味着真诚与良知的表达,意味着诗人通过由心智灌注的诗,去寻找、发现以及表达从真诚与良知中吸取痛苦和美的力量,这也就是诗性智慧的力量。因而,无论是对人生的真实叹喟,还是对人间悲欢的真切体验,对生命律动的真诚袒露,诗的过程均蕴含着真诚与良知,这其实正是中国传统诗性文化(即古典美学)的特殊气质与魅力:它厚重、深刻而典雅,并向往和追求精神的纯洁与神圣。越是在历史的动荡或不尽的黑夜里,诗人越是以真诚的自我去审视历史与现实,以维护人类自身的尊严和对生命本体的珍惜。所以,同美学存在的意义一样,诗性智慧的价值尺度也是以人的解放和对自由的无限追寻为标志的,这始终是美学本体理论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命题。
在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本体层面中,独特的诗性观念和诗性精神的产生,也是极为重要的价值构成,它既关联着人的本质,也关联着美的本质。因为中国诗美学的最高目标,是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对主体生命状态的领悟与把握,因而,中国诗性文化与人的存在及人的精神深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它主要表达了在审美生存意义上诸种不同的观念与精神。
古代儒家推崇中和之美,所谓“中和”,《中庸》开篇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段解“中和”的话,包含了儒家诗学的全部奥秘。既然“喜怒哀乐”等生命原欲是“天下之大本”,那么,就不应该使之堵塞,于是,儒家美学一方面以诗与乐来作为疏导人性的渠道,另一方面则试图使这种渠道规范化,使之“温柔敦厚”而不再有任何破坏性。所谓“发而皆中节”的“和”与“达道”,也就是怎样“发礼节情”、“以道制欲”,达到“发于情、止乎礼义”的境界。而这种境界的实现,正是孔子所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过程。这是一个以艺术的作用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审美实践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经理性、再到感性的过程,它的最后阶段是跨入审美自觉的领域。同“兴于诗”相比,“成于乐”更加强调道德修养在审美中的完成。这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与最高的审美境界的统一,这也就是儒家美学所追求的最高的人生境界。有学者曾总结道:“美的本质:理义;美的形态:中和;美的功能:成德。这就是儒家美学体系的主体结构。从一般美学理论的高度思考这个体系,就会发现:儒家始终是围绕社会理性与个体感性的关系来思考审美问题。”(注: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73~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总之,从建立社会理性与个体感性完满和谐的理想,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去阐释诗与美的本质,这种观念和理论即使在今天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与儒家美学体现的伦理智慧不同,道家美学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自然”智慧。道家的审美理想为“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并不是说“道”之上还有“自然”,而是说“道”之法就是“自然”,就在于“自然”。这样,“自然”就作为道的根本法则、根本性质确定下来了。它既包括无为、无情、无我等一切天地之德,也包括“自然平淡”。所以,道家美学所强调的正是让个人在自然中消融了己身,导向一种随顺自然的静态诗学,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即让个人在不脱离感性的超越中达到自身的永恒不朽,这就是一种审美的境界。由此可见,在道家的“诗学”体系中,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思维是一种智慧,崇尚自然,与道同一也是一种智慧;超越自然,淡化主观情感,达到“虚静”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智慧,“逍遥游”式的自由洒脱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智慧。总之,道家诗学所表现的“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表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毋宁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态度,这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辉,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注:李泽厚:《美的历程》,28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它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虽然都有诗化倾向,虽然都超形质而重精神,弃经世致用而倡逍遥抱一,离尘世而取内心,追求玄远的绝对,否弃资生的相对,企求以无限来设定有限,以此解决无限与有限的对立,但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浪漫精神不重意志,不重渴求,不讲消灭原则的反讽,而是重人的灵性、灵气,温而能厉,威而不猛,恭而能安。中国浪漫精神所讲的综合就不像德国浪漫精神所讲的综合那样;实际上是以主体一方吃掉客体(对象)一方,而是以主体的虚怀应和客体的虚无。(注:刘小枫:《诗化哲学》,76~77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美学所体现的诗性智慧与精神,其整体形态基本上是一个由气、道、元、心结构而成的生命境界。所以,艺术(诗)生命化是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核心所在,它从生命的本体层面上深入揭示了美的内在本性,不仅滋生出中国古代美学关于形神兼备、神韵、境界等大量概念与范畴,而且也对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以宗白华为代表的生命美学这一中国化美学本体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在今日,对思考和建立中国当代美学的本体理论来说,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
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西方美学对美的本体问题的理论思考中,一些重要的哲人和美学家十分重视从“诗性”与“诗化”的概念入手来思考美的基本问题,他们普遍推崇思与诗的对话与融合,借用诗的本性与方式来诠释美学与艺术的本体性质问题,以寻求美的真正本源与根基。如卡西尔指出过“把哲学诗化”或者“把诗哲学化”的问题,海德格尔把诗意之思上升为存在之思,认为传统哲学已经终结,思想成为诗人的使命。思想的诗人与诗意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伽达默尔在哲学中首先讨论“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凡此种种,均表明了当代哲人从诗性角度对美的本体内涵的不断追问的理论意向。而海德格尔对思与诗内在关系的理解,尤其富有理论启发性。
美学是一门人文性的思考学科,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真正的思应从存在出发,去思存在(应思的东西),这是人的天命,思要完成这一使命,就需要与诗结缘,因为,在思的源头,思与诗是结合在一起的。“思必须在存在之谜上去诗化,诗化才把早被思过的东西带到思者的近处”(注:转引刘小枫《诗化哲学》,23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海德格尔如此重视思与诗的关系,重视真理与诗的内在关联性,这对理解美学思的根基和人文性质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指出,“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的,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注:海德格尔:《林中路》,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在其本质上就是一个本源: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理历史性的生成的突出方式”(注:海德格尔:《林中路》,58~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联系海氏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系统论述,艺术与诗的根基及本质含义是:艺术和诗与人类的生命存在有着极为特殊的关联,它所表征的是人的本质存在和对人类的生命感性体验的状态。诗性文化与诗性精神的重要,正在于它密切关联着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关联着人的生存意义的自由表达和“真理”的“敞开”,关联着人类深层精神领域中的某些深邃的心灵感受和生命体验,因而也具有某种神圣而深刻的性质和品格。诗性文化之所以神圣,正在于它能够让人从游戏般的娱乐中提取出一种生命意义,体验和领悟“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真实含义;而诗性文化之所以深刻,也正在于它能敞开真理,剥离生存假相,真实展示人类生存的整体图景。由此可见,美学学科所要思考的存在,正是艺术尤其是诗所要追问的生命本体的存在状况。海德格尔之所以要努力地使哲学变成诗,在于改变近代以来由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泛化所造成的生存的真实性与意义被不断地遮蔽和悬搁的状况,以拯救已不再“思”的形而上学。
这其实正体现了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理论意向:“中国美学不是从天人二分而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不是从理性追问而是从诗性追问的角度,不是从对象性而是从非对象性的角度,不是从思与世界的对话、思与神灵的对话、思与科学的对话而是从思与诗的对话的角度,不是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认识行动、把握方式之一而是从把审美活动作为人类根本性的生命活动、超越性的生命活动的角度,不是从说可说的现实世界而是从说不可说的超越性境界的角度,不是从外在的超验的终极价值而是从内在的超越的终极价值的角度,不是从追问‘有’而是从追问‘无’的角度去考察审美活动”(注:参见潘知常《对审美活动本体论内涵的考察》,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与美学学科的本体内涵。西方当代美学的“诗化”倾向与中国美学“诗性智慧”的内在契合,对当代美学本体理论的发展和建设有重要启示。
一方面,它恰恰说明了,美学之为美学其核心在于美学作为人文学科,必须植根于人类生存的深厚背景之中,必须关注和思考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种种现象,必须追问和透视人类生存的终极根据和内在动机。即海德格尔所坚持的,美学必须思考存在和敞开真理,这才是美学的根基和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美学本体理论建设中轻视或放弃本体根基的倾向已经愈来愈突出,美学学科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精致、美丽的形式符码,美学的完整性和意义深度被不断地分解和切割。面对这种状况,当代中国的美学本体理论建设,需要发掘和继承“诗性智慧”资源,在中国美学诗性精神的范式里获得当代理论发展的潜在价值和积极意义。“诗性智慧”作为中国美学的传统和精神,也许更贴近生存的本相和意义的领域,也许能给无根的美学和形式化的美学,提供一种返本开新的未来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