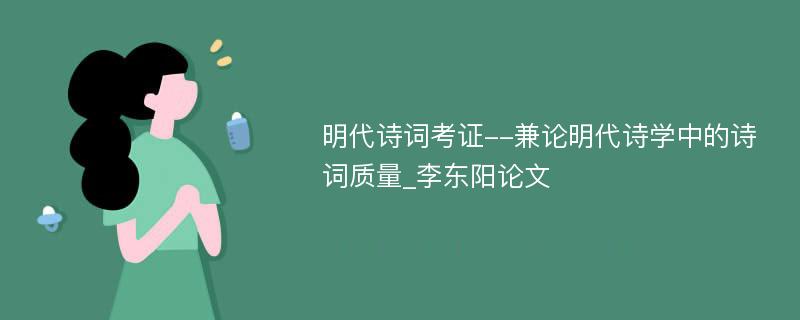
明代歌诗考——兼论明代诗学的歌诗品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诗学论文,的歌论文,品质论文,歌诗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诗与歌唱的伴生关系,经历宋元词曲由歌到诗的演变后而结束,此后诗与歌作为两种艺术形态各自独立发展,诗是用来抒情言志的书面艺术,歌是付诸竹肉的演唱艺术。也就是说明代以后,诗与歌基本上没有了关系。《四库全书》集部词曲类词话属《碧鸡漫志》提要勾勒歌诗之脉络云:“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渐衰,词乃大盛。……迨金元院本既出,并歌词之法亦亡。文士所作,仅能按旧曲平仄,循声填字。自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非复律吕之事。”①皮锡瑞《经学通论》“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可证”条也持同样的观点,云:“古者诗教通行,必无徒诗不入乐者。唐人重诗,伶人所歌,皆当时绝句;宋人重词,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当时之曲。有朝脱稿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词不歌诗,于是宋之诗为徒诗;元歌曲不歌词,于是元之词为徒词;明以后歌南曲,不歌北曲,于是北曲亦为徒曲。今并南曲亦失其传,虽按谱而填,尟有能按节而歌者。如古乐府辞皆入乐,后人拟乐府,则名焉而已。”②他们都认为先前的歌体逐渐与声乐脱离,到了明代歌诗不复存在,清代连南曲的歌法也失传。这种观点代表了清代人普遍的看法,其影响至今。
明以后的歌体除了剧曲外有无歌诗?本文专论这一问题,涉及民间俗曲与文人歌诗。由于民间俗曲的流变情况比较清楚,从略;而对明代文人歌诗,学术界的认识则是一片混沌,因此用较多笔墨进行考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明代歌诗在明代诗学中的格调论以声论诗和性灵说求真入俗问题的地位。
明代民歌的流变情况,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记载甚为清晰:在明初五六十年间盛行的歌曲是元人小令;宣德、正统到弘治以后六十年左右,流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曲;弘治、正德、嘉靖前期几十年间流行起了《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嘉靖、隆庆又兴起了《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钮丝》等曲;万历以后,流行曲又增加了《打枣竿》、《挂枝儿》二曲③。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经冯梦龙搜集整理的《挂枝儿》、《山歌》可见一斑。
歌诗概念出现甚早,从先秦时期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到汉代乐府,再到唐代的曲子词、宋词、元曲,概指可以歌唱的诗④。这样理解,着眼点是我国古代诗与乐之关系,因而“歌诗”是一个名词,特指入乐的诗。本文所言歌诗排除了剧体、曲体、词体,局限于与诵读之诗相对的可歌之诗。明代有无歌诗?任半塘先生的《唐声诗》第八章之“附见唐以后之歌诗”,列举了较多的资料,说宋元明清始终存在着歌诗,只是“唐人歌诗是主流,宋人歌诗已是尾闾”,而宋以后之歌诗更是“流变而已”⑤。在论述明代歌诗时,任先生列举的材料,有李东阳《麓堂诗话》中“古歌诗之声调节奏”条、朱载堉《醒狮辞》中《诵字令》七言四句、邱齐山《新镌分门定类绮筵雅令》之《杭城四句歌》、王穉登《吴社编》数种。任先生《唐声诗》问世数十年来,唐前歌诗的研究近年来有所起色,而唐以后歌诗研究仍处于沉寂状态。明代关于歌诗的记载不胜枚举,就是李东阳的《麓堂诗话》,除了任先生所举条外,还有多处留下当时歌诗的信息,略举数例:
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祯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声于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闻潘言,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
予所闻者,吴则张亨父,越则王古直仁辅,可称名家。亨父不为人歌,每自歌所为诗,真有手舞足蹈意。仁辅性亦僻,不时得其歌。予值有得意诗,或令歌之,因以验予所作,虽不必能自为歌,往往合律,不待强致,而亦有不容强致者也。
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汉以上古诗弗论,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
篇幅并不大的《麓堂诗话》里保留了这么多关于歌诗的材料,学术界注意到了李东阳诗论的音乐性,但对这种音乐性却没有作进一步追究。此外《李东阳集·诗后稿》卷二《习隐二十首》之八:“晓起遍庭白,夜来闻雪声。疏林缀冰叶,千树开群英。玲珑透远日,拍塞阻闲行。如登梁园台,对客停飞觥。如经山阴道,访友随扬舲。居然城市间,此景何从生?退公日已暝,酒罢还复醒。呼童煮雪水,坐歌诗脾清。慎勿扫我雪,留以待书灯。灯前少年事,老大难为情。”⑥“坐歌”者自然是歌诗,而不会是小曲,否则和诗中情景不能协调。
李东阳是明前期最优秀的诗人,也是复古派由南宋到明代具有承上启下贡献的诗歌理论家,他关于歌诗的论述,自然值得我们重视。歌诗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同样也在李东阳前后其他人诗文集中留下了记载,我们略举数例:
宋濂《棣华堂记》:“子邕位跻法从,为时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辞,子邕幸相率发为声诗,勒成简编,如唐之李又《华萼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献酬之际,时出一二章,歌以侑觞,人闻其诗者,宁不油然而兴起矣乎。”⑦宋濂用“声诗”,而不用歌诗。关于声诗之概念,任半塘先生《唐声诗》第一章《范围与定义》论述甚详,认为声诗是相对于无声诗而言,“歌诗者,殆视‘歌’与‘诗’为二事,分指乐府歌行与普通无声之诗。但乐府歌行中,仍混杂许多拟古之作,当时已不歌,未能剔出”。因此“以声诗为准而通校之,则诵诗不如吟诗,吟诗不如歌诗,歌诗不如乐诗,乐诗不如声诗”⑧。也就是说歌诗的概念有时还泛指诗歌,而声诗的概念则确指入乐之诗。宋濂此处用“声诗”,并说“歌以侑觞,人闻其诗者”,既歌且闻当然不是无声之诗,也不是诵读之诗。宋濂的《送方生还四明诗》,前有小序云:“晚得天台方生孝孺,其为人也,凝重而不迁于物,颕锐有以烛诸理,间发为文,如水涌而山出,喧啾百鸟之中见此孤凤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别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悬灯默坐,因发于声诗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来字者,冀负笈重至,以迄于有成也。”十四章之间以“解”断开,如第一解:“北风何逶迤,雪花大于手,之子有远役,忍劝尊中酒。”第二解:“念子初来时,才思若茧丝,抽之已见绪,染就五色衣。”⑨十四解全部是齐言的歌体。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五《陈母伊安人寿序》,说翰林侍讲陈敬宗之母八十三岁寿诞,“敬宗欣欣然”,捧觞趋拜,并“与其朋友相聚宴乐,而宾客亦皆乐敬宗有母之乐也,相与分题为庆寿之诗。”“客之为诗者十,序诗者一。于是敬宗寓其简以归,将使其子弟日歌诗侑觞,以祝寿嘏,又使读诗者,因序以知夫寿之有本也。”⑩陈敬宗为母祝寿,参与宴会者之庆寿之诗,部分可选为歌诗。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十《故礼部右侍郎吾公神道碑》称颂碑主:“公三佐宗伯,一佐司寇……持己以正,不阿谄,不琐细严刻,任性率直,于人长短,一无所较。会宾客故旧,剧饮尽醉,或脱帽抚掌,歌诗以为娱,或纵意谈笑,以戏谑为乐,若甚放旷,而其中亦有止节。”(11)这里的歌诗显然是一种娱乐方式,应该指的是唱诗,而不是一般的咏诗。
王直《抑庵文集》卷五《刘仲高挽诗序》称赞其友“读书有材艺,其襟度夷旷,而神气充悦”。作者后连丁内外艰,“仲高数过予相慰藉,意甚厚。及服除,则又数来与予游,或邀止其家,弹琴弈棋,饮酒歌诗,相得益欢甚”(12)。此处的歌诗也是一种可以和弹琴、弈棋并列的娱乐方式,指唱诗而非吟诗。
陈献章《陈白沙集》卷二有《梦游衡山》一诗,完整的诗题为《梦游衡山,遇南极数老人,来过却须先生作主,与诸老对酌,洪崖、寿崖在旁歌诗以侑觞,合坐皆喜,予以诗一首识兴》,诗云:“衡岳去天能几何,一株松下月明多。南极老仙骑鹿过,一瓢斟月两崖歌。”(13)从梦境中参与聚会的人和场合看,洪崖、寿崖自然不是娱乐圈里的歌者,他们所歌也不是流行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类,而是可歌之诗。
胡彦升《乐律表微》卷四录冯班《古今乐府论》:“今太常乐府,其文用诗。余尚及闻前辈有歌绝句者,三十年来亦绝矣!宋人长短句今亦不能歌,然嘉靖中善胡琴者犹能弹宋词。至于今则元人北词亦不知矣,南词亦渐失本调矣。乐其亡乎?今按古乐久失其传,唐宋诗词及元曲歌法纵令至今尚存,亦不足以存古乐之遗声,然语其大概,则唐宋声歌犹未为大失,而以一字一声拟古者,直谓之念曲叫曲可也。”(14)冯班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卒于康熙十年(1671),这一条材料记录了明代后期及清初歌诗的信息,嘉靖时期善胡琴者能弹奏宋词,明末尚在歌绝句,清初太常乐府则用诗。
明代的诗文别集中类似的材料很多,不一一列举。以上引述旨在于证明明代数百年间始终有一种不同于南北曲、俗曲的歌诗活跃于社会生活中,这与清代以来关于明代诗乐分离的认识不同。
歌诗在宋元已经边缘化了,从逻辑上讲到了明代只能是强弩之末,奄奄待毙。但是事实恐非如此。明代社会为歌诗提供了休养生息之地,厥然而醒,虽不至于跃居为一代艺术主流,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非常活跃,是文人士夫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明王朝从建鼎之初就在营造一种重造乾坤、再现汉唐盛世的复古气氛,政治、军事、文化机制效仿汉、唐,思想上尊奉程朱理学,与此相应的是意识形态各个方面无不崇尚复古,其中乐与诗受到了明代帝王超乎寻常的关注。《明史·乐志一》云:“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釐定。”朱元璋十分重视明代雅乐的建设,金陵甫克,即设典乐官,“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第二年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朱元璋还亲击石磬,与乐官一起分辨五音。于歌诗,朱元璋也有具体指示:“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诗,章淫以夸。故一切谀词艳曲皆弃不取。”永乐时更定宴飨乐舞;代宗时“敕命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和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如古《灵台》、《辟雍》、《清庙》、《湛露》之音,以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弘治时曾动议选精通乐艺者诣京师;嘉靖帝排廷议,定“大礼”,以制作礼乐自任,亲制乐章,命太常协于乐谱。
明王朝历代君主对制礼作乐的重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遗留下来的礼乐混乱,也是歌诗悄然兴起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召学士朱升检校乐舞,朱升审音的水平竟不如朱元璋,不辨宫徵之别。“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永乐时宴飨乐舞“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弘治皇帝“亲耕耤田,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出狎语”。尽管历代皇帝如此重视,而终明之世,音乐难达古雅,“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灿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15)。“雅俗杂出”既不能满足朝廷庙堂之用,也不能满足文人士夫的审美需求,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古雅乐不传,俗乐又不足听。今所闻者,惟一派《中和乐》耳。因忆诗家声韵,纵不能仿佛赓歌之美,亦安得庶几一代之乐哉!”(16)《中和乐》是明代的圜丘迎神曲。圜丘,是帝王冬至祭天地的场所。圜者,象天圜也。迎神曲句式有齐言、骚体两种,齐言如:“坤德博厚,物资以生。承天时行,光大且宁。穆穆皇祗,功化顺成。来御方丘,严恭奉迎。”骚体如:“昊天苍兮穹隆,广覆焘兮庞洪。建圜丘兮国之阳,合众神兮来临之同。念蝼蚁兮微衷,莫自期兮感通。思神来兮金玉其容,驭龙鸾兮乘云驾风。顾南郊兮昭格,望至尊兮崇崇。”(17)这样一种乐歌及乐曲成了当时很流行的雅乐,无怪乎李东阳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复古是既定的目标,但是汉唐的声乐难于寻觅,于是企望通过“诗家声韵”体会“赓歌之美”,建立“一代之乐”。而“一代之乐”的设想就是与歌诗相符称而接近于汉乐府音乐和唐代燕乐的音乐体系。
李东阳的议论自然不会是异想天开,而是明前期很多人文学艺术实践后的理论表述,也是李东阳自己的文学实践的依据。李东阳曾经创作《拟古乐府》二卷101首、《长沙竹枝歌》10首、《茶陵竹枝歌》10首,大概都是为唱而写的歌诗。《麓堂诗话》多次提到张泰(字亨父)、王佐(字仁辅,自号古直,以号行)善歌,张不为人歌,而王则不时得其歌,云:“予值有得意诗,或令歌之,因以验予所作,虽不必能自为歌,往往合律。”(18)李东阳请王佐所歌之诗最有可能的是这些歌体诗。另胡缵宗有《拟涯翁拟古乐府》二卷、《拟汉乐府》八卷,“于千年以外求汉乐府之音节”(19)。这种诗乐实践,其辞的部分被后人当作诗来对待,而乐的部分则完全淡出了后人的视线。
当时所歌之诗大致上有四种情况:一是《诗经》、汉乐府。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古诗歌之声调节奏,不传久矣。比尝听人歌《关雎》、《鹿鸣》诸诗,不过以四字平引为长声,无甚高下缓急之节。意古之人不徒尔也。”(20)叶春及《石洞集》卷七《社学篇》叙述社学每天的课业,说到学生下午的功课有歌诗一门,所歌之诗有《诗经》的《鹿鸣》、《菁莪》、《关雎》、《四牡》、《伐木》、《棠棣》、《蓼莪》、《采繁》、《采苹》、《南山》、《有台》、《缁衣》、《淇奥》,“抑诸篇有关系可歌者各一篇,或古体、律诗、绝句,情性正、音律和者各二篇”(21)。一是句中或句尾带兮的诗,如杨荣《送黄大尹之庐江》:“君世家兮江之西,联簪缨兮绍弓箕,学有得兮才有为,名所传兮人所知,乃膺荐兮官贵池,欲与聚兮恶勿施,抚鳏独兮恤孤嫠,风礼让兮弦歌诗,徭役均兮耕牧时,桑柘茂兮蚕绩宜,饥得食兮寒得衣,吏不见兮犬生牦,嗟古之人兮畴与齐,召父杜母兮应可期。”(22)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二十七《宾山楼诗序》附载的《肃宾之歌》:“层楼兮两扉,君之来兮委蛇。洁吾席兮修我仪,我延君兮君勿辞。迎君兮朝霏,送君兮夕晖。君不我兮遐弃,淡终日兮忘归。”《代宾答》:“风檐兮露闼,昼筵兮夜榻。我之来兮莫予或遏,礼我兮燕我,楼之中兮席之左,朝荣兮夕悴,谁定其交兮,其宁以我为可。”(23)祝允明《芝庭记》结尾处“永之以歌诗”,其词曰:“烨神蕤兮翘吾庭,粲吾嗣兮协厥灵,友黄绮兮采岩垧,粲者起兮甘泉九茎,芝兮芝兮绵修龄。”(24)这些歌诗与庙堂上用的乐曲相同,并与《史记·高祖本纪》、《乐记》、《赵世家》与《汉书·艺文志》所记楚歌体相同。一种是长短句的诗。《怀麓堂集》卷三题目即为“长短句”,其中的诗目多为歌体,如《捕鱼图歌》、《答罗明仲草书歌》、《寿岂堂歌》、《北原牧唱》、《送王公济归武昌歌》等。还有一种是句型整齐且词义明白的诗。吴与弼《舟中听诸生歌诗》:“行李宁家已有期,云帆更喜夜风吹,诸生各有平安庆,促膝闻歌往复诗。”(25)李梦阳《梅山先生墓志铭》录鲍梅山《灯花诗》:“秋灯何太喜。一焰发三葩。拟报明朝信,应先此夜花。重重辉绛玉,朵朵艳丹霞。爱尔真忘寐,闻蛩忽忆家。”(26)
明代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诗音乐和歌唱方法不清楚,是后人无视这种艺术现象的根本所在,但是我们仍可从零散的记载中发现蛛丝马迹。刘基《竹川上人集韵序》云:“昔邵子以音声穷天地事物之变,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没,虽有书,不得其传,故有能言而莫精其义者,则于声之轻重、清浊且不能辨,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来杭时,识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坛寺,见其为歌诗,清越有理致。遂相与往来,因语及声音之学,而出其所为书,则集凡天下之音声,比其开发收闭之类,而各使相从,凡有声而无字者,咸切而注之,审音以知字,因母以识子,如指其掌也。”(27)竹川上人善歌诗,精音律,使刘基非常赞赏。“清越有理致”,形容其歌诗声乐上的特点,较之《中和乐》有个性。竹川的音律造诣,表现为“审音以知字,因母以识子”,也就是音乐之声与字之音二而合一。这里反映的是明初人在成就“一代之乐”的问题上共同的思路。程敏政《诗坛丛韵序》所序作者为滁阳吴孟章。程敏政称赞其人:“虽世将家,而博雅好文,喜为歌诗。”因歌诗而研究音韵之学,积十余年写成《诗坛丛韵》一书,其研究方法是寻求音乐之律吕与歌诗之声韵的契合。程敏政接着补叙了吴氏研究音律学的背景:“我高庙当南北混一之初,首命儒臣为《洪武正韵》,以一五方之音,祛旧习之陋,嘉惠天下,以求复乎虞廷诗歌声律之制,万世之功也。我文庙入继大统,亦首召天下儒生,为《永乐大典》,其法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凡有涉于兴观群怨之旨,可以为博闻洽物之助者,囊括几尽,亦近古所未有也。”可见明初音律学从钦定到个人研究,其思路大体一致。
李东阳关于歌诗唱法的记载更加具体,云:“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20)前提及《麓堂诗话》“古诗歌之声调节奏”一条,说明当时的发声方法“以四字平引为长声,无甚高下缓急之节”。具体到各地域,“惟吴、越有歌,吴歌清而婉,越歌长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
后七子的开山者谢榛善歌,同时也善诗,以两栖的行家身份发表了关于歌诗声韵与歌唱抑扬关系的体会。其《诗家直说》第三十四条云:
予一夕过林太史贞恒馆,留酌。因谈诗法:妙在平仄四声,而清浊抑扬之分。试以“东”、“董”、“栋”、“笃”四声调之,“东”字平平直起,气舒且长,其声扬也;“董”字上转,气咽促,然易尽,其声抑也;“栋”字去而悠远,气振愈高,其声扬也;“笃”字下入而疾,气收斩然,其声抑也。夫四声抑扬,不失疾徐之节,惟歌诗者能之。……安得姑苏邹伦者,樽前一歌,合以金石,和以琴瑟,宛乎清庙之乐,与子按拍赏音,同饮巨觥而不辞也。
诗的四声与歌的抑扬相关,其中的美妙只有能歌者才能表现出来。姑苏邹伦歌诗时,还有金石琴瑟伴奏,其音乐效果很雅,谢榛形容为“清庙之乐”。第三十五条云:
夫平仄以成句,抑扬以合调。扬多抑少则调匀;抑多扬少则调促。若杜常《华清宫》诗:“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上句二入声,抑扬相称,歌则为中和调矣。王昌龄《长信秋词》:“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上句四入声相接,抑之太过;下句一入声,歌则疾徐有节矣。刘禹锡《再过玄都观》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句四去声相接,扬之又扬,歌则太硬;下句平稳。此一绝二十六字皆扬,惟“百亩”二字是抑。又观《竹枝词》所序,以知音自负,何独忽于此邪?
谢榛列举的这些唐诗在当时都是入乐的,显然在明代也可以歌唱。谢榛把诗的四声与歌的抑扬放在一起考察,当然是在指导诗歌写作如何合调,如何控制抑扬疾徐。第三十六条云:
杜牧之《开元寺水阁》诗云:“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声,韵短调促,而无抑扬之妙。因易为“深秋帘幕千家月,静夜楼台一笛风。”乃示歌诗者,以予为知音否邪?(29)
为别人改诗,一字之别,境界全出,诗歌史上时有这样的佳话,但是谢榛改诗,则全从歌唱的疾徐出发,与明代歌诗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明代歌诗是学术界一个盲区,如果我们改换思维,确立了明代歌诗的意识,像李东阳、谢榛这样的资料为数甚伙。
明代的歌诗有很强的工具作用,首先是“颂”。任何时代,只要自诩是盛世,都不免示意文人墨客歌功颂德。由明代元,结束了草原民族对华夏的粗犷统治,休养生息,藏富于民,普及教育,恢复传统,以理学整饬风俗等一系列国策大见成效。一时间“朝廷务导扬恩意,歌功颂德,推序勋阀,以昭明文物”。而文人紧随其后,“乘维新之运,以雄辞巨笔,出而敷张神藻,润饰洪业,铿乎有声,炳乎有光,耸世德于汉唐之上,使郡国闻之知朝廷之大,四夷闻之知中国之尊,后世闻之知今日之盛”(30)。大约一个世纪间,颂声一片。人际交往中,迎来送往,挽悼叙志,称寿记传,以颂为主。张宁《松溪處士挽词引》说:“松溪陈处士没,其外孙嘉兴府学生王论博求士大夫歌诗以表扬之,征予为之引。”(31)康海《张舜卿东征诗序》为表彰张舜卿帅军东征大捷而归,“缙绅大夫闻者皆为歌诗,以嘉舜卿之绩命,曰东征大捷诗。”(32)沈炼《送常州焦别驾考绩歌诗序》是一篇关于明代歌诗的珍贵文献,略云:
常别驾焦公,将以考绩上天官,而郡邑之士大夫为歌诗赠之,宜兴进士汤君属其事于余为序。
余入境,观常之风俗,又读诸大夫之歌诗,而知公之绩遒美矣。昔者商周之际,乘轩车而仕者,其时冠裳皆有成纪;长贰参辅,皆有成职;金谷师宾,皆有成度;岁月旬时,咸有成要。君子率皆守职,因循奉宪……于是乎有街衢之谣,舆校之颂,于其往来征行之际,又有大夫士赠送之什,于是诸侯陈之天子采之,而百官之令绩章焉。
公之参于常,见诸守,其摄于宜兴也,无所改于其令,而大夫士之颂美咸辑焉,知其不言而入于民之心者深也。夫也者,假丝缕为言也,考者征诸其实行也,故官师之绩,譬如丝缕,然日积于民心,然后为绩,乃若稽时日之程,累米盐之数,钩朱墨之故,计胥吏之言,此具文矣乎,不可以征焉者也。然则何征?征诸其歌诗已矣。夫民心之蕴积,动而为咨嗟,形而为颂美,发而为歌诗,传而为金石,乃今观诸士大夫之歌诗,洋洋乎,济济乎,皆嘉树之咏羔羊之风义,声仁泽流,被乎篇籍。夫令誉不率成,美言不虚袭,众好不佞得,嘉礼不妄招,然则公之令绩不懋著矣乎!公为政之年,无所受,独受诸大夫之歌诗。呜呼!此其为歌诗征矣。(33)
此文的典型意义,它本身是“颂”的结晶。一个官员主政一方,离开时,当地的官绅士人感戴其政绩,写诗作歌,表达谢忱,再把这类歌诗经过编辑,请一名人作序。此文还透露了明代对商周秦汉的观风、采诗、陈诗旧制追摹的文化背景,企图通过这种制度,充分发挥歌诗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明代人看来,诗歌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是观政采风体制缺失造成的。李东阳《赤城诗集序》感慨“诗之为物也,大则关气运,小则因土俗,而实本乎人之心者”,但“自乐官不以其诗为教,使者不以采诗为职,是物也,若未始为天下之重轻而所关者,固在也。”(34)认可这种古老的体制,甚而效仿这种做法也在明前期偶然出现过,《明史·西域四》说德文“采诸方风俗,作为歌诗以献,帝嘉之,擢佥都御史”。(35)《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一《明故丹邱先生姚公墓志铭》,叙姚绶解官后,“作为歌诗,列于管弦,裨化陈风。”(36)可见明代的歌诗也在发挥“风”的作用。
其次,是教化。明代以理学治国,明前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教味都很重。文学是以形象表现倾向性的,但是明代各种文体充斥了忠孝节义、纲常名教的演说。诗歌如前所述,过分重视诗为六经中一教,过分留恋采风陈诗的旧制,都会导致政教功用被放大、强化。歌诗通俗、易于传播的特征,促使当时人们对歌诗的教化作用特别重视。贺钦曾就宴会歌诗的作用说道:“今人于宴会若制为歌诗,辞语明白,不必文饰,令左右人歌之。或父子骨肉间,则说孝慈;或同僚之间,则说彼此劝勉,莫忘公务;或言饮,不可过多;或言醉后威仪,言语当谨慎;或以古之清廉者为劝,或以贪污者为戒,使人于晏乐之时不忘警惧之意,则亦大有益也。”(37)宴会时佐以歌诗,本来是为了娱乐,但是娱乐不忘教化。甚至与娱乐无关的撰作,也要和教化联系在一起,如王磐撰《野菜谱》,“所记野菜凡六十种,题下有注,注后系以诗歌,又各绘图于其下,其诗歌多寓规戒,似谣,似谚,颇古质可诵”(38)。说明性的著述,也要附着教化性的歌诗,既便于记诵,又能在“多识草木之名”的同时,也受到教育。利用歌诗进行教化是明代很有特色的教育行为。崔铣记载当时童子之学,云:“其行:爱亲、敬长、事师;其役:洒扫应对;其艺:习礼、诵书、学字、歌诗。”(39)接着又介绍各种课程进行的时间,歌诗一项安排在日中,“令群立歌诗,一人倡之,众乃和之。诗用《孝顺》三十章及邵子《子养亲》六章,渐进之《二南》及《鹿鸣》”。歌诗教育针对少年儿童“喜呼呶而少舒徐,乐佻达而少雍逊”而设置,通过歌诗“可以泄其呼呶而移之祥定”。这种理念也反映在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中,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云:“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王守仁《教约》还规定歌诗时要注意的精神状态:“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40)少年时的歌诗训练,既有适应其年龄特征,疏导其性情,并进行教化的作用,也是诗的语言、节奏、声音等方面的学习过程。这样,歌诗训练在受教育者成年后的人际交往中轻车熟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影响着明诗的语言风貌。
其三,娱乐。明代的娱乐方式是比较多的,如戏曲、说话等方兴未艾,是社会各层次都喜欢的文艺形式。而把歌诗作为一种娱乐的范围很小,娱乐群体主要局限于文人士夫,娱乐场合主要是文人士夫的祝寿送别聚会饮酒。因此歌诗在明代不再像《诗经》、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那样,是一个时代的娱乐主体,而是一小部分人的风雅之事,是文人士夫家庭朋友间的私人性娱乐,甚至是个人排遣孤寂郁闷的一种方式。《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八《陶子沾墓志铭》说陶子沾“穷居一室,杜门自乐,饮酒歌诗,形影相答”(41)。李梦阳《梅山先生墓志铭》记述鲍梅山的生平个性,其中豪酒能歌云:“李子有贵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觞细杯,穷日落月。梅山醉,每据床放歌,厥声悠扬而激烈。已,大笑,觞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欢。李子则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轻梅山,于是则大器重之,相结内,明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贵客,欲其欢,于是多邀梅山。”(42)鲍梅山和客人唱和的自然不是曲而是歌诗,其中可能有鲍梅山和客人自己的诗作。鲍梅山因善饮且善歌,能使宴席气氛热闹活跃,饮者尽兴,而成了陪酒待客的热门人物。歌诗既是人类早年劳动的产物,也是娱乐的产物。娱乐的本质在历代不同歌体中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明代的文人歌诗,虽然它被人际关系中的“颂”声扭曲,它被政教所利用,而娱乐的功能还是存在的。
由于歌诗的实用、易传播的特征,擅长歌诗创作,也是成名的便捷途径之一。后七子的谢榛就是从写作歌诗而走上成名之路。《明史·文苑传三》云:“谢榛,字茂秦,临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43)胡应麟成名的途径与谢榛相似,也是由歌诗闻名里社的。其《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九《石羊生小传》叙述平生,五岁学属对,九岁受书里中师,十三四岁为歌诗,稍稍闻里社中。这里的“歌诗”不排除是一动宾结构,当然所歌之诗是自己的作品。晚明的王襞也是因为善歌而在童年就受到王守仁的青睐,《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处士王东崖先生襞》云:“王襞,字宗顺,号东崖,泰州人,心斋之仲子也。九岁随父至会稽,每遇讲会,先生以童子歌诗,声中金石。阳明问之,知为心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儿也。’令其师事龙溪、绪山,先后留越中几二十年。心斋开讲淮南,先生又相之。心斋没,遂继父讲席。往来各郡,主其敎事。归则扁舟于村落之间,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44)王襞以歌诗起步,后来在其讲学生涯中歌诗仍然是亮点。
明代数百年间雅乐成就十分有限,《明史·乐志一》归结其原因:“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晓其义。是以卒世未能明也。”(45)但是明代以韵统字,以字系事,起声音律吕以尽天下的思路贯彻到诗领域时,则是音乐之律吕与诗歌之声韵二而合一,成为体与用的关系。我们知道以诗求声,或者以声求诗,是典型的汉乐府与唐代歌诗的创作思路,而这也正是明代诗学复古派贯穿始终,格调论成为一代诗学特色的深层背景。
格调的概念能够成为复古派诗学的核心理论,学术界过分夸大了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的作用。《沧浪诗话》的核心理论之一即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的诗法论。其诗法论中的“格力”“音节”即是格调说的前奏。郭绍虞校释本引陶明浚《诗说杂记》解释严羽的诗法论特别形象:“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把音节落实到言语,而不是音律与声韵,准确地抓住了严羽音节论的语意,显然严羽已经认同了歌诗方法的失传,只就诵读之诗而论。因此严羽的“体制”、“格力”、“音节”与明代李东阳提出的“格调”有联系,但有根本差异。《麓堂诗话》云:“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无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46)袁震宇、刘明今的《明代文学批评史》说“眼主格,格指诗的体格;耳主声,声指诗的声调,合而言之即为格调”(47),准确指出了李东阳之“调”乃可歌之声,而非诵读之音节。因此,李东阳以声论诗的格调说不是来源于严羽,而是吸纳了当时流行的歌诗资源,是一具有创造性的诗学范畴。
李东阳以声论诗,说到底是在讲诗与乐如何二而合一的问题,与明代的音乐和声韵理念建立了逻辑上的同构关系。《麓堂诗话》第一条在全文中具有纲领作用,云:“诗在六艺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这一段话概述诗在声音上的三种层次:六艺中之乐、诗与声和、诗乐判而为二。“排偶之为文”不能称之为诗教,人声与乐声之和,是为诗,乐教变而为诗教。如何实现“声之和者”?李东阳提出了“往复讽咏,久而自得”的观点。云:“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今泥古诗之成声,平侧短长,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若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48)通过“往复讽咏”,揣摩乐府诗播之律吕的声韵之美,达到歌与诗的相得益彰。《麓堂诗话》全文围绕着“取其声之和者”,回归诗教的宗旨展开。对此潘德舆批评道:“诗与乐相为表里,是一是二。李西涯以诗为六艺之乐,是专于声韵求诗,而使诗与乐混者也。夫诗为乐心,而诗实非乐。若于作诗便求乐声,则以末汩本,而心不一,必至字字句句,平侧清浊,亦相依仿,而诗化为词矣。”(49)潘德舆一方面领会了李东阳诗学的肯綮之处,另一方面认为李东阳以诗求乐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还会“以末汩本”。任半塘先生反驳道:“按原则诗与乐必相表里,大处互准,而小处则声可就辞。不能谓歌辞之凡由声定辞者,便是‘以末汩本’。声,非末也;相表里,非相汩没也。心之求一,在于求诗与声之体用相宣,而不在于一心主文,求体不求用也。”(50)“体用相宣”,正是李东阳以声论诗的关键,因此他说:“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51)
李东阳以声论诗,以乐论诗,具有明代特征的诗学从此确立。之后,复古派的诗学不同程度都存在着这一倾向。李梦阳论诗,过去我们比较关注其情遇、模拟、尊汉魏盛唐贬宋元等观点,而以声乐论诗则一直没有得到注意,其《缶音序》就是以声论诗的纲领性文章,云: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必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扬唐贬宋,而支撑这一观点的根据是唐代虽古调亡,但是有唐调,因此诗仍可歌,入律吕。唐调,也就是燕乐。宋代的诗是诵读的,不再追求声音的香色流动。李梦阳认为,是否可歌,是否入乐,是唐宋诗高下之关键因素。李梦阳《与徐氏论文书》中说他与徐祯卿的遇合:“仆西鄙人也,无所知识,顾独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忧。”明代吴、越人善歌,李梦阳生在西北,没有歌诗的环境,只得独自歌吟,而得知徐祯卿以吴人“少而善歌吟而有异才”,更渴望与徐结交,歌诗成了他们交好的连接点。李梦阳虽然自己不以善歌名,但是他的夫人左氏善抚琴。不幸左氏42岁亡故,祭奠时有异象,李梦阳写了《结肠》之作,抒发自己的肠断之情。后来京口人李鳌把这篇作品写成琴谱,鸣之以琴,李梦阳又撰写了《结肠操谱序》。这是一篇关于诗与乐的重要理论文章,但至今各种诗学论著没有充分关注。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在说诗的声韵与音乐调的关系。李梦阳说自己写作《结肠》之选音达情:“曩予有内之丧,亲睹厥异,伤焉警焉,吟焉永焉,于是援笔而布辞,疏卤荒鄙之音,聊世愤愤、闷闷、汶汶焉耳”。陈鳌“始鸣之琴也,泛弦流徽,其声噍以杀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五音,黯以伤也,知其音商也。已而申奏摛节,其声谌谌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雊于朝,鹤鸣在阴。其余音则飒飒然,若欲诉而咽,已吐而中结也,斯楚之遗些也”。陈鳌的琴曲用的是商调,其声“噍以杀也”,产生的抒情效果较之诗有升华之功。李梦阳深受感触,云:“予为是篇也,长歌当哭焉矣。知其思索,以悲忉别怲,离若逐臣怀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知其些之犹楚也;知其情萧焉瑟焉,若回风陨叶,寒蝉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抒哀焉已矣,而不知其声噍以杀也。”(52)琴曲中表现出来的“楚之遗些”与自己妻亡后的悲痛迷茫,“然不知其些之犹楚也”的感情若何符契。由此,李梦阳得出“是故声非琴不彰,音非声何扬”的结论,这与他判断唐宋诗之高下的思路是一致的,与李东阳诗和乐“体用相宣”的思路也如出一辙。
何景明与李梦阳关于如何学古有分歧,但是在以声论诗上则是一致的。其批评杜甫七言诗,“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并且改弦易辙,效仿初唐四杰,背后的理论支点也是诗的声韵与音乐合一。因此何景明期待自己的新体“俟审声者裁割”(53)。后七子巨子王世贞关于格调进行了总结,提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的观点(54),音乐之“调”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后世文人由于音乐素养的缺失,歌诗流行范围有限,歌诗对诗学的渗透在逐渐淡出,到了清代沈德潜那里,虽然恪守着格调说的理论框架,对声韵也格外重视,称为大厦之基石,但只落实到了韵脚。
明代诗学第二个创新性理论是性灵说。性灵的诗学概念同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明代人在自己的生态环境下完成了求真、入俗的审美观念,并用真趣、俗趣支撑起性灵说的诗性元神,才使之成为一代诗学之门面。
明代诗歌始终承受着拟古与理学的双重挤压,而民歌是文人诗冲决挤压,寻求内在品质突破的有效参照。台阁体盛行时,杨荣、李东阳都借助民歌来批评当时的文人创作。杨荣以“真趣”批评时风:“世之为诗者务为新巧,而风韵愈凡;务为高古,而气格愈下。曾不若昔时闾巷小夫女子之为,岂非天趣之真与夫模拟掇拾以为能者,固自有高下哉!”(55)李东阳比较文人诗与民歌曰:“彼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而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穷老至壮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56)民歌的“天真之趣”、“真情实意”进入诗学批评,给规模肤廓,气韵呆板的盛世文学吹入了一缕清风,也透露出明代人创造自己诗学本位的方向。
复古派诗学与时代的沟通,一是通过以声论诗,构建了格调说;一是吸取民歌真趣的义谛,把真、遇作为诗歌的核心价值。弘治、正德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民歌开始进入“我明一绝”的角色。这时,李梦阳、何景明徙居汴梁,听到《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类,大为惊叹,“以为可继《国风》之后”(57)。李开先在《词谑》中对李、何酷爱民歌有更具体生动的记载:“有学诗于李空同者,自旁郡而之汴省,空同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请问其详,空同告以‘不能悉记也。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越数日,果闻之,喜悦如获重宝,即至空同处谢曰:‘诚如尊教。’何大复继至汴省,亦酷爱之,曰:‘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每唱一遍,则进一杯酒。终席唱数十遍,酒数亦如之,更不及他词而散。”(58)民歌的真实自然使李、何敏锐地把握住了具有时代本体诗学的命脉,他们面临的“第一义”与“情遇”、诗与歌、诗韵与乐律诸种理论困惑迎刃而解。李梦阳晚年在《诗集自序》对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借助的武器也是民歌。其中的民歌音乐的特点、民歌的表现手法、否定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都是依托于真的哲学观念。民歌音乐的特点涉及曲、调、声与诗哪个更真实的问题。王叔武说“今真诗在民间”,而李梦阳则认为民歌“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调靡靡”,存留着金元之声,因此不能称为真。王叔武持“音之发而情之原”的观点,即乐声是最真实自然的,经过了金元胡化后的金元之俗,自然会有金元之声,虽然与当下的雅乐不同,由于其真性决定了它已经超越了雅俗之辨。王叔武的观点与上文引用的《结肠操序》中陈鳌所说的音律“发之情而生之心者也”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共同的思路就是由声音的真来论证“今诗在民间”的结论。李梦阳以声论诗,确立了尊唐贬宋的格调论,又通过对民歌的顶礼膜拜,确立了真实自然的诗学价值。
嘉靖以后,民歌一方面尽展自己的风姿,一方面对正统诗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首先,出现了文人仿民歌体的诗。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说因《山坡羊》、《锁南枝》“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他受一“狂客”的怂恿,仿其体,“命笔改串传歌未当者,积成一百以三,不应弦,令小仆合唱,市井闻之响应”。可惜的是这103首仿民歌诗不经意间竟然散失,又一狂客“坚请目其曲,聆其音”,不得已李开先通过寻找、重写,“补完前数”(59)。再如冯梦龙整理编辑的《挂枝儿》,就有由他改订和仿作的十二首(60),《山歌》中收录冯梦龙、苏子忠、张伯起、傅四等仿作五首(61)。其次,求真的人文精神完全占据了诗学的话语权。李开先搜集整理通俗文学,仿作民歌,并写作了《市井艳词序》、《市井艳词又序》、《市井艳词后序》。从中可知,民歌多“淫艳亵狎”,但这并不妨碍作者的推崇,是因为“语意则直出肺腑,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62)李开先揭示了一种时代信息,即从嘉靖时期始,诗歌价值的真超越了社会伦理的评判,真是这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尺。第三,文人开始对民歌进行搜集整理。万历后期,冯梦龙整理《挂枝儿》、《山歌》,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序山歌》一文,把当时的民歌与《诗经》相提并论,如果不否定《诗经》郑、卫之音为经典,民歌就是今天的郑、卫之音。更有趣的是冯梦龙在真假这个尺度上把民歌中所表现的真实自然和主流社会的虚伪空套进行比较,赋予“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深刻主旨。
民歌与晚明诗学联系最紧密的当属公安派。公安派的诗学可以概括为求真、尚变、入俗,每一点里都能看到民歌的渗入,事实上公安派也在自觉把民歌质素建构到自己诗学之中,袁宏道《叙小修诗》云:
吾谓今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63)
袁中道《游荷叶山记》记载他们兄弟在一起听民歌,“有声自东南来,慷慨悲怨,如叹如哭。即而听之,杂以辘轳之响。……夫人心有感于中而发于外。喜则其声愉,哀则其声凄,女试听夫酸以楚者,忧禾稼也;沉以下者,劳苦极也;忽而疾者,劝以力也。其词俚,其音乱”,感慨道:“真诗果在民间乎!”(64)民歌之真,在于“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而“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正是公安派性灵说的落脚之处。后人评论公安派的诗莽荡粗率,俚俗如莲花落,恐怕正是由于濡染民歌太深导致的面貌。袁宏道《与伯修》书说:“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擘破玉》为诗,故足乐也。”(65)民歌之真趣、俗趣对公安派诗学的理论构建、创作风格的形成,其功之大,不亚于当时的社会思潮。
明代歌诗使用的范围走向两极,文人歌诗主要在部分文人士大夫中,民歌主要在市井民间,都没有构成一代之歌体,但是,它们对明代诗学特色的构成,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个尚未被学术界认识的课题,本文姑且抛砖,祈大家斧正。
注释: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9《集部·词曲类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1826页。
②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54—56页。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中华书局,1997年,第647页。
④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⑤任半塘:《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31页。
⑥李东阳:《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3年,第468页。
⑦宋濂:《宋濂全集·宋学士文集辑补》,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06页。
⑧任半塘:《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21页。
⑨宋濂:《宋濂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961页。
⑩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李时勉:《古廉文集》卷1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王直:《抑庵文集》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陈宪章:《陈宪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516页。
(14)胡彦升:《乐律表微》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张廷玉等:《明史·乐记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1499—1509页。
(16)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7页。
(17)张廷玉:《明史·乐记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1519—1521页。
(18)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7页。
(1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6《集部·别集类存目三·拟汉乐府八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1571页。
(20)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6页。
(21)叶春及:《石洞集》卷7《社学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杨荣:《杨文敏公集》卷7,见沈云龙编《明人文集丛刊》第1期,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正德十年杨氏重刊本,1960年,第324页。
(23)李东阳:《怀麓堂集》卷2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祝允明:《怀星堂集》卷2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吴与弼:《康斋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李梦阳:《空同集》卷4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刘基:《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28)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9页。
(29)李庆立、孙慎之:《诗家直说笺注》,齐鲁书社,1987年,第356—359页。
(30)徐一夔:《始丰稿》卷5《陶尚书文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张宁:《方洲集》卷2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康海:《对山集》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沈炼:《青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93年,第12页。
(34)李东阳:《怀麓堂集》卷2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张廷玉等:《明史》卷332《列传》220《西域四》,中华书局,1987年,第8609页。
(36)黄宗羲:《明文海》第5册,中华书局影印涵芬楼藏钞本,1987年,第4523页。
(37)贺钦:《医闾集》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2《子部·农家类存目》,中华书局,1987年,第855页。
(39)崔铣《洹词》卷7《休集·训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89页。
(41)黄宗羲:《明文海》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4960页。
(42)李梦阳:《空同集》卷4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张廷玉等:《明史》卷287《文苑》3,中华书局,1987年,第7375页。
(44)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处士王东崖先生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39页。
(45)张廷玉等:《明史》卷61《志》37《乐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1499页。
(46)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1页。
(47)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48)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0页。
(49)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4,见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61页。
(50)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页。
(51)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2页。
(52)李梦阳:《空同集》卷5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何景明:《明月篇序》,见蔡景康编《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54)王世贞:《艺苑卮言》,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中,中华书局,1978年,第964页。
(55)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1《逸世遗音集序》,见沈云龙编《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19页。
(56)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
(5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中华书局,1997年,第647页。
(58)李开先:《李开先集·词谑·时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276页。
(59)李开先:《李开先集·闲居集》6《市井艳词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69页。
(60)关德栋:《挂枝儿序》,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61)关德栋:《山歌序》,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0页。
(62)李开先:《李开先集·闲居集》6《市井艳词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69页。
(63)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
(64)袁中道:《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31页。
(65)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