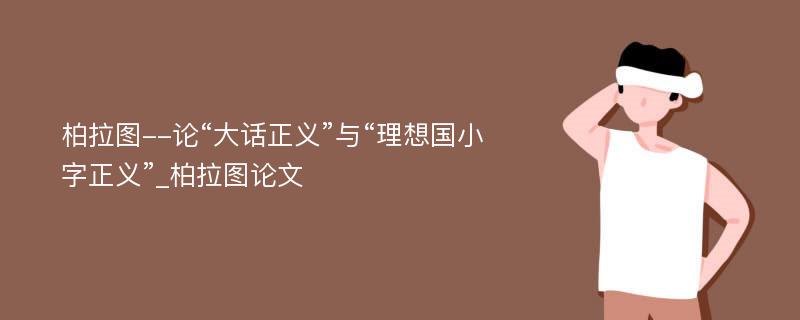
《理想国》中柏拉图论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的一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义论文,柏拉图论文,理想国论文,小字论文,大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0)01-0030-14
1963年,David Sachs发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谬误”(“A Fallacy in Plato's Republic”)一文,在其中,他着力论证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论证的一个根本的逻辑悖谬,即,在《理想国》的最初被提出来并希望得到论证的是一个世俗的正义概念(the vulgar conception of justice),但是,随着这一论证的发展,取而代之的实际上是对一个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the Platonic conception of justice)的论证。前者是关于城邦的社会生活的,后者却是关于个人的灵魂生活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前者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关,后者却仅仅同个人内心各种力量的平衡有关。Sachs在其论证中,不仅具体指出了这两种正义概念的互不相干,而且还扩展地讨论了是否有可能从后一种正义推出前一种正义作为其必然的结果,而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这样,柏拉图《理想国》中正义论证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困难就被以一种分析哲学的方式得到了清晰的揭示。
Sachs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理论反响,而随着论争的展开,在柏拉图正义论证中的城邦和灵魂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自然为研究者们所关注。1973年,Bernard Williams发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和灵魂的类比” (“The Analogy of 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一文,对构成正义论证基础的城邦和灵魂之间的类比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逻辑分析。而分析的结果同样是否定性的,这就是,柏拉图在建立城邦和灵魂之间的类比关系的论证上也存在着基本的逻辑混乱,他混淆了两种关系,即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的基于正义的内涵的类比关系(the analogy of meaning),以及城邦的正义和灵魂的正义的基于整体和部分的类比关系(the whole-part rule)。Williams认为,正是对这两种类比关系的混淆,造成了柏拉图在正义论证上的种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他深入分析了这些漏洞的逻辑困难。
Sachs和Williams的文章自发表以来,便受到学者们广泛的引述和讨论,有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他们的论证的,也有从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出发来针对他们对柏拉图的批评并为柏拉图的论证进行辩护的。我们看到,直至2005年,Terry Penner还在《国际柏拉图协会互联网期刊》(The Interac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to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柏拉图式的正义和我们用‘正义’意指什么”(“Platonic Justice And What We Mean By Justice”),专门针对由Sachs和Williams所挑起的这一问题做了辩护性的回应。① 而我国青年学者吴天岳2009年在东京大学The 3rd BESETO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上发表的一篇会议论文“Rethinking Bernard Williams' Criticism of the City-Soul Analogy in Plato's Republic”,也是就这一问题所做的一个辩护性的回应。② 本文并不打算针对Sachs或Williams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论证,也不打算针对后来的论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进一步的支持或反对的论证。本文仅仅打算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中有关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类比关系的论证和分析来表明如下观点,即:一方面,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的类比关系对于柏拉图来说是成立的,它们是一种严格的内涵一致的关系,也就是说,“正义”的所指在柏拉图那里无论是对于城邦还是对于个人都是完全一致的,从而,在这里,我潜在地既反驳了Williams,也反驳了Sachs;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表明柏拉图有关正义的论证是成功的,相反,由于他所依据的无论是城邦的结构还是灵魂的结构的抽象性,即,它们共同的“正义的”秩序的抽象性,从而,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从对正义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讨论中偏离了出去,他最终所讨论的只是一种抽象的正义,它体现为抽象的城邦秩序,并内化为个体心灵的秩序,由此孳生出来的就是一种抽象的幸福概念,于是,在这里,我又潜在地支持了Sachs和Williams的观点,暗示了实际上的两种正义概念的存在,和作为其论证基础的城邦和个人的分立。同时,在作出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更为明确地指出,内在于柏拉图正义论证中的这些问题所明确显示的柏拉图的一个思想倾向,即柏拉图的宗教主义趋向,本文还试图指出,柏拉图在他的对抽象的灵魂正义的讨论中,以及在一种抽象的内心幸福的论证中,实际上是放弃了现实的社会生活,而逃避到了一种僧侣式的内心安宁的状态中,而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柏拉图主义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来源。
一
在《理想国》的第二卷,柏拉图告诉我们,他将以这样的方式来研究“正义”,这就是,他将首先研究大字的正义,也就是城邦的正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研究小字的正义,也就是个人的正义,看看两者是否一致。③ 很显然,当柏拉图最初预告这一研究顺序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柏拉图在这里预设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基础是什么?这一基础是否足够牢固,以致他能够完满地建立起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有没有在根本立论基础上的某种不严格性造成了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最终的完全互不相干,从而导致柏拉图的整个正义论证归于失败?无疑,这些问题正是在David Sachs1963年的那篇文章“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谬误”中被以明确的方式提出来的,他并且针对柏拉图所使用的正义概念的内涵做了最严格的逻辑分析和检验,而最终的结果对于柏拉图是不利的。这也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所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并且追问在什么意义上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正义就是个人的正义,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一致性。显然,Bernard Williams1973年的那篇文章“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和灵魂的类比”就是对上述问题从一个更为专门的层面所进行的更具分析力度的思考,他的答案同样对于柏拉图是不利的。但无论如何,这更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迫切性,而只有在更深入地研读文本、正确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不仅能够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确立的这一对正义的研究程序作出清楚的理解,同时,也才能够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进行的这一关于正义本身的研究作出更好的认识。
但这样一来,首先应当指出的就是,人们不应当认为柏拉图对这些问题是没有思考的,人们亦不应当认为柏拉图是不假思索地预设了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然后据此来想当然地确定他的研究程序的。在《理想国》的第二卷中,柏拉图初步提出这一研究程序时,人们似乎有理由产生这样的误解和疑问,但是,在更进一步的阅读和理解中,一个可以确立的事实是,柏拉图自己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将它们明确提了出来并加以清楚地说明和论证。
例如,在《理想国》的第四卷开始探讨个人的正义的部分,柏拉图就明确提出了上述问题。他这样说:
我们还不能把这个关于正义的定义就这么最后地定下来。但是如果它在应用于个人时也能被承认为正义的定义,那时我们就承认它。因为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呢?否则我们将另求别的正义。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来做完刚才这个对正义定义的研究工作吧。在这一工作中我们曾假定,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具有正义的大东西并在其中看到了正义,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看出正义在个人身上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曾认为这个大东西就是城邦,并且因而尽我们之所能建立最好的城邦,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好的国家里会有正义。因此,让我们再把在城邦里发现的东西也应用于个人吧。如果两处所看到的是一致的,就行了,如果正义之在个人身上有什么不同,我们将再回到城邦并在那里检验它。把这两处所见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仿佛相互摩擦,很可能擦出火光来,让我们照见了正义,当它这样显露出来时,我们要把它牢记在心。(434D-435A)
很显然,在这段话中,柏拉图不仅明确地表述了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在对正义的研究中具有彼此相关的重要性,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应当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还对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一致性关系提出了详加审查的要求。这就表明,柏拉图不是贸然地建立起所谓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之间的关联的,而是对于它们之间的关联有着清醒而自觉的问题意识的,是在充分考虑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才引入先讨论大写的正义,然后再讨论小写的正义的顺序来对正义进行研究的。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有关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问题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柏拉图都成立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考虑,柏拉图究竟是如何来设想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清楚回答,显然构成了柏拉图整个正义论证能否成立的基础。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我们看到,对正义问题的讨论是从一个似乎非常空泛的人生问题开始的,即,一个人应当如何度过他的一生才是美好的一生。④ 但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个问题被揭示为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生活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一个人在社会中如何生活的问题,从而也就是这个人的社会生活的问题。这样,最初的那个泛泛而谈的人生问题在论辩逻辑的迫使下就被揭示为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它所关涉的不是单个人的生活,而是人们的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从而它与正义问题根本相关。⑤ 潜藏在《理想国》第一卷中的这一逻辑似乎向我们表明,在柏拉图看来,个人的生活是同他在社会中的生活,亦即他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据此,对个人生活的正义的研究应当同对他的社会生活的正义的研究,进而是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正义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这样,个人的正义和社会的正义就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个人的正义就是社会的正义,社会的正义也就是个人的正义。对社会生活中的正义的研究正有助于理解个人的正义,从而最终也将回答为什么一个人只有正义地度过他的一生才是美好的一生的问题。⑥ 这样,至少从《理想国》的第一卷到第二卷的内容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柏拉图究竟是如何来理解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以及他是根据什么来设定首先研究城邦的正义然后再研究个人的正义的研究顺序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被暗示的一致性关系,它还需要更为严格的和理论上的说明。无论是我们还是柏拉图都必须清楚地表明,这种一致性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的一种一致性,它究竟仅仅是一种基于结构相似的一致性,还是有着严格的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内涵上完全的一致性。因为结构相似的一致性至多可以在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造成一种形式上的类比关系,即,两种正义都拥有相似的形式结构,但却不必意味着两者也在正义的根本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⑦ 于是,柏拉图就必须针对构成他的正义论证基础的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明确表明,他所期望和要求的究竟是哪一种意义上的一致性。
在《理想国》的第四卷讨论完城邦的正义之后接下来讨论个人的正义时,柏拉图似乎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答案。他这样说:
苏:那么,如果两个事物有同一名称,一个大一个小,它们也相同呢,还是,虽有同一名称而不相同呢?
格:相同。
苏:那么,如果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也毫无区别吗?
格:是的。
苏:现在,当城邦里的这三种自然的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并且,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他某些情感和性格而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
格:是的。
苏:因此,我的朋友,个人也如此。我们也可以假定个人在自己的灵魂里具有和城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那几种组成部分,并且有理由希望个人因这些与国家里的相同的组成部分的“情感”而得到相同的名称。(435A-C)
假如我们仔细分析这段话,那么,无疑头两句问答向我们清楚地传达出,有关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柏拉图明确意识到的,柏拉图并没有忽略这个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看成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而接下来的两句问答则向我们表明,柏拉图是肯定它们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一致性关系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一关系,因而在研究上采取先研究城邦的正义、然后再研究个人的正义的顺序才是有根据的。但是,很显然,这也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它们两者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一致性关系?我们能否说,城邦的正义就是个人的正义?或者只能说,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仅仅具有一种结构上的类似性,而它们在各自的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显然,当柏拉图说,“如果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也毫无区别”,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不清楚的,从而是需要澄清的。而接下来的最后几句话则似乎向我们仅仅表明的是后一种可能性,即,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仅仅具有结构上的类似性,它们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基于结构的秩序性的正义因此也就是可比的和相似的,因为它们都体现了由于结构本身的和谐秩序的保持而来的一种正义,从而,“就正义的概念而论”,它们是一致的。假如这就解释了柏拉图所说的在“正义的概念”上的一致性,那么,显然,这就是一种不严格意义上的一致性,因为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一致性关系,而不是内涵上的。城邦的正义是城邦的正义,它体现的是城邦自身所固有的秩序,而个人的正义是个人的正义,它体现的是个人灵魂内部所固有的秩序,二者都是秩序,都体现了秩序所固有的和谐,却完全可以是不同的秩序。柏拉图所要求的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的一致性关系,是这样的一种一致性关系吗?
柏拉图接下来的论证也似乎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他接下来的论证似乎关注的正是个人灵魂和城邦之间的一种结构上的类似性,他似乎在全力证明,就像城邦中存在着三个阶层,即求利的农工商阶层、防卫的军人阶层和管理的统治者阶层那样,在灵魂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三个部分,即欲望、激情和理智。于是,就城邦而言,便要求有一种在这三个阶层之间基于统治和被统治的和谐的秩序;同样,就灵魂而言,也要求有一种在这三个部分之间基于统治和被统治的和谐的秩序。尽管它们都是秩序,具有结构和功能上的类似性,但是,却有着可能是不同的秩序,从而在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城邦的秩序将规定和要求生活在城邦中的个人这样或那样生活才是正义的,而灵魂的秩序所要求于个人的正义却可以是与此完全无关的一种单纯的心灵和谐的状态。准此,这似乎也就说明了柏拉图由此可以完全撇开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而通过抽象地讨论个人的内心生活来寻求一种和人们实际的社会生活的幸福完全不同的、仅仅属于内心的幸福,保有内心的一种正义。⑧
我们说,这就是柏拉图接下来讨论个人的基于灵魂内部各种力量的平衡和秩序的正义时有可能向我们暗示的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种仅仅在结构上的类比关系。然而,这却只是一种表面的理解和认识。因为柏拉图在探讨灵魂的构成时一开始所说的一段话,实际上已经向我们明确地表述了灵魂的结构和城邦的结构之间不只是一种仅仅基于结构形式的类似性,而是同时具有在内涵上的严格的一致性关系。我们看到,柏拉图这样说:
因此我们不是很有必要承认,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和城邦里一样的那几种品质和习惯吗?因为除了来自个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须知,假如有人认为,当城邦里出现激情时,它不是来自城邦公民个人……那是荒谬的。其他如城邦里出现热爱智慧这种品质……或贪婪财富这种品质时……也都应该认为这是由于公民个人具有这种品质使然的。(435E-436A)
这段话,尤其是开始的两句,不仅向我们表明了个人灵魂中具有和城邦中相类似的三个部分,从而具有结构上的类似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它们在各自所具有的品质的内涵规定上也是根本一致的,城邦中的三个阶层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实际上具体体现为灵魂中的三个部分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由此,我们当然可以说,城邦中三个阶层的“正义的”秩序也就同样体现为灵魂中三个部分的“正义的”秩序,于是,它们就不仅拥有结构上的类似性,而且还拥有内涵上的类似性。这样,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古人的国家和个人同构的观念相一致(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我们也同样发现了这样的设定),灵魂的秩序不过是城邦的秩序内在于个人的体现,而城邦的秩序不过是灵魂的秩序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反映,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样,柏拉图的这段话就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说明了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的一致性,表明了个人的正义实际上是城邦的正义作为个人的道德品质的体现。
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这种在内涵上的一致性关系,在柏拉图接下来的说明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我们看到,当柏拉图完成了对欲望、激情、理智这三个部分在灵魂中相互独立的论证之后,他便针对个人的智慧、个人的勇敢、个人的节制和个人的正义说道:
那么据此我们不是可以立即得到如下的必然推论吗:个人的智慧和国家的智慧是同一智慧,使个人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和使国家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是同一品质?……我们也可以推论: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是同一勇敢,使个人得到勇敢之名的品质和使国家得到勇敢之名的品质是同一品质,并且在其他所有美德方面个人和国家也都有这种关系。(441C-D)
这段话当然可以被具体理解为是对大字和的正义小字的正义之间的内涵上的一致性关系的一个明确的说明,表明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在根本内涵上是一致的,它们只是同一个正义在个人和城邦那里的具体体现而已。
当然,不只是这样的具体文字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在柏拉图对城邦的勇敢、城邦的节制的论证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已经渗透了对个人灵魂的勇敢和个人灵魂的节制的理解,在那里,并不是像最初表明的论证程序那样,通过理解城邦的勇敢来理解个人的勇敢,以及通过理解城邦的节制来理解个人的节制,而是倒了过来,通过理解个人的节制来理解城邦的节制,通过理解个人的勇敢来理解城邦的勇敢。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
在柏拉图对城邦的节制的论证中,他一开始就这样说,“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430E),在此之后其所展开的并不是对城邦中的节制的分析,而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分析。他说:“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一个较坏的部分,而所谓‘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的控制。……当一个人由于坏的教养或者和坏人交往而使其较好的同时也是较小的那个部分受到较坏的同时也是较大的那个部分统治时,他便要受到谴责而被称为自己的奴隶和没有节制的人了。”(431A-B)显然,这是对个人的节制的分析,它分析了一个人的灵魂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柏拉图对城邦的节制的讨论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他接着上面的分析立即说:“现在来看看我们的新国家吧。你在这里也会看到有这两种情况之一。因为,既然一个人的较好部分统治着他的较坏部分,就可以称他是有节制的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那么你应该承认,我们说这个国家是自己的主人是说得对的。”(431B)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城邦的节制是基于个人的节制而得到理解的,个人的节制和城邦的节制不仅具有结构上的类似性,而且实际上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
在柏拉图对城邦的勇敢的论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城邦的勇敢和个人的勇敢之间的这种不是基于结构的类似性,而是基于内涵的一致性的交互渗透和影响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柏拉图对城邦的勇敢的论证是具体落实到对城邦中的某一部分个人的勇敢的分析上。其次,这一部分个人的勇敢不仅是通过对他们的灵魂中各种力量的抽象的对比关系的分析来表明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柏拉图在对个人的勇敢的反复界定中,不断地运用了“法律”以及“法律的教育”这样的概念来作为中介。例如,他在一开始便这样说:“国家是因自己的某一部分人的勇敢而被说成勇敢的。是因这一部分人具有一种能力,即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他们都保持着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相信他们应当害怕的事情乃是立法者在教育中告诫他们的那些事情以及那一类的事情,这不就是你所说的勇敢吗?”(429C)在这里,勇敢不是一种内心力量例如激情的单纯占据主导地位的表现,相反,勇敢是非常具体的,它具体地体现为实际上是对有关于城邦秩序的法律在个人内心中依照教育的一种保持,这就说明了勇敢者所勇敢保持的不是别的,就是城邦的秩序,一个人灵魂的勇敢在于他对城邦秩序的勇敢地保持。而接下来的一长段话,同样向我们传达了城邦的法律和相关的教育在界定个人的勇敢上的重要地位。柏拉图这样说:
因此,你一定明白,我们挑选战士并给以音乐和体操的教育,这也是在尽力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竭力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要他们像羊毛接受染色一样,最完全地相信并接受我们的法律,使他们的关于可怕事情和另外一些事情的信念都能因为有良好的天性和得到教育培养而牢牢地生根,并且使他们的这种“颜色”不致被快乐这种对人们的信念具有最强褪色能力的碱水所洗褪,也不致被苦恼、害怕和欲望这些比任何别的碱水褪色能力都强的碱水所洗褪。这种精神上的能力,这种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的完全保持,就是我主张称之为勇敢的,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的话。(429E-430B)
在这里,柏拉图谈到了内心中各种力量的对比,谈到了个人的勇敢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精神能力,即它能够保持一种信念不被快乐、苦恼、害怕、欲望等心理力量所战胜,而赋予那种作为勇敢的精神能力以具体内涵的信念不是别的,正是“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是对这种正确信念的完全保持才被称为勇敢。这就明确地向我们表明了,个人的勇敢恰恰体现在对城邦秩序在一个人的内心中的保持,而当它以个人行动的方式在城邦中具体实施出来时,也就体现为城邦的勇敢。
这样,通过上面对柏拉图关于城邦的节制和城邦的勇敢的讨论和分析,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城邦的正义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个人的正义,它是对城邦的正义的作为个人道德品质的体现;而城邦的正义正是有赖于个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以及在自己的具体行动中加以实施才可能得到实现和维护。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当我们再来看柏拉图《理想国》的第四卷稍后部分的这几句话时,其意思不就非常清楚了吗?
苏:个人的正义其形象在我们心目中不是有点模模糊糊,好象它是别的什么,不大像它在国家里显示出来的那个形象吗?
格:我觉得不是这样。
苏:这就对了。(442D)
苏格拉底这个有意的反问和格劳孔斩钉截铁的否认明确地向我们表明,个人的正义正是城邦的正义,它是城邦的正义形象在个人身上的体现。
而接下来苏格拉底采用引入有关城邦的正义的具体例子,来进一步检验前面关于个人的正义的认识是否正确的论述,⑨ 则更进一步向我们具体说明了对于柏拉图而言,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在根本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丝毫不矛盾的。柏拉图这样写道:
苏:这就对了。须知,如果我们心里对这个定义还有什么怀疑存留着的话,那使用一些很平常的事例就可以充分证实我们所说的不谬。
格:你是指什么样的事例呢?
苏:例如假设要我们回答一个关于正义的国家和一个与正义国家有同样先天同样教养的个人的问题,即,我们是否相信这种人——如果把金银财宝交给他管的话——会鲸吞盗用它们,你以为有谁会相信这种人会比不正义的人更像干这种事的呢?
格:没有人会这样相信的。
苏:这样的人也是绝不会渎神、偷窃,在私人关系中出卖朋友在政治生活中背叛祖国的吧?
格:决不会的。
苏:他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不信守誓言或别的协约的。
格:怎么会呢?
苏:这样的人决不会染上通奸、不尊敬父母、不履行宗教义务的罪恶的,尽管有别人犯这种罪恶。
格:他们是决不会的。
苏:这一切的原因不是在于,他心灵的各个部分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着,被领导的被领导着吗?
格:正是这样,别无其他。
苏:那么,除了能使人和国家成为正义人和正义国家的这种品质之外你还要寻找什么别的作为正义吗?
格:说真的,我不想再找了。(442E-443B)
这段对话虽然很长,但却通过具体事实展现了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不冲突,并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具有一种在根本内涵上的一致性关系;城邦的秩序所要求于个人的正义也正是个人灵魂的秩序所要求于个人自己的正义,在城邦那里体现为个人必须遵循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行为准则的正义,在个人那里则被作为个人内心的道德品质、道德操守来体现的。这样,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在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它们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一个体现为城邦的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本身,而另一个则体现为个人的道德品质本身。由是,城邦的正义内在于个人的灵魂之中,就成为个人灵魂的道德品质;而个人的正义体现在个人具体的社会活动之中,就成为城邦的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要求的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这样,我们就阐明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我们表明,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在根本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城邦的正义就是个人的正义,而个人的正义也就是城邦的正义,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正义的”秩序在城邦和在个人灵魂上的分别体现而已。但是,阐明这一点又能说明什么呢?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关系对于柏拉图来说更进一步意味着什么呢?
二
我们说过,整个《理想国》是从探讨人生问题开始的,它首先表现为一个空泛的人生问题,即一个人应当如何度过他的一生才算是美好的一生。但是,随着对这个空泛的人生问题讨论的展开,人生问题便同正义问题关联在了一起,因为答案似乎是,一个人只有正义地度过他的一生才算是美好的一生,这就表明了个人的生活是同他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度过他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他作为个人在社会中度过他的一生,于是,他个体人生的美好是同他在社会中如何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表明了正义问题是理解上述那个显得十分空泛的人生问题的关键,而这又是与社会生活中的正义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从逻辑上,我们就建立起了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也建立起了个人生活的正义和社会生活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很显然,柏拉图正是由此入手来首先分析社会生活亦即城邦生活中的正义的,而我们理所应当地期待,这样分析得到的正义同时也就构成了个人的正义,因为,对社会生活中的正义的分析不是别的,正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的正义的分析。这样,社会生活的正义当然也就意味着是个人生活的正义。而更进一步,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人生活的幸福也就是他在社会中生活的幸福,并且这必然是和他在社会中的生活的正义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正义地生活,他才可能有真正真实的幸福可言。按照这一逻辑,正义和幸福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们期待于柏拉图所论证的,而柏拉图从《理想国》的第一卷到第二卷所具体进行的论证也似乎满足和证实了我们的这一期待。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在同克法洛斯的对话中暗示性地引出了人生问题同正义问题的关联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格拉底同玻勒马霍斯进行的对话中,通过反复的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所要澄清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正义不是一种单纯个人的专门技艺,相反,它存在于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中,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活动所牵涉的利益分配关系的体现。在接下来的同色拉叙马霍斯的对话中,则从一开始就通过色拉叙马霍斯毫不犹豫的断言表明了,所讨论的正义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和人们的政治生活相关。但是,在接下来的辩论中,由于苏格拉底单纯借助理想的技艺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论证遭到了色拉叙马霍斯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经验的无情嘲弄,于是,很显然地,对社会现实生活进行一番深入的讨论,以及从对社会现实生活分析的角度出发来建构和澄清实际的正义概念就成为理论上的必需。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留给了第二卷来着手实施,而第二卷的一开始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同样基于社会现实生活经验的论证,以及一个粗糙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提出,更加重了分析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迫切性。于是,在提出首先研究大字的正义亦即城邦的正义之后,苏格拉底所实际着手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他提出了一个与基于人们的同意的单纯的社会契约理论完全不同的社会劳动分工理论,在人们彼此之间的劳动分工关系的基础上来构建城邦,并且以此来探讨城邦中的正义。这样,在第二卷所实际展开的论证程序中,柏拉图向我们所展示的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分析,来实际地澄清同人们的社会生活有关的正义概念,而这也就能够相应地确立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人的正义概念。
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二卷最初的讨论中向我们所展示的一个基本的论证思路。然而,明显可见的是,当柏拉图在上述社会劳动分工理论所建立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凭空引入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统治阶层亦即护卫者阶层时,这样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分析来寻求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论证思路便被打破了。这样,由于孤立地引入了一个护卫者的阶层,并且在主观上企图确立这个护卫者阶层的理所当然的统治地位和这一统治秩序的合法性,于是,柏拉图所现实建立的城邦就不得不让位于一个“理想的”城邦,亦即一个具有抽象统治秩序的城邦。这样,为了维持这个抽象的城邦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柏拉图在论证上就不得不由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正义的探讨转向了对抽象的城邦秩序的探讨,而正义也就不再是个人在社会中现实生活的正义,它成了既是社会生活的正义又是个人生活的正义,最终则变成了对某种抽象的社会生活秩序亦即城邦秩序的维护,因而在根本上体现为一种内心秩序和对这种内心秩序通过个人的道德活动的抽象保持。
本文认为,这才是我们理解柏拉图所阐明的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关键。这就是说,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是成立的,但却不是基于个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正义的一致性,而是基于某种抽象的社会秩序的一致性;因此,这种一致性就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脱离出去的一致性,是个人对一种抽象的社会秩序的实际上仅仅在内心的保持。柏拉图之所以从第二卷中对社会生活的基于劳动分工理论的现实的分析,转向在第四卷中对一种抽象的城邦秩序的从四主德出发的具体的探讨,如上所说,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基于社会分工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上凭空引入了一个护卫者阶层,也就是说引入了一个凌驾于社会分工各阶层之上的抽象的统治者阶层,而正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统治者阶层存在的合法性,他才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由对城邦现实社会生活的分析转向了对城邦抽象社会秩序及其相应的个人内心秩序的探讨。⑩
关于这一点,从《理想国》的第四卷一开始阿得曼托斯所提出的那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和苏格拉底的相应的回答可以充分地得到说明。我们看到,在第四卷的一开始,阿得曼托斯这样说道:
苏格拉底,假如有人反对你的主张,说你这是要使我们的护卫者成为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人,使他们自己成为自己不幸的原因;虽然城邦确乎是他们的,但他们从城邦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不能像平常人那样获得土地,建造华丽的住宅,置办各种奢侈的家具,用自己的东西献祭神明,款待宾客,以争取神和人的欢心,他们也不能有你刚才所提到的金和银以及凡希望幸福的人们常有的一切;我们的护卫者竟穷得全像那些驻防城市的雇佣兵,除了站岗放哨而外什么事都没有份儿那样。——对于这种指责你怎么答复呢?(419E-420A)
这个问题是十分尖锐和切中要害的,因为,按照《理想国》的第三卷结束时柏拉图对护卫者生活的描述,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护卫者阶层在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中将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而这是同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就已经预设,但在第二卷中又被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所极力要求辩护的那个有关正义和幸福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系的命题直接对立的,因为,按照这个命题,正义的人被要求同时就是幸福的人。护卫者作为城邦秩序的维护者,他当然毫无疑问是正义的人,但是,这样一个正义的人,在柏拉图的实际上是抽象秩序的城邦里却过着一种非常悲惨的现实生活,这就直接表明柏拉图对有关正义和幸福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辩护已经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而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理论抽象,因此是不成功的。很显然,假如柏拉图不对他既有的论证思路做出某种修正的话,那么他将无法回答阿得曼托斯的这个问题,也不能圆满地解决他在一开始就许诺要予以说明的正义和幸福之间的必然关联。我们说,正是阿得曼托斯这个十分犀利的问题迫使柏拉图从对城邦现实社会生活的分析中寻求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的一致性关系的思路上转移出去,而去寻求别的途径以维护他在理论上构建起来的那个抽象的城邦的合理性。
我们看到,在苏格拉底接下来的回答中,柏拉图表明他完全不想通过从分析现实生活幸福的角度出发来避免阿得曼托斯的那个问题的攻击,他让苏格拉底这样说:
嗯,我还可以替他们补充呢:我们的护卫者只能得到吃的,除此而外,他们不能像别的人那样,再取得别的报酬;因此,他们要到那里去却不能到那里去;他们没钱给情人馈赠礼品,或在其他方面像那些被认为幸福的人那样随心所欲地花钱。诸如此类的指责我还可以补充许许多多呢。(420A)
这表明,柏拉图坚持认为,他从理论上已经构造起来的城邦秩序是合理的,按照这样的城邦秩序的规定,护卫者就必然具有这样一种从现实看来是极其悲惨的社会生活,但是,柏拉图非但不为此感到丝毫的理论上的困窘,而是认为他完全有办法摆脱这一看起来的理论上的困境。
他紧接着上面这段话这样写道:
阿:如果这些话一并包括在指责里,怎么样呢?
苏:你是问我们怎样解答吗?
阿:是的。
苏: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路子论证下去,我相信我们会找到答案的。我们的答案将是:我们的护卫者过着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生活而被说成是最幸福的,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420A-B)
而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现在已知道,柏拉图摆脱理论上的这一困境的根本策略就是,完全撇开从社会现实生活的正义和幸福的实现的角度来探讨的思路,转而从抽象的社会秩序的保持与维护的角度来探讨。这样,他当然就可以避开阿得曼托斯的那一问题的锋芒。他会表明,那样一种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幸福是不可取的和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一种本身就是公正的社会秩序和相应的内心秩序的保持,正是在这样一种保持中才有真正的幸福。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四卷中围绕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实际上都是在这样一种对抽象的秩序的维护和保持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他在结束探讨之后说的这段话,则清楚明确地表明了柏拉图式的正义的全部内涵和重点不过就是对一种抽象的内心秩序的保持。他这样说:
但是,真实的正义确是如我们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东西。然而它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当他将自己心灵的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加以协调,仿佛将高音、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各音阶合在一起加以协调那样,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和谐的整体时,于是,如果有必要做什么事的话——无论是在挣钱、照料身体方面,还是在某种政治事务或私人事务方面——他就会做起来;并且在做所有这些事情过程中,他都相信并称呼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把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作愚昧无知。(443C-444A)
在这里,内心的秩序亦即灵魂的各部分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被看成是首要的,一个人全力所要做的不是实际地进行一种现实的社会生活,而是竭力保持自己内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秩序和平衡,然后,在此基础上,才有行动的采取。而我们看到,行动的采取也并不是为了行动的现实效果本身,而是通过采取一定的行动来保持内心的秩序。同时,行动的正义与不正义不是由行动本身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效果所决定的,而是由行动是否有利于保持一个人内心的秩序和平衡来决定的。我们说一种行动是正义的,就是说它有助于保持内心所固有的那种抽象的秩序,保持内心的平衡,而一种行动是不正义的,就是说它无助于这一点。于是,内心的秩序成了判断行动正义与否的根本标准。
这样,本来是通过城邦的正义来理解个人的灵魂的正义,但是,柏拉图却将其倒了过来,即通过个人的灵魂的正义来理解城邦的正义。这一颠倒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才是可理解的,这就是,城邦的正义对于柏拉图来说不是任何现实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正义的体现,而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社会秩序,正是由于它是一种抽象的社会秩序,从而它首先就只是作为一种观念、一种理念,总之,作为一种内心秩序或主观心境而存在。这样,在柏拉图这里我们也就看到了宗教。因为宗教正是通过对一种主观心境的保持来克服外在生活的苦难,而并不企图诉诸现实以坚强有力的行动。这样,和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关注于人的社会现实生活、关注于人的基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活动的正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幸福的世俗的正义概念和幸福概念相反,柏拉图式的正义概念和幸福概念却恰恰是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他试图通过对一种单纯主观心境的维持来实现所谓人的正义和幸福,而这样的正义和幸福就只具有一种主观心境的特征,它毫无疑问是宗教主义的。我们在随后的第六卷中,也就是在探讨护卫者阶层中的精英阶层,亦即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阶层的哲学王在城邦中的个人命运的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柏拉图的这样一种抽象的论证思路所最终达到的具有宗教性质的结论。在那里,由于完全丧失了正义在城邦生活中的现实力量,而仅仅将正义作为一种单纯的美好心灵秩序和内心幸福感来保持,柏拉图的哲学王在城邦生活中的命运最终也就只能是这样的:
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雨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496D-E)
三
纯粹出于补充的缘故,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的论证。
首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围绕正义的全部论证归结为这样一个论证主题,即,以合理的方式建立起正义和幸福之间的必然关联,从而得到这样一个命题——正义的就是幸福。显然,这正是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的一开始所许诺以及格劳孔、阿得曼托斯所向他要求的。
其次,让我们从康德的命题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命题。很显然,它不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分析命题,反倒是一个综合命题(因为,幸福是正义的后果,于是,正义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个概念分析的关系,而是一个概念综合的关系),这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实际上想要通过论证来建立的就是正义和幸福的一个综合命题,而且还企图排除后天综合命题的可能,建立起一个有关正义和幸福的先天综合命题来。按此来理解,在第一卷中,克法洛斯和玻勒马霍斯所试图建立的就是“正义的就是幸福的”这个后天综合命题,而色拉叙马霍斯则通过经验举证否定了这个后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并且试图同样建立起一个完全相反的后天综合命题,即“不正义的就是幸福的”和“正义的就是不幸福的”。接下来,在第二卷中,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同样通过经验的举证否定了“正义的就是幸福的”作为后天综合命题成立的可能性,从而敦促苏格拉底建立起一个关于“正义的就是幸福的”先天综合命题。而苏格拉底从第二卷后半部分开始所试图进行的,正是要达成这样一个有关正义和幸福的先天综合命题。他所走的道路就是,无论是在对城邦正义的分析上,还是在对灵魂正义的分析上,都采取了一种抽象化的思路,也就是说,采取了一条同经验现实完全分离(这是就理论取向而言)并且同经验现实完全相反(这是就实践取向而言)的思路。当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针对正义问题所采取的这样一种思路,同他的整个理念论的形而上学的总体理路是内在一致的,理念就是同经验现实的完全分离,并且是对经验现实的绝对排斥,这样,柏拉图只不过是要通过对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双重抽象化的分析,来获得一个绝对的正义的理念而已。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柏拉图采取这样一种理念论分离的论证方式,在《理想国》自身的叙述结构中还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第一卷中,柏拉图所实际采取的是一种关于正义概念的逻辑论辩的方式,他通过对正义概念的种种字面上的逻辑分析,以表明从正义的字面意义来说,正义的就是幸福的。但很显然,这样的分析是未经批判的,也就是说,它是基于流行的或传统的有关正义的种种说法所进行的对正义和幸福之间关系的观察,而并没有对正义本身撇开其字面的种种涵义来进行考察。所以,在这一卷的最后,苏格拉底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关于正义和幸福之间关系的论证是在未弄清究竟什么是正义的情况下进行的,所取得的对色拉叙马霍斯的辩论的胜利也只是口头上的胜利,从而,合理地将论证的重心指向了对正义本身的考察。
从第二卷起,针对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不是基于人们关于正义的种种传统的看法、而是基于城邦现实生活经验的分析,柏拉图开始引入一个同样针对城邦生活的分析,这个分析相较于无论是色拉叙马霍斯从强权角度对正义和不正义的经验观察,还是格劳孔从契约角度对正义和不正义的理论观察,无疑更具有分析的深度和力度,因为它撇开了对人们生活的种种基于混乱经验的表面上的观察和设想,深入到了人们的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生存的层面上,在这里建构起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企图从中找到正义。显然,这是一个撇开人们关于正义是怎样说的,以及撇开混乱的经验观察附加在正义上的种种偶性,而对正义本身的基于人的现实生活的一个考察,就此而言,我们尚不能说柏拉图是游离在格劳孔、阿得曼托斯乃至色拉叙马霍斯对正义考察时所活动的那个范围之外,亦即城邦现实生活的范围之外,他同样考察的是人们实际的社会活动和由此发生的社会生活关系,同样关注的是现实的正义和现实的幸福。在这里,现实的正义是指向现实的幸福的,两者不是分裂的。
但是,随着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关系通过分析被建构为一种抽象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基于此而获得的正义理念也就与人们现实的正义行为分离了开来,同样也就与现实的幸福分离了开来,这样,到了《理想国》的第四卷,柏拉图就不得不承认并强调正义与现实幸福的分裂和对抗的特点,并由此转向对一种心理性的或精神性的幸福的考察,于是,一个把已经抽象化的城邦秩序转变为一种灵魂秩序从而获得灵魂上的和谐满足的论证过程也就开始了,通过这个过程,正义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被建立在了并且被仅仅建立在了灵魂上,个人在城邦生活中的正义和幸福变成了个人在灵魂生活中的正义和幸福,而这是不考虑个人在城邦生活中的正义和幸福的,或者说,这是不以个人在城邦生活中的正义和幸福为前提的。这样,很清楚的是,尽管正义和幸福的必然关系虽然被建立起来了,但却是被主观地建立起来的,实际上,正义成了个人良心上的事情,成了一个人单纯的道德心性。于是,柏拉图对正义和幸福之间关系的考察就表现出了宗教主义的特征。
收稿日期:2009-02-24
注释:
① Terry Penner,“Platonic Justice and What We Mean by ‘Justice’”,The Interne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to Society,vol.5,2005,URL:http://gramata.univ-paris1.fr/Plato/rubrique5.html.
② Wu Tianyue,“Rethinking Bernard Williams' Criticism of the City-Soul Analogy in Plato's Republic”,URL:http://utcp.c.u-tokyo.ac.jp/events/2009/01/the_third_beseto_philosophy_co/index_en.php.其中对相关的文献做了令人钦佩的追溯和评述。
③ 参见《理想国》368C-E。本论文中所有关于柏拉图《理想国》的转述和引用均依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斌和、张竹明的《理想国》译文。
④ 参见《理想国》328D-E,在那里,苏格拉底以闲谈的方式提出了有关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才是美好的一生的那个所谓的人生问题:“说真的,克法洛斯,我喜欢跟你们上了年纪的人谈话。我把你们看作经过了漫长的人生旅途的老旅客。这条路,我们多半不久也是得踏上的,我应该请教你们: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呢,还是一条康庄坦途呢?克法洛斯,您的年纪已经跨进了诗人所谓的‘老年之门’,究竟晚境是痛苦呢还是怎么样?”
⑤ 例如,在与克法洛斯的谈论中,克法洛斯已经以一种不明确的方式表明了对上述人生问题的回答与一个人是否正义地度过他的一生相关,这样就把人生问题同正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而随着在苏格拉底与玻勒马霍斯、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的对话中对“正义”概念的反复澄清,正义概念遂被表明为是一个人们的政治生活层面的概念,从而与正义相关的人生问题也就被表明为是一个有关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公正的问题,它最终落实到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分析上。
⑥ 2009年5月初,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Thomas M.Robinson教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了一次有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论证的专题讲座,题目是“Justice in the Republic:Stren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Theory”,其中,他指出(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正义概念本来是一个关系概念,即,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柏拉图引入基于工具的功能的类比论证,正义概念就逐渐蜕变为一个功能概念,由此就将对正义概念的讨论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Robinson关于正义概念是一个关系概念的提法,有助于理解我这里所提出的社会的正义概念和个人的正义概念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的观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他本人完全没有做这样充分的考虑,同时,据我有限的知识,正义概念是一个关系概念的看法最早是由Vlastos在一篇谈及Sachs的观点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见Gregory Vlastos,The Argument in the Republic that“Justice Pays”,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65,No.21,Six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Eastern Division(Nov.7,1968),pp.665-674。在其中,Vlastos明确讲到了正义概念是一个关系谓词(relational predicates),指“一个人或一个人群对人们或人群行为或倾向于行为的方式”。
⑦ 就此而言,我认为,Bernarld Williams在对含义的类比关系的讨论中忽略了第一种可能性,即仅仅在结构形式上的相似。他的整体-部分原则不是针对结构上的相似来说的,而是针对整体和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说的。
⑧ 显然,像Sachs、Williams等人所指的柏拉图正义论证上的内在逻辑的不融贯之处正发生在这里。
⑨ 这是按照前面所预告的讨论个人的正义的程序。对此,柏拉图这样说:“我们曾认为这个大东西就是城邦,并且因而尽我们之所能建立最好的城邦,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好的国家里会有正义。因此,让我们再把在城邦里发现的东西也应用于个人吧。如果两处所看到的是一致的,就行了,如果正义之在个人身上有什么不同,我们将再回到城邦并在那里检验它。把这两处所见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仿佛相互摩擦,很可能擦出火光来,让我们照见了正义,当它这样显露出来时,我们要把它牢记在心。”(434E-435A)
⑩ Bernard Williams从城邦和灵魂的类比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这个护卫者阶层的存在给柏拉图的正义的城邦所造成的种种理论上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