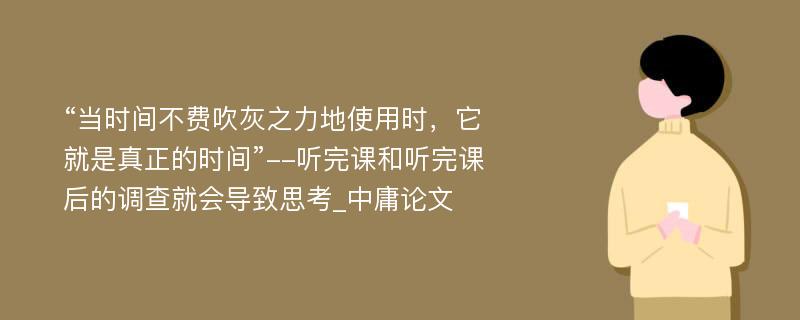
“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听课及听课后的调查引发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夫论文,课后论文,著力论文,方是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末大儒劉宗周(1578-1645),字起東,號念臺,浙江省山陰縣人,因講學山陰縣城北蕺山,後世學者多尊稱爲蕺山夫子。自1603年拜心學傳人許孚遠(1535-1604)爲師①始,至1645年“首陽一餓”而殉道,蕺山從事學術問辨和哲學研究達四十餘年。在此期間,蕺山多數時間在家讀書、講學②,于經史子集、論孟學庸、周程張朱等等學問,遍覽無遺,新說迭顯③,然其“爲學之要”却有三變。劉汋在《蕺山劉子年譜》中指出:“先君子學聖人之誠者也。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獨,而晚歸本于誠意。誠由敬入,誠之者人之道也。意也者,至善栖真之地,物在此,知亦在此。意誠而後心完其心焉,而後人完其人焉。是故可從扶皇綱,植人紀,參天地而爲三才也。”而且,劉汋以“誠意”概括蕺山爲學主旨:“先君子之學,以誠意爲宗而攝格致于中,曰:‘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本之斯止之矣;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止之斯至之矣。’”④蕺山弟子黄宗羲《子劉子行狀》亦看到了蕺山爲學三變之特性,但以“慎獨”爲蕺山學主旨:“先生宗旨爲‘慎獨’。始從主敬入門,中年專用慎獨工夫。慎則敬,敬則誠。晚年愈精微,愈平實。本體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仍不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亦並無這些子可指,合于無聲無臭之本然。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風霽月。消息動静,步步實歷而見。”⑤據此可知,蕺山爲己之學經歷了由敬而慎獨、由慎獨而誠意的“三次”轉變。但是,“敬”、“慎獨”、“誠意”各有何指?三者爲什麽會發生這樣的轉變?三者究竟是蕺山爲學“工夫”,還是蕺山哲學思想的“宗旨”?三變之學之本質爲何?本文對此展開論述,求教方家。
一、“始致力于主敬”
蕺山爲學“始從主敬入”,自然始于執贄許師孚遠之時。據《年譜》“二十六歲”條載,宗周問許孚遠“爲學之要”,孚遠告以存天理、滅人欲,遂北面納贄許孚遠。蕺山請許師爲其母作傳,許則以“敬身之孝”勖宗周:“使念念不忘母氏艱難,謹身節欲,一切世味不入于心,即胸次灑落之明,古人德業不難成。傳所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乃劉子所以報母氏于無窮也。”蕺山雖杖履許師孚遠才“月餘”,却“終身守師說不變。自此勵志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整齊嚴肅入。自貌言之細,以至事爲之著,念慮之微,隨處謹凜,以致存理遏欲之教。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由來爲之何?又勘明後决裂更當如何?終日端坐讀書曰:‘吾心于理欲之介,非不恍然。古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理,彼若何而欲。”則其存之遏之也,不亦恢恢有餘地乎?’”⑥許孚遠授蕺山一“敬”字,蕺山便忠實接受並“終身守師說”,蕺山前半生所形成的那種“嚴毅清苦”⑦之氣象不能說與此無關。
“敬”者何謂?蕺山在1613年與門生陸以建的書信中清晰地指出:“君子之學,言行交修而已。孔門屢屢言之曰:‘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不敢’二字,何等慎著,真是戰兢惕厲心法。此一點心法,是千聖相傳靈犀,即宋明主敬之說,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不必另說天說性,作蛇足也。”⑧在蕺山看來,“敬”者乃爲孔門千聖“相傳靈犀”,“不敢”便是戰兢惕勵、謹微慎密、求真務實,便是“慎著”。“敬”之爲學要法便是端莊檢點、行事慎微,歸根結底便是實現自我約束、自我規制、自我監督。
“敬”本爲宋儒程頤致力爲學之方法。他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⑨朱熹釋二程之學,强調“敬”的重要,“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⑩,“持敬是窮理之本”(11)。在程朱理學,“敬”乃是“静時涵養”之道德修養工夫,其前提是“静”與“動”、“涵養”與“省察”之二分。而且,“敬”自身之中便已藴涵有“二分”之義,即涵養對象與涵養主體之間具有相分性。孰知,主體體悟涵養的過程與體悟涵養的對象以及所獲取的“體悟”效果本是一體,無分內與外、動與静,三者本是通貫。這對于後來講究思想“融合”的蕺山來說(12),“敬”之學問自然不能達致內心世界的自我主宰、自我融貫、自覺自在。
人在進學之初,脚踏實地,實心踐履倫理道德規範,在點滴事件中體認人性與天理。但是,在這樣的道德修養工夫進行一段時間之後,隨著內心世界對爲學爲道之必要性、性天之理的必然性和行爲處事的自在性的覺悟,原先的具有强制性的道德修養手段自然“落後一著”,由自我的“被動”走向“主動”,自我主體性的逐漸覺醒、自在自覺性的不斷培育,內心終將達致一種“豁然開朗”的自覺境界。此時用功,當尋另外一番天地。蕺山用功于“敬”,並于四十歲時撰就《論語學案》,正體現出踐履敦篤之“敬”修之功。劉汋曾對是著這樣描述:“先生壯年力學,不可盡考。讀《論語學案》而知當時進修之敦篤,居身之謹嚴,有寧卑毋高,寧峻勿夷之意,居然孔子下學法門。”(13)亦正是此著,蕺山由敬而讀書致知明理的爲學取向,實現了對宋明儒尊德性與道問學“分途”的消解,是“新學”方向的開顯。(14)
二、“中操功于慎獨”
蕺山在主“敬”治學一段時間之後,隨著自己哲學思辨能力的提高和問題闡釋角度的轉换,“敬”學淡出,而提倡能够統合動與静、內與外的“慎獨”(15)之學。早在1613年與《與陸以建年友一》的書信中,蕺山便表達這樣的觀點:“聖學要旨攝入在克己,即《大》、《中》之旨攝入在慎獨,更不說知說行。周子‘聖學有要’段,亦最簡截,與克己慎獨之說相印證,此千古相傳心法也。”(16)周子“聖學有要”一段是這樣說的:“‘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虛、動直,静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朱子釋此章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17)周子之語表明,學不可分動與静,因爲静之虛與動之直本是無間精微的。“静”表像爲虛,實則是一種心“明”;“動”表像爲直、現象、顯現,實則是一種人性自我主宰的外顯。就其作爲“自我主宰”的自存、自在講,衆人皆有,萬物共通,內在静存而已。即是說,“静”中內藴著“動”的主宰之功,“動”中亦在體現“静”的主宰之實,任何單純的静或者動根本是不存在的。“慎獨”作爲《大學》、《中庸》之要旨,便是實現了“動”與“静”的統合。據此,蕺山在1629年所著的《大學古記約義》對朱子以“動静二分法”解“慎獨”之說進行了批評:“《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朱子……至解慎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静存工夫。則愈析之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曰:‘慎獨即是致良知。’即知即行,即動即静,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静者也。其有時而動静焉,動亦慎,静亦慎也。而静爲主。使非静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静矣。”(18)動静不可二分,動中有静,静中有動,動中之静表明動中有必静之理;静中有動凸顯静中有必動之則。
從三十七歲悟“心”(19)到四十八歲專提“慎獨”,這十年是蕺山生命歷程中極爲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蕺山從陽明學中探尋原義,以抑制當時玄談空虛的學風;一方面要針對陽明學及其後學不重工夫的缺點闡發新的工夫義理,並與陽明學內在契合,實現從陽明學內部來扭轉陽明後學弊病的目的。(20)蕺山所選擇的工夫理論便是“慎獨”。據《年譜》“四十八歲條”(1625)載:“每會必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爲入道之基。嘗曰:‘此心絶無凑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裹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真凑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于是有慎獨之說焉。”(21)而促使蕺山“專用慎獨之功”的契機則是1626年黄尊素(22)被逮事件。據《年譜》記載,是年三月,黄尊素爲閹宦魏忠賢所逮,劉宗周餞之蕭寺,“促膝談國是,危言深論,涕泣流漣而別”,及返而謂門人:“吾生平自謂于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此中怦怦欲動,始知事心之功末可以依傍承當也。”遂携子劉汋課讀于韓山草堂,“專用慎獨之功”,謂:“獨只在静存,静時不得力,動時如何用功夫。”(23)據此可推知,蕺山因“性命之交友”將爲奸宦所殺,于生死關頭,內心震動較爲激烈,自覺學力不深,由此反思爲學之方,頓感“静”中用力的重要。“静時不得力,動時如何用功夫”清晰地表明,捨“不動心”工夫,無論如何也不能實現遇事之後的自我欣慰、自我滿足和自我停當。欲求“不動心”,必須“静”時涵養。因而,能够進行“不動心”的“静”的工夫必然是一種能够將“心”與“事”、“已發”與“未發”相統合的工夫。這就是“慎獨”。
因而,蕺山以“慎獨”解“中和”並融貫“已未發”,實現爲學思辨邏輯的創新。1626年的《學言》有論:“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中爲天下之大本。慎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24)在蕺山看來,“中”即是隱微之未發,“和”即是顯見之已發,然隱與微,本即是合一。“中”隱藴著發的可能與必然,“和”暗涵有發的基礎與本質。“中”與“和”既是狀態,又是過程。說它們是過程,表明“中”有隱“發”這樣的潜在,並且“發”之潜在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之中;說它們是狀態,表明“和”之顯發的表面現象中始終內涵者“中”的基礎與實質。從表層的“顯”角度講,“中”與“發”都是過程,也都是狀態;從深層的“隱”角度講,未發之“中”潜存“發”的可能,已發之“和”內涵“中”的自然本質,“中”即是“和”的基礎和前提,“和”即是“中”的自覺與規範。戒懼與慎獨本身即是對“中”之發的潜在性和“發”之“和”的自覺性和規範性的體認。不睹不聞之戒懼是對“發”之潜在性的自覺和體認,慎獨是對“發”之過程中“和”之趨向的明晰和順從;慎獨的過程就是戒懼的過程,戒懼的過程就是慎獨的過程。戒懼與慎獨,本非二功;致中之外,本無致和之功。戒懼與慎獨、致中與致和是“一藴二、二合一、一二和合存在”的意境。不經慎獨之功,內心有所動,自然溢于言行;而經慎獨之功,自然可實現隱與微、顯與發間的融貫。
所以,蕺山將“中”看做是“獨體”,將“和”看做是“獨之所以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獨體也,亦隱且微矣。及夫發皆中節,而中即是和,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未發而常發,此獨之所以妙也。中爲天下之大本,非即所謂‘天命之性’乎?和爲天下之達道,非即‘率性之道’乎?君子由慎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本,無所不達矣。達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達于萬物,萬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萬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則俱致,一體無間,極之至于光岳孝靈,百昌遂性,亦道中自有之徵應,得之所性固然,而非有待于外者。”(25)喜怒哀樂之未發之“中”自然潜存喜怒哀樂之“發”的必然性、必定性,而喜怒哀樂之“發”中亦自然內藴了喜怒哀樂之“中”的節制性、自在性。已發之中有獨體的自在存在、自然存在,未發之中自然有發的潜在,然其“發”自經“慎獨之功”而自自然然、停停當當,隨心所欲不逾矩。未發之中盡顯“獨”之“天命之性”之本體,已發之和盡體“獨”之“天下達道”之工夫。所以,蕺山說:“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26)從此年(1631)撰寫《中庸首章說》始,蕺山“專揭慎獨之旨教學者”。(27)
三、“晚歸本于誠意”
不過,從1636年始,蕺山治學專提“誠”。據《劉宗周年譜》載:“是時先生工夫只在略綽提撕間。每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無爲,無欲故静,有所向便是欲’等語……自此專舉立誠之旨,即慎獨姑置第二義矣。”(28)蕺山于是年專提“誠”,自然與他對“意”的理解分不開。
是年,蕺山于《大學》“誠意”說發明了“意爲心之所存”之論。在蕺山看來:“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29)朱子在《大學章句》中以“已發”訓意,指出:“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于善而無自欺也。”(30)以後的理學家多以已髮指意。陽明也認爲“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又說“意之本體便是知”。(31)而在蕺山,意爲“心之所存”,是“心之存主”。一方面,蕺山說意爲“心”之存主,此“心”並不就是個體之人心,當爲聖人之心、本根之心,是就“道心”而言的。個體之心非無道心、無聖人之心、本根之心,只是說,非全體個體之心皆彰顯了此道心、本根之心,道心、本根之心自自然然、正正當當,自能好善惡惡,自然行其好惡判斷而又無違道德規範。因此,蕺山有這樣的論說:“此心之存主,必有善而無惡矣。何以見其必有善而無惡?以好必于善,惡必于惡也。好必于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于此也;惡必于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于彼也。必于此而必不于彼,正見其存主之誠處。”(32)另一方面,意爲心之“存主”,有此“意”,必有此“彰善抑惡”而無不善之“心”。但是,“意”又如何能够做到“好惡”的呢?蕺山曾有是言:“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謂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言謂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無惡歸之至善謂之物。識得此,方見心學一原之妙。不然,未見不墮于支離者。”(33)聖人之心、本根之心本質便是自在、自主,能够使此自在、自主活動起來的自然是“意”,“意”之本質是善必好、惡必惡,“心”以“意”爲主宰,心自然能够見善必好,見惡必惡。“意”之“好惡”實質上是一種“自覺地行”,是基于“知善知惡”之“知”的“行”。無對善與惡的“知”,哪能有對善與惡的“自覺”道德評價?也就是說,有“知”方有“行”,有“行”自然建基于真“知”。知是行之基,行是知之實,“‘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34)有如此自然而有的知善知惡之“知”,便自然“好善而惡惡”。就知善知惡之自然而然的能力講,“知”的只是“善”,凡不“善”自然便是“惡”。“知”更是一種智慧,是真知即是行的自在之知。不過,無論是“意”還是“知”,從心上講,他們都是“好善”、是“知善”,而“心”亦是“善”心。但從人生活的實際境遇講,芸芸衆生,人心萬種,有善有惡,善惡並存。本根之心、聖人之心只是“好善”、“知善”,一旦面對與此心相异的萬象之個體之人之人心時,本根之心便能够由“好善”、“知善”而自然、自覺“惡惡”、“知惡”。只是,從終究的意義上言心、意、知,只有“善”可爲,而“心”、“意”、“知”自身就是“善”,是“善”的化身。千善萬善,終歸一善;知所有善,終歸是知“善”。“心”“意”“知”所行所在,本便是“有善無惡”。“有善無惡,歸之至善”,蕺山名之爲“物”。“心”是“意”之外顯,“意”是“知”之施行,“知”是“物”之細則,“心”與“意”與“知”根本爲“善”,是“物”之“至善”的自然推演。由而,蕺山定性心意知物:“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35)從終極意義、自我主體性講,本心之之有意之主宰,意中又有知,能知之所在之物,貫穿始終的是“至善”本質。從生存世界、多元個體之心的存在講,此心、意、知、物或是被障蔽,或是被彰顯,不一而足。但心、意、知、物之至善本質却不會因個體之心之多元性和多義性而泯滅無迹。
蕺山析“意”不僅與心、知、物相融貫,而且與“誠”相統合,以此構設“誠意”工夫。何爲誠?蕺山在1645年《答史子復(36)二》中討論陽明“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之論時指出:“夫‘真切篤實’非徒‘行’字之合體,實即‘誠’字之別名,固知‘知行’是一,‘誠明’亦是一……惟立教之旨,必先明而後誠,先致知而後誠意,凡以言乎下手得力之法,若因此而及彼者,而非果有一先一後之可言也。”(37)這樣,一方面,蕺山以“真切篤實”釋“誠”。在蕺山看來,“真切篤實非徒‘行’字之合體,實即‘誠’字之別名”,“真切篤實”既在描述事實,又在描述過程。從事實之描述講,“真切篤實”反映出心之“知”的誠實無欺性和真實無妄性;從過程之描述講,“真切篤實”反映出心之“知”能够、能動、自覺、主動地真實無妄地、誠實無欺地體知和反思自我、體認萬物。所以,蕺山將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歸結到“誠”上,以一“誠”貫之,體現了蕺山融合陽明學的學術特徵。另一方面,蕺山以“誠明合一”釋誠。“知”與“行”所實現的過程與狀態的“合一”便是“誠”,“誠”從而內藴了即狀態即過程的事實存在。“誠”作爲心上做工夫的狀態,是人之“道心”的體露;作爲心上做工夫的過程,是人去尋求自我的“純真”。體露“道心”,就是“明”心,使心得以“澄明”、“光明”;尋求自我的“純真”,就是心之“至善”、“自覺”、“誠實無欺”得以自在地開顯。“誠”的過程是“明”善、“明”覺的過程,“誠”的狀態是至善、自覺、自在得以“光明”的境遇。所以,蕺山說:“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者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38)
從對蕺山之“意”與“誠”的分析可以看出,蕺山所論之“誠”與“意”自身都是動作性、過程性與描述性、狀態性雙重意義的和合統一體。“誠”是真實無妄,是真,是止,是人心之自在性、自覺性、純真性,是人之所以爲人的那個靈明。實現了“誠”,就是彰顯了人的本質。“誠”作爲人性本真,與“意”本質相通。當然,二者亦有其“立場”的不同。“誠”是從天性之路和人性之路的融通講的。蕺山曾說:“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39)即是說,“誠”彰顯出“天道”意藴,而“誠之”則是在彰顯“人道”,“天道”不遠,惟內藴人心,方有著落之處;“人道”自在,但須上達天道,以天道爲理論推演依據,方顯客觀性和必然性。“意”是從“心”之“所存”來講,强調心之主宰和心之“好惡”動作過程。這樣,“誠”既是顯象、描述意義上的“誠實無欺的”,體現爲“必然如此”;又是動作、過程意義上的“誠實無欺地”,表現爲“事實如此”。“意”自身乃是一種“志”,是一種自覺地評判善與惡的能力,亦是好善惡惡的過程,具有作爲顯象、描述意義上的“能力”、“自覺”之“意”與作爲過程、動作的“意志”、“能够”、“好惡”之“意”的雙重屬性,從而體現出“必然如此”與“實際如此”之意。
當蕺山將“誠”與“意”相統合而論說“誠意”時,誠意便落實爲“功夫”。1636年的《學言》就有這樣論斷:“《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始,正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于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真功夫。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40)按蕺山之意,格致便是“致至善”,而此“致至善”便是誠意之功效;誠意之功,是于心之意之上的發用過程。故,離却意根,則無格致可言。意根便是善,格致便是致至善,格致與誠意從而是一不是二。實際上,從蕺山對誠意工夫的體認,可以將誠意進行四種可能境域下的詮解:其一,“誠實無妄”的“意”,表明“意”之能力、自覺性的客觀性;其二,“誠實無妄”的“意”,表明“意”之好惡性的正確性;其三,“誠實無妄”地“意”,表明“意”之能力、自覺性被誠實無妄地發揮和自覺發揮;其四,“誠實無妄”地“意”,表明“意”之通過“好惡”去真實無妄地“體認”社會與人生、“體認”道德規範與倫理價值的過程。“誠”與“意”相結合,探求的正是“工夫與本體”的合一,惟有從誠意入手,方可稱之爲“真功夫”。無論“誠意”之解之重心落實于“誠”還是“意”,誠與意皆是過程與狀態、動作與目標的融合通貫,亦惟此統合之態,蕺山才將之看做是“致至善”的“真功夫”。
四、“學不知本,即動言本體,終無著落”
蕺山之學由敬而慎獨、由慎獨而誠意,由對先儒學問的自覺接受到思辨創新,蕺山爲學功力日深,求學之道日明。探究蕺山“學凡三變”之意藴,可窺測其中三方面特徵:
其一,蕺山學凡“三變”之“變”體現了蕺山學思明辨逐漸走向完備、爲學之功逐漸達致成熟的“階段性”特徵。
隨著學力的增强,對問題分析能力和認知能力的逐漸提高,蕺山站在後一階段反觀自己前一階段用力功效時,自然存在著前後期對己之“爲學之要”的不同認識。劉汋《蕺山劉子年譜》深刻揭示出蕺山的這一前後變化:“先生從主敬入門。敬無內外,無動静,故自静存以至動察,皆有事而不敢忽。即其中覓個主宰曰獨,謂于此敬則無所不敬,于此肆則無所不肆,而省察于念慮,皆其後者耳。故中年專用慎獨工夫,謹凜如一念未起之先,自無夾雜;既無夾雜,自無虛假。慎則敬,敬則誠。工夫一步推一步,得手一層進一層。晚年愈精微,愈平實,絶無儱侗虛無之弊,洵乎爲伊洛正脉也。”(41)劉汋之論正是對蕺山之學三變由低到高、由不系統到系統、由不成熟到成熟演變歷程的真切體認。站在較高層次、較系統、較深刻、較完備的哲學思辨角度反觀己之“前見”時,必然會有這種以己之“後學”修正己之“前學”的“自我批判”。這是爲己之學走向進步的自然現象。當蕺山對“慎獨”的理解達致較爲完備的層次而反觀“敬”時,不自覺中將其視爲較低級階段,這便有了1636年《獨體編》對先前主“敬”之法的批評:“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懼來。然敬字只是死工力(一作夫),不若《中庸》說得有著落,以戒慎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爲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個敬字也。”(42)當蕺山晚年對誠意有較深刻理解和體悟之後,當蕺山對爲己之學之方向有所衡定之後,亦自然批評前期的“慎獨”說。1639年,蕺山在《答葉潤山(43)二》的信中說:“所舉‘視無形,聽無聲,持行無地’等語,亦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意,歸之慎獨而已。‘獨’即前所謂幹體也,然不免悠謬其辭,近于佛、老之說,反晦本質。質之修辭立誠之意,殆不如此。乃知吾輩論學,只是樸實頭地,一是一、二是二,即指畫身心性命,亦須一一有著落。若天道有已然之迹,方可捱步尋求,不墜落虛空窠臼耳。”(44)蕺山認爲,將“無聲無臭”之地、“戒慎恐懼”之意概之爲“獨”,有“悠謬其辭”之弊,近于佛、老之學。而晚年的劉蕺山,學愈進步愈精醇,愈是明辨儒釋,愈發凸顯己學之“醇儒性”,凡是表像出與釋學相似的學問思想,蕺山都要厘清與廓正。故,在蕺山那裏,若學問有儒釋混搭現象,必修正不殆,以免讓學者入“异端”,體現了蕺山“醇儒性”的學術性格。因此,若以“慎獨”作爲蕺山始終不變的“爲學主旨”,自然未能從蕺山自身學術演變史角度加以分析,立論有些武斷。
當然,蕺山並不是完全否定前期用功功效,而是以己之後來成熟的思想體系反觀、查檢前期思想中所存在的問題,甚至在一定的思考基礎上,將前後期思想融通起來。比如,到1639年,蕺山在《讀〈大學〉》中便將誠意與慎獨相融通起來:“《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也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至。故格物致知爲誠意而設,非誠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必言誠意先致知,正示人以知止之法,欲其止于至善也。意外無善,獨外無善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致知,後此不必在正心。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並無修齊治平之功也。”(45)不僅誠意與慎獨相通,意亦與獨通合:“好惡云者,好必于善,惡必于惡,正言此心之體有善而無惡也。故好惡兩在而一機,所以謂之‘獨’。如曰有善有惡,則二三甚矣。獨即意也。知獨之謂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以所發言,明矣。”(46)
其二,蕺山“學凡三變”之本質是即工夫證本體,體現出“工夫與本體”合一的特徵。
蕺山“三變”之敬、慎獨、誠意究竟該定性爲“工夫”還是“本體”,擬或既是工夫又是本體?甚或它們之後還隱含有另外某種思想觀念?爲解决此些問題,且先看蕺山在1631年所撰《中庸首章說》中的一段話:“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于道生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真用力于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异,多系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于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于慎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復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即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捨淵淵静深之地而從事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47)此處有兩個問題需分析:其一,真工夫:“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于道生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其二,知本:“學不知本,即動言本體,終無著落”。
在蕺山看來,爲學之“真工夫”應該是“用到無可著力處”的工夫,而“無可著力”應該就是“大本”。即是說,“真工夫”是與“本體”相“合一”的工夫,“本體”通由“工夫”而彰顯,工夫與本體在“無可著力”處達致融通。這就是蕺山工夫哲學所堅持的“工夫與本體合一論”。一方面,認定本體做工夫:“說本體,先說個‘天命之性’,識得天命之性,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說工夫只說個‘慎獨’,獨即中體,識得慎獨,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在其中矣。”(48)天命之性與本體相融通,以性天之理標示本體,本體既是客觀自在,却又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于本體之體知處,一真則無所不真、一誠則無所不明。惟有洞徹了本體並認定本體做工夫,本體才能于工夫中切實落實,工夫亦自然才有客觀理據。另一方面,于工夫中見本體:“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才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正當處。若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凑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49)真切的道德實踐工夫乃是彰顯本體的基本手段,而切實行工夫的同時便是本體呈露之時。蕺山將本體與工夫打合爲一,本體是工夫的主腦,工夫是本體的落實,本體與工夫“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這裏要注意的是,蕺山將工夫與本體相打合,旨在强調“工夫”的必要性和客觀性,他所說的“肯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正當處”,是“工夫與本體合一”,而非“本體與工夫合一”。這樣的工夫哲學邏輯是建立在他對陽明後學“躐等之弊”的批判與回應基礎之上的。如果說蕺山在爲學主“敬”階段還未對“敬”的詮解達致“工夫與本體合一”哲學思辨的話,到爲學主“慎獨”、“誠意”階段,蕺山已經明確將它們看做爲“工夫與本體合一”的哲學理念,並以此思辨彌補先儒在相關問題上的不盡之意。故,蕺山“學凡三變”之“變”雖是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爲學之要”,但都是以工夫證本體,終究達致“工夫與本體”合一的爲學價值方向:“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50)“明善之善,不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者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51)
其三,蕺山“學凡三變”不離“本體”的建構,歸根到底是挺立“心”體。
前所引《中庸首章說》需分析的第二個問題便是“知本”問題。“本”爲何?蕺山曾經多次講到“獨體”、“性體”、“心體”、“意體”,但是,它們是否就是蕺山哲學所强調的終極“本體”呢?此外,蕺山還講“盈天地間皆性”、“盈天地間皆道”、“盈天地間皆人”、“盈天地間皆易”、“盈天地間皆心”、“盈天地間皆氣”等等,究竟蕺山以何爲“本”、“本領”?且他所理解的“本”之本質究竟爲何?《中庸首章說》撰寫于1631年,是蕺山“中操功于慎獨”時期。是時,蕺山拋出“學要知本”一句,其前提“後之學者,無復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提到了“吾心”概念,反求之“吾心”,于“吾心”之處“根本一著”,而“從此得手,方窺進步”。以“慎獨”在“吾心”處用工夫,“吾心”自可使人進步、明朗、頓悟。那麽,“吾心”當爲何心?吾心之“心”是不是蕺山哲學所構設的“本體”呢?
蕺山1643年所撰的《讀易圖說》已經最爲詳盡地明白了“吾心”之意義和價值。《讀易圖說》因《人極圖說》而作,而定本《人譜》亦因《讀易圖說》而完善和定型。在《讀易圖說》中,蕺山指出,“人心之妙,無所不至”、“讀易而見吾心”、“盈天地間,皆心”,此“心”便是“本心”。蕺山曾多次提到“本心”概念。如,蕺山1638年的《學言》說:“學問之宗,心尚矣。然心一也,而學或异。有本心之學,有師心之學,有任心之學。本心之學,學得其心,聖學也。師心之學,索隱行怪,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任心之學,則小人而無忌憚矣。”(52)1642年的《學言》亦指出:“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53)《人譜》之“改過說”中指出:“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54)“本心”就是人“心”,是能够“管攝”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心”。統體而言,三才之道皆“心”,就人而言則爲“本心”。正如《人譜》之《人極圖說》所言:“無善而至善,心之體。(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義一也。)”(55)人之爲人,有其“本心”;“本心”與管攝三才之道之“心”一以貫之,《人極圖說》的哲學邏輯結構正是對“心”、“本心”、“人極”之意藴的展示。(56)至善之“心”體天道、明地道、盡人道,融天地人于一體。“心”無所不在,亦無所不能,它不僅是“天之所以爲天”的“所以然之理”,還是“地之所以爲地”的“所以然之理”,“三極”統于“人極”,從而“人之所以爲人,心之所以爲心”。(57)而且,“人雖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與聖人一樣。只爲習染所引壞了事。若才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泉達,滿盤已是聖人”(58)。人心自存良心“本心”,“本心”生天生地生萬物,一旦對“本心”明瞭徹悟,自然能够認定本體而自覺地改過去惡、却妄還真,在“即知即行”中達致自我“本心”的彰明。
據此反觀《中庸首章說》,是時蕺山思想尚未定型,但其對“本體”的不懈追求和誠心向往已表露無疑。蕺山將工夫與本體相打合,其所論說的工夫自然是內藴了本體的“工夫”,“工夫”之“無可著力”處自然便是“本體”彰明處。實際上,本體本並不與工夫相分,本體自然流漏處便是工夫,工夫正當處便是本體,“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並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知,則亦無這些子可指”。(59)從爲學入手講,學要重工夫;從工夫實質講,即工夫證本體;從工夫與本體合一講,本體便是“吾心”之“本心”。
由上可知,蕺山之學凡三變,從“主敬”入手,便是爲學之初工夫踐履上的戰兢恪守、整齊嚴肅;中期專用“慎獨”,即是逐漸將先儒爲學之旨之動静、內外、中和、涵養省察等二分的工夫路向達致“合一”,而以戒慎恐懼、静中涵養爲用工之要;晚年歸本“誠意”,則是在對《大學》全新解釋基礎上,在對先儒哲學思想全面補偏救弊的過程中,以《大學》統攝《中庸》,以意主心,以性天之誠通合人性之意,在好善惡惡中求索至善自在。蕺山“學”雖“三變”,“變”的是“爲學之要”,即每一時期爲學之功的用功主旨,體現出爲學工夫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系統到系統、由“照著講”到“自己講”轉變的階段性特徵。蕺山雖“學”有“三變”,然其“不變”的是工夫論的實質,即能够認定本體做工夫,且于工夫中體證本體,堅持即工夫證本體,達致“工夫與本體”合一的“真工夫”境界。
①據《年譜》“二十六歲條”(1603)載:“仁和陳植槐感其(劉宗周——引者注)誼,爲介紹德清許孚遠。是年三月,先生如德清而納贄焉。”(姚名達:《劉宗周年譜》,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1頁)許孚遠師從唐樞(1497-1574,字惟中,號子一,人稱一庵先生),唐樞則是湛若水入室弟子。故可說許孚遠具有心學淵源。
②據《年譜》“六十七歲條”(1644)載:“按先生通籍四十五年,在仕版者六年有半,實際立朝僅四年,而被革職爲民三次。”(《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471頁)
③蕺山之子劉汋(1613-1664,字伯繩,山陰人)曾說,蕺山“退而居於野也,橫經論道,講學淑人,上自《四書》、《六籍》,一一厘正之;下之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人人折衷之。闡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訛謬,存天理於幾微,留民彝於一綫,其見於著述者愈弘且偉焉”(劉汋:《蕺山劉子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74頁)。
④《蕺山劉子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73、174頁。
⑤黃宗羲:《子劉子行狀》,《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39頁。
⑥《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231頁。
⑦劉汋說:“先君子盛年用功過於嚴毅,平日齋莊端肅,見之者不寒而慄;及晚年造履益醇,涵養益粹,又如坐春風中,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蕺山劉子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74頁)黃宗羲亦指出:“先生……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風霽月。消息動靜,步步實歷而見。”(《子劉子行狀》,《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39頁)
⑧《書·與以建四》,《劉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02頁。
⑨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88頁。
⑩朱熹:《朱子文集》卷七十五《程氏遺書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頁。
(11)朱熹《朱子語類》卷九《學三·知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50頁。
(12)拙文:《劉宗周與宋明理學“方法論”走向》,《江淮論壇》2012年第3期。
(13)《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262頁。
(14)拙文:《劉宗周與宋明理學“知識論”走向》,《孔子研究》2012年第1期。
(15)有些學者以“慎獨”爲蕺山學說的宗旨,如張豈之《論蕺山學派思想的若干問題》(《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張踐《劉宗周“慎獨”哲學初探》(《中國哲學史研究》1985年第4期)、衷爾钜《蕺山學派的慎獨學說》(《文史哲》1986年第3期)、董平《論劉宗周心學的理論構成》(《孔子研究》1991年第4期)、陳寒鳴《劉宗周與晚明儒學》(《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3期)、黃敏浩《劉宗周及其慎獨哲學》(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等等。與其以“慎獨”爲蕺山哲學的宗旨,不如以之爲蕺山工夫論的主要進路,正如張學智所說:“劉宗周整個工夫論的總綱即慎獨。”(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57頁)另,步近智以爲:“劉宗周提倡的‘慎獨’已經不是以往儒家所說的一般的道德修養方法,而是本體論、認識論、道德修養論和人性論融爲一體的理學思想。”(步近智:《劉宗周的思想矛盾和“慎獨”、“誠敬”之說》,《浙江學刊》1986年第3期)雖其意不錯,但終未契合蕺山“學凡三變”本旨。
(16)《書·與陸以建年友一》,《劉宗周全集》第三册,第298頁。
(17)周敦頤:《通書·聖學》,《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1頁。
(18)《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315頁。
(19)據《劉宗周年譜》“三十七歲”條(1614)載,是年,“劉宗周著《心論》,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256頁)。
(20)東方朔:《劉宗周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6~67頁。
(21)《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296頁。
(22)黃尊素(1584-1626),字真長,號白安,余姚通德鄉黃竹浦(今浙江省余姚市梁輝鎮)人,與劉宗周有婚姻關係。據《劉宗周年譜》“四十九歲”條(1626年)載,“黃尊素被逮,劉宗周餞之蕭寺。促膝談國是,危言深論,涕泣流漣而別。是時,黃尊素與劉宗周預訂爲婚姻。”(《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302頁)黃宗羲《子劉子行狀》載:“(蕺山)孫男四:茂林、士林、長林、道林,而茂林則羲之甥也。”(同上,第39頁)即蕺山塚孫茂林(字子本,崇禎壬申生)爲黃宗羲次女婿。
(23)于此,劉汋有案語:“先儒以慎獨爲省察之功,先生以慎獨爲存養之功。”(《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302頁。)
(24)《學言》上,《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72頁。
(25)《說·中庸首章說》,《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299~300頁。
(26)同上,第300頁。
(27)《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356頁。
(28)同上,第398~399頁。
(29)《學言》上,《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90頁。
(30)朱熹:《大學章句》,《四書集注》,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6頁。
(31)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1《語録一·傳習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頁。
(32)《書·答葉潤山四》,《劉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73~374頁。
(33)《書·答史子復(孝復)》,《全集》三,第380頁。
(34)《人譜》,《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19頁。
(35)《良知說》,《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18頁。
(36)史孝復(?-1644),字子復,號文學,別號退修,余姚人。董瑒《蕺山弟子籍》著録其爲蕺山弟子。(《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615頁)
(37)《書·答史子復二》,《劉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85頁。
(38)《學言》下,《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53頁。
(39)《學言》中,《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08頁。
(40)《學言》上,《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90頁。
(41)《蕺山劉子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83頁。
(42)《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397頁。
(43)葉廷秀(?-1650),字謙齋,號潤山,明末濮州(今濮陽)人。董瑒《蕺山弟子籍》著録其爲蕺山弟子。(《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615頁)
(44)《書·答葉潤山二》,《劉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54~355頁。
(45)《劉宗周年譜》,《劉宗周全集》第六册,第427~428頁。
(46)《書·答史子復(孝復)》,《劉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80頁。
(47)《說·中庸首章說》,《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01~302頁。
(48)《學言》上,《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82頁。
(49)《書·答履思二》,《劉宗周全集》第三册,第309頁。
(50)《說·中庸首章說》,《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300頁。
(51)《學言》下,《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53頁。
(52)《學言》中,《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26頁。
(53)同上,第435頁。
(54)《人譜》,《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17頁。
(55)同上,第3頁。
(56)拙文:《心學視域下的劉宗周〈人譜·人極圖說〉釋義》,《江漢論壇》2013年第10期。
(57)《讀易圖說》,《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122頁。
(58)《人譜》,《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15頁。
(59)《學言》上,《劉宗周全集》第二册,第404頁。
标签: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