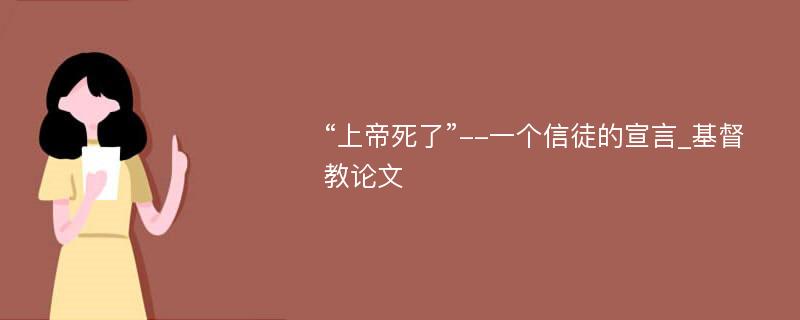
“上帝死了”———个信徒的宣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了论文,信徒论文,宣言论文,上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126 节题为“疯子”中宣告:“God isdead”(上帝死了)。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再次重申这一命题。这使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西方世界感到极为震惊。舆论惊呼,“这是无以复加的疯狂”。而德国以及欧洲学界,则象以往对待尼采哲学的方式一样,保持了带有敌意和恐惧的沉默。不过,在尼采逝世后不久,学术界终于打破了沉默,探讨尼采学说的各种理论纷纷面世,围绕“上帝死了”这一命题展开的激烈争论经久不衰,一直持续了百年之久。
“上帝死了”是一个隐喻,正因为如此,哲学家们对这个命题的解释众说纷纭。因此,对于尼采这一命题的解释,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免不了有“洞穴假象”。既然如此,在诸多“洞穴假象”中再添上一个也无伤大雅。
上帝死了不是信仰死了
《快乐的科学》第126节题为“疯子”。 尼采在这一节中首次指出:“上帝死了”。随后又在第243 节题为“喜悦的含意”中再次指出:“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上帝已死’;对于基督教上帝的信仰成为不可信的了——已经开始把它最初的阴影投在欧洲大地上”。〔1〕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查拉斯图拉之序篇”中, 查拉斯图拉在下山的路上遇到森林圣哲,问圣哲干什么事,圣哲答道,他在制作赞美上帝的诗歌,查拉斯图拉心中暗想“这位老圣哲在他的森林里,还不曾听说“上帝已经死了”。一些哲学家鉴于尼采这两本书写于尼采患精神分裂症前不久,便断定,这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家略带乖张的观点,他后来不是疯了吗?何以见得这不是一个近似于疯狂的念头。或者可以说,即使不是疯话,最多也只是一个无神论者个人的极片面的观点。为了避免草率从事,我们必须弄清楚尼采这句话的本来意思。
笔者认为,“上帝死了”确实是哲学家个人的见解。但是,却不仅仅是无神论者的一个断言,也不是思想家乖张的观点,它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它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或者圣徒的宣言。 《快乐的科学》第126节“疯子”最能体现出这一特点。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原文全文摘录如下,这样做尽管显得冗长,却可以对尼采的基本思想有一个清晰的印象:
“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疯子大清早手持提灯,跑到菜市场,不断地大喊:‘我找到上帝了’!‘我找到上帝了’!由于四周的人均不信仰上帝,遂引起一阵骚动;怎么搞的!他失魂了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走错路了?另一个说。还是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人群之中,并张大双眼瞪着大家。‘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叫,“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如何犯下这案子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而将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怎么办?它将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空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阔的空间可让我们呼吸与休息吗?那儿不会更冷吗?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清晨点着提灯吗?难道我们听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近掘坟穴者吵嚷的声音吗?难道我们没有嗅到神的腐臭吗?——即使上帝也会腐坏!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神圣与万能的他如今已倒卧在我们的屠刀下,有谁能清洗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不会对我们显得太过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为伟大的了——而因此之故,我们今后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尚的历史之中!’
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然无声并惊讶地看着他。最后,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火熄。‘我来的太早了’,他接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家也需要时间,即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目睹!”
同一天,那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并唱吟他的安魂弥撒曲,而当有人问他缘由时,他总回答说:‘假如这些教堂既非上帝的陵墓,也不是纪念馆,那么,究竟是什么玩意?”〔2〕
尼采描述的疯子是一个信徒,他手提灯笼跑到菜市场时,周围聚集了一批“不信上帝”的人。这些人对于疯子说“找到上帝了”大惑不解,议论纷纷,进而哄笑不止。这疯子是信徒,而那些自认为有权嘲笑他的人则是没有信仰者。疯子主动承认,他找到的上帝是死的。因为他认为,“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教堂就是上帝的陵墓。杀死上帝以后,疯子感到有些惶恐,上帝死了好比地球被移到了太阳以外的地方,没有太阳,人何以生存,人何去何从?人从此是否永远迷失了自己?人能使自己成为上帝吗?疯子认为这倒是值得一试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成功,人类将生活在一个更高尚的历史之中。因此,“那疯子的话恰恰是说,‘上帝死了’这个说法与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们的乱七八糟的空洞意见毫无共同之外”。〔3 〕如果仅仅把“上帝死了”理解为无信仰的公式,就等于放弃了尼采最关心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深深的误解。
尼采在《反基督》第20节中明确指出:“在我谴责基督教时,我确实希望不要伤害拥有更多信徒的相关宗教。”〔4〕换句话说, 尼采只是把基督教作为一种错误的信仰进行批判,其目的是反对信仰中的错误,而不是反对信仰。在《反基督》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在对佛教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研究时,几乎是带着赞赏的口气谈论印度佛教。他认为,与基督教相比,佛教要真实一百倍。佛教是“活生生的遗产”,他能够面对客观的、冷酷的问题。佛教是“人们在历史上遇到的真正积极的宗教”。他并不谈及与原罪斗争,而是关心征服苦难的问题。尼采在谈到犹太教时说,犹太教承认人有“Sin”(原罪)。因此, 人生要经历种种磨难,才能洗清原罪。人在生活的历程中要经得起磨难,在苦难中顽强地生活。尼采认为,以原罪说为基础的犹太教徒的生活态度,充满了人趋向强力的意志,因此,他认定犹太人的宗教和生活准则是积极的。如果我们觉得,能够这样生活的人不仅是犹太教徒,而且也是基督徒,那么耶稣是历史上唯一的基督徒。唯有他以这样的信念生活,达观地历经生活的种种磨难,最后,带着执着的信念坦然受死。然而,这唯一的基督徒“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
《福音书》问世和保罗传教之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完全与早期犹太人的生活准则,从而与早期基督教的生活准则相违背。他们不是以积极的态度正视苦难的生活,而是对生活的价值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他们孜孜以求的只是来世的生活,把苦难的尘世仅仅看作步入天国的阶梯,或者威廉·詹姆斯所说的“外部脚手架”。这种基督教信仰,使人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以种种制度化的设施,强迫人们采取消极的生活态度。使人变成一个信仰的标本。人生在世,只是为了让那偶像化的上帝看一看,我是如何遵循您的教诲,摆脱生活的诱惑,成为无色、无性、无用的僵尸,生活在基督教看来是一种罪恶。因此,尼采认为,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误解了基督教赖以形成的基本原则,因此,它是一种错误的信仰。它使人鄙视生活和生命,从而使人失去生活信念,失去积极的创造热情,失去属于人的一切,人穷得只剩下一个称号——“偶像的信徒”,这一称号是以人失去属于人自身的一切价值为代价换来的。
由此可以看出,尼采不反对信仰,而是反对消极的、压抑人的活动能力和积极的创造性的信仰。他也不是一般地反对基督教,而是反对制度化了的、自保罗传教以来的基督教。因为制度化了的基督教,并不是基督教信仰,而是由传教士、偶像、戒律、制裁等制度化设施构成的统治方式。它是外在的、束缚人的桎梏,它象一切制度一样,以利益为依托,人在追逐利益时导致人自身的异化。而作为人的信仰方式的基督教,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精神生活,人依靠它而生而死,它是人生命的寄托。只有在信仰中,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人,才能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之路,信仰是人的专利。与尼采基本上是同代人的威廉·詹姆斯,对于信仰也做过类似的描述。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曾经说过,米达斯国王问精灵西勒诺斯,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在国王逼问下,精灵说“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这种民间智慧旨在向人们说明,生活是苦难的。为了生存,希腊人为自己创造了诸神,诸神不是偶像,而是人生存的信念。有了他们,
“人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而荷马式人物的真正悲痛在于和生存分离,尤其是过早分离——关于这些人物,现在人们可以逆西勒诺斯的智慧而断言:‘对于他们,最坏是立即要死,其次坏是迟早要死’”〔5〕
人的生活态度的改观,是因为人在苦难的生活中创造了信仰。人籍信仰而生活,信仰使人有了生活下去的依据。制度化的基督教,把上帝变成偶像,使之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为了追寻他,人必须放弃现世的生活,如此一来,便使被逆转过来的西勒诺斯智慧,重新逆转回去。人的生活,再次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上帝既然创造了人,却又剥夺了人生存的意义,人生既无意义,人需要上帝干什么呢?若是人不需要上帝,上帝的存在也失去了根据,所以,上帝死矣!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不是说“人们再也不能够信仰《圣经》启示的基督教上帝了。”在尼采心目中,基督教并不仅仅指是《新约全书》问世之后,或者保罗传教之后的基督教,也指一度在西方存在过的早期基督教生活。虽然那一段只能算作基督教的前奏曲,对于当时西方世界的影响,远不如制度化的基督教更大。但是,它身上积极的东西甚多,至少从它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早期基督教何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的真正原因。
作为一种生活信仰的基督教是颇具魅力的。它保持了属于人的一切古朴、真诚、执着、顽强、善良的东西。回顾古老的宗教,总使尼采感到心旷神怡。但是,随着《新约全书》问世和保罗的传教活动,特别是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体出现,基督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而是成为权力象征,体现了世俗政治与神权,理性与教条对人、人性、人的生活的专制。这种意义上的基督教与早期基督教信仰的教养迥然不同。早期的基督教充满活力,“就连一种非基督教式的生活也能肯定这种基督教,并且把它当作强力因素来使用。同样,反过来讲,一种基督教式的生活也并非需要这种基督教。正因为如此,一种与基督教的争辩,绝非一定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斗争,正如一种神学批判,并不就是对神学所解释的信仰的批判。”〔6 〕尼采实际上把作为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基督教信仰,与作为文化、教会权力、政体、世俗政治,一句话,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化的基督教区分开来。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不是指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基督教信仰死了。如果我们从宗教的角度看待“上帝死了”这一命题,那么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上帝和教会的权威丧失了。或者可以说,使真正的信仰窒息的因素死了。
在尼采心目中,信仰不等于教条,更不等于制度。确切地说,信仰与任何制度化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尼采也不是无神论者,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清楚地表明他对诸神世界的态度。认为希腊诸神是人创造的,人创造诸神是为了使苦难的生活变的可以忍受。尼采崇尚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的结合,无疑他所崇尚的是两种神的结合。因为尼采认为,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酒神仪式,展示了人面对苦难生活时的希望式的“乐天”。它们没有压抑人的强力意志,而是使这通过适当克制的形式渲泄出来,从而使生命成为可能。因此,尼采并不反对信仰,也不反对信仰神。但是,尼采反对一神教的至高无上的神,这种神是偶像,对于至高无上的神之信仰,实际上就是偶像崇拜。为了维护偶像,这种宗教便需要迷信,迷信是靠各种教条、制度来维系的。因此,也可以说,尼采说“上帝死了”,意味着教条的信仰和对偶像的崇拜,使教会成为嗜血的东西。血淋淋的基督教会非但不能拯救世界,反而用偶像和迷信窒息了世界,世界由此成为没有正当理由的存在。上帝创世方显出上帝的本领,而这个世界由于上帝的存在已经僵死了,上帝到哪里去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呢?按照尼采一贯的见解,如果一种东西不能促进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它就对人的生活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可以说它死了。
信徒创造了上帝,也杀死了上帝
上帝是怎样死亡的呢?死于虔敬,福音书和教会之手。尼采在《反基督》的开篇用朦胧的语言说,“我们面面相视。我们是北极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地方有多么遥远。‘你在土地和水中都不能找到通往北极人的道路’。……穿过北极、穿过冰层、穿过死亡——那里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幸福。”〔7 〕这厚厚的冰层就是指以基督教信仰为背景的大文化。穿越这一切,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自我、生命和幸福。然而这一切谈何容易,漫长的历史早已经遮盖了原本清晰可见的路,我们不知道自己如何进来,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出去。这就是现代病。一种慵懒、满足于无所作为的平静、习惯于说“Yea ”(是)和“Nay”(不)的现代病。生活在这种现代病中, 还不如生活在冰层更好些。尼采指出,要找到出路,就必须说明我们是如何进入这没有土地,没有水的冰天雪地中来的。换句话说,只有说明基督教的起源,说明基督教何以一步步走向错误,我们就能真正找到上帝死亡的原因,纠正制度化的基督教,走出这了无生机的冰层。这个过程通常被福柯称之为追溯“谱系”的过程,它具有治疗作用。揭示上帝的死因的过程,也正是治疗错误信仰的过程。
尼采指出,基督教被称为虔敬的宗教。然而,正是虔敬这个听起来似乎十分美妙的东西,把上帝变成死囚。“虔敬与一切强身健体的激情相对立,而这种激情能够扩大人的活生生的情感的能力。因此虔敬是一种抑制性的东西。一个人要是虔敬,便会失去强力”。〔8 〕虔敬会使苦难加重上千倍,使苦难像瘟疫一般流行。在某些环境下,它将使人失去整个生命和活的能量。然而,这只是虔敬小试牛刀。还有更严重的。如果人们凭借虔敬的作用来测量他的影响,他对生命究竟有多大威胁就一目了然了。
虔敬要求人的目光只追随着上帝的教诲,他不求行动,不求发展进步,不求充分发挥自己的强力意志,在苦难中孜孜以求地生存,他要求人们除了信仰之外不能有任何所求。他津津乐道的东西是上帝的拯救和不朽。为了被上帝拯救出苦海,他要求人必须全身心地献给上帝,除此之外不能有其它的作为。久而久之,人类文明中的一切进步的、积极的东西都将被虔敬所窒息。长期过着虔敬生活的人,丧失了人的一切有力量的东西。于是虔敬将挫败一切进化法则。虔敬的作用在于保存一切应该而且必须被摧毁的东西,他总是为保卫那些受到生命谴责的东西而战,他赋予生命的总是一些阴暗的东西。
人类把虔敬称之为道德是一种十分不明智的冒险行为。因此尼采告诫我们:“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虔敬产生于虚无主义的哲学立场,它的档板上赫然雕刻着否定生命,并且使否定变得有价值。”〔9 〕它的最大作用在于用虔敬的本能反对一切保存并且提高人类生命的本能。虔敬劝告人接受毁灭,当然他不把这称作毁灭,而是叫作“来世”,或者上帝,或者真正的生活。尼采指出,从哲学史上看,亚里斯多德就曾经指出,虔敬是一种疾病,是心灵的一种危险的状态。在一切不健康的现代主义中,任何东西都没有象虔敬那样不健康。它之所以是最不健康的,乃是因为它反对人采取任何保存生命的措施,一切代表人的强力的东西,都被视为不虔敬而受到禁止。它用邪恶来称谓人的健康的本能。强壮的人、积极行动的人因为没有以赞赏的目光注视上帝而受到斥责,被他们称之为无家可归者。它倡导一切软弱、低下、拙劣的东西,把一切健全的生命所拥有的积极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视为敌人而大加笞伐。由于虔敬盛行已经近两千年之久,它已经大大地腐蚀了人的理智中最有生气的力量。人类罹患重病,首恶当是虔敬。虔敬使人退化、软弱、无所作为、没有创造性。试想神、上帝都是人创造的,只有强壮的人才富有这样的创造力。尔今,人已经衰弱到朝不保夕的地步,如何还能继续保护并且再创造出他自己理想的神灵,上帝休矣!因此,从基督教的性质来看,完全可以断定,孱弱的信徒根本无力保护并且继续创造出人类理想中的神。虔敬杀死了上帝,或者说至少虔敬是上帝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尼采对于宗教虔敬的批判必然会引发对于上帝概念的批判。人对上帝虔敬,在信徒眼中是最高的美德。然而,上帝是什么?尼采认为,上帝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存在,他是人创造的。人生活在苦难的世界中,一切能够使他生存的条件,或者至少他认为能够使他生存的条件,都会使他兴奋不已。他常常把种种希望投射到一个富有力量的对象身上,于是神便集中了人类心目中的一切美德。他富有、强大、自信等。人类需要这样一个神。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只是一种感谢形式。人们为自己的存在而感谢他:为了生存人类需要神”。〔10〕但是,既然神是人造的,就必定会集中人的一切能力。他利弊兼备,亦友亦敌,亦善亦恶。尼采这里所说的神,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古代希腊的神,或者犹太教的神。然而基督教阉割了神的一切自然本性,使之变为一个“善”神,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它除了引来那痴迷的虔敬目光以外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人有喜怒哀乐,人也需要把这一切投射到某个对象身上,而基督教的神,“恰恰违反了人类的倾向,因为人类需要恶神,也需要善神”。被阉割后的基督教的神,既无胜利的喜悦,也无失败的沮丧。他不食人间烟火,这种神无人能理解,他已经不符合人们造神的初衷,谁还需要他呢?上帝当然必死无疑!
尼采还对基督教的心理基础进行了分析。尼采指出,基督教的心理状态中,被征服和被压抑的本能占上风。因此,基督徒中最关心是他们如何能够被拯救。随之而来的是不厌其烦地讨论自己身上的罪过有多少,如何洗清罪过,自己如何虔敬得不够,如何进行忏悔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如何获得良心才能保证进入至福王国。他们信奉禁欲主义,把肉体视为不洁的东西,摒弃一切感官和肉体的要求。在这种心态下形成的信仰是阴暗的,尼采嘲笑基督徒不能公开讨论自己的信仰,甚至进行忏悔的场所都是一所黑屋子。“这里也没有公开的交往,隐蔽和黑暗的房子就是基督徒”。〔11〕对于苦难的恐惧和对于拯救的期待,扭曲了基督徒的心灵,使他们的心灵异常阴暗。他们残忍地对待他人,尤其是非信徒和异教徒。他们不自觉地把心目中的地狱搬到了人间,用幻想中的地狱惩罚对待一切不合他们意图的人。他们憎恶地球的主人,憎恶贵族,憎恶知识、智慧、勇气、自由和骄傲,憎恶一切感官和感官享乐。基督徒也口口声声地高叫博爱,然而他们唤起人的爱不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更有生机,而是为了让人们更驯服。基督徒念念不忘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一个目的,使自己将来被拯救,进入上帝的至福王国。尼采鄙夷地称基督徒为进行“祈祷的野兽”,作为野兽还能有什么真正的信仰,人可以创造神,而兽如何能够再保护并且创造神呢?上帝倘若是兽的信仰对象,他何以还能作为人的信仰对象而活着?
最后,尼采把他那批判的笔锋转向福音书。尼采认为,福音书是上帝致死的主要原因。什么是福音?福音书答曰,就是发现真正的、永恒的生活。这不仅仅是一种承诺。这种生活就在这里,就在你自己之中。他就在爱之中,不用静修和独处就要以得到。在充满融融爱意的真正、永恒的生活中,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作为上帝的孩子,人人都是平等的。福音书所倡导的真正的、永恒的生活,在尼采看来不是积极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要求人避开真实的世界,遁入自我之中。福音书勾勒的真正的、永恒的生活,使人“生活在没有任何现实的世界中。只有内在的世界是唯一‘真实的’、‘永恒的’世界。”这种生活没有自然死亡概念,因为死亡不属于福音书所描述的生活。死亡时间也不是福音书的概念,因为时间只属于肉体生命。上帝的王国没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它只是人心中的一种体验,它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因此尼采认为,福音书中描述的生活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生活方式,他是无生命的,消极的。它没有积极的抗拒,没有捍卫自己的权力,他没有努力避免最不如人意的结果出现,他不能喜自己所喜,怒自己所受不公,他不能谴责他人的过失,亦不能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如果有成就的话)。总而言之,他什么都不能,他什么都没有,那他活着干什么,要上帝干什么?尼采指出,福音书所提倡的生活根本不是耶稣传教时提倡的生活。从历史上看,真正按照基督徒生活准则活着的基督徒只有一个,他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本人,然而他已经死了。倘若说耶稣死后,其精神尚存人心中,那么自从福音书问世以后,耶稣真的死了。因为耶稣生活的准则已经被福音书葬送了。基督教的发展史,就是通过福音书逐步误解基督徒生活准则的历史。因此,它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它的历史命运是,从一开始它就患了不治之症。患病的基督徒教,最终不得不靠教会的力量维持自己的苟延残喘,因此,尼采说教堂是耶稣的墓地。
信徒们首先用自己的虔敬,用自己盲目的崇拜扼杀了自己活生生的创造力,使自己成为上帝的奴仆。他的生活只有一个价值(如果可以称之为价值的话),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意志。而所谓上帝的意志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福音书的意志,甚至教会的意志。信徒牺牲了一代代人的真实生活,建造了一个根本不体现上帝意志的基督教会,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基督徒这个称呼,而失去的是整个现实世界的现实生活。吉勒斯皮(Gillespie)先生概括说,“尼采说上帝死了, 这是因为人太软弱了,根本无法创造并且再创造上帝和真理,而这恰恰是保持流行的信仰所不可缺少的。用他的隐喻式的语言来说,上帝死于人的虔敬,死于虔敬所造成的人的软弱和意志薄弱。”〔12〕神本是人造的,假如人失去了创造性,就等于失去了造神的能力。“两千多年没有新神出现”,证明了人类处于无创造力的软弱状态,软弱的人根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维护那个听起来十分强大的上帝,上帝死矣!
注释:
〔1〕尼采:《快乐的科学》,尼采文集《悲剧的诞生卷》,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6页。
〔2〕尼采:同上,第246—247页。
〔3〕海德格尔:《林中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年,第204页。
〔4〕Nietzsche,Antichrist,tran.H.L.Mencken,New York,P.68.
〔5〕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第12页。
〔6〕海德格尔,《林中路》,第204页。
〔7〕尼采:Antichrist,P.41.
〔8〕同上,P.47.
〔9〕同上,P48.
〔10〕同上,pp.63—64.
〔11〕同上,p.72.
〔12〕Gillespie,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Chicago,1995,p.xi.
标签:基督教论文; 尼采论文; 上帝已死论文; 悲剧的诞生论文; 文化论文; 快乐的科学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