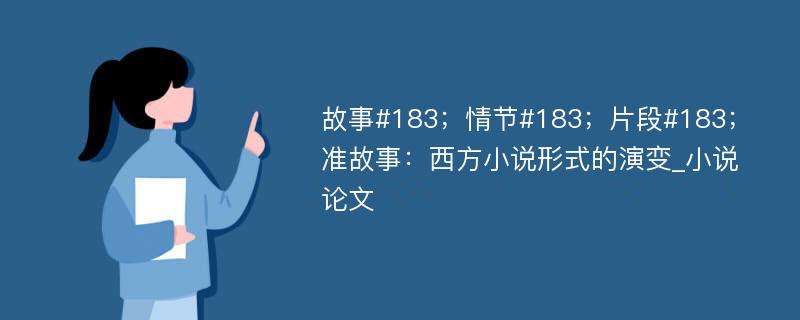
故事#183;情节#183;片断#183;拟故事——论西方小说形式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事论文,片断论文,情节论文,形式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西方小说形式的发展,自狄德罗、福楼拜以来,小说对传统的背离和反叛愈演愈烈,甚至于“对叙述技巧和程序的试验”〔1〕已成为当代小说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小说的结构形式经历了故事、情节、片断和拟故事的衍变过程。在本世纪初,“形式”成为小说评论关注的中心。西方评论家们断言:“谈论内容本身根本就不是谈论艺术,而是谈论经验;仅仅当我们谈论实现的内容,即形式,即作为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时,我们才作为艺术家说话。”〔2〕而当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刻,人们猛然回首,竟不再能够如此自信地重复这段话了。在形式经过极度的扩张,最终完全吞食了它所意欲实现的内容时,形式自身的存在由于缺乏相应的参照而显得极端空洞与荒诞。与此同时,当后现代小说在结构形态上的革新走到了B·S·约翰逊等人的活页小说时,小说家们把小说的实验已经做到了极限。正所谓:“某些形式已经枯竭,某些可能性已经试尽,”〔3〕小说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自杀的悬崖,小说文本实际上完全割断了与现实的参照关联,成为不指涉任何世界的、不透明的文字集成块。
“在上一个三十年里,与历史上任何可比时期相比,更多的小说出版了,其质量高低姑且不谈,甚至没有任何时代对小说究竟是什么更缺乏确信的把握,或者更加怀疑‘想象的’文学的价值和功能。”〔4〕在这个多产的时期里,小说文本已经让人们捉摸不定;小说形式上的变革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如今,形式成了目空一切的自我反照的范畴。”〔5〕人们要求冲破混乱的语言和结构的“牢房”, 要求呼吸指涉意义的新鲜空气。这是保罗·德·曼的“寓言阅读”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他的方法也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置换”。〔6〕因此, 今天我们来谈论形式,不能仅仅终止于形式,而是要回到文本和阅读背后所立着的那道“威严可敬的道德指令”。〔7〕重新强调“语言的内在、 形式和自身结构同它们的外在、指涉和公开效果之间的关系”。〔8〕当代西方关于文体的形式与意义之争,与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之间的哲学之争颇有关联。伽达默尔在与德里达的一次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对话中宣称:“任何开口说话的人都能希望被人理解,否则他无须说也不用写……然而无疑德里达认为(如果我试图理解德里达,我希望他能谅解我),对于本文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对他来说,任何以书写形式出现的字词总已是一种缺口,这尤其适用于文学的文本……”〔9〕这场对话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与“拒绝理解”。在伽达默尔以及他所代表的、具有极其古老的传统的解释学看来,文本并非是一个封闭的天地,任何文本都以阅读作为实现其功能的唯一途径。而文本之所以能够被“搁置”起来,即脱离它们的话语参照而单独存在,仅仅是因为它尚未曾被人们阅读的缘故。一旦作为一个阅读的“事件”发生了,我们就不会仅仅看到了文字、领会了语义而不同时联想到它的意义即参照。而后现代小说文本如果自动地以混乱不堪的形式来将自身封闭起来,它无疑就在拒绝理解。就人类而言,“理解是人的存在的原始特征和基本方式。理解行为发生在人类生存的一切方面,体现了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全部关系,具有不可否认的普遍性。”〔10〕文学文本作为一个语言文字的世界,与人的唯一关联就在于理解,这一点也是不可置疑的。因此,文本对理解的拒绝,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对其自我存在的否决。
在一种召唤理解的大气候中,西方小说文本的结构形式在经历了片断式的混乱和绝望之后,开始显示出一种对叙事的连续性的回忆,并且在反讽的形式掩盖下,走向了一种隐含着故事这一古老结构形态的模拟式复杂叙事,由于这一新的结构形式同故事的传统关联颇多而又以戏拟和模仿加以革命性改造,所以姑且称之为“拟故事”。这种新的尝试,是以故事式的清晰叙述为理想的一种“革新”。这种貌似回归的革新并非小说家们的又一次异想天开或花样翻新,而是一种严肃的自我拯救的手段。因为后现代小说变得极度混乱、封闭、不可卒读之时,小说世界已经走到了科学所预见的热死状态。也就是说,小说世界中的熵已达到了最大值,处于这种状态之下,一切演化、变革、创新都失去意义,因为一切都已归于死亡。于是,唯一的出路便是向小说的源头回归,退一步海阔天空。
故事
文学史家大多同意,欧洲小说起源于《圣经》和《荷马史诗》。但是,可以明确地称为小说的最早文本大概可推《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从这两部小说及其随后的众多文本可推导出:“散文小说的最简单形式,是记载一连串每每惊人事件的故事。”〔11〕因此可以说,故事是小说最初的结构形式。这里,我们所说的“故事”,不仅是“作品中叙述的,按照它们的自然顺序排列的事件”,〔12〕更多的是指“对一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13〕另一方面,在西方古代文论中,我们不难为“故事”这一原始的结构形式的形成寻找到美学依据。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到关于“故事”的确切定义,只需把其中的“悲剧”置换成“小说”:“悲剧是对一件圆满、完整、又颇有规模的行动的模拟。……所谓完整,指有始、有中、有末。所谓始,指事之不一定继他事之后而起,但他事则继其自然发生。所谓末,指事之必然或多半继他事之后自然发生,但再无他事继其后。所谓中,指事之承前启后而言”〔14〕亚里斯多德这里强调了“完整”、“有始、有中、有末”和事件的“自然发生”,从而明确地指涉了故事的下列三种叙述成规。
首先,时间的顺延性是故事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叙述成规。“倘若小说家在他的小说结构中,不谈时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必须沿着故事的线索(哪怕一点一滴也好)写下去,必须顺着那条冗长无比的绦虫摸索下去……”〔15〕在《十日谈》中,开头是作者阐明讲故事的理由:为逃避瘟疫出城的人们自娱自乐。随后按照顺序从第一天到第十天依次排列。《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构架同《十日谈》极为相似,一群人去朝圣,事先商定好“每位在去坎特伯雷的路上要讲两个故事,作长程中的消遣”。〔16〕然后按照所抽到的签号依次讲叙。上述两部最早的小说都采用了一种在一个大的框架中堆砌许多各自独立的故事的结构形式。它们实质上是两部短篇故事集,而时间的顺延性是其唯一的结构线索。其次,故事的第二叙述成规是“有头、有身、有尾”。这种行动的整一性显然直接借鉴于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理论。珀西·卢伯克在欧洲第一部系统的现代小说理论著作《小说技巧》(1921)中强调说:“开始使人感到各种方面都会很好地发展,到结尾时,显示出一种正式收尾的样子。而在头尾两点之间,故事发展过程是充满了疑问的。”〔17〕在《堂·吉诃德》中,这一叙述成规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出来。小说开头以主人公宣誓成为“骑士”开场,中间部分以他的三次出游为主要内容,最后以他的死为结尾。最后,作为前二种叙述成规的引申和发展,故事的第三叙述成规衍变为连贯性。即小说在结构上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前后贯通一气的联合体。引发这一结构效应的方式除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之外,还可以利用人物来把一系列不连贯的故事串联起来,使它形成一种单一整体的样式。这在自《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鲁演逊飘流记》中的鲁滨逊、《查第格》中的查第格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充当结构线索的作用。特别是法国十八世纪初期的作家阿兰·勒内·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中的吉尔·布拉斯,他“完全不是人,而是一条缝合小说情节的线——这是一条苍白无力的线”。〔18〕
情节
当狄德罗提出“美在关系”,他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亚氏以来的整一、秩序、和谐、统一之说的承接,同时也是一种狡猾的反叛。因为他所谓的“关系”既包括了和谐的关系,又能够涵盖不和谐的关系。事实上,他已经提出了美与丑的相对论,同时,也动摇了故事中的整齐划一的统一性,对故事的完整性进行了象征化改造。“‘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便是情节。”〔19〕福斯特这个著名的比喻道出了故事同情节的主要差异。关于这一点,福斯特又进一步强调:“故事与情节不同,它可以成为情节的基础,而情节属于一种更高形式的有机体。”此外,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在其早期也区分了散文作品展开结构的两种方式:“情节的展开和讲故事。”〔20〕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还从艺术技巧上强调了情节与本事的区别:“情节的概念过于经常地与事件的描写相混淆,与我建议之为本事的东西相混淆。《叶甫盖尼·奥泥金》的情节不是主人公与塔吉雅娜之间的恋爱,而是通过插进打断叙事的插叙方法,对这个故事的情节加工。”〔21〕
上述论述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故事式的叙述过于简单化了,人们要求小说能跟上生活的脚步,人们意识到“最流行的那一类小说把我们寻求的东西真正抓住的时候少,放跑错过的时候多”。〔22〕因此,许多小说家开始通过种种途径,进行形式上的探索,力图摆脱讲故事的公式化、程式化的老生常谈,以求更加真实、逼真。相对于故事而言,情节的叙述特征主要有两大发展。
首先,因果关系取代了时间的顺延性,成为小说叙述中最重要的成规。在《简爱》、《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复活》、《悲惨世界》等大量的情节——因果关系为主要叙述成规的十九世纪的小说中,作品开头往往是一段颇能引人入胜的预叙,随后再进行一段补叙或追叙。这正是福斯特所说的“王后死了,原因不详,后来才知道她是因国王去世而悲伤过度致死的。”〔23〕例如,《悲惨世界》开场是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的感化,而关于冉阿让是谁,他如何入狱和获释,读者随后才知道。这种时间上的倒错由于有强大的因果关系为后盾,并不使读者感到困感,它事实上是小说家们用以取得戏剧效应的最方便手段。情节的这种对时间顺延性的侵犯,又自然而然地割去了传统故事的“头”。小说从此常常以一个场面或一个形象开场,甚至可以说,现代小说家有权利选择一个任意的点来开始他的叙述。
其次,小说结构形式由故事的单线条走向情节的复调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小说所描绘的再也不是单个人物的线性行动,而是众多人物、行动和事件的总体场面。例如《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前者以四大家族及其兴衰为描写对象,四条线索纵横交错,以宏伟的气魄构建了小说的叙述框架;而后者则以安娜和列文两条几乎并例的线索和平行发展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构架。在这种复杂的、多线条的情节结构中,坚持同一事件的连贯性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一条线索到另一线索的转化和移位在上述小说中俯拾即是。
西方小说发展到本世纪初,即现代派小说出现时,又有了更大胆的、叙述形态上的飞跃。实际上,现代派小说中的情节,已属于一个广义的概念。普鲁斯特就曾声明:“大多数小说都凭情节,造成某种悬念,通过一系列冒险事件,达到必然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追忆逝水年华》没有情节,书中没有这样的东西。”〔24〕韦勒克·沃伦曾经指出,“情节”一词的含义扩大到能够包括契诃夫、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已经是一种延伸。同时他又认为,这种内涵的扩大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于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将乔伊斯、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的作品也包括进去,把“情节”作一次更大胆的延伸。这里,放宽标准的依据是,他们的作品虽然复杂,但仍是可复述的、可理解的,因而能符合韦勒克的定义,应称为“较复杂的情节。”这种“较复杂的情节”较之于一般的情节主要有两大特征。其一,表现为时空观念的巨变。当亚里斯多德宣称“凡是人的悲或喜”,“都是以动作来表现的”时候,他几乎没读过小说,尤其没看过现代小说——他只看过《奥德赛》,并没有看过《尤里西斯》。〔25〕在以《尤里西斯》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中,作者所潜心叙述的不再是人物的外部动作而是他的内心意识之流。在《尤里西斯》中,“乔伊斯打破叙述时序,把小说的结构变成了传达其美学意旨的工具。”〔26〕此外,“《尤里西斯》具有一种空间感。”〔27〕具体表现为破除原有的时间顺序,突破语言的线性化局限,把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呈现于读者面前,达到某种共时性。乔伊斯的这种象征的结构对故事、情节等结构形式的冲击很大。然而,尽管如此,在以《尤里西斯》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中,“具有一种同读者群体共享的秩序相对立的、独特的、个人的想象秩序。”〔28〕因此说,意识流小说并没有完全背离传统,它仍然具有“一个由人生阅历之流交织而成的梦幻轨迹。这条梦幻轨迹或称愿望轨迹象一条线索贯穿于内心独白,把小说结构成一个整体”。〔29〕其二,表现为向开放式结局的转移。即有意识地反叛传统小说中“有情人终成眷属,坏人们狼狈不堪,阴谋诡计统统被戳穿”的结尾模式,走向不封闭的、开放式的结尾。最明显的有意而为之的此类小说文本可推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以三种不同的结局作为小说的虚拟式结尾,极为明显地指涉了各个不确定的开放式结尾的存在。其他的例证还有乔伊斯的《芬尼根的觉醒》和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抄龙!》。在《芬尼根的觉醒》中,作者主要引进了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并使作品的结构“与维柯的循环、与永无休止的沉浮降升,产生一种对应关联。”〔30〕小说以一个句子的中间部分开头,又以这个句子的开头部分结束,象征一种循环。作者声称,读者可以从此书中任何部分开始阅读,进入循环。这里,结尾向本文的内部世界开放了。《押沙龙,押沙龙!》则更进一步。小说直到最后一页仍然布满无数疑问。昆丁和施里夫虽然根据推测编造了一个迹底,但是其中太多的想象反而更引起读者的疑问。这种只提问不回答的手法导致了一个真正的开放式结尾。
片断
如果说,现代派小说是渴望模拟生活的模糊性,并将其展示出来,那么后现代主义小说则是在认识到世界真正的混乱之后,企图面对混乱、接受混乱并且进一步制造(文本中的)混乱。作家们意识到:“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秩序……我们必须就范于混乱的要求。”于是他们纷纷宣称:“我偏爱不连贯性……我在混乱中扎混儿,我的整个一生都是为它而存在的,是通向混乱的一次旅程。”(弗德曼)“我靠混乱兴旺起来。”(苏克尼科)在这种大混乱中,后现代主义小说创造出无数无意义的、不可拯救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这里,片断和不连贯性被接受为规则,记忆的幻觉被湮灭了,因果被认为是可以转换的,逻辑的世事被作为碎片玩弄。〔31〕后现义主义小说创造了一个不可复原的片断式文本。象唐纳德·巴塞尔姆的《雪白》、理查德·布鲁蒂根的《在美国捕鳟鱼》、托马斯·品钦的《V 》和《万有引力之虹》等小说中的片断是望远拼凑不成一体的,无论是从历史的、神话的、心理学的角度,还是以象征的、隐喻的方式来重构。后现代片断小说对任何阐释性的话语都不信赖,唯独信赖孤立的、沉默的片断。“后现代主义者只是割断联系,他们自称要持存的全部就是片断……”〔32〕。
这种片断式的零乱所带来的正是文本的不确定性。面对只以破碎残片为生存形态的后现代小说文本,“我们犹豫不决,只作相对考虑。不确定性确乎渗透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它构成我们的世界。”〔33〕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小说内在规定性的丧失。小说占有了其他体裁(诗、散文、哲学文本)等领域,却独独丧失了自己的领地。它不再讲故事,不再叙述,它已退化成一种语言的片断的随意聚合。“如此下去,小说将变成最危险的词语的抗争,一种最终不了了之的措施的堆辞,一种涉入其它思想领域而缺乏统一性的大杂烩。”〔34〕文本的这一不确定性进一步演绎成对阅读与解释的抑制与拒绝。“无等级秩序的原则意味着在创作这个文本的过程中,拒绝对语言或其他元素作有意识的选择,而对于准备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阅读文本的接受者来说,无等级秩序的原则意味着避免形成一种首尾一致的解释。”〔35〕后现代主义小说在结构形式上如此刻意模仿世界的混乱,主要是因为“它不想落入某种易于辨认的模式和节奏,于是使在阅读程序上效法了世界对于解释的抑制。”罗兰·巴特则更加明确地宣称,“只有‘不可卒读’才体现了文学的最终目的,因为它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使其注重于符号本身,而不去寻找额外的意义。”〔36〕他以他那优雅的符号嬉戏完全排除了对文本进行解释的可能性。“我抚摸着我的语言,它也轻抚着我,仿佛言语也代替了手指。”〔37〕在这种迷乱的欢欣中,语言的多重意义转化为多重欲望,解释成为一个不知趣的第三者。
拟故事
当小说“嘲讽叙述并使其内在化,小说拒绝了它的大众读者。但在小说免除了十九世纪美学的同时,它永远不能象诗歌和批评那样体面地抛弃当作顾客的十九世纪的读者意识,那样有点不洁但最终不可动摇的与现实的联系。”〔38〕因为“在小说里,总存在一种并非自愿的意义过剩。绘画通过改变几何学的原理变得自发自足起来,小说则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与其总的环境发生关系的互相影响。”〔39〕小说脱离不了现实,关键在于,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另外,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又抱怨着:“我们‘纠缠在故事中’,我们的自我解释是由我们的传统的童话和记述所决定的。”〔40〕人、语言、小说这三者就象是三个缺一不可的支撑点,少了任何一点,就无法取得平衡。西方小说正是在一度失去平衡之后,又再次“设法与书页之外的读者和世界重新进行联系。”〔41〕80年代以来,西方小说在结构形式上产生了一种回归的趋势。例如,曾经最热衷于小说试验的巴思,“发现自己对叙事传统的不同侧面产生了巨大的兴趣,”〔42〕于是,他“决定回到18世纪……去考察英文小说的源头……回到英文小说的最早形式——书信体小说中去。”〔43〕在这一复归中,他创作了小说《书信》,并且认为它“代表着利用并且遵循小说的形式的真诚努力。”比尔·奥利弗在《美国短篇小说的新繁荣》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接近生活的小说——充满可认识的人物和主题、情节和戏剧性,有开端结局的小说,已在厌倦了残缺和古怪的广大读者面前重新维护了自己的形象。”〔44〕在法国,这种回归更加明确。曾经是新小说派的主要代表作家罗伯一格里耶推出自传作品《重现的镜子》;而被誉为新小说之母的娜塔丽·萨罗特于1983年率先出版了真实记录其童年生活的自传作品《童年》。新小说派作家纷纷回归自我,回归叙事,开始创作“一个真实的人以他自己的生活写成的散文体的回忆故事。”〔45〕人们重新发现了小说是一种道德教训,一种生活方式。小说作为一个不及物动词的时代结束了。
然而,小说结构形式上的回归并非简单意义上的重复和模仿,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模拟。因为人类不可能停止生长,更不会退后到去相信:“仅仅存在着一个故事,包容一切人类事件”〔46〕的地步。企图以一个简单的故事来描绘一幅具有终极意义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童话。因此,小说结构形式的回归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回归到故事的简单化和程序化,而只是一种反讽式的戏拟。例如巴思的《书信》尽管“仅仅包含一些书信,但是这些书信的内容及其写作与阅读使它的复杂性不亚于《芬尼根的觉醒》。”〔47〕因为在今天,要想当一名说故事的人,“只能采用反讽式的说法。”〔48〕。
尽管如此,“拟故事”一词之所以被用来归纳西方小说结构的新形式,关键仍在于“故事”。虽然,故事作为一种成规式的叙述手段已不再存在,但故事是小说的童年,小说的成长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抛开故事,就象人类的进步脱离不了自己的祖先,而个人的发展始终存有儿时的幻想一样。“小说是要讲故事的,小说而没有故事则无法成其为小说。故事是小说构成的基本层面,它决定了小说存在的前提。小说的其他诸种功能只有在故事的层面上才能生存和创造。没有故事,小说的所有美学因素将无以寄寓。”〔49〕也就是说,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内在规定性的重要因素,故事是小说存在的前提。故事的重要性是中外小说理论家们或多或少都曾留意到的。而我们这里所强调的故事更接近于结构主义者西摩·查特曼的观点。他认为,每部叙事作品都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故事,即作品的内容;其二是话语,即表达方式和传递内容的手法。在拟故事式的小说中,故事不再是一种叙述手段,而更是一种内容,一种意义,一种连续性。
首先,故事作为一种内容与意义,经过现代作家们的有意识的互文性改造,在文本中充当提示小说主旨的重任。例如《尤里西斯》和《押沙龙,押沙龙!》。而正如前文所述,在现代派作品中,主旨实际上已成为其构成整体感和统一性的唯一结构线索。因此,不难推论出,尤里西斯和押沙龙的故事其实在文本中具备了结构功能。拟故事正是充分地、自觉地利用故事这一结构功能来创作的小说形态。在意大利小说家伊卡诺·卡尔维诺的《如果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个旅行者》中“有一连串的开头,通向一个个永无休止的故事。因此,实际上有十个故事,从而把终点永无止尽地向后推延。”〔50〕而在巴思的《书信》中,“六个部分的众多故事缠绕在一起组成了第七个故事,”巴思“用框架故事的形式”〔51〕将小说构成一个连续性的整体。
其次,故事里所蕴含的连续性与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关联很多。人类无法摆脱时间之河,一切都在变动之中,而又都是前后相续的。故事一词在英文中,古义是“历史”,这绝非偶然的巧合。故事曾经确实是人的唯一的历史。例如,《圣经》和《荷马史诗》。故事的时间性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在符号的层面上向过去和未来伸延,具有了历史性。故事在小说中的永恒地位也可以从人类生存经验的重复性和自相似性来论证。人们大都觉察到,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生老病死是人人都注定要经历的,又是文学表现的固定范畴。正是由于现实生活的重复性和自相似性,才会有众多大同小异的民间传说和故事。于是,结构主义批判家将这种重复简化为诸种结构功能(普罗普)和二元对立的普遍模式。而从生活的自相似性来说,把某一个故事这一叉枝拿出来进行局部放大,便会得到一幅同生活之树极端相似的某种性质。因为故事貌似简单其实具有无限的嵌套性和丰富的层次感。而利用故事的叉枝对生活进行局部放大也正是小说大师们的拿手戏。最为突出的例证要算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了。《尤里西斯》写的是“一个地方一天之内发生的事,任何人都会写。”〔52〕然而,乔伊斯把它写成了一部现代史诗,展现了“全部生活,全部历史,”〔53〕并把它们“聚缩在1904年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中。”〔54〕。
在论证故事的永恒意义时,我们特别强调了故事与人及人的世界的关联。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故事中每每隐含着一个独立存在的、自己的世界。故事不仅仅是人的世界的延伸,而更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虚构的世界。当代小说家再也不象巴尔扎克那样为社会生活充当“书记员”了。他们惬意地漫游于自己的虚构世界中,只以心灵感应的方式同现实进行某种程度的沟通。这一类小说的大量例证是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一切都是可能的存在,无论如何神奇或不可思议都不足为奇。而在当代众多的以元小说类称的文本中,虚构世界的虚构行为本身已成为故事,并且充当了小说的结构功能。这就证明了,故事本身具有独立于人、现实世界之外的内在规定性。故事的这种本质特征更加强调了作为一种叙述形式其存在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任何归纳都是有例外或反证的,比如,《唐·吉诃德》虽然主要是一部符合故事叙述成规的古典小说,但它在主干故事中又插入了许多与主干故事无甚关联的小故事。拉伯雷因为无视小说严格意义上的连贯性,而被今人们称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二十世纪的后现代浪潮中始终能够以最清醒的叙述来抵制外部世界的混乱的小说家大概可推英国作家戈尔丁、大卫·洛奇、约翰·福尔斯等。这些例外和反证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故事作为小说的内在规定性的存在及相对稳定性。
注释:
〔1〕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页。
〔2〕〔28〕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3〕John Barth:"The Friday Book:essays and other nonfiction",New York,G.P.PUTHAM's SONS,1984。
〔5〕〔6〕〔7〕〔8〕〔33〕〔35〕〔36〕〔37〕〔38〕〔39〕〔41〕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307页。
〔9〕《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引自《哲学译丛》1991年第3期。
〔10〕伽达默尔的观点。转引自《读书》1993年第4期。
〔11〕爱·缪尔《小说结构》,引自《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12〕什洛米斯·里门一凯岚《叙述性的虚构作品:当代诗学》,麦修恩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页。
〔13〕〔15〕〔19〕〔22〕〔23〕〔25〕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5、75、76页。
〔14〕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七章,转引自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第79页。
〔16〕《乔叟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
〔17〕珀西·卢伯克《小说技巧》,引自《小说美学经典三种》。
〔18〕雅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故事和小说的结构》,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页。
〔20〕〔21〕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 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24〕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译林出版社,1991年版。
〔26〕Joseph Frank,"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From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
〔27〕〔29〕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186页。
〔30〕Armin Arnold,"Jams Joyce",Frederick Unger Publishing Co.,Now York,1969,P99。
〔31〕〔32〕佛克马编《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34〕纽曼《后现代气息——通货膨胀时期的虚构行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40〕T·德·布尔《从本质现象学到解释现象学》, 《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42〕〔43〕何帆等编《现代小说题材与技巧》,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
〔44〕比尔·奥利弗《美国短篇小说的新繁荣》,《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第129页。
〔45〕法国作家勒热纳语。转引自《外国文艺》1987年第1期。
〔46〕〔52〕B·S·约翰逊《小说——形式与手段》,引自《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780页。
〔47〕〔48〕Stan Fogel and Gordon Slethang,"Understanding John Barth",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0,P156.
〔49〕Max F.Schulz,"The Muses of John Barth",London,TheJohns Hopkins Univerisity Press,1990.
〔50〕Melissa Wstts,"Reinscribing A Dead Auther in 'If on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From"Studies on Modern Fiction",Pub.by Purdue Ressearch Foundation ,Vom.37,1991.
〔51〕Heide Ziegler,"John Barth",London,1987.
〔53〕〔54〕Water Allen,"The English Novel",Penguin,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