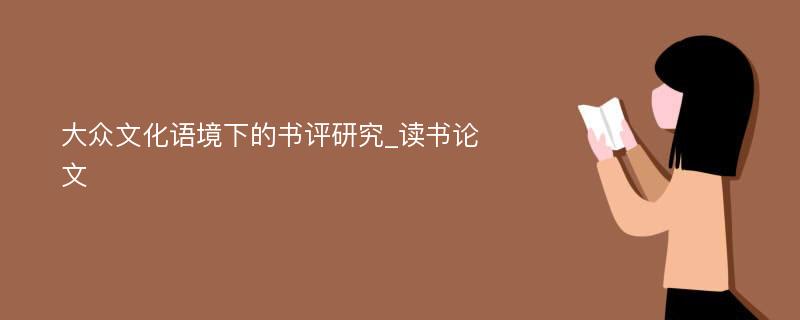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书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大众论文,书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6-0104-06
书评的文化身份
在大众传媒介入文化生活日益深入的当今社会,书评在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显著,甚至文学介入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借助大众传媒通过书评的形式开始它的接受过程。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信息时代的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对书评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尽可能作出理性而深入的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但是书评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本呢?对此我们当然不会落入本质主义的圈套去尝试给予一个清晰但是立刻就会招致无穷诘难的定义,不过这也无妨对其内涵作出比较确定的言说。必须承认,即使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宽广一些,不独书评,影评、乐评、画评以及摄影评论等文本形式也可以纳入这个问题予以思考。但是,限于篇幅以及因为书评本身的代表性,我们不妨把注意力集中到书评上。
首先,书评是关于书的评论。概而言之,书评的客体可以分为两类,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就非文学文本而言,它可能是旅游手册、烹饪指南、宠物饲养必读,或者关于哲学、环保、生物工程、基因疗法的科普说明等等。就文学文本而言,无论是专业批评还是作家批评,其批评客体可能是一本书,但更可能是单篇的文本或者文本的片断,或者一个作家所有或部分文本的集合,或者是由归属于某个名字的所有或部分文本集中体现的作家,或者是某个时代某种文化之下的文本集合所体现的作者。总之,专业批评和作家批评的批评客体可能是确定的,也可能是漫无边际的。相比而言,书评的对象比较确定,书评是关于一本(套)书的批评,虽然这本书可能是一个文本,比如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也可能是多个文本的组合,比如形形色色的小说集、散文集;这种组合可能是内在有机的,比如王安忆新近出版的《回忆上海》,也可能是随意松散的,比如“文化部长”龙应台的《这个动荡的世界》。其次,如前文所说的,书评的客体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对于这种差异,利维斯立即会紧皱眉头,不屑一顾;而德里达和保罗·德得曼会说:这一切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这些差别只是表象,因为并非关于书的批评就是书评。这里我们必须引入一种特别的历史主义的眼光,否则本文的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于是引出第二个问题——其次,书评是现代社会附着于大众传媒而诞生的一种文本形式。这是尤其不能忽视的关键,否则关于书评的任何讨论都只能是形式主义的。无论如何,我们决不会把柏拉图关于《荷马史诗》的评论视为书评,同理不会把王逸关于屈原《离骚》的评论视为书评。关于书评的认识,永远都必须以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为参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自然会明白,书评决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生产中的一个环节。第三,书评的商业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和作为文化事业自身的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就必须进入思考的范围。关于这一点,从作为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的书评出发,可以为探讨书评的价值提供一个极佳的入口。
书评和大众传媒
将书评的身份认证和大众传媒紧密联系起来,决不是一种机械的形式主义,相反,恰恰引入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思考向度。——当然,如今使用“历史主义”也是一种冒险,但是我们对反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们诘难已做好准备,不过需要另找时机予以应对。脱离现代社会下文化工业中的大众传媒,书评将变成一种无法认识的东西,它将失去自身的统一性,并流散到各种各样的文本中直到一无所有。坚持这样一种前提,自然会招致纷纭的责难。确实,书籍是一种古老的发明,伴随着它的诞生,与之俱来的就是关于它的批评。但是,毛伥、朱熹对《诗经》的批评,班固、赵翼对《史记》的批评,亚里斯多德和阿里思托芬关于《荷马史诗》的批评等等,我们决不会将之视为书评,还可以进一步大胆地断言,即使是莱辛的《汉堡剧评》也不能列席书评。原因不是别的,正在于他们的诞生缺乏文化工业下的大众媒体的语境。书评是关于书的批评,但是它只能产生在现代文化工业生产语境中的大众传媒上,产生在报纸、杂志、电视或者还有互联网上。——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在书评的身份认证上坚持出生论正是理论研究所要求的历史主义的体现。
关于这条我们必须捍卫的原则,并非只是出于某种既定目标的一种理论预设。书评不是书籍必然的衍生物,而是现代社会伴随着文化工业的壮大、出版业的逐步繁荣而出现的。因此,要正确认识书评,就必须把它置于现代社会甚至或者后现代社会的结构原则和文化逻辑之下,结合此历史语境中的大众文化与传媒的关系来理解。
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项标志性区别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最高法则,换句话说,商品生产成为社会运作的中心任务。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产品的匮乏,那么,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则相反表现为产品过剩,不是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资料的整体匮乏可以视为一种不成熟阶段的特例;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矛盾的焦点已经由生活资料产品的过剩进一步转移到符号产品的过剩,文化失序的问题日益凸现。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得到强调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资本自身的逻辑必然以追逐利润为目标,于是生产的目的变化为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对使用价值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尤其是世纪之交的科学管理和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建构新的市场、通过广告及其它媒介宣传来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1]。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同样遵循此逻辑。伴随着大众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出版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满足求知的需要,而是服从于资本自身的需要,结果自然是符号产品的过剩。符号产品的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则开始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初。
1980-1999 图书出版统计略表(注:本表数据来源于中国年鉴网.http://www.pac.org.cn/htm/nianjian/2000/.
种数
总印数
出版年 合计
增长率
(万册)
增长率
1980
15669 / 191013 /
1985
34106
1.18 3416950.82
1991
83275
1.44 5934450.71
1995
98987
0.19 6272340.06
1999 139339 0.41 7268050.16
注:此图书统计不包括中小学教材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早在1980年,中国人均书籍占有率就高达1.9本,1999年,人均占有书籍6本。如果再把文盲率考虑进去——据中国青年报国际扫盲日(2002年9月8日)统计,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成人文盲率已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下降到8.72%。但我国文盲绝对数依然高达8500万——这个数字将是6.6。年人均6.6本图书似乎并不高,但是考虑到实际人均图书购买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符号产品实际已经过剩。这一点从中国许多出版社高居不下的库存图书来看更能给人深刻的印象。据统计,2002年中国图书库存积压总量高达3000亿码洋。
伴随着文化符号产品的超量生产,作者的地位在这种产业化中被贬值了。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书籍的生产者是它的作者,出版社只是在编辑、复制和发行上进行操作。在文化工业形成之前,出版社的稿源绝大多数为自然来稿,但是文化产业化之后,自然来稿急剧下降,所占比例不过百分之五;甚至在某些出版社完全绝迹;与此相联系的是,在出版社内部,新型的策划编辑应运而生,并取得对案头编辑的绝对优势,选题策划能力成为衡量新时代编辑能力和素质的关键指标;在出版社外部,大量的文化工作室也诞生了,它们采取各种灵活的经营方式与出版社合作,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参与渗透到文化出版业,并最终控制了少数缺乏选题策划能力的小型出版社。今天,任何人只要步入书店,就会立刻发现,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比比皆是的是丛书套书,无论是高雅堂皇的学术著作,还是精美豪华的文学作品,以及追逐时尚迎合大众口味的通俗读物,甚至用于辅导中小学生应付考试的教学辅导书,无不统一着装齐头并进,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基本绝迹了。这些变化深刻地证明了文化生产的动力和动机已经由作者转移到了出版者,作者仍然还在耕耘,不过他现在已经沦为丧失生产资料为人做佣的雇工,惟一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的悲哀处境可能并不悲哀。文化工业的突飞猛进,使出版机构变成文化生产功率强大的发动机,它不仅生产文化商品,而且直接生产读者大众的阅读需要,当然,后面一项任务,它需要借助大众传媒来实现——这一点正是书评诞生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评是一种特殊的广告。
出版产业化是文化工业的必然要求,资本遵循自身的逻辑,生产的目的只能是销售。但是,在符号产品超量饱和的文化市场上,读者并不能自主把握自己的需要,需要并非预先给定的,也无所谓真实和虚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是对刺激和诱导的反应——阿多诺关于大众消费居高临下的精英意识遮蔽了他对此真理的认识——所以,惟一要紧的就是生产读者消费的需要。在文化产品相对过剩的形式下,资本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在生产文化商品的同时,生产消费文化商品的需要。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了书评,但是必须借助大众传媒帮助完成。
书籍不太容易直达受众,不仅因为价格比较昂贵,读者在购买之前要三思而后行,而且因为书店并非触手可及;但是以报纸为代表的各种传媒却完全渗透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借助它们,书评、书讯可以及时深入人心。但是,大众传媒绝非仅仅作为图书宣传的一种方便的工具,文化工业的内涵本身就包含了大众传媒的繁荣。它们不仅满足了出版机构传播书讯的告知需要,而且它们本身一旦设立,就必然成为催生书评的制度性机构。
1980-1999全国报刊出版统计略表(注:本表数据来源于中国年鉴网.http://www.pac.org.cn/htm/nianjian/2000/.)
出版年报刊种数
平均期印数
总印数
(万份/册) (万份/册)
1985 报纸 69814970 1997560
期刊470523952 255999
1990 报纸157615288.11
2069752
期刊607817145 184437
1995 报纸208917643.66
2632727
期刊758319794 233671
1999 报纸203818632.39
3183815
期刊818721845 284638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985年到1999年,无论是报纸还是期刊,总体而言,都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截止1999年,我国每年人均消费报纸265.3份,消费期刊23.7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更大一些。大众传媒的繁荣不仅可以满足出版机构生产读者阅读消费符号产品的需要,而且,作为一种庞大的产业,它首先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对于任何一种综合性的现代传媒来说,其关注的中心内容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娱乐。不必说中华读书报和《读书》这种专门刊发书评、书讯的报刊,几乎任何大城市的晚报、早报、周报、都市报、文学报,甚至商报、金融时报等都辟有读书专栏。就广播电视而言,比如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以及各地文艺音乐频道也都设有围绕读书的节目。因此,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正是这些专栏和节目控制着书评的生产。书评的作者不仅是出版者的佣工,它也是大众传媒的佣工。
在前现代社会,书籍的诞生是作为文化创造的进步结果,文化生产的动机和动力都由作者本人掌握;无论是诗人的发愤著书、不平则鸣,还是哲人对自然大道与社会规律的研究概莫例外;由此衍生的批评,其目的甚至不在于弘扬和传播特定的文本,而是以之为基础生发新的文化创造。但是现代文化生产的动机和动力被转交给了大众出版业。在文化工业的语境之下,不独书籍的作者沦为出版者的佣工,甚至书评的作者也不免这种命运。书评不再自发产生于读者的有感而作,而是受制于大众传媒自身的制度性需要,受命于图书策划人和出版者。
作为文学批评的书评及其辩证法
对大众文化语境中书评的身份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作为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的书评的辩证法了;以书评中的文学批评文本为例,是因为它本身的典型性。对文学批评的审视和考察历来是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的,其一是从作家方面,其二是从作品方面。当然这种区分一般而言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已,不过对新批评而言倒也是个例外。在现代阐释学或者接受主义批评蔚成大观之前,文学批评的对象主要是集中在作者身上,这一点无论中外皆然;经历了文本转向之后,作者被宣判了死刑,关于文学批评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文本之上,但是作者的幽灵仍然盘旋出没在批评者的笔下,即使是最严格的新批评家也不免为之深受困扰(注:新批评派主张将文学批评严格限制在文学文本上,但是当他们把批评对象从诗延伸到小说和戏剧,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松开新批评方法的紧身衣。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布鲁克斯的《邪恶的发现:(杀人者)分析》。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但是,文学批评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就是从批评主体来考察。从这一个维度来审视文学批评,姑且可以将之区分为三种批评:专业批评家的纯粹批评,作家批评,读者批评,或者称之为大众批评。但是还有一种批评文本更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与大众传媒密切相关的书评。在大众传媒介入文化生活日益深入的当今社会,作为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的书评的地位和影响也愈加彰显;甚至可以说,文学介入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借助大众传媒通过书评的形式开始它的接受过程。尽管如此,从批评主体来界定文学批评已经是一种冒险,而将针对文学文本而生的书评提示出来作为其中之一种,无疑具有更大的风险;确实,迄今为止,文学批评史上关于作家作品的那一种真知灼见来源于书评?且不说书评的话语模式缺乏学理、疏于文本细读、少深致辨析,多为停留于观感层面上的印象式的经验之谈,仅仅就它与媒体可疑的密切关系,以及隐藏其后但又昭然若揭的促销动机,似乎都使人有足够的理由将书评从文学批评的神圣殿堂中清除出去。但是,如果这种冒险有助于我们更理性更深刻地认识书评的文化身份,倒也值得尝试。
如果文学批评的身份严格从属于文学文本这一前提,那么,将书评从文学批评的阵营里驱逐出去就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为旨归的《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和《妥斯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能够被奉为文学批评经典,海登·怀特以历史哲学为鹄的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能够被奉为文学批评杰作,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书评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而拒绝接受它呢?况且保罗·德曼的批评就致力于证明,由于语言本身的修辞性(转义和隐喻)导致了它无法确切表达自己的真实意义,因此,文学与哲学、宗教、法律等文本一样都是虚构的、自相矛盾的,从而最终自我解构,不可阅读。文学和非文学之间、文学批评和非文学批评之间并没有区别(注:保罗·德曼关于文学与非文学的解构主义的观点,可以参阅保罗·德曼的《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拒绝接纳书评进入文学批评可以理解,但是因此而对书评不屑一顾,其种种理由虽然冠冕堂皇,但是适足以暴露传统文学批评的精英意识,为了维护自身的纯洁,而将自己自恋式地封闭起来,其后果不仅是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且无助于对文化的更理性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提示出作为文学批评的书评,不是为了在文学批评的殿堂里再邀请一位异质的佳宾,而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考察大众文化语境中书评的文化身份。讨论书评的价值可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当然,这绝非惟一的角度。那么,作为文学批评的书评能够给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呢?
我们不能奢望从书评里读到出自于专业批评家细致绵密、洞幽烛微的文本分析,也少有可能分享职业作家体贴入微、知冷知热的同感共鸣。前者如布鲁克斯的《叶芝的根深花茂之树》,沃伦的《邪恶的发现:〈杀人者〉分析》,后者如余华的《眼睛和声音》,王安忆的《残酷的写实》等批评文字(注:分别参见《读书》1998年第11期,《读书》1999年第11期。)。那么,我们能从作为文学批评的书评里得到什么呢?在现代消费社会,如果书评的作者已经沦为出版商的佣工,基本丧失文化生产的主动性,如果书评只是一种广告,一种生产书籍消费需要的特殊生产方式,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书评的价值何在?换句话说,除了生产受众的消费欲望,书评还应该具备别的什么东西?
书评的根本目的在于介绍新书,生产读者的购买欲望。这一点决定了书评作者在批评活动中的批评意识、阅读方式、批评话语等诸多特质完全不同于作家批评和专业批评。当作家以批评者的身份介入文本,他的兴趣和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与自己的创作甘苦声气相通之处,尤其落实在叙述技巧和话语风格上;与新批评家相比,作家批评显得更注重文本分析。至于专业批评家的文学批评,由于他们具备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训练有素的批评技巧,因此,他们的批评方法论意识非常显著,往往以一定的批评方法为指导或者为旨归。书评的外向性目的和特殊的语境决定了书评的作者既不可能像专业批评家那样,以一定的批评方法为指导或者为旨归,对批评的文本进行精深的阐释,也不可能像作家批评那样对批评文本作细致的体验。书评不可能是细读式的,只能是宏观的;不可能是内向的,只能是外向的。纵观查尔斯·麦格拉斯精选上个世纪100年的纽约时报书评编辑而成的《20世纪的书》,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并非因为书评的作者缺乏理论修养,或者对批评文本不够敏感细腻,书评的特殊身份规约了书评的形态。
但是,书评不可能是细读式的、宏观的,决不意味着书评是粗枝大叶的、浮泛空疏的;书评是外向的,决不意味着书评就是言不及义的。书评的目的在于介绍新书,生产读者的阅读欲望,书评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只要它介绍的是真正值得阅读的书,而且以一种充实、艺术的文字进行介绍,从某种宏观的角度揭示出作品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在文化符号产品丰盈过剩的现代消费社会,书评不仅作为这种符号产品过剩的社会产物,而且升华为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正是借助于书评,我们才得以可能在泛滥的符号产品中选择我们真正需要的书籍。也许有一天,离开书评,我们甚至无从购买书籍,就像现在,离开广告我们几乎不能在林林总总的商品汪洋中实现一次微小的消费。
书评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广告,优秀的书评则不仅是一则优秀的广告;作为一种广告,书评要真正实现它的广告的目的,它就决不能只是一则广告。这就是书评的辩证法,纽约时报中的许多书评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辩证法。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我们所说的读者很可能对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一知半解,他也许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俄国小说里尽是些早该送进疯人院、或才从疯人院逃出来的人。如果他已有此成见,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故事恰恰可以助长这个没有大碍的想法,更加证实了俄国无异于一所规模庞大的精神病院,院里的看护和病人患有相同的疾病。即便读者这样认定,他仍然无法否认书中每一个人——这840页介绍的每一名男性、女性、孩童——都是活生生的人,生动得那么令人信服,令人骇然。他们得疯狂是由于他们对每一丝情绪都有强烈的自觉——因为他们看待每一丝情绪有如整个生命一般。所以就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俄国小说里弥漫着歇斯底里的气氛,因为西方人有着大不相同的生活逻辑——一套精密繁复的折扣、分配、妥协的逻辑。我们不都是小心翼翼地精打细算着让喜悦和哀伤的情绪收支平衡,仔细分配我们的爱,作恶前先计算清楚利弊得失,为善不求回报,因为另有所图的伪善到头来可能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就此养成了生意人小聪明小智慧的生活态度?甚且不容许任何人把它视为是变相的生意经而加以轻蔑[2](P27)。
请原谅我在此不厌其烦的大段引用这篇作者待考的书评文字中的一段,因为我认为它集中体现了书评的典范;作者并不沉浸到文本中去,他以一种宏观的视野高瞻远瞩地揭示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精神特质,并将之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人情物理作对比,鲜明、尖锐地批评了西方人精神生活的苟且和平庸。我毫不怀疑读到这段文字的人一定会产生阅读《卡拉马作夫兄弟》的欲望。
真正的书评就应该达到这种高度,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时下的书评完全背离了书评的辩证法,将书评的写作降格到非常庸俗的吹嘘的地步。中国时下的书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者自发主动的批评,这种书评虽然很少,但是颇有代表性,因为往往呈现为清一色的暴评、酷评,比如王朔对金庸的批评,周泽雄对余秋雨的批评。但是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谀评,因为我们今天遭遇的书评基本上都是谀评。无论暴评还是谀评,都违背了书评的辩证法;前者旨在批判,更近乎一种学术争鸣,效果适之与生产读者的阅读欲望相反——偶尔也能奇迹般的激发出读者的消费欲望,因此可以存而不论;至于后者,则正是我们的关心所在。因为它过分追求实现商业目标,最终导致它完全背离了自我的特质从而与其目的永远背道而驰。
书评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为了成功实现自我,它就必须不能只是一种广告。这就是书评的辩
证法,背离这一辩证法,书评必将自我颠覆,自我解构。
标签:读书论文; 书评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化工业论文; 大众传媒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