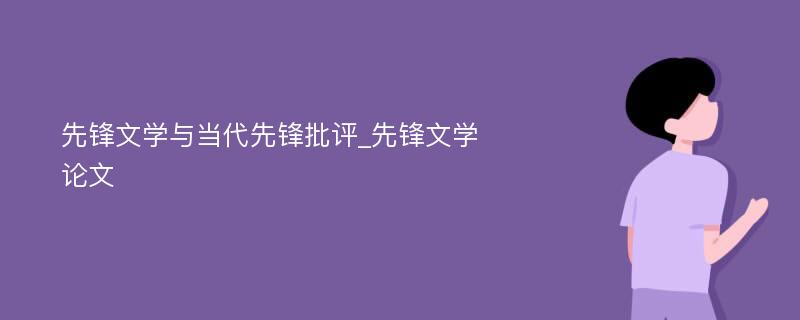
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当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当代论文,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是先锋文学、先锋批评最终形成。研究者在论及中国大陆的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与当代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总以为它们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有些评论者对先锋文学、先锋批评除抱有同情之外,还对此寄予期望,以为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因素,逐渐削弱当代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在我看来,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很少与当代意识形态发生尖锐冲突,从未遭受过禁锢的厄运。相反,在广播电视等宣传部门,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却可以不受阻碍地畅行。这些现象,多多少少能够让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与当代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但我们的确很少能够见到在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与当代意识形态关系的问题上,有较为深刻的批评文章。即便有个别文章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也常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所纠缠,譬如讨论什么中国是否需要先锋派,中国先锋文学接受了哪些外来影响,或是中国先锋文学、先锋批评的本土性在哪些方面构成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差异,等等。
事实上,中国的先锋作家、先锋批评家哪有什么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不要说他们对西方后现代文化是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迄今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就是从他们的创作及批评来说,又何曾受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约束呢?如果一定要说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先锋批评有什么联系的话,我想主要还是借助“后现代”这一名称,而使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中国大陆变得名正言顺起来。也因为有了这种后现代的来头,结果许多评论者放弃了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先锋批评自身内容的研究,而要去补什么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一课,这就使得不少评论更是离题万里。
“先锋”的概念
“先锋”一词,取义于西方先锋派,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主要指八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某种文学现象。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尽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缺乏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界定,但从目前人们经常提到的作家作品及评论家的评论文章看,大体还是有一个范围。所谓先锋文学,是指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这批作家包括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他们年龄相仿,大都在三十岁左右,并且都生活在南方。至于先锋批评,是以阐释上述作家作品为主,鼓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批评。先锋批评家几乎全部集中在北京,生活于学院。虽然他们喜欢谈论文化边缘问题,但从文化位置上判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处于文化边缘状态。在论及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与当代意识形态关系时,我以为有两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一,是“先锋文学”概念的由来;第二,是先锋批评家为什么要用“后现代”来指称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文化现象。
有关“先锋文学”的由来问题,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指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陈晓明先生在给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先锋小说精选》所作的序中,认为1987年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历史纪元,因为在1987年末,上海的《收获》杂志在第五、第六期连续发表了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人的作品。这种划分从时间上看,并没有多少问题,但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在1987年,这批年轻的南方作家头脑中没有强烈的“先锋文学”的意识,而且他们也没有将自己的创作从新时期文学中分离出来的要求,当然,更没有将自己的创作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在当时的评论家眼里,这批南方作家的创作延续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形式上的探索,并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中直接获得滋养。我以为,当时评论家的这种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成效越来越显著。最初是“意识流”小说的探索,从马原开始,小说形式的探索才与作家的个人经验结合到一起。在他那一组以西藏为背景的小说中,马原展示了一个汉人初到西藏时的陌生感受。这种感受,通过小说叙述手法的变化,非常巧妙地传递出来。马原用自己的创作,为新时期小说叙述变革开辟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后来的许多年轻作家,正是从马原身上,直接感受到创造的灵感。在马原之后,便有了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创作。他们年轻而聪明,创作时全然没有马原那份沉重的心理负担,因此,他们能够将马原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才创造出来的叙述风格,轻而易举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苏童笔下,叙述的连贯性和对故事情节有节制的控制,真正使小说呈现出优美的姿态。
在这批南方作家的创作成长过程中,理论上不断给他们以支持和帮助的,是当时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南方批评家。如批评家李劼和吴亮。他们与上述作家个人之间有直接交往。在马原的创作国内评论界无人反应之时,李劼发表许多评论,积极予以鼓吹和肯定〔1 〕,对予尚未登上文坛的一批南方作家,则竭力予以推荐。吴亮发表《向先锋派致敬》的文章,推动这批作家向小说文体更为精致的写作方向发展〔2〕。通过与南方批评家的个人交往, 这批新小说家们不仅获得了自信,而且文体方面的意识也在他们头脑中坚固起来。这一时期是苏童、余华等人创作激情最饱满,优秀之作纷呈的时期。现在评论界所公认的先锋作家最有代表性的几部作品,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写就。这一时期,在南方批评家笔下,尽管开始出现“先锋”或“先锋派”等字句,但他们很少表示出要用“先锋文学”来划分出一个与八十年代文学相对立的文学时代,当然更不用说倡导什么后现代主义了。将这批南方作家的创作界定为“先锋文学”,那是后来鼓吹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批评家们追加上去的。
我认为苏童、余华等一批南方作家的创作,最初与后来盛行“先锋文学”没有什么联系。在南方批评家心目中,“先锋派”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而是执着于艺术探索的艺术与文化中的先驱现象〔3〕。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的许多研究文章中会有这样一种非常奇怪的观点,即认为先锋文学与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相对立,并且与后现代主义相关联呢?这实际上体现了南方作家自身思想的一次转变,也意味着中国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与当代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经过八十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后,中国当代文学面临反省的任务,以解构为旗号的后现代主义的确吸引了许多思想文化界人士的注意。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解构的对象主要应该是当代意识形态,当然还包括当代文学中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部分内容。不管那些鼓吹后现代的先锋批评家们怎样为自己辩护,经过后现代理论二、三年的理论解构,当代意识形态对文化艺术的控制并没有削弱,而新时期以来,对当代意识形态最具挑战性的对人的问题的关注热情,却受到严重消解。在先锋批评家眼里,对人的现实生存环境及文化环境的关怀,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反思,似乎都是八十年代特定时代的思想产物,而到了九十年代,应该是后现代主义时代,以往的问题都成为陈旧的过去了。至于后现代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状况,先锋批评家的做法,便是通过强调先锋文学等文化现象与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对立来实现的。先锋批评对先锋文学的概括与总结,并不象原先南方批评家那样执着于艺术形式的探求,相反,先锋批评仅仅满足于用先锋文学来证明中国当代文化已处于后现代文化时期,并且后现代是与新时期完全对立的这样一种结论。先锋文学是否代表了后现代文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人们的确可以讨论。但先锋批评使用后现代及先锋文学等概念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提出几个文学、文化概念,而在于用这些概念消解新时期文学的思想意义,仿佛九十年代是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时期,已往的思想问题、文化问题统统不用再提。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应该说有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传媒与先锋文学、先锋批评
在分析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先锋批评时,不能不提到传媒系统对扩大先锋文学、先锋批评的社会影响所起的作用。与已往的文学现象不同,已往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往往是文学作品首先靠文学自身的力量获得了社会声誉,然后电影编导们才根据文学原作改编电影。但先锋文学的成功,首先是借助电影拍摄成功而获得的。人们对先锋文学的兴趣,是由观赏电影拍摄电视而引发的。许多读者起初并不知道苏童的《妻妾成群》和余华的《活着》,只是因为张艺谋将这些小说改编电影,读者才知道苏童、余华,才想到要去找他们的作品阅读。这种现象多少可以让人们在评价当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文学价值时有所反省。电影电视广播等现代传媒工具,在中国大陆与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意义复合,在大陆的各种艺术类型中,电影电视始终是意识形态说教味最浓的,即便是当今相当成功的“第三代”导演制作的影片,也不能完全免俗。
象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一旦涉及到现实问题,批评的锐气明显软下来,总之是含含糊糊,朦朦胧胧。导演张艺谋的几部影片更是如此,象《红高梁》、《秋菊打官司》、《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说不清到底要表现什么,似乎什么主题都搭着一点,但没有哪一个主题深入下去。我这样评价“第三代”导演们编导的艺术电影,当然不是要贬抑他们个人的艺术才华,而是希望人们注意到某种艺术形式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相当程度上,这种艺术形式自身是有缺陷的。因此,没有必要将电影的成功,简单归结为电影艺术的成功,而忽略了其中的意识形态内容。如果说,电影编导们在选择剧本时,不能不考虑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口味的话,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被选中而改编成电影的文学作品本身,也不会对当代意识形态有什么触犯。这就难怪被影视所改编的一些先锋文学作品,从文学角度讲,往往不是作者最优秀的作品,即便是极个别的优秀之作,经过电影改编之后,小说的风格原貌总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很难说《妻妾成群》是苏童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从苏童对人物的刻划及作品文字的驾驭功力看,《红粉》理应更为出色,而且在原作中,苏童也寄予了反讽的内涵。我以为,这部文学作品是苏童作为南方作家时期最为出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电影处理上是根本无法复现其艺术原貌的。虽然在电影《红粉》中,导演通过电影语言对改造妓女活动的粗鄙之处,作了某种程度的嘲讽,但同时在许多地方也强化了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电影电视等传媒在中国大陆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这原是非常明确的不争之事,因此,没有必要将电影电视造成的社会轰动效应看得非常重要,更没有必要以此作为判断作家作品成功的标志。
然而,在先锋文学、先锋批评看来,电影的成功也意味着文学创作的成功。先锋作家、先锋批评家不仅没有对电影等传媒工具的意识形态功能有所警觉,反而以占据影视市场作为创作和批评的重要目标。在先锋批评家看来,文化艺术进入传媒是后现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批评家们用不着为文学作品与传媒的结合大惊小怪。在先锋作家眼里,传媒是宣传作品的最好帮手,作品通过传媒,可以扩大社会影响,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社会声誉。但事实上,在文学与影视等传媒的结合过程中,受损害最大的莫过于文学本身了。凡是对大陆近几年文学创作状况有所了解的人,几乎都知道作家们是如何为迎合影视编导的口味而随便编排自己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哪一位作家与影视沾边,那么这位作家的创作就会出现停滞现象。我不知道苏童对自己改写的《红粉》剧本是满意还是失望,但我相信绝大多数评论者,甚至包括苏童本人都会意识到,从他以及一批先锋作家开始为影视编写脚本起,他们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八十年代时的那种状态了,而且他们的文学创作就此进入自我重复的恶性循环之中,很难见到有出色的力作奉献于世。
值得反省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九十年代最终形成,实际上意味着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已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到今天,大陆评论界到底有多少人还相信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且到底有多少人相信先锋文学、先锋批评真是什么“先锋”。不过,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在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兴盛发展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软弱表现,倒是让人有相当多的感叹。具体地说,在当代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几乎没有真正行使过有力的批评。我以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评论者对先锋文学、先锋批评抱有幻想。许多评论者不加区分地认为先锋文学、先锋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驱现象,因而在批评尺度上,我们的评论家们宁愿持宽松态度而不愿坚持批评的立场。先锋文学、先锋批评正是在人们这种唯新是从的心态中奇迹般地膨胀起来。他们以文化边缘人自居,但从先锋批评、先锋文学急于制造一个后现代文化时期的举措看,分明是想确立一种中心,这种中心便是被当代意识形态所认肯的中心。事实上,我们在考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先锋批评的地域分布时,便会注意到,先锋批评家全都集中在北京,而被先锋批评家们封为“先锋作家”的一批南方作家,主要活动区域也慢慢移到北京。北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在中国大陆的地位绝对是中心而不是边缘,先锋批评、先锋文学正是从北京这一中心地带辐射向全国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一批南方作家被确认为“先锋作家”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再谈及自己与南方批评的关系,更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从新时期文学中获取滋养。他们认同先锋批评的价值尺度,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或是什么外来文化影响,其实,无论是个人学识还是对外国文学、文化的了解,他们并不见得比大陆许多作家、批评家有优势,只是先锋批评家、先锋作家敢于谈,有机会在电视、广播,大会小会中放言高谈,大众传媒也乐意作推波助澜的宣传工作,再加之有“先锋”作旗号,声势还能不显赫吗?于是,许多批评家,特别是大陆的评论者只得放弃对先锋文学、先锋批评的分析,而急于在知识上补什么后现代主义之课,以为补完了这一课才有资格来评论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表现得既天真又脆弱,我敢说,哪怕是批评家们补完了后现代这一课回过头再来评价中国的先锋文学、先锋批评,还会发现许多课补不胜补。
第二,许多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以旁观的姿态对待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他们既不赞同也不批评,听任这股文学思潮自生自灭。九十年代以来,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家沉湎于封闭的批评理论构想之中,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不一定涉及当代各种思潮而可以自成一体,只要批评理论完备,许多具体的现实问题便可自动解决。但我以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实践性非常强的思想活动,正是在对当代文学的敏锐反应中体现出自己的思想价值,如果要论研究,完全可以有专门的学问来承担此任。假若我们的批评家对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文学事件都不能做反应,那么,构造再多的批评理论,又有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破冰启航,为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批评辟出一条通道,现在回想起来,不是具备了完美的批评理论、批评方法之后才进行的,而是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中,不断反省自己也反省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中,才取得较大的文学进步。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问题曾使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当代批评一度陷于困顿,那么,今天我们的批评应该有更多的勇气敢于正视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我想每一位批评者不应该被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威势所击倒,而是应从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是否真正起到推进作用这一点着眼,在批评实践中接受各种挑战。
注释:
〔1〕李劼1987 年在《上海文学》第三期发表《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1988年在《上海文论》第二期发表《论小说语言的故事功能》;《钟山》杂志第五期发表《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
〔2〕吴亮《向先锋派致敬》,1988年发表在《上海文论》第一期。
〔3〕南方批评家心目中的“先锋派”的概念, 大都与法国作家欧仁·尤奈斯库所论述的“先锋派”概念相似,是指“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的现象”,是“一种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参见欧仁·尤奈斯库《论先锋派》,载《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
标签:先锋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苏童论文; 红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