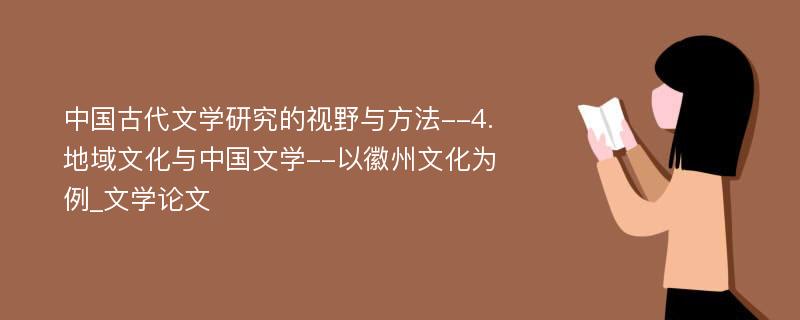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4.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为例论文,文化与论文,地域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邀主持人 朱万曙 [主持人语]新的视野和方法推动着学术的发展。王国维先生对于视野和方法就非常重视。他关注到“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并由此论及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体现其视野的开放。在《古史新证》中他言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个别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是他在方法上的自我总结。缘于此,“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语)。回顾百年古代文学的学术史,无论是王国维、陈寅恪,还是胡适、鲁迅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往往都与视野的拓展、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 “视野”与“方法”是相互联系又含义相异的概念。就词义而言,“视野”指目力所及的范围,“方法”则是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视野意味着了解各种学术观点,关注各种学术方法,进而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方法则意味着解决某一学术问题的手段和路径。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视野的拓展。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视野上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史,还需要把握国外汉学的历史和最新动态,甚至需要借鉴与古代文学相关的学科研究成果。视野不断拓展,方法不断创新,古代文学研究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2013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多位名家云集会议,围绕“视野与方法”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切磋讨论。本专题从此次研讨会论文集中选取了四篇论文,以反映当前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视野和方法上的新思考。 袁行霈教授的《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从宏观的视野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时”与“地”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也需要补充地域文化的内容”。文章虽然是就文化研究展开阐述,但对文学研究多所涉及,无疑拓展了我们的学术思维。 李炳海教授的《视野与方法——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以楚辞学案为例,论述了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文章以具体的例证,充分说明了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研究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学术视野的拓展。文章还论述了学术视野的掌控需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需要以博济约、以约统博、博约适度。文章以个案切入,让我们对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得更为深入。 左东岭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论述了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三种关系,以及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思想的方法。文章探讨了在文人心态研究中如何合理使用文献以及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进而论述了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以及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文学观念的学术路径。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牵涉到如何重新审视文学思想史和古代作家及其创作,有着开启新方法论的意义。 近年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已蔚为风气。朱万曙教授的《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结合作者多年的徽学研究实践,提出了对地域文化新的理解。文章阐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同构关系、“文化下移”与下层创作、经济支撑与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地方视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如何进一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恰与袁行霈教授的观点相呼应。 早在20世纪初,文学的地域文化性质就已经有学者关注和论述。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论述道:“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訧焉。”[1](P291—293)刘师培还曾撰《南北文学不同论》[2]对文学和地域地理的关系进行论述。近年来,地域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学史的研究也在走向深入。但是,关于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理论思考似乎还不够丰富。本文拟以徽州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为例略作探讨,期待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 一、何谓“地域文化”? 何谓“地域文化”?目前似乎没有权威和达成共识的定义。依笔者所见,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成,并经过长期积累的包括观念、风俗在内,具有自我特色的诸多文化元素的总和。这个定义包括四层含义:第一,是“一定的地理空间”,它不仅指历代行政区划所界定的地理空间,还包括自然地理空间。关于地理之于文化的影响,梁启超也早已关注:“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3](P4259)第二,地域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在本地域,它足以成为一种传统,影响着在该地域生活的人,并且不断沿袭。第三,如同诸多“文化”,地域文化也是以观念作为核心,然后扩展到物质层面和其他文化元素之中。第四,可以称之为“地域文化”的文化,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完全可以被感知到。 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徽州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上述“地域文化”的定义。“徽州”是一个地名,从宋代到民国时期也曾经是一个行政区域,但是,“徽州文化”确实是一个可以感知的有着自我特色的地域文化。 从地理空间上看,它位于皖南山区,境内山峦林立,其中有著名的黄山和齐云山。众多山涧形成的河流汇集为两条大的河流,一是由西向东的新安江,一是由东往西的阊江。新安江流入千岛湖,最后注入钱塘江;阊江则通往鄱阳湖。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徽州文化的累积过程相对封闭,在经过长期积累后,具有“超稳定性”。 从积累过程看,徽州承接了中国历史上两晋、唐末和两宋之交的三次人口的迁入。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战乱,迫使百姓们纷纷南迁,其中的一部分就迁徙到以山峦为屏障的徽州,他们在这里安顿、休养生息,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文化。特别是部分世家大族,在原居地就有着丰厚的文化积累,南迁徽州后,仍然保持着家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化观念和耕、读的传统。宋代科举考试正常化以后,徽州的文化积累得到了一次爆发的机会,诸多士子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既为家族带了荣耀,也垂范后世,加之朱熹自命为徽州人,进一步强化了徽州“崇学”、“崇儒”的文化传统。明代以后,由于徽州人口增长,徽州人纷纷外出经商,在为家乡带来可观的物质文化的同时,徽商与徽州籍的文人将“崇学”、“崇儒”的文化传统进一步予以强化。 从文化元素构成看,徽州文化观念首先就表现为“崇学”、“崇儒”。明代程瞳著有《程朱阙里志》,将徽州视为“程朱阙里”,以此而自豪。在诸多族谱的“族规”、“家训”中,崇敬朱子、强调遵守儒家伦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历代徽州学人的著作中,对儒家经义的阐释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由儒家观念出发,徽州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意识和组织也不断被强化,进而延伸到村落、祠堂等物质文化元素中;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也演变为矗立在村头田间高高的牌坊。“崇学”的观念,转变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诸多的书院建筑,进而培育出高于其他地域的进士数量,当然,也带来了刻书业的发达以及诸多的藏书家、藏书楼。其他文化元素也因此而显示出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气象:因为文士多,所以舞文弄墨者众;因为徽商带来的富裕,所以文化消费能力强,戏曲演出之类的活动频繁,由此又催建了为数不少的戏台建筑。种种文化元素在这里汇集交错,却无不有着地域的动因,带上地域的色彩。 最后,徽州地域文化拥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自我特征。就其表层、可视或物质文化元素看,徽州的建筑颇为独特:村落依山而建,村落中的民居一律粉墙黛瓦,辅之以马头墙,这种风格的建筑被称之为“徽派建筑”。就深层审视,一个村落,往往是一个宗族的居住地。祠堂中的祖宗牌位庄重摆放,显示着族人敬祖爱宗的伦理情感;村口村外的牌坊,昭示着“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精致的石雕、砖雕、木雕,既透露出徽商曾经富有的历史信息,各式各样的图案也叠印着徽州人祈求平安、祥和的愿望。还有随处可见的楹联、学者们关注的大量刻书文献、契约文书,都共同展示了这个地域“崇学”、“崇儒”的文化观念。 中国版图辽阔,地域众多。应该说,并非所有的地域都有地域文化,特别是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不少曾经有过深厚积累的地域文化都被分割乃至消解,以至于对于地域文化的含义理解不一,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难以深入,有些所谓的地域文化研究,或无比较,或自说自夸。就地域文化而言,徽州文化是一个典型的个案。透过徽州文化,我们能够对什么是“地域文化”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二、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同构 地域文化与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是同构关系。毫无疑问,地域文化对文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影响之一,是对创作主体——作家的影响。任何一位作家都出生、生长在某一地域,该地域的文学元素必然植入其记忆和心灵之中,这往往形成作家的“故乡”情结,从而又自然地渗透在其创作之中。有的作家因为仕宦或其他原因,离开故乡,寄籍他地,时间一长,第二或第三“故乡”的文化也自然影响其心灵和创作。 影响之二,是同一地域作家之间的交往以及地域作家群的形成。文学史上的流派,往往因文学风格、主张等相同而形成或被后人概括命名,但因地域相同而结合的文学流派也是重要的现象。特别是到明清以后,文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因为“地缘”关系,更容易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形成文学创作的“群”和“派”。例如“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都是以地名作为流派之名,其开创者和代表人物都出自同一地域,后来的成员才扩展到其他地域。又如明末清初戏曲创作的“苏州派”,则全为生活在苏州的戏曲家。近年来,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地域作家群或流派陆续得到挖掘,例如有的学者就提出晚明诗歌中有“新安诗群”①,有“金陵六朝派”②等。 影响之三,是作家对题材内容的选择。一地有一地之山水,一地有一地之文化景观,一地有一地之人物,一地有一地之民情风俗。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在题材选择上,必然会将自己最熟悉的对象写入作品中。例如出生于徽州的汪道昆,在其《太函集》中,就有70多篇徽州商人和商妇的传记,其诗歌中也多有徽州景物的描写和吟咏。也有一些寄寓他乡或在某地短暂停留的文学家,同样将地方风物、人、事摄入笔端,李白晚年曾经流寓宣城一带,他的诗中,就有对九华山的赞叹,也有对桃花潭的情感抒发。至于现代文学作家,地域文化之于题材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沈从文的湘西风情、老舍的京味小说等等,无不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影响之四,是地域文化观念在作品中的渗透。中国自秦汉以降,成为大一统的帝国,儒家思想文化在多数情况下占据着绝对统摄地位,思想史研究者关心和讨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的变化,如从先秦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发展,但却忽略了在不同地域,其作为观念支配人心的程度深浅也不相同。例如在明代中叶阳明“心学”兴起,肯定“人欲”、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已经蔚为时代思潮之际,地处崇山峻岭之中的徽州却仍然崇奉“朱子之学”和“朱子之教”,守节、殉节的妇女仍然被表彰。这些地域文化观念也必然渗透在文学创作之中,例如汪道昆的文集中,就有不少节妇的传记。对于理学的崇奉,使得徽州地域的文学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景象:一方面,由于重视教育,这里舞文弄墨者众,乃至有诸多的诗社、文社;另一方面,这里又没有出现在文坛有足够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这种矛盾现象的内在原因,乃在于该地域文化观念的相对滞后。 文学对地域文化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一,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往往是地域文化的显性符号。文学家因文得名,对本地域而言,是文化象征,是一份骄傲;对地域以外的人而言,是让人知晓、了解这个地域的符号,如杜甫之于成都,汤显祖之于临川和遂昌,吴敬梓之于全椒、南京。文学作品和作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作品因为和地域密切相关,如苏轼咏西湖、王士祯大明湖赋《秋柳》,其对地域文化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符号作用,它们都让读者对作品产生或所写的地方生出向往之情。其二,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强化地域文化的自我特征,或者为地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一般而言,文学家在身份上往往是士大夫,他们有着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因之他们往往也是思想的代言人。就地域文化而言,文学家——士大夫无不具有强化地域文化自我特征的作用。由于具有士大夫的身份,文学家又对本地域的文化风尚起着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本地人仿效的榜样,地域文化的传统因此而形成,地域文化的特征也因此得到强化。另外,古代的文学家们往往会走出本地域。他们本来就是“精英文化”圈的成员,在入朝为官后,他们结交的都是士大夫身份的人士,彼此之间同气相求、互相影响,原有的文化观念在碰撞中发生变化,同时因为宦游而了解到他地的地域文化,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渠道(如致仕、退隐回乡,如与家乡的书信交流)而对其原先所属的地域产生影响,从而赋予地域文化新的内涵。 分而言之,地域文化之于文学、文学之于地域文化,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合而言之,二者又互为同构。就一个地域文化而言,文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情形有二:一是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参与地域文化的建构,这种参与,不仅有出生于本地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也包括出生于其他地域却与本地域联系密切的文学家,他们或宦游本地,或长期寄居本地,或曾经短期来此游历。徽州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也体现了文学家参与建构的情形,如明代中叶的文学家屠隆曾任徽州府推官,他参加了汪道昆组织的“白榆社”,和徽州的乡绅多有交谊,彼此间诗文唱和。二是本地域的文学传承和传统。地域文学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特别是那些文化积累深厚的地域。一方面,一个地方因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必然有师承,教师往往既是学者,也是文学家,至少能诗能赋,他对于学生的文学影响就建立了文学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还有家族的文学传承,父辈对文学的爱好乃至成就,对于后代更起着熏陶作用。近年来,对于文学家族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实际上,文学家族恰恰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上的师承和家族传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地域的文学传统,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层面和内涵。 三、文化下移和下层创作 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在明清时期有一重非常重要的表现,那就是文化下移带来下层文学创作的活跃。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长,读书人增加,而科举取士名额有限,造成了大量读书人留滞下层社会,他们未能步入仕途,不能居“庙堂之高”,但为了生计,或为塾师,或为幕僚,或为商贾,或为乡医,甚或为方术之士,形成了读书人的职业分流现象。他们虽然属于社会下层,虽然为生计故从事的不是“士”阶层的职业,但由于曾经读书,在文化观念、文化行为上和“士”阶层保持着一致,有相当多的人也和“士”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下层社会有文化的群体,他们的存在和文化活动,充分显示了明清时期文化的下移趋势。 诸多的读书人沉潜于下层社会,吟诗弄文是他们书写人生或寄托心志的重要方式。他们缺少宦游的机会,留居本地的时间较多,因而在身份上更具有地域色彩,从而使得地域文学得以蓬勃兴起。从身份和经历上,我们可以将这些地域性的文学家分为以下三类予以审视: 第一类是基本上留居于本地的文学家,他们虽然曾经读书,但科举考试不顺利,为了生计而放弃科举道路。在城市,他们的职业选择可以更加多元,明末清初苏州的一批文人,以写戏为职业,如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叶时章等,成为戏曲史上的“苏州派”。他们是曾经读书之人,但因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了走科举道路。在乡村,他们或当私塾先生,教书为生;或奉行“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行医乡里。例如创作了《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郑之珍,据传记资料,他因为“病目”而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做了私塾先生;明代徽州还有一位“山人”江瓘,他选择的职业是医生,而且撰有医学方面的著作,但同时也吟诗为文,留下了一部《江山人集》。这些文学家以在本地生活时间为多,出游外乡他埠的经历少,交游面也不是很广,是名副其实的“地域文学家”。 第二类是没有取得科举功名、既留居本地又经常游历外地的文学家。这类文学家家庭大体上比较富有,在家乡有田有产,家乡观念也很浓厚。但或者是追求人生的体验,或者因为生活的需要,他们经常游走于外地特别是繁华的城市。他们交游面很广,诗词歌赋既是他们和上层士大夫交游的媒介,也因此而成为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他们参与地域性的文学活动,也因为“见多识广”而为地域文学带来新的信息。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地域文学之间、士大夫文学之间的互动。这类文学家在我们所研究的徽州比较多,典型的如潘之恒,他科考不顺,游历各地,但徽州又是他的家园。他的交游极为广泛,所交往的上有大臣名士,下有徽州本地的乡村读书人。他曾经邀请和陪同冯梦祯等人到徽州游历,也曾经在南京、扬州等地品曲论戏。他参加汪道昆组织的“白榆社”的活动,得到汪道昆的提携,他也和汪道昆以外的士大夫们来往密切,包括汤显祖和公安“三袁”。徽州是他的根据地,但他的身影却活跃于当时的文化中心,这让他的视野比仅仅留居在徽州乡村的读书人开阔很多,也让他在文学创作、戏曲批评甚至文献编纂诸方面建树更多。另外,他也以这种出入本土和外地的方式,沟通了徽州与外界的联系。 第三类是寄居他乡的文学家。明清以降,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读书人也是如此。如果说宦游还是在本籍以外的地方短暂地停留居住,那么大批未能步入仕途的读书人却可能为了生计而移居他地。这在徽州表现得很突出。徽州由于山多地少,从明代成化年间开始,徽州人就大批外出经商。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他们就逐渐地寄居在经商地。徽商“贾而好儒”,他们重视子孙的读书,不惜本钱。他们有浓厚的宗族和家乡观念,加之考试也必须在本籍参加,故而其子孙多在徽州读书并参加科举考试。即使不在徽州读书,也得回到徽州参加考试。自然,落选者非常多。这些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徽商子弟最终只能继承父业,成为他们本不屑为之的商贾。他们也要离开家乡,到父辈所在的经商地去经商和生活。他们的身份比较复杂,既是商人,又曾经是读书人。经商是生存乃至家庭家族的的需要,但曾经读书的经历,让他们对文化有着抛却不了的情结,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成就。例如明末清初居住在杭州的汪然明,清代乾隆年间主盟扬州文坛的“二马”兄弟和江春,均属于此类情形。就地域文学而言,他们于故乡徽州似乎没有参与和发生影响,而是融入到所居住地的地域文学之中。 以上三类文学家,在文学史上似乎都没有什么地位。他们大多失意于科举考试,从此委身于下层社会,自然也无从在正史上留名。而目前的文学史还是“士大夫文学史”,对这些文学家的关注程度还很不够。实际上,他们的文学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体现了明清时期在经济活跃、文化水准提升环境之下的“文化下移”走向。他们曾经读书,其中不乏才学之士,只是科举录取名额有限,使得他们不能实现通过科举入仕的梦想,从而滞留于士大夫阶层之外。他们的创作可以称之为“下层创作”,带着比较鲜明的地域色彩。 四、经济支撑与文学语境 在讨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我们不能忽略经济要素。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繁盛衰落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一个地域文化是否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时显示出优越性,也与其经济实力大有关联,文学相应地在此语境中呈现出地域的差异性。在学术界,“江南”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地域概念。“江南文化”在明清两代似乎也展现出令人羡慕的繁荣气象:那里人文荟萃,书香沁鼻;那里园林建筑,布局精巧。江南,是文学的温床,哺育着诸多高雅。这一切,和京城以皇家气象为底气的文化迥然不同,和中原、山陕等地的文化色调差别更大。而形成这种差异的,除了山水地理、文化传统等原因外,经济是重要的原因。 汤显祖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徽州的诗,诗题为《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4](P726)对于这首诗的解释,有的认为是赞美徽州,有的则认为是鄙薄徽州的铜臭之气,其实都缺乏对汤显祖写诗之时心态的考究,他是表明自己不愿意像有些文人士大夫那样拿着身份到徽州去“打秋风”。但是,这首诗又实在地透露了徽州极为富有的事实。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之活跃、徽商之富有,诸多的文献多有记录。万历年间的进士谢肇浙在其《五杂俎》一书中记载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新安,就是徽州;山右,则是山西。在明代,徽商与晋商是两大商帮。在他的笔下,徽州商人之富,令人称羡,他们以经营盐业致富,有的资财达到上百万两银子,那些只有二三十万资财的只能算个“中贾”。归有光在为一程姓徽商写的寿序中说道:“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倚顿之盐,鸟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毂,拥赵女,鸣琴踮屐,多新安人也。”[5](P319)归有光分析了徽州人经商的原因,描述了徽州人经商的种类,也夸耀了徽州人经商后的豪奢生活——“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毂,拥赵女,鸣琴踮屐”——比其他地方的人奢侈多了! 徽商的商业利润,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返回家乡,用以购买田地和建筑房屋。徽州因为徽商的商业利润,成为处于江南边缘最富有的地域之一。经济上的富有,使得徽州在文化上也得到超出其他地域的迅速发展。于是,这个地域文学的文化语境渐渐变得特别起来。 其一,财富让这个地域的读书人成倍地增加,文学队伍得以扩大。 徽州本来就有重视读书的传统。对于希望能够长久保持家族荣誉和家族秩序的徽州宗族来说,教育是亢宗之本,是宗族有效延续的必备手段,要尽可能地保证族中子弟读书进取。《茗洲吴氏家典》规定:“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校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6](P18)。徽商富有以后,更加重视子孙的教育,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诸多文献都记载,他们广建义学、义塾,为宗族以及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读书的场所,如明代歙县商人洪世沧,在吴越经商,“家稍裕,遂承先志与族党中,捐赀二千金入宗祠,以其息设义塾二堂”[7]。清代婺源商人詹荫梧“创建义学,并置田租培植寒畯为久远计”[8]。乾隆年间,朝廷重臣曹文埴告老还乡,鉴于朱熹曾经读书于歙县紫阳山,倡议修复“古紫阳书院”,两淮盐商纷纷响应,捐银11000两,使该书院得以修复完成。 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让徽州这个人口不多的地方读书人比例大为提升,其标志之一是科举录取人数。据徽州方志的记载,在明代,徽州一地共有文进士446人,文举人1237人。到了清代,徽州的举人和进士更是层出不穷,文进士有664人,文举人2067人。[9](P276)这个数字应当包括寄籍外地的读书人,但却只是难以统计的读书人中科考成功者。读书人的成倍增加,无疑扩大了文学队伍。 其二,财富让这个地域崇尚风雅的风气愈加浓厚,文学创作蔚然成风。 有个例子比较典型。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四记载:“延宾,早能成立,商游吴、越、奇、鲁。且性颖敏,好吟咏,士人多乐与之交,而诗名日起。人谓孺人(延宾母)曰:‘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孺人叹曰:‘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哉!’”商人王延宾虽然经商,却经常和文人诗歌唱和,声名渐起。有人因此向他母亲建议:心不能二用,做事情也没有各方面都做好的。但这位母亲却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已经是世代经商了,如果我的儿子能够因为写诗得以和文人交游,那么商业上小小的失利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在其他文献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像王延宾这样的“好吟咏”的人。例如明代休宁率口程氏家族,定期举行诗会,并且将诗作刊刻成集。[10] 其三,财富让这个地域的文学作品得以大量刊刻。 徽州的刻书和版画,曾经被郑振铎等学者高度推崇。这是从中国刻书史或版画史的视角出发的赞赏。就地域文化的角度审视,刻书业同样因财富而勃兴和发达。财富让这个地域的读书人大增,读书人读书的需求促进了刻书业的发达;读书人既写书,又有财力刊刻出来,进一步让刻书成为产业,于是有了虬村黄氏刻工的活跃,同时也促使他们在镌刻技术上越来越精进。③ 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对于高石山房刻本《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的插图是否算得上是徽派版画发展的分水岭有所争议。这个刊本的意义还在于,徽州人的财富,让能够撰写或者创作文学作品的读书人,有能力将自己的文字刊刻出来,流布于世。那部戏文的作者郑之珍虽然只是一个私塾先生,但他的父辈以及家族通过经商积累了不少的资财,尽管戏文作品篇幅很大,但他仍然请了虬村黄氏的刻工将它刊刻了出来。类似于郑之珍将自己的作品刊刻出来的徽州读书人还不少,有的自己在世的时候没能将作品予以刊刻,但儿孙们将其刊刻出来,以此表达追念先人的孝心。作品得到刊刻和流布,即使水平一般甚至糟糕,却也显示了他们作为文学家或者仅仅是文学爱好者的存在,这一大批作品的留存,呈现了地域文学曾经的繁荣以及地域特色。 五、“精英意识”与地方视野 考察地域与文学的关系,“精英意识”和地方视野之间的分别、联系和互动,也是不能绕开的问题。所谓“精英意识”,是指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庙堂的士大夫们的思想观念。所谓地方视野,则是指那些科考失败、滞留于本乡本土的读书人的思想观念。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判然为两个阶层;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国”观念以及血缘、地缘、学缘的关系,使得两个阶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后,无疑进入了“精英阶层”。他们身在朝廷,获得了身份的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精英”,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除了官场上的互相支撑外,还有彼此之间的同气相求、思想观念的交流,包括文学主张的交流和共识。在明代,就有了前、后“七子”颇有声势的复古主张,也有“唐宋派”对复古主张的不满和矫正。另外,他们对于新的思想观念更容易接触和了解,当“异端之尤”李卓吾出现以后,诸多的士大夫纷纷关注,无论是挞伐者还是推崇者,共同关注都是事实。 “精英”们风云际会、意气风发,引领着风气,左右着文坛。但他们和沉埋于家乡的那批读书人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实际上,无论他们在仕途上曾经多么得意,但从明中叶后开始,由于党争愈演愈烈,官员被斥退、贬谪或因言官弹劾而请辞,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精英”们不时回到家乡,或待机而动,或甘心退隐,至少暂时在熟悉的家乡生活一段时间。他们会和地方政府有联系,他们和本地的读书人也有密切来往,甚至建立起交游圈,组织各种活动,在这些交游和活动中,他们排遣了被朝廷冷落的寂寞,并且能够体会到作为士大夫一员的优越感。 反之,未能入仕的本土读书人也会积极地向精英阶层靠拢。一方面,因为有着血缘、地缘、学缘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借着和精英阶层的交往而提升自己的地位。读明清徽州人的诗文集,这种感受很强烈,他们谒见徽州籍在京城为官的士大夫,将写给他们的诗作郑重地收入自己的集子里,尽管那些诗作实在毫无意义。 精英阶层与本土读书人的这些交往,必然让“精英意识”向本土传播。他们会将在朝廷、在外面世界获得的见识、观念传递给本土的读书人。在徽州地域文学史上,汪道昆之于本土读书人的影响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虽然未入后“七子”之列,但和王世贞交好,在文学上都主张复古。在解职回乡后,他组织了丰干社、白榆社等诗社,一时追随者甚众,其成员多为徽州本地读书人或在徽州任职的官员。[11]作为中过进士、担任过兵部侍郎的士大夫,汪道昆既对诗社成员有提携、有鼓励,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特别是在文学观念上,对他们影响甚大。袁宏道曾说道:“近日江南北谈诗者,什九出汪、王二公之门,其一虽不出二公门,然用意属词,居然在二公绳尺内。间有稍知趋向耻为模拟者,虽亦时时姗笑此辈,及下笔,未免为格套所缚,浮泛雷同,往往而是,杂毒之入人甚矣。”④袁宏道所说的“汪、王二公”,指的就是汪道昆和王世贞,他站在性灵说的立场上,批评复古派在汪、王影响下的“模拟”之风。但他们的影响恰恰说明了“精英意识”向地域传播的事实。 尽管精英阶层对本土的读书人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但是,本土读书人毕竟不属于精英阶层。身份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异、和精英阶层交往的疏密,都决定了本土读书人作为一个中间阶层的地方视野。这种地方视野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就是题材的选择。在他们的作品里,本地的人、事和风物往往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在明代徽州有个叫吴文奎的读书人,曾经师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但在他的诗文集《荪堂集》里,有关于他自己营建的园林的记录,也有他的祖父、父亲、叔伯等人的传记,还有不少关于徽州风物的描写。[12]明末清初的汪子祜是徽州祁门县人,他“性豪迈不羁,厌绝科举之学,不屑为。舅氏方西郭工诗善画,推择名流八人为诗社,而先生与焉,年最少,而才又最高,顷刻千言立就。每遇美景乐事,则招邀数子,行觞无算,醉里成诗,悲壮高凉,时露英雄本色”[13]。这是一个有个性、有才华的人,他不屑于走科举应试的道路,他的性格“豪迈不羁”,他少年时就好为吟咏,又受到舅舅辈的影响,更以诗吟为乐。他的《石西集》中,有大量的山水田园诗作。类似吴文奎和汪子祜的本土诗人还可以列举不少,他们的创作,充分显示出和精英阶层不同的地方视野。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理论命题。这里笔者只是结合近年所承担的“徽州与明清文学”的课题提出了对几个问题的思考。但这些问题实在牵涉到如何拓展文学史研究空间以及如何把握文学史发展面貌的思维向度,特别是对于明清文学的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拓展的空间也更大,需要我们提出更多的思考、付出更多的努力。 注释: ①参见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第二章第四节“汪道昆与新安诗群”,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②参见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载《文学评论》,2006(2);张燕波:《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3);另外,陈斌所著的《明代中古诗歌接收与批评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二章论题亦为“嘉靖六朝派及其诗学承担”。 ③关于徽州刻书业的发达,参见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0。 ④袁宏道:《涉江诗序》,此诗在通行的《袁宏道集》中漏收,转引自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29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