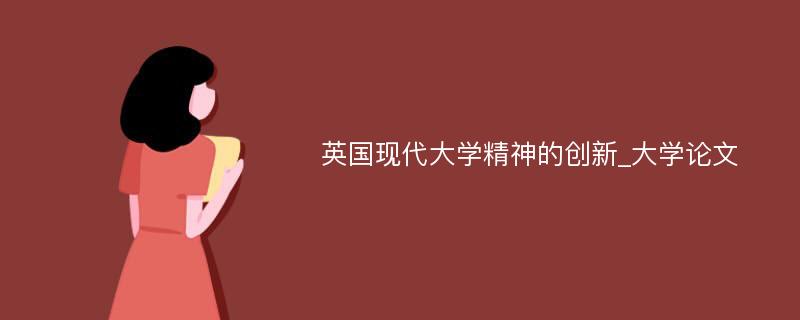
英国近现代大学精神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近现代论文,精神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5)05-0031-10 DOI:10.14138/j.1001-4519.2015.05.003110 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大学履行的职责与今天完全不同,它们主要从事牧师和教师训练以及与之相关的职业训练。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其主要任务是维护知识霸权和已经建立的国教秩序,而不是鼓励科学进步或提供自由教育。虽然社会精英通过大学培养,但他们很少完成学业和获得学位。“工业化以前大学的附属使命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实现未来精英的社会化。大学只是中等教育的一种扩展形式。”①进入19世纪后,民主化浪潮、工业革命和职业阶层兴起,不仅导致对更加完善的大学制度的需求,而且也塑造了大学的精神气质。 一、自由教育传统与大学精英精神 自1852年纽曼出版了《大学的理念》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学是一个与众不同而且拥有特权的机构,它需要一种重要的办学理念或精神气质。自由教育就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古典大学极力倡导的教育理念,其核心在于对古典人文主义的坚守和社会精英的培养。 1.自由教育的传统 长期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和滞后性。它们坚持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课程内容以古典人文学科(希腊语、拉丁语、雄辩术、诗歌、历史、文法)、经院主义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为核心,教育目标是培养在教会和公共生活中拥有优先权的牧师和英国国教派绅士,非国教派人士不能担任大学教员。它们也抵制自然科学的教学。虽然19世纪早期法律和医学专业比较重要,但它们只是表面结构,其基础仍是扎根于古典学科的自由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体制性障碍,如研究员职位、学额奖学金、希腊语,是古典大学根深蒂固的症状,尤其是牛津大学根本不相信教育对工业的作用。由密尔和帕蒂森强烈表达的对‘自由教育’和非职业教育的普遍信仰……才是真正的抑制剂。”②19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是传授自由人文学科的机构,并否认有其他任何与之相对的目的。 牛津和剑桥对古典人文主义课程的迷恋,体现了英国大学自由教育的传统。约翰·密尔指出:“大学不是职业教育的场所,它不是为了教给人们一些谋生的知识……人们在成为律师、医生、商人和制造商之前必须先成人,如果你使他们成为有能力和明智的人,他们也将会成为有能力和明智的律师和医生。”③因此大学并不传授专业知识,而是引导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同样生活在19世纪的纽曼也对自由教育进行了论述,他反对功利主义和“大学以研究为中心”的观点,而主张把自由“人文学科”(liberal arts)作为课程的核心。他说:“当别人问我,大学自由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所构建的自由知识或哲学知识目的何在?我的回答是,它有很具体的、真实的和充分的目的,但这一目的不能与知识本身分开。知识本身就是目的。”④这种知识被称为自由知识或绅士知识,大学教育就是为了获取这种自由知识,其目的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即绅士。“自由教育不是培养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而是绅士。即如何成为一名好的绅士,使他具有高超的智商、敏锐的鉴赏力、公正公平、冷静的头脑,在生活中品德高尚、行为谦恭。”⑤自由教育追求纯粹的知识,厌恶专门的职业训练。因此当牛津和剑桥开始允许自然科学进入大学讲坛时,强调的也是纯科学而不是应用科学的教学。这种对古典教育或自由教育的坚守,反映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保守主义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大学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分层制和固守仪式的组织,大学并不像其他机构,它基本上是保守的,其声誉不是建立在创新基础上,而总是有意地抵制突如其来的变革。”⑥ 2.精英教育的理念 自由教育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和社会精英,它折射了英国古典大学精英教育的理念。自由教育向学生提供进入上层阶级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因此它在控制个体与社会流动以及职业状态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纽曼和乔伊特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责是造就好公民,同时它应该为未来的国家事务和高级职业培养精英人才。“在自由教育的价值体系中,大学的作用被看作是保护精英价值观和培养精英人才。”⑦作为一种保留精英身份的成功方式,自由教育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它对于那种非精英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深表怀疑。艾略特认为,“自由教育是维护少数人文化品性的基本条件,它应该继续成为少数人的文化。”⑧自由教育认为性格比技能重要,身心和谐发展比专业成就更可取,礼仪端庄比自信更优越。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促进成功而是防止失败,它把社会道德而不是智力品质作为教育的目的,美德、高尚、献身、智慧、高贵、谦逊、勇敢等品质,都是自由教育追求的理想目标。 在英国大学制度中,牛津和剑桥的统治地位使它们在上层阶级中获得了特有的权力和社会声望。正如哈尔西和特罗指出的,“牛津和剑桥的‘魅力’构成了英国精英社会地位象征的基本组成部分”。⑨这种地位促使它们追求那种有抱负的职业,从而使其毕业生有优先进入教会、政治、法院和重要工业领域的权利。到19世纪中后期,“牛桥”大学毕业生仍然处于教育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牛津和剑桥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公学和文法学校。据统计,19世纪剑桥大学来自公学和文法学校的学生分别占54%和20%。⑩公学被誉为英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它们与牛津和剑桥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来自公学的男孩有更多机会获得牛津和剑桥的入学资格与奖学金,从而使得“牛桥”成为公学教育的自然延伸。艾略特指出:“精英必须在自己的机构进行培养,在英国意味着公学和紧随其后的更加智慧的牛津和剑桥大学。”(11)总之牛津和剑桥奉行精英主义教育理念,它们的目标是培养能维护英国利益的社会精英,这种独特的社会功能和大学精神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植根于“牛桥”传统中的自由教育传统逐渐遭到了破坏。学术职业、原创性研究、与外部机构建立新联系等,不仅改变了自由教育的传统,也引起了整个大学精神的变革。“在社会和经济压力的驱使下,在自身科层组织的推动下,以及在新右翼激进分子的攻击下,英国政府发动了一系列改革,以此重构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并增强国家对大学事务的控制。”(12)1963年发表的《罗宾斯报告》标志着国家精英和大学精英之间的分化,自由教育传统与大众高等教育的相关性开始受到质疑。这意味着构成精英权力基础的大学作用的转变,也预示着古典大学自由教育精神的式微。 二、城市学院兴起与大学服务精神 “从19世纪50年代起,要求大学为工业服务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牛津和剑桥直到20世纪才满足这种需要,很显然必须创办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从而导致了在一些新型工业城市中城市学院的诞生。”(13)城市学院的兴起不仅改变了英国大学面貌,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同时对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构成压力,最终迫使科学教育进入大学讲坛。 1.城市学院的兴起 “城市学院”也称为“地方大学”,自19世纪50年代起,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学院不是由英国政府创办,而是由富商投资或公众捐办。1851年经营棉花的富商欧文斯捐资97000英镑,创办了一所没有任何宗教偏见的大学学院,其学生可以攻读伦敦大学的校外学位。欧文斯学院开设的课程范围广泛,涉及人文学科、自然和生物科学、数学和政治学等。它于1873年开设医学课程,1874年开始招收女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达1000余人。欧文斯学院后来发展为曼彻斯特大学。建于1870年的梅森科学学院清晰地反映了创办者的工业背景及意图,它明确表示以技术和职业为导向。梅森科学学院在1900年获得皇家特许状成为伯明翰大学。1879年铁器制造商弗斯慷慨捐资建立一所艺术和科学学院,提供工程和应用科学方面的教学,并于1897年成立大学学院,后在市政当局和私人捐助下于1905年成为谢菲尔德大学。19世纪60、70年代,利兹和布拉德福德也成立了提供高级医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技术和艺术教育的大学学院。布里斯托大学学院成立于1876年,从事科学和工艺教学,并建立了附属医学院,它受惠于私人资助和市政府财政拨款,于1909年获得大学特许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共有8所城市学院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包括伦敦、杜伦、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谢菲尔德和布里斯托。与此同时,诺丁汉(1881)、雷丁(1892)、南安普顿(1902)、莱斯特(1918)、埃克塞特(1922)、赫尔(1928)等也纷纷成立了大学学院。 城市学院的诞生代表了地方的感情和需要,它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事物。赫尔大学在《为什么赫尔需要一所大学》的小册子中指出,大学能够成为一种“动力”,它是所在社区智力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它为所在城市及地区提供了新的智识活力,它是推动地方社会进步的保障。大学的影响力将辐射到整个社区。(14)在所有工业城市,公民的自豪感和在轮船、棉花、羊毛、重工业和财政方面的繁荣,为大学以每个城市命名创造了条件。由于这些大学越来越成为城市和地区的文化与知识中心,大学创办者也为这种迅速扩大的影响力而感到惊喜。城市学院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特别强调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科学与技术教育,带有强烈的科技教育与职业教育特征。城市学院的建立是英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英国大学职能及大学精神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只是为教会和统治者服务,也不再为少数富有阶级所垄断,而是面向广大中产阶级子女,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2.服务于地方工业 城市学院大多以当地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依托,并致力于为后者服务,重视采矿、工程、冶金和其他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教学,是所在城市的工业研究中心。“事实上,为了获得工业界的支持,几乎所有城市学院在不同时间都声明,它们的目的是服务于地方工业。”(15)从创办之日起,欧文斯学院就宣称,他们的科学研究是建立在为工业服务的基础上,如纯数学研究是为实际的和未来的工程、勘测、统计、计时、航海做准备。约克科学学院的目的在于为工艺美术提供科学指导和紧急需要。梅森科学学院就是为了适应制造商对实用的、机械的和艺术的需求,以及中部地区的工业需要。利兹大学为工业服务的目标也很明确,1907年利兹成立了英国大学中第一个煤气和燃料系,它关于燃气点火、燃气爆炸等装置的设计,都是在与工业界的合作中进行的。到20世纪初,城市学院逐渐成为促进地方工商业发展、实用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机构。这些学院与工农业和商业贸易密切相关,使它们获得了与牛津和剑桥完全不同的声望。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城市大学对于工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和相当重要的,即使在创办之初也是如此。它们正成为产业创新的主要来源,而迄今为止牛津和剑桥从未如此。”(16) 城市学院为地方工业服务的主要途径是提供咨询和加强科学研究。1857年罗斯科成为欧文斯学院的化学教授,他是第一个在广泛的工业领域从事咨询工作的英国教授,在推动城市学院与地方工业的联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罗斯科认为城市学院只有获得地方工业的信任和财政支持才能成功,他为当地卫生部门检验化学危害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为化工厂的废品回收、避免气体泄漏和工厂布局等提供建议。他检验布料及其化学质量,分析蒸汽锅炉里的水分,为曼彻斯特的城市供水做出决议。罗斯科是英国化工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主张新型工业应以科学为导向的重要人物;他既是城市学院服务地方工业的构思者,也是英国现代化学教育的奠基人。在布里斯托大学,尼伦斯坦关于奶酪制作的生化研究,推动了当地干酪工业的发展;麦克贝恩关于胶体化学肥皂的研究,不仅对英国肥皂行业做出了贡献,也促使了利弗休姆在布里斯托大学设立慈善基金。在利兹大学,普罗科特是第一个从事皮革化学研究的人,他在制革材料的控制与质量改进、铬革和皮具生产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轴承润滑、煤矿抽水机、钒钢、铬革、煤气取暖、火花塞、电台调谐、乳酪、肥皂、啤酒、四冲程发动机等工艺产品的开发和改进,都受益于城市学院(或城市大学)教授们的研究工作。”(17) 三、“牛桥”课程改革与大学科学精神 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巨大进步对英国大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自由教育无法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人们对其保守与落后进行了严厉抨击。“结果,英国自由教育无论是在外观还是现实中,都出现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动机和学术优先在大学史上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在自然科学领域,医学专业尤其重要。自然科学的扩充导致了‘科学精神’的传播,以致没有哪个学术科目能够逃脱它的影响。”(18) 1.围绕古典教育的大辩论 1809年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埃奇沃思在《爱丁堡评论》发表一系列论文倡导专业教育,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进行抨击,并提出“所有知识的价值最终必须由其实用性决定”的命题,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大学教育的大辩论。《爱丁堡评论》是辉格党的阵地,以激进和功利主义见称,它赞同埃奇沃思的观点并通过书评的方式对牛津大学进行猛烈斥责。“在英格兰大学,每年有大量的人才被埋没……每个人必须花费人生的一半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古典学科被认为是培养人才的最好工具,而且这一想法从未消失。”(19)古典语言把人的思维束缚于词语,并阻止对事物的学习;它们只教授语法和作文,而不是作者的思想。因此,它们切断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只局限于一部分古典遗产,是狭隘、片面和粗鄙的。《爱丁堡评论》对英国大学教育内容和目的公开提出了质疑,它并不否认古典学科和神学作为教育工具的价值,但令人反感的是它们成了唯一的学习科目。“大学似乎在为社会培养绅士和提供严格学术训练的理想之间割裂开来,英国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很模糊,它缺乏清晰的定义。”(20)对古典大学的批评同样来自《威斯敏斯特评论》和《教育季刊》,前者要求由世俗人士控制大学,以便大学摆脱国教会的束缚;后者呼吁对大学的知识体系进行改革,将自然科学和数学作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面对批判,维护古典教育传统的保守派发起了大肆反击,他们拼命为古典教育辩护。关于古典学科的功效性,他们的论辩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个男孩在古典学科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获得了什么报酬?古典学习能使他适合从事什么职业?古典学科怎样才能使他增加财富?爱德华·科普斯顿指出:“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古典教育学科不适合他从事专门的职业或者增加财富。……古典教育虽然不能使一个人胜任生活中的任何职业,但它可以使人更加充实和高贵;古典教育虽然不能教给一个人在任何政府机构工作的特殊业务,但它可以使人在每一个部门表现得更优雅和高尚。如果恰当地设计和引导,古典教育可以成为那种完整和高雅教育的主要成分。”(21)《季刊评论》是保守的托利党和正统国教派的守卫者,也加入了这场论战,声称“知识本身是好的”。在整个19世纪,这些论辩和主张成为了古典教育捍卫者信仰的基本原则。在英国进行的这场广泛而激烈的论战中,不少享有崇高社会声誉的学者参加了辩论。19世纪70年代“关于科学教学和科学进步”皇家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指出:“在英格兰,‘文学人’与‘科学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也许约翰·密尔可以看作文学人的代表,而赫胥黎则可看作科学人的代表。”(22)在论战中,赫胥黎倡导的科学教育无疑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精神,它对19世纪英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自然科学进入大学讲坛 19世纪50、60年代,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大学内部一些关键人物的改革热情,推动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科学教育的发展。牛津大学的早期科学,始于1850年创办的自然科学荣誉学院及其考试条例,该条例规定只有那些首先获得古典语言和数学荣誉学位的人,才能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当时一名学者指出:“无论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反对毕业生在离开大学时对于物质世界的一些重要法则完全无知。大学有责任合理利用已有的基础,促进解剖学、植物学、化学、自然哲学和地质学等方面的教育。”(23)1855年牛津大学建立了科学博物馆,1870年建立了英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1877-1879年成立了化学系。剑桥大学1848年设立自然科学荣誉学位,70年代各学院开始进行科学教学,1873年建立了卡文迪什物理实验室,同年成立了卡文迪什物理学会。随后剑桥大学又相继出现了医学、化学、动物学、解剖学、工程和机械科学的实验室。自然科学推动了剑桥实验大楼的建设,如1888和1909年的化学楼,1873和1895年的物理楼,1879-1884、1894、1900、1903和1912年的工程楼。(24)自然科学对讲座室、实验室、博物馆和工作人员任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改变了剑桥大学的校园景观,也打破了学院与大学之间的权力平衡。牛津和剑桥的改革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鼓励,1877年《大学法案》规定今后大学可获得一定比例的税收,用于加强和拓宽自然科学的教学。至19世纪80年代两所大学的科学研究日益兴旺。1850至1900年,剑桥大学70名教授中有科学教授18人,占26%;牛津大学84名教授中有科学教授15人,占18%。(25) 进入20世纪后,为了应对外部压力,牛津和剑桥进一步改变了知识结构。“在这个世纪,国家主要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报告,从四个方面向大学已有的知识结构施加压力:大学应该提供更多的知识;相对增加科学的比例;扩充应用科学和其他以职业为中心的学科;从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平衡转向以研究为主。”(26)从1922-192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在所有学生中,牛津大学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学生从10.2%上升为11.4%;医学和牙医学生从3.5%上升为4.6%。牛津大学研究生从6.3%上升为6.8%,其中自然科学研究生从11.8%上升为23.5%。但牛津和剑桥的人文与社会学科仍然占据很大比例。(27)1949-1950年度,在所有学生中,牛津和剑桥自然科学学生分别为16.8%和22.6%,人文科学分别为74.7%和55.1%;研究生总人数分别为12.4%和18.5%;1969-1970年度,自然科学人数分别上升为25.6%和25.3%,人文科学分别为38.6%和32.1%,社会科学分别为22.2%和18.6%;研究生总人数分别上升为28.0%和20.5%。(28)1969-1970年度,牛津大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全日制本科生人数分别为40.8%、22.2%和25.5%,剑桥大学分别为34.0%、19.6%和24.1%;到1988-1989年度,牛津大学分别为41.3%、20.3%和27.1%;剑桥大学分别为29.3%、21.2%和22.5%。(29)以上知识结构及学生人数的变化表明,整个20世纪自然科学与科学研究在牛津和剑桥所占比例逐步提升,在大学讲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平分秋色,“大学是以研究为中心的机构”已成为大学的精神特质。 四、新型大学的出现与大学创新精神 新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是战后英国大学创新的两个主要领域,其中多科技术学院在1992年升格为“新”大学。新大学校园位于开放的空域,其知识结构包含整个人文和自然科学;多科技术学院通常位于狭窄的城市中心,它更局限于职业教育传统,且大多数课程有严格的专业要求。这两类大学的新地点、新建筑风格和课程设置,更新了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认识。 1.新大学的建立 建立新大学的想法缘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最初被视为战后福利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并承诺向英国社会开放。但由于新大学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背景发生转变时它才正式招生。新大学在物质、组织和学术三方面颇有特色。它们位于小乡村,如东安格利亚、约克、兰开斯特、华威、苏塞克斯、埃塞克斯和肯特等。新大学的校舍以红砖为主,改变了过去大学以石头和青砖为主的古典风格,代之以鲜明的现代化格调,赢得了“红砖大学”的称号。新大学位于绿地之中(green-field),创办之初就被认定为国家机构,由国库直接拨款。它们属于校园型大学,校园建筑设计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建筑风格体现了创办者的愿望。“新大学既是一个学术的村落,又是城市和市民学习的象征。它们依山傍水,独立地向人们提供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设施……新大学在空间组织和外观形象方面的影响是决定性的。”(30) 几乎所有的新大学(华威大学例外)都废除了老大学中那种学科和部门结构之间的严格界限,而强调更加宽广的学科群,并提供更大范围的跨学科学习。在组织文化方面,新大学似乎是工人教育协会、美国大学和英国自由教育的混合体。“正如1963年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和同年《罗宾斯报告》描述的一样,它们是英国面临与美国同样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时,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制度一种特有的反应。”(31)新大学体现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新思路和新的组织范式。在新大学中发展起来的教学文化,也许不是那种宏伟的知识地图,而是基于想象中的学科联合和师生之间更加轻松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大学的民主始于新大学,而不是老大学的等级制度和多科技术学院的工具体系。“今天在‘老’大学和‘新’大学之间有一种广泛的平等。如果没有新大学,就会产生一种不平衡,并导致两种痛苦的结果—— 一部分是更加精英化和封闭的‘老’大学;另一部分是更加功能化和俗气的‘新’大学。”(32)20世纪60、70年代,在新大学中发展起来的知识文化继续支配着英国高等教育。这种文化是社会学的,而不是学术性(如老大学)和功能主义(如多科技术学院)的;它是批评性的,而不是学究式和工具主义的。新大学是面向中产阶级的现代化高等教育机构,它比老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更接近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理念。新大学无论在专业科目和课程设置方面,还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组织管理领域,都注重试验和创新,打破了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开辟了创办高等教育的新路径。 2.多科技术学院的创办 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多科技术学院属于另一类型的‘新’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和新大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物理空间方面,最初多科技术学院有三分之二建立在英格兰北部和中西部的老工业区以及内伦敦地区。多科技术学院是以技术教育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发展培养熟练工人,因此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价值取向,多科技术学院都属于地方当局,它们以特定的社区为基础。多科技术学院发扬了继续教育的传统,是一个开放的机构。它们大多数位于卫星城市的中心区域,比新大学更加方便入学,尤其是对于那些非全日制学生。多科技术学院的办学思想十分明确,即提高地方或地区人们的基本技能。多科技术学院也继承了非大学机构的服务传统,不是把追求知识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通过专业和职业教育满足经济和社会需求。因此它们的本质不是选拔性的,而是为了满足学生对更高职业技能的需要,提供范围更广的培训机会。多科技术学院的严重缺陷是资源不足,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它们就为自己的身份而抗争。1992年多科技术学院升格为“新”大学后,为了增强与“老”大学的异质性,它们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革。但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新职业主义的兴起,这种外在的压力也改变了“老”大学的发展模式,结果导致“老”大学与“新”大学之间的区别逐渐减少。 总之,作为英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扩张的两个主要创新,20世纪60年代的新大学代表了一种大学传统的更新,而多科技术学院是对传统大学的一种替代,二者都取得了成功,无论是在外观、空间和学术方面,都有助于重构现存大学的内部生活;它们建立了一种新的高等教育范式,与战前存在的学究式“牛桥”和地方性“城市大学”之间的两分法完全不同。多科技术学院的最大贡献在于重组了高等教育制度,不是通过思想层面的斗争,而是通过使继续教育中发展起来的不同价值和实践制度化以挑战大学的霸权。它们用一种动态的、开放的高等教育制度,取代了那种限制大学发展的静态模式。多科技术学院是英国政府向其他大学施加的一种压力,促使它们更加符合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的需要。新大学的建立被看作英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多科技术学院则被视为第二次浪潮,而且更加成功。建立新大学是为了扩充和改革大学部分,而创办多科技术学院是为了把分散的高级技术教育和职业训练统合起来,以弥补大学部分的不足。两者的不同特性源自不同的议程,而不是有意的竞争导致的。然而,对于大众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强调异质性的多科技术学院模式,或许比怀有整体抱负的新大学模式更加合适。多科技术学院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从最初的小型机构发展为大型和有效的机构,使得高等教育更加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引入了更多适合不同学生群体的课程;开辟了高等教育的新途径;鼓励少数民族和成年学生参与;引入更多的高级学习科目;开发新的课程模式;使扩张控制在可支付能力之内。(33) 五、提高大学参与率与大学民主精神 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是大学规模和学生人数的扩张。有学者指出,二战结束后的25年是英国大学的黄金时期,表现为空前的扩张和赢得公众的尊重。(34)随着《罗宾斯报告》发表以及大学生参与人数急剧上升,英国大学性质及大学精神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大学精英教育的理念逐渐为大众高等教育所取代。进入60年代以后,大学的性质、结构、类型和发展规模等成为英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社会对多规格、多层次人才的需求与英国大学贵族性、精英型传统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1963年10月发表的《罗宾斯报告》,拟定了到1980年为止的英国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罗宾斯报告》表明扩张是一种正式的国家政策,从而揭开了二战后英国大学发展的序幕。“国家前所未有地渴望通过控制大学为自己服务……人们也把大学看作国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学成为了公共机构。”(35)《罗宾斯报告》的意义不只是扩张,它对于高等教育机构模式、教师培训、财政、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大学学位的扩展、全国奖学金理事会的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大学校长委员会权力的加强等都产生了影响,它奠定了英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英国大学副校长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埃特金评价说,《罗宾斯报告》就像洪水一样,是英国历史上的分水岭。(36)《罗宾斯报告》之后,高等教育扩张,多科技术学院改革,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制和福利国家的进程,对战后出生的两代人的个人抱负、社会期望和经济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导致随后的高等教育与19世纪末以来标准的精英模式完全不同。当然它也遭到很多批评,有学者认为罗宾斯委员会对于快速扩张引起的广泛结果过于乐观,特别是在组织管理、人员配备、学科平衡和维护自治权方面。它没有充分考虑对学生经济条件的影响,过于强调结构和传统的大学作用,而忽视内容和大学未来的发展。 《罗宾斯报告》发表后,英国各级各类大学都进行了扩充。据拨款委员会的报告统计,从1949-1950至1969-1970年度,剑桥和牛津大学的全日制学生人数分别增加了29.8%和47.9%,而英国所有大学生人数的增长率达到156.7%。(37)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90年,英国适龄青年的大学参与率增长了4倍多,从8%提高到28%,1994年达到31%。(38)1990年英国大学生总人数为120万,到90年代中期超过150万,1996-1997年度达160万人,其中110多万属于全日制大学生或修习三明治课程,20万就读于继续教育学院。全日制大学生占65%,非全日制占28%,开放大学的学生占7%(也被看作非全日制)。女大学生比例从1962-1963年度的26%和1979-1980年度的37%上升为51%。21岁以上修习本科课程和25岁以上修习研究生课程的成年人占50%多,其中大多数属于非全日制(包括开放大学)。(39)可见大学不只适合于有特权的精英,也为更多的年轻人和成年人提供了入学机会。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2004学年近60%的大一新生是女性。2005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研究《高等教育中的青年参与》强调指出,到2000年进入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高于男性的比例达18%。(40)自《罗宾斯报告》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期望与男性一样高。很显然,大学扩张为原来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的群体(如工人阶级、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提供了更多的入学机会。 六、高等教育企业计划与大学企业精神 20世纪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开始竭力提升英国的工商业竞争力,并建立了专门的企业部。鼓励企业精神是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由于认识到英国大学长期以来对经济发展贡献不大,在经济、工商业和财富创造方面的地位没有得到彰显,1988年企业部启动了第一轮高等教育企业(Enterprise in Higher Education)计划,共投入合同资金6亿英镑,用于加强大学与企业的合作。该计划每一轮为期四年,大学可以通过投标的方式竞争。其目标在于帮助高等教育机构通过与工商业合作,使每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发展与企业相关的能力和兴趣。“这个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大学生一系列的企业品质、技能和态度,使他们增强就业能力,并对社区做出更加有效的贡献。”(41) 高等教育企业计划投入的大量资金既满足了高等教育机构的需要,也使大学生有机会培养更多的企业品质。那么这些企业能力和品质指什么?《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指出,前者包括每个大学生应该了解工商业世界,并熟悉某些管理和商业技能;后者包括帮助所有大学生发展那些人类必备的企业技能和特性。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关心大学生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尤其是谨防其“反商业”的势利行为。企业精神对于维持和改进就业、促进繁荣和公共服务是必需的,高等教育应警惕对企业的迟钝反应,并寻求机会鼓励学生培养企业精神。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应养成大学生对待工作的积极态度,高等教育企业计划的基本理念就是培养企业家。一般说来,高等教育企业项目的设计首先是根据一个成功企业家应具备的能力,包括领导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决断力;其次是基于雇主认为的重要知识和特有品质,如运用计算机能力、外语、批判性思维、交流和表达能力。英国共有66所高校获得了高等教育企业基金项目,第一轮有11个高等教育机构中标,包括布拉德福、杜伦、格拉斯哥和兰开斯特4所大学,6所多科技术学院和位于阿伯丁的罗伯特·戈登技术学院。在第二轮15个中标的机构中,大学占据了8个,包括伯明翰、布鲁纳尔、爱丁堡、利兹、利物浦、谢菲尔德、萨里和开放大学。第三轮中标机构更加凸显了大学的实力,阿伯丁、肯特、利兹、莱斯特、诺丁汉、萨尔福德、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3所医学院联盟和威尔士2所大学学院在27所参与机构中占据了12个指标。(42)虽然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的动机和投标热情不尽相同,但在当时财政拮据的背景下,可用资金的诱惑无疑是一个明显的刺激物。 高等教育企业计划意味着一种新的大学企业精神的出现。“它引起了一系列变化,如从雇主需要转向社会需求以及雇主接纳的个人发展;它不仅是商业目标的需要,也是从企业技能到生活技能的转变。”(43)该计划虽然没有渗透到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但它引起的系列变化有助于改写大学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设计和塑造了大学的传统与精神。企业精神已成为公共政策和高等教育话语的一部分,英国大学在新的环境中必须重新定位。如布里斯托大学就在一份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将在最广泛意义上融入企业文化和活动,继续发展和鼓励企业精神,以使大学成为具有强大企业文化背景的国际竞争机构。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大学变革的步伐十分缓慢,20世纪前半期英国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战争的影响。大学拨款委员会声称,战争威胁的逼近使得大学精神黯然失色。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大学处于文化生活、文明价值和文化精英形成的中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观念。(44)1948年利文斯通在《关于大学教育的思考》演讲中指出:“如果你想毁灭现代文明,最有效的途径是废除大学。”(45)20世纪后半期英国大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从只有少数知识或社会精英参与的机构发展为面向更广泛的职业和社会阶层。随着大学自身的变化,大学精神也不断创新。但是,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传统英国大学制度与精神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对英国大学精神特质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它们在形成英国大学模式的价值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种价值也正是其他部分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向往的。牛津和剑桥模式是独特的,但这两所大学建立的价值观在整个20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有力的反响。”(46)尤其是它们在确立“大学是由学者管理的自治机构”这一理念上最具影响力。“实际上,尽管不愿意,但19世纪末地方商业阶层认为,他们所创办的大学应体现‘牛桥’文化,而不是自己本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那时起,附加于大学制度的所有新事物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并做出了同样的让步。”(47)哈尔西指出,英国有一种独特的大学精神,它也被视为一种理想,它是一种源自牛津和剑桥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48) 收稿日期:2015-07-20 注释: ①Peter Scott,The Meanings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5),12. ②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1850-1970(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35. ③Harold Silver,Tradi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Wi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39 ④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5),122. ⑤Ibid.,124. ⑥Harold Silver,Tradi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Wi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40-41. ⑦Ted Tapper and Brian Salter,Oxford,Cambridge and the Changing Idea of the University(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12. ⑧Ibid.,11. ⑨Ibid.,7. ⑩William Gibson,"The Social Origins and Education of an Elite:The Nineteenth-century Episcopate," History of Education 20,2(1991):101. (11)A.Boyce Gibson,"Education,Culture and Elites:T.S.Eliot," Melbourne Studies in Education 8,1(1965):5. (12)Ted Tapper and Brian Salter,Oxford,Cambridge and the Changing Idea of the University(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3. (13)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1850-1970(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61. (14)Harold Silver,Higher Education and Opinion Mak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Woburn Press,2003),19. (15)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1850-1970(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81. (16)Ibid.,93. (17)Ibid. (18)Roy Macleod and Russell Moseley,"The 'Naturals' and Victorian Cambridge:Reflections on the anatomy of an elite,1851-1914,"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6,2(1980):179. (19)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5),35. (20)Peter R.H.Slee,Learning and a Liberal Education: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Cambridge and Manchester,1800 -1914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9. (21)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5),36-37. (22)G.W.Roderick & M.D.Stephens,"Scientific Studies at Oxford and Cambridge,1850-1914,"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XXIV,1(1976):50. (23)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5),89. (24)Michael Sanderson,The Universities and British Industry 1850-1970(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35. (25)G.W.Roderick & M.D.Stephens,"Scientific Studies at Oxford and Cambridge,1850-1914,"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XXIV,1(1976):57. (26)Ted Tapper and Brian Salter,Oxford,Cambridge and the Changing Idea of the University(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114. (27)Ibid.,116-118. (28)Ibid.,123-124. (29)Ibid.,139. (30)Peter Scott,The Meanings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5),54. (31)Ibid.,55. (32)Ibid.,56. (33)David Smith and Anne Karin Langslow,The Idea of A University(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1999),121-122. (34)Ted Tapper and Brian Salter,Oxford,Cambridge and the Changing Idea of the University(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120. (35)Harold Silver,Higher Education and Opinion Mak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Woburn Press,2003),178. (36)Ted Tapper and Brian Salter,Oxford,Cambridge and the Changing Idea of the University(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12. (37)Ibid.,121. (38)Peter Scott,The Meanings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5),22. (39)Harold Silver,Higher Education and Opinion Mak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Woburn Press,2003),230. (40)Carol Dyhouse,Students:A Gendered History(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6),PX. (41)Harold Silver,Tradi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Wi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114. (42)Ibid.,109. (43)Harold Silver,Tradi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Wi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116-117. (44)Harold Silver,Higher Education and Opinion Mak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Woburn Press,2003),80. (45)Ibid. (46)Ted Tapper and Brian Salter,Oxford,Cambridge and the Changing Idea of the University(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225-226. (47)Ibid.,6. (48)Ibid.,7.标签:大学论文; 剑桥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大学精神论文; 英国大学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