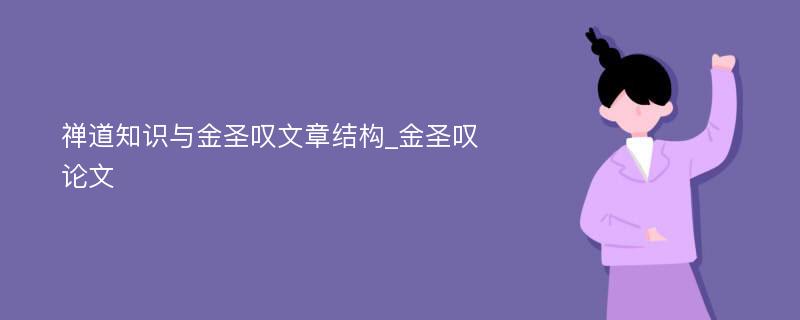
禅、道的知识学与金圣叹的文章结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知识论文,文章论文,金圣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5)04-0054-06 “知识学”一词出于齐良骥先生的《康德的知识学》,内云:“知识学就是对于知识本身进行基本的、原理方面的考察。”[1]知识学不同于单纯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学。由于大乘中观学派龙树主张去除知解分别的作用,纯粹依靠直觉体悟实相,因此,本文所借用的“知识学”概念不同于瑜伽行派的因明学和量论。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存在世界的本体、现象界的组织结构、获取知识的途径、理论表述的形式等。 “法天地”的叙事观念在中国上古时代就已经奠定下来,体现了观念形式对叙事结构的深刻影响。杨义先生指出,读中国叙事作品不能忽视以结构之道贯穿结构之技的思维方式,不能忽视哲理性结构和技巧性结构相互呼应的双重构成[2]。金圣叹的文法理论讲究严整神变,与传统的结构松散的“缀段”式叙事方法有很大不同,具有严密的结构。在他的文章结构理论背后,隐含着禅宗、道家的宇宙构成图示和体悟方式。因此,我们说禅宗、道家的知识学与金圣叹的文章结构理论相汇通,是金圣叹论文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一、禅、道的知识学 西方人对真理的探索总是在主客关系中展开。康德认为知识最初源于客观存在物对人的刺激,存在物只有在人的先天直观形式中显像才能为人们所掌握。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逻辑结构是“在……中”,即“存在”从属于一个特定的“世界”[3]。只有认知主体展开一个“世界”,认知对象才从一种遮蔽状态中如其所是地绽放出来。因此,在西方视角下的认知过程中,主客体是独立外在的关系。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所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罗素曾经批驳了一种存在论的主张,认为将宇宙的每个部分视为“一个小宇宙”,且作为“全体的一个缩影”,只是“一种贫乏的想象”[4]。然而这种观念正体现了禅宗、道家知识学的特点。由于禅宗、道家是两个庞大的思想系统,本文以对金圣叹影响较大的临济宗和老庄思想为例,谈一谈禅宗、道家的知识学及其对金圣叹文章结构理论的影响。 临济宗人主张佛性遍及世间一切“无情”之物,因此,禅修旨在从根本上打破种种差别相,实现向本然生存状态的回归。义玄有“心清净”一说:“尔要与佛祖不别,但莫外求。尔一念心上清净光,是尔屋里法身佛;尔一念心上无分别光,是尔屋里报身佛;尔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尔屋里化身佛。”[5]义玄认为世人无法脱离苦难,是受了世俗情智的搅扰,心内不清净恣意妄动所致,欲寻求解脱,须返身向内。“心清净”的关键是破除将“心”视为实有心的执见,超越知解分别的障碍。南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6]临济宗人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对“无”字的参悟中。《法演禅师语录》最早记录了“赵州无字”公案:“上堂举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僧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州云:‘为伊有业识在。’”方立天先生指出:“‘无’字公案中的‘无’字本身不是思想,而是一种禅修的方法。不能把‘无’字当作虚无或有无的无来理会,如果把‘无’字作为哲学思想来思考、分析,就陷入‘恶知恶觉’的困境,而不得解脱。”[7]“无”字公案意在告诫人们耽溺色界法相固然是痴迷,但执着于“无”,将其视为超然物外的绝对本体同样不可取。 老庄关于“道”之体用的说法与临济宗相似。“道”不可言说,不在万物之外,而是万物如其所是的根本原因。《庄子·知北游》曰:“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欤?”[8]故鄙贱如“蝼蚁”、“稀稗”、“尿溺”无不呈现了“道”之内容。道家认为要超越现实存在的有限性达到与道合一的境地,须“心斋”、“坐忘”。“心斋”即去除各种功利的企图和欲念,“坐忘”即消解物我存在的界限与万物合一。《老子》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9],主张去除人为的扰动,使万物回复到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中。 临济宗和老庄思想对金圣叹影响非常深刻。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载,有人问金圣叹“圣叹”二字何义,他回答说:“《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10]金圣叹又以佛教中观学说阐释曾点的境界:“南泉大师所谓‘随分纳些须’者,即曾点‘暮春’遗意也。”吴正岚说:“金氏认为曾点‘暮春’遗意和佛教无分别观念一样,象征着无偏无倚、洒落自得的境界。”[11]金圣叹在《语录纂》卷之一中写到:“物各得其所则不乱,故云所;既得其所,即于此安身立命,故云立。‘卓尔’者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各各自立,不相倚藉之谓。”[12]又写道:“如来者,如了来,非来了如。久已好端端,如在这里,只管簇新来。”[13]万物各安性命之情、处常待变,是金圣叹理想中的存在秩序。至于佛教的戒律,他认为是破坏本性的妄作。金圣叹说:“夫大慈悲,止于不食肉而已乎?麋鹿食蔫,牛马食料,螾蚓食泥,蜩螗食露,乃至蛣蜣食粪,皆不食肉,即皆得为大慈悲乎?”[14]金圣叹还每于登坛讲经前吃狗肉,表达了不同流俗的见解。他在《圣人千案》中用“月爱三昧”解说“独超案”,形象地说明了他的思想。“独超案”讲述了一则禅门故事:西堂、百丈、南泉随侍马大师“玩月次”,三人各言己志,西堂欲“供养”,百丈欲“修行”,南泉则“拂袖便行”[15]。金圣叹指出三人虽行止不同但都是顺性命之情,“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无高下之别。所谓“月爱三昧”指的是这样一种境界:月照当空,为众生“作大荫凉”,于是一切尘劳停息,皆“呈露清凉本性”。而“本性”于万物有不同的表现,在美女为“爱”,在西堂为“供养”,在百丈为“修行”,在南泉为“独超”,总之,各自适其所适。 徐增描述金圣叹的神情时说:“盖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16]金圣叹自己也曾说过:“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销陨在花里边去;花看人,花销陨到人里边来。”[17]这两句话形容的是一种去除了“我执”,达到物我一体、万物一齐的禅修境界。金圣叹将宗教信仰付诸生活实践,尤能显出禅宗、道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二、最大的章法:由“生”到“扫” 金圣叹删改《水浒传》的动机是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胡适、鲁迅等学者早早地给这个问题定了性。鲁迅说:“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的可以。”[18]金圣叹的文法被认定为旧文学的积弊,而他本人也被视为思想反动的旧乡绅。这样一种观念抑制了当时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研究[19]。建国以来,张国光撰写了大量文章,旨在阐明金圣叹有讴歌革命的思想,他不是封建反动文人,不是《水浒传》“最凶恶的敌人”[20]。其实,就金圣叹的政治立场而言,各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金圣叹的思想非常复杂,诚如陈洪先生所说,金圣叹先前把“绝意仕进”、向慕五柳的话讲得太满,后来又作了《春感八首》表达对顺治帝的悼惜眷恋,思想上失去了一贯,呈现出了自相矛盾的人格缺陷[21]。陆林先生的金圣叹史实研究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宗教实践家的面目,了解到在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内容。陆林先生指出:“金圣叹早期的扶乩降神活动对其一生影响巨大:不仅为其社会评价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而且给其随后从事文学批评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22]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留意金批《水浒传》、《西厢记》文本结构所隐含的哲学思想。谭帆先生认为:“他在世界本原和文学本原之间似乎找到了某种共通之处,并直接用佛理阐发了文理。”[23]谭先生将《西厢记》“生——空写”的结构分为“起、承、转、合”四部分,并详加阐释。樊宝英从《周易》的“物不可穷”论、老庄的“有无”思想、佛教的梦幻观三个方面入手,探讨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西厢记》的深层文化原因[24]。张曙光将金批《水浒传》分为超故事层面、故事层面、微观层面三个层次,指出最外层的整体结构遵循的是“天地之数”[25]。 金圣叹在绝笔诗中写道:“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可见他对文学批评的重视。金圣叹称他批读六部才子书用的是“同一副手眼”。李雅在《木厓集》序中说:“尝观其五种才子书及唐诗前解、后解,所评所论,但一枝笔也。”[26]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一副手眼”、“一枝笔”其实正是他的宗教人生观和世界观。金圣叹给予《水浒传》和《西厢记》极高的评价,直视为世间“万千文字之总持”,由于两部作品概括了万物最一般的存在状况。在金圣叹看来,世间万物都是假象,因此有生有灭。金圣叹说:“圣人看万物不是物,都是鬼神……神无物而有物,少不得见者神之状;鬼有物而无物,永不得见者鬼之状。欲生出一切万物,如父母法者,神之情;欲敛藏一切万物,如盗贼法者,鬼之情。一个搬出来,一个搬回去。”[27]这里的“神鬼”指万物本身包含的产生和灭亡的两个趋势,金圣叹又称之为“生”和“扫”。所谓“生”,指“太虚空中本无有事,而忽然有之”;所谓“扫”,指“一切世间妄想颠倒有若干事而忽然还无”[28]。这种万物由“生”到“扫”的过程就成了金圣叹文法中“最大的章法”。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修改也是循着这样的思路。 金圣叹首先将《水浒传》第13回中原本并不重要的晁盖梦北斗七星的情节突出强调了一下:“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29]如此一来,性格鲜明的一百八人连同他们的事迹就成了迷离恍惚的“颠倒梦想”。他又将原书70回后的内容删去,以卢俊义一梦一百八人一齐处斩收束,并加上批语:“晁盖七人以梦始,宋江、卢俊义一百八人以梦终。”[30]至此,金批《水浒传》就形成了一个起于梦幻、终于梦幻,包含着宗教寓意的结构。金批《西厢记》也呈现出了类似的结构,金圣叹说:“然则如《西厢》,何谓‘生’?何谓‘扫’?最前《惊艳》一篇谓之‘生’,最后《哭宴》一篇谓之‘扫’。盖《惊艳》已前无有《西厢》。无有《西厢》,则是太虚空也。若《哭宴》以后亦复无有《西厢》。无有《西厢》,则仍太虚空也。”[31] “最大的章法”说的特殊之处在于,金圣叹强调《水浒传》、《西厢记》中所有的文字只是引导人们因色悟空的手段,一旦目的达到,便可全部废弃。金圣叹指出《惊梦》是《西厢记》中的“空写”一篇,“一部大书,无数文字,七曲八折,千头万绪,至此而一无所用”,并且“立地快然其便裂坏”[32]。因此,他说了一句颇有深意的话:“《西厢记》只是一个‘无’。”这里的“无”即佛家常说的“毕竟空”,是形而上的本体概念。 过去,我们习惯于以老庄“有无相生”的思想解读“最大的章法”,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有无相生”中的“无”是相对的,不能借来解释形而上的本体。《楞严经》曰:“汝观此一邻虚尘,用几虚空和合而有?不应邻虚合成邻虚。又邻虚尘析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若色合时,合色非空;若空合时,合空非色。”因此,释家所讲的本体之“无”是恒常寂净的。金圣叹说:“单说一空,空有对待,仍是色法。空空则无对待。”[33]倘若“无”能生“有”,就会与诸色“同于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无”了。金圣叹对“一”和“元”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本体的“无”和“有无相生”的“无”的差别。金圣叹解释“一”字时说,伏羲欲世人知“无画处”故作此一画,告之“此一画也者,无此一画者也”。而世人却固执地以为此为“一画”,反于“一画”之外寻求所谓“无一画”。于是,伏羲大戚,“便取前画而拆示之”,必使之明白“无一画”正是“此一画”[34]。金圣叹对“一”的解释说明了释家“真空”、“妙有”本为一谛的观念,他对“元”字的解释则是对万物生生不息的描述。他说:“元之上半,寂然不动也;其下半,则不动者初动也……夫今年之动而出者,即去年之动而入者也。动而至于底尽处,其为动也甚微,有似乎不动焉,而非不动也。”[35]他将“元”字上半“双钩空处”比作“色究竟天”,“色究竟天”为色界十八天之最顶层,因此不能与本体之“无”混淆。 论述至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上个世纪的那场争论。腰斩《水浒传》、《西厢记》并不能反映金圣叹的政治立场。他固然有同情农民起义的一面,但这仅仅是因为他的哲学观指出万物有其本然的状态,此为“乾元之节”,末世的君王扰乱了这种生存的秩序,使得万物不能“自尽其调”,于是就要“犯上”。同样,也不能说一百八人一齐处斩的结局显示了他对农民起义有多么仇视,他如此删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诸法皆空的观念。南泉禅师曾因弟子争夺寺院的猫,下狠手将猫杀死,用意正在于以颠倒正颠倒。我们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倒是能够依稀辨出南泉的身影。 三、作为修辞的“三境”说 金圣叹曾为徐增的《怀旧诗》作序,将集中咏怀故人的400首诗誉为“佛氏的至言要道”,将其等同于释家的“如幻三昧、月爱三昧、一切佛集三昧、宿王游戏三昧”[36]。倘说由“生”到“扫”谈的是意象之辨,那么“三境”说讨论的是象言之辨。金圣叹说:“‘齐’者,物我一齐,是非两忘,承上‘游’字说来。有物我,则有是非,而‘论’出矣。‘论’者,不齐之极也。”[37]由于“不齐”,故“论”时要“扣其两端”。金圣叹又说:“《鲁论》只是‘扣其两端’,故谓之论。两端,乃段绢一疋,两头卷到中心,非两疋也。车轮、鸟翼之谓两,乃彼此一合相,不作二字解。”[38]在文论中,金圣叹对矛盾范畴的运用得心应手。在人物描写方面,金圣叹说:“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39]在行文方面,金圣叹主张在文章紧要处插入闲笔;在实写处加入虚写;“事之钜者”将其“隐括”,“事之细者”反欲“张皇”。正是这种笔法的变化不定使文字焕发了生命力。 “三境”说源于金圣叹对言象关系的思考,他发现事物的形象很难用语言写尽:“天下莫易于说鬼,而莫难于说虎。无他,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时,真是大段着力不得。”[40]文字一旦坐实,难免神采遗落,倘若作者一味要穷形尽相,那么笔下的形象便会趋于恶劣。以“黑水澄时潭底出,白云破处洞门开。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四句为例,其中“黑水”、“白云”、“红叶”、“绿苔”,色色俱到,一味实写,金圣叹评曰:“一何丑乎!”[41]又如《水浒传》母药叉形象描写一段,作者从武松和两个公人的眼中由远及近细细地描摹了母药叉的装束。金圣叹在此段文字下批“如画”,并由此生发出如下感慨:“尝言美人之美,乃在或远或近之间,今写此妇人,既远近皆详矣,乃觉眼前心上,如逢鬼母,何也?”[42]金圣叹指出“一笔实写”非但不会传神,反倒使形象更加丑陋。 “三境”说的具体内容是:“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者,文章之化境也。”[43]在具体阐释之前,笔者先对“心”字加以说明。王先霈先生指出,“心”是“作家的艺术思维”,“亲动心”指“作家化身为人物,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44]。陈洪先生也说,“心至”即为“动心”之意。金圣叹认为纸上的文字乃至世间万物都是心造的幻相,他经常表现出惊人的“格物”本领。金圣叹在叶绍袁家的那场扶乩招魂活动中,同时模拟了四位女性的口气进行“易性写作”,显示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出众的文字水平[45]。因此,心中腾起想象,构出一种妙景,此即“心之所至”的含义。“三境”中的第一境指言尽象尽,即金批中的“如画”之意。在“三境”中的二、三两境中,具体可感的形象被冲淡了,作者将目光投向了难以言诠的形象之神采处,遂把创造的权力让渡给了读者。有一点不同的是,在第二境中,作者仍然会向有无明灭中淡抹几笔,让读者去添枝加叶。金圣叹指出“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46]。就杜甫《画鹰》“耸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两句而言,“耸身’句是传神,‘侧目’句是写照”[47]。因此,第二境即金批中的“传神”之意。第三境中的形象全在文字之外,读者心中。金圣叹在《吴周维之升》中说:“三四写得秾丽,最是好手。但好手写到秾丽时,必是空无一字。”[48]“三四”指律诗三、四两句,由于唐律中三、四两句多为景句,故有此一说。不着字的地方最能唤起读者的想象,以此第三境成了“三境”中的最高一境。 其实,“三境”中的第三境并非金圣叹笔法中的至高境界。第三境虽不立文字,但表现的中心仍是形象,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无争议。王先霈指出:“注彼写此有两种方式,一是为了描写某人,却不着笔在他身上,而写他周围别的人;一是为了描写某人的某种特性,却不着笔于这种特性,而写他别一方面的行为或心理。”[49]吴子林也认为:“这些‘化境’文字,都是含而不露的写人之笔。”[50]有一种笔法则直达神理。金圣叹评刘宪诗“柳色梅芳何处所,风前雪里觅芳菲”时说:“不知是虚是实,但觉欲离欲合。真可谓玄解之宰,向虚空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者也。”[51]作者作诗时的心理正如庖丁解牛,“官知止而神欲行”,目中所见已非生活实景,乃是一种神理。禅宗有则公案讲杨岐骑三脚驴踏破天下。当人们的知解被踏破后,就会体悟到“雪中芭蕉”的妙处,也就能对艺术的高下作出更准确的评判。 四、文章的三层结构 金圣叹曾用一个譬喻说明文章的三层结构:“一时佛,象。在舍卫国,卦住了。过无量佛刹,有一佛刹。卦。中有一世尊,象。有两大菩萨,二爻五爻,善能为众生广说佛事。辞。”[52]在“象”之先是“万物之性”,即存在本体,金圣叹曰:“意是实法,识是光影。”[53]我们姑且名之为“意”;“象也,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圣人胸中先有象而复有卦;圣人为“摇动”象与卦,遂“算出辞来”。“象”虽各别,只言“一副妙理”,“辞”虽满纸都为阐明这个“象”,文章由此形成了意、象、言三个层次。但“象”与“辞”都已经“走了样”。金圣叹说:“‘齐’里边没有‘物’,‘物’里边没有‘论’。‘论’走了‘物’底样,‘物’走了‘齐’底样。”[54]金圣叹强调当人们领悟了妙理,务必“坏此三昧”,不得执着于“象”与“辞”,《齐物论》的“下手工夫,全在打破‘论’字”。 依照上述思想,我们可以清楚地理出《西厢记》的层次来。“无”是《西厢记》寓含的妙理,是整篇文章的主旨。“双文”“张生”“红娘”是形象层面中的三个关键人物,故为各章节的小题目。金圣叹说:“前《请宴》一篇,只用一红娘,他却是张生、莺莺两人文字;此《琴心》一篇,双用莺莺、张生,反走过红娘,他却正是红娘文字。”[55]至于夫人、法本、白马将军等人,不过是作者为写三人“忽然应用之家伙耳”。金圣叹对文章主次关系的处理很特别,他不主张直接写入正题,而是在“题前”、“题后”下功夫: 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逦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56] 这种主干用枯笔,枝叶用腴笔的写法其实正是上文提到的“三境”最高一境无字的具体运用。金圣叹对此笔法十分赞赏,他作过很多比喻。如将其比作狮子滚球,使出通身解数“不放脱,却不擒住”;比作下双陆棋,“彼人大欲作,我乃那辗如不欲作”;比作采珊瑚,观其长势先下一网,待落入网中将其通体举起;比作作画,先自“最下一角”“作从旁小景”,既而“渐渐添成”。在过去,人们只要一提到金圣叹就会想起“八股调”。金圣叹的文法论确实有八股文论的形貌,但与其他文论家相比,又有其独特之处。明代吴默说:“要说得题到,须先识题。夫有题之皮肤,有题之筋骨,吾舍其皮肤而操其筋骨,故片言有余,不然,费尽心力,只成一篇训诂。”金圣叹和吴默都重视文章的主干,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吴默认为文章“理胜则神王”,“辞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着一分辞,便掩一分意,意思到时,只须直写胸臆”。其笔墨所向与金圣叹正好相反。因此,我们说金圣叹文法理论的根本在于禅宗、道家思想。 文章三个层次的思想还为我们明示出创作的次序:首先,金圣叹强调创作一定要有缘故,不可妄作。“缘故”指作者觑见了一种“道理”,金圣叹说:“若教他写伯牙入海,成连径去,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苦心力学人满肚皮眼泪来。”[57]金圣叹论创作灵感带有很浓的禅学意味,有如禅宗的机锋一般,过此一刻便如泥牛入海永无消息。他说:“仆尝粥时欲作一文,偶以他缘不得便作,至于饭后方补作之。仆便可惜粥时之一篇也。”[58]其次,作者下笔前定是“先有成竹藏之胸中”,且经历过一番惨淡经营。姚文放先生说:“艺术家要在内心铸成鲜明的艺术形象,在创作冲动的驱策下使这种艺术意象浮现到明晰的意识中,甚至达到呼之欲出的地步。”[59]金圣叹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说:“‘经营’者,将马从头至尾一直看去曰‘经’,复从马四面看转来曰‘营’。将军经营良久,俨然见天马立于绢素间,然后纵笔一拂,须臾而天马出矣。”[60]再次,作者下笔当“随笔迅扫”,书毕自看便觉“字法句法章法都被占尽”,修改不得,遂至“辞达”的境地。“辞达”非“明白晓畅”之意,而是指文章的“严整神变”、浑然一体。 金圣叹谈造字法时说:“造字者,造天地所造之物之字也,造天地所以造物之字也……天地不变异,物不变异,物所作业不变异,则字法不能变异也。”[61]他在论古诗时说:“知累累千余言,皆从无字句处架造,皆从无字句处收拾矣。”[62]由此可见,金圣叹的论“字法”、“诗法”、“文法”,无不灌注了他的一整套禅宗、道家的观念。对金圣叹思想与文章结构论关系的研究,既能深化我们对其理论内部的有机结构的认识,也为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收稿日期]201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