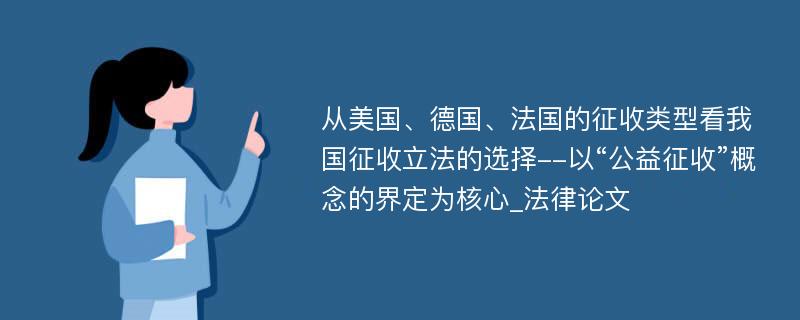
从美、德法上的征收类型看我国的征收立法选择——以“公益征收”概念的界定为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我论文,公益论文,概念论文,类型论文,德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益征收的类型与其概念密切相关,但在各国法上,并不存在“公益征收”(征收)的宪法或法律定义。因此,在类型与概念的逻辑关系上,由抽象的征收概念推演出具体的征收类型的思维进路是行不通的。相反地,如果可以确定征收的具体类型,再经由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归纳,则可以大致确定征收的内涵及外延,从而给出一个较为确切的征收定义。我国未来的统一征收立法也不可能对征收做出明确的概念性界定,但由于我国立法者往往更习惯于遵从演绎式逻辑思维,因此,如果在学理上能提出一个为立法者所接受的征收概念,以其作为立法时类型推演的前提和类型选择的依据,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本文在对美国与德国的征收类型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法上应选取的征收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广义的征收概念。
一、美国征收法理中的征收类型
(一)正式征收与反向征收
这一分类的标准是征收程序的不同启动方式。正式征收(formal expropriation),是指联邦或州政府为满足公共使用的需要,通过启动正式征收程序而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反向征收”(inverse condemnation),顾名思义,是逆正式征收程序而发动的一种征收;具体而言,是指因政府在未采取正式征收程序而剥夺私人财产权的情况下,由财产所有人为寻求补偿而发动的征收诉讼。(1)因此,单就概念而言,正式征收与反向征收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其一,正式征收的启动主体是政府,反向征收的启动主体是私有财产权人。其二,政府在正式征收程序中处于主动地位,而在反向征收程序中处于被动地位。其三,正式征收是国家征收权(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的正式、公开发动,须严格遵循相关的征收程序;而在反向征收中,政府试图规避正式征收程序,从而达其不欲补偿的潜藏目的。其四,若启动正式征收程序,政府必须给予补偿;而在反向征收诉讼中,政府是否负有补偿义务,由法院裁决。其五,正式征收是一种行政程序,而反向征收是一种司法程序。
反向征收又可再分为“占有性征收”(physical takings)和“管制性征收”(regulatory takings)。但若从广义上讲,实际上inverse condemnation与regulatory takings二者同义,因为所有的“反向征收”往往都是因为政府的“regulation”(管制)而引发的。因此,广义上的“管制性征收”包含了“占有性征收”,所谓“占有性征收”只是一种包括了事实上的“侵入”(invasion)或“占有”(occupation)因素的管制性征收而已。因此可以说,在与“反向征收”同义的意义上,广义的管制性征收可区分为包含了占有性或侵入性因素的管制性征收与不包含占有性或侵入性因素的管制性征收。将反向征收区分为占有性征收与管制性征收的意义在于:在占有性征收情形,存在对土地等财产的有形物理侵入(invasion),并且形成了永久性的实质占有(permanent physical occupation),该种侵入或占有等同于对所有权的剥夺,因其对财产权的侵犯和剥夺是明显的,所以必须予以征收补偿,故其本身构成了判例法上的一种本质规则(per se rule);而在管制性征收情形,完全不存在有形的物理侵入,只是因过度的法管制而导致财产使用权等的被侵损或剥夺,因而管制性征收并不构成一种本质规则(not per se rule)。②由于占有性征收在认定上往往不存在大的困难,所以美国现今的征收法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了“管制性征收”的同名词,③几乎所有的疑难复杂案件都是围绕着管制性征收而引发的,“takings”实际上已经等同于“regulatory takings”。
(二)全部征收与部分征收
之所以存在这一分类,与美国财产法上“所有权整体性”(the unity of ownership)和“概念性分割”(conceptual severance)两种不同的所有权概念观有关。“所有权整体性”本源上是大陆法系的一种所有权观,认为所有权是一种独立的不可再分的权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仅为所有权的权能,而非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独立权利。与此不同,英美财产法的通行观念则认为,所有权是一个“权利束”(a bundle of rights),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不仅为构成所有权的要素,而且其本身即分别是一种独立的权利(discrete right)。在征收法上,这两种不同的所有权概念观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征收必须是对所有权整体之剥夺,还是对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所有权之部分的剥夺亦可构成征收?这就涉及全部征收(total takings)与部分征收(partial takings)的类型区分问题。在美国征收法上,就财产权之全部剥夺而构成的全部征收而言,不存在任何争议,而极具争议的只是部分征收问题。
“概念性分割”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学者Margaret Jane Radin于1988年提出的,用于概括和描述部分征收问题。根据Radin教授的界定:“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财产利益恰好是政府从财产所有人处取走的,从而宣称该特定部分之整体(that particular whole thing)被永久地剥夺;由此,概念性地假定那些受政府管制影响的权利(strands)被从整个的权利束(the whole bundle of rights)中分割出来,并且在整体上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整物(in the aggregate as a separate whole thing)。”④简言之,根据“概念性分割”观,构成财产权这一“权利束”中的任何一支权利(a stick of right),都被视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对其的剥夺都可能构成征收。此种情形下的征收,即为部分征收。
在Tahoe-Sierra Preservation Council,Inc.v.Tahoe Regional Planning Agency案中,⑤美国第九巡回法院认为:“财产利益可以存在诸多面向,例如,物理性面向(描述的是所涉财产的大小和形状),功能性面向(描述的是财产所有人可能使用或处分其财产的范围),以及时间性面向(描述的是财产利益的时间跨度)。”该判决实际上提出了财产权概念性分割的“三维向度”,即物理分割、功能分割和时间分割。⑥由此三种分割情形所决定,部分征收也就包括了物理上的部分征收、功能上的部分征收和时间上的部分征收三种类型。
在对待部分征收问题上,美国学者Epstein教授持坚定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征收条款对私有财产权之每一部分(each part)所提供的保护与其对财产之整体所提供的保护是同样的,既不多亦不少(no more and no less)。不论构成所有权这一权利束中的基本权利(basic entitlements)被如何地划分,也不论此种划分被进行过多少次,这些基本权利之整体以及每一种基本权利,都不脱征收条款之保护范围。”⑦因此,在Epstein看来,不论是财产权的物理分割、功能分割还是时间分割,都会构成财产权征收从而应予补偿。正是立基于此,Epstein在其著作中,就占有权的征收、使用权的征收、处分权的征收等做出了相当详尽的分析。⑧
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对于是否应当遵循“概念性分割”观,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和相互矛盾的判例。如就财产权的功能分割而言,在Andrus v.Allard一案中,⑨法官们就全体一致地拒绝将商业开发权(commercial exploitation)从整体的权利束中分割出来。主笔该案判决的Brennan大法官认为:“所有人拥有完满的一束财产权利,对该权利束中一支(a strand)权利的破坏并不构成征收,因为该权利束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in its entirety)。”但仅仅时隔8年之后,在Hodel v.Irving一案中,⑩法院即判决对只涉及一块部落土地的2%继承权益的剥夺构成征收。执笔该案判决的O' Connor大法官认为:该法之所以构成征收,是因为它剥夺了“财产权这一权利束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一项权利,该权利是将某一类型的财产权传至继承人的权利,而继承权是自封建时代以来英美法律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如就时间分割而言,在First English Lutheran Church v.County of Los Angeles一案中,(11)法院判决,当一项法令暂时性地剥夺了财产所有人的所有经济可用性时,所有人即有权请求损失补偿。涉案法令被宣告违宪,因为它没有规定任何的期间限制(durational limit);但法院判决认为,该法令之被撤销并不能剥夺所有人对因法令生效期间而造成的损失的补偿请求权。执笔该案判决的Rehnquist大法官指出:“暂时性征收(temporary takings)与永久性征收(permanentones)具有相同的地位,因为在涉案期间它就是永久性的。”但在Tahoe-Sierra Preservation Council,Inc.v.Tahoe Regional Planning Agency一案中,(12)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派(六位)大法官认为,对涉案土地的开发权推迟32个月并不构成征收;但该案判决同时又指出,根据Penn Central(13)一案确立的“诸因素平衡论”(multifactor balancing approach),类似于该案的推迟开发(moratoria)仍然可能构成征收,其中推迟的时间是一个必须考虑的事实因素。
综上所述,关于“概念性分割”观在美国征收法理中的地位,因联邦判例的反复而变得晦暗不明,学者Epstein的自由主义主张亦尚难实现,从而致使“部分征收”是否还是一种独立的征收类型也不明朗。
(三)不动产征收、动产征收、智慧财产权征收及其他财产权益征收
这是根据征收标的所作的分类。统观美国的判例与学说可以发现,在美国的征收法理中,不论被侵害的对象为何种类型的权益,都可能构成征收。换言之,财产权的类型、客体形态与是否应纳入征收范围加以讨论以及是否构成征收问题并不相关。所以,按照我们大陆法系的习惯思维,我们可以把美国法上的征收类型化为不动产征收、动产征收、知识产权征收以及其他财产权益的征收等各种类型。不论是从传统还是现代来看,不动产征收都是最重要的征收类型,如土地征收、房产征收以及其他构筑物的征收等。动产征收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是常见的,如上文提及的Andrus v.Allard一案,(14)就属于对老鹰羽毛制品此种动产处分权的征收。美国法院较少审理智慧财产权征收案件,但智慧财产权毫无疑问也属于美国宪法征收条款所保护的财产权范围,因此,对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商业秘密等智慧财产权的剥夺都完全可能构成征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Ruckelshaus v.Monsanto Co.案中,(15)就政府是否能够以及何时能够对智慧财产施以实质干预而不抵触宪法上的征收条款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法院在该案判决中指出:无形财产权(intangible property),如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属征收条款意义下的私有财产权。就本案而言,环境保护局(EPA)对商业秘密的披露,如果发生于法律明确予以保护而不许披露的期间,那么很显然会构成征收;但由于本案不存在免于披露的明确保护,因此Monsanto不存在基于投资的合理预期(reasonable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所以也就不构成征收。至于其他财产权益的征收,套用大陆法系的术语来讲,主要是指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的征收以及合同权益的征收。如在Armstrong v.United States案中,(16)就涉及对法定优先权的征收;在United States v.Willow River Power Co.案中,(17)就涉及对水权的征收;在Almota Farmers Elevator & Whse.Co.v.U.S.案中,(18)就涉及对承租权的征收。
综上所述,在美国征收法上,凡是对宪法财产权条款意义上的任何财产权益的剥夺,都可构成征收。
(四)行政征收、立法征收和司法征收
这是根据征收权启动的不同主体所作的分类。在美国法上,行政征收即正式征收,是指由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依法启动正式征收程序而发动的征收;立法征收即管制性征收,因为所有的管制性征收都是由议会或政府的管制性法令造成的;但关于司法征收,在美国尚存较大争议。
法院通过做出新的判决,就先前对普通法、制定法或宪法作出的先例解释予以撤销或变更,从而致使财产权人因法律地位的改变而发生损失,由此而导致的征收问题即为司法征收(judicial takings)。在美国,不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一直坚持认为,司法判决不可能构成司法征收(亦即不能被作为管制性征收而予以挑战)。(19)在学理上,拒绝认可司法征收的理由是:法院既不像立法者也不像行政主体,其本身并不拥有对私有财产权予以征收的权力。因此,适用于管制性征收的规则并不能适用于法院。我们不能说,当法院必须通过启动征收权而非警察权来取得私人财产的情况下,其改变法律的目的就在于规避自己应负的补偿义务。法院无权取得财产,它当然也就不可能拥有用以补偿司法征收的资金。最重要的一点理由在于,法院不可能将自己的行为定性为征收,因为这将把它们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从而妨碍他们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解决纷争。所以,基于这些理由,法院始终认为,当它们对财产法重新作出解释时,它们从来没有否定任何人的财产权,它们只是在简单地澄清:那样的财产权在事实上是从来不存在的。(20)正如有判例指出的:“在任何的普通法规则中,一个人既不拥有财产权,亦不拥有既得利益”;(21)“在任何的法律规则中,没有人拥有既得利益可以使其有权声称为了其利益法律必须保持不变”。(22)
虽然法院不会自找麻烦地将自己的判决认定为征收,但不能说司法征收在美国征收法上完全不可能存在。实际上,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完全有可能将州法院的判决认定为构成司法征收。因为这样做,根本不会影响到联邦法院的司法权威和自由裁量权。这种可能性在1994年的Stevens v.City of Cannon Beach案的不同意见书中有所显现。(23)在该反对意见书中,Scalia和O'Connor两位大法官表明了其观点,认为应对一个重新分配财产权的州法院判决,就其违反征收条款的可能性做出评估。Scalia大法官指出:“该案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涉及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征收问题。……其重大性一方面在于,它涉及一个问题判决的合宪性问题;另一方面在于,它对土地的攫取(landgrab)将漫延整个俄勒岗海岸。……不论是立法性法令(legisla tive fiat)还是司法性决定(judicial decree),都不能授权州政府在无补偿的情况下将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转变为公共财产(public property)。”Scalia大法官的上述反对意见至少表明一点,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意于对司法的再解释(judicial reinterpretation)不能构成征收的传统观点予以重新考虑。
在Munn v.Illinois案中,(24)法院判决在指出“在任何的普通法规则中,一个人既不拥有财产权,亦不拥有既得利益”之后,同时又指出:“基于普通法规则而已经构建的财产权,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是不能被剥夺的。”这一判决实际上已经表明,虽然普通法不能直接授予个人以财产权和财产利益,但个人基于对普通法规则的信赖而构建的私有财产权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出一个推论:若一项司法判决所采取的法律规则已为权利人所信赖,权利人亦基于此规则而形成了某种私有财产权,而另一个司法判决却改变了该规则,致使权利人的财产权丧失或遭受重大限制,则后一个判决就引发了一个征收问题。举例来说,假设州普通法授予滨岸权利人(riparian owner)一项权利,基于该权利其有权阻止他人进入平均水位线以上的沙滩,但此后的一项州普通法判决却改变了此项规则,宣告滨岸权利人无权阻止他人进入植被线以内的沙滩。这后一判决就剥夺了滨岸权利人的一项独立财产权(discrete asset),即阻止他人进入由平均水位线至植被线以内沙滩的权利。这就会引发一个司法征收的问题,在此,并非因为前一项普通法规则本身就是一项私有财产权,而是因为前一项普通法规则被用来构建了一项私有财产权,而新的法律规则却剥夺了该项既成的私有财产权。(25)
综上所述,在美国法上,虽然对司法征收能否构成一种独立类型的征收尚存争议,并且亦无确定的判例以资证明,但其在学理上的证成还是完全可能的,并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亦为其开放了可能性空间。
二、德国征收法理中的征收类型
虽然德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征收法理的形成却主要依赖于联邦普通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而这两家法院的意见分歧与交错,使整个征收法的类型体系显得有些不确定和零乱。本文于此主要根据德国权威行政法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的分类,把德国的征收类型划分为典型征收、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准征收侵害和征收性侵害四类。此外,由于德国法上的立法征收不同于美国法上的立法征收,所以还将顺便提及行政征收与立法征收的对应分类。
(一)典型征收
在德国,典型征收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传统征收(又称古典征收)阶段。所谓传统征收,是指根据依法作成的行政行为将不动产财产转让给服务于公共福祉的企业,但予以全面补偿。传统征收的实质要素包括:①作为征收客体的地产;②作为法律过程,将财产交付新的法律主体;③作为法律形式的行政行为;④作为征收目的,服务于公共福祉企业的现实需要。第二阶段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一般称为“扩大的征收概念”。1919年的魏玛帝国宪法虽然仿照传统征收概念于第153条第2款规定了征收条款,但帝国法院和权威理论却对其作了扩大解释。经扩大了的征收概念包括以下特征:①征收客体:根据传统征收概念,只有地产和动产;而根据扩大的征收概念,所有的具有财产价值的个人权利都可以征收,如债权、结社权、著作权。②征收的法律形式:根据传统征收,只能依法通过行政行为(行政征收);而根据扩大的征收,还可通过法律(立法征收)。③征收的法律过程:根据传统征收,是向国家或其他法律主体交付财产;而根据扩大的征收,尚包括单纯的财产限制,主要是使用限制,例如禁止在文物保护区内对登记的建筑物进行改建。④征收目的:根据传统征收,只能出于特定的、具体的事业;而根据扩大的征收,也包括一般的公共利益。(26)综合以上四个特征,扩大的征收概念可以表述为:为公共利益目的,经由行政行为或立法对具财产价值的私人权利予以限制或剥夺,并给予全面补偿。第三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的征收。根据该规定,征收须具备以下要件:①必须是为了公共福祉而征收;②必须有充分的法律基础;③“比例原则”必须被尊重;④必须予以“公正补偿”。与魏玛帝国宪法规定的征收相比,基本法规定增加了一个“唇齿条款”(Junktimklausel,又译“一揽子条款”或“联结条款”)。依此条款,财产征收,惟有依据法律,而该法律并“同时”有规定征收补偿的“额度”及“种类”时,方可准许之。这种“无补偿即无征收”条款,促使立法者“事先”就必须知道,其制定的征收法之合宪与否完全系乎有无补偿的规定。(27)
(二)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
在德国法上,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其根据是《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2句的法定征收规则。财产所有人原则上应当接受此种从法律或者其执行中产生的限制,但这并非没有例外。以宪法允许的方式对财产作一般限制的法律规则在特殊的例外情况下可能导致特别负担,从比例原则的角度来看不再具有正当性和可预期性。在这种例外情况下,这些额外负担可以通过财产公平补偿予以消除,并且据此避免违反比例原则和财产保障原则。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规则创立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81年7月14日的义务示范判决,(28)旨在补充和完善联邦宪法法院先前的征收判决。《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的应予补偿的征收限于通过具有特定目的的主权性法律行为,剥夺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而同条第1款第2句规定的是无偿的内容及范围限制,而在这二者之间肯定还应存在其他的选择。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恰好就提供了这一选择:其一方面实现了产生于公共利益的财产约束,另一方面平衡了从中产生的特别负担。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主要适用于主权性经营设施或者机构造成的不合乎比例的强烈公害,以及文物保护和自然保护领域里不合乎比例的负担。(29)
(三)准征收侵害
准征收侵害又称为“类似征收侵害”(Der enteignungsgleiche Eingriff),(30)其发展之初系以《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的征收制度为依据而形成,故名其曰“准征收”。征收侵害以侵害合法为前提,但对于违法侵害是否构成征收的问题尚未解决。对于过错违法侵害行为,关系人根据职务责任法可以取得损害赔偿;而关于无过错违法侵害行为的赔偿责任,德国法上却没有法律根据。德国联邦法院最终通过类推的方式填补了这一漏洞:如果对合法财产侵害应当补偿,那么对违法财产侵害同样应当予以补偿,即准征收侵害应当予以补偿。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最初定义,准征收侵害是对财产的违法侵害,“就其适法性而言,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效果方面都可以视为征收,实际上具有给关系人造成特别牺牲的效果”。在这一最初定义中,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将“违法性”与“特别牺牲”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而这一等同处理表明,准征收侵害的法律概念已经发展成国家对其机关违法行为的直接的、无过错的赔偿责任,最起码表明过错在征收补偿法上并不重要。构成准征收侵害的“侵害行为”,既可能是法律行为,也可能是事实行为;既可能是作为,也可能是不作为。根据德国判例,构成准征收侵害的情形众多,例如:就事实行为而言,违法计划或者执行的道路建设工程对经营的侵害,公路沿线工程对建筑物安定性的破坏,冲出道路的联邦军队的坦克对旅店造成的损害,洪水防治设施建设对水的侵害,地方净化设施的气味公害,实际上的建设禁止即建设法和土地法容许的施工行为客观上造成的不便;就法律行为而言,邻居不动产的建设许可造成的不动产损害,根据《德国建设法》第36条规定因乡镇拒绝同意造成建设计划的推迟。(31)
(四)征收性侵害
征收性侵害,又称“具有征收效果的侵害”(enteignender Eingriff)。此一概念的意旨略谓:人民的财产权因合法行政行为的附随效果(Nebenfolgen)而受有损失者,如该附随效果具有特别的持续影响,逾越公益牺牲的界限者,国家应予补偿。例如,因道路的修筑而阻碍周边土地的对外交通,从而使道路周边商家的营业量减少。依德国联邦普通法院的判决,类此影响原则上应纯属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范畴,无予补偿的必要。惟就附随效果的种类、范围及强度以观,如财产权人所受的影响,已达特别牺牲的程度者,即得依公用征收的原则请求补偿。(32)征收性侵害与准征收侵害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前者情形,主权性措施是合法的;而在后者情形,主权性措施是违法的。举例来讲:原告的个人商店因街道建筑工程以及与街道建筑工程有关的交通限制,遭到重大的销货倒退,原告主张建筑工程一再拖延,而且可能还需更多的时间,他要求损失补偿,其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对此的回答是:如果工程的中止与延迟是可以避免的,则营业经营受到交通限制的损害便是违法的,于此情形,在职务执行人有责时,可以依准征收侵害要求补偿;反之,如果建筑工程合乎规定地予以计划与执行,而该工程的中止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原告例外地被置于征收性侵害的要件下,其所受的营业损失逾越了特别牺牲的界限而应受到补偿。(33)
(五)立法征收与行政征收
《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规定的征收可以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进行,因此,行政征收或者立法征收都是可以的。(34)但在二者中,前者为一般情形,后者只构成一种少数例外。这是因为,征收作为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的剥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职能,立法机关——从分权原则和法治国家原则的角度来看——必须留给行政机关。(35)可见,德国法上的立法征收作为一种例外,与美国法上的立法征收(管制性征收)存在质的差别:前者只是行政征收的一种补充,而后者几乎成为了征收领域的常态;前者专以征收为目的而制定相应的征收法律,而后者非以征收为目的却造成了相应的征收效果。
三、征收的概念及我国的立法选择
我国学者梁慧星主持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48条规定了“征收”条款。在该条的“说明”中,该建议稿对征收作了一个定义性界定,全文如下:“所谓征收,指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取得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在中国,征收的对象常常包括所有权和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物权(如土地使用权)。征收的特征在于,征收的主体一方是政府,而且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从自然人和法人手中取得物权,自然人和法人必须服从。故征收是强制剥夺自然人和法人物权的行为。”(36)这一征收概念,对我国学说及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通说地位。但我们认为,这一征收概念存在诸多问题,缺乏比较法上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关于征收的方式。根据上述定义,征收是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所为的行政行为;(37)换言之,征收即“行政征收”,除此之外不再存在其他的征收方式。但由上文述及的美、德立法案例可以看出,除行政征收这一典型的征收方式外,两个国家都共同地认可“立法征收”这一征收方式。虽然美、德两国的“立法征收”在概念内涵上存在差别,但二者的共性都在于通过“立法行为”而非行政行为实施征收。实际上,美、德两国的立法征收,分别代表了立法征收存在的两种不同样态:前者是立法者所为的一种隐蔽性征收,经由财产权人的“反向征收”诉讼而使之浮出水面;而后者是立法者所为的一种公开性征收,也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立法征收,无需司法的介入即直接成立。如果将征收单纯地界定为行政征收,而将立法征收排除在外,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立法征收行为排除在了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外,从而造成规范体系上的漏洞,致使财产权人的私权陷入无从救济的境地。如果说德国式的立法征收在我国并不普遍,甚至是鲜见的,或者迄今尚未出现,那么美国式的立法征收在我国却是极其普遍的。美国法上的立法征收(管制性征收),主要存在于如战时立法、行业保护立法、都市计划及土地分区使用管制立法、古迹保护立法、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土地政策立法及促进重大竞争利益的立法等诸多方面;而在这些方面,在我国同样属于立法性干预私权和社会的领域。如果说在美国可以成立征收,为什么在我国就不能成立呢?举例来说,我国的枪支管理法规定未经许可不许持有枪支,对于未经许可而持有的枪支应予收缴;那么对于先前合法持有的枪支,在上缴时是否须予征收补偿呢?再如,对于明清时期的民居,因时过境迁而被划定为某个级别的文物,从而未经允许不得擅自修缮或者翻建,那么对此种禁止而造成的损害是否应予征收补偿呢?又如,对于个人承包的“四荒”土地经整治垦殖后植树造林,成林后因立法性行为而被列入禁止采伐之列,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是否应予征收补偿呢?还如,对位于城区的存在潜在危险的化工企业,政府不是通过搬迁企业的行为来避险,而是通过地方规划立法,将企业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列为禁止开发土地,那么对于周边土地价值增值的损失是否应予征收补偿呢?凡此种种,我们认为,其回答都应当是肯定的。此等立法行为,不论是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还是地方政府的规范性行政行为(即抽象行政行为),因我国既不存在立法违宪审查制度,亦不存在抽象行政行为可诉制度,因而导致当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为公益而遭受“特别牺牲”时,都无从救济。所以,我们认为,在设计我国的征收概念及选择相应的征收类型时,不能将“立法征收”排除在外,而应明确地在征收立法中予以提出,并给予人民以相应的救济手段。
其二,关于征收的对象。上述定义,先是将其界定为“财产所有权”,进而又扩及至“他物权”,并最终定位于“物权”,这是对征收对象不恰当的限缩。我国甚至还有学者做出了比上述定义更为狭隘的界定,认为征收的对象(标的)仅限于“不动产”,“动产”不具有“征收能力”;“同时,征收仅涉及征收标的物所有权变动”(38)这种对征收对象不恰当的限缩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对于所有权之外的、不动产之外的、物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的过度限制或者剥夺,应当如何给予救济呢?上述观点显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宪法上的财产权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所有权”,亦不等同于民法上的“物权”,而是扩及至“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甚至在某些情形下尚包括具财产价值的“公法上地位”;(39)在财产权形态上,不仅包括不动产,还包括动产;不仅包括所有权,还包括他物权;不仅包括有体财产,还包括知识产权等无体财产;不仅包括财产权,甚至还可扩及至“非财产权”。(40)因此,将征收的对象限缩为“物权”等,会不恰当地将大量应予征收法保护的私有财产权排斥在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征收类型的选择上,除“非财产权征收”尚有待进一步论证外,不动产征收、动产征收、所有权征收、他物权征收、无体财产权征收以及债权征收等,都应当是恰当的征收类型。
综上所述,我国近乎处于通说地位的征收概念界定是有待修正的。我们认为,所谓征收,是指国家通过主权性行为——包括立法行为、行政行为(41)——对人民拥有的一切具财产价值的权利作出的过度限制或者剥夺,从而应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美国法上的正式征收与反向征收(管制性征收)、全部征收与部分征收、各种财产权益征收、立法征收与行政征收,德国法上的典型征收、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准征收侵害、征收性侵害、立法征收与行政征收等,都应当被纳入征收立法的选择之中。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对于征收概念的界定,应持一种广义征收的观念,并在征收类型的选择上亦采较为宽松的标准。之所以这样考虑,总体的理由在于:我国目前私权保障的观念仍非常淡薄,面对来自公权的侵害,私权不堪一击;而造成此种私权保障地位至为脆弱的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私权保障体系,从而造成诸多的制度体系漏洞,使得私权面对公权侵害时无从救济。我国未来征收立法的任务与目标,应致力于构建一道制度的“防火墙”来保障私权,而非瓦解这道“防火墙”来弱化私权。
注释:
①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7th edition,West Group 1999,p.287。
②参见蔡怀卿:“美国之土地使用法管制以及其宪法许可界限”,《玄奘法律学报》2004年第2期。
③See Gregory S. Alexander,The Global Debate over Constitutional Property:Lessons for American Takings Jurisprudenc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69.
④Margaret Jane Radin,The Liberal Conception of Property:Cross Currents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akings,88 Colum.L.Rev.(1988),p.1676.
⑤See 216 F.3d 764,774 (9tn Cir.2000).
⑥对此三种分割,美国学者Henry A.Span作了系统阐述。参见Henry A.Span Public Shoice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Utility of The Takings Clause,40 Idaho L.Rev.11 (2003),pp.49~53。
⑦Richard A.Epstein,Takings: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57.
⑧Ibid,pp.57~106.
⑨See 444 U.S.51 (1979).
⑩See 481 U.S.704 (1987).
(11)See 482 U.S.304 (1987).
(12)See 535 U.S.302 (2002).
(13)See Penn Central Transp.Co.v.New York City 438 U.S.104 (1978).
(14)See 444 U.S.51 (1979).
(15)See 467 U.S.986 (1984).
(16)See 364 U.S.40,49 (1960).
(17)See 324 U.S.499 (1945).
(18)See 409 U.S.470 (1973).
(19)See Barton H.Thompson,Jr.,Judicial Takings,76 Va.L.Rev.1449,1463~72 (1990).
(20)See David A.Dana,Thomas W.Merrill,Property:Takings,Foundation Press 2002,p.230.
(21)Munn v.Illinois,94 U.S.113,134 (1877).
(22)New York Central R.R.v.White,243 U.S.188,198 (1916).
(23)See 510 U.S.1207 (1994).
(24)See 94 U.S.113,134 (1877).
(25)参见前注(20),David A.Dana书,第233页。
(26)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4~665页。
(27)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426页。
(28)参见BVerfGE,第58卷,第137页。详情参见前注(2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书,第675页。
(29)同上,第701~705页。
(30)参见杨明勋:《德国类似征收侵害制度之研究》,台湾中兴大学法律研究所1993年硕士论文,第7页,注二。
(31)参见前注(2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书,第669、670、707~708页。
(32)参见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9页。
(33)参见王服清:《德国“具有征收效力之侵犯”制度之研究》,中正大学法研所1995年硕士论文,第26页。
(34)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4~405页。
(35)参见前注(2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书,第689页,注44。
(36)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37)参见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38)前注(37),江平主编书,第63页。
(39)前注(27),陈新民书,第409~410页。
(40)沈开举:《征收、征用与补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48页。
(41)关于美国法上的“司法征收”,由于在美国法上本身尚未被公认为一种独立的征收类型,因而在此暂不将其包含于征收的定义中。但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主权性行为,因司法行为而构成征收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是否接受“司法征收”作为一种征收的类型,是一个观念问题,而非事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