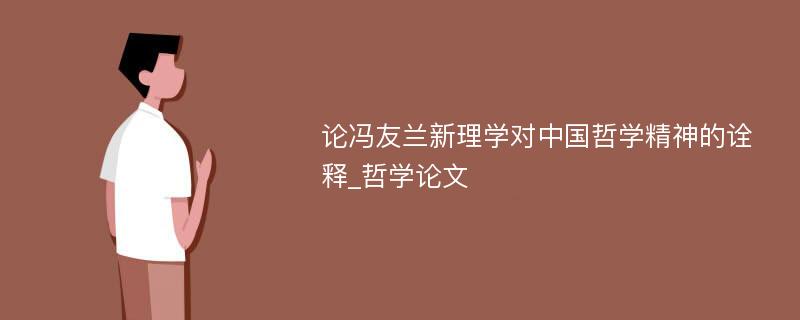
简论冯友兰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冯友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新理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概括和提升
有方家认为,冯友兰先生一生的哲学历程,是由论入史,由史而论,又由论到史。三、四十年代,冯先生的“贞元之际所著书”所建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作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显示着其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贞元六书”中的《新原道》,在其以往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按照他自己确定的标准,又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哲学。这个标准既是他以往考察中国哲学史的总结和概括,又是他在《新原道》中重新评论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一个尺度和准绳。这个标准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先生从《中庸》里借来这一语,并赋予了其新的意义,也就是于日用常行中追求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从而成为圣人。冯认为,中国哲学从先秦至明清,求解决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因而它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的传统、思想的主流、中国哲学的精神。只是在其发展中,有的哲学偏于“极高明”,有的偏于“道中庸”。只有先秦儒学和程朱理学不同程度地达到了二者的结合,故而堪可以称之为代表中国哲学精神的正统或道统。这是冯友兰新理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总的基本的看法。
非常明白,冯先生是以“境界”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在冯先生确立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裁断中国传统哲学的标准中,包括着三个内容:第一是“极高明”;第二是“道中庸”;第三是二者的统一。“极高明”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圣人的境界,这是一个人修养的最高精神成就,谓之“内圣”。“道中庸”指的是人的行为,即人的平常的生活和实践,这是一个人的社会功用和作为,称之为“外王”。这二者的统一表明,达到和实现“极高明”的精神境界,要通过“担水砍柴”、“事父事君”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作为来完成,“道中庸”的“外王”之功和作为所体现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就是实现最高的精神境界。或者说,“有这种境界底人的生活,是最理想主义底,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底。它是最实用底,但是并不肤浅。”(注:《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7 页。)一个人应该是积极入世的,但于积极入世中追求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的核心和灵魂,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即“极高明”的境界。冯友兰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注:《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6页。) 以这种思想来衡论中国传统哲学,那么就首先的、主要的和根本的看其是否讲了“高明”或讲到了“极高明”。这样则区分出“极高明”的、“高明”的和不“高明”的哲学。“高明”的和“极高明”的哲学,属于理想主义的或最理想主义的。从这一立场来说,在冯友兰看来,孔、孟、老、庄、《易》、《庸》、玄学、禅宗、道学,属于此列。而孔、孟、老、庄、玄学、禅宗则讲到了或一定程度上讲到了“极高明”。从这一方面说,冯友兰新理学对早期儒家,特别是孟子,老庄、玄学和禅宗,肯定甚多,批评甚少。
不仅如此,冯友兰进而还以境界和境界的实现的统一来论中国传统哲学。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和主要精神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但不是说只要是“高明”的或讲到了“极高明”的哲学,就可以和能够代表中国哲学的传统了,还要看这种“高明”或“极高明”的境界是如何实现的,即看如何“求”这种境界,也即看能否“道中庸”。如果是“极高明而不道中庸”,则是一偏,即偏于“极高明”。按照与之相对的另一派哲学的观点看,有这种主张的哲学偏于太理想主义,是无实用的,是消极的,是所谓“沦于空寂”的。反之如果是“道中庸而不极高明”,则是又一偏,即偏于“道中庸”。按照前一种哲学的观点,这种哲学是太现实主义的,是肤浅的。冯友兰认为,这种哲学虽然注重人伦日用,讲政治说道德,但不讲或讲不到最高的境界,“不真正值得称为哲学”。(注:《三松堂全集》第五卷 ,第6页。)从学理上说,这两种哲学都是偏执的,都具有内与外、本与末、精与粗、玄远与俗务、出世与入世、静与动、体与用的对立,也即冯友兰所概括的“高明与中庸”的对立。冯友兰认为,在古代中国哲学中,有这种对立。有这种对立,那么,只是“道中庸”者,不真正值得称为哲学;只是“极高明”者,虽境界极高但仍可批评,也应当批评。这两种哲学都不符合“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只有“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即主张于人伦日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求最高境界的哲学,才真正称得起中国哲学主要的传统,标志着中国哲学的精神。
在冯友兰看来,从实际的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看,没有哪一个阶段或时期、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学,是完全符合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的。但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又是一个主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这表明,冯友兰新理学确立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标准,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实际的历史发展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它以实际的中国传统哲学为依据,但又高于实际的中国传统哲学,体现了对于实际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精神,以这种精神为精神,来反观和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则又体现了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继承与维护。这也就是说,按照冯友兰新理学的观点,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超越精神,中国传统哲学整体上是一种超越的哲学,而冯友兰新理学所提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标准,又是对中国传统的超越哲学的超越,以及对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还表明,冯友兰新理学确立的这一标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标准,自我标准,而非外在标准;是站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立场以较高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如是的结果,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则既不会完全否定,一笔抹煞,也不会不分清浊高下,一概肯定或褒扬,一定是肯定其所当肯定,否定其所当否定,或者说存扬其所当存扬,去弃其所当去弃。只是这种评定所依据的标准究竟确当与否,则另当别论。而就冯友兰新理学本身来讲,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必有其对中国传统哲学“接着讲”的关系,而不会只去“照着讲”。这种“接着讲”,实际上蕴含着对中国传统哲学同情的了解,理性的评判,超越的发展。因此,作为后来者,对于冯先生所提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哲学标准,进一步加以反思或琢磨,对于较好地认识冯氏新理学“接着讲”的精神和方向,对于正确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审察维度,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意义了。
二 新理学所阐扬的中国哲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把几千年来的中国哲学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言以蔽之,充分显示出冯先生的理论睿智和高度的思想省察力,以及深邃的总体把握。这是一个哲学史家和一个哲学家融而为一的集中体现,或者说是一个哲学史家到哲学家,又由一个哲学家对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反思所得。其价值和意义窃以为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这一精神凸显了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实践理性的价值取向和形上追求。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于人,注重于人的本质、地位、价值、理想、境界、伦理等,偏执于人自身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形上关切,实践理性大大超过理论理性。这确是中国哲学的突出特点,甚至于从一种意义上说是一可贵的传统。研究哲学或哲学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发掘其“珍贵品”,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即阐发其有永久价值的东西,以作为未来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继续发展的养料。这种“珍贵品”或“有永久价值的东西”会因哲学家的所见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欲发掘“珍贵品”或阐发“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这一点是共同的。基于这种思想,冯友兰新理学认为,哲学的作用主要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不能使人增加实际的知识和才能,但可以使人得到最高的精神境界。通过哲学的反思和领悟,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正是中国哲学之所长,也是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和精神。《新原道》指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乃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注:《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 6页。)这种境界把理想与现实、高明与中庸、出世与入世,以及内与外、本与末、精与粗、动与静等对立面都统一了起来,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最高的哲学智慧,也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中国传统哲学从孔子到现代的进展,尽管各家各派都不免陷于一偏,或者不能完全符合“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但把各家各派作整体观之,包括历史的总体和哲学理论的总体,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作了辩证统一的解决。这是中国哲学的贡献。
第二,“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中国哲学精神,具有贡献于未来世界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冯先生不仅着眼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主流和精神,而且着眼于这种传统、主流和精神的世界意义和未来发展。他曾说:“随着未来的科学的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注:《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303页。)他在1948 年发表的《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一文中,阐述中国哲学对于未来世界哲学可以有何贡献时,又着重讲了两点:“一点是哲学使用的方法,一点是由哲学达到的理想人生。”(注:《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 512页。)冯先生的这一观点,可以说见地惊绝,意义深广,道出了他阐发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宽广而深远的理论视野。中国哲学的历史,曾有儒道互补,儒、释、道的融合;冯友兰坚信,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也必定是或至少说是中西互补、中西融合。互补与融合,就是各以其哲学理论思维的所长,补彼哲学理论思维的所短。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和精神,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超越精神,超世哲学,在冯友兰看来,这与未来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目标方向非常一致,换言之,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传统,代表了未来哲学发展的方向。而西方哲学注重于理论理性、工具理性的传统和精神,是以外在的形下追求为旨归的,其入世有余却未必能达到理想人生和最高的境界,对于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有贡献但也有缺憾。立足于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这一视角,对于中西哲学取互相补充、互相融合之说,显然大大超过了和高出于以“体用”论中西文化的立场。从哲学所使用的方法来说,冯友兰认为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两种。正的方法是逻辑分析的方法;负的方法是“烘云托月”的表显方法。冯友兰认为,“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注:《三松堂全集》第六卷,第 305页。)而就中西哲学的实际发展看,“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因此,“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注:《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 305页。)就是说,在哲学使用的方法上,中西哲学也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并且应该亦能够这样的。
第三,冯友兰新理学阐释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旨在强调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一精神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利益与道德、能力与修养、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和谐等许多方面愈益矛盾乃至冲突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该是统一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存在着正确认识和处理义和利、精神和物质、理想和现实等许多关系,需要将各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人的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同样包括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文明、修养等内在精神的提高和进步。现实社会生活中,对于那种只执着于经济的发展,仅限于追求物质的文明,而忽视或者不要精神文明建设,将两个文明建设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思想和行为,不是应该需要特别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把精神文明建设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吗?而对于救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腐化堕落等思想和行为,加强法律首先必要,而强调提高精神境界也同等重要,这二者相辅为用,并行不悖。法律惩治于人的行为之后,思想道德教育和感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往往作用于人的行为之前。当然,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道德,并不脱离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是以其为基础。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辩证统一。冯友兰新理学所阐扬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与我们今天的这种思路非常一致。尽管冯氏所阐明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高人生境界的真正内涵与今之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迥然有别,但其抽象的意义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甚至于说,冯友兰所认为的在中国文化中,由哲学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主张不脱离人的日常生活达到超道德的最高精神境界,这对现代社会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注:见陈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一文。《冯友兰研究》(第一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6月出版,第288页。)这不仅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伊始和继续深化的条件下是如此,广而言之,在那种注重于形下追求,甚至于物欲横流,精神颓废的社会中,冯友兰阐释的上述中国哲学精神,其意义更远远跨越了国家民族的界线,而具有了世界的性质。
三 新理学所阐扬的中国哲学精神的局限和偏执
“贞元六书”所建立的新理学体系,一方面存在着如冯先生本人所指出的“总纲”与“分论”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确实包含了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巨大的理论张力。于此点已有学者指出并作了精到的分析,这里姑且不论。仅就《新原道》所阐释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而言,似仍可作进一步的检讨。
首先,把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凝炼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确当但失之偏狭。确当,且包括其价值和意义,本文已述。偏狭,根据有二。其一,因为冯所概括的这一中国哲学精神的实质是求最高的境界,而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除了这一特质外,显然还远不止于此。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名、兵、农等诸子百家,其理论旨趣的差异悬殊,自不待言。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墨学中绝,儒术一尊,其他式微,但中国哲学思想之流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主流与支流同汇,传统与主要的传统共构而成,也是无疑的。就中国哲学专注于人来说,人之义与利、形与神、心与性、理与欲、群与己、人与天、力与命、古与今、循与革、礼与法、知与行、参验与是非,等等问题和关系的探讨,用“求最高的境界”恐怕是不能概括无遗的。其二,冯先生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是特定的,视域也大有限制。显而易见,冯先生衡论中国哲学的理论视角是人生哲学,进一步说是人的精神境界。从这一特定的视角来观中国哲学,冯先生的结论是正确恰当而深刻的。并且将其置于世界哲学的广阔理论空间,也较易发现中国哲学之异及其独特贡献。问题是也正因为这一特定的理论视角,使冯先生有意无意地限制自己的视域,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采摭裁剪百家,凡是阐述这一问题的取,否则就舍。50年代冯先生曾回顾说:《新原道》“把我在《中国哲学史》里所真正同情的一些哲学派别提出来作为‘主流’,其余都是‘断港绝河’,一概置之不理。”(注:《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第114页。)这样一来, 中国哲学精神也就真正成为了冯先生所讲之中国哲学的精神,《新原道》也真正成为了冯先生所“原”之“道”。
其次,新理学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冯先生亦主张“内圣外王”统一的观念,但是,其理论旨趣明显地偏重于强调“极高明”的“内圣”之德,而把“道中庸”的“外王”之功只是作为实现这一人生理想的途径、手段和方法,置于了次要的地位。就是说,求最高的境界是人生的目的;日常生活,“担水砍柴”、“事父事君”,是途径,表明了如何求最高的人生境界。这一观念表明,求最高的人生境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比起那种只是出世间的或者入世间的哲学来,超世间的中国哲学确有更大的合理性。然而,人的精神境界与人的生活和实践,作为内在与外在、“高明”与“中庸”、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多重的辩证的关系,仅仅以主从言之是不是过于单一了呢?甚至如果改变一下看问题的立场,二者的主从关系或许是又可以倒置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