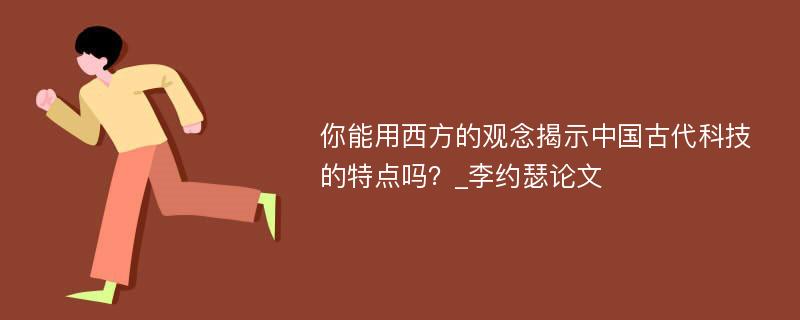
用西方理念能揭示中国古代科技的特质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特质论文,理念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是世界科技史上第一部由一个人完成的体系一贯的中国科技史的著作。它对比较科技史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人来说,它发掘了很多科技史料,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先祖并不缺乏创造性,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有过巨大贡献。同时,对中国搞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人来说,由于书中引证了许多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因而可从中广泛了解西方同行的观点。对西方人来说,阅读此书可较为系统地了解中国科技史,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自我中心主义和对中国的一些偏颇狭隘的认识。因此,该书虽至今尚未全部出版,李约瑟博士也已经仙逝,但该书仍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但是,李约瑟毕竞是一个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外国人,西方的观念不可避免地积淀于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用西方人的观念框架和习惯性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
1 西方观念
指导李约瑟梳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观念,仅仅只关注了事物的外在方面。他是从科学技术的外史,也即科技社会学的角度,与西方的情况相对照着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这具体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其一,宗教—科学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核心框架:科学源于宗教,又受宗教的束缚,因此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又必然要从宗教中独立出来。李约瑟认为:“道家极端独特而又有趣地揉合了哲学与宗教,以及原始的科学与魔术。”[1]道家(道教)虽然是“世界上唯一不强烈反对科学的神秘主义”[2],但它后来也同样成为科学发展的阻碍:”道家由不可知论的自然主义,一变而为神秘的宗教信仰,进而成为三位一体的有神论。其准科学的实验主义,一变而为占卜算命和流行乡间的法术。”[3]
但这个观念框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它对西方中世纪以后是大体适用的,但却不足以解释古希腊、古罗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产生于此后等事实。实际上,三大宗教创立之后,它们关注的都只是社会问题。文艺复兴前后宗教干涉、迫害科学,完全是出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需要,如保持政教合一、把持大学讲坛等等。而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对宗教教义作出另一种解释。
这个观念模式对中国则完全不适用。从《老子》、(庄子》这些道家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宗教和魔术的影子。至于道教,东汉晚期才正式形成。它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等道教组织,有一定的教规教仪和崇拜神。它的核心观念是“太平将至”。正如汤用彤所说:“《太平经》屡言太平气将至,大德之君将出,神人因以下降。故其所陈多治国之道。”[4]太平道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5]要使天下太平,当然要尊奉神,如“大神人”、“真人”,但不必凭藉巫术。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跪拜首过”,“以善道教化天下。”[6]他们的目标是使天下太平,所以也不追求个人长生成仙。
关于炼丹、求仙,《汉书·刘向传》说,淮南主刘安已从事过炼金活动。后来刘向如法炮制,没有成功。求仙在汉武帝以后也归于沉寂。张敞劝汉宣帝“斥远方土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7]”。谷永说:神仙之事都是左道惑众,“欺罔世主[8]”。根据陈国符的考证,《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都是西汉末年的著作,它们应是方士们的作品。直到东汉末年的《周易参同契》,尚未发现它们和当时勃兴的道教有什么直接联系。葛洪也批评炼金(丹)求仙活动的方士,说他们“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9]不过在葛洪时代,道教与炼金术已经开始结合。但道士们炼金丹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长生。一旦目的达不到,他们就会把炼丹术抛齐。魏伯阳、葛洪还多少相信炼丹,托名阴长生的《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则说:“铅贡自在人身,不假外求。”[10]唐朝有五六个皇帝死于丹药,唐朝末年以后出现的丹经,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反对服食金丹。唐末宋初的“钟吕金丹派”、宋金时代道教的南北二宗,也不讲丹鼎。符箓派自不必说,金元时代的太一教和真大道教也不讲黄白之术。炼丹术被道教抛弃了。
战国时代,安期生、石生、卢生、侯生、徐市、韩终、聚谷诸人,已经掌握了服食行气、房中诸术,形成了以方术谋生的职业集团,活跃于上层社会。用自我锻炼的手段去保持身体健康,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卓有成效。《庄子·刻意》、《荀子·天论》皆有论述。《黄帝内经》讲得更加详细。《淮南子》中也记载有导引行气、长生久视之术。这些都在道教产生之前。道教初期也不注重这一点。把导引、胎息、按摩、扣齿、咽液、吐纳、服气、内视、房中术等等纳入道教是东汉末期才开始的。到唐代,这些服气术才差不多与炼丹术一样兴盛。但是,柳宗元在(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中反对,著名道士吴筠也反对。[11]钟吕金丹派则不仅反对炼丹,也反对服气,而主张炼内丹。南宗 道教创始人张伯端则内丹也不甚注重。他说:“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体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12]白玉蟾也说:“如所问道,则示之以心;如所问禅,亦示之以心;如所问金丹大药,则又示之以心。愚深知一切唯心也。”[13]全真教首领王重阳他说:“要行行,如卧卧,只把心头一点须猜破。”[14]这样,心肾交媾的内丹事实上也被道教抛弃了。因为它们只是“术”,而道士追求的是“大道”,是超自然,超世俗,超现实的高级精神境界。
虽然道教徒对炼丹、中医药等某些科技领域确实有很大贡献,但炼丹、服气等等这些方术却从来就不是道教的本质和主流。而天文、历法、算术、医药、农学、纺织、印染等与道家、道教无直接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也就谈不上科学技术依附于宗教或原始宗教中孕育了科学技术。既然这样,类似于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的情况,在中国当然就不会出现。事实上,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道教的关系并不大。它们是因应人们的需要和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二,科学技术与人文政治的对立。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古代发达的科学技术必有一个观念基础。他认为这就是道家哲学。他从“道教在一千多年来总是和一切力图推翻现有秩序的叛乱牵扯在一起”,认为“道家实质上是一种反封建力量。”[15]他在如此给道家的政治立场定位的基础上,进而得出一个论点:”道家严格区分了两种知识,一种是儒家和法家的‘社会’知识,这是理性的,但却是虚假的。一种是他们想要获得的自然知识,或洞察自然的知识,这是经验的,甚或是可能超越人类逻辑的,但却是非个人的、普遍的和真实的。”[16]可见,这是以西方近现代人文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紧张对峙关系作为梳理论证的模板。对此,李约瑟有更加明确的说明。他认为,道家思想是一种有机论哲学。“中国的有机论哲学曾经阻碍近代实验科学在中国的产生。但这种有机人文主义可用于把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17]对反科学运动(指针对机械论的唯物观在技术方面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而发的运动),李约瑟有一定的肯定。他说:“我倾向于认为,反科学运动后面的真正意义在于坚信不应该把科学看成是人类经验的唯一有效形式。”[18]
李约瑟把《庄子》在自然界的追问中表现出的理性精神的特点和古希腊哲学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对形而上学的厌恶,始极和终极都是‘道’的秘密。人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对现象的研究和描述;这确实是自然科学的一纸信仰宣言。”[19]他认为,庄子拒绝承认现象背后存在着非现象的东西,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认知原则相一致。李约瑟把这作为论证中国传统科技只能从道家哲学中寻找思想基础的基本论点。由此可见,李约瑟是以西方人的观念,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关系的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由此也不难理解他用道家的政治立场来论证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哲学基础。
但这却与中国古代的情况不相符合。
道教建立初期就反对原始的巫术迷信。[20]后来道教也一直排斥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和巫术迷信。无论哪一派的道教徒,都强调对于“真道”、“伪文”、“伪技”,务须严格区分,不容混淆。如《老子想尔注》说:“真道藏,邪文出,世间常伪技称道教,为大伪不可用。”又说:“道教人结精成神,今世间伪技诈称道。”葛洪也说:“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逛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分药石之救,惟专视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崇,……淫祀妖邪,礼律所禁。”[21]唐朝的司马承祯在皇帝的支持下,废除了五岳的“山林之神”,代之以真君祠。宋代以前的道教,也多戒淫祀和巫术。《妙林经》、《老君七十二戒》、《老君说一百八十戒》、《说百病》等均反对占星行卜、淫祀鬼、神禁咒巫蛊等巫术。以后这些东西也与道教若即若离,并没有成为道教的本质和主流。
实际上,这些东西并非道教的“专利”。根据顾颉刚的考证,秦代的方士和儒生几乎难以分辨。占筮、劾鬼、求仙、炼金,都是儒生们所从事的活动。[22]号称一代儒学大师的董仲舒不也在方术盛行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亲自学习、掌握求雨和止雨的神仙方术吗?刘歆也搞过巫术。后来的佛教,根据《宋书·周朗传》、《魏书·清河王传》、《广弘明集》等等诸多史籍的记载,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在这些方面比起道教来就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从起源上看,战国、秦、西汉时,巫术、方术的种类就已经相当多并得到了广泛传播。《汉书·郊祀志》、《史记》中有很多记载。这些都在道教产生之前。东汉顺帝在位20年,农民起义有十余起,其中多数利用方术等作为鼓动和组织群众的思想纽带,说明有“反封建性质”的巫术、方术在道教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了。东汉末年,曹操将善于术数的方士集中于魏国监禁起来,原因是“诚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斯众,行妖慝以惑民。”[23]道教此后的发展,与方术也是时即时离,最后也抛弃了它。如东晋杜子恭重建道教组织的核心原则是“方当人鬼淆乱,非正一之气无以正之”[24],把混杂在道教中的巫术之类清除出去。由此可见,道教的反封建性质虽然与《老子》、《庄子》对现存秩序的批评有关,但基本上是由混杂在其中的巫术、方术提供的。至于与朝廷关系密切的上层道教,是谈不上反封建性质的。
道教强调一切顺其自然,对世俗的人伦礼法至少是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而它的组织松散,道教徒蓄发,生活习惯也与俗人区别不大。任何俗人只要一穿上道服就可称为道士。一个隐居的人,即使他自认为不是道士,别人也要说他是道士。所以,民间的巫婆、神汉,浪迹江湖的术士、侠客等等,如果要攀附一种势力,最方便的就是道教。
2 西方方法
与上述两种只关注事物外在关系的观念相适应,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所采用的方法,是在把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明的东西,当作一堆静止的、封闭的、不变的材料来进行比较基础上的因果关系分析,同样也是只关注了事物的共时态的外在关系。这样的方法,是文艺复兴以来由牛顿力学所确立起来的机械还原论的表现。
这首先表现在他没有严格区分道家与道教,把这二者直接等同起来。这样,导致他对方术、巫术、炼金、炼丹、服气等等,没有揭示出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道教的时即时离的关系,误把它们当成了道教的本质和主流。
其次,他认为道教起源于战国哲学家、古代的巫和方士。这没有揭示出道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特点,把道教某一部分思想理论内容的历史渊源联系夸大为整个宗教的起源。道教在其1800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材料,都依据时势和自身的需要,先汲取改造,不合需要时又加以抛弃。表面一看,它的内容就显得十分庞杂。因而,简单地定论道教起源于什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把历时性的道教当成了一个共时态的整体,从中梳理出甲乙丙丁各项内容,与古代有关内容加以比较而得出结论。这种静止的分析忽略了道教自身的发展过程以及道教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经济等历史背景。
再次,在提出“李约瑟难题”时,他是把中国、西方作了共时态的比较,认定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事实,然后再对中、西文化作共时态的一一对比,确定其中各项内容是中学西源还是西学中源,然后,从中国文化体系中找出中国特有的事物而贴上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标签(如有机论哲学、封建制度、辩证逻辑、汉字、社会、经济、地理等都被李约瑟认定为阻碍因素);从西方文化体系中找出它所特有的事物而贴上促进近代科学产生的标签(如机械唯物论、拼音文字、因果关系、形式逻辑、实验主义等等)。在对比中,往往不自觉地把不同时代出现的事物拼凑在一起进行比较。这既忽视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各自的历史发展,也忽视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各自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严密整体。就以西方现代科技为例来说,它也远远不是一个逻辑上严谨统一的整体,其中渗透着各种实用的处理,如物理学经常放弃数学的严密性来处理问题。此外,如前所述,在这种比较中渗透着李约瑟作为西方人所接受的西方观念。对中国特有的事物用西方观念强行拆解,缺少对它们作多层面的把握,也就难以抓住其实质。例如“用”这一概念经常被他置于较低的地位而被认定为经验主义。其实,“用”的含蕴是多层次的,实用观念未必都是危害。再如他认为《易经》的符号系统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因素,理由是它过于繁琐、复杂和“导致一种对概念的因袭,对大自然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25]”。这失之于简单化。实际上,这种繁琐和解释之所以不是解释,是由于李约瑟和我们现代人所接受的西方教育而产生的。何况作为《易经》分支学派之一的宗教学本身就在历法、地理、中医药等科技领域中有充分的运用。
最后,忽视了历时性的研究,就导致李约瑟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庄子之前的发展一笔勾销了,也忽略了庄子对此前和当时的科技发展的成果、水平、状况的吸收和思考,把庄子思想当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也使他在对庄子思想进行剖析后就停步了,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特质。
科学技术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如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等,有复杂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个子系统及其间的相互作用都在变化。科学技术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必然有许多互不相同的特点。现象的相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来源、功能也必定相同。不是任何相同性都能说明“历史联系”,或者一个民族从另一个民族吸取。既要作共时态的比较,也要作历时性的比较。在比较时,要注意哪两者之间可比,哪两者之间不可比,即对比较科技史的有效范围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超越这个范围。总之,上述三方面归结起来,都是先确定一个研究对象,再在这个研究对象之外去与另一个对象联系起来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因果分析。实质上都是只关注了事物的外在关系。
3 哲学思想
上述观念、方法,实际上都是李约瑟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概括为三点:“(1)人类社会的进化一直是逐渐的,但真正的增长在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对外在世界的控制方面;(2)这个科学是一个终极的价值,它的应用形成不同文明的今天的统一;(3)沿着这个进步过程,人类社会朝着更大的统一、更复杂和更有机的方向发展。”[26]
他的思想的第一点,与中国古代哲学观不一致。中国哲学强调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这二者的发展要服务于个体生命本真的健全与永恒。为此,他们主张民胞物与,“物物而不物于物”,不忽视人文化成。
第二点与他谈及反科学运动时的话有矛盾,有唯科学主义的色彩。科学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根本动力,也不是国家强盛、文化先进的根本判据。古希腊科学发达,却难免灭亡的命运。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科学发达,国家却四分五裂。西汉汉武帝时期、唐朝贞观之治,国力强盛,科学上却鲜有成就。宋代国力衰弱,科学文化却高度发达。
第一、二点结合,“进化”就成了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线进化论。这种直线进化论与前述的共时态的因果分析观念——强调唯一的、普遍适用的规律的存在——相结合,就成了单线进化论。李约瑟认定的有机论哲学起源于中国的观点就表明了这一点:怀特海—科勒、伍杰、迈耶等生物学家—劳埃得·摩根、亚历山大、斯马茨、塞拉斯、恩格斯、马克思—莱布尼茨—中国。[27]虽然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还可探讨,但应该指出,在研究中国、西方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科技、文化现象时,这种直线进化论、单线进化论往往是不敷应用的。
第三点比较接近于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人特有的世界主义。由此,他认为,中国文明也有科学特性,中国的科学技术必定会再度辉煌,中国文明必将复兴,中国必将再次强盛。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自己的特质。如果不是17世纪以后欧洲的崛起和19世纪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中国的科技也会按自己的特质发展下去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他认为这种特质就是有机自然主义。
但我们认为,以有机自然主义来概括中国古代科技的特质,至少是不全面的。例如,《庄子》的“道法自然”概括了疱丁解牛、乐师、津人之操舟若神、善射者、轮人等等例子,它们说明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将征:工具简单、个体劳动、技艺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验诀窍和个人体悟。
总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科技的特质。以西方科技作为标准,用西方特有的方法、观念、思想来研究它,是难以揭示出它的特质。用这些东西作为标准来评判它,是有失公允的。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同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一样,我们呼吁,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上,现要倡导和实现本土化。
标签:李约瑟论文; 道教起源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科技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道教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