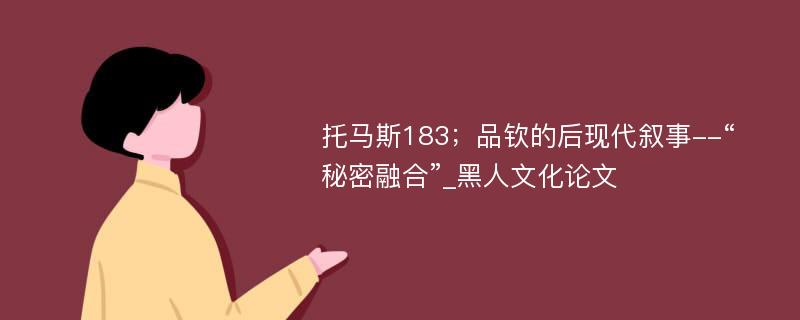
托马斯#183;品钦的后现代叙事——《秘密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后现代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后现代状况?也就是说,什么是后现代叙事试图在故事中反映或批判的状况呢?对于利奥塔,任何被普遍接受的宏大叙事的缺失或匮乏,都是后现代主义特点的表现。而戴维·哈维则强调1972年以后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的时空体验之变化。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而言,后现代状况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由与晚期资本主义相关的文化因素决定的,或者他称之为“多国资本的世界空间”决定的。正如他在《后现代主义》一书中的第一句所强调的,后现代状况基本上是对历史的遗忘。而“后现代”这个概念则表示试图在缺乏历史眼光的时代用历史的眼光思考现在。很显然,这就包括对建筑的思考,因为对詹姆逊来说,建筑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例证。对詹姆逊而言,后现代状况是一回事,作为文化和思想风格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另一回事,而后者企图使后现代状况从隐秘的状态进入人们的视野,让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应当表现为当前对历史的一种觉悟,或者用历史的眼光思考当前的一种方式。后现代状况和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或内在因素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
后现代状况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对历史无声的、不经意的遗忘。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美学风格,则是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说是在艺术、哲学、理论和批评领域表现后现代状况的方式。
后现代叙事有哪些特点呢?我将用托马斯·品钦的短篇小说集《笨鸟集》(Slow Learner)中的故事《秘密融合》(" Secret Integration" )作为早期后现代叙事的代表作来加以说明。我将把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一书中的分类稍作改动,并列举出后现代叙事最显著的一些特点:风格混杂——即不同时期各种风格的混用;对以前各种风格的戏仿;典故的运用;各种文类的混用;缺乏深度;缺乏情感(或许我应该说,情感转变成了一种被称为“酷”的奇特的讥讽情感);全知全能叙事的弱化,更为确切地说,叙事者与读者进行心灵交流,而不对故事加以评判或解释;间断性,即由情节构成的叙事经常被中途打断;荒谬(词源学意义上)的时间转换,使用的手法有进喻、预叙、回叙、倒叙、埋伏笔;翻写文本,通常由故事中的某一个角色重述故事;突兀的语体变化或语气转换;高度间接的叙述,以至于通过暗示、影射之后,故事中似乎还隐含着另一个故事;某种幻觉的运用,又称反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最近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即用现实主义的风格讲述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魔幻故事,换句话说,作者坚持使用宗教、迷信、魔幻和超自然的题材,并加以讽刺;过度地夸张地对喜剧和闹剧的运用;或者无政府状态社会激变;使用框架故事来控制、阐释故事本身并最终用讽刺手法消解故事原本的意义;关注边缘人、弱势群体、“天下不幸的人们”的经历;一种反对社群自身的感觉,自我牺牲,或自杀性的,德里达称之为“自动免疫”的自我解构过程;认为做出道德判断或担负道德责任的意义本身存在问题;要求对某些直接或间接的虚构性或实质性问题的关注,即背离叙事的传统,对叙事自身的模式及其社会功能进行质疑。
在托马斯·品钦的《秘密融合》中,所有这些特点都有所表现。我将以此故事作为范例,用以确定后现代叙事的底线。当然还有大量可以用作范例的作品,譬如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它也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我所列举的各种后现代叙事的特点。品钦的《秘密融合》的优势在于它篇幅短小,简单易懂。故事发生在1964年的某个日子,美国民权运动之初的一天,是约翰F·肯尼迪1963年遇刺的一年之后,比马丁·路德·金遇害(1968年)早4年。随后发生了暴乱和反对种族隔离的示威活动。这一切促成了美国的民权立法,它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美国,尽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在赋予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平等权利”这一问题上,我们正在大踏步倒退。品钦的故事在《星期六晚报》上首次发表。那是一份当时美国家庭广为订阅的杂志。40年代我还很年少时,我出身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父母也订阅了此杂志。
《秘密融合》的框架故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品钦在1984年写在《笨鸟集》的前言中模棱两可的评价。品钦在前言中对其早期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尖锐而讥讽的批评,尽管他也说明了历史的原因,同时对其新作《秘密融合》也进行了着墨不多的揄扬。《秘密融合》讲述了一个青少年“四人帮”男孩子们的故事。他们就像“内部秘密集团”那样,在伯克希尔一个废弃豪宅的地下室里秘密聚会,神情肃穆,隐秘谨慎。他们在酝酿一个与身边的成人“机制”和“路线”抗衡的庞大计划。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已经上了大学的名叫格罗弗·斯诺德的“神童”。叙事者说,每次干扰了成人的计划之后,他都忍不住咯咯地笑。这四个孩子热衷于开“实际的玩笑”(practical joke)。他们特别喜欢在铁路上、学校里和家长会上开这种玩笑。几年来他们一直秘密聚会,进行“军事演习”,密谋筹划。他们的武器是从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偷来的沾水即爆的钠。他们还有一套潜水员的服装,其中一个男孩曾经穿着它,把给当地造纸厂供水的一条小溪搅浑,致使该厂停产一周。另一个男孩用弹弓把少许的钠射向一个大庄园的游泳池边正在举办的晚会,钠发生了爆炸,引起了令人满意的绝妙效果。他们还成功地用绿色聚光灯使一辆火车停车。当火车驶近时,25个带着面具的人在绿色的灯光中突然出现,惊呆了火车机组人员。他们也从小学招募新兵,培训新生力量,或者叫“肉弹”,以便实施同时在不同地点袭击学校的庞大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叫停成人社会的机制。在故事发生的时间,他们正在计划为以电影命名的“斯巴达克斯”行动的第三年作准备。为了真正的奴隶起义,第三次军事演习代号为“A行动”。格罗弗告诉他混沌无知的共谋者们,A代表Abattoir(法语:屠宰场——译者注)和令人毛骨悚然的“Armageddon”(世界末日来临时的善恶大决战——译者注)。统治着今日美国的青少年“四人帮”,庄严肃穆地扮演着成年人的角色。他们几乎都相信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这种行为就像伊拉克战争一样,是替上帝打响了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当大街小巷血流成河时,被救的人们将被从山顶上救到天堂,最好是戴维在耶路撒冷的小山顶。
今天我们会把品钦的男孩们这种“四人帮”的形式不无讽刺地叫做“恐怖主义小巢”。国土安全部会找他们的麻烦。品钦绝对有先见之明。他看出这些兴高采烈的致人于死命的青少年的破坏性和他们的宗教信仰,诱发了今天的恐怖主义分子、肉弹,以及像在格伦拜中学发生的杀死多名同学的学生,还有最近一名在教堂枪杀了7名做礼拜的人后开枪自杀的那个男子,以及新近发生的一名用枪杀死了祖父和7名学校的人后开枪自杀的17岁男子。这种恐怖主义分子会说,“让我们想想,怎样才能把世贸大厦干掉?那将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最大象征的一次袭击。劫持商用飞机来炸怎么样?太棒了!动手制定计划吧!”9·11后,据说本·拉登对计划如此完美地得以执行而感到喜出望外。
其间的区别,而且是最大的区别,在于据叙事者所言,品钦的青少年恐怖主义分子清楚地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对其家长或家长的代言人——老师或警察,实施真正的暴力行动。与读者进行心灵交流的叙事者将此说得十分明白——注意我没有用“全知全能”这个词。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用间接语篇讲述了男孩子们知道的事,而没有让他们知道他在讲。无论是作者还是文本都未做出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判断。
关于品钦的青少年恐怖主义秘密团体就谈到此。然而,正如标题所告诉读者的,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意义。这个由男孩子们组织起来密谋对抗社会的故事,只是个幌子,真正的故事是关于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的美国的种族主义。有一段倒叙,讲述了这几个男孩子在旅馆与一位酗酒的黑人爵士乐演奏家卡尔·麦卡菲的相遇。麦卡菲最终被警察作为流浪汉抓进监狱,当时他正因戒酒而身体不适。无论孩子们怎么劝阻,他还是要了酒,而他没钱支付旅馆费和买酒的账单。他的故事就是警察粗暴而不公正地对待黑人的活生生的例子,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叫卡尔·巴林顿的黑人男孩。这个男孩好像刚刚搬到这个社区不久。他立刻被接纳为这个团伙中的一员,并被平等相待。他们甚至赞美他的肤色,它使他们联想起“所有种族的融合”。当蒂姆想到卡尔时,他总是看到卡尔被燃烧着的红色和赭色所环绕。孩子们天然的包纳精神与汤姆·斯维福特儿童故事中的种族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格罗弗悲叹道:你们知道汤姆·斯维福特的那个黑人佣人吗?记住,“他对另外几个孩子说,他的名字叫伊拉笛凯特·桑普森,他对待黑人佣人的态度令人反感。他们想让我读这本书,想让我也像他们那样吗?”
与此相反,这些孩子们的家长和社区其他的中产阶级白人一样,都被巴林顿家的到来吓坏了。他们立刻开始谈论“住宅区恐慌症”和种族融合问题。蒂姆无意中听到母亲在给巴林顿打电话威胁他,并破口大骂:“你这个黑鬼”,她突然啐了一口,“肮脏的黑鬼,从这个城里滚出去,滚回皮茨菲尔德,快滚,否则有你好看的!”
故事情节高潮的到来是在一次秘密碰头会之后,当孩子们送卡尔回家时,发现他们的父母和邻居们给巴林顿家的草地上倒满了垃圾。孩子们认出了那是来自他们自己家的垃圾。
故事发展至此,也就是在故事即将收尾之前,故事标题的意思似乎已经十分明白。德里达认为,社群总体上有个规律,即都会生一种叫做“自动免疫”的疾病。《秘密融合》中的自杀性自动免疫疾病以两种表现形式存在:它以戏仿的、绝对无害的形式讲述了孩子们的秘密社群与他们密谋破坏的成人社群之间的关系;它又以较为严肃的形式描述了源于奴隶制邪恶的美国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使得孩子们的父母亲常常对他们的非洲裔邻居充满仇恨。故事似乎在说,生活在成人社群之中的青少年秘密社群毫无种族主义偏见。在“秘密融合”中,孩子们对卡尔·巴林顿的感情是兄弟般的感情,没有“自动免疫”,它提供了一种民主的范式。品钦以典型的玩弄词藻的方式,将种族融合与神童格罗弗最初对“融合”一词唯一意义的理解进行了类比。他理解“融合”是微积分中的一个术语,用于把曲线分为无限小的部分,这些部分之间存在缝隙,在各种不同运算中都可以利用。按照这种多少有些奇怪的类比,种族融合能够使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栅栏障碍上的木棍变得有穿透性,因此黑人总能穿越栅栏,并且被融合,正如这个“四人帮”孩子们将卡尔吸收为合格的一员一样。这就使得他们的秘密团体成了一个理想的、充满幻想的、乌托邦的、救世主的、平等主义的、无阶级的社群。品钦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们都应该像这些天真的男孩子一样,讲真话。孩子们自然而然地作出了正确的道德伦理选择,接受卡尔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他们的长辈却以非常不道德的、以自杀性的自动免疫方式拒绝了搬迁至该社区的这个黑人家庭。该社区人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人体患上了诸如糖尿病或关节炎那样摧毁人体器官或组织的反人体疾病。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的完整的人体形态就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隐喻,如同在“身体政治”中那样。该词在该故事中出现,是在格罗弗向其他男孩解释什么叫“动作协调”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在健身房锻炼时,胳膊、腿,和头都要一起动,我们也是同样,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几个人就得像你们身上的各个部位一样协调。”
然而,在《秘密融合》中,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在前面提到,对超自然、鬼怪或幽灵的运用,以及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是后现代叙事的一个特点。幽灵般的骑兵队长的故事是《秘密融合》中最先对超自然力量最明显的描写。他脚穿带有马刺的马靴,带着一把短枪,出没于孩子们每次在废弃豪宅的地下室秘密碰头时所必经的树林。身高7英尺的骑兵队长很容易被当成是对这些青少年毫无伤害的集体幻觉。
然而,较难解释的但也更为重要的,是读者逐渐(或突然)发现卡尔·巴林顿本身也是一个幻觉、一个幽灵。我不得不承认品钦愚弄了我。卡尔被描写得像别的孩子一样有血有肉。当另外三个男孩出于好奇去看这户黑人家庭搬入的新居时,他们在那儿相遇了。“靠在钢管做的街灯柱上”,“一个穿着毛衣的细高个黑人男孩”,“一边打着响指”,一边告诉他们,他的名字叫卡尔。“对,卡尔·巴林顿。”此后,他就成了这个团伙人,他被接受了。比如说,他眼很尖,能从立交桥上将球形玻璃容器准确地扔到桥下经过的汽车挡风玻璃上。他会摆弄格罗弗“业余组装”的收音机,等等。只有到结尾处,当孩子们发现巴林顿家的草地被扔满了垃圾时,前面较为隐蔽的暗示才变得明朗化。卡尔是孩子们的集体幻觉,是一个幽灵、一个鬼怪,是他们无意识间虚构的故事。当卡尔独自在雨中走回他们藏身的密室时,他们未加阻拦。孩子们意识到他们破了咒符,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离开了卡尔·巴林顿,把他留给了老房子里其他萎缩的幽灵以及这个不稳定的居所。只有在卡尔离开后,叙事者才揭示了整个故事的欺骗性。
细心的读者,也许是天真的读者(比如我),此时会在怀疑中回顾前面的内容,想看看前面是否有暗示。叙事中丝毫没有暗示说卡尔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灵活现的真实存在。比如说,他并不是透明的,或者能在你眼前消失的。他一点也不像真正的幻影那样来无影、去无踪。叙事者没有任何能够揭示这个秘密的交代,几乎没有。一开始就像是青少年孩子们在做疯狂的事。在一连串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故事中,一个怪异的插曲讲述了两三个男孩的故事。蒂姆和埃廷埃尼在前一年的夏天跳上去皮兹菲尔德的货运列车,到销售“实际的玩笑”用品的商店去购物。在那里他们买到两副假胡子和扮演黑人用的两支化妆品。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时,埃廷埃尼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在使一个朋友复活。”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麦卡菲先生,那个酗酒的黑人流浪汉,孩子们在旅馆碰到的爵士乐演奏家。他就叫卡尔,蓄有小胡子。此时,读者意识到卡尔·巴林顿就是那个卡尔·麦卡菲的转世。孩子们曾乞灵于上帝,将他召唤到真实世界中来。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异化和作为他者的现实,以及他们被剥夺的经历和所遭受的屈辱,是白人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的。叙事者强调,孩子们与麦卡菲相遇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痛创,因为这次经历“向他们暗示了麦卡菲先生是多么落魄。”蒂姆与麦卡菲相遇之后感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迈向深渊的边缘——谁也不知他走了多久。他往下看了一眼便吓得转身走开了。麦卡菲转世成为卡尔·巴林顿,也就是“退场”所采取的形式。
当读者发现卡尔·巴林顿完全不是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幻想的游伴时,他/她会怎么理解呢?卡尔是一个只有这几个男孩能看见的幻影,是用言词、意象,以及成年人不知何故拒不承认的、否定的、可能保留着的边缘性建构起来的,仿佛它们是埃廷埃尼父亲库房里的零件。卡尔是“这些男孩们的朋友和机器人,他们为他买碳酸饮料喝,或者派他去做危险的工作,最后又任其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与卡尔·麦卡菲不同,或者说与他们父母亲那令人厌恶的、可怕的、破坏性的、自杀性的种族歧视不同,卡尔·巴林顿完全在这几个男孩的控制之中。人们也许会说,卡尔只在语言或思想的意义上是真实的。叙事者强调了构建卡尔的机械方法,他是碎片的,是堆砌而成的生物,好像是用库房里的零件组装而成的,是成人们宣称不可融化的碎片,必须被放置在社区的安全围墙之外的东西,从而使自己保持纯洁、安全、免疫,受到保护,而卡尔则成为替罪羊似的献祭。美国的黑人就是这样被排斥,被看成废弃的不可同化的碎片和垃圾。可是,这垃圾有一种在排斥、遗忘中坚守的方法,和在放逐中求生存的方法,能变成亡魂萦绕曾经排挤过他们的人们。这几个男孩用碎片和痕迹把卡尔组装起来,在用言词、意象和可能性(你可以称它们为意识素)组装时,卡尔成为《秘密融合》故事本身。故事把看上去杂乱无章的一系列事件以适当的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其意义自动地或机械地从碎片组合中产生。当然,在幕后的品钦狡猾地把这个故事建构成一种机器,在碰到正确的读者时,故事便产生意义。同样,男孩子们“无意识地”秘密建构了卡尔·巴林顿来满足某种欲望。
印刷在纸上的言词和作为故事中角色的卡尔·巴林顿,都体现了德里达所称的“生存状态(survivance)”,但不是“生存者(survival)”而是“仍在生存(surviving)”的东西,是一种积极/消极的生存状态。碰巧到我手中的《笨鸟集》一书中的印刷符和这些意识素——“言词、意象,以及成年人不知何故拒不承认的、否定的、可能保留着的边缘性”——都是由德里达所说的痕迹构成的。这些堆砌物作为制造卡尔和创作故事的方式,必然会存留下来。两者都将生存,并且像幻影死去/活着一样,只要有读者将生命的气息吹入故事之中,就像活死人一样,随时都可能复活。
阅读一个故事就是培育一个幽灵,使故事中所有虚构的角色苏醒,给其注入精神,召唤其亡魂,包括虚幻故事中的虚构角色,幽灵和鬼魂,像卡尔·巴林顿那样。
人们肯定会想,卡尔之作为幽灵、不真实的、虚幻的角色,对于理解《秘密融合》的意义会产生什么差别呢?这似乎会使故事的意义有别于我所讲到的意义。我在前面说过,也许故事表明男孩子们天生没有种族歧视观念。他们组成了一个乌托邦社群,与成人的“自动免疫”社群抗衡。但是,卡尔是一个幽灵,这是否真的会使以上的解释不能成立?我想说,《秘密融合》有着浓厚的双重性。它可以从几个相互矛盾的方面进行解读,我不知道读者将如何选择解读方式,因为它们都是毫不含糊地建立在文本证据之上,尽管他/她能够——也许必须——作出伦理道德的选择,或者得出某种解读比其他解读更加令人满意的结论,以便为了社群的利益而推广。
就在读者还认为卡尔是真实的人时,蒂姆明白了“融合”就意味着“白人的孩子和有色人种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这时他说道:“那么,我们已经融合了”。格罗弗回答道:“是的,他们(成人们)还不知道,而我们已经融合了”。我想,这就是该故事标题的含义。他们吸纳卡尔入伙是秘密的融合,因为它的存在只是对他们而言。成人们压根儿不知道卡尔的存在。这就意味着至少看上去融合卡尔对社会秩序完全没有价值。它没有力量去改变任何东西。“当男孩子们放逐了卡尔,令其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时”,埃廷埃尼问格罗弗,“我们还是融合的么?”格罗弗回答道:“去问你父亲……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是个重要问题。他们还是融合的么?如果他们是在与自己虚构的幻影融合的话,如果他们现在把自己制作的机器人放逐了,他们还是融合的么?很难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心灵的融合与真实的融合似乎完全不同。故事以男孩子们各自回家而结束,回到“热水澡,干毛巾,睡前看电视,亲吻道晚安,再也不会全都安全的睡梦”。去掉最后这一点,这个故事似乎讲述了男孩子在短暂的叛逆之后被同化,又回到成人社群与家人团圆。他们很快就会和这个社群一样持有种族偏见。品钦没有用感伤的笔触描写黑人对美国白人种族歧视的抗议。《秘密融合》正是在读者认识到这一点时达到了高潮,想到1964年试图改变美国种族隔离制度所遭遇的顽固抵抗时,读者不免感到悲哀。
故事中的最后这一点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产生了与我刚才阐述的故事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力度。男孩子们回到各自的家中,回到了再也不会全都安全的睡梦,尽管卡尔·巴林顿是一个幻觉、一个鬼影,但他是用被排斥的词语和用意象在社区的安全区之外的社会库房里一片一片地建构而成的。孩子们通过与种族隔离主义的牺牲品卡尔相遇相知,同时也通过亲眼目睹种族歧视以及他们父母亲的恐惧,自觉地意识到美国的种族关系的现实。通过接纳卡尔·巴林顿,并自然而然地以亲情对待卡尔,他们的心灵融合了,这给这些男孩子和读者同时提供了一个战胜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未来民主的范式,我们应当为之努力。品钦的作品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之努力,尽管卡尔只是一个理想的建构。但是,他是用在社群的边缘依然存在的那种改良的潜在可能性建构的。民权运动和所有解构种族主义隔离的立法,以及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使美国的形势有了极大的改观,但还远远不够,最近曝光的洛杉矶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警察对黑人的粗暴行为便可证明。
谁能说《秘密融合》不是在以其微小的努力为美国未来的民主作出贡献呢?怎样才能做出贡献?一件虚构的文学作品如何能做到不流于肤浅的娱乐,也不止于对虚拟角色及其行为的描述,而是用言词作为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做出贡献的行为方式呢?
《秘密融合》本身为此问题提供了答案。该故事以一个奇怪的插曲开场,它除了表明男孩子们与家长对立之外,似乎与主题毫不相干。其中一个男孩子蒂姆长了一个瘤子,大夫给他涂了一种红色的东西,在紫外线下发出很亮的绿光,然后大夫告诉蒂姆:“啊,好的……绿的。这就是说瘤子将会消失”。蒂姆无意中听见大夫告诉别人,说他用了“暗示疗法,半数情况下都会奏效”,如果不行,他会用液体的氮。当蒂姆问格罗弗什么是暗示疗法时,格罗弗说,是一种“类似信仰疗法的治疗,这种治疗对瘤子没有任何作用”。“他们想把瘤子说没了,但是我刚才给他们搅和了”,他得意地说。绿颜色被编码为代表幻觉,或者可能奏效的小窍门,它后来在故事中以品钦特有的杜撰情节的方式又一次出现。当这几个男孩和25个雇来的人用“吓人的绿色探照灯停住火车后”,格罗弗说,“好奇怪”:“我现在感觉很奇怪,在绿色中感觉比较好,尽管绿得吓人,尽管只有一分钟时间”,绿色是暗示疗法的颜色,这一奇怪的细节似乎想说明虚构的暗示对世界能产生良好的作用,比如在《秘密融合》中所描述的。
我的论点是,《秘密融合》有着一系列暗示疗法或者信仰疗法的功能,正如男孩子们把骑兵队长和卡尔·巴林顿看作是真实的人一样。幽灵和幻影在他们的世界中是有作用的。同样,《笨鸟集》一书中印刷符号的作用,和利用暗示疗法产生鬼魂或幻影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卡尔·巴林顿在读者的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与其他虚拟作品完全一样。词语比角色的生命力更长,或者说词语是角色赖以无限生存的方式,词语使读者无论何时读此故事,都有可能将蒂姆、格罗弗或任何其他角色看作幽灵。从这个角度看,卡尔·巴林顿与其他角色并无两样。他也是被文字塑造成真人的。当读者发现卡尔是男孩子们虚构的幻影时,读者会同时意识到其他角色的真实性和他的一样。这是一种品钦独具匠心地用文化碎片塑造出的真实,所有的角色都显得像“真人”。这些虚构的或幻影的真实被间接地作为幻影表现出来。卡尔·巴林顿是个幽灵,如同带着枪、穿着马靴的骑兵队长一样,亦真亦幻。然而,这并不能使这些幻影产生他们在读者的真实世界所产生的作用,正如卡尔·巴林顿考验了男孩子们“融合”的能力一样,该故事教育读者,要像书中的男孩子们那样对待其他族裔的人们。《秘密融合》向读者提出了挑战,要求读者必须就如何对待同胞作出选择。
我认为,我已经用《秘密融合》作为例证说明了我在文章开头罗列的后现代叙事的特点。它有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自我消解的框架故事。除了在很少情况下有些模棱两可之外,故事的叙事者没有实施作者做出判断的权力。超自然或幽灵、幻觉手法在故事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该故事是关于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及社会功能的。它要求读者作出伦理道德的判断。故事的意义来自按照真实时间顺序组合的孤立的插曲。故事是多种不同文类的拼凑或戏仿,全都不连贯地迭加在一起。该故事戏仿卡尔·麦卡菲讲述自己故事时所用的叙事方式。品钦在前言中提到,在他写该故事时,受到他曾一度误解了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他清楚地暗示说故事中有数种文体并存。他还提到好几部电影,如《斯巴达克斯》,约翰·韦恩的《巷战》(Blood Alley),还有一部不知名的二战时期的电影,一天晚上孩子们路过郊区房子时断断续续地听到电视上正在重播:“(劈劈啪啪的声音,搞笑的叫喊声)噢,对不起,先生。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日本间谍……”;“我怎么能是日本间谍,我们有五千人……”;“我会等你的,贝尔,我会等你到……”。《秘密融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幽灵故事,就像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秘密融合》是对儿童读物的戏仿,比如前面提到的汤姆·斯威夫特的儿童故事。尽管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过,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我年少时在杂志上读过的故事的颠覆性戏仿。我所记得的故事都比较伤感,思想意识比较保守,大约都是写给白人中产阶级读者的,或者是为捍卫经常出现在那家杂志封面上的著名的罗曼·罗克维尔绘画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品钦有可能在向《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说什么,也许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且想比平时的穿透力再大一点,风格上再老辣一些。《秘密融合》最终证实了我所说的,后现代叙事表现出德里达所谓的自我破坏性的自动免疫逻辑。
通过对一个例证的探讨,我似乎证明了这种后现代叙事的存在,证明了它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可加以说明的文体、规范以及主题的特点。这些特点应该能使品钦的故事成为后现代叙事的范例。把它清楚地指定为后现代叙事会产生一个问题。当你以此来讨论比如说塞万提斯的范例故事《训诫小说》时,会发生什么呢?我并不否认两个作品有着主题的差异和历史的差异。两部作品都以多种方式深深地镶嵌在各自的历史地点和时间之中。我并没有忘记詹姆逊的口号:“永远历史化。”可是,假如形式产生意义,我认为是这样的,那么,当你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时,“后现代叙事”这个概念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问题是,《秘密融合》中所有的特点都能在塞万提斯的《训诫小说》中找到,毫不奇怪,它们是不同历史成分的不同方式的混用。《训诫小说》发表于1613年,比赛万提斯逝世早3年,比《堂吉诃德》第一卷晚8年。若想把相同的细节指出来,并指出这些细节如何决定《训诫小说》的意义及言语行为的力度,就需再写一篇论文。假如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它们的相似之处,而我认为能够说明,那么关于“后现代叙事的手法是某种独具特点的、前所未有的叙事”的说法便会遭到质疑。
译者简介:徐颖果,天津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天津 300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