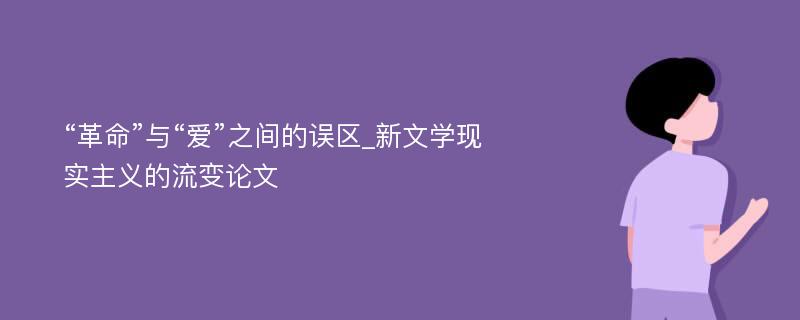
“革命”与“恋爱”的歧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途论文,恋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革命加恋爱”作为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小说中的一种题材,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述里被普遍使用。但是,多数研究者都把它当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而很少对其加以(并非不必要的)界定,这样就难免造成某种模糊与混乱。这种情形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在2008年第五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就发表了熊权女士的文章《论“革命加恋爱”概念的历史建构》(以下简称“熊文”),该文试图“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合理的‘革命加恋爱’概念”①,认为“革命加恋爱”是一个经由不同历史时段被建构起来的概念。可惜的是,熊文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却存在着疏忽,甚至导致对这一概念的历史建构过程认识的偏差。
本文即试图重新梳理“革命加恋爱”这一概念的产生过程,并考察它的最初含义,同时探究这种文学现象受到批判的真正原因。
一、从“革命与恋爱”到“革命加恋爱”
一般认为,较早对“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小说进行概括、评价的是钱杏邨,被列举的批评文本则是他发表在《太阳月刊》1928年第二期上的《野祭》书评②。但是,在之前的《太阳月刊》创刊号的《编后》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评价:“孟超在《冲突》里所表现的,更是现代的一个大问题,——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在这一篇里是革命战胜了恋爱。”③这可能是“革命与恋爱”一语第一次在评论中出现。当然这只是编者对该期刊物上所登载作品的简评,真正对这一题材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的,还是钱杏邨的《野祭》书评,他在该文中说:“现在,大家都要写革命与恋爱的小说了,但是在《野祭》之前似乎还没有。”④后来的研究者一般都将蒋光慈的《野祭》视为“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开山之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钱杏邨的这段评论有关。
“革命与恋爱”小说最初是指蒋光慈、孟超等人的作品,此外通常被视为这类小说的突出代表的,还有洪灵菲的《流亡》、《前线》,丁玲的《韦护》等等。但实际上,“革命与恋爱”小说的创作在192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一个潮流,而且无论是读者还是左翼评论界,对这类作品的评价也基本是正面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比如1928年3月的《文化批判》上就载有读者来信,指责蒋光慈某些作品“内容仍然带有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思想”,所写革命是“学生式的浪漫”,使人读了可能反而讨厌革命,⑤不过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并非主流。
然而到了1930年代初,情况却发生了变化。1931年11月,由冯雪峰执笔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必须抛弃那些“定型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而“恋爱和革命的冲突”就作为此类题材之一而被列举(此外还有“身边琐事”、“小资产智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等等)。⑥次年4月,左翼文坛上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茅盾、钱杏邨、郑伯奇、瞿秋白、阳翰笙五人为阳翰笙的小说《地泉》再版本作序。熊文称这次作序是“集中批判‘革命加恋爱’公式”,但实际上,在这五篇序言中涉及“革命”与“恋爱”的只有一处,他们真正“集中批判”的,其实是“革命的浪漫蒂克”,二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应该混为一谈。有意思的是,五篇序言中唯一一段批评“革命与恋爱”小说的话,恰恰出自此前曾经热烈赞扬蒋光慈作品的钱杏邨笔下:“书坊老板会告诉你,顶好的作品,是写恋爱加上点革命,小说里必须有女人,有恋爱。……至于那些因恋爱的失败而投身革命,照例的把四分之三的地位专写恋爱,最后的四分之一把革命硬插进去。”⑦批评的口吻相当严厉,而且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革命加恋爱”一语的雏形了。
过了两年多以后,茅盾于1935年1月1日的《文学》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回顾这类题材小说的发展史。在他看来,这类小说在最初阶段是“指出了‘恋爱’会妨碍‘革命’,于是归结为‘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的宗旨”,并说“有人称这样的作品为——‘革命’+(加)‘恋爱’的公式”⑧。其实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第一次明确总结出“革命加恋爱”这一“公式”的,正是茅盾的这篇文章。紧接着,茅盾又总结了“革命与恋爱”小说之后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革命决定了恋爱”,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女的挑中了最“革命”的一个男性;第三阶段是“革命产生了恋爱”,表现为从事革命工作、志同道合的男女自然而然地成熟了恋爱。茅盾称后两类小说为“‘革命’×(乘)‘恋爱’的公式”⑨。
显然,在茅盾那里,“革命加恋爱”仅指“革命与恋爱”小说的三种模式之中的一种,即所谓“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中,“革命加恋爱”则基本变成了描写“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小说的总称,而熊文在引用茅盾的这篇文章时,同样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区别。诚然,如熊权女士所说,“革命加恋爱”的概念本来就是在历史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确定的、本质性的概念,因此我们不能说后来的文学史著作中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当我们对史料进行分析、梳理以求较准确地把握一个概念的时候,却不应该不注意这类细节。
从“革命与恋爱”到“革命加恋爱”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却大相径庭。“革命加恋爱”的“加”字,本身就突出了其作为“公式”的性质,所以,这样的命名其实是包含着明显的批判意图的,反映了一类曾经流传甚广的小说的评价史的演变,忽略了这一变化,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妨碍我们认识这种文学现象的复杂性。
二、“革命与恋爱”、“革命的浪漫蒂克”和“创作方法”的流变
通过对“革命加恋爱”这一概念产生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既然“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小说曾经风行一时,并拥有大量的读者,那么左翼文坛为何在1930年代初会突然之间群起而攻之呢?如果说这仅仅是因为其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那么批评家们在此前又为何没有发现?其二,茅盾发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的时候,这类小说的流行早已过去(按照茅盾自己的说法,这类小说早在1931年丁玲发表《水》的时候就被“清算”了⑩),他为何突然之间有了这样的冲动,来为一种昔日的文学现象重新“命名”?这就不得不考察批判“革命与恋爱”的现实语境,尤其是左翼文坛先后引入的各种文艺理论。
从1920年代末开始,左翼文学阵营就显示了对“创作方法”的异乎寻常的关注,而其原因,则要追溯到发生于1928年初的“革命文学”论争。可以说整个左翼文坛都在论争中发现了自己在理论方面的欠缺。于是一时间形成了介绍、引进海外左翼文艺理论(尤其是所谓“创作方法”)的热潮。
首先被引入的是日本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在1929年左右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讨论文章,但“新写实主义”在当时仅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还没来得及引起理论上的探索和创作上的实践,就被“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所取代了。(11)中国的“左联”作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当然要执行上级的决议,加之当时的“左联”本来就注重理论的引入,于是在1931年到1932年间,“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被大力提倡。1931年11月的左联执委会决议就专门提出了“创作方法”的问题,从“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特别要和观念论及浪漫主义斗争”(12)等表述中,是可以极为清楚地看到提倡“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意图的。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强调“世界观”对创作具有决定作用,要求作家通过作品来体现“唯物辩证法”,它在后来被看成“左”的机械论口号。正如温儒敏教授所说:“历史总是比后人的想象要复杂得多。从‘拉普’传来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是“左”的机械论口号,但当时左翼文坛却又企图借这口号去反对“左”的机械论文学观。”(13)当时的提倡者认为,要确立“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就必须反对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等倾向,而这些倾向到最后就被归结为一点——“革命的浪漫蒂克”。
“革命的浪漫蒂克”一语,最早可以溯源到蒋光慈的论文《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他在论及诗人布洛克时说,“布洛克是真正的罗曼蒂克,惟真正的罗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寻出美妙的诗意,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14)。这里的语气虽然是赞美的,但是我们从中已经可以看出把“革命”浪漫化、理想化、纯粹化的倾向了,而这正是后来“革命的浪漫蒂克”被指责的原因之一。对“革命的浪漫蒂克”最集中的批判,就是瞿秋白等人为《地泉》所作的序言,题目即为《革命的浪漫蒂克》。瞿秋白并没有明确指出“革命的浪漫蒂克”具体的含义是什么,不过他们大致都提到表现形式上的标语口号主义、公式化、人物的脸谱化,以及思想观念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将现实斗争理想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等等,并最终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障碍。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再来看“革命与恋爱”小说,就会发现它似乎是“革命的浪漫蒂克”非常典型的体现:这类小说总是以“革命”与“恋爱”来结构故事,这当然是“公式化”;而且,对爱情的缠绵悱恻的描写,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表现。实际上当时对“革命与恋爱”小说的批判,也基本上是从这样的角度进行的。
因此,可以说“革命与恋爱”小说的被批判是受了“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株连”,而这又是由于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缘故。然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带来的弊端确实是太明显了:“由于‘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是把世界观混同于创作方法的,所以在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思想情调的同时,连浪漫主义也给摒弃了……连创作主体性也给反掉了”(15),这样,它自然遭到了一些作家的反对;更重要的是,后来又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口号取而代之,于是,中国左翼文坛的风向也随之发生了偏转。
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是周扬发表于1933年11月《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一期上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耐人寻味的是,周扬在此文中采取的是一种在今天看来极其“别扭”的发言姿态,他在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提出过程后,紧接着就说:“新的口号在中国是尤其容易被误解和歪曲的。特别是,这个口号是当做‘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否定而提出来的。”(16)文章表明了周扬的紧张心态:他一方面意识到了左翼文坛之前存在的偏颇,另一方面却又担心自己的检讨会成为反对者的口实。该文涉及的问题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价,这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周扬否定了以前那种把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直接等同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看法,反对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但同时仍然不忘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虽然不是“对立”的,但也不是“并立”的……此外还特地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和古典的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乃至‘揭起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旗帜’的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17)也就是说,周扬既要为浪漫主义“恢复名誉”,又要避免让人以为之前对“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批判是错误的。
至此,我们可以试着回答本小节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茅盾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发表于1935年初,一方面,此时距离周扬发表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已经一年有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已经成为了左翼文坛的共识;另一方面,随着新理论的引入和接受,当年提倡“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旧事,已经很少有人提及。或许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抛弃种种顾忌、重新反思一种曾被归为“革命的浪漫蒂克”并遭到清算的文学现象,才会成为可能。
如上文所述,“革命加恋爱”这一命名,本身就包含着明显的批判意图,然而在茅盾对“革命加恋爱”和“革命乘恋爱”的区分中,又明显存在着某种裂隙:虽然都是公式,但是,“从‘加’到‘乘’,自然是进步。即使不加说明,读者只一想‘乘’是‘加’的累积,也就可以了然罢?”(18)这绝不是什么文字游戏,因为紧接着茅盾就对“革命与恋爱”小说的三个阶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其中对描写“恋爱与革命的冲突”(“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仍然主要持批判态度,但是对后面的两类则做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并最后总结道:“从‘恋爱与革命’小说的三阶段的进化过程看来,我们也会明白了我们的作家们在短短五六年中怎样努力摆脱了个人感情的狭小天地的束缚。”(19)与数年前的严厉批判比起来,这里的语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实际上,茅盾对“加”和“乘”的区分,也可以看成一种策略。这样的区分一方面可以继续批判“恋爱与革命的冲突”,而避免了同之前对“革命与恋爱”的批判直接对立,但另一方面,由于把“革命与恋爱”的缺点主要归于这类小说的“第一阶段”,就为一定程度上肯定后两个“阶段”的作品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遗憾的是,读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茅盾的这番苦心。相反,倒是他的“革命加恋爱”这一策略性的命名,后来竟变成了对所谓“革命与恋爱”小说的一种否定性的通称,这可能是茅盾当初所万万料想不到的吧。
三、“革命”与“恋爱”的歧途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1930年代的左翼阵营之所以对“革命与恋爱”小说进行批判,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错误”的创作倾向,而与主流的创作方法产生冲突。各种文学史在提到这一文学现象时,采取的口径也与当初批判它的时候基本一致。然而赵园先生在她的《艰难的选择》一书中,却对这种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
该书在论及“革命与恋爱”的流行主题时,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这种题材确实是时代生活的产物,而绝不是什么“虚伪的题材”;第二,从“五四”开始,婚姻爱情就是现代文学中一个主要的题材,到了“革命文学”时期已发展成熟,因而“恋爱与革命”结构的产生有其文学史上的原因;第三,以往批评这类“公式化”的小说时,都是着眼于小说的“结构”,但实际上这样的结构未必就妨碍“性格”的创造,赵园先生还通过具体分析丁玲的小说《韦护》,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借助“恋爱与革命”这样的结构,同样能够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此她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要为了‘结构’而否定或忽视形象呢?在这种情况下,‘公式化’究竟属于哪一方?‘创作’还是‘批评’?”(20)
这些观点无疑是引人深思的。然而倘若说“革命与恋爱”小说并非是“公式化”的,那又该如何理解它当年所受的批判呢?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年的左翼批评家,会不约而同地“误以为”“革命与恋爱”小说是“公式化”的产物?
前面说到,左翼文学阵营一直对所谓“创作方法”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又很明显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即“现实主义”。左翼文学阵营对“创作方法”的关注,当然不是完全从文学自身出发的。我们不妨来分析另一个与“现实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真实性”。周扬曾这样概括二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的真实,就不外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客观的真实之表现……对于社会的现实取着客观的,唯物论的态度,大胆地,赤裸裸地暴露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穿所有的假面,这就是到文学的真实之路。从文学的方法上讲,这是现实主义的方法。”(21)然而“现实主义”仍有新旧之分,笼统地说坚持“现实主义”就可以抵达“文学的真实”,就难免造成“阶级立场”的模糊,所以周扬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总结道:“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根本法则,才是到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22)
如果注意到这里所构造的“现象”与“必然”、“本质”的对立结构,以及特别强调的“革命阶级的立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在当时虽然是一种极其现实而普遍的现象(23),却被指控为“虚伪的题材”。因为写这类题材的小说却往往没能表现出这样的“本质”:革命是首要的、崇高的、纯洁的,而恋爱则是微不足道的、仅属于本能的、甚至是庸俗的。就连茅盾那篇试图谨慎地重新评价“革命与恋爱”的文章,也体现出了这样的逻辑,他在论及“革命产生了恋爱”(“三阶段”中最高的一个阶段)的小说时,就是这样肯定它的:“在这里,‘革命’是主要题材,‘恋爱’不过是穿插;‘革命’是唯一的人生意义,而‘恋爱’不过像吃饭睡觉似的是人生的例行事务的一项罢了……在‘革命’的光下,所谓‘恋爱’者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值不得为它发狂。”(24)
说到底,“革命与恋爱”小说之所以遭到批判,并不是因为它违反了“现实主义”,而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革命”的表达。这可以从一个例子上得到很好的证明:温儒敏教授在论及“革命的浪漫蒂克”时,曾经敏锐地指出,“革命的浪漫蒂克”有两种典型体现,一是“革命+恋爱”,二是正面写革命斗争和工农觉醒反抗的作品,其中后者往往直接宣传革命道理、图解演绎政治概念,艺术价值低于前者,但是在后来的评论中,“如果指摘新兴‘革命文学’的缺失,就专点‘革命+恋爱’,仿佛‘革命的浪漫蒂克’弊病莫过于此;而当要从新兴‘革命文学’中寻找‘现实主义’和‘革命性’时,又专拣正面表现革命的作品,仿佛只要写到革命,就有‘现实性’”(25)。当然,温儒敏教授此处主要指的是后来文学史中的评价,并非当初的批判,但我们却能在当初的批判中发现相同的逻辑,比如上文所引的1931年11月左联“决议”中,被点名批判的几种题材里,就有“恋爱和革命的冲突”,却没有提到概念化地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
可以说,无论是左翼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同时具有革命者的身份,所以都要遵循两种逻辑,一是“文学”的逻辑,一是“革命”的逻辑。这两种逻辑之间往往会有裂隙,然而他们自己却未必会意识到,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要想方设法来弥合,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解释就是一例,对“革命与恋爱”的批判同样也是一例:“恋爱”当然不会妨碍文学,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都以恋爱为主题,但它倒确确实实会妨碍“革命”(不是指现实中的革命,而是指作品中对“革命”的表达)。所以必然要对其加以批判,但在批判的时候,却又总想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所捍卫的不只是“革命”,还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所谓“革命与恋爱”小说“虚伪”、“公式化”之类的在今天看来未免言过其实的指责。
四、余论
在左翼文坛对“革命与恋爱”小说批判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左翼以外的批评家对此的反应却比较冷淡。李健吾在评论巴金《爱情三部曲》的文章中就提到:“直到如今,我们还听到关于革命与恋爱的可笑言论。没有比这再可笑的现象了: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至少也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26)表面看来,这段话是“革命”“恋爱”并重,甚至还有抬高“革命”的意思,但是细揣后半段的表述,就会发现作者是在隐隐地表达着对左翼把恋爱变得“不自然”的不满。当然,不同立场的批评家对这一文学现象有不同的反应,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分歧,却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类似题材的小说此后的历史命运。
抗战期间,也曾经有过“抗战与恋爱”的提法,但已经很少有人注意了;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也有不少小说同“革命与恋爱”题材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像《洼地上的“战役”》、《红豆》、《青春之歌》等等,而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批判,我们会发现,虽然批判它们时不会再用“公式化”、“概念化”这样的断语,但其背后的逻辑仍和当年批判“革命与恋爱”时毫无二致;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当“恋爱”已经不再需要借助于“革命”而获得合法性、甚至连“革命”本身都要被“告别”的时候,“革命与恋爱”这一题材也就自然寿终正寝了。然而在今天的革命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我们仍能时时看到一些穿插着的恋爱故事,可见,时代尽管变迁,但“革命与恋爱”的创作模式始终存在。
注释:
①熊权:《论“革命加恋爱”概念的历史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②《太阳月刊》1928年1月创刊,同年7月停刊,共出版7期,第2期即为2月号。熊文在引用这篇文章时,将其发表时间误为1928年10月。《野祭》为蒋光慈的中篇小说,1927年出版。
③《太阳月刊》1928年第1期之《编后》。该文仅署名“编者”,但从杨邨人所写的第2期《编后》中可知,月刊前两期是由他和钱杏邨共同编辑的,因而只能断定:第一期《编后》的作者为二者之一。
④钱杏邨:《野祭》,《太阳月刊》1928年第2期。
⑤转引自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113页。
⑥(12)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页。
⑦易嘉、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华汉:《〈地泉〉五人序》,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5-876页。
⑧⑨(18)(19)(24)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茅盾文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页,第337-338页,第338页,第339页,第339页。
⑩茅盾:《女作家丁玲》,《茅盾文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437页。
(11)参见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第二章第三节《“新写实主义”的演变与得失》,第111-122页。
(13)(15)(25)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第129-130页,第94-95页。
(14)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出版。
(16)(17)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一》,第73页,第84-85页。
(20)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0-95页。
(21)(22)周扬:《文学的真实性》,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一》,第32页,第46页。
(23)赵园曾援引洪灵菲等作家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参见《艰难的选择》,第91页。
(26)李健吾:《爱情的三部曲——巴金先生作》,《咀华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此文最初发表于1935年,这段话很有可能是针对茅盾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