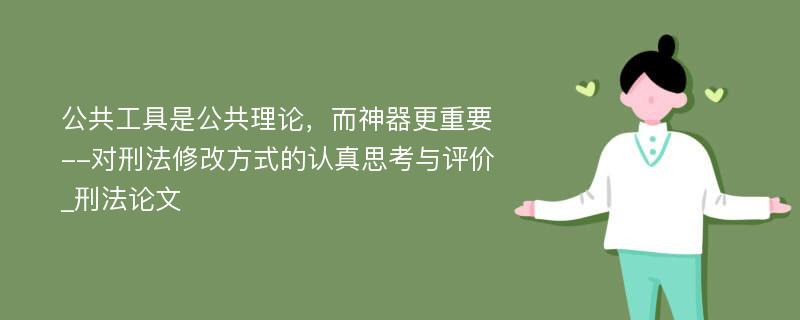
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论论文,持重论文,神器论文,刑法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公布了,如同每一次修改一样,总会得到司法实务界和刑法理论界的赞美与喝彩。但面对刑法如此频繁的补充修改,面对此次刑法修改有点“伤筋动骨”的现象,面对整个社会对刑法寄予过高的“救火”治世的期望,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对刑法补充修改的立法观念、制度设计和立法技术是否需要进行一番反思和改进。
一、关于刑法补充修改与法律的稳定性、长远性要求
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曾说过一句令我们至今依然感慨万分的话:“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① 一个国家过分重视刑法在国家管理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正像一个国家过分重视暴力在国家管理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一样,是社会政治文明程度不高、当政者对管理手段自信不足、整个社会环境依恋以暴力和准暴力为倾向的明显表现。在中国,由于受历史刑法观念、传统政治思维和刑法文化传承的影响,刑法一向被视为治国安邦、实现长治久安的治世工具。历朝历代,无论春秋战国的李悝制《法经》、子产“铸刑鼎”,还是“汉鉴秦弊,蠲繁削苛”,及至一部“唐律”及其疏议的面世,其精美严谨更成为刑法备受重视的明证,都在“竭力追求制定一部百世不改、垂范久远的良法。”② 这些都无不显示出刑法在中国传统的道统、法统和政治治统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光阴荏苒,时序轮回,在我国社会开始想要进入法治时代的今天,刑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作为“二次性违法规范形式”的产物,是公法,是公器,更为神器,故其制作定规哪怕是补充修改都需要在极其严肃、认真和慎重之中进行当属不争之题义。
曾记得1997年刑法准备修订之时,围绕着是否需要修改、修改的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到底是大修还是小修等问题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很自信地宣称要修订一部完备的刑法进入二十一世纪,“这次修订刑法,主要考虑:第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将刑法实施十七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将拟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和中央军委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条例编入刑法,在刑法中规定为贪污贿赂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两章;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过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第二,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刑法的原有规定,包括文字表述和量刑规定,原则上没什么问题的,尽量不做修改。第三,对一些原来比较笼统、原则的规定,尽量把犯罪行为研究清楚,作出具体规定。……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是继去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步骤,对于进一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重要意义。”③ 我国老一辈刑法学者高铭暄也曾自信地说过,这部刑法“深深凝结着中国法律专家的心血与汗水”,④ 起码管用很多年。谁曾想世事难料,仅仅过去十多年,诸多补充修改规定就已经横空出世,一部刑法也已是不知从哪里读起方解其意。立法者的自我欣赏和学者们一时的倾情赞美,并不能掩盖其已有的明显瑕疵与严重不足。
刑事立法关涉国家治世观念,关涉公民的生杀予夺,乃治国安邦之公器神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护国之宝。就中国传统的历史刑法文化而言,制定刑法典,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件极其庄重之事。刑事立法者自当有一种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为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指标和参考尺度,例如一部法国《刑法典》从1810年制定后直到1994年才进行大规模修订,可为体现稳定性之楷模。而我国社会已经取得的文明进步,也已为我国制定一部垂范久远的刑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基础。因此能否制定一部较为反映社会现实需要并能为后世借鉴的良法,应当作为一种立法指导思想首先加以确立。我国的刑事立法者理当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必要的估计,不能过分强调时下的国情,满足于一时的“社情民意”需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有风吹草动,便进行刑法的补充修改。否则,朝令夕改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中国社会目前依然处在激烈的社会解构与重构过程之中,很多的制度设定还在论证之中,很多的观念还在形成之中,很多的行为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刑法作为第二次违法规范形式的产物,它的完善还有赖于首先制定和完善一些前置性的法律为刑法的制定提供基础。刑法的有效执行,还有赖于前置性法律的有效执行。只有当前置性的法律无法惩治和阻挡一般违法性行为时,才需要刑法闪亮登场。不然刑法的补充修改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前车之鉴,比如当年我们曾经有过操纵期货市场罪的补充修改规定,由于我们有关期货市场还未开通,有关期货交易的法规还未制定,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操纵期货市场罪等于是一纸空文,被束之高阁。所以,与其让刑法的有些内容一直处于不断的需要补充修改的过程,不如暂时放一放,等条件成熟后再进行较为慎重的修改为好。此次刑法修正案涉及的社区矫正制度,我们又面临诸如刑法中有关社区矫正制度的运用,然而,直到现在还无一部《社区矫正法》出台。刑事立法又一次出现“倒逼”现象,这说明我们的立法观念出了问题。我们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法治不像政治可以具有极大的灵活性,细水长流、恒水常稳是它的基本表现特征,也是它的生命所在。古人云: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斯为下矣。故有学者早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时就指出:“立法之时,若无垂范久远之念,心存临时之意,则立法效果可知。”⑤ 此言诚哉,其语之义今日仍可一听。是故若过分以眼下的“国情”和社会民情民意为由着意作近距离服务而频繁修改补充立法,不但理由并不充分,而且暂时的社会现象和民情民意也会潮起潮落。正所谓“不以规律为立法要旨,而以因应特定现象为立法要旨,不可谓之明智。”⑥
二、刑法的补充修改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刑法修正案(八)》涉及对刑法进行较为全面的补充修改和重大内容的调整,就必然涉及刑法的立法权限问题。刑法是我国的基本大法,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进行制定的。依据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律只有补充修改的权力,并且只能是依法进行才有法律效力和法律意义。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对何为“全部”、何为“部分”进行明确的限定,也没有明确指明什么是基本原则,有多少个基本原则,而刑法理论中所理解的刑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其内容的过分抽象,仅仅起到一种观念的提示作用而无规范效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刑法修正案》是否与刑法基本原则不相协调的问题。
《刑法》在第3-5条之中仅仅规定了一些原则的、抽象的规定,这种规定在整个总则中比比皆是,但是否就此可以称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法理论上和法律事实上依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部分刑法进行补充修改,但部分加部分能否等于全部?此次《刑法修正案(八)》篇幅之大、文字之多,已远远超出一般人所认定的“局部”之概念。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部分刑法进行补充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那么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如何来检测刑法的补充修改已经同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了呢?
我国《刑法》是通过总则与分则上、下“两编”进行建构的,刑法总则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一般性原理和一般性原则的规定,刑法分则是一般性原理与一般性原则的具体化表现形式。其实从两者的基本结构和相互关系来看,刑法的总则都是具有奠基性功能作用、统领全局作用以及能够制约刑法分则的原则性规定。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循名责实”政治哲学观念,刑法总则内容的规定可以称之为基础性的规定、基本性的规定或原则性的规定。简而言之也就是基本原则的规定。由此我们在这里大胆地提出一个带有原则性的结论,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补充修改不能涉及刑法总则的内容,也不得与刑法总则的内容发生冲突与矛盾,并且应当受刑法总则内容的约束。对刑法总则内容的补充修改,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进行。
然而从《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来看,很多地方都已经突破了刑法总则的规定界限,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里仅以死刑的削减和限制问题为视角进行必要的透视与剖析。
《刑法修正案(八)》减少了13个罪名的死刑规定,占原68个死刑条文的19.1%之多。削减死刑,笔者举双手赞成。然而此次规定的对死刑削减的数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在十多年前,我们曾如此地盛行重刑主义、曾如此地偏好死刑。但仅仅十多年的时间,死刑就作如此大的改动,不难看出我们的刑事立法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形而下的区间而缺乏超前意识。即使如此,与当今世界众多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来比较,我国刑法的死刑依然是一个为人瞩目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和鼓动我国的刑事立法者应当更快、更大比例地限制死刑和削减死刑,直至融合到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中去。⑦ 所以今次大规模、大面积、大手笔削减死刑应当说是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的积极动作。
然而,当我们回头审视这一举动时,却在理性的层面与法理的层面受到阻却。当年设定这一死刑规模时,是以全体民意为依托的,是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得到确认和通过的。而现今废除这些死刑规定,却是在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进行的。全国人大代表有3000多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160多人,而且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数出席就算合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100多人代表全国13亿人对这些死刑作出一锤定音的决定,显得多么的不协调。不管我们刑事立法者的出发点和主观愿望是多么的合情合理,但在客观上已有了“架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嫌。在倡导严格依法办事的今天,这并非是一件小事。同样,对75岁以上行为人废除死刑完全是合乎道义的举动,但涉及行为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同样属于刑法总则的带有奠基性的问题,怎么能由人大常委会来修改变动呢?法律本为人心所设,刑法如何规定,完全取决于刑事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但涉及如此多的刑法总则原则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似乎有越位之嫌。
因此,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规定在刑法总则中都属于带有原则性的规定,人大常委会不能说改就改。宁可再等待一些时日,由日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进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一问题上完全可免越俎代庖之责。因为刑法毕竟是涉及生杀予夺的刚性法律,没有足够的数据而轻言改动,本身是一种不够慎重的表现。我们过去有过太多的不慎重,能否从今天开始变得慎重一些,这已不是过高的要求。当时不顾死刑的基本理念,重刑主义观念膨胀,使死刑数目不堪重负。今天为了改变死刑过多过重问题,又不顾程序正当性的嫌疑,想一举大量削减众多死刑。尽管这是一个文明之举,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之举,但也得先反思一下曾经的重刑思想给我们形成的沉重法律包袱。所以在对待有期徒刑的上限和其他刑罚制度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轻易改动刑法总则的设定界限。不然再过十多年,是否又一次对刑法进行大规模修改,绕了一圈再回到原地?
三、关于“犯罪圈”大小的问题
“犯罪圈”的大小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犯罪学和刑法学中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主张尽可能缩小“犯罪圈”的主张从来没有一次能够阻止立法者对“犯罪圈”的日益扩大。《刑法修正案(八)》依然如此。根据修正案,此次刑事立法新增了3个罪名:醉酒驾车或高危驾车罪、恶意欠薪罪、非法出卖人体器官罪。除此之外,《刑法修正案(八)》对一些具体犯罪的构成内容进行了明显的扩大,例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强迫交易罪、强迫职工劳动罪、盗窃罪……等等在构成要件内容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扩大。我国刑事立法者对“犯罪圈”的扩大总是有一种为了“适应形势需要”的理由,并且其背后的理由总是现成的。然而,多次的补充修改,就是看不到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是否有的罪名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只见新罪的增加而不见旧罪删除。随着“犯罪圈”不断扩大,使得刑法本身有尾大不掉之嫌。其实所谓的恶意欠薪罪,本来也可以通过社会诚信建设、加强行政执法、民事司法救济等途径加以解决,其入罪的必要性令人费解,其效果值得怀疑。古人曰:“治国之要,刑非所先”,⑧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应该让我们获取更多的启示。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有的罪名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就会涉及刑法补充修改的非犯罪化问题。据有关学者考察与研究,现代意义上的非犯罪化运动起始于20世纪中叶。二战之后,在全面推进刑法改革事业的英国、德国、美国等国,非犯罪化成为问题进而成为一种价值倾向。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止,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犯罪,如同性恋、近亲相奸之类的行为因其并不存在值得保护具体的法益,应当从刑法中加以删除的呼声日益高涨,并逐渐成为现实。在英国,1957年出台了《关于同性恋和卖淫的沃尔夫登委员会报告》,该报告建议通过一项立法,允许2l岁以上的男子间自愿私下实施同性恋行为。以该报告为契机,英国在1959年至1967年对以下行为实行了非犯罪化:淫秽犯罪、自杀、堕胎、同性性交等。英国的非犯罪化改革对西方国家的刑法理论及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此影响,欧美、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都掀起了非犯罪化运动,在刑事立法中削减有关违反公共道德的犯罪。可以说非犯罪化问题一经提出便如火如荼,被称为世界性的刑法改革运动。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法律规定律师、医师、宗教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一样,有为当事人保密并拒绝作证的权利,这是为了不公然违逆大众伦理或一般道德认知;也正是基于这一伦理基础,西方国家刑法一般没有“律师伪证罪”或支持犯罪嫌疑人告发自己辩护律师的判例。任何国家的法律,决不能仅仅为了眼前的治安利益而伤害人道、人性、人伦的基本价值,就像古代、近代中国及古今西方法律都允许“亲亲相隐”(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一样。这场非犯罪化运动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刑法理论界,近年来,非犯罪化问题也日益引起我国刑法学者的关注。从刑法的进化来说,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不断重新界定都是符合其进化规律的。然而我国的刑事立法似乎仍然喜欢只沿着犯罪化的单行轨道向前运行。从1997年《刑法》全面修改后的10多年内,我国立法机关增加30多个罪名却没有删除过一个罪名。
正是从这一基本的刑法理论分析的角度出发,刑法应该要尝试重新划定犯罪化的边界,对无社会利益侵害的犯罪主要是一些无被害人犯罪,例如一般性赌博罪、聚众淫乱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等刑法理论界比较普遍认为的属于无被害人的犯罪进行非犯罪化的处理。同时,刑法中已有了一般的伪证罪,像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也是多余的,反而给人以歧视律师或其他辩护人之嫌。另外,侵犯通信自由罪、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所侵犯的是公民的通讯自由权,这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中一项比较轻微的权利。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类犯罪发生率低,几乎成为虚置条款,也可以考虑进行非犯罪化的处理。
此外,以往的刑法修正案中新增设的一些犯罪并非全都属于必要,如骗取贷款罪。由于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设的贷款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要件,所以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许多贷款不还的案件。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又增设了骗取贷款罪。但贷款行为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如果借贷方不是出于恶意占有的目的,虽然给对方造成了损失,也只是属于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可以通过民事手段来解决,刑法无需介入民事法律可以调整的领域,以致影响正常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
注释:
① 转引自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范忠信:《再论刑法应当垂范久远》,《法学》1999年第6期。
③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1997年3月6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7年第2期。
④ 高铭暄:《刑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⑤ 同前注②,范忠信文。
⑥ 同上注。
⑦ 参见高铭暄、苏惠渔、于志刚:《从此踏上废止死刑之路》,《法学》2010年第9期。
⑧ 鲁嵩岳:《慎刑宪点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标签:刑法论文; 法律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刑法修正案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