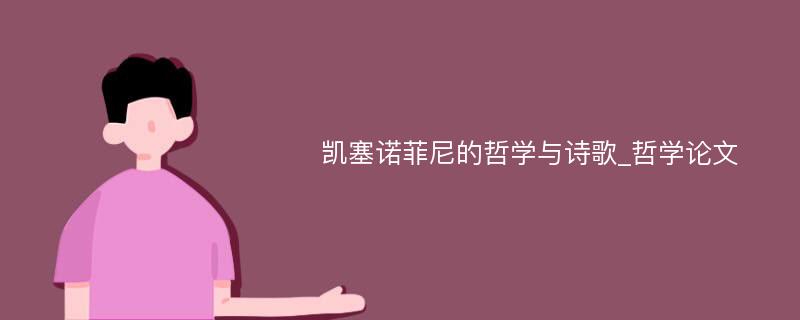
克塞诺芬尼的哲学与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哲学论文,克塞诺芬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075-05 我们通常以为,哲学与诗歌品性迥异,尤其就文体而言,哲学多以严格的论文,或稍不严格的散文形式写成:诗歌作为一种文体,讲究格律与形式,或长于抒情,或富于情节,甚或二者兼而有之。但是,这样的分类标准在柏拉图和尼采面前会突然失效——我们难以设想,柏拉图和尼采的思想不够深刻,更可能的情形或许是,这样的分类着实不妥。实际上,作为文体,诗歌是老字辈,论文体只是后生。尤其是,落诸笔端的各种文字,其文体本身并不仅仅如王国维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更是与政制有着莫大的关联,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制对共同体中人的灵魂的熏染。除了文明早期的传统礼法(甚至包括传统礼法本身),后世的任何一种文体或者政制的确立,背后都有一种哲学的权力意志之手在起作用。 如今,我们所面对的论文和诗体的严格分野,首先来自现代的学科界限,尤其是各种现代哲学的通俗形式,更加彻底破坏了人的生活感觉——论文取代了诗歌在人的教育过程中的角色。但这并非现代启蒙独有的现象。在西方哲学产生的早期,也就是更早的启蒙时代,哲学的非诗体创作就已经和诗歌体裁形成了最早的争执,甚至早于柏拉图笔下诗歌与哲学之间“古已有之的纷争”,我们或可称之为散文体与诗体之争。① 公元前6世纪,便是这一场争端出现的最早时刻,散文体在西方诗文史上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在此之前,一切严肃的创作均采用诗体。这个时代恰恰是希腊社会从贵族政制向民主政制变化的时期,而泰勒斯开启的希腊哲学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对应,非韵文的散文体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并逐渐成为思想的传达形式。对于希腊的传统社会来说,诗歌是最习常的思想载体,诗歌中的诸神是活生生的生活现象,同时,传统诗歌还具有诗教的作用,对城邦的年轻人施行教化。②传统的诗歌,总是以对神(尤其是缪斯女神)的吁请开篇,比如荷马、赫西俄德,但是,散文体出现之后,诸神隐退,与传统诗歌不同,它们不再吁请缪斯,这首先体现出的是作为人的写作者对自己智性能力的信任:人的位置不再需要神来确立,人通过自己的哲学和智性,能够为自己代言——换言之,不再需要诸神和传统的束缚。可是,正是在这样的潮流滚滚之下,还有三位逆流而动的哲人:克塞诺芬尼、帕默尼德和恩培多克勒。这三位哲人在希腊哲学史上都是重要的人物,可是他们依旧采取传统的韵文诗歌写作,而不是新派哲人惯用的散文形式,这就成为解释他们思想时无法绕过的难题,莫斯特甚至称其为“早期希腊哲学的奇耻大辱”③。拙作暂且以克塞诺芬尼为例,试图对这个问题有所深入。 克塞诺芬尼在希腊哲学史上留有盛名,史称第一位埃利亚哲人,还是帕默尼德的老师。西方思想中念念在兹的“理念”之说,其发端就是克塞诺芬尼,同样,所谓一神教的最早说法,他也可谓开其端绪,因此两点,他得到后世无数的赞誉,但同时又得到无数的指责:原因在于,据说他对这两点的思考毫无深度。克塞诺芬尼诞生于公元前565年的克洛丰。25岁时,哈尔帕格率领米底人占领了这座城邦,克塞诺芬尼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涯。对于他此前的生活经历,我们知之甚少。在此期间,他曾居住在西方的臧克和卡塔拉,据说还参与了埃利亚城邦的建立。诗人相当长寿,他曾在公元前473年,也就是自己92岁高龄时,用下面这四行诗总结自己的人生: 我曾用六十七年的时间 反反复复地为希腊这片土地思索。 而我生命的头二十五年 我真不知该从何说起。④ 这位大哲人就这样一直用诗歌写作。由于克塞诺芬尼采取诗歌的写作方式,后来学者对他的研究无外乎两类,要么出于对其哲学的理解而忽视其诗歌形式,认为这只是一种从众做法,殊无深意;或者因其诗歌形式而对其哲学加以贬抑,认为克塞诺芬尼的哲学虽在哲学史上有着一席之地,但其实并不足道,开启这一说法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从不写诗,相反,柏拉图年轻时最早写的,恰恰是诗歌。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个根本的身份认知:克塞诺芬尼可以称得上哲人吗? 什么是哲人?哲人自然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人。那么,什么是哲学?希腊语叫爱智慧,哲人就是追求智慧者,但是这不过是泛泛之言。所谓哲人,就其本质而言,关注最为根本的存在问题。理解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人一直会说,哲学诞生于希腊。我们不妨列举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希腊哲人之言,来简述何谓哲学。哲学,或谓西方哲学诞生于泰勒斯的思考,当他说“水是万物的本原”的时候。尼采在说到史上这位哲人泰勒斯何以为哲人的时候说道,由于泰勒斯说水是一切之源的时候,这句话含有了这样的意思:“一切皆一”,一种形而上学的普遍化的信条出现了,这就是哲学思考的本源:“我们在所有的哲学里,连同那些一再被更新的、更好地表达这种起源的尝试中,都会遇到这个信条:‘一切皆一’。”“一切皆一”的“一”,就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本质。转换成海德格尔的说法,这就是凝视存在之为存在的存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曾谨慎地定义哲人:“热爱智慧的哲人渴望整全的智慧”,这样的人看到的是事物之为事物的本质,只有哲人才能够根据事物本身之所是来把握事物。所谓整全的智慧,是关于世界整体的智慧,也就是世界本身作为“一”而被把握的那种智慧;所谓事物本身之所是,则是这种“一”的整体原则下具体事物的“一”。所以,苏格拉底对阿德曼托斯说: 一个人的思考若是真正转向了存在,就无暇向下留意人类的事物,也不会因与他们争斗而充满妒忌和坏的意愿。相反,他所见和所专注的,是整齐规划的事物,是永远处于同一种条件下的事物——这些事物彼此间不行不义,也不会遭受他者之手的伤害,而全都处于理性的秩序之下。(《王制》) 苏格拉底已经明言:哲学之为爱智慧,就在于思考存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最具哲学意味的《形而上学》中说:“凡能得知每一事物必然如此的终极原因的知识,必然优于次级的学问;这些终极的目的,个别而论就是一个事物本身的‘善’,一般而论就是整个宇宙(或者秩序)的‘善’,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世间第一原理’。”⑤这种第一原理,最根本的基质,同样不脱“万有为一”的根基。哲学之为哲学,其根本并不是泛泛而言的爱智慧,而是对智慧之爱必须要达到对整全的智慧之爱,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之爱。这就是尼采所说泰勒斯的信条:“一切皆一”。 可是,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本原”之中所透显的“一”,仍然只是一种蕴含,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潜能,还没有成为思想的事实,泰勒斯仅仅是“从云雾之中凸显出来”,但云雾依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的说法已经异常清晰,那么,在泰勒斯和他们之间,是怎样的过渡?真正拨开了这层云雾的,其实就是克塞诺芬尼。他在辑语23中写道: 唯一的神,是现有诸神与诸人中最伟大者 无论在肉身抑或精神上都与我们不同。 后世学者经常因此而将克塞诺芬尼称为“神学家”,将这一条辑语视为西方最早的一神论表达。这固然是一种研究的途径,但是,这样的思考落脚点在“神”上,而不是在主语神的界定“唯一”上。译为“唯一的神”,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克塞诺芬尼这里的说法并不是以“一”来界定神,相反的,他是将“一”描述为神,至于后面的两个补充说明,“诸神与诸人中最伟大者”和“无论在肉身抑或精神上都与我们不同”,实则是“一”何以是神的补充说明,两者都试图传达出作为整体的“一”与作为部分的存在之间的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记录。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记载:“克塞诺芬尼是第一个提出‘一’的人……他凝视整个苍穹,说‘一’就是神。”⑥“唯一的神”这个难题,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得到了澄清:“一”是“神”,所以才成为“唯一的神”。当亚里士多德说克塞诺芬尼“凝视整个苍穹”的时候,这个细节恰恰展现了“一切皆一”在克塞诺芬尼思想中的存在:整个正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这位埃利亚哲人吐露出“一切皆一”的哲学,但随即又罩上了一个“神”的面纱。刚刚清晰的面目随即变得晦暗。 在柏拉图看来,这样的做法恰恰是埃利亚哲人的做派。在《智术师》里,柏拉图让埃利亚的异乡人明白地说:“我们埃利亚这族人,从克塞诺芬尼,甚至更早,就以神话的方式讲述‘一切’,如他们所言,一切其实就是‘一’。”传授哲学的方式就是神话,或称之为“作诗”。如此看来,据说是克塞诺芬尼学生的帕默尼德,同样以诗体写作,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因为,他们都懂得“以神话的方式”讲述哲学。埃利亚异乡人和他代表的埃利亚哲人,代表了一种古老的哲学方式。根据这种哲学方式,隐藏的风格恰恰是哲学的本性所在。而在《智术师》里,异乡人对数学式明晰的展现和拒绝,如施特劳斯所言,他对这两者既敏感又拒绝:“由数学及一切和数学有关的东西带来的才能的魅力”,或者“人类灵魂及其体验的沉思而带来的谦虚而敬畏的魅力”。后者凭借的正是诗歌和神话。所以,克塞诺芬尼将“一”描述为神,就不仅仅是宗教或神学的思考,更是哲学本身的考虑,是基于政治哲学的考虑。 那么,根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的说法,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克塞诺芬尼是有史可查最早明确确立了“一切皆一”这一哲学根基的哲人,正是在他这里,所谓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开始转向,不再仅仅思考事物本身的形成,而是转向了万物存在的形而上学基质,这就是存在或者“一”,很明显,如果没有这个形而上学思考的形成,柏拉图的“理念”论或许就不会出现。 但是,克塞诺芬尼以神话的隐晦传达自己的教诲,也就是柏拉图说的“神话”表达。埃利亚派哲人有其自身的学脉传统,这可以保证他们内在的哲学传承,所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定有我们今日无缘得见的证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善于以神话和诗歌的方式传达,就让哲学获得了一层面纱,不至于让哲学伤害普通人的生活。 所以,克塞诺芬尼没有公开传达这份关于哲学的教诲,而只是说出一些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次级的学问”,克塞诺芬尼在自然哲人的层次上讲述了关于世界的构成,而不是关于形而上学的根本,比如: “无论如何变化生长,一切都是土和水”(辑语29)。 大海是水的根源,是风的根源;因为,如果没有浩瀚的海洋,风就不复存在,流动的河水和天空中的雨滴也荡然无存;不但如此,浩瀚之海还是云朵、风和河流的父亲。(辑语30) 这些辑语所传达的学问,大抵与泰勒斯开启的自然哲学类似,根据尼采的说法,皆可称之为科学,而在希腊语里有另外一个对应的词汇:episteme,是指人所获得的知识,对于世界的某种认识,某种深化的认识。但是,这些都是次一级的学问,并不能说是哲学根本的本质,或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形而上学。 克塞诺芬尼对前辈哲人甚至有些不敬,不过这似乎也是哲人的典型特征,这个叫做哲人之间的争论。据说,他“反驳了泰勒斯、毕达哥拉斯等人的观点,甚至还责难过爱庇门尼德斯”。他如是批评毕达哥拉斯: 一天,他遇到一只饱受虐待的幼畜,心生怜悯,于是说道(或据他们所说): “别再折磨它!当它哀鸣时,我认出了一个往昔挚友的灵魂。” 诗行中的他,或者说是毕达哥拉斯,或者说是毕达哥拉斯派哲人——这个差别并不大,关键是这个“他”持有的哲学信念:灵魂的轮回。这里的戏谑笔法其实很细腻,哀鸣的希腊文常常用于表达人的声音,这里可谓妙笔生花。我们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批评毕达哥拉斯的立足点在哪里?在著名的辑语1的结尾,克塞诺芬尼写道: 谁若在饮酒时畅谈回忆高贵的往事和 对美德的追求,请赞扬他吧。 他既不会谈论泰坦之战,不会谈起巨人 或是人马怪,或其他古老的幻想, 或者那些剧烈的争执。 这首诗歌的主题是会饮,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场合,在这样或大或小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场景里,谈论的人,应该拒绝那些奇谈怪论,玄思妙想,因为这不够“高贵”。一个真正高贵的人,应该言说对美德的追求,而不是智性的炫耀。毕达哥拉斯的错误正在此处,灵魂轮回之类的幻想,在其极端处,会让人和狗显得没有区别。既然如此,人的存在价值又如何彰显?人和动物之间的伦理区别又何在?克塞诺芬尼批评毕达哥拉斯的根据在于根植于传统的政治伦理。 一个哲人对另一个哲人所以不保持友好,其缘由竟然是由于传统的伦理,这种做法完全不像我们常识理解中撼古动今的哲人做派。事实上,这就是苏格拉底后来在做的事情。哲学从其诞生的时刻开始,就必然会同传统产生冲突,因为关于什么是好的问题,传统给出的答案是传统礼法,但哲学要给出好之为好的本质。可是,哲学对智性的要求极高,根据尼采的说法,哲学的探问必然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这对大多数人栖身之中的政治生活来说,都是一项太危险的行为,无论是对哲人本身,还是对大众来说,都是如此。我们通常说,苏格拉底意识到这个巨大的问题,这才导致他的第二次起航,从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但是,在笼统的“自然哲人”这个称呼里,克塞诺芬尼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其深度不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但这足以让我们把哲人关于政治哲学的自觉提前到克塞诺芬尼这里。 这就是克塞诺芬尼采取诗歌这种文学样式的根本原因:哲学是少数具有哲学天性和才智的人的事业,但诗歌却关乎所有人的共同存在、共同体的存在。所以,他把关于“一”的学问以神话诗歌的方式说出,这可以吸引有智慧和天性的人,但同时,他的诗歌更多是为保护多数人的在世生活,也就是保护他们生活赖以维系的道德根基。所以,我们细细检审一下克塞诺芬尼的辑语,就会发现,他更多的诗歌讲述传统伦常,而不是这些所谓哲学和科学。据说,他曾写有两千行的长诗,关于自己的母邦克洛丰和殖民城邦埃利亚等,假如它们流传后世的话,其性质或许类似于后来维吉尔所作的《埃涅阿斯纪》——这表明哲人克塞诺芬尼和城邦之间的关系有某种立法者的意味。他还写作诉歌和讽刺诗。古希腊诉歌采取对句的方式写作,或者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对偶,诉歌对句是“抒情诗中六音步英雄史诗的一个变体”。它由两行诗形成一个完整的诗句或诗节。第一行诗类似于六音步史诗,只不过在结构上稍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二行,人们往往称之为五音步格。同时,诉歌对句采用六音步的诗体,这种形式不但继承了赫西俄德的诗歌类型,同时还继承了他的道德训诫。 比如,在相对完整的辑语1中,克塞诺芬尼写道: 首先,怀着发自内心的欢乐歌唱神明, 歌中充满庄严的故事与纯洁的言辞。 会饮的场合虽然看似闲适放松,但一个人恰恰能够突出体现出自己的性情。这既是一个展现的场合,也是一个接受教育的场合。克塞诺芬尼这首辑语是会饮场合的歌曲,可以想象,这既是对会饮场合的描绘,也是适合于这个场合歌唱的曲目——克塞诺芬尼故邦沦落之后,他流浪于希腊各邦,据说就以传唱或者制作这些歌曲为生。与他年代相仿的忒奥根尼斯,其诉歌同样在会饮场合歌唱,也表达出同样的意蕴,他也通过对会饮这个小型社会团体的描绘和教育,构造出一个关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教诲。所以,在这样的场合里歌唱的歌曲反而更要故事庄严,言辞纯洁——对比一下柏拉图《会饮》里看似敬神实则渎神的许多会饮者言论,就能够明白苏格拉底是如何恪守传统的。 但是,令后来读者不解的地方是,既然克塞诺芬尼如此钦慕传统礼法,他为何还要攻击希腊传统礼法的教育者荷马和赫西俄德呢? 荷马和赫西俄德都说,诸神 和人类一样,有种种耻辱和过错: 通奸、偷盗、说谎,他们无不精通。(辑语10) (荷马和赫西俄德)传布诸神的种种缺陷,诸如偷窃、通奸和谎言。(辑语12) 这两则辑语或是同一句诗的两种版本,它们当然是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直接攻击。但是,克塞诺芬尼攻击的原因不是因为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在诗歌中传达出不审慎甚至渎神的言论:神怎么可以欺骗?怎么能够偷盗说谎?要知道,“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同样师从于荷马……”(辑语9),这样的教师会教出怎样的学生?当然有可能做出同样的欺骗和偷盗行为,其德性怎不会让人生疑?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克塞诺芬尼才进一步讽刺这样教育下的人们: 人们以为,神也是生出来的, 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说话,有一样的身体。(辑语14) 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后来被冠以“唯物主义”之名的诗句:“如果牛、马和狮子有手,能用手作画,能做人能做的工作,那么马则画马形为神,牛则画牛形为神,它们都会按照自己的形象画神,让神的身体和它们自己的身体一般”(辑语15)。不理解克塞诺芬尼的思想,直接给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唐突。这个“如果”的表述并没有认可与表扬的意味,如果联系到克塞诺芬尼诗歌的整体气息,牛、马和狮子之类的想象,恰恰是教养不足者的象征。 所以,在批评荷马和赫西俄德这一点上,克塞诺芬尼恰恰秉承了二者的原则,秉承传统教化的原则而不得不为之事,比克塞诺芬尼稍晚的品达,同样持有激烈反对这种虚妄神话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理解柏拉图对荷马的批评。如果回溯的话,柏拉图的批评一定受惠于克塞诺芬尼的思考,无论是其哲学还是其转向。 克塞诺芬尼的辑语2也相对完整,也有20多行,这首诗嘲讽了希腊传统的竞技体育,但是,他事实上和品达一样,品达通过对竞技比赛胜利的歌颂,鼓励胜利者追求卓越的传统美德,而克塞诺芬尼的讽刺,则针对沉迷体育而不追求美德者。克塞诺芬尼写道,竞技的胜利者固然获得了各种殊荣,但是,即便如此,城邦并不会活得更有良好法度。 城邦没什么值得为此而欣喜, 倘若有谁在皮萨岸边的比赛中赢了的话: 因为这丝毫不会丰裕城邦的根基。⑦ 竞技比赛本来是为了追求美德,追求美德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个人的某种才华,而是为了更有益于城邦的共同福祉。也就是说,通过竞技比赛呈现出的个人美德,令胜利者可以为城邦的“法度”尽自己的卓越之能。这就是克塞诺芬尼使用良好法度一词的含义所在。在希腊的传统政治智慧里,这才是优良的政治生活。质言之,传统的贵族政制所追求的,几乎可以以良好法度一词而道尽。 梭伦当年面对雅典的种种混乱时,为城邦开出的济世良方,便是要以良好的秩序来取代当前的混乱状态: 我遵从内心的命令,提醒雅典人: 多数由混乱所带给我们的灾祸 都可以在良好的秩序下重归和谐: 它会给邪恶的人以约束, 会驯服粗暴,消除肆心,惩戒残忍 铲除刚刚萌芽的愚蠢行为, 它能杜绝欺诈,让自大者变得文雅, 还能制止可恶的派系之争 与势不两立的冲突。一切事物 将在人们当中得到智慧与有序的安排。(辑语3) 在品达的笔下,传统贵族致制之优良,就在于良好的秩序。他曾用此词形容岛屿城邦埃吉纳——在被雅典侵占之前,这是希腊最古老的贵族政制的承续者。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曾对安提诺奥斯说,神明的眼睛环绕着城邦,探查哪些人狂妄,哪些人遵守法度。 而在赫西俄德那里,良好的秩序与正义、和平一样是忒弥斯的孩子。一言以蔽之,良好法度才是人类政治生活得以维持并向往美好生活的政治保护膜。克塞诺芬尼最后使用的根基一词,本意是洞穴或者建筑的最深处,“根基”的译法或许有些强硬,但是对于一个城邦来说,最深处的东西,不是哲学,而是良好的礼法秩序,它才能够为城邦提供最深处的支撑。 克塞诺芬尼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隐匿——而非取消——自己的哲人身份,并敞开自己的诗人面相。他和埃利亚异乡人一样,具有哲学探究的理性,但是,他以诗歌传达自己的教诲。在克塞诺芬尼的教诲里,哲学并不缺席,但他更多的笔墨集中在城邦道德的规劝上。他所采用的诗体,本身就是在时代的潮流下转身向后,他所张扬的,正是与传统诗歌相衬的贵族政制所要求的德性。 ①下文以散文指称哲学性的非诗体写作,这更符合希腊早期的文学类型,与如今学术产业下的论文品质与类型均不可同日而语。 ②参见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G.Most,The Poetic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50. ④辑语8,赵翔译文。文中所引克塞诺芬尼诗歌,希腊文原文和诗歌编号,根据晚近的权威疏本《克塞诺芬尼辑语:文本考订与疏证》(Xenophanes of Colophon:Fragments:a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a Commentary),James Lesher编辑、翻译并疏解,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1年。 ⑤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⑦刘小枫编:《凯若斯——古希腊语文读本》(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标签:哲学论文; 柏拉图论文; 泰勒斯论文; 芬尼论文; 诗歌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赫西俄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