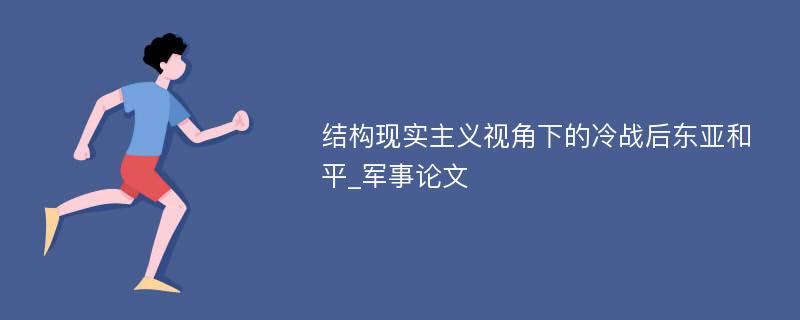
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冷战后东亚地区和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战后论文,视角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06 )06—0049—07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于世界与地区和平的关注似乎更为强烈。在国际政治学界,形形色色探求和平道路的理论或者假设相继出现,如“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等。但是,和平作为人类一直想要达到的目标,却似乎总是很难实现,而且更加难以维护。地区性的战争或冲突仍然接连不断,像中东的巴以对抗,中亚的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非洲的种族争斗,以至两次海湾战争等等。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却保持了相对程度的安宁。虽然学者和政治家一直对这一地区的安全状况表示担忧,但是自1990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以来,整个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新的战争,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和平地区之一。
对于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和平状态,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为全面认识构成本地区政治结构的复杂因素提供了帮助。本文力图对这些理论解释作进一步的辨析,尝试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去分析构建东亚和平的核心与主导因素,并借此对霸权与地区稳定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关于东亚和平的主要理论辨析
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极体系崩溃,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新的态势,国际政治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对这种结构的认识差异引发了对和平主导因素的不同解释。总体来说,大致有以下四种主要的理论观点。
1.伙伴关系互动论
有的学者认为,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逐渐向多极化演进。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出于不同的战略需求,纷纷开始倾向于建立双边伙伴关系,形成中美、中日、中俄、俄日、美日、美俄之间的四方六种双边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特征是:不搞互相敌对和对抗,倡导互相协调和合作,双方互相尊重和平等互利;不针对和不伤害第三国。因此,其互动关系“增强了国家的对话,弱化了对抗,加强了合作,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①。正是这种双边伙伴关系的互动保证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然而,这种观点对于国际政治社会的认识显得过于理想化,而且冷战后东亚的现实状况也与这种伙伴关系互动论不相吻合。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写道:“所有国家都情不自禁地(没有什么国家能够长期不为所动)使自己的特殊期望和行动披上普遍道德目的的外衣”②。他强调,国家在国际政治社会中一定要遵循审慎的原则,抽象的文明社会的道德原则并不适用于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政治家的行为。冠冕堂皇的口号只是混淆对手和公众舆论的工具,国家的行为总是以国家的利益为指导的。
冷战后,大国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也并非单纯是为了实现和平。在现实国际交往中,各国总是以国家利益为行动指南的。因此,伙伴关系背后掩盖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并不完全一致。即使主观上建立伙伴关系的初衷是不搞对抗,我们也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伙伴关系的效果就能维护和平。其中原因很多,突出的一个就是建立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相当于半同盟的形式)有可能增加第三国的安全恐惧。当中国同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发展时,美国出于这种安全恐惧千方百计地想加以干扰。针对中欧之间在用于和平目的的“伽利略”计划中的合作,以及欧盟可能的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美国的抱怨与威胁不断。此外,对于中国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美国更是极尽打压之能事。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称“中国购买先进军事技术会威胁其亚太邻国”③。
东亚地区的安全状况与伙伴关系之间也不是呈对应的关系。众所周知,冷战后东亚地区大国伙伴关系是由少到多逐渐增加的过程,而此地区的安全形势却是呈S状的不断波动。冷战后初期,东亚地区的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结构性的矛盾日益凸显,美国利用其在该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日同盟,加紧遏制中国,再加上该地区存在的一些热点问题,像中日钓鱼岛之争、1996年台海危机等等,使得东亚的局势相对紧张。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有所转移,开始忙于反恐,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所缓和,东亚地区的安全系数又重新回升。
因此,伙伴关系互动论虽然解释了东亚和平的一些原因,但却不能确切反映维持和平的主导性因素。
2.复杂利益牵制论
有的学者认为,冷战后,中、美、日、俄四国构成了6种双边关系和4种三边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形成了相互牵制的作用,使得东亚地区和平相对稳定④。这种观点有点像万能钥匙,因为无论是合作抑或是冲突,我们似乎都能用复杂利益说来解释。如果大国之间进行合作,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它们的复杂利益牵制所致,反之,我们也可以说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复杂利益产生的矛盾所致。而且,复杂利益究竟怎样衡量,怎样界定?似乎也没有科学的计量方法。
19世纪末的欧洲,可谓是欧洲大国复杂利益关系的高峰,当时有德法矛盾,英德矛盾,英法矛盾,俄奥矛盾等等,各国之间的利益复杂异常,相互交错。俄国倾向于为实施对奥作战而进行筹划和准备,而非对德开战,因为前者阻碍了俄国控制连接黑海与地中海海峡的企图。但是法国却只有在击败德国之后才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英国则志在消除德国对其帝国权威的挑战。但这并未阻止欧洲迅速地分裂为两大阵营,进而走向战争。这里主要说的是大国之间的矛盾情况,即使是经济上的复杂利益关系也并不能阻止战争。美国当代国际政治学家查尔斯·库普乾指出:历史记录清楚地说明,即使当国家彼此关系足够融洽使其高水平经济相互依赖得以出现时,它所导致的联系也不是长久和睦的保障。由一体化经济联结起来的国际社会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瓦解,看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十年的欧洲就足以说明问题。欧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而言,一百年前比今天还要多⑤。
同样,当代中东地区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和以色列存在着矛盾,但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共同的民族和宗教掩盖下的是相互之间利益的矛盾和摩擦,所以它们对待巴勒斯坦的政策难以协调也就不难理解。结果是巴勒斯坦在与以色列的敌对和军事冲突中依旧处于劣势,和平的实现似乎遥遥无期。
回到东亚,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冷战时期的东亚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冷战之后。在冷战初期是中美日三国同苏联对抗,新中国成立后则形成了中苏结盟对抗美日,而中苏关系破裂后又出现中美联合来遏制苏联的霸权,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但是到了冷战末期,中苏由对抗走向缓和,进而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中美从1989年“六·四”风波后则从事实上的盟国转变为对手。尽管这段时期东亚地区大国的利益关系错综变幻,互为影响,但是也并未因此而阻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的爆发。
3.非均势核威慑论
一些学者认为,冷战后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之间出现了非均势态势下的核威慑。在非均势态势下,核威慑双方的安全目标是不同的。双方都不追求对等安全。强势一方追求绝对安全,为了扩大安全利益,它宁愿卷入小国之间或它们内部的军事战争或冲突;弱势一方只追求生存安全,为了生存它不再卷入小国之间或它们内部的战争。但是,当强势一方的军事扩张直接威胁到弱势一方的生存安全时,弱势一方仍会以核战争相威慑。这就迫使强势一方采取适度扩张而非无限扩张的政策⑥。持此论者认为,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惟一的军事超强,东亚地区的两极均势格局被打破,中俄在与美国的相互威慑中都是弱势国家,它们的安全目标只是生存安全而非对等安全,因此,它们采取防御性的安全战略。而美国作为强势方,它在东亚的安全目标是追求绝对安全,要进行军事扩张。中俄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扩张都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即只要美国的扩张不直接威胁到它们的生存安全,它们就不会采取军事对抗行动⑦。
这种观点为我们分析冷战后东亚的和平开辟了新的视角,但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它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完美的解释。冷战时期,中国与美国的实力相差甚远,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与美国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均势核威慑,与今天东亚力量对比中的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极其相似。但是,这并不能真正遏止中国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当美国极力向东南亚和东亚扩展势力时,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主动出击,力图在外交和军事两条战线上发挥自己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力。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正是这种企图以弱胜强战略的具体表现,虽然事实上苏联人在这两场战争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考虑到当时美苏之间的对抗主要集中在欧洲,我们还是必须把中国也看作是两次战争的主要当事国。而这些战争正是在中美之间的非均势核威慑的情况下进行的。
4.中美地缘均势论
传统国际政治学理论强调大国间均势的出现有可能维持和平。于是,一些地缘政治学家(主要是西方的学者)据此认为,冷战后东亚地区和平的基础是中美在东亚形成的地缘均势。当然,这些学者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作为大陆强权维护东亚大陆的和平,而美国是海洋强权则维护了东亚海岛国家的安全。东亚国家按地缘关系在中美之间选择一方作为安全依靠对象,如大陆国家朝鲜、韩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乃至俄罗斯选择中国作为依靠对象;而日本、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则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⑧。虽然中美在朝鲜半岛和台海地区有安全利益冲突,但双方在这个地区没有生存性的利益矛盾,因此都愿意保持现状⑨。
这种分析同样存在缺陷。我们知道,韩国与美国存在着现实的军事同盟关系,除非这种关系瓦解,它才有可能寻求其他大国的安全保护。而俄罗斯,虽然处于转型时期矛盾丛生,实力大减,但它的军事实力却未受到削弱,况且在强势总统普京的带领下,一直没有放弃过对复兴大国梦的向往,它本身就是促使世界多极化的一极,总体实力不存在明显差距的俄中两国也不可能形成依赖关系。至于越南虽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作为东盟这个强调独立性(中立性)和大国均衡外交战略的地区组织的成员,其地区集体安全的取向自然不会把中国当成自己惟一的安全屏障。更何况两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还有待解决。可见,地缘均势论者的分析有淡化矛盾的片面性。况且,他们所倡导的均势一说也根本不符合中美两国的现状对比,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远远落后于美国。
从中美两国经济总量上比较,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9,404亿人民币,按8.27∶1的汇率折算,合10,811亿美元;美国的GDP为99,631亿美元。两国当年GDP总量之比为1∶9.22。如果将两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比较,差距更加明显⑩。美国官方对各大国的国力增长预测也显示,未来20年内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对比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据估算,到202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6.4万亿美元,而美国则为22.3万亿美元(11)。
从军事上比较。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保有强大的驻军,在东南亚除维持传统的同盟国关系外,还不断加强与多个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近年又在新加坡获得了现代化的港口作为海军补给基地,并寻求介入马六甲海峡联合防务以及租用越南的金兰湾。而中国只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俄罗斯和几个中亚国家有事实上的军事合作。在军费开支方面,美国是中国的十几倍。早在2002年,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的军费开支不过310至380亿美元(12)。
诚然,均势确实可以避免战争,维持和平。但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和平是相对的,只发生于均势国之间,而且为了争夺利益,这些大国还有可能发动“代理人战争”。事实上,在均势的情况下,世界上局部的战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冷战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明证。即使未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国能够真正与美国在本地区构成势均力敌的态势,也不能假设依靠这种均势可以确保东亚地区的稳定。
二 冷战后美国在东亚霸权地位的确立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排除了苏联的争夺,美国成为目前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现存的东亚地区秩序随之显露出美国霸权的印记。直到今天,这一点仍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是从绝对力量或是相对力量衡量,东亚地区也不会出现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的新兴大国(13)。
总的说来,美国在东亚霸权的确立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美国拥有当前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总体实力,同时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个体市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对美贸易,这一点在东亚表现得特别明显(如表所示)。
东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单位:%)
时间 19801985199019952000
中 国
5.4 8.5 8.2 16.620.9
日 本
24.537.631.727.530.2
韩 国
26.435.629.919.322.0
菲律宾
16.412.816.920.820.5
新加坡
12.521.221.318.317.3
泰 国
27.519.722.717.622.5
马来西亚 27.535.938.035.829.9
资料来源: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2002.
第二,美国在东亚地区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存在。美军在亚太地区共驻有14.91万人,其中陆军5.14万人,编有一个集团军司令部和2个师;空军3.87万人,编有4个航空队部、8个联队(大队)、23个中队,装备飞机338架(作战飞机306架);海军(含陆战队)5.9万人,编有1个舰载机联队、1个陆战队航空联队和1个陆战师,装备飞机390架(作战飞机240架)(14)。其中,3.7万人驻扎在韩国,4.7万驻扎在日本。近10年来,美国的国防费用一般占GDP的比重为3.12%。2003年美国的国防费用已经高达3793亿美元(15)。继2003年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关岛部署64枚ACM—86型战斧巡航导弹之后,美国还计划未来5—10年投资10亿美元完善该基地的海空设施,并计划必要时在此部署一支航空母舰编队(16)。
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对美国这种超强的实力作了清晰的概括:“我们的整体实力是无可争议的。我们的军费开支目前大于其他所有的国家的总和;我们的武器装备比最接近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先进整整一代,我们的军事技术是这样的优越,以致伤亡率之低在科索沃战争中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我们还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将我们的力量投放到全球每一个地区的国家。”(17)
第三,美国在东亚地区构筑了以它为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在冷战的年代,美国为了与苏联相抗衡,在东亚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建立了双边军事同盟关系。虽然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想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但是它在东亚的同盟关系却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是它在东亚存在的一个基石,新日美安保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1999年春夏之交,日本众参两院相继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表明日本为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所需的主要立法基本完成,日美安保体制调整基本结束。在新日美安保体制下,美日防卫合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合作的范围和日本的作用都有所扩大,日本将协助美国共同扮演远东地区警察的角色(18)。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美国将加强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同盟与合作,扩大对东盟地区论坛和其他地区多边合作的参与,积极营造以美国为主导,以双边同盟为基础,以多边安全对话为辅的亚太安全合作框架(19)。
联合军事演习是维系美国与地区盟国关系的重要纽带。单2003年这种大型联合军事演习就达12次。另外,美国于2004年度对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军事教育和培训支出比上个年度增加了30%(20)。
第四,美国在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构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冷战后,美国通过支配一些国际组织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政治霸权和制度霸权地位(21)。借此,美国在东亚事务中扮演了强势参与者及某种程度的操控者角色。比如力图操纵亚太经合组织的议事日程,扩大其在共同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当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倡议成立具有本地区独立色彩的“东亚核心论坛”,立即遭到美国的反对,使建立新型地区合作机制的进程延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由于美国害怕会因此损害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对此也持反对态度,日本只好作罢。东亚的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如果离开美国,解决的难度是相当大的。美国在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三 霸权结构与冷战后东亚和平的维护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leberger)于20世纪70年代在经济领域提出,金德尔伯格认为:“由一个国家主宰的霸权结构,非常有利于强大国际体系的发展,这个体系运行规则比较明确,并且得到很好的遵守……可以预料,霸权结构的衰弱,将是相应的国际经济政治系统实力衰弱的前奏。”(22)
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理论被罗伯特·吉尔平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他认为,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类似经济学上所谓的公共物品。因为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联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单位个体对这种公共物品的一定量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这种物品同量的消费。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那些没有承担供应公共物品责任的个体可以“免费搭车”(free-rider),自动享受别人提供公共物品所能带来的好处。
推及到国际关系中,国际关系领域有三种这样的公共物品,一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开放贸易制度,二是稳定的国际货币,三是国际安全的提供。霸权国有能力并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公共物品,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社会体制,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流通,在某种程度上管理汇率机构,并对各国国内货币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由此获得其他国家认可,维护秩序稳定(24)。
因此,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如果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国家能够并且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物品,如安全、稳定,那么国际体系就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霸权稳定体系与安全稳定之间有一种相关的关系。
奥尔森(Mancur Olson,Jr.)在论述集体行动逻辑时说:“集团越大,就越不会促进共同利益。相反,集团越小,其成员的利益越不平等,其中的某些成员——较大的个体——就越有可能为集体的利益而非仅仅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行为体的相对规模越大,就越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与系统的利益视为一体。”(25) 结构现实主义者接受了这个观点,并且认为,如果不存在极端的情况(如个体吞并整个系统,单元利益和系统利益之间的差别消失),在任何存在着功能相似而能力相异的单元系统中,权力最大的单元将担负起特殊的责任。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东亚的力量对比中取得绝对优势,成为了权力最大的单位。美国愿意为东亚提供诸如安全、经济稳定等公共物品,虽然这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但是,东亚的稳定也符合美国的利益。2000年美国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把美国的全球战略概括为:创造国际安全环境、对威胁和危机作出反应、准备应付将来不测事件,其目的就是要继续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它体现为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经济利益,推行民主、人权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亚太地区的稳定(26)”。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美国还在东亚地区推行所谓的“预防性防御”战略,遏制所有敢于挑战它的权威的国家。
但是,需要注意一点的是,霸权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喜欢使用武力。国际政治结构是一种权力结构,权力更侧重于对它国的影响力。强国往往能够采用其他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或实现自身的意愿,例如说服、劝诱,经济上的讨价还价以及贿赂,提供援助,直至进行武力威慑等,从而使强国必须动用武力的情况比弱国要少(27)。在现代社会里,霸权更加不是经常性的运用压服力量(虽然在某些时候霸权国家也会这么做,比如海湾战争),因为这样会损耗霸权国家的实力。它更多的是运用结构性权力形成或明或暗的世界规范或世界秩序,而其他非霸权国家想要参与国际主流社会就无法摆脱这种影响。即使某些国家在某个结构上可以对美国的霸权有提出异议,但它却无法超越整个体系框架,这也是各国所面临的一个困境(28)。
在现有霸权体系下,东亚各国的最大利益是生存,而不是试图挑战该系统。“对危险和灭亡的强烈意识,将导致国家对它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作出清晰的界定。”国际政治结构对服从该体系的行为加以鼓励,对那些背道而驰的行为则加以惩罚。这种结构的约束作用不会因人的意愿而消失,尽管许多人对此无法理解(29)。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与美国相比,明显地处于弱势,如果想要推行“均势”战略去平衡美国的霸权,自然存在着遭遇惩罚的危险。同样,如果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破坏了和平,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会导致美国的干涉或是制裁。既然美国为东亚的安全与繁荣提供了一些公共物品,在结构性的压力下,东亚国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搭便车”,而不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挑战霸权的权威。
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宣称:“尽管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对我们的价值观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他们同时是我们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最主要的支持者。”(30) 一些美国军事专家也认为,“尽管存在着不同意见,美国军事存在仍然受欢迎。在亚洲有许多人相信,美国军事存在可以阻止新兴的大国对东亚大陆和通过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线的控制……同时,有许多人不会忘记日本在历史上的作为……虽然美国的许多朋友和盟友不会公开谈论美国在日本的存在阻止了它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但是却感谢美国在东北亚驻军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当中国公开声明反对军队驻扎在外国领土是它的一项原则时,中国领导人私下也承认,美国在日本的存在是一种阻止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行为,同时,他们私下也承认,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半岛的存在有利于半岛的稳定。”(31) 虽然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敢完全苟同,但是它毕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东西。
结语
冷战结束这十多年来,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在今后20年内,美国的实力仍然是其他大国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正是美国在东亚的强势存在维持了冷战后这一地区相对程度的和平。但是,也要看到,东亚地区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热点问题,像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以及台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东亚和平的隐患,它们的解决不仅与霸权国有关,而且牵涉到这一地区的崛起国,特别是中国的意图。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的战略意图也与霸权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可以把这种意图看作是霸权稳定的补充变量。因为这种意图,无论是对霸权的挑战还是合作,都直接影响到东亚的和平。虽然国家意图不好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行为来推测。中国在冷战后积极参加了世界上的各种国际组织,不管是政府间的,还是非政府的。而且,在东亚的一系列地区问题特别是反恐问题上,中国是美国的合作者。这表明中国是当前秩序的维护者,是要参与建设,而不是颠覆或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不是对东亚和平的威胁。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2003年12月10日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的和平理念: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的崛起的道路(32)。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4月中美峰会上也特别强调,中国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持久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在未来20年内,中国最大的利益是充分利用当前霸权结构的稳定因素完成国家现代化,而不是像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那样挑战霸权。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不发生不可预测的重大突发事件,国际政治结构不发生重大改变,东亚地区在霸权结构下的稳定还会持续下去。
[收稿日期]2006—11—17
注释:
① 孙建设:《亚太大国“伙伴关系”的互动性和不对称性》,《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8期。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杨歧鸣等译《国家间政治》,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③ George W.Bush,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17,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c8.htm.1
④ 〈日〉宫本信生:《东亚的安全与威胁——不协调的‘日美中俄’四重奏》,《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3期,转引自《国际政治》,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2001年第6期。
⑤ 〈美〉查尔斯·库普乾,潘忠歧译《美国时代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2—123页。
⑥ 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10页。
⑦ 同上,第11页。
⑧ Robert S.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4,Spring 1999,pp.82—86.
⑨ Ibid,pp.111—114.
⑩ 王志平:《中美经济“数字比较”及其启示》,《经济师》,2001年第10期。
(11) 美国国防部2006年《中国军力报告》,引自牛新春《中美关系的新特点:平衡、稳定、竞争》,《和平与发展》,2006年第3期。
(12) 叶自成:《中国迈向世界大国之路》,《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美国兰德公司:《中国军事现代化:机会与制约》,2005年5月,转引自张林宏《评析美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和平与发展》,2005年第4期。
(13) 宋国友:《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与美国霸权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14) http://www.china817.com/home/list.asp?id=1354
(15) 柳剑平、刘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的成本比分析》,《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
(16) 贾曦:《美国亚太军事力量调整的特点、原因及影响》,《和平与发展》,2005年第4期。
(17) Samuel R.Berger,American Power:Hegemony,Isolationism orEngagement,speaking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on October 21,1999,转引自倪峰《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02年第7期。
(18) 杨成绪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透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60页。
(19) 同上,第70页。
(20) 贾曦:《美国亚太军事力量调整的特点、原因及影响》,《和平与发展》,2005年第4期。
(21) 颜剑英,周志武:《浅议美国政治霸权主义》,《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2)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23) 苏长河: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24) 冯艳君:《霸权稳定论和美国的新霸权主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5)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26) 参阅《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美新署2000年1月5日电。
(27)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28) 戴平辉:《结构性权力下的美国霸权》,《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1期。
(29)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1—145页。
(30) 倪峰:《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02年第7期。
(31) Robert H.Scales.Jr and Larry M.Wortzel,The Futur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Landpower and Geostrategy of American Commitment,April 6,1999,p.4,转引自倪峰《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02年第7期。
(32) 新华网2004年3月12日,转引自李文《中国的和平崛起何以能与何以为》,《当代亚太》,2004年第5期。
标签: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公共物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