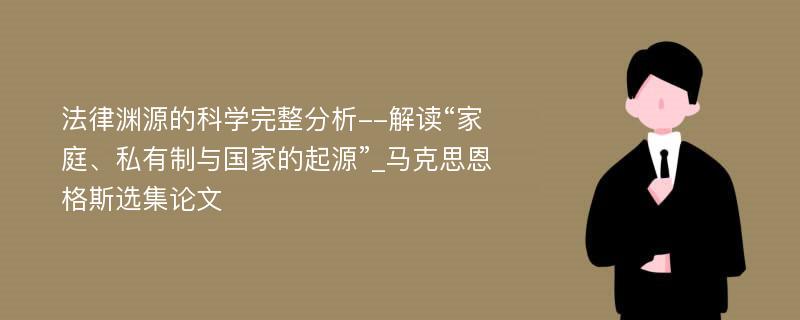
科学完整地阐析法律起源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私有制论文,札记论文,完整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0766(1999)06-0019-04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这些历史唯心主义者不可能对法律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
相反,恩格斯则是以唯物史观研究法律起源问题。他在《论住宅问题》中作出了如下著名论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这段经典论述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共同规则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所必需。任何社会要生存下去都必须一刻不停地进行生产,以及相应的分配和交换的活动,并使个人服从这种生产、分配和交换的一般条件。为此,就要有共同的规则对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加以调整。于是为维持社会存在而必须进行的经济活动,便成为共同规则产生的前提和客观要求。其二,共同规则来自对经济活动中重复行为的抽象。每日每时,从不间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行为,首先表现为个别、具体、重复的行为。与无数这种个别行为相适应的,是仅有个别社会调整意义的规则。但同时,这种生产行为又“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页。)所以,这种重复的行为天长日久,必然逐渐地被抽象为一般的、概括的行为规则,即具有一般社会调整意义的规则。这些行为规则日后又一步步地得到固定,最终形成了模式化的共同规则。其三,共同规则的形成,经历了从习惯到法律的过程。固定的、模式化的共同规则,开始是表现为习惯。习惯作为人类社会的生活惯例和行为标准,是原始社会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人们长期沿袭下来的以及自然地、逐渐地养成的,是人们共知、共信、共行的结果。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习惯又发展为习惯法即最早的法律。其四,与法律产生的同时,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力即国家。在更晚的时期,由于国家立法机关的出现,文字的发达,法律又发展为或多或少的成文习惯法,再进一步便是制定法。通过以上概括不难看出,在这段简短而深刻的论述中,恩格斯以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深透洞察力,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表达了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
但是,无庸讳言,这段概括性的论述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阐发。最明显的是:表现为共同规则的习惯产生于“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究竟指哪个阶段?“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法律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二者的内在必然联系是什么?等等。
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们仍否认原始社会的历史,认为凡缺少具体实证材料的地方就没有历史,只有“史前时期”。“这个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岂只如此,甚至作为整体的历史科学还处于摩西五经的阴影下,被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所笼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页。)。稍后,一批学者们相继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而大大开阔了人们对原始社会某些领域认识的视野。尽管如此,十分有限的成果还不足以使人们对原始社会总体的认识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此,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原始社会经济活动的分析,主要还是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阐述的那些经济学原理。由此可见,尽管恩格斯对涉及法律起源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他当时对原始社会历史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进而也就决定了此时恩格斯有关国家与法律起源的思想尚处于变动不居的过渡的状态。前面说到的若干存疑,也来源于此。
1877年美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历经40年之久对印第安易洛魁氏族制度的亲身考察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撰写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古代社会》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并且在保持时间最长的母系氏族制度下是没有任何人奴役人的现象存在的,氏族社会才真正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打开希腊、罗马上古史的哑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还由此开辟了研究原始社会的新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面对这个使人耳目一新的科学成就,马克思便暂时中断了几乎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对《古代社会》进行深入地批判、思考和借鉴,写下了厚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在该《摘要》的基础上,同时以自己对原始社会和古代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为根据,认真审视并弥补了《古代社会》的某些缺陷,撰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考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过程中,对与之紧密相连的法律的起源问题,集中表述了一系列深刻的新见解,并对以前的存疑做了明确的解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科学完整地阐述了法律起源问题
恩格斯以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为主要依据,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法律起源问题作了符合实际的科学系统的阐述。国家和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依据史前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具体的实际材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不知国家和法为何物的社会。法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它是氏族习俗的延续和变革,是私有制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和法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阶级的完全消灭,国家和法也就失去存在的条件,将自行消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解答了《论住宅问题》中关于法律起源的那段论述所包涵的几点主要的存疑:
1.“某个很早的阶段”和“后来”所指的时间。
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可以看出,“某个很早的阶段”显然指的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阶段。按照摩尔根的分期法,这应属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若按现代史学界的一般分期法,这一阶段应是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如同恩格斯所说:“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因此,这时还不可能有重复的、经常的交换行为,只有当畜牧部落出现,并从野蛮人中分离出来之后,形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具备“经济交换的条件”,方才有经常的交换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
“后来便成了法律”,这里的“后来”,需要从这段论述所讲的法律产生的政治特征,即“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的出现来判断。关于公共权力或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一个不从事生产而专营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从而使人类“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
2.经济关系究竟如何决定习惯质变为法律。
与10余年前写作《论住宅问题》时的情景不同,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再次谈及古雅典和古罗马法律产生原因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古雅典和古罗马这两种立法,都是纯粹由于经济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3页。)这里的“经济强制”的提法,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它指的是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末期,雅典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由债权债务关系引发的富有的债权人对贫穷的债务人,强制实行以当事人的人身和他的妻及子女作为债务抵押和偿还的一种奴役制。可见,“经济强制”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对此,恩格斯引述马克思在《摘要》中的一些论断作了分析。他说,正是由于“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正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才使氏族制度的机关“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与这一变革相适应,反映氏族成员平等关系及“权利与义务没有任何差别”的习惯,也就必然要质变为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习惯法。
3.“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关于法律和国家产生的基本思想是:法律和国家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基于同一根源和动因,并且始终相互作用,而同步产生的。提修斯为解决氏族同族共居与不同氏族成员杂居的矛盾,在雅典设立中央管理机关,把从前由各部落处理的事务移交给这一机关管辖。这样便开创不以氏族组织和血缘关系,而以地区和财产来划分、管理居民及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先例,显示出雅典国家的雏型。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雅典民族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6页。)提修斯改革后,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为适应这种趋势,梭伦又颁布《土地最大限度法》、《解负令》等一系列法令。最后,克里斯梯尼又顺乎时势,实行旨在消灭氏族贵族残余的整套改革,这既促使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也促使《贝壳放逐法》等法律的制定和颁行。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还结合上述雅典国家和法律产生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二者何以共生的原因,也就是分析了法律的产生与公共权力出现的联系。他说,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就需要有区别于先前军事民主主义时期那种真正公共权力的“特殊的公共权力”,而官吏则掌握着这种公共权力并凌驾于社会之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于是,官吏们就不满足于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和自愿的尊敬。诚如恩格斯指出的,“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这里的“特别的法律”与“特殊的公共权力”(国家),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一方面,“特别的法律”必须以“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掌握着“特殊的公共权力”的官吏们,又需要通过“特别的法律”来维护自身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标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法律论文; 恩格斯论文; 科学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古代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