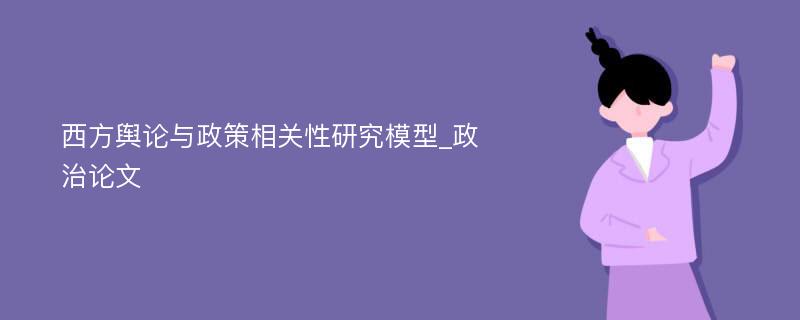
西方民意与政策相关性研究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关性论文,民意论文,模型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08)08-0186-04
民意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18世纪法国的卢梭首次提出了公众意见即民意(Opinino publique)的概念,自此,西方对于民意的研究逐渐展开。19世纪初期,政治学家开始探讨民意的本质和功能,发掘民意与社会控制、民意与法律、民意与威权、民意与政府的关系。然而,分析和判断民意在不同政治环境下对于不同政策所起到的作用与角色,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决策和民意始终处于一种复杂的动态互动的过程之中。依雷尼·B.夏普和鲁贝格在其研究中设立了民意与社会政策的相关性模型,对民意与政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诠释与探讨。
一、民意与社会政策的相关性模型
依雷尼·B.夏普(Elaine B.Sharp)在其1999年出版的《民意与社会政策的相关联系》(The Sometime Connection-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Policy)中对民意与政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概括了民意与政策发生联系的四种可能性模型:
(一)无态度:民意—政策的不相关性模型
民意—政策的不相关性模型所要表达的是民意与政策是不相干的,这是因为通过民意测验数据估定的民意是不真实或没有意义的。它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普通民众的反应和意见很容易被政治精英操纵,二是民众对候选人和重大事件的反应并不是在认识基础上作出的。态度通常被定义为“对某一特定目标的相对持久的认识”,而显示在民意选举中的意见则表面上是“态度的可见显示”。真实的态度和态度中表明的意见是相对持久的,因为其既包含认识因素(知识)也包含情感因素(价值观)。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挣得收入税收贷款”(EITC),那他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真实的态度。而对一个目标没有真实态度,必然妨碍人们在面对民意测验问题时作出回答。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或者他们对这个话题毫不关心,或者因为他们愿意表现合作所以民意测验者可以很快结束,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民意测验的受测者可能会作出与相关事实和价值观无关的无意义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无态度”。
概括说来,至少有三种证据可以为民意充满了无态度的观点增添说服力,即态度随时间表现出的不稳定性、民意缺少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以及民意测验所表现的民意很容易改变或被操纵。另外,还可以加上民众对公共事务缺乏兴趣和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定与公众偏好相符的政策是没有必要的。当这种偏好显示在选票中时,将被视为迅速消失的而且不宜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并且,以解决问题和有效治理为目标的官员根本不会考虑试图与这些意见相符。
(二)决策者操纵民意模型
与民意协调的政策要求公共政策在最低限度上同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意见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是政策与民意协调的足够的基础,这是因为民意和政策的一致性也可以通过政策制定者塑造民意使其与政策一致达成,而不是通过政策顺从民意而达成。这种民众的“事后”同意可能会满足一些民主理论的要求,但是它并不标志政策的民意协调性。而且尽管通过使用褒义词如“领导”等,政治精英影响民意的做法可以被积极地看待,许多学者还是指出了这种模型的许多危险方面。从最消极的角度看,像“蛊惑民心”和“政治煽动”等词汇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并且通过影响民意来构建民意和政策的一致并不比广告人通过精心策划吸引消费者高明多少。但是至少这一模型表明民意被政治精英“操纵”了,“操纵”这个词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理解空间。
在这一领域最具批判性的分析者是金斯堡(Ginsberg),他认为当前统治者所留意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国家政府本身造成的,并且它们的影响持续存在。金斯堡强调现代社会在运用公共关系技巧时非常老练,民意已经被民意测验的体制化驯服了,因此,政府可以控制、操纵并利用公众的意见。
这种模型所显示的是政府的精英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来影响民众的观点,同时民众的观点也往往很容易受到这种引导。对民意的控制体现在教育民众与操纵民众两个方面。前者是给予参与者一种充分的选择自由。而后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给予民众大量的误导性的信息,最终民众的意见受到诱导并作出对自身利益可能有害的选择。
(三)无响应:公共政策与民意反映不一致模型
在代议制民主社会中,很多情形下,政府的最终决策与民意的反映并无关联。这是由于政府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考虑民众的各种具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在有些情况下,政府所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甚至与民众的偏好相反。然而,在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有时不得不对民众的要求有所牺牲。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民众的要求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得到满足的。比如,民众总想缴纳更少的税金而得到更多的政府服务。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和民意发生背离也就不足为怪。
事实上,在公共政策与民意反映不一致的情况下,受控制的民意模型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反映出这种张力情况。但是,考虑到政府最后会操控民众的意见以便使其和政府的决策一致,因此,只要政府能够采用恰当的手段来教育民众,那么这种公共政策与民意反映不一致的状况就很有可能得到改善。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利益与民众的意见是不能相互协调的。虽然民众可以通过民意表达来将其愿望施加于政府的精英决策,政府的决策者也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迎合民众民意的需要,但是,即便如此,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仍然会出现不考虑民众意愿而强行推行政府决策的、不对民意进行响应的政治模型。
(四)响应模型
响应模型反映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受民意的影响或者与民意的偏好呈现一致,即民众的意见最终构成政府决策的幅度范围,民意是政府决策的重要的约束因素,而不像一般机构对政府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有两个因素对于政策的响应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是制定公共政策机构的换届选举;二是现任官员为了避免在新的选举中被击败的理性预期,特别是像美国总统在大选的时候都会注意如何去迎合民意。
然而,即便是在民意与政府决策十分吻合,这种吻合也极有可能是虚伪的现象。换言之,有时这种吻合只是碰巧发生,因为无论政府决策还是民意都需要与社会的大趋势相符合,而并不是一方影响另一方;这种吻合甚至有可能是政府精英对民意塑造的结果。
依雷尼·B.夏普认为,在概念的层面上,政策与民意之间相互影响的模型的建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大众的民意不受精英的影响与引导,以及精英不考虑大众民意而制定政策这种特别理想的状态。不管是响应的模型,还是受控制的模型都不可能完全去除这两个相互影响的变量。在很多情况下,相互影响的模型和响应的模型之间的差别是很微小的。依雷尼·B.夏普认为,民意与政策的相互影响并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模型体系。这是由于,目前除了按照经验主义对民意和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外,并没有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应当采用一种动态的而不是代表性的模型来研究民意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动态的研究方法下,需要有更多的对于政策的历史性描述以及与政策相关的能够反映民意的数据。而这种动态的、极为精密的、民意与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模型的建立就目前而言似乎还不太可行。
二、民意影响公共政策的模型
在民主国家,民意被认为是可以影响公共决策的。然而,民意与公共政策的联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鲁贝格(Norman Luttbeg)在其1968年出版的名为《大社会的政治联系》的论著中建立了六种民意与政策的动态模式。
(一)参与者模式(Participant Model)
在参与者模式的政治联系中,没有领导者,人人参与决策。民众自己对自己表达需要,自己制定并执行政策,后果也由自己承担。除了马克思所设想的无阶级以外,现实社会不可能具有这种功能。但参与者模式似乎可以解释系统功能失调时的特殊状况,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或1960年末期美国的反战示威等。在这两个状况中,民众未必实际参与,但是在心理上被波及,具体表现在民众对局势发展结果的关切。
(二)理性行动模式(Rational- Activist Model)
理性行动模式与美国开国政治哲学家提出的分权制度至为契合。在这种模式中,民众被假定为都是消息灵通、对公共事务具有理性以及参与兴趣的人。民众可以通过投票来表达他们政策上的喜好即选择候选人;当选的执政者因为害怕被民众投票推翻,所以也必须制定符合民意的政策。事实上,政治理性人难得一见,尤其是在选民缺乏参与政党政治的兴趣的社会环境中。
(三)政党模式(Political Parties Model)
英国的议会政治颇能反映这种模式。政党模式实际上是由两个理性行动模式联结起来:一是民众和政党,一是政党与决策者。这种模式显然比前两种模式更接近实际状况,因为它提供了运作的基础。一般而言,由于民众的知识程度有限,因此不可太能期望他们对政府的决策作直接判断和施加具体的影响。而政党一方面可以直接与民众联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协助决策者制定政纲,将民众无定形的要求转为具体的可行办法。此模型的缺点是忽略了一个事实:民众除了投票之外不太可能操纵政党,政党则可以利用提名支持来操纵决策者。如果政党干部有违反政纲的行为,决策者可能会碍于其提名权而不加追究,这实际上也会导致违反民意的结果。
(四)压力团体模式(Pressure Groups Model)
压力团体模式从团体理论衍生而来,将决策视为各竞争团体势力的持续互动。对于某一既有问题,竞争团体纷纷出面,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因而政策的结果与利益团体的大小、组织和效率有直接关系。
(五)共享模式(Sharing Model)
共享模式假设在同性质社会里,民众与决策者的意见和利益一致,民众及决策者在政策上的偏好也一致,政治参与的实质或方式并不重要。由于民众与决策者共享同样的价值观及政府目标,因而选举也是非竞争性的。总之,在这个系统中,结构的运作是没有压迫性的,人际关系是融洽的,但在现实环境中这种模型是很难找到的。
(六)角色模式(Role Model)
在角色模式所假设的社会中,决策者的决定是完全遵照选民的意见行事,民众的任务就是谅解并选举能听命于他们的角色。由于决策者仅为民众的代理,因而他不能作独立判断;而民众必须保持消息灵通,具有高度的判断力,才能确保他们所选择的角色忠诚。
由于和谐一致只存在于理想的民主原则之中,因而共享模式与角色模式均难以站得住脚。
三、民意与公共政策的吻合程度分析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托马斯·R.戴伊(Thomas R.Dye)在其2002年出版的著作《理解公共政策》中谈到:民意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早在经典民主理论中就已成为颇有争议的主题。18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埃得蒙德·伯克认为,在决定公共政策的问题时,民主的代议者应该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埃得蒙德·伯克看来,民意是否应当成为影响公共政策重要和独立的力量,这一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回答,但是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回答在实践中民意是否会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独立的影响这一问题。
在评估民意对决策制定者的独立影响时,关键问题是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是否有助于形成民意。公共政策应当和民意相一致,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究竟是民意塑造了公共政策,还是公共政策塑造了民意。
美国著名政治家小V.O.凯伊的著作《民意与美国民主》中写道:“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政府努力去塑造民意,为他们所倡导的政策寻求支持。如果这一努力存在的话,公共政策与民意交叠的就应该表达为体现民意的政府,而不是民意形成的政府。”虽然凯伊本人也坚信民意确实对公共政策具有独立的影响,但是他不能有力地证明这个观点。
而托马斯·R.戴伊认为,公共政策塑造民意比民意影响公共政策的情形更多一些。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除了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之外,几乎很少有人对大量的政策问题有自己的主见。其次,民意非常不稳定,它会随着诸多突发事件的产生而发生改变。第三,决策制定者对民意往往缺乏清晰的认知。大部分决策制定者接收到的沟通信息来自其他精英——新闻工作者、利益集团的领导者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而并非来自普通民众。因此,托马斯·R.戴伊认为,公共政策的过程并不总是能够符合人们的意愿。同时,政治利益主体会根据自己的目的,接收、拒绝或者利用这些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08-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