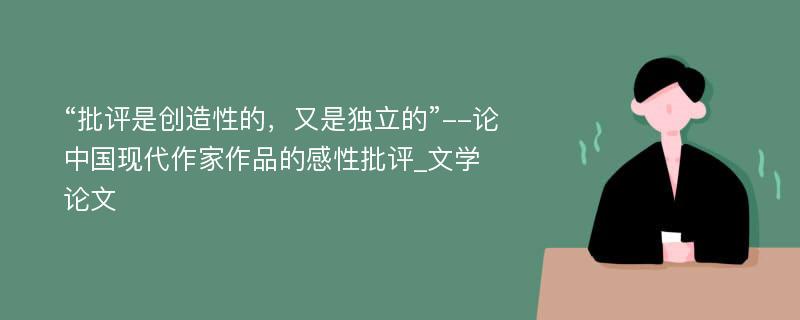
“实际上评论既具有创造性也具有独立性”——论感悟式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立性论文,中国论文,性也论文,批评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3)05-0025-08
在中国新文学诞生与发展过程中,最初对于现代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感悟式批评的特征,在介绍与评论现代作家与其创作中,表现出批评家各自不同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为数众多的批评者中,沈雁冰、李健吾、李长之、沈从文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批评取向与批评方法,在感悟式的批评中开拓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
一、沈雁冰:“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
沈雁冰是以文学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他倡导为人生写实的艺术,受到丹纳的社会学批评理论的影响,沈雁冰的文学批评具有从时代、社会的背景观照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价值的特征,他强调“文学是时代的反映,社会背景的图画”[1](P171),强调文学创作为人生的意义。受到左拉的自然主义的影响,早期的沈雁冰有着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的状况。他以进化的文学观观照文学,认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2]从总体上观之,沈雁冰常常以敏锐的眼光、理性的观察批评新文学的创作,在宏观的文学形势的分析中,在微观的作家作品的研究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沈雁冰就密切关注着新文学创作的动向,发表了诸多宏观批评的文章,在《春季创作坛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创造>给我的印象》、《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中,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提出了诸多具体切实的批评。1921年沈雁冰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对于当年三个月中发表的120多篇小说做了综合性分析,指出“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的现象,批评作家对于城市劳动者的隔膜,“对于社会上各种问题还不能提起精神注意”,以及“强烈的享乐主义的倾向”。批评恋爱小说写法相同、人物相似,缺乏对于人生经验的体察,“是模拟的伪品”。并指出“描写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显然和劳动者的实际生活不符”。在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中,却“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了”。文章特别推崇鲁迅的《故乡》“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3]。1922年沈雁冰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他将中国现代小说分为新旧两派,在分析了旧派小说在思想与艺术上的弊端后,反对“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他还提到新派小说的弊病:“现在的青年作者大都犯了对话不毕肖的毛病。其次,往往掺杂着许多作者主观的心理,弄得非驴非马。第三,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凭空想像出一些人事来迁就他的本意,目的只是把胸中的话畅畅快快吐出来便了;结果思想上虽或可说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4]他提出以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和实地观察弥补小说描写缺乏客观态度、取材缺乏目的性的不足。1923年沈雁冰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中对于当时文坛吟风弄月的唯美倾向的产生做了分析,认为是近年来政治的愈趋黑暗,人们想在“所谓唯美主义的文学里求得写精神上的快慰,或求得灵魂的归宿”,是中了中国名士狂放脱略思想的毒,认为“在酷好空想的美的文学的作家,并未产生实在伟大的值得赞美的作品”[5]。沈雁冰的宏观批评,能够敏锐地分析文学创作的动向,在肯定创作实绩中批评创作中的不良倾向,并努力从宏观的背景中发掘其原因,寻找改变创作现状的路向,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自1923年发表了《读<呐喊>》后,1927年沈雁冰又发表了《鲁迅论》,1928年又发表了《王鲁彦论》,30年代他接连发表了《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落花生论》等颇有影响的作家论,以其全面的观察、精到的评说展现出其理论家的风貌。沈雁冰的作家论以其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观评论作家的创作,尤其注重将作家作品置于时代的背景中予以评说。
在对于作家创作的评论中,沈雁冰注重对于创作主旨和社会学意义的分析把握。他概括鲁迅小说“大都是描写‘老中国儿女’的思想和生活”,“这些‘老中国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6]。他评论王鲁彦的创作,指出:“王鲁彦小说里最可爱的人物,在我看来,是一些乡村的小资产阶级”,“我总觉得他们和鲁迅作品里的人物有些差别: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的儿女,而前者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7]。他评说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认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认为志摩的诗歌“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8]。他评说庐隐时强调她是“五四”的产儿,“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9]。他评价冰心的创作,关注冰心的“爱的哲学”,在谈及冰心“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时,指出:“她既已注视现实了,她既提出问题了,她并且企图给个解答,然而由她生活所产生的她那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末了,她只好从‘问题’面前逃走了,‘心中的风雨来了’时,她躲到‘母亲的怀里’了……”[10]。他评说许地山的创作,认为:“他虽然最喜欢用‘异域情调’的材料,可是他在那些小说里是要给一个他所认为‘合理’的人生观;他并没建造了什么‘理想’的象牙塔,自己躲在里面唱赞美歌。不过他的人生观是多少带点怀疑论的色彩罢了。”[11]在作家论中,沈雁冰常常努力梳理作家创作轨迹,在知人论世式的评说中道出所评作家创作的特征,揭示在时代影响下作家创作的发展变化,并客观地评说作家创作的长与短。
在对于作家创作的评论中,沈雁冰常常也以其敏锐的视角与独到的艺术感悟,对于所评论作家的创作风格、艺术特色等作简约评点,在寥寥数语中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在评说鲁迅的小说时,沈雁冰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12]在评论王鲁彦的创作时,沈雁冰指出“我以为这种焦灼苦闷的情调是贯彻在王鲁彦的全体作品内的”,并说“在描写手腕方面,自然和朴素,是作者的卓特的面目”,还道出其“最大的毛病是人物的对话常常不合该人身份似的太欧化了太通文了些”。[7]在评论庐隐的小说时,他指出:“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技巧上炫奇斗巧。她的前期作品(包括《海滨故人》及《曼丽》),结构比较散漫;……她的后期的作品如《归雁》和《女人的心》就进步得多了。”[9]在评说丁玲的小说创作时,沈雁冰指出:“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颂赞,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与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3]在对于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评说中,沈雁冰指出:“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14](P109)他指出许地山的创作具有异域情调的浪漫主义、颠沛生活描写的写实主义两种形式,并指出“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14](P114)
沈雁冰对于新文学的批评,具有开阔的视野、深刻的见地,理性的分析、细致的梳理、独到的感悟等,都使他的新文学批评具有深入思辨的魅力。对于文学创作为人生主旨的过于看重,对于文学创作艺术形式的相对忽略,使其新文学批评又呈现出重内容而轻形式的不足。
二、李健吾:“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以刘西渭为笔名发表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先后结集为《咀华集》、《咀华二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深受法国文学熏陶的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被认为是一种印象式批评,西方的文学批评家阿诺德、法郎士、王尔德、蒙田等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他谈到文学批评时引用法郎士的话:“犹如哲学和历史,批评是明敏和好奇的才智之士使用的一种小说,而所有的小说,往正确看,是一部自传。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15](P138)在他的文学批评中,艺术家的灵魂在杰作中畅游与冒险,努力真切地表述他在杰作之间畅游的奇遇与感想。他并不注重对于创作的审判,而强调对于作品的感悟。他说:“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锻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16](P156)李健吾尤其追求批评的艺术性,他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在文学世界里游历,强调自由的、公正的、真诚的批评,他将批评看作是一个富有人性的独立存在,在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中,表达他对于艺术美的发现与感受。《咀华集》共有17篇文章,被批评的作者有十一二个,这些作家除巴金外,其余都是当时不被社会文艺界人们所注意的。李健吾谈到文学批评时说:“批评者注意大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他更注意无名,唯恐他们遭受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17](P159)李健吾批评的作家有巴金、沈从文、废名、罗皑岚、林徽因、萧乾、蹇先艾、曹禺、卞之琳、叶紫、萧军、李广田、罗淑、徐志摩、何其芳、张天翼、芦焚等,他对于介绍推荐青年作家及其创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以其独具的才情,注重评说作家的艺术特点与风格,显示出其印象式批评的生动与独到。他赞同这样的方式,“分析一首诗好像把一朵花揉成片片。冷静下头脑去理解,潜下心去体味”[16](P158)。李健吾就是如此潜心研究文学的。他评说巴金《爱情三部曲》的特点:“他生活在热情里面。热情做成他叙述的流畅。你可以想像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气势。在这二者之间,巴金的文笔似乎属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18](P11)他将巴金与茅盾作比较:“茅盾先生拙于措辞,因为他沿路随手捡拾;巴金先生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先生冷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用叙事抵补描写的缺陷。”[18](P11)恰如其分地道出巴金创作的风格及其长与短。他甚至说:“读茅盾先生的文章,我们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底下也有的是绊脚的石子;读巴金先生的文章,我们像泛舟,顺流而下,有时连你收帆停驶的工夫也不给。”[15](P138)在比较中说出其在杰作中探险的独特感受。他评说废名小说的独特:“唯其善感多能,他所再生出来的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留连忘返的桃源。《竹林的故事》的问世,虽说已经十有一载,然而即使今日批阅,我们依旧感到它描绘的简洁,情趣的雅致,和它文笔的精练。”[19](P144)将废名创作的特性与价值简约道出。他评论沈从文的《边城》说:“《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20](P58)他还说:“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20](P55)李健吾以细腻独到的艺术感受,将沈从文小说的特色真切地道出,令人赞叹。他谈论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那样浅,那样淡,却那样厚,那样淳,你几乎不得不相信诗人已经钻进言语,把握它那永久的部分。……言语无所谓俗雅,文字无所谓新旧,凡一切经过他们的想像,弹起深湛的共鸣,引起他们灵魂颤动的,全是他们所伫候的谐和。他们要把文字和言语揉成一片,扩展他们想像的园地,根据独有的特殊感觉,解释各自现时的生命。”[21](P107)细致深入地分析卞之琳诗歌的特点,把自己的感受与体会细细道出。他谈论蹇先艾小说的特点:“他有的是个人的情调,然而他用措辞删掉他的浮华,让你觉不出感伤的沉重,尽量去接纳他柔脆的心灵。这颗心灵,不贪得,不就易,不高蹈,不卑污,老实而又那样忠实,看似没有力量,待雨打风吹经年之后,不凋落,不褪色,人人花一般地残零,这颗心灵依然持有他的本色。”[22](P87)他以纤敏的笔触将作家的特点条分缕析娓娓说来,让读者不知不觉地进入其描绘的艺术境界里。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以其坦诚的姿态,注重从审美的视角评说创作的艺术价值,显示出其直观性鉴赏的灵动与蕴蓄。他说:“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的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这不仅是出于礼貌,也是理之当然。”[18](P2)李健吾以一种文学鉴赏的眼光评析作家的创作,强调其在艺术上的价值与特色。他评说废名的意义:“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没有一位更像废名先生引我好奇,更深刻地把我引来观察他的转变的。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自己的。凡他写出来的,多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假定创造不是抄袭。”[19](P144)他强调废名创作独特的个性与价值。他评价乡土作家蹇先艾的意义:“蹇先生发现了自己,他离开他的身边,走回他的故乡——贵州。在我们今日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里面,他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位。”[22](P89)他谈及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23](P67)以鉴赏的笔触表达其对于作品阅读的感受,表现出生动直观的意味。他评价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但是这里的文字那样单纯,情感那样凝练,诗面呈浮的是不在意,暗地却埋着说不尽的悲哀,我们唯有赞美诗人表现的经济或者精致,或者用个传统的字眼儿,把诗人归入我们民族的大流,说做含蓄,蕴藉。”[21](P113)以中国古典诗学色彩的词语评说卞之琳的诗歌,贴切中肯,鞭辟入里。他在评说巴金的小说《神·鬼·人》时说:“所以,像巴金先生那样的小说家,不幸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满腔热血,不能从行动上得到自由,转而从文字上图谋精神上的解放。甚至于有时在小说里面,好像一匹不羁之马,他们宁可牺牲艺术的完美,来满足各自人性的动向。”[24](P48)由表及里的深入评析简约深刻,切中肯綮。他评论萧乾的小说:“他会把叙述和语言绘成一片异样新绿的景象;他会把孩子的感受和他的描写织成一幅自然的锦霞。坏的时节,你觉得他好不娇嫩!然而即使娇嫩,你明白这有一天会长成壮实的树木。他的文笔充满了希望。”[25](P85)指出萧乾创作的追求与未来。他评说沈从文的创作:“例如巴尔扎克(Balzac)是个小说家,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严格而论,不是一个艺术家,更遑论乎伟大的艺术家。……然而福楼拜,却是艺术家的小说家。……沈从文先生便是这样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乔治桑是一个热情的人,然而博爱为怀,不唯抒情,而且说教。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20](P54-55)将沈从文定为不说教、抒情的、诗的艺术家的小说家,在指出沈从文的特点中道出其独特的价值。李健吾执著地从艺术审美的视角评说作家及其创作,以充满机智与诗意的笔触评论作家及其创作的特点与意义,以其丰富的外国文学的学识观照所评论的中国现代作家,常常在比照中突出所评论作家的特征与风格,以精辟而生动的评说把握住所评论对象的特色。
李健吾在谈到文学批评时说:“我多走进杰作一步,我的心灵多经一次洗练,我的智慧多经一次启迪:在一个相似而异的世界旅行,我多长了一番见识。”[18](P4)他将对于杰作的评论视为“在一个相似而异的世界旅行”,看作是心灵的洗练。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以其感悟性的印象式批评,以其文笔的灵动洒脱表达其对于所评论对象的独到感受,以其注重文学审美批评的视角发现批评对象的独特价值,常常以其独具的慧眼发现与彰显诸多无名作者与作品,虽然他的含蓄蕴藉的印象式批评缺乏明晰的理论深度,但是他从审美的视角评论作家与创作是值得肯定的,以至于司马长风说:“严格的说,到了刘西渭,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26](P249)
三、李长之:“使作品的真面目真价值大白于天下”
标举着“感情的批评主义”的李长之,反对屈服于权威、欲望、舆论、传统等的奴性批评[27](P377),他强调批评应设身处地地研究作家的创作,他说:“正因为他们能够吟味创作历程中的辛苦,可以设身处地,分担作者对于作品的关怀,并且予关怀之中,又想到作品的进一步的开展,唯独这一点,在作家却是因为创作一篇作品后的疲劳而不假思索的,恰是批评家帮了忙。作家对作品冀求太切,也太奢,而求来的那些苦恼,批评家正能予以安慰,予以原谅,予以勇气,凡是作家自己所不曾意识到的才能,禀赋,批评家往往抉发出,指点出,使作家认准了方向,可以运用他那天才之最大的限度所能企及的步骤,以完成惊天动地的为了全人类的大功勋。伟大的批评家,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使太重视自己作品的作家来一个清醒,又使太失掉自信的作家重建起自信,同时那些流俗的足以动摇视听的褒贬,以及会影响作家的高兴或扫兴的舆论,批评家也负着扫荡廓清的职责,总之,任务在使作品的真面目真价值大白于天下,不但为读者,也为了作家。”[28]受到德国康德哲学与宏保儿特、温克耳曼等德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他注重对研究对象精细深入的审美批评,并强调对于作家创作发展轨迹的梳理,还关注作家人格性情对于创作的影响,这使其文学批评常常具有开阔的视野与独到的见地。
李长之是因研究鲁迅而为文坛瞩目的,1935年5月29日起,他在天津《益世报》和《国闻周报》上开始发表鲁迅研究的系列论文12篇,1936年1月结集为《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出版,成为第一部鲁迅研究的专著。他在该著的序中说:“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唯一的批评者的态度。”[29](P3)年轻而自信的李长之深入地研究了鲁迅的人生与创作,并努力联系鲁迅的生活环境、心理性格评价其创作,道出诸多求真的独到见解。在《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中,他细致地将鲁迅人生与创作分为六个阶段,并指出了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轨迹,精警而深刻。他评说鲁迅《狂人日记》发表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上开了初期最光彩的花。这重要不止在鲁迅,而且在中国!”[30](P18)他将鲁迅置于新文化运动、新文艺的发展中予以评价,恰如其分地道出鲁迅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他联系鲁迅的人生评说鲁迅的小说创作,认为:“哄笑和奚落,咀嚼着弱者的骨髓,这永远是鲁迅小说里要表现的,我已经说过,这是鲁迅自己的创痛故。因此同情充满了他的全作品,虽然有时他为他所同情的人物之堕落而愤慨或激昂。”[31](P49)这种深入独到的分析,道出鲁迅小说主题表达、情感基调与鲁迅人生之间的关联,切中肯綮。他赞赏《孔乙己》、《风波》等八篇小说,揭示鲁迅小说所表达的基本主题:“这八篇东西里,透露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之深切的了解,对于愚昧、执拗、冷酷、奴性的农民之极大的憎恶和同情,并且那诗意的、情绪的笔,以及那求生存的信念和思想,统统活活泼泼地渲染在纸上了。”[31](P48)他指出鲁迅小说外冷内热的情感特征:“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31](P56)他评说鲁迅作品中的抒情成分:“广泛的讲,鲁迅的作品可说都是抒情的。别人尽管以为他的东西泼辣、刻毒,但我以为这正是浓重的人道主义的别一面目,和热泪的一涌而出,只不过隔一层纸。”[31](P62)李长之的这些评说都以其深入细致的观照与感受,将鲁迅作品的特性精辟地道出。李长之评说鲁迅杂文的长与短:“他杂感文的长处,是在常有所激动,思想常快而有趣,比喻每随手即来,话往往比常人深一层,又多是因小见大,随路攻击,加之以清晰的记忆,寂寞的哀感,浓烈的热情,所以文章就越发可爱了。有时他的杂感文却也失败,其原故之一,就是因为他执笔于情感太盛之际,遂一无含蓄……”[32](P103)大胆而老到的评说,寥寥数语将鲁迅杂文的特点精确地道出。李长之以其独到的艺术敏感指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失败之作:“我觉得鲁迅有几篇东西,却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在《呐喊》里,是《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和《端午节》,在《彷徨》里,是《在酒楼上》,《肥皂》和《弟兄》。”在指出这些作品的不足之后,李长之联系鲁迅的性格谈论原因:“故事简单,是材料的问题,独白而落于单调,是手法的问题。这都不是根本,根本是,鲁迅不宜于写都市生活,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练,老辣,简峭都似乎更宜于写农村。”“在鲁迅写农民时所有的文字的优长,是从容,幽默,带着抒情的笔调,转到写都市的小市民,却就只剩下沉闷,松弱,和驳杂了。”[31](P76)这种评说虽然并非完美,但却表现出李长之不人云亦云、努力道出其真诚独到见地的个性。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专著,体现出李长之努力以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对于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的系统研究中,道出其独到的真知灼见,在对于鲁迅作品的艺术感受与深入评说中,体现出其独立思考、深入研究、整体把握的研究特点,推进并拓展了鲁迅研究。
以鲁迅研究而享誉文坛的李长之,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执著耕耘,他的研究涉略了当时文坛上诸多作家:茅盾、郭沫若、许钦文、胡适、曹禺、老舍、李广田、卞之琳、巴金、吴祖光、吴组缃、张资平、沙汀、梁实秋、田间、臧克家、姚雪垠等,他几乎将当时有影响的作家都纳入其批评的视野中。李长之在谈到评论时说:“我们理想中的书评应该符合一般的批评文章的条件,那就是:要同情的了解,无忌惮的指责,可以有情感而不能有意气,可以有风趣而不必尖酸刻毒,根据要从学识中来,然而文章仍须是优美而有力的创作。”[33]有情感而无意气,有风趣而不尖刻,这也是李长之所追求的批评风格。李长之的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努力在对作家创作的发展进程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在对于作家创作历程的梳理中予以深入的研究。在《许钦文论》中,他将许钦文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并指出各时期的代表作,认为“专门擅长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犹豫起伏的心理,这就是我所谓许钦文风”[34]。他评论郭沫若的剧作《棠棣之花》,将其置于当时文学创作的情境轨迹中考察,认为:“也许,中国的文艺是要有一个大转变了,说不定不久就从写实的清浅的理智色彩中解放而出,渡到热情的理想境界去,——那算是我们馨香祷祝的!假如真是这样,郭先生这创作,便可以代表一个消息,而这消息是太值得的了!……文艺创作原不只是暴露黑暗,而且更重要的,乃是创造光明!”[35](P132)。他评价茅盾的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将其置于茅盾创作的整体中予以评说:“我从前觉得茅盾先生的长处是长于写动乱,如《三部曲》中之写誓师礼及《子夜》中之大出丧和吴桥镇的暴动,都可为例。这观察,我现在还没有变。《霜叶红于二月花》中写农民在小曹庄打轮船一章便是说明。”[36]他将沙汀的《淘金记》放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发展的轨迹上评说:“近代中国小说的发展,大部分是写实的,写实中又大半农村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已开其端。《淘金记》中茶馆的舆论,也有些似乎是阿Q示众时舆论的延长。可是《淘金记》不能不说比那时又进步了许多步。在写实的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最近又有许多人专走地方色彩的路,我们不妨称之为乡土文学,作为农民文学的又一类小说吧。《淘金记》者,却是我们仅见的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收获了。”[37]李长之这种将作家的创作置于其创作发展历程中的考察,使其对于作家的研究具有了比较全面与动态的特征,常常在揭示出作家创作的发展变化中更加深入地道出研究对象的特点。
在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李长之努力联系作家的生活与性格分析其创作的独特个性,常常有褒有贬,具有真知灼见。他在评说胡适的创作时说:“从小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失掉练习音乐和绘画的机会,他曾悔恨着说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加之早年就接受了范缜、司马光反对鬼神的议论,所以他起始即是在理智的生活里发展起来的了。”“由于性格上的相宜,胡适尤其表现了启蒙的精神。这精神的核心就是清楚浅显的理智。”[38]从胡适的生活与性格观照其创作的特点。他评论李广田的小说《引力》说:“作者向来的文章,一如他的为人,是淳朴,诚实,不夹半点儿假的。他那思想上给朋友或一般青年人的感染上是如此,他那构成吸引人的散文风格的缘故也在此。可是这种优长到了他写小说的时候便成为障碍,使他有点迈不开步了。”[39]他评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有人说他迎合读者心理,我以为倒不如说他恰抓着现在青年婚姻问题的时代。他一点也没有特意挑拨,他写的是性爱的悲剧。他的成功在于自然主义派的技巧,他的失败在有时对自然主义的作风偶尔放弃。他的技巧方面的长处,是一般人所忽略,他的故事方面的兴味,却有着不良的影响。”[40](P234)他批评老舍的小说“更恰当地说,他的幽默是太形式的,太字面的,不过作为讽刺用的一种表现方法”[41](P170)。他认为曹禺的话剧“实在有些小说化”,“仿佛有种耽于造型的形象追忆和描摹的本能在迫使他,让他在无意间表现了小说家的本领”[42](P191)。李长之这种立足于联系作家分析作品的方式,这种跳入作者的世界中去的评说,构成了其既注重艺术的感悟、又强调理性分析,雄辩与细腻融合的批评风格。
四、沈从文:“将文学当作一种宗教”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以其执著的乡下人性格挚爱着文学,他的小说创作以其对乡土世界的讴歌与对都市人生的针砭构成文坛独特的风景线。他对于文学怀着一种宗教般的执著与虔诚。他曾说:“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惮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43](P170)他以“将文学当作一种宗教”的姿态从事创作,也以这样一种精神从事文学批评。
沈从文注重文学的人性与文学性,强调要将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脱出来,在文学批评中,他注重其人生体验与艺术感受。在谈到评论时,他说:“理想的书评有待于理想的书评家。一篇书评对作者读者同样有意义,当然不容易。但如果一个书评家,对于近20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长成有一贯的认识,对于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内容得失欣赏且能说明,执笔时不敷衍,不苟且,这样子写成的书评,至少对于读者是有意义的。理想的书评家,应当是懂得各种作品且能够中肯的说出那个作品得失的人……”[44](P208)沈从文特别强调评论对于读者的负责,强调对于文学的发展历程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因此在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中常常对于近20年的文学作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1931年他在《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中,对于小说发展的历程作了简约的扫描与评点。他回顾国语文学运动的兴起,认为当时的文学:“在文字方面,与一个篇章中表示的欲望,所取的手段方面,都朴素简略,缺少修饰,显得匆促草率。每一件作品,都不缺少一种欲望,就是近于言语的文字写出平凡境界的悲剧或惨剧。”[45](P360)他在这种背景下评说鲁迅小说的影响:“当时还要‘人生的文学’,所以鲁迅那种作品,便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45](P361)沈从文介绍“人生文学”创作的王统照、冰心、庐隐、叶绍钧、许地山;评点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提及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黎锦明、蹇先艾;介绍淦女士、凌淑华。沈从文评说杨振声、川岛、章依萍;推崇茅盾、丁玲、老舍、施蛰存。他在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回眸中纵横捭阖,他在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评点中评头论足。他谈论冰心的小说:“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忆上驰骋,写卑微人物,如何纯良具有优美的灵魂,描画梦中月光的美,以及姑娘儿女们生活中的人物,虽处处略带夸张,却因文字的美丽与亲切,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45](P364)他评说张资平的“恋爱故事”:“错综的恋爱,官能的挑逗,凑巧的遇合,平常心灵上的平常悲剧,最要紧处还是那文字无个性,叙述的不厌繁冗……”[45](P367)他评论许地山的创作:“以幻想穿串作品于异国风物的调子中,爱情与宗教,颜色与声音,皆以与当时作家不同的风度,融会到作品里。”[45](P365)在《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中,沈从文简明地回溯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认为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46](P179-180)在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后,他认为“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四位诗人特别有影响”[46](P180-181)。在谈到新诗一度沉寂以后,他认为“孙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这些人完全不是理论家,却有作品证明‘新诗不是无路可走,可走的路实在很多’。”[46](P182)在对于新诗发展历史的简洁勾勒中,对于诗人们的成就与影响作了评点。沈从文以其广博的视野观照“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在对于现代小说创作发展的历程梳理中,在对于现代诗歌创作历程的梳理中,对于不同作家的创作予以简约精到的评说。
沈从文的作家论注重对于作家创作文体与风格的研究,他常常以简约生动的笔触评说作家的特点,有褒有贬,常常见出其机敏与精辟。他评说施蛰存的短篇小说:“略近于纤细的文体,在描写上尽其笔之所诣,清白而优美,施蛰存君在此等成就上,是只需把《上元灯》那个集子在眼前展开,就可以明白的。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动人的故事,如《上元灯》中《渔人何长庆》、《妻之生辰》、《上元灯》诸篇,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然而作者方向也就被限制到他的文体中,拘于纤细,缺少粗狂,无从前进了。”[47](P286)感觉的准确,评说的到位,可见一斑。他评论冯文炳的创作:“则冯文炳君所显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48](P296-297)他指出冯文炳的《莫须有先生》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把文字转到一个嘲弄意味”,“趣味恶化”[48](P294-295)。以充满感悟的语言评说冯文炳的创作风格,贴切而生动。他谈论许地山的创作:“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的周作人,徐志摩,冯文炳诸人当另论)。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揉合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作者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49](P300)从作家的文化背景中观照许地山的创作,将其创作的特点和盘托出,深入而深刻。他评说闻一多的诗歌:“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避;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作品上,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是闻一多先生的《死水》。”[50](P311)以透视般的眼光,将闻一多诗歌创作的追求与特点深刻地道出。他评论汪静之的《蕙的风》:“作者在对自然的颂歌中,也交织着青年人的爱欲幻觉与错觉,这风格,在当时诗人中是并不缺少一致兴味的。”[51](P332)他谈论朱湘的诗歌:“能以清明的无邪的眼,观察一切,无渣滓的心,领会一切——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悦目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各样的音籁,皆以悦耳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52](P335)沈从文的作家论,以其对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体验与感受,努力把握所评论对象的特点,以其富有诗意的笔触道出其独到的见地。
沈从文在他的《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中说:“我这些文章于青年朋友不合用,我想得到。文章的汇集,它的用处似乎只足供一个预备着手写‘现代中国文学’的朋友作为参考。”[53](P38)沈从文的这段话语,可以说道出了感悟式作家作品批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立的价值和意义。英国文学家奥斯卡·王尔德在《批评家也是艺术家》一文中说:“可是评论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正如艺术创作必须运用评论的才能一样(如果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创作),评论也完全是创造性的(就其字面的最高涵义而言)。实际上评论既具有创造性也具有独立性。”[54](P259)沈雁冰、李健吾、李长之、沈从文等的感悟式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既具有创造性也具有独立性。除了如上的批评家外,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钱杏邨、苏雪林等人,都曾以感悟式的作家作品批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3-06-15
标签:文学论文; 李健吾论文; 鲁迅论文; 沈从文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艺术评论论文; 作家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巴金论文; 边城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李长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