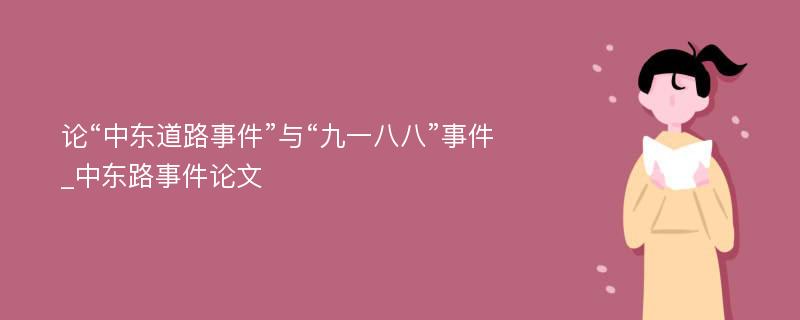
试论“中东路事件”与“九#183;一八”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路论文,事变论文,试论论文,一八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中东路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影响的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东路事件影响下的中苏、中日关系,全面地探讨了中东路事件与九·一八事变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中东路事件 九·一八事变 中苏日关系 内在联系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研究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历史的时候,涉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大的国际背景,往往忽视一些表面与日本发动事变无关而实际相关紧密的因素,使得研究的深入受到很大影响。如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地区的国际关系中的中、苏、日三角关系,特别是苏、日关系对事变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对这一不仅涉及中苏关系,而且由于中国东北特殊的国际地位而涉及中国与日本等国家关系的问题进行剖析,探索其和1931年9月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九·一八事变的内在联系,并进而加深对九·一八事变史的研究。
一
近代以来,中俄之间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在中国东北,中东路问题是最具代表性的。早在1924年3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代表王正廷与新的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在北京订立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草案》和《七项附件》,对中东路问题多有涉及。苏联政府重申,“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中东路除本身营业事务直属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苏联政府“允诺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回中国”,并准备办理“解决偿路之款额及条件暨移交中东路之手续”。“两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苏联方面还强调,“在未将中东路各项事宜解决以前,两国政府根据……1896年9月所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所有之权利与本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暨中国主权不相抵触者仍为有效”[①a]。由于两国议定:“在新条约协定等项,未经订定以前,所有以前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概不施行。”[②a]所以直到5月31日,双方才以上述条约为基础重新订约。9月20日,苏联代表又与中国东北地方代表签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协定》(即《奉俄协定》),苏方重申,中东路“纯系商业性的机关”,“除该路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华民国国家及地方政府权利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该路本身必需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处置”。苏方还同意,中东路合同期限“由八十年减至六十年”,“此项期满后,该路之一切附属产业为中国政府所有,无须给价”,“中国有权赎回该路”[①b]。
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是相互谅解和相与为安的。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和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苏联和日本等皆因各自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问题,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以压迫三省当局使不受国民政府之拘束”[②b]。特别是苏联方面,在中东路的活动甚为频繁,中苏双方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才开始尖锐起来。
1929年开始,在国民政府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要求影响下,中国东北当局依据中苏有关条约的精神和原则,相继收回中东铁路的电务、机务、会计等权利。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③b]为由,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成为“中东路事件”的导火线。
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力促东北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主权”,7月10日,张学良派军队占领中东铁路,并将苏联在沿线地区的一些机构查封,中东路及周围一些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苏两国的对立更加尖锐化。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18日又宣布与南京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外宣言,称“此次中东路事件之发生乃由苏俄政府违反中东路协定之精神全部,及指使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与利用中东铁路机关及其人员之名义,为其宣传共产主义,图谋颠覆中国政府”、“扰乱东省治安”[④b]。23日,中苏正式断交。
8月6日,苏联政府成立了远东特别军,准备与中国方面开战,这一切完全出乎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的预料,18日,张学良仓促宣布总动员,准备对付苏联方面的军事进攻。从8月下旬开始,苏中两国在中国东北境内展开正式武装冲突。苏联强大的远东特别军从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绥芬河等地攻入中国东北地区,由于中国军队缺乏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结果被准备充分、装备精良的苏联军队打得一败涂地。10月25日,南京政府就解决中东路事件发表对苏宣言,要求“中俄各以全权代表会议,按照中俄及东路协定,解决悬案,变更现状,互释被拘侨民,停止边境军事行动,折衷双方意见,拟定共同宣言”[⑤b]。这一要求被苏联方面拒绝。直到11月,战争才基本结束。在军事失败前面,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东北地方当局派交涉员蔡运升与苏联政府代表直接进行谈判。
12月3日起,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不断照会非战公约各国,详细说明中苏关于中东路纷争发生的原因、经过,并宣布:“随时与苏联政府谈判解决此项争端”[⑥b]。同日,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曼诺夫斯基签订《奉天政府与苏联政府间议定书》,双方表示“尽力协助排解中苏冲突并消除继续复杂化之一切原因”[⑦b]。12月22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伯力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双方协定,中东路问题应“按于最近之中苏会议解决之”[⑧b]。
伯力协定签订后,“两国拘留之人民,已由双方释放”,“该路交通已恢复原状”[⑨b],中苏间有关中东路问题的矛盾开始逐步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为待中东铁路问题之最后解决起见”,决定派代表前往苏联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专门与苏联方面讨论“中东铁路善后问题”[⑩b]。
1930年10月,几经周折后,中苏在莫斯科召开有关中东路问题的正式会议。苏联代表加拉罕曾经一再强调,会议应遵守的各项原则,“已由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予以规定”,“对华政策,已于各该条约中完全表现,此等条约,即系实行苏联政府1919年、1920年对中国国民宣言中所定之政策,苏联政府抱此政策,始终不渝”[①c]。10日,苏联方面又照会中国代表莫德惠,要求中东铁路的现状在“中苏会议未经同意变更东路现行办法,或由中国赎回东路以前,按照中俄、奉俄协定,任何一方不应以片面行为,或强制行为,加以变更”[②c]。中国代表也发表了相应的照会,阐明了双方在中东路问题上应持的立场、态度和应恪守的原则。12月4日,在莫斯科会议上双方议定组织一个关于“中东路事项委员会”,专门负责中东路问题的处理。为加强对苏交涉,尽快解决善后问题,1931年2月27日,在莫德惠等谈判代表之外,国民政府又加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胡世泽等为代表。
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特别是苏联方面的一再承诺,中东路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但由于苏联方面缺乏应有诚意,中苏莫斯科会议步履维艰,双方谈判断断续续,先后达24次之多,但始终未能达成协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苏莫斯科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当然,中东路问题也就没能解决,中东路最后被苏联以微薄的价格卖给日本,苏联方面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二
就在中苏两国为中东路问题大动干戈、纠缠不清的时候,中国东北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苏、日三角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苏、日关系的变化是最值得注意的。
近代以来,俄、日在中国东北的矛盾和斗争,是远东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东北的中、俄、日三角关系中,本应作为主要一极的中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起不了主导作用,反而处处受制于俄、日。结果,无论是俄国还是日本,都可以分别在这种失衡的三角关系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好处。
俄国十月革命后,采取了一些革命的外交政策,放弃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但是,在许多具体利益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苏俄并没有作出让步。在列宁之后,苏联在许多方面与帝俄时代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东路问题上,其后苏联的做法就表明了这一点。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日、苏依然和从前一样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依然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各自从中国获得利益。当然日、苏之间在中国东北的矛盾也和当年日、俄之间的矛盾一样,非常尖锐。南京政府建立后,日本政府仍企图单独拉住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对抗南京国民政府、排斥苏联,实现其独霸东北的野心。与此同时,苏联也随着自己国力增强和外交状况的改变,在对华问题上改变最初的做法,特别在中东路问题上,许多政策退回到沙俄时代。
中、苏、日三国内部的状况,引起三国关系的很大变化。特别在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以后,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直接影响到列强的华的利益,当然也包括日、苏在中国东北的权益。特别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在1929年7月初,强调“哈尔滨事件,以及今后东北对外交涉,无论对日或对苏,均移归南京办理”[③c]。此后,这种三角关系在中国东北变得更加复杂,“日、中、苏三国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满洲”,“是最危险的地方”[④c]。中东路事件则在这种三角关系,尤其是苏、日关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东路事件打破了长期以来中、苏、日在中国东北关系上的微妙平衡。中、苏之间对立直至武装冲突,使得三角关系中的中日、苏日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中东路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处理过程中,中国政府尽管知道日本的侵华本质未变,但为了集中力量处理好当时和苏联的冲突,便对日本采取了“拉”的策略。但是,由于日本的实用主义的侵略外交政策,以“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绝对不干涉中国内政”相标榜,实质是以扩张日本在华经济权益为主要目标,为其进一步的扩大武装侵略打下基础。
而且由于中国“用武力收回外国在华权益的计划”,在日本看来这对日本“在南满所处的地位无疑是敲了一次警钟”[①d],从而导致了日本与苏联的“默契”甚至“勾结”。
中东路事件发生不久,很快就有传闻,“日俄已有成约,日本允助苏俄,俄国则允将北库页岛之渔业利益让与日本。并闻日本反对美国提议干涉中俄事件云”[②d]。这种传闻又很快被证实。这两个“固有宿怨”的国家,“为了满洲的问题”,“为了中东铁路的问题”,不久就“相互了解”和“友好亲善”起来[③d]。为了减少日本方面的疑虑,苏联政府还一再“转告日本政府说,苏军的作战出于防卫目的,无意长期停留于占领区”[④d],并表示“尊重日本在南满内蒙特殊权利”[⑤d]。7月19日,日本方面曾发表通电,表现出“克制”与“中立”的态度。
而实际上,日方一面“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南满铁路“通过长春”北运,另一方面却让“日商在胶州等处买大批粮米运海参崴,接济俄方”[⑥d]。
为了达到其目的,日本甚至还搞出了“单独调停”的花样。当时舆论就指出:“日本单独调停的用意,居心简直是不堪问。她自这次事件发生以来,一方面言调停,一面却于南满铁路大增其兵,同时且利用其电信机关大造谣言,以挑拨中俄双方的恶感,制造战争的空气。以便日本又可乘机出兵,借获意外利益。”[⑦d]
正是借着中、苏特别是苏、日之间这种相互关系的遽变,日本加紧了其在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扩张和武装侵略的准备,实际上是乘中、苏冲突之际,对中国行“趁火打劫”之实。资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日本一方面纵容、支持苏联对中国的行动,另一方面自己也借机明目张胆地在中国东北搞自己的一套。
归纳起来,日本乘中苏在中东路冲突和纠纷时,在东北主要进行了以下一些侵略扩张活动:(一)“增兵”。日本为巩固南满势力,南满铁路已集中5000余人,陆续尚有增加。关东军司令部在长春建筑大规模陆军营房,日本增设满洲守备队,连前共一万三千人。(二)“操演战斗”。中东路问题发生后,日本竟变本加厉地在长春作长期之围城战演习,甚至以沈阳城为目的物,尤属骇人听闻。实际上,“这种肆无忌惮的横行,不啻就是武力侵略的先声”。“国人若无法对付,则南满方面亦有发生严重问题的可能”。(三)探听情报。许多日本军官都“巧装华商韩农,游历各地,测绘地形,窥探虚实”[⑧d]。“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从1927年7月起,乘机“开始到长春、哈尔滨等地作了第一次‘参谋旅行’,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讨论”[⑨d],企图“用谋略制造机会”,“变满蒙”为日本领土[⑩d]。(四)“移民”。时人指出:“日本乘我北满多事之秋,积极进行其移民政策”[(11)d]。(五)“挑起事端”。从中东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的两年多时间里,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的、针对中国的事端明显多于以前,“铁岭事件”、“长春事件”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
三
通过对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直至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前,中、苏、日三角关系在中国东北的错综复杂的变化,特别是苏、日关系的微妙变化,给日本带来有利侵华时机这一问题的把握和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之间的深层关系。
第一,中东路事件,苏联远东特别军对中国东北地方军队打击严重,对东北经济也造成很大破坏,使得东北边防军和东北地方抗击日军侵略的实力和能力都大大的降低。
事件发生后,“苏联远东特别军在加伦将军指挥下,集中步、空、炮、坦克部队十余万之众”,分别向“吉林省绥芬河、穆棱两地(现属黑龙江省),和黑龙江黑河、满洲里(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发动进攻;中国东北边防军在张学良统帅下编成两个军,“‘防俄’第一军军长王树常,指挥三个步兵旅,和骑、炮、通讯部队,开往东铁东线;‘防俄’第二军军长胡毓坤,指挥三个步兵旅和骑、工、通讯部队,开往东铁西线作战”[①e]。战争期间,“苏军连续轰炸绥芬、北安镇,”“苏联阿穆尔河舰队,进入松花江,直冲两省腹地”,与“东北海军江防舰队战斗激烈”,“江防舰队损伤过重,不得不撤出战斗”[②e]。直至后来苏联舰队连续沿松花江攻占同江、富锦。苏军陆、空、骑联合攻占扎兰诺尔,东北守军旅长韩光第战死,“所部东北军第17旅全军覆没,全旅7000人仅逃出1人”。在满洲里被围困时,东北守军“梁忠甲所部数千人,包括梁忠甲本人在内全部被俘”。据当时估计,中东路事件中苏武装冲突过程中,东北军官兵伤亡人数“大约总在一万数千余人”[③e]。而据苏联方面统计,仅“1929年11月17日至20日的战斗结果是”“我(苏)军击溃了满洲里地区的两个加强旅,总共两万人左右,俘获一万人,打死打伤许多中国士兵”[④e]。更重要的是通过战争,日本人看到东北军的弱点,认为东北军“简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从而激起了它的军事冒险欲望。
此外,战争完全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苏军不仅陆军而且空军、海军都深入东北腹地,摧毁东北许多地方。如1929年11月2日,苏军就“纵火焚毁两县各公共机关,城内劫掠一空”,“仅富锦县之面粉损失一项计算,便已达七十万元以上”[⑤e]。东北的工商业,尤其是哈尔滨地区的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从此由盛而衰。日人长谷川洁在《哈尔滨经济概观》中就指出:“中苏边境争端爆发”和“世界性经济萧条”,“不仅使在哈尔滨的日商、外商陷入困境”,而且也使发展一直比较顺利的中国的“工商业陷入全面滞销。其结果,不仅哈尔滨的主要工业油坊、面粉厂,而且连各种中小工业也相继停产或倒闭”[⑥e]。据当时统计,“地方及人民损失在一万万元以上”[⑦e]。后来进一步统计“财产损失约十亿元(约五亿美元)”[⑧e]。这种损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北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与日本在东北抗衡的经济基础。
第二,中东路事件,使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从1929年7月至1931年9月这段时间内甚至更长时间内,在东北的外交上一直为中苏关系所困扰,无力和无暇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作出及时和有力的扼制。
由于“东北易帜”后,“东北对外交涉,无论对日或对苏,均移归南京办理”,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中东路事件后东北地区的中、苏、日三角关系时,只能按照轻重缓急,按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应付对苏联的问题,对日本则采取“拉”的方式,但由于日、苏之间在对付中国、获取权益上的一致,这时已很难拉住日本。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从“谈判—战争—再谈判—再战争—再谈判”,经历了两年多但最终没有结果,这中间中国一直试图把冲突上交给国联去解决,让国联用“非战公约”去约束苏联,“但苏联不是非战公约的签字国,国联制裁不了它”[①f]。中国为中苏“免再起冲突”,又力图将“争端提交无偏袒之第三者公断”,又为苏联方面拒绝,“苏俄之外交手段,实使远东陷于危险地位”[②f]。这样,中苏围绕中东路问题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经历了几十次谈判而未果,中东路也完全恢复到事件前的状态,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也给后来在东北处理对日问题留下很大的阴影。此后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在“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③f]。很多事情,特别是后来对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的扼制,国民政府就不敢轻易诉诸武力了,以至于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
第三,中东路事件,苏联用武力解决和中国的纷争,为日本发动武装侵略东北作了一个直接的“样板”;事件发生后苏联和日本之间相互“默契”、“纵容”甚至“勾结”,使苏联方面在中苏冲突时得到了日本的“中立”,而最主要的则是日本以对苏中冲突的所谓中立,换取了日后苏联对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问题上的最大程度上的容忍。
“东方会议”后,日本对其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侵略容易引起苏联的干涉这一点很敏感,担心“招致麻烦”,特别是自己“独占”的企图一旦暴露,定会引起苏联的不满甚至引发战争,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因为日、苏两国之于中国东北,“方法虽殊,而目的则一”,都企图“多占”甚至“独占”。日本要想达到目的,就要有机会,就要乘中国或苏联乱,“日人无时不怕中国之不乱,借可获利于鹬蚌”[④f]。中东路事件确实给日本这种“乱”的机会。按日本的逻辑,日本现在对苏联在东北的行动不干涉,将来苏联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也不能干预,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要侵害对方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任何第三国也别想从这一范围内得到权益。后来的形势发展也确实如此。“中苏冲突突起后,美政府匡合世界力量之脆弱,尤予日本人从满洲自由行动之信念,关东军诸参谋,准备柳条沟事变之北满旅行即于此时出动,不为无故。”[⑤f]
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后,日本拒绝参与四国调停,默认和支持了苏联对中国的“直接交涉”,“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坚持中日直接交涉之伏线”[⑥f]。也正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日本方面,尤其是关东军,才对其“所悬悬者”最后作出判断:日本在东北发动和挑起事端,“苏联不至干涉,可下臆断”。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早已有之,但是,在侵华的时机的选择上却有很大的偶然性。特别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地点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就更有很大的偶然性了。这一点当年日本政友会就表达得很清楚:“我国对华外交”,“决定方策”时,“必须参酌四周情势,以期实行”[⑦f]。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国东北地区中、苏、日三角关系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东路事件后,中苏断交,苏联对中国的武力政策和对日亲善缓和的政策,客观上给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政策及其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的和区域的条件。即日本以对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上对中国的武力政策的默许,甚至在一些具体举措上的支持为代价,换取了苏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扩大在中国东北侵略行径的默认。“日本安然地利用中苏纷争这个偶然的良机。”[①g]当年,明眼的中国人已看出:“苏俄今日与日本提携即阴伏将来之祸机,以祸不远,预料三年之后,即有爆发之可能。”[②g]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在其1937年所著《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书中,谈道,“中东路问题,伤了东北军的元气,暴露东北军弱点,这使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种下了九·一八事变之一因。”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中东路事件原是中俄两国的冲突,结果却予日本以侵略东北之良机。”[③g]这也是本文所要作的结论。
注释:
①a ②a 《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8号,第132—133、136页。
①b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36页。
②b 《东方杂志》,1924年第20卷19号,第54页。
③b 《黑龙江历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25页。
④b ⑤b ⑥b ⑨b ⑩b 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4、547、548、553页。
⑦b ⑧b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36、737页。
①c ②c 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4、557页。
③c 惠德安:《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④c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页。
①d [日]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②d ③d ⑦d ⑧d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南满的情形》,《东方杂志》第26卷第15号,1929年8月10日。
④d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2页。
⑤d ⑥d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1页。
⑨d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卷1,日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62页。
⑩d [日]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11)d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南满的情形》,《东方杂志》第26卷15号,1929年8月10日。
①e ②e 惠德安:《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76页。
③e 《民国日报》1929年12月29日。
④e 〔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⑤e 《呜呼暴力劫持下的中俄交涉》,《东方杂志》第26卷21号,1929年11月10日。
⑥e 《哈尔滨经济资料文集》,第2辑,哈尔滨市档案馆,第4页。
⑦e 《民国日报》1929年12月29日。
⑧e 《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349页。
①f 惠德安:《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②f 《法比舆论界对于中俄事件之评论》,《东方杂志》第26卷19号,1929年10月10日。
③f 《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页。
④f 《满洲中俄事件之写真》,《东方杂志》第26卷19号,1929年10月10日。
⑤f ⑥f 梁敬镦:《九·一八事变史述》,台湾世界书局1968年版,第185、187页。
⑦f 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125—126页。
①g 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②g 童平山:《对俄特刊·发刊词》(1929年),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5辑,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③g 《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1984年版,第350页。
标签:中东路事件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中东铁路论文; 中苏论文; 中俄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