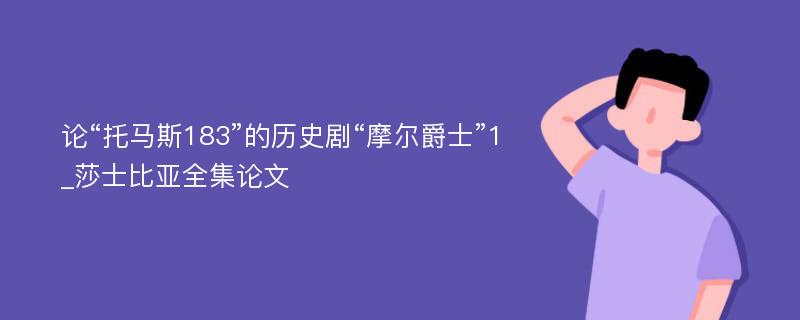
论历史剧《托马斯#183;莫尔爵士》的审查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尔论文,托马斯论文,历史剧论文,爵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剧《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以下简称《莫尔》)的手稿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写就之后,② 一直湮没无闻,不想到了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竟在学界掀起了惊天波澜,因为人们发现,手稿中有147行可能是莎士比亚本人的手迹。此前,学者确认的莎士比亚手迹仅有六个签名和两个单词,这一新发现显然令人欢欣鼓舞。自维多利亚时期亚历山大·戴斯(Alexander Dyce,1844)和理查德-辛普森(Richard Simpson,1871)以来,数代古文书学家(paleographer)和莎学学者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显著者如W.W.格雷格爵士(1911)、爱德华·蒙德·汤普森爵士(1916)、A.W.波拉德(1923)、R.W.钱伯斯(1931)、R.C.鲍尔德(1949)等,③ 终于在20世纪中叶基本确定了《莫尔》一剧中莎士比亚的手迹和部分作者权。如今,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一结论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只有“极少数人”仍坚持否认那147行是莎士比亚的手迹。④ 事实上,自从查·贾·西森编辑的《莎士比亚全集》(1954)⑤ 率先收入哈罗德·詹金斯(Harold Jenkins)编辑的《莫尔》全文后,各种《莎士比亚全集》的版本⑥ 都开始部分或全文收录《莫尔》一剧。约翰·乔伊特(John Jowett)(牛津版的编者之一)正在为第三系列的阿登莎士比亚丛书编辑《莫尔》。⑦ 可以说,《莫尔》作为莎士比亚经典的地位已经确立。鉴于此,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也收录了孙法理译的《莫尔》的两个片断。⑧
本文无意重述莎士比亚手迹和作者权的鉴定过程。⑨ 笔者将换一个角度,讨论该剧的审查(censorship)问题。这一问题或许没有笔迹和作者权鉴定那么复杂,但几十年来同样聚讼纷纭,并且与剧本的创作和修改时间纠结在一起。本文试图从历史的可表演性(performability)这一角度切入,通过历史文本和戏剧文本的比较研究,探讨伊丽莎白时期审查官的角色定位以及戏剧审查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莫尔》是一部历史剧,中心人物是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7-1535),剧本描写莫尔如何成功地制止伦敦市民反对外国人的动乱,后来因为拒绝支持亨利八世而被囚被杀的故事。据研究,《莫尔》一剧故事的首要出处是拉斐尔·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主持编写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以下简称霍林希德《编年史》)。⑩ 在何种程度上历史真实被允许在舞台上表演是本文切入的角度。我们所关注的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书本表演和舞台表演有何区别?对史书的审查与对史剧的审查之间是何种关系?珍妮特·克莱尔认为戏剧审查和文学审查是两个“基本不相关的”和“独立的”系统,(11) 果真如此吗?本文通过对比研究《莫尔》和霍林希德《编年史》的文本和审查过程,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蒂尔尼对《莫尔》的审查
《莫尔》的手稿现在珍藏于大英图书馆(MS Harley 7368)。手稿中除了五位合作剧作家[据考证,他们是安东尼·芒戴(Anthony Munday)、亨利·切特尔(Henry Chettle)、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莎士比亚,大概还有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和剧院簿记员的手迹外,还有第七个人,即审查官(又称喜庆长官,Master of the Revels)埃德蒙·蒂尔尼(Edmund Tilney)的手迹。手稿第一页上,蒂尔尼就在页边写道:
完全略掉关于暴乱及其原因的描写,以托马斯·莫尔爵士在市长治安法庭上露面开始,此后以报告的方式讲述他担任伦敦市法官期间平息针对伦巴第人的骚乱的功绩,只准简短报告,其它方式不许,否则你们自己面临危险。/E.蒂尔尼(12)
关于这段著名的话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最后一个短语“否则你们自己面临危险”(att your own perilles)。对此,威廉·朗评论道:“我认为,[蒂尔尼]强调‘你们自己’意在表明他自己不愿意为剧作家们可能的轻率行为承担责任。”(13) 非常正确,但是有何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以为,蒂尔尼的措辞来自女王陛下,正如审查官的权威来自皇家授权一样。1581年12月24日,伊丽莎白女王颁发委任状,正式任命“朕尊敬的埃德蒙·蒂尔尼”为喜庆长官,职责包括审查演出剧本和监禁、惩罚违法的演员。在委任状的结尾,女王称呼——“朕的诸位法官、市长、郡长、乡长、警察及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仆从和忠实的臣民”:
因此,朕希望和命令你们和你们每一个人必要时务必帮助、支持和协助上述埃德蒙·蒂尔尼或其全权代理人正确行使朕所述职权和命令,因为你们和你们每一个人都为朕的意愿服务,否则你们会面临极端危险。(14)
蒂尔尼的“否则你们自己面临危险”可读作女王的“否则你们会面临极端危险”(at your vttermost perills)的减弱的回声。两种场合中,权力行使的语码是一致的,不平等的结构关系也相似:审查官之于演员,恰如女王之于臣下。显然,戏剧审查官的权力来自宫廷,喜庆长官隶属于宫廷大臣,即英国皇家的总管。女王命令各级政府官员“帮助、支持和协助”蒂尔尼行使职责,可见在市政当局与喜庆长官的摩擦中,女王是支持后者的。这就解释了为何伦敦市长也要让着喜庆长官三分。当然,市长会寻求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的帮助(参见他1592年2月25日致大主教的信件)。(15) 这一权力三角结构(宫廷、市政和教会)最好地体现在枢密院(Privy Council)建立戏剧审查委员会的计划中,委员除喜庆长官外,一名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任命,一名由伦敦市长任命(参见1589年11月12日枢密院会议记录)。(16) 所以,喜庆长官作为戏剧审查官的职位不是简单静止的,如埃德蒙·蒂尔尼1579-1610年担任喜庆长官时那样;(17) 相反,它是伊丽莎白时期复杂的权力体系中一个竞争的焦点。蒂尔尼本人也面临着诸多危险。
“你们自己”的强调把蒂尔尼放到了与剧院及演员对话的关系中。而这一关系的性质如何?蒂尔尼是专制的纪律执行者还是自由演员的合谋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伊丽莎白时期戏剧审查性质的评估。正如学者们的考证,蒂尔尼既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又是剧院的方便工具。蒂尔尼从审查剧本和剧院的工作中获得了一笔稳定的收入。(18) 如果对剧院活动限制太严格,则不利于他的个人利益。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人的各种欲望,为了个人收益而向演员让步甚至与演员合谋是完全可能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否则你们自己面临危险”貌似严厉,其实隐含着对演员的关切:照我说的做,否则你们要么无法演出,要么将冒着被惩罚的风险。
看来,对“否则你们自己面临危险”的解读反映了两种历史观:辉格党历史观和修正派历史观。事实上,审查官并没有禁止《莫尔》的演出。威廉·朗对蒂尔尼的审查意见的结论是:“审查官在《莫尔》剧本中留下的记录并不能支持严厉审查的假定。他的批注意在避免问题,而非禁止演出。”(19) 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朗的意见。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简单的事实,认为伊丽莎白时期的审查是专制性的。而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这一事实,更趋向于修正派的观点。例如,T.H.霍华德-希尔讲:“[蒂尔尼]与演员的关系虽然最终是专制的,但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同僚。”(20) 理查德·达顿也同意霍华德-希尔和朗的意见,认为“蒂尔尼显然愿意看到它在舞台上演出(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演出过)。这表明伊丽莎白时期的政治审查有时比人们认为的要自由得多。”(21) 以上三位学者都反对传统的辉格党历史观,因为它把“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专制主义的发展”作为千真万确的信条。(22) 三位学者挑战了这一假设,从审查的历史事实出发,发展了他们的修正派历史观。笔者参照三位学者的研究,在都铎专制主义的铁壁中找到了一条裂缝,发现戏剧审查严厉的外表下其实仍隐藏着温柔,于是加入了修正派的阵营。
二、变形记:从史书到史剧
1954年,哈罗德·詹金斯提出《莫尔》中关于不祥五朔节(Ill May Day)的场景主要源于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编年史。(23) 现在,这一看法已经被证伪。梅尔基奥里和加布里埃利两位意大利学者——罗马大学的教授,也是《莫尔》的编者——通过细致的对比研究,指出《莫尔》故事的首要出处是1587年版的霍林希德《编年史》,而非霍尔的《两个卓越的贵族世家的联姻》(1550)。(24) 除了措辞和标点外,他们还提供了一组拼写名单:
《莫尔》——Lincolne,Sherwin,Standish,Spittle,S[t] Martins,Mewtas,etc
霍林希德——Lincolne,Shirwin,Standish,spittle,saint Martins,Mewtas,etc
霍尔——Lyncoln,Shyrwyn,Standiche,Spyttell,saynct Martynes,Mutuas,etc
显然,《莫尔》与霍林希德的看法更接近,梅尔基奥里和加布里埃利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牛津版和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者都采用了这一结论。(25) 本文在已有的出处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史剧对史书的改写以及种种改写对审查结果的影响。
1587年版霍林希德《编年史》写道:“就这样,他(指比尔博士)狡诈地唆使或者说不谨慎地煽动民众起来反抗外国人。因为这一愚蠢的布道,许多轻率的人勇气倍增,公开发泄对外国人的不满。”(26)
如何理解这里的用语,如“不谨慎地”、“愚蠢的”和“轻率的”?这些词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倾向?笔者认为,它们强烈谴责动乱者,代表着官方的或“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试比较伊丽莎白女王1559年的一则公告:
不得允许任何描述宗教事宜或者国家政治管理的剧本上演,除非权威、饱学、智慧之士执笔,此类事宜不适合入剧,观众也仅限于庄重谨慎之人。(27)
庄重-轻率,谨慎-不谨慎地——亦步亦趋的反义词表明霍林希德非常忠实地顺从于国家意识形态。(28) 比尔博士煽动性的布道是“愚蠢的”,而斯坦迪什博士“明智地”拒绝了林肯要他发布呼吁书的请求。(29) 这些价值判断透露出历史学家与统治阶级的同一立场。同样,动乱者被称作“年轻的坏人”、“作恶者”、“做错事的人”等。(30) 所有这些用语都不是中立客观的,而是包含价值判断和负面评判的。此外,历史学家偷偷利用被动语态来掩盖外国人的作为,从而减轻甚至开脱他们的罪行:“后来,她的丈夫知道了,要求归还他妻子,回答是(answer was made)他不能得到她;他又要求归还他的银质餐具,同样回答是(answer was made)他既不能得到餐具,也不能得到妻子。”(31)
伦巴第人弗朗西斯·德巴尔在被动语态中完全消失了,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监禁和杀头之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英国老百姓在《编年史》中遇到的是冷冰冰的语言之墙,称号是“恶人”。但是政府喜欢这样的立场,所以霍林希德《编年史》得以在市面上流通。
但《莫尔》一剧却没有用被动语态来掩盖责任者;相反,外国人的斑斑劣迹在舞台上暴露无遗。舞台媒介的直接性暂且存而不论,史剧对史书的改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情节的浓缩;增加了女性人物多尔·威廉逊(Doll Williamson);(32) 直接呈现(showing)与间接报告(telling)相结合;第一幕第一场的场景从布道坛改为大街上。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在《编年史》中,比尔博士于复活节周在布道坛宣布了林肯的呼吁书;在剧中,林肯本人在大街上向公众宣读了呼吁书(比尔博士的宣讲仅仅作为背景提及):林肯篡夺了神圣传道士的角色,成为唯一的“暴乱头子”。(33) 是林肯而非比尔博士,“狡诈地唆使……民众起来反抗外国人”。林肯最急于复仇,但又是唯一一个建议要有耐心的人:“我们也许不能[把他们打倒],贝茨。耐心一些,再听听”(Ⅰ.i.30)。这个经纪人知道什么时机该冷一下,以把火煽得更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伦敦大街上。如果说《编年史》中的布道坛是双重封闭——布道坛的封闭空间又被封闭在史书中——的话,那么,《莫尔》中的大街则是双重暴露的——大街的开放空间将要在公共舞台上演出。(34) 反叛的行为是一样的,但在双重封闭与双重暴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是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差别。在达顿称蒂尔尼的考虑中,“反抗外国人的因素很可能是决定性的”。(35) 我认为,当初审查官要求把第一场完全删除,不仅因为其中有反抗外国人的描述,更是因为这场戏极端蔑视当局,无视权力系统中的三方:城市、宫廷和教会。
考虑到双重封闭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历史的书本表演实际上是一种非表演(deperformance),尤其是与历史的舞台表演相对照时更是如此。《编年史》对历史进行了非表演,还表现在此书的写作与国家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阅读史书需要识字,而伊丽莎白时期的识字率相当低。如果说布道坛是等级空间,那么大街则是民主空间。大街解放人,而布道坛压迫人。开放的大街闪烁着真正的革命精神,一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普通民众自发起来反抗压迫者,无论他们是谁。在舞台上表演此类革命当然会吓坏统治阶级。从布道坛到大街的变化看似不大,其实是革命性的改造,宣布了新的方式,新的秩序,新的世界。
剧本新增加了女性人物多尔,多尔直言无忌,目无法纪,是个反抗外国人的女英雄,在剧中第一个出场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蒂尔尼删掉第一场戏,是为了让多尔闭口。剧本引入多尔这一人物是为了使情节紧凑:一个外国人抓住了多尔,另一个外国人抢走了她丈夫的鸽子——而在《编年史》中这两个事件本来是分开的。剧作家选取温存善良的女人和鸽子,来衬托外国人的残忍。正是多尔表达了对外国人的极端蔑视和勇敢的反抗:“我一丁点儿姿色都不会下作地迎合外国佬”(Ⅰ.i.6-7);“如果我们老公被法律管着,不得不忍气吞声,那么他们的老婆就要犯点小法,打你们个落花流水(soundly beat ye)”(Ⅰ.i.65-68)。一个“忍”(bear),一个“打”(beat),一个字母之差,却是截然两种态度;“犯点小法”有意轻描淡写,soundly则一语双关(打得合情合理;暴打),说明“犯点小法”有正当的理由。即便临死前,多尔仍大义凛然,坚守民族气节:“只要我还能看见一个英国男人,法国佬荷兰佬甭想亲我一下……我宁死不做外国佬的玩物”(Ⅱ.iv.129-132)。总之,多尔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剧本的颠覆性,不仅表现在排外情感上,而且推翻了传统妇女的父权形象:多尔贞洁,但并不娴静少言。
蒂尔尼“简短报告”的命令已经在剧本中使用了。多尔简述了金匠及其妻子所受的冤屈(Ⅰ.i.9-13),后来托马斯·帕尔默爵士、萨里伯爵等人详细讨论了他们的冤屈(Ⅰ.iii)。对威廉逊夫妇的直接呈现和这些间接报告互相配合,证实了弗朗西斯·德巴尔的厚颜无耻。同样,林肯在大街上宣读呼吁书与关于比尔博士在布道坛上宣讲的间接报告互相配合补充,更令人信服地交待了动乱的起因。
总起来说,剧本以各种戏剧手法改编改造了史书,使得历史的书本表现这种非表演,成为舞台表演或真正的表演。剧本中也包含非表演的成分,最突出的是刻意模糊莫尔反对的所谓“条款”(大约是“最高权力法案”,亨利八世借此摆脱罗马教皇,成为英国国教首领),这一场戏通过了蒂尔尼的审查。可见,审查官反对的不是非表演或不表演,他严禁的正是有关反抗外国人的动乱的表演,尽管他并不禁止整部戏的演出。他“简短报告”的命令实际上要把表演变为非表演。莎士比亚的诗行——“威权使艺术缄默”——描写的正是这种情景。但我认为,“艺术”这里指剧院演出或作为艺术的表演,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文学。(36)
由此,通过与史书的比较,我们讨论了剧本的颠覆性。威廉·朗有个奇特的论点,他认为是政府委托剧作家创作了《莫尔》,以教育民众,减轻暴力危险。朗声称:“所有公民必须为其错误负责。这一重要的反面教材几乎不可能不被次要的人物领会。”(37) 但笔者以为,它肯定不会被领会。和达顿一样,(38) 笔者也认为朗的奇怪论调是荒谬可笑的。
三、霍林希德《编年史》的审查出版;结论
《编年史》第一版在全部印刷完毕后方在“书商登记簿”(Stationers' Register)中登记,因为该书现存的所有本子都标明1577年出版,而登记日期则是1578年7月1日。(39) 考虑到它的登记费用非常之高昂(二十先令加一样本;而通常登记一本书只需六便士),笔者认为此书有可能在登记之前就已经发行流通,昂贵的登记费包括了罚款。第二版自1584年开始计划,(40) 并于同年登记了两次,时间为10月6日和12月30日。(41) 其中第二次登记的版权经女王批准,归纽伯里和德纳姆所有,这说明该书的扩充和修订是得到官方正式许可的。第一版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有关规定,第二版则在出版之前早早地使自己合法化。有证据表明,霍林希德及其继任者很清楚地知道审查的压力,(42) 所以他们在正式审查之前很可能已经实行了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尽管如此,枢密院对两版《编年史》都进行了干涉。
1577年12月5日,枢密院致信伦敦主教,禁止《编年史》继续印刷和销售,因为书中对爱尔兰若干事件的记载与该王国的古代记录相左。(43) 在编纂者斯塔尼赫斯特(Stanyhurst)做了解释,修正了错误,财政大臣(Lord Treasurer)出面以后,枢密院才允许该书重新出售。(44) 第二版于1587年1月中出版。(45) 同年2月1日,枢密院致信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惠特吉夫特,要求停止《编年史》的发售,直至完成进一步的检查为止。(46) 枢密院对“霍林希德编年史增补”的“各种东西”表示不满,特别是“有关近年来国事的报道”和“提及有关苏格兰国王事宜”的文字。结果,该版遭到“阉割”,许多页码被注销,包括提及科巴姆家族的部分,约翰·斯托(John Stow)对1586年巴宾顿阴谋的记述以及他对苏格兰和爱尔兰近事的讨论。(47) 审查后的文本以简要概括替代了对巴宾顿阴谋的详细叙述。(48) 这让我们想起蒂尔尼以简短报告取代第一场戏的要求。
以上信息来自各种出处,从中可见枢密院行为的动机主要是政治考虑。他们很关心一个动荡地区的历史记载是否正确,并有意把有关时事的话题排除在外。对《莫尔》的审查大概受到1590年代早期排外风潮的影响。(49) 舞台和书本审查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尤其关涉时事政治的考量。(50) 看来,戏剧审查和文学审查遵循着一些共同的原则,两种系统的联系比有些论者分析的还要紧密。例如1551年意在控制出版业的皇家公告就把印刷商和演员相并列。(51) 剧本出版的审查方式与史书出版的审查如出一辙,有时两种文类还一起遭禁。1599年6月1日,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惠特吉夫特与伦敦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Richard Bancroft)命令书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的主持人和诸会员“不得付印英国历史,除非得到女王陛下枢密院成员的批准;不得付印剧本,除非得到权威人士的批准。”(52)
硬币有两面。一方面,戏剧的表演性使它区别于史书。书里允许的舞台上禁止。喜庆长官删去不祥五朔节那场戏部分是由于舞台媒介的直接性和颠覆性。一个悖论是,剧本的可表演性正是由于其表演性遭到了质疑。蒂尔尼行使了他的职责。另一方面,蒂尔尼行使职责时与演员不无合作。出于个人经济原因他并没有禁止《莫尔》的演出。审查官并不像有些人相信的那么专制独裁。因此,《莫尔》的审查表明伊丽莎白时期的审查官既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又是剧院的方便工具。
注释:
① 本文的英文稿曾在北京大学和美国Ouachita Baptist University联合举办的莎士比亚研讨会上宣读过(2007年6月5日,北京大学英语系),与John Wink教授和胡家峦教授的讨论使我获益匪浅,特此致谢。
②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Harold Jenkins认为,《莫尔》原作于大约1590-1593年,修改于大约1594-1595年。见“Supplement to the Introduction,”The Book of Sir Thomas More,ed.Sir W.W.Greg,Oxford:The Malone Society,1961,p.xliii.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者认为《莫尔》原作于1590年代早期,修改于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死后不久。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者认为原作于1592年末至1595年中,很可能是1592-1593年,修改于17世纪初。
③ sir W.W.Greg ed.,The Book of Sir Thomas More,Oxford:The Malone Society,1911(1961重印),尤其是Greg的“Introduction.”Sir Edward Maunde Thompson,Shakespeare's Handwriting:A Study,Oxford:Clarendon,1916.A.W.Pollard et al.,Shakespeare's Hand in the Play of Sir Thomas Mo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3(1967重印).R.W.Chambers,“Some Sequences of Thought in Shakespeare and in the 147 Lines of‘Sir Thomas More’”,Modern Language Review 26.3(July 1931):pp.251-80.R.C.Bald,“The Booke of Sir Thomas More and Its Problems,” Shakespeare Survey 2 (1949):pp.44-61.
④ 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P.2012。
⑤ Charles Jasper Sisson ed.,William Shakespeare:The Complete Works,London:Odhams,1954.
⑥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2[nd] ed.,ed.G.Blakemore Evan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97.The Oxford Shakespeare,2[nd] ed.,ed.John Jowett,William Montgomery,Gary Taylor,and Stanley Wells,Oxford:Clarendon,2005.The Norton Shakespeare,gen.ed.Stephen Greenblatt,New York:Norton,1997.
⑦ 《莫尔》在Alexander Dyce编辑的本子(Sir Thomas More:A Play,Now First Printed,London:The Shakespeare Society,1844)以前从未印刷过。20世纪重要的《莫尔》版本包括Greg所编(见注3)和Vittorio Gabrieli and Giorgio Melchiori eds.,Sir Thomas More,The Revels Play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0.Gabrieli和Melchiori合编的本子初版于意大利(Bari:Adriatica,1981),1990年和2002年在英国出版了两次。本文中《莫尔》的引文来自两位意大利学者1990年的本子,幕、场和行数在文中直接注明。
⑧ 《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传奇剧、诗歌卷》下,附录一,第403-413页。
⑨ 孙法理在《关于新确认的莎士比亚四部作品》一文中(《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简述了《莫尔》的鉴定过程,可以参考。但孙文在一些细节上不够准确,如认为Alexander Dyce是第一个提出莎士比亚作者权的(应为Richard Simpson),手稿含有六种笔迹(实际上有七种),Thompson于1871至1872年鉴定莎士比亚的笔迹(应该是1916年)等等。另外,孙文显然参考了R.W.Chambers(见注3),典型的如25-26页关于“最明显的例子”的讨论直接来自Chambers 263-5,却并未注明出处。读者可能会误以为是孙独立研究的结果。
⑩ Raphael Holinshed“只是该书的编者之一,近十二个人花了二十多年才完成编写,先后两版也截然不同,第一版1577年,1587年的增补版主要是在霍林希德死后完成的”。见Annabel Patterson,Reading Holinshed's Chronicl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3.“霍林希德《编年史》”是这部史书的习惯名称。
(11)(47) Janet Clare,“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Dramatic Censorship,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0,pp.16,20,p.26.
(12) Greg与两位意大利学者对这段话的解读有一字之差,但不影响文义。最近,学者Diana E.Henderson指出,《莫尔》是“现存含有蒂尔尼‘编辑’和边注的唯一手稿”。这是学者们对这段边注如此重视的原因。见Henderson,“Theatre and Controversy,1572-1603,”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Theatre,vol.1 Origins to 1660,ed.Jane Milling and Peter Thom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46.
(13)(19)(37) William Long,“The Occasion of The Book of Sir Thomas More,”见T.H.Howard-Hill ed.,Shakespeare and Sir Thomas Mo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46-47,p.54,p.52.
(14)(15)(16)(27) E.K.Chambers,The Elizabethan Stage,vol.4,Oxford:Clarendon,1951,pp.285-7,pp.307-8,pp.306-7,p.263.
(17) 1581年之前,喜庆长官的主要职责是为宫廷提供适当的娱乐;1581年的委任状颁发以后,喜庆长官开始负责戏剧审查。
(18)(21)(35)(38)(49) Richard Dutton,Mastering the Revels:The Regulation and Censorship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1,pp.53-79,p.86,p.85,p.86,p.85.
(20) 引文见Dutton 1991,p.80.
(22) Dutton 1997,p.288.
(23) Sisson ed.,p.1235.不祥五朔节指1517年5月1日伦敦市民爆发针对外国人的动乱。
(24) Giorgio Melchiori and Vittorio Gabrieli,“A Table of Sources and Close Analogues for the Text of The Book of Sir Thomas More,”见T.H.Howard-Hill ed.,Shakespeare and Sir Thomas Mo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97-202.下面的拼写名单见该文pp.197-8。
(25) 牛津版编者认为,《莫尔》出自霍林希德《编年史》和Nicholas Harpsfield的莫尔传记。诺顿版编者认为,《莫尔》出自1587年版霍林希德《编年史》、Nicholas Harpsfield的莫尔传记以及Thomas Stapleton用拉丁文写的莫尔传记。
(26)(29)(30)(31)(33) Vittorio Gabrieli and Giorgio Melchiori eds.,Sir Thomas Mor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0,Appendix A,p.230,p.228,pp.231-233,p.228,p.240.
(28) Patterson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编年史》的编写是一项公民事业。表面上看,女王公告和1587年版《编年史》之间有着近三十年的距离;实际上,《编年史》第一版编辑时正是在女王公告前后。
(32) 孙法理译本中,多尔的译名作“陶乐”。
(34) 没有证据表明《莫尔》曾在早期现代的英国演出过(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本文关于历史可表演性的讨论)。20世纪以来,《莫尔》在英国舞台上演出过若干次(1922,伦敦;1938,坎特伯雷;见Sisson ed.,p.1236)。2005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该剧,这是《莫尔》演出最著名的一次。见The Oxford Shakespeare,p.813。
(36) 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66首。Katherine Duncan-Jones注解道:“虽然‘艺术’通常指技艺,而非创造性艺术,‘缄默’的形象说明这里指的是文学审查,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常常要接受审查。”Katherine Duncan-Jones ed.,Shakespeare's Sonnets,The Arden Shakespeare(3[rd] ser.),London:Thomson Learning,1997,p.242.此处“文学”(literature)的说法是一个时代错误,应该是“剧院或剧本的审查”。
(37) Patterson,p.11.Edward Arber ed.,A Transcript of the Registers of the Company of Stationers of London; 1554-1640 A.D.,5 vols.,London:privately printed,1875-,Ⅱ.329.
(40)(44)(45)(48) Patterson,p.12,p.11,pp.11-12,p.237,p.261.
(41)(52) Arber ed.,Ⅱ.436,438,Ⅲ.677.
(42) 霍林希德在《致读者》开头称:“宽容的读者,像我这样,在如此广阔的领域里漫游是危险的,因为如此众多的各色人等可以从各个方面控制我。”引文见Patterson,p.15.Abraham Fleming。
(46)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ed.John Roche Dasent,new series,vol.14,1586-1587,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897,pp.311-12.
(50) 参见Dutton:“我们会看到,蒂尔尼及其继任者做出的干预大部分与时事相关,与当时具体的人和事的影射相关,而非与教条的考虑相关。”Dutton 1991,p.85.Janet Clare称:“看不出一贯的政治、道德或文化标准;相反,历史时机决定了审查官每一次审查的决定。”Clare,p.211.但是,Dutton和Clare的讨论仅限于戏剧审查。
(51) 引文见Patterson,p.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