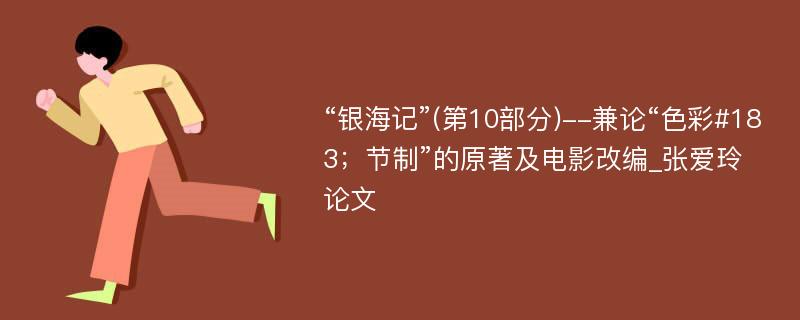
银海遐思录(之十)——也谈《色#183;戒》的小说原作及电影改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遐思论文,原作论文,也谈论文,电影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片《色·戒》在国内上映后,据说全国许多地方的报刊都发表评论文章,众说纷纭,热闹非凡。仅从《电影评介》刊物上,我就看到了不下20篇的有关评论,有赞扬的,有否定的,也有持折中意见的,不一而足。这个“色戒现象”在时下相对沉寂的中国电影评论界似乎颇有“激起一片涟漪”的作用,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和议论一番。
小说作者创作心理窥探
张爱玲这篇万余字(不是如某些评论所说的只有3千字)的短篇小说,写于1950年并于当年就完成书稿,但是却经过近30年的不断修改,一直到1978年才将这篇小说和其它两篇小故事《相见欢》、《浮花浪蕊》结集成《惘然记》出版。张爱玲在卷首语里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三十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在她22岁大学毕业后,不顾家庭极力劝阻,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据说是“深受其品格魅力与才华所吸引”的汪伪政权的一个大红人胡兰成。据某评论材料说,她很可能是从胡兰成那里听到了重庆中统女特工郑苹如为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施行“美人计”诱他上钩,却被丁某发觉而终遭杀害的故事。郑苹如和丁默村显然就是《色·戒》中王佳芝和易先生的原型。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张爱玲如何将这两个人物加以“改造”之后移植到自己的小说中来,以及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创作心理或称心态。
从艺术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位创作者对其生活经历中感受最深的人和事,往往会“感同身受”,甚至会从中找到自己的某种“化身”。我们当然不能武断地说,小说《色·戒》中的王佳芝和易先生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化身”。因为这两对人物既有若干相似之点,又有颇多相异之处。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张爱玲必定从王佳芝这个人物塑造过程中,“放进”了她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包括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感情历程等。王佳芝也可说是书香门第出身,她本是个涉世不深、有朦胧爱国心的清纯的女大学生,这些背景与张爱玲何其相似。王佳芝原本只是为了完成爱国学生们及随后重庆派来的特工头子(老吴)所托付的任务而接近并色诱易先生,对后者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然而当王佳芝感到“和老易在一起后,觉得自己像是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全都冲掉了……”,尤其是当易某用1 1根大金条的代价为她买了一只6克拉的“鸽子蛋”钻石戒指,心想“他还是爱我的”之后,她确确实实是爱上易某了,所以才有对易某说的“你快走”的警告以及最后她和几位同学先后被捕终遭枪杀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张爱玲婚前婚后与胡兰成的感情历程,但从她数年后与胡离异,对胡仍相当关心,甚至去走国民党上层路线(当时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胡多方奔走,以使其免遭“漏网敌伪分子”的指控和责罚的情况来看,她对胡某仍是旧情难忘的。小说结尾处,易先生在下令捕杀王佳芝等几位爱国青年之后,对他家里的那些“黑斗篷”女麻将客们吵嚷着要他请客表情冷漠,“在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小说这最后一笔,不如影片中所表现的易先生回到王佳芝的房间,惘然若失地轻轻抚摸着她的床那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两者所包含的意蕴,读者与观众能同样领会。
张爱玲在她故事集的卷首语里所说的“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个“爱”的对象指的是什么?是指小说本身?是指王佳芝?是指易先生?是指胡兰成?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有一些,才会使她如此执著地“甘心”不断修改了近30年。
我们从文学史上很难看到一位作家会花费这么长时间完成一部仅有万余字的作品,但是因“感同身受”而至“爱不释手”的事例却并不罕见。
小说作者价值观透视
时下很兴“价值观”这个名词,其实这就是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艺术观等等的统称。从《色·戒》这篇小说中的种种描写,结合张爱玲自身的生活和感情经历,不难透视作者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有一篇评论文章称王佳芝这个人物形象是“一次家国叙事的颠覆”,说得颇有几分道理。王佳芝当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她初上舞台演抗日戏以及后来奉命与易先生接触终于“假戏真做”,都出于对同学邝裕民的暗恋。然而需要补充一点:小说作者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家国意识”,这不仅因为她甘心情愿嫁给了一个大汉奸,还由于小说中处处所流露出来的意识和情调。她对爱国学生们可能有少许同情,但行文中对他们的计划和举动不甚恭维,甚至有迹近儿戏的暗示。重庆派来的老吴在她的笔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虽然从“家国意识”方面来说,他毕竟还是在抗日灭伪。我们不知道她与胡兰成成婚后他们家中有没有挤满“黑斗篷”或男性陪客的麻将牌局,但从小说中看来,以麻将桌始、又以麻将桌终的描写只是作为情节发展的线索,并不具有什么批判或揭露的意义。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两句话曾被许多评论文章广为引用。小说中称这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学者说的”,虽然张爱玲借王佳芝之口说“不相信那话”,但小说作者对之显然是颇为欣赏的。我不知道我们大多数男士和女士们对这两句“名言”究竟作何看法?一般地说,男人受到女人“勾引”,不见得都是由于那女人会做出几样好吃的饭菜,更多地是因为女人的美色或别的什么引起男人的迷恋,所以这句话更确切地说应是“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他的眼睛”(欣赏到女人的容貌、体态、品性或其它)。至于“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句话,恐怕我们广大女同胞是不会赞同的。也许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到女人阴道里的路通过她的心”更符合实际情况。然而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却的确在证实那原话。王佳芝钟情于邝裕民而得不到应有回报,又极度嫌恶那个使她获得“性经验”而失去童贞的梁闰生,这个易先生虽是按年纪可做她的父亲的四五十岁的矮子,却可以在交欢之后使她感到“像洗了个热水澡”,消除了心中的“积郁”,也就使易某不仅进入了她的阴道,也同时进入了她的心,以至小说作者不禁写道:“难道她有点爱上老易?”
易某给王佳芝买钻石戒指使她感到“他真的爱我”而最后把他放走,其实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延续和发展。这里,张爱玲鲜明地体现了她的价值观即人生观:情是高于一切的,“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人们不难看出,她在这里仍然流露了对她前夫胡兰成的悠悠思念之情。
一位真正的作家是应该有“家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人为了纪念终身难忘的一段情缘尽可以用30年时间不断改写这段回忆录放在家里留作“永久的纪念”,但作为作家则不同,他或她不应只为了宣泄个人的情感而不顾及其作品的社会效果。我们不否认小说《色·戒》的作者有才华,作品也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但是,罂粟花越是艳丽,其毒性也就越大。
电影改编得失谈
李安对《色·戒》的电影改编堪称对小说原作相当完美的阐释。他可说是“吃透”了张爱玲。影片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细节上的补充。如增添了王佳芝身世、处境和心态的描写:父亲去了英国另娶新欢,对她不闻不问;来到上海后,舅妈对她十分冷淡,还企图侵吞他父亲行前托付的房产;她为了完成任务而“破红”之后,同学们对她冷眼相看;重庆来的老吴把她托付寄给父亲的信,在她离开后付之一炬;她在上海时领救济粮的艰难处境;她看电影时对于加演的战争新闻片表情冷漠而提前离开了影院;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王佳芝与易先生亲密接触以至“有点爱上老易”作了很好的铺垫。更值得注意的是,易某从小说中有点秃顶的矮子换成了影片中由梁朝伟扮演的英姿飒爽、体态优美的标准情人。这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汪伪特务头子在听王佳芝吟唱的《天涯歌女》时,居然可以被感动得润湿了眼眶,内中是多么有“人性”啊。我看到有的评论文章还处处颇为这个大汉奸着想,说他也是在别人(包括日本人和企图暗杀他的人)的“窥视”即监视之下,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似乎也颇为“可怜”而值得同情。这种评价的准则真叫人吃惊。
三场性爱戏当然是李安的“巅峰之作”。只看过“洁本”的观众恐怕难以对影片作出应有的评价。我看到的是香港发行的“无删节本”,从中不难看出导演的精心设计,即从第一次王佳芝被性虐待似的施暴,到第二次男女主人公经过一番调情开始颇为情投意合而翻江倒海起来,再到第三次王佳芝完全采取主动,俩人轮番发动“进攻”,直到双方筋疲力尽方休,此时王佳芝脸上流露出既满足又有些许懊悔(懊悔从此恐怕无法执行“任务”)的神色。这三场床戏在银幕上占有近10分钟的时间,比张爱玲小说中只是隐隐约约地一笔带过,至多用“洗个热水澡”来形容要淋漓尽致得多。
我是从导演阐释小说原作的角度来看电影改编之“得”的。李安确有某些才华,要不然那部颇为沉闷乏味的影片《断臂山》恐很难获奥斯卡金像奖。他是看准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同性恋者正在争取同性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选中这个颇受人们关注的题材,而在艺术处理上颇合美国人的欣赏口味而受到青睐的。
电影最忌陈旧感。李安能发现“新颖”的题材并在艺术上作出“新颖”而又大胆处理,这是使他的影片《色·戒》也能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的重要原因。
我所指的“失”是就影片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效果而言。主要由西方某些“精英”人士组成的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不见得会对中国的历史情况有什么深切的了解。我所接触过的许多西方电影界人士对中国的抗战,包括重庆国民党政府与汪伪政权的相互关系,几乎都一无所知。他们对于模糊“家国意识”的作品更难以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感兴趣的可能只是颇为“新颖”而大胆的性爱场面的处理,只要这些场面“有助于情节的发展”或“有助于深化作品的主题”,他们也会高抬贵手予以放行,甚至给予某种奖项的。听说此片在一些国家遭到禁映或经过较多删节,而在美国是作为“PG”片(即少年观众只能在父母陪伴和指导下观看)发行的。可见,它在国外也不是就畅行无阻的。不仅如此,有人告诉我,他最近从网上看到,《色·戒》被美国网站“今日美国”评为“年度最令人失望电影”,同时被美国女影人协会评为“年度十大耻辱电影”。其评选依据尤其是“耻辱电影的评价”,是否也像我们国内某些网民那样认为此片是一种“汉奸文学”,就不得而知了。上述评选信息我因非亲眼所见,仅作为一说,立此存照。
影片《色·戒》该如何定位
电影与文学作品不同。小说尽可以独自在家里观看。像《金瓶梅》或若干年前有“现代金瓶梅”之称的小说《废都》,过去虽明令禁止,但大都禁而不止,其实禁不禁也无伤大雅。
电影则大不一样。电影具有群众性、形象性尤其是直观性,对观众的视觉和心智都有强烈的冲击力,尤其是那些颇有“艺术魅力”的影片更是如此。前些时候我为《电影评介》写的一篇文章里,曾顺便提到《色·戒》是一部“类似春宫电影,其暴露程度远超过世界色情片的老祖宗法国《艾曼妞》的影片”。有一位年轻晚辈来访时看了这篇文章的底稿后,曾指出我的评价“过于严厉”,同时又颇感兴趣地想知道“春宫电影”与“色情电影”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我这里再把我对他说过的话重复一遍。所谓“春宫电影”是表现各种性交行为的片子或录像,只有极简单的“情节”或完全没有情节可言,只是展示各种各样的性交姿势,而且男女主人公的性器官暴露无遗。这种录像带在国外(如在美国)只能在录像店的“后院”方能租到,少年儿童是不许问津的。所谓“色情电影”与前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不能暴露男女的性器官,而且有相当多的“情节发展”,为男女主人公达到性高潮作充分铺垫。在世界各国电影中,最著名的色情片除法国1974年率先摄制的《艾曼妞》外,当首推1976年法国与日本联合摄制、由世界新浪潮电影重要代表之一大岛渚执导的《感官王国》。此片是根据1936年发生在东京的真实的“阿部定案件”搬上银幕的。影片描写年轻漂亮的阿部定在一家餐馆当女佣,偶然窥见店主人吉藏与他妻子做爱的情景,不禁春心涌动,不能成寐。不久后,阿部定在吉藏一再挑逗下心甘情愿地投入吉藏的怀抱,一有机会,就在一起翻云覆雨,尽情做爱,以至于吉藏说他的“家伙”只有小便时才能得到休息,可见其频繁程度。吉藏为了尽情享受他生活中的唯一“乐趣”,抛弃妻子带阿部定私奔,住到一家旅馆里。有一次,他们在性交时为了体验施虐和受虐的滋味,相互用布条子勒住对方的脖子,被阿部定紧勒住脖子的吉藏突然断了气。阿部定口里叨念着吉藏的名字,用利刃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来,然后她蘸着血,在他身上写了两行字:“阿部定和吉藏永不分离”。……这部影片在表现性交场面时,其颠鸾倒凤的疯狂程度与影片《色·戒》可谓“异曲同工”;在情节构成和主题展示(“为情而死”)方面,也堪与《色·戒》相媲美。《艾曼妞》是1984年我在巴黎看到的,当时正值它的“十周年纪念”,巴黎有几家影院盛映不衰。比起《感官王国》来,《艾曼妞》似乎略为“文雅”些,但其情节发展,即如何通过各种铺垫而达到男女主人公的性高潮,则同样颇有条理并有较大说服力。无论《感官王国》或《艾曼妞》,其暴露程度和挑逗性都不如《色·戒》。《色·戒》中王佳芝(汤唯)和易先生(梁朝伟)不仅性交动作极富挑逗性,而且王佳芝(汤唯)的阴毛昭然若揭,虽没有完全暴露出他们的性器官,但俩人下身紧紧“连接”的展示比起赤裸裸的暴露更具挑逗意味。有一篇替《色·戒》说好话的文章,曾称此片如果引起某些人的“秽思”,其责任不在影片,而在观者本身。多么“奇妙”的逻辑!还有评论说,不应该只看到“性”,而应该看到“人性”。我们说,七情六欲,饮食男女,人之常情。在我们也已经开始重视青少年性教育的今天,对表现性爱的作品人们已习以为常,不必大惊小怪。然而这跟西方一些国家的人士大力鼓吹“性开放”或“性解放”因而任何色情电影甚至春宫电影也都可以“开放”之说,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千万不要将净化银幕的要求看成是“道德说教”式的老生常谈而不予重视。提起“道德说教”,过去美国《海斯法典》连一部影片能允许有多少次接吻镜头都有明确规定,这当然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时代潮流,后来他们又把影片分成若干等级,以规定适于看各该影片的年龄段;在英国,迄今为止对于仅有个别床上镜头的影片仍打上“X”印记,不允许18岁以下少年观看,至于色情片则更不会被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放行。正如当年《感官王国》只能在法国和别的一些国家上映,而被日本警视厅禁映的情形一样。可见,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很重视“道德教化”尤其是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的。
对于影片《色·戒》,我将它定位为“类似春宫电影其暴露程度远超过世界色情片的老祖宗法国《艾曼妞》的影片”,是完全不冤枉它的。人性值得尊重和弘扬,王佳芝这位弱女子的悲惨遭际也值得人们深切同情。但我们如果把“人性”仅仅解释为“性”,未免有点可悲。所谓“色易戒,情难忘”这种评价上的折中主义,也是没有真正分清“情”的各种不同性质,属于一种糊涂的观念。另有一篇评论分析影片中王佳芝临刑前态度从容,甚至脸上还带着某种“胜利”的神色,说这是因为她觉得终于得到了易某的“爱情”,这样,不但自己死而无憾,就连由于她放走特务头子导致几位爱国同学遇难也都可以无愧于心。这种观念就不单纯是一种“糊涂”了。
至于《色·戒》这篇小说(以及影片)是否可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汉奸文学”,这我还没有想好。在我看来,张爱玲正如她笔下的王佳芝,是个不大过问政治、“家国意识”淡薄、容易为情所困的“弱女子”(或如某篇评论所称的“小女人”)。她不是像张资平那样货真价实的“汉奸文学家”。她颇有才气,但也绝不是如某些“张爱玲迷”所说的什么“大师级”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会占有多大的位置。就“色戒现象”而言,我更加担心的倒是我们某些年轻朋友的评价准则。他们往往从国外某些“理论家”那里捡来什么精神分析学、阐释学、叙事学之类的东西,无视作品基本思想倾向,更不顾及客观的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而做一些纯形式上的分析。这可能就是我在上一期刊物的文章里提到的那位美籍教授所担忧的当前国内电影理论工作“不正”或“不振”的现象之一吧。奉劝这些年轻朋友:对于各种“新理论”、“新学说”,我们都需要加以了解,但千万不要为其所迷醉,还是应该多学点马克思文艺理论,包括“传统”的电影理论为好。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深知什么理论有用,什么理论没有用。你要想“影响”电影创作实践,用那一套理论是根本不行的,也不会有人听你;而在一般读者看来,可能会觉得你是在为获取某种职称或完成某篇学位论文而发表这一通议论吧。言词也许苛刻了一些,但我相信自己还是出于一片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