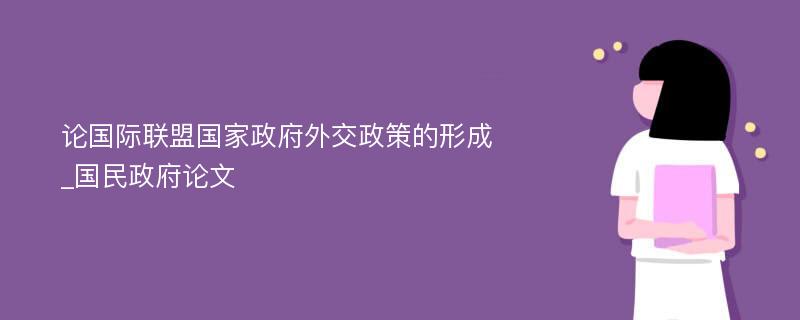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外交政策论文,国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是指国民政府在处理“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形成并实施的对日政策。其内容是将日本侵华事件诉诸国际联盟,静待其裁判,并拒绝中日两国之间就事件的解决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它与“不抵抗主义”政策相呼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两大基本政策。“不抵抗主义”政策是军事方面的,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多;对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学术界研究较少,近年有人对国民政府坚持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原因作了静态考察(注:参见宗成康:《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外交析评》,《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 该文将依赖国联外交政策之所以被坚持是因为国民政府急于“安内”、对国联存在幻想、“信守”国际条约和缺少抗日勇气。),本文拟对其形成作些动态分析。
一
关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说,“当此之时,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立即以武力对付日本之挑衅,这自然是极度艰险之路;二是采取延缓的措施,藉外力压迫日本从东北撤退。此第二途径曾利用于民国十年(1921)山东的僵局。由于日本在东北之举动出于关东军之自发,显然未与其东京之日本首相协商者,故我国采取第二途径,未必完全无望。于是蒋总统决计再度利用国际的干涉”(注:董显光:《蒋总统传》(二),(台)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版,第216页。),于是便有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产生。据此,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似乎完全是蒋介石决定的,是蒋介石个人考虑的结果。这与史实有较大出入。
根据有关资料,最早提出依赖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是蒋介石。事变发生的次日早晨,张学良召顾维钧、汤尔和、戢翼翘、于学忠、张学铭等人商量对策。会上,他们提出了两种处理事变的办法:即直接与日本交涉的办法和依赖国联的办法。主张直接交涉的代表人物是戢翼翘,他提出“派人直接和他们交涉,责他们侵略,要他们提出条件,决定是和是战”(注:李毓树等:《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第87页。);主张依靠国联的代表人物是张学良,他认为直接交涉将无效果,不如依靠国联(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416~417页。)。无独有偶,南京中央政府接到事变的报告后,于19日晚8时召开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会议, 也提出了依赖国联处理事变的办法。这次会议的主席是戴季陶,陈立夫、邵元冲、吴稚晖、陈布雷等要人均与会。据参加会议的邵元冲记载:“会议中众意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注:邵元冲著、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5页。)。 这表明依赖国联来处理事变是参加会议的党政要员的共识。另据这次会议的记录,会议同时决定“电令驻外代表向国际间宣布”(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8页。 )。同日,外交部向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发出指令,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已向日本政府紧急严重抗议,现在日军尚无立即退出占领区域之意态,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措置,使日本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9辑,总第9011页。)。20日是星期天,21日施肇基即向国联秘书长发出照会,指出“本代表奉本国政府训令,请行政院根据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力,立采步骤,阻止情势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9辑,总第9012~9013页。)。这一照会被视为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的法律依据(注:韦罗贝著:《中日纠纷与国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7页。),同时也表明国民政府已将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付诸实施。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从向国联申诉需要一定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和前后时间顺序的情况看,施肇基向国联申诉的行为只能是根据前述外交部19日的指令进行的。上述情况说明,从事变发生到21日蒋介石回南京前止,国民政府已有不少要员主张以依赖国联作为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外交政策,并已着手实施。
那么,蒋介石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关系如何呢?
蒋介石是在19日接到由上海发出的电报才知道日军发动事变消息的。19日晚8时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会议作出决定, “由常务委员电请蒋主席回京”(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8页。)。常务委员吴稚晖、 于右任、戴季陶等于该日亥时发出电报,请蒋“即日返京,以便共议方策”(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8页。)。同时,蒋亦有电致张学良云, “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9页。),未提其它对日政策方针问题。20日, 蒋回电南京国民党中央,仅表示“已即刻回京”(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8页。)。 这些文献都无只字片言涉及依赖国联外交政策问题。这表明蒋介石回南京前并未指示将依赖国联作为处理事变的外交方略。21日下午2时,蒋抵南京, 即时召开会议,商讨对日政策。在这次会上,蒋介石才第一次提出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史料记载:“蒋主席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81页。)。次日上午,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将依赖国联的政策公之于众,并作出论述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皆各国为确保世界和平而订定。余敢信凡国际联合会之参加国及非战公约之签字国,对于日本破坏条约之暴行,必有适当之裁判”(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82~283页。)。上述事实可以证明,蒋介石回南京后,支持并确认了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并公开作出阐述,表明他对国联或非战公约组织将予日本以制裁充满信心。有了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依赖国联处置“九·一八”事变的对外政策得到了更加坚定的实施。对国内,国民政府于23日第一次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内称:“国际联合会之设立,本为防止战争,且谋合各国群力,以防止侵略”。“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断不容以任何意气情感,摇动中央所决定之方策与步骤,以影响一致救国之决心”(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86~287页。)。这表明国民政府实施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之决心十分坚定。在国联,中国代表施肇基语气坚决地表明国民政府的立场。他指出,“中国一大部分领土已在日本军事占领之下,是该国已于交涉之方法以外谋解决,吾人安能再与之进行直接交涉”?国联应依盟约规定程序解决中日问题,除此而外,“非复可以斟酌办理之”(注:韦罗贝著:《中日纠纷与国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3~54页。)。这样,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不可动摇的态势。由此可见,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一经蒋介石确认和支持,成为更为稳定的政策,他在这一政策的形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并不是蒋介石个人考虑的结果,尽管蒋介石在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形成有着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所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整体上看,它在形成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分歧和阻碍。
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党政要员迅速作出依赖国联处理事变的决策,并立即实施,仿佛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这是否表明国民政府早在事变之前就已有筹备呢?也就是说,依赖国际力量来抑制日本是否就是国民政府早已确定的外交政策呢?要解答这一问题,还必须从“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曾出访日本,要求日本政府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北伐统一,但日本方面为维护其所谓在“满蒙”的权益,出兵山东,干涉国民政府的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济案”虽经中日双方直接交涉,以日本撤兵结案,但中日关系因“济案”所形成的阴霾并未随之而消失。尤其是随后日本对“东北易帜”的阻挠,更加暴露了日本强硬推行“满蒙政策”的图谋。这些不能不影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国民政府事实上也开始以一种警觉和谨慎的态度来考虑中日关系问题,如1929年4 月制定的《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就将日本列为第一假想敌国。草案中指出:“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而判断,将来与我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豫想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之日本”;并认为最有可能发生战事的地方是山东,因为对日本来说,“占领山东,其直接为图在华北之势力,而间接则为巩固其经营满蒙之政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这说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从侵华阴谋及中日矛盾的严重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如何应付这种危险呢?国民政府认为,在政治上因美国与日本存在利益冲突,应当“遇事与之声援”;同时又指出,“预想某国将加侵略于我时,应运用外交手腕,以联结其他各国之盟好,使其孤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这里的“预想某国”显系指日本,所要联结的国家当是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欧美国家。正是在此种前提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两项基本内容:一是发展与欧美国家的关系,间接地来抑制日本;二是尽量避免中日矛盾的激化。
就第一项内容来说,国民政府追随美国加入非战公约,聘请欧美国家的有关人员为国民政府顾问, 改善与国联的关系等等。 欧美国家在1928年以后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如同意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积极干预与国民政府有关的“中东路问题”。美国还为国民政府提供救灾的美麦贷款。国联则在拉西曼的计划下,在公路建设、公共教育、农业、文官制度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等方面向国民政府提供帮助。国民政府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处于稳步发展之中。就第二项内容而言,国民政府在“济案”以后,对日本总采取消极态度。外交部长王正廷说,对“济案”的遗留问题,“俟其觉悟再与之交涉”(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七十二辑,(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1977年版,第290页。)。对中日间的关税问题, 王也主张“以不了了之”(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七十二辑,(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1977年版,第176页。), 对当时中外关系中的法权问题王正廷则明确指出“交涉重心,厥在英、美、法三国,本部奋斗之力,亦集中于此”(注:辽宁省档案馆编:《秦系军阀密电》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1页。)。 这表明国民政府外交部竭力避免与日本就敏感问题进行交涉,尤其是不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改善中日关系。不仅外交部是这样,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亦有此种心理。如蒋介石在纪念“济南惨案”一周年时就说,对日本,“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七十二辑,(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1977年版,第16页。)。这话尽管还包含着其它动机,但对日退避之意甚著。又如对国民政府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力的戴季陶,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仍认为:“对日总以不问不闻为唯一无二之好主义,若至于国家存亡有关时,则以死拼之”(注: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如果我们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两项内容的实施情况作一番比较,则不难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联合欧美抑制日本就已成为一项稳定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东北贯彻得最为明显,张学良积极把美国势力引入东北。1931年春,东北当局向美措款1000万银元修筑铁路,后又与美商签订了建造奉天飞机工厂的协定和商谈了建造汽车装配厂的事宜,还与荷兰一家公司签订借款2000万美元以修建葫芦岛港的协定。而对日本,据张学良的要员戢翼翘说,“易帜”以后,张学良“把对日外交全交中央,有问题向中央推”,而碰到不能推的问题就拖(注:李毓树等:《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第72页。)。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鉴于中日关系的状况,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对日政策中整体上形成了一种以欧美抑制日本的政策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日之间一旦有较大冲突就很容易请求欧美国家干预。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9月10日,外交部曾向新闻界表示, 准备将中村事件真相及“日方企图满蒙特殊权利事实,相机向国际宣布”(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9页。)。在这里,国民政府虽然未提出向国联申诉,但希望国际干预中日纠纷问题的意愿已露端倪。因此,从外交政策的发展来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迅速确立并实施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不能不说是其长期以来实行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以前国民政府以欧美抑制日本的政策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也就很容易形成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在决策时的共识,从而使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三
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是请国联主持公道,国联是国民政府要依赖的对象。那么,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与国联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国民政府与国联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中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是国联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在国民党北伐统一告成之前,北京政府仍然是国联承认的中国的合法政府,南京政府与国联没有多少往来关系。“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所有外交途径均列入考虑之中,它包括与日本直接交涉、通过美、英等大国对日本施加影响等,也包括通过国联使事件获得公正解决。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曾致函国联秘书长,要求国联对“济案”干预、调查、公断。函称:“余兹特请执事注意:现在日本侵略行动,实已侵犯中国领土与独立,而危害国际和平;应请执事依照国际联盟规约第十一条第二项,即行召集理事会会议。余亟盼国际联盟知照日本,停止日军暴行,并立即撤回山东军队。国民政府深信我方理直,对于此次事件之最后处决,愿承诺国际调查或国际公断之适当方法”(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140~141页。)。这是国民政府首次向国联申诉。尽管为推动国联作出公断,国民政府也想了不少办法,但由于国联尚未承认国民政府,结果无功而终。这表明国民政府当时就试图通过国联来处理外交事务,其所反映的是弱国在受到强国欺凌时希望国际组织主持公道的良好愿望。它可视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起源。
国联对“济案”不能主持公道,曾一度引起国民政府有关人员不满,因之而对国联评价不高。蔡元培、吴稚晖主编的一本小册子中曾说,“欧洲化之国际联盟于欧洲以外之国际问题,盖绝无设法处决之能力”,“联盟之和平事业,以不许破坏现局为要义”,维持强国的既得利益(注:蔡元培、吴稚辉主编、夏渠著:《国际联盟》,万有文库版,第93、96页。)。还有人指出,“至于东亚事件,该会又以牵及列强利权,不愿与闻”,“丧失其维持世界和平机关之性质”(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何应钦对国联更无好感,认为国联“实为帝国主义用以欺骗宰割弱小民族之工具”(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40页。)。应该说,这些认识较为客观。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在遇到与外国的武装冲突时仍然希望请求国联及有关条约组织主持公道。在距“济案”仅一年多时间的“中东路事件”中,国民政府第二次试图通过国联来解决中苏冲突问题。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方面接收中东路后,苏联军队越过边境,中苏军事冲突发生。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对此事的处理,除通过中国驻德大使蒋作宾借助德国政府保持与苏联的间接接触外,“两次通告非战公约各国,声明我国本和平素旨,遵行公约,随时准备与苏联直接谈判,并为提出国际联盟之准备”(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时期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53页。)。 所谓“为提出国际联盟之准备”,即是准备通过国联干涉来解决中苏冲突。1929年9月19日, 外交部正式通知蒋作宾作好请国联干涉的准备,然后等待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最高机关下令实施。11月,由于苏军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外交部25日电令蒋作宾“依据十一、十七两条(指国联盟约第十一、十七条——引者注)提出国际联盟”(注: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 )。 蒋作宾受令后于26、27两日积极赶办有关事务,国民政府通过国联解决中苏军事冲突的策略大有付诸实施之势。后来,由于英、日反对国联干预“中东路事件”和苏联一再声称拒绝第三者插手中东路问题,国民政府请求国联干预中苏冲突的举措才未被实施。
上述两个未被国联接受的国民政府要求国联干预中国与外国军事冲突的事例说明,“九·一八”事变之前,国联就是国民政府在处理中外冲突事务中很想利用的途径,而且并不因为人们对国联评价较低而放弃。这为“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决策倾向上的前提。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决策倾向呢?首先,国民政府不能以军事力量进行抗击,战而图存;而屈辱求和又为其所不愿,因而总想于和战之外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国联恰好适合了国民政府这一需求。“九·一八”事变后,戴季陶有一番话可以作此注脚。他说:“昔时因无国际组织,各国间亦无相互遵守之公约,故对于外国之侵略,只有和战两途,现在世界既有国际组织,有国际公约,则当然于和战两者之外,有正当之第三途径”(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5辑,总第7944页。)。其次,国联是英、法操纵的外交工具。按蒋介石的看法,英、美、日、苏等国,“在东方,或者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595页。)。既然如此,处在矛盾冲突中的中国在与其中某国发生冲突时,就可以借助第三国来与对方抗衡。国民政府请求国联干预“济案”与“中东路事件”,无非是要借英法来抑制日本和苏联。正是因为上述两个原因,国民政府一再求助于国联。也正是因为如此,国民政府在1929年以后大力发展与国联的关系,开始交纳积欠很久的会费,聘用国联官员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积极参加国联的会议和活动,与国联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并在国联开展竞选非常任委员席位的活动,通过这样一些措施来密切与国联的关系。国民政府在国联展开的一些外交活动也确实收到了成效,王宠惠、吴稚晖、刘瑞恒等被邀担任国联有关机构的委员,国民政府所要求的技术合作也得到批准,中国在1931年成为国联行政院非常任委员。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中国已与国联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为“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上述内容说明,“九·一八”事变以前,国民政府就已形成请求国联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这种倾向不仅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决策前提,而且还推动国民政府发展与国联的关系,为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国民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申诉不像关于“济南惨案”和“中东路事件”的申诉那样在国联受到冷遇,而是受到较为积极而认真的重视。国联在接到中国的申诉后,很快受理,并将中国代表的照会转致各会员国。国联行政院也在收到中国的申诉照会后的次日(9月22日)就开始讨论中日纠纷问题,并很快形成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在英、美、法等大国支持下于9月30日通过。 其内容除要求日本将军队迅速撤至铁路区内之外,还授权国联行政院必要时再行召集会议,继续就中日问题进行讨论。10月3日,日本继续向通辽、 锦州进行军事侵略,国民政府根据情况要求国联行政院提前召开会议。国联行政院接受中国的要求,比原计划提前1天(原定10月14日开会)开会, 并在美国支持下,于10月24日通过了较前更为强硬的决议,要求日本在限期内完成撤兵。这一系列行动说明国联很想在调解中日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国联的这种较为积极姿态对国民政府执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在国联9月30日决议作出后, 国民政府立即按照决议,多次发布约束人民抗日行动、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命令。蒋介石也发表讲话表达对国联的信任。尤其是在10月24日的决议形成后,蒋介石更是称赞不已,认为它是“国联第一步精神的表现”,待以时日,“一定有第二步的精神表现”(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5辑,总第7889页。)。言辞之间,不仅包含着推动国联进一步采取抑制事态发展的动机,也体现了他对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的信心更为坚定。尤其是美国表示支持国联采取行动之后,国民政府中支持推行依赖国联政策的人更多。因此,国联在有关大国支持下对“九·一八”事变采取较为积极的姿态,使依赖国联成为国民政府更为稳定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国联在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和稳定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从动态上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前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样地,正是由于采取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形成了利用国联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突的决策倾向。这种倾向推动中国与国联建立了密切关系,从而为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而国联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较为积极的姿态,也在这一政策的形成和稳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中华民国大总统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蒋介石论文; 国际联盟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九·一八事变论文; 伪满洲国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万历朝鲜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