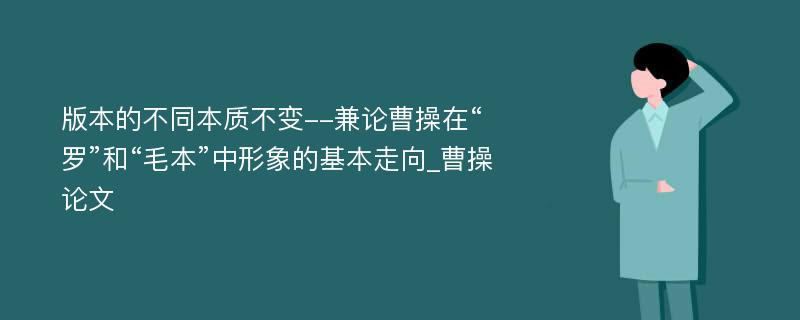
版本不同 实质未变——也谈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质论文,未变论文,也谈论文,倾向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我国古代几部第一流的长篇章回小说,大都存在由于版本不同而引发出来的对人物形象评价的分歧意见。其中,经过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润饰并加以评点的《三国演义》(后文均称毛本),与现已发现的一度被认为最接近罗贯中原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文均称罗本)中的曹操形象,到底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导致了形象本身的质变,从而出现了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现象,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拜读有关宏文伟论,受益良多,同时也觉得在有些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因为它不只是对《三国演义》两种不同版本中的曹操形象的具体评价问题,也涉及对其他小说中类似现象进行研究时某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故略申愚见,以求教于专家们。
一
任何一部经过他人增删润饰的长篇章回小说,特别是象被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由高鹗续成全帙的《红楼梦》那样的小说,都必然会这样或那样地渗入增删润饰者的思想倾向与审美追求。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思想倾向与审美追求的渗入度,必须控制在不违背原著的整体构架和基本艺术逻辑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不是属于正常的增删修饰,这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借鸡下蛋,即借原著中某些情节或人物为引线,或以原著的基本精神为指导,生发开去,另行创作,如《水浒传》的续书《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西游记》的续书《西游补》、《后西游记》等等;另一种是因不满原著而做翻案文章或歪曲文章,写成小说,如俞万春的《结水浒传》(《荡寇志》),完全是反《水浒传》之道而行之;必令生旦当场团圆的种种《红楼梦》的续书,则对原著精神任意加以肢解歪曲。上述两类非正常的续书,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范围。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那些与原著发生共振的增删修饰问题。所谓共振,是指经过增删修饰后的版本,与原著相比,至少在客观上没有改变原著情节结构的基本框架和发展逻辑,也没有改变原著中人物形象的主导性格倾向。被腰斩成七十回的《水浒传》,也许体现了金圣叹认为一百单八将不配受招安的思想;也许金圣叹平添卢俊义惊恶梦的尾巴,只是一种掩饰,他正是要在这种掩饰下,斩去他所不愿见到的招安结局和宋江的叛变行为,使这一形象显得高大一些。但不管评论家持何种见解,都无法改变腰斩本所提供的客观逻辑: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既是梁山义军发展的项点,同时又是走向失败的起点。宋江在这时重又提出的“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思想路线,虽遭到李逵等人的公开反对,但根本无济于事。这条路线的发展逻辑向人们提出:义军的失败迟早必然出现,悲剧的结局是无可避免的。至于是象金圣叹所设计的那样被斩尽杀绝,抑或是像原著那样接受招安,最后落得个兔死狗烹的结局,都没有背离前七十回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至于宋江这一形象,虽然由于腰斩而避免了他亲自毁坏梁山根据地的有关描写,但并不能改变他思想性格中“权居水泊,专待招安”的根深蒂固的一面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发展逻辑。因此,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并没有将一个具有反抗与妥协双重性格的宋江,“斩”成为一个彻底叛逆的农民起义领袖形象,而没有被腰斩的宋江形象,也不过是最终完成了前七十回中这一形象的必然发展逻辑罢了。
再看《红楼梦》的有关情况。被高鹗续成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与曹雪芹未完成的前八十回相比,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所续成的后四十回的确难与原著完全相符,但从整体格局和主要人物思想性格来看,高鹗是力求续到能与原著融为一体的。在曹雪芹的原始构思中,也许不会有宝玉中举,兰桂齐芳之类情节,但宝玉悬崖撒手,贾府获罪被抄以及诸金钗的各种悲剧结局,在总的发展趋向上,是不违背原著已展示出来的“千红一窟(器),万艳同杯(悲)”的悲剧逻辑的。虽然,探佚学专家们可以根据内证外证,推论出后四十回中不少可能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甚至是歪曲了原著精神的情节。但平心而论,在一般并不苛求的专业工作者的眼下,特别是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虽然会有人凭着艺术的直觉,感到后四十回的艺术韵味远不及前四十回,但大都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欣赏与研究,而且不会感到在情节上有太多的枘凿不入,更不会觉得在前八十回中活动着的人物,一到后四十回中便都走了样,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后四十回中的有关续笔,前八十回中的一些人物在整体上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因而将曹雪芹的原著前八十回与高鹗续成的百二十回本相比,便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宝玉、两个黛玉、两个宝钗等等的问题。我们不赞成这样的分析方法及其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因为长篇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体系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是由无数情节和细节进行有序组合而成,其主要情节的走向和性格的主导倾向,只能由其中的大多数因子来决定,个别情节与细节的变异和与原著的枘凿不入,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原著的局部面貌,但难于在实质上改变原有走向和主导倾向。因此,我们在研究上述作品不同版本中人物形象的区别时,千万不宜抓住某些具体情节或细节的不同,以作出置整体倾向于不顾的结论。明乎此,我们再来评价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异同,就比较容易获得解决问题的参照系了。
二
罗本与毛本的区别,不存在像《水浒传》或《红楼梦》那样几十回地被砍去或续上几十回的问题。其特点是毛纶、毛宗岗父子在保持罗本大小框架的前提下,对罗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增删润饰。罗本虽然倾注了罗贯中的毕生心血,堪称集三国故事之大成的杰作。但由于在将历史素材与民间创作揉合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中,对某些素材的利用还缺乏明确认识,因而难免存在取舍不严、锤炼不够之处。这就为毛氏父子留下较多的可供增删润饰的用武之地。另外对于罗本的思想倾向,毛氏父子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在润饰中也会自觉地将其渗透进去,并因此而涉及到某些情节的增删和改动。其间虽然有得有失,但总的来说,经过毛氏父子修改后的《三国演义》,其伦理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在大方向上是与罗本基本一致的。虽然,细加审阅,也会发现二者存在诸多不同处,但从全书看,那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而不是大异中的小同,从艺术上看,则使原著增色不少。这就是为什么毛本一出,就能迅速广泛流传,而罗本倒从此较少受到人们注意的主要原因。那么,毛本是怎样对罗本进行加工改造的呢?这种改造的结果,是不是出现了两种《三国》,两个曹操的现象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对罗本中的曹操形象进行比较全面客观的分析,然后才有可能评论毛本在修改中的得失。
众所周知,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学典型形象的构成,是他或她的全部言行的有机组合,也是作为性格发展历史的情节的有机组合,单个的情节与细节,单个的言行与性格因素,只有融入这井然有序的机体中,才有它存在的价值。在无数的情节与细节、无数的性格因素的有序组合过程中,形成了性格的复杂性及其主导面与多侧面,同时也在书中众多人物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各种对比参照系数。而当这种格局确定之后,对其中个别情节与细节和个别言行的增删变换是不可能使形象在根本上发生移位的,更不是某些插入书中的诗文评论所能改变这种定型了的格局的。虽然,我们并不排斥这些改动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物性格某些方面所起的强化或弱化作用,但只要是在主要方面保持着原著基本情节的框架,保持原著人物性格中的核心因素,就决不可能由于有限的增删润饰而使同一人物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或典型,这就是我们分析罗、毛本曹操形象异同的基本观点。
从罗本中构成曹操形象的全部材料来看,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对其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而罗贯中所认识和所要表现的曹操,是在汉末天下大乱、群雄角逐中的曹操。虽然在作品中并没有抹煞其作为能臣的某些因素,但其性格的主导面是典型的奸雄性格。从罗贯中体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主要观点来看,所谓奸雄与能臣的区别,在论理价值观念上是着重于看其是否维护汉王朝的正统地位。对其“能”与“奸”的具体描写,也以此为标准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大致地说,罗本中的曹操,是被作者置于两个价值系统的对比中来完成的。一是在汉末分崩离析的政局中,以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谋诛阉竖、兴兵讨伐董卓等事件为线索,构成了曹操与十常侍、董卓、吕布、李榷、郭汜等人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曹操是以剿戮黄巾军和讨伐“迁天子,徙百姓”的乱臣董卓等和以维护汉王朝统治的功臣的身份出现于作者笔下的。以此为基点,又有曹操与袁绍、公孙缵、孙坚等属于阶段性同路人之间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他是以“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暗藏韬略”的具有两重性的杰出人物的身份出现的。在这一由两方面的对比所组成的价值系统中,作者对曹操虽非没有微词,但总的倾向是褒扬多于贬抑的。当纷纷攘攘的群雄角逐局面逐渐走向三国鼎立之势的时候,曹操也被逐渐拉入了另一价值对比系统之中,那就是与孙权、刘备特别是与刘备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才能的对比仍是重要因素,但已不存在前一对比中的那种巨大反差,而是构成了一种等量级的对比,这正如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中,曹操在批倒天下英雄豪杰之后对刘备所说的那样:“方今天下,惟使君与操耳。”针对两人在这一轮攻心战中的智能较量,作者议论说:“曹操虽奸雄,又被玄德瞒过。”在这一价值系统的对比中,评价是非功过和表达感情倾向的主要标准仍然是上一轮对比标准的延续与深化。也即是以是否忠于汉王朝的正统地位,是以仁义保天下、治天下,还是以奸雄夺天下、驭天下的对比,正如卷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时刘备自我总结的那样:“今吾与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以皇叔的身份与曹操争天下,这在作者看来,他在政治上、道义上无疑是居于上风的。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情节描写的客观情况来看,刘备并不是全然不玩弄权术的忠厚长者,真是那么忠厚,他就无法在政治风云与残酷的军事斗争中站稳脚跟;曹操也非处处奸险狡诈,事事急功近利的泡沫人物,否则,他就不可能延揽那么多文韬武略的人材,就不可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袁绍,平定北方,就会成为志大才疏的袁绍或残暴专横的董卓之流,而不可能成为三国鼎立之中的强者。不过,从总的倾向来看,作品的确很注意突出刘备的宽厚仁义与忠于汉室的忠贞品格,使之成为其性格的主导面因素。对于曹操,则通过许田射猎,杀害皇室功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以各种方式和名目杀害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各类人物——从近侍、仓官到主簿杨修、刺史刘馥乃至高层谋臣苟彧等,使这些人都成了他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祭品,至于借刀杀祢衡,疑忌杀华陀,也是作者对其性格刻画所用的诛心之笔。当这些因素在实质上大量渗入其才略之中时,便构成了他作为乱世之“奸雄”的性格主导面。在这一点上,罗本是毫不含糊的。在作品所客观展示出来的与刘备相对比的价值系统中,离开了曹操的才略来谈论他的“奸诈”,或离开了“奸臣”的特点来强调其才略,都不符合由整体情节所展示出来的曹操性格的构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在罗本中有若干描写曹操的情节与对他的评议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但这类局部矛盾,并不足以使占主要地位的情节倾向出现根本性的移位,但却为后来毛本的修改提供了依据,这点后文将要论及。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恰恰是在上述两个价值对比系统中,毛本完全继承了罗本的基本精神,由于只是在这种基本精神的框架内增删润饰,因而也就不可能导致曹操形象主导面的质变。
下面且看在第一个价值系统对比中,毛本对曹操的态度。在第四回写及曹操自告奋勇,献行刺董卓之计,王允为之酌酒壮行等时,毛本批曰:
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
写得慷慨动色,仿佛荆卿渡易水时。
当曹操奋力截杀董卓,兵败而归时,毛批曰:
此败非操之罪,众诸侯之罪也。
曹操此一战,虽败犹荣。
第五回写虎牢关大战,关羽自告奋勇,欲斩华雄,袁绍以其为弓马手而加以蔑视,曹操急止之,教人斟下热酒,让关羽饮酒上马杀敌。关羽立斩华雄之后,操又暗使人赍牛酒抚慰当时地位很低的刘、关、张三人。对此,毛本批曰“阿瞒的是可儿。”当曹操在饮宴间慨叹“吾始兴大义,为国除赋……以顺诛逆,立可定也”之际,而众诸侯“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第六回)时,对于曹操言谈间所申述的如何平定董卓的计谋策略,毛氏颇为赞赏,批曰:“所言的是良策”。从诸如此类的批语可以看出,毛氏虽在整体倾向上贬抑曹操,但对他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仍然在某些方面有选择地加以肯定。它至少可以说明,毛氏父子在主观上,并无意于不顾原著的基本情节框架,一股劲儿要把曹操的正面因素全给删削抹煞,因而在第一个价值系统的对比中,曹操形象是没有也不可能被毛氏父子改得正负相反、面目全非的。至于在与刘备相对照所构成的价值系统中,毛本的修改,是否会使曹操形象完成了由英雄到奸雄的质变,则需要将增删情况进行全面的客观对比分析,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三
据不完全统计,毛本对罗本的增删修饰,大至对个别情节大刀阔斧地增削,小至对个别字句的改动,不下千百处,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与曹操形象有关,而这有关部分中的重要者也有六七十处之多。从这些重要增删处看,有删削曹操正面因素的地方,也有增加其正面因素的地方;既删去了某些贬抑他的负面文字,也增添了一些贬抑他的负面文字,决非一味只删正面因素和平添负面因素。这些增删修饰,或出于艺术上的考虑,或着眼于思想上的褒贬,或二者兼而有之,需要进行全面分析,而不能只强调某一面,而忽视与之相连的另一面。
从艺术处理角度来看,小说的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绝大多数有成就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基本创作原则。我国古代优秀小说,就其主要倾向来看,也莫不如此。但由于传统教化观念的渗入,民间说书形式的影响,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在以形象感人的同时,也往往程度不一地插入某些诗文形式的评语。这类评语中,有的与情节的发展融为一体,有利于表达作者的是非观念,但过多地特别指点,也会起着阻碍情节脉络畅通的消极作用,而那些掉书袋子、炫耀才学和与情节发展不大相干的评语,更是破坏艺术完整性的赘疣。这种情况,在罗本中也存在着——它在通过情节描写来表明倾向的同时,又不厌其烦地大量引用诗文或用叙述者的语言来评头品足,而且有不少前后重复或互相矛盾之处。对此,毛本作了大刀阔斧的删削加工,这无疑有利于更多地让形象本身来表明自己的美丑善恶,有利于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这类删削修饰,并不一定纯然是出于修改者的褒贬态度。比如罗本卷二《刘玄德斩寇立功》中对曹操出场时的一段概貌性描写,毛本只保存了“为首闪出一将(罗本作“英雄好汉”),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这两句外貌勾勒的内容,删去了对其才能的介绍:“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胸内熟谙韧略。”这段把他既比齐桓、晋文,又比赵高、王莽的话,不过是同一节中所写许劭对他的评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的具体化,删之既使文字简洁而意不相重,又不影响作者的褒贬态度,还避免了叙述者的特别指点,删掉有什么不好呢?在袁绍、孙坚、周瑜以及其他许多人物出场时,罗本都有类似的套语介绍,毛本不管其倾向如何,大都予以删削,足见其主要是从艺术表现着眼的,并不完全是出于贬抑曹操的需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罗本在《曹孟德许田射鹿》中,借伏完之口,大骂曹操“真乃赵高也”,这该是正中毛氏父子下怀之语,但也被毛本删去,又作何解释呢?又如罗本《夏候惇拔矢啖晴》中,在写及郭嘉论操有“十胜”,绍有“十败”之后,紧接着又写荀彧论操有“四胜”。“四胜”的内容并未超出“十胜十败”的范围,毛本删去“四胜”,完全是为了避免累赘重复。
这类主要从艺术提高角度着眼的删繁去重之处,虽然也涉及思想上的褒贬,但这一修改原则并不只是用于曹操,也同样用于曹操的对立面形象。比如,罗本卷五《曹公分兵拒袁绍》中写及陈登劝刘备写信向袁绍求救,以敌曹操,刘备顾虑自己不但与绍无恩,而且还并了他的兄弟,绍将拒绝求助。陈登便建议刘备向郑玄拜求书信,然后差孙乾送往袁绍处,接着有如下一段描写
绍览(郑玄书信)毕曰:“刘备灭吾兄弟,当复其仇!”孙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不从耳。”绍曰:“吾闻玄德世之杰士,吾当救之。”
这里写袁绍阅信后,先是表示拒绝,并声称要向刘备复灭弟之仇,经孙乾轻轻一说,其态度便来了个180度大拐弯,决心发兵相助,这就显得有点不合情理,而托郑玄写信求助的事,也似可有可无。对此,毛本第二十二回改为
绍览毕,自忖曰:“玄德攻灭吾弟,本不当相助;但重以郑尚书之命,不得不往救之。”
这样一改,指出了袁绍由不愿相助刘备到不得不相助的原因,是碍于郑玄情面(当然也有其内心深处的个人打算),便显得情当理合了。毛本改动后,加批语曰:“袁、刘素不相亲,却用郑玄联络之,事出意外。”这实际上是说明他之所以要如此修改,主要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如果只是为了贬曹褒刘,大可把罗本中袁绍赞扬“玄德世之杰士”这类话保存下来,以光大刘备形象,但毕竟没有采用这种硬塞的办法,可见毛本是比较重视艺术上的斟酌的。
还有一种值得提出来的现象,那就是毛本为了褒刘,对刘备属下的人,也往往褒之,这当然反映了毛氏父子的思想倾向,但这也不过是对罗本中原有倾向的强化,而且也并非不加选择的一律强化,如罗本卷三《刘玄德北海解围》中写刘备与管亥对阵时,对关羽有这样一段描写:
太史慈却待向前,一匹马早先飞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读《春秋左氏传》,武使青龙偃月刀。云长径取管亥。两马相交,众军大喊,正如燕雀之物,而慕冲天之栖;大羊之蹄,而移近日之步:势不可为也。量管亥怎敌云长,数十合之中,青龙刀起,劈管亥于马下。
这段文字,毛本删改如下:
太史慈却待向前,云长早出,直取管亥。两马相交,众军大喊。量管亥怎敌云长,数十合之间,青龙刀起,劈管亥于马下。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毛本将罗本中赞扬关羽文武全才和形容关、管对阵时褒关抑管的文字全给删去了。这当然不是不愿意褒扬关羽或有意削弱对他的褒扬,而是为了避免那些落套的介绍,并使文字简洁化。罗本中这类落套文字所包含的内容,在对关羽一生的描写中,于他处多有所见,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致成赘疣,由此也可以推求,毛本删削某些在罗本中褒扬曹操的地方,也不一定仅是为了贬曹。不承认这点,也就失去了评价毛本删削刘、关等人正面因素的对等原则,就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之中。
当然,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样,主要从艺术着眼的增删修饰,最终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思想内容的表达,但它与纯粹出于思想褒贬的增删毕竟是有区别的。这种情况,也体现在毛本对罗本某些诗文评语的增删修饰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就罗贯中加工整理的原始依据来看,其中当包含着民间传说成分、根据史书进行艺术加工的成分和直接引用史书的成分。这三种成分的融合渗透,既非完成于一时一地,也非出自一人之手。正如前面已提及的那样,罗贯中在进行加工创造的过程中,虽然在宏观上有自己的主心骨,但有时也不免陷入莫知所择的惶惑之中,于是便不可避免地把某些见仁见智的认识反映到作品中来,这在引用他人诗文评语上显得尤为突出。对此,毛本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其间固然直接表明了毛氏父子对某些人和事的主观态度,但又并不尽然。从对曹操的评价来看,直接表明这种态度的,莫过于对在曹操死后罗本所引诗文评语的删改。在罗本卷十六《魏太子曹丕秉政》中,除引用司马光、陈寿等赞扬历史上曹操的功德等评语外,还引用了前贤以及唐太宗、晁尧臣等的诗文评语,它们的是非褒贬视点各不相同。照搬这些文字来评论经过艺术加工后的曹操形象,就难免显得堆砌累赘和莫衷一是了。毛本第七十八回删去了司马光等史论中的评语,并综合四首诗文的内容,改写为《邺中歌》,以表明对曹操“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的看法。这样修改,既把原诗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语调和成为代表作者观点的看法,也避免了堆砌累赘之弊,这在艺术处理上无疑是成功之笔。
有的删削,孤立地看,似是为了贬曹,但联系全书来看,又不尽然。比如,曹操死后,罗本所引司马光和陈寿高度评价曹操的赞语,全被毛本删去。看来,这似乎是大删曹操正面因素。但刘备死后,罗本在《白帝城先主托孤》中所引陈寿肯定刘备的话:“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同样被毛本删去;罗本在《刘玄德败走江陵》中,引用了习凿齿盛赞刘备的一段话:“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也被毛本删去。如果毛氏父子只是一味热衷于褒刘贬曹,大可以删此而留彼,以突出刘备的仁德。但竟一视同仁,全予删削,看来还是从艺术表现角度来考虑的。这一情况,还可以从对评价孔明、关羽、张飞等人的诗文的删削中得到印证。罗本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中,孔明死后,引用了陈寿等十余人盛赞历史上孔明的诗文,几乎成了弘扬孔明功绩的诗文选。这样暂停情节的运行,不厌其烦地转引历代人的诗文来为孔明唱赞歌,固然表明了作者对他的崇拜,但对于情节结构的疏畅、紧凑显然是有损的。对此,毛本大刀阔斧地加以删削,只留下白乐天“先生晦迹卧山林”、元微之“拨乱扶危主”以及杜甫“长星昨夜坠前营”三诗。这三首诗,一以当十,完全可以涵盖孔明一生功绩。这样处理,在艺术上显胜罗本一筹。罗本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中写及张飞死后,作者引用了六篇诗文来评议张飞,毛本删去五篇,也起到了与删削评论孔明的诗篇类似的作用。
另外,罗本中的人物对话,有时引经据典过多,掉书袋子过甚,某些书札、文告,冗长拖沓,或照搬史书,其中也有涉及曹操形象的内容,凡此种种,毛本都力求改得简洁明了,这也主要是从艺术着眼的。
严格地说,罗本中的这些诗文评语及毛本对它的增删修饰,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已由大量的情节与细节描写所完成了的曹操形象,而曹操形象本身的基本倾向,罗、毛本又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类第三者口吻的指点评议,与读者的批评是相似的。它与对作品本身的增删修饰,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码事。作为评点者,他们可以直接表现其帝蜀寇魏、褒刘贬曹的鲜明倾向。作为增删者,虽然也会将主体意识渗入其中,但毕竟只能在尊重罗贯中笔下艺术形象本身逻辑的前提下去增删润饰,否则,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就不如另起炉灶去创作一部同题材的小说。要将一个在罗本中已经定型了的完整的曹操形象,通过增删修饰而变成一个与原倾向完全不同的形象,而又不改变全书的整体构架和书中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大刀阔斧地改变曹操形象自身的许多重大活动和言行,那是难以思议的事。当然,从接受美学观点来看,这类评点,也是那些历久不衰的文学作品其所以获得生命力的因素之一,但毕竟改变不了作者在情节描写中,通过语言符号所明确表示出来的客观倾向性。无庸置疑,毛本在修改过程中,自觉地强化了罗本中原有的正统观念,但毛本并没有因要强化正统观念而忽视艺术逻辑的合理性原则。与此相连,它对诗文评语的增删,虽然也融入了属于正统观念的主体意识,但艺术原则的制约仍然是第一位的。看不到这一点,就容易脱离整个形象的具体描写,片面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倾向的干预作用。
四
从思想褒贬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必须对增删的内容进行全面分析,而且在考虑为什么如此增删时,仍不宜忘记艺术逻辑的作用。
客观地对照罗、毛本的异同,就不难发现毛本对罗本的修改,在不少地方是有利于显示曹操的正面因素和隐慝其负面因素的,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删贬曹诗。如在写及曹操师败淯水、车胄被杀、许攸被杀以及大宴铜雀台(二诗删一)等情节后,罗本都有诗直接或间接贬曹,责其“奸雄世莫同”“穷奢极侈兴群怨,诈力欺天天肯眷”等,全被毛本删去。二是删贬曹语,如罗本《青梅煮酒论英雄》中,当刘备将惊雷失箸事掩饰过去后,作者评论说:“曹操虽奸雄,又被玄德瞒过”,又让刘备对关、张说:“曹公只可同忧,不可同乐,若心一变,死无地矣。”这些都被毛本删去。又如罗本在《曹孟德忌杀杨修》中,指责曹操“平生为人,虽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于己”,毛本删去了这段话。类似情况,还可举出一些。三是删贬曹操情节或增加褒曹操情节,前者如罗本《曹操勒死董贵妃》中,写操“将与董承来往者黜退,重者责入逆党论。似此不可胜数,皆被其害。自此,许都内外大小官员莫敢交头接耳。”毛本删去了这段交代。后者如陈琳为袁绍作檄讨曹,辱及曹操父祖。但陈琳被俘后,操怜其才,不念旧恶,仍用为从事。这段有利于表现曹操“大度”的情节,是由毛本增写的。
当然还要看到,毛本也相应地从上述几个方面删削了罗本中的一些褒曹成分和新增了贬曹内容,其重要者,大都已为有关文章所指出,这里不再赘述。虽然,经过毛氏的修改,贬曹成分比罗本更强一些,但总的来说,毛本仍然保存了罗本中曹操形象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在对曹操形象进行定位分析时,如果只强调了毛本删去罗本中曹操正面因素的一面,而避谈其删去曹操负面因素和增加他正面因素的另一面,就无法使人看出罗本和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全貌及修改者的全部态度,从而容易给人这么一种印象:罗本中曹操形象的主导面是好的,但因毛本的删削,使之变成了一个主导面是坏的典型。如果我们全面地来分析这类删削,结论就不会这样了。比如,罗本写曹操攻破下邳后,有“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白门曹操斩吕布》)的话被毛本删去了。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删去了这两句有利于曹操的话,而没有同时指出毛本在第十九回中,将这两句话改写为“曹操入城,即传令退了所决之水,出榜安民”这一事实,就难免失之偏颇。如将二者客观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不仅“出榜安民”几字包含了不扰良民之意,而且使前文所写曹操决沂、泗之水以掩下邳的描写有了交代,弥补了罗本在这一点上的疏漏。又如,罗本在同一节中,写陈宫被俘,不愿降曹而请出就戮时,“操起身而送之……与从者曰:“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怠慢者斩!’”毛本将这一段改为“操起身而送之……谓从者曰:‘即送宫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怠慢者斩’。”两相比较,罗本的分量虽然重一点,但很难说有原则区别,更不会因这种区别而使曹操形象的色质发生由红变黑的根本性变化。
毛本在涉及对曹操形象增删问题的重要之处时,删褒增贬与增褒删贬的正负处理,比之罗本来看,虽呈降调趋势,但对于一部洋洋70余万言,由千百情节与细节所组成的小说来说,这种降调式的增删,决不可能使本来不失英雄本色的曹操蜕变成为奸雄的典型,而只可能在局部上起到强化或弱化的作用。如果只是从个别事例出发来强调某一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忽视与之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很容易把罗本的基本倾向看歪,而将毛本的降调处理夸大到质变的程度。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首先,从对待人才的态度来看,罗本通过曹操哭典韦、厚遇刘备及关羽等情节的描写,的确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延揽人才方面的某种风度。如果作品仅仅是强调了这一面,我们当可视其为唯才是举,求贤若渴的具有博大胸怀的政治家。但当我们看到作品中大写特写曹操傲睨和忌恨乃至杀害人才的许多情节时,特别是感到这一面比前一面写得更为生动形象时,就不宜抛开这被作者更为强调的后一方面而去片面肯定其前一方面了。而应当从两方面的辩证联系中去寻找为作品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曹操形象的主导面。且以厚遇刘备一事为例来作一分析。为了说明问题,无妨先简述一下罗本中的有关情节:先是刘备在徐州时,曹操企图用“二虎竞餐”和“驱虎吞狼”之计消灭刘备、吕布等人,均未获逞。后吕、刘反目,刘备投奔曹操,荀彧等劝其杀刘备以除后患,操不同意,认为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因而资助刘备,使配合攻吕。刘备被吕布打败后,再投曹操,汉献帝便趁机认刘备为皇叔。这时,荀彧等又建议除备。操说:“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向外耶?”还针对刘烨的看法,胸有成竹地说:“好亦交三十年,恶亦交三十年。好恶吾自有主意。”然后一方面与刘备同舆共席,“恩若兄弟”;另一方面又“青梅煮酒”,进行试探,并作出了“玄德为无用之人”的错误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让刘备带兵外出“截击”袁术。及至发现受骗,又立即派人追赶。当许褚复命,转述刘备挑拨曹操与郭嘉等人关系的那番话时,操又转责郭等。及至郭等提醒他又被刘备瞒过时,他才笑着说:“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怨乎。不罪汝等,汝等勿疑焉。”实际上,正如作品指出,“此是曹公半疑半信”处。
从上可见,曹、刘间都是互相利用,彼此勾斗。备之投操,固是“勉从虎穴暂棲身”;操之留备,又何尝不是在新的情况下对“两虎竞食”、“驱虎吞狼”之计的变通运用。他对刘备作好了“好交”、“恶交”的两种准备,“好”则为我所用,“恶”则另有对策,所以虽可谓热诚款待,但决非以诚相待。惟其如此,他便外宽内紧,煮酒试探,直到产生刘备无大志的错觉后,才任其叛离而去。在追不回来而又“半疑半惑”的情况下,他又顺水推舟,“高姿态”地说了那番不予追究的话。而且当他真正明白过来后,便暗令车胄谋害之,并不是任其溜之大吉。因此,与其说这些描写表现了曹操的恢廓大度、博大胸怀,倒不如说反映了他在与刘备的这轮较量中,机谋还不够成熟,以至屡被刘备瞒过而失误。毛本对这段描写改动颇大,如删去了关于“好交”、“恶交”及“恩若兄弟”等文学,改写为曹操认为留刘备在许都,实则在他掌握之内;又如在“煮酒论英雄”一节中,删去了曹操对郭嘉等人忠谏之言和刘备的挑拨言论所持的将信将疑、犹豫寡断态度的描写,只写他虽疑刘备,但认为有自己的将领朱灵、路昭在彼监视刘备,料其不敢变心,因而不再追他。这类改动,虽揭去了曹操恢廓大度的幌子,更不利于说明他的好处,但联系其平生谲诈多谋,果断自信的一贯特点来看,倒符合曹操的性格发展逻辑和他在彼时彼地的思想逻辑;因而使人更觉情当理合。这种改动,应该说在艺术上是成功的。
其次,从对待人民的态度来看,如果我们只看到罗本中写曹操在征张绣和征袁绍时不许掳掠扰民的号令,以及他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话来教育部下的这一面的话,当可视曹操统帅的军队是“泽如凯风,惠如时雨”的仁义之师。但如果联系到他虐民的一面来看,联系到罗本在这一问题上对刘备的描写态度来进行对比,又不能不使人感到,曹操的所谓恤民,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己。在这一点上,罗本和毛本描写的客观效果基本是一致的。通观罗、毛本全书,凡涉及与人民关系的描写,对刘备可说是无保留地加以肯定,且有“携民渡江”的重点情节来突出其“爱民”;对曹操则褒贬相间,着墨也不甚多。作品第一次写及曹操与人民关系之处,是他为报父仇而兴兵讨陶谦时,竟迁怒于民,命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因而“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罗本《曹操兴兵报父仇》·毛本改后一句为“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残酷至极。在攻寿春时,他“纵军入城掳掠……寿春城中,抢掠一空”(罗本《曹操会兵击袁术》。毛本删去“纵军入城掳掠”);在对袁战争进攻南皮时,因百姓不愿为其敲冰拽船,他便命令捕杀百姓(罗毛本同),后虽有所通融,但至少可以说明,他在一怒之下,是可以视民命如草芥的。很明显,此类情节,都是作者为了揭露曹操的残民以逞而设置的。但作品又确有几处写他关心民事的地方,如征张绣时不准践踏麦田,攻袁绍时严禁下乡杀人鸡犬,不教枉废民业,让冀州百姓于后军就粮以及减免租赋等。这种虐民和“恤民”行为,似属不可调和的两极,实际上,“虐”也好,“恤”也好,都统一在“利我”这一点上:徐州屠戮,是报杀父私仇;南皮杀令,是解进军之急;寿春纵掠,是迎合军心。而各种“恤民”措施,则是为了树威信,买民心,以便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攻冀州时,他因禁令使军民震服,便“心中暗喜”;向襄樊攻刘备时,刘烨建议他“必用先买民心,民心若定,纵兵微亦可守矣。”(罗本《刘玄德败走江陵》。毛本删“民心若定”等)这都可以作为他以利己为中心的“恤民”的注脚。
在曹操的“恤民”措施中,还有一引人注目之处,即仓亭大捷之后,他否定了诸将要求一鼓作气,攻克冀州的要求,坚持要待到老百姓秋收后再采取行动,这无疑是于百姓有利的决定,不宜抹煞其意义。但这是不是为了“恤民”而不顾及军事上的胜负了呢?(当然也不宜这样)恰恰相反,他首先考虑的还是军事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禾稼,他在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冀州粮食极广,审配又有机谋,急未可拔。见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废民业。姑待秋后,取之未晚。”(罗本《曹操仓亭破袁绍》。毛本删“功又不成”)可见他作出秋后取冀州的决定,是以在军事上“急未可拔”为前提的,当时如果急攻硬取,不仅“功又不成”,而且还会“枉废民业”,造在不良影响,这就是他当时的完整想法。事实上,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曹操的分析是合理的。他的决定,正好是否定了将领们那种虽合乎兵书的教条、但不符合当时军事和政治利益实际情况的要求。至于曹操随后所说的那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话(毛本删去),不过是为了说服众将服从他的决定所设的堂皇之辞,即使有“恤民”因素,也不是他作出决定的根本出发点。关于这类描写,罗、毛本虽互有不利或有利于曹操的异文,但总的来说,毛本并没有改变罗本在这方面对曹操所采取的基本态度。
历史上有建树的政治家在思考成功之道时,几乎没有不知道民心的向背在政治斗争这一天平上的分量的。作为汉末逐鹿天下的敌手的曹、刘,都必然会很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注意收买民心。这种收买,有的体现在大造舆论上,有的体现在由政策法令等所规定的具体措施上。从这两个方面的客观描写效果及作者的态度来看,曹操的不践麦田,禁杀鸡犬以及减免租赋等,确属具体措施。但不要忽视,作品在写及这些时,大都有玩弄权术的强烈暗示;而在写及刘备的有关情况时,则采取比较明朗的褒扬态度。而且,写刘备入川之际,“号令严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斩之。于是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罗、毛本同)这与曹操的不践麦田,禁杀鸡犬,是没有原则区别的。曹操抚定冀州时,有减免租赋的措施;刘备屯驻新野时,“政治一新”,人民用“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罗、毛本同)的谣谚讴歌他,其中难道就不包括某种利民措施吗?因此,用刘备作参照系来看曹操的民本思想,作者显然是更倾向于肯定刘备的。在这一点上,毛本基本维持了罗本的原貌。
从整个形象来看,罗、毛本对曹操形象的描写,都是注意辩证地表现其性格内涵的。既重点写出了他那“奸雄”的主导面,又能“恶而知其善”,不回避对他某些正面因素的描写,而且将“恶其丑”和“知其善”这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贯串形象的始终,但恶其丑的一面是作为主导面来描写的。因此,在开头不久便写曹操杀吕伯奢一家这一使人怵目的情节,这不仅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也是为后文写及曹操许多“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行为张本。正如在他出场不久,便写他发矫诏讨董,是为后面写他某些正面因素张本一样,正负两面的描写,都是必要的。
总之,实事求是地指出罗、毛本的差异和毛本贬曹倾向更强烈一些,这是必要的。但应看到,这种差异,只是量的增减,远远没有构成质的变化。因此,对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评价,在总的倾向上,只能得出基本一致的看法。
标签:曹操论文; 刘备论文; 曹操后人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三国论文; 性格改变论文; 水浒传论文; 袁绍论文; 奸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