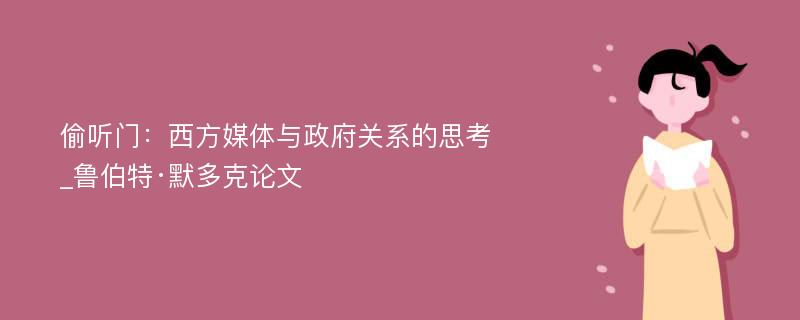
“窃听门”事件:西方传媒与政府关系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件论文,传媒论文,关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犹如投向英国社会的一颗炸弹,其爆炸所引发的冲击波已远远超出媒体圈,波及到了包括首相卡梅伦在内的众多重量级政治人物。在这次事件中,人们有诸多疑虑,以捍卫自由自居的英国媒体为什么反而成了侵犯民众隐私的罪犯?政治人物与默多克的新闻帝国究竟存在何种联系?这个事件对英国政坛的影响有多大?
三条线索、三大挑战
近期的美国新闻集团在英国的子报《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引发了各方的讨论。该事件本身贯穿着三条线索:
第一,党派之争。长期以来,默多克被称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默多克支持哪个党派,哪个党派就会胜出。默多克曾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结成联盟,连续三次在竞选中支持保守党,以及现任首相卡梅伦。虽然前任工党首相布莱尔和布朗的当选也得益于新闻集团的造势,但多数时候新闻集团下属报纸都力挺保守党,因此工党一直耿耿于怀。窃听事件曝光后,工党及反对默多克全资收购天空卫视的势力趁机呼吁,保持一个国家媒体多元化和相互监督的重要性,避免默多克集团滥用他们所占据的强势媒体地位,并希望借此事件将默多克挤出英国传媒市场。
第二,数字电视平台利益和安全之争。2008年英国开启下一代数字电视平台建设,而英国的天空卫视(BSkyB)是英国第一家卫星电视,在英国的影响力巨大。考虑到数字边疆和文化安全问题,英国数字产业并不希望外资过分染指乃至控制英国的数字文化产业。
第三,伦理之争。从《世界新闻报》最初涉嫌窃听被视作个案、个人行为,到一系列窃听丑闻被公布,到前首相布朗要求调查自己被窃听事件,到窃听失踪女孩米莉事件,新闻集团下属的媒体不断挑战着新闻伦理、社会伦理的底线,以至于从个案被妥协到引发众怒,这就为后来的英国朝野上下要求彻查窃听事件,阻止默多克收购天空电视台奠定了伦理和普通群众基础。
“窃听门”事件不断演进、延伸,凸显了三大挑战:
挑战人们对新闻基本功能的认识——传媒业究竟是信息的提供者,还是观点和意识的提供者?
挑战媒介伦理底线——传媒业究竟是从前门把受众需要的信息送到门口供人们挑选使用,还是从后门把受众的信息偷走供别人娱乐和自己赚钱?
挑战我们对西方新闻理念的认识——迄今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和理念中,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纵观“窃听门”事件过程我们发现,英国政府和美国新闻集团英国公司彼此的关系如此之深,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关系模式的界定。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单纯的媒体收购事件,竟然广泛涉及到政府、产业、文化、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尤其是事件本身暴露出传媒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者震动最大。要充分认识这个关系,还需要从历史和辩证的视野来看待和研究。
传媒业和政府的三大关系
历史上来看,贯穿西方传媒业和政府的关系有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基本关系。用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父子的话来说,“控制某一工业方法之一是先使它成为垄断企业,然后再要它的董事们对工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负责”,“新闻出版事业是属于统治者”。从产业分类来说,传媒业兼跨第一和第二大部类,既有摄像机、编辑机等属于生产资料性的产业,也有关于围绕内容生产的采、写、编、评等服务业,从宏观上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法律和许可权力等对整个传媒业实施管理,这就决定了传媒业绝不可能独立于政府来行事,这就是传媒业和政府最基本的关系。
第二,微观细分关系。从微观角度来看传媒业与政府的关系,还体现在商业、资本和文化变迁上。
从商业和资本角度来看,西方传媒业的发展是伴随商业发展、资本扩张的进程开始而开始,发展而发展的。16世纪早期报业以传播商业信息为主,政治信息也是服务于商业的发展。早期资本自由贸易对于行情和信息的渴求催生了一些“搜集信息的机构”,这些人员被称为“采访者”和“报道者”,威尼斯和欧洲的一些商业城市先后出现了手抄报纸。但这样的手抄报纸并非单纯的商业信息,其中夹杂了一些地方政局稳定与否,战争进展情况的报道等政治信息,甚至还有针对宗教的批评性言论,这就直接触犯了政府和教皇并遭到限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早期报业服务于商业的本质。
西方传媒业的发展同时也和资产阶级革命、西方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步进行,走过了一个从“消息化”到“政论化”到“报道化”的过程。
17、18世纪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报刊业发挥了一种反抗封建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维护资本利益和资本主义秩序的宣传、鼓动和启蒙作用。在资本势力下,传媒也客串着监督政府和监督资本的“扒粪”作用。到了19、20世纪随着广播和电视的产生,报纸从“信息纸”变成了“观点纸”,广播和电视业演变成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延伸。此时,传媒业已经彻底演变成为资产阶级舆论和扩张工具了。从19世纪末成立第一家报团史克利普斯-麦克雷报系(Scripps-Mcrae League of Newspaper)开始,逐渐形成了跨国、跨媒体、垄断的信息产业集团,隐含在记者被称为“第四等级”之后的,是传媒业构筑的庞大的隐形传媒帝国。
窃听门事件回顾
7月4日《世界新闻报》窃听失踪少女遭曝光
7月6日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对《世界新闻报》窃听案进行独立调查
7月7日默多克新闻集团宣布关停《世界新闻报》
7月10日《世界新闻报》因丑闻正式停刊
7月12日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另两家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也深陷窃听泥潭
7月13日新闻集团宣布放弃收购天空广播公司
7月14日英国逮捕9名涉案人员,美国FBI介入调查
7月15日默多克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最高级别经理、新闻国际首席执行官丽贝卡·布鲁克斯辞职。几小时后,新闻集团旗下道琼斯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斯·辛顿(曾任新闻国际总裁)辞职
7月16日默多克在英国各大报纸刊登道歉信
7月17日新闻集团前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被逮捕,后获保释
7月18日《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揭发人身亡
7月19日默多克父子就窃听丑闻出席英国议会听证会接受质询
7月20日英国首相卡梅伦接受议会质询
7月22日新闻集团纽约总部秘密“大脑室”疑为窃听中心
7月23日默多克之子被指在英议会作伪证
7月25日英国镜报集团每日镜报等多家报纸被揭发窃听,并宣布展开自查,9月公布结果
传媒业和政府之间还有一个微观性属关系。不同的传媒集团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而服务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和方向,因此,笼统来说“传媒集团”与“政府”的关系只具有理论意义,具体到某些现实问题上,就需要追溯某传媒集团与某政党或者利益集团的关系,则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哲学博弈关系。西方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实质是“权”与“势”的博弈关系。政府有“权”,传媒有“势”。传媒通过对新闻的选择和连续报道造势,他们虽然可能很难决定大众“如何思考”,但他们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决定大众“思考什么”。因此,从长远来看,传媒获得的“权”要么是由政府赋予的,要么是通过造“势”获得的。虽然大部分时间里,媒体获得“权”的过程就如同雕沙一样,它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聚集大量的沙,但即便这样,城堡依然是建在沙滩上,甚至连城堡本身都是由沙雕成的——如果这个沙滩上的城堡不能承受一个孩子的小便,那就更不要说跟海浪对抗了。
上述的这些传媒和政府的关系一旦跨越了国界,则另当别论。跨国媒体将这些关系全部打破。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打造的西方现代文明有两个典型成果,一个是文化的,即市场经济的推行;一个是文明的,即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作为新的文明要素发挥新的整合作用。诚如美国文化学者霍米·巴巴所说,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带有全球野心的跨国媒体的介入,“致使文化如何表意,或者说,通过‘文化’究竟是什么被表示出来,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窃听门事件挑战传媒与政府的关系
具体到默多克新闻集团的“窃听门”事件,更是全面彻底地挑战上述这些关系:
第一,从“宏观基本关系”来看,默多克新闻集团是美国的,接受美国政府的管理,英国政府只能通过法律等国际公认的手段来实施间接影响。多年来默多克与英国保守党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收购”天空卫视这一触动英国国家文化和产业安全的根本利益的事件、“窃听”这一触动大众基本伦理底线的行为,都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随着事件的一波三折而成为新闻集团和英国政府绕不过去的“坎儿”。这就是为什么早在2002年和2005年就已经曝出新闻集团的窃听事件,一直推迟到2011年才通过新的窃听事件而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原因。
第二,从微观细分关系来看,当英国传媒产业资本的利益受到威胁,政治和传媒就再也无法彼此闻鸡起舞了;当新闻集团的传播公信力被釜底抽薪,集团下属传媒业传播出的传媒观点和公众舆论同样也就无法相向而行了。
第三,从哲学博弈关系来看,传媒通过传播建构的“势能”本来就是建构在沙滩上的城堡,看似牢固,实际在公信力被抽取掉后,马上就会堕入捉襟见肘的状态。不管你的危机处理能力和危机表述能力有多强,问题是你的表述本身已经出现了危机——这就是危机的表述和表述的危机的差别。
构建国际传媒新秩序的反思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记者是奴隶。但是,当传媒产业化到一定程度,垄断的本性必然使得传媒最初的基本角色定位发生改变,由信息的提供和服务者演变成为或利益集团的附属、或政治的延伸、或某种程度上的第四等级。默多克事件让人反思传媒业的基本角色定位,后退是不可能了,但需要让更多的民众增强媒介素养,从意识上将媒体所树立的“将军”地位打回原形,更加客观和冷静地看待传媒业提供给我们的戏剧。尤其是以默多克新闻集团事件为例,我们发现,如果个人或者小群体意识,通过传媒业介入甚至决定文化生产乃至政治进程的现象继续加剧,事件的下一步进展就不仅仅是针对窃听事件的道歉、赔偿,也不仅仅是新闻集团在英国被彻底妖魔化乃至退出英国,更绝非仅仅是默多克在新闻集团的下野,而是世界范围内对当前国际传媒秩序的彻底反思。
英国首相卡梅伦不是表示说,“媒体的自我监管已经失效,需要设立一个独立于媒体和政府的新机构负责监督媒体遵守行业标准”吗?那么,由此及彼地看,国际范围内跨国媒体本身就缺乏一套有效的兼管机制和部门。凑巧的是,前段时间中国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中提出建立一个“媒体联合国”。英国爆发的这次传媒业丑闻事件,足证西方传媒秩序中本质性的一些问题,也足证当前国际传媒秩序亟待改革这一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窃听门”事件如果能够推动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反思和建设,或许还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