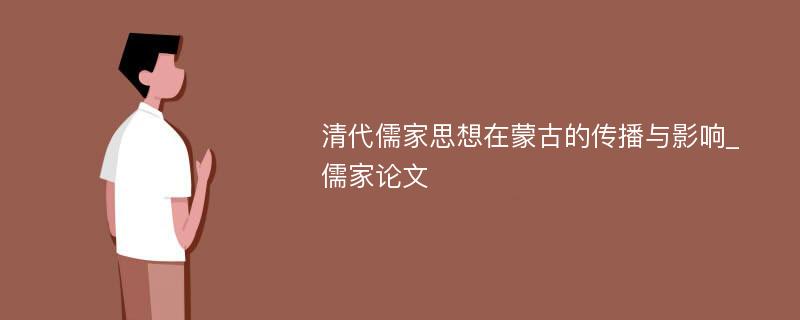
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儒学论文,清代论文,人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49“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5)02-0034-05
一、清以前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
早在蒙元时期,儒学便传入蒙古地区。1206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即位,1271年(至元八年)将大蒙古国改称大元。汉文文献则习惯称为“大朝”[1]。蒙元时期,随着契丹族和汉族知识分子如耶律楚材、郝经、许衡等人在朝廷中地位及作用的日益提高,儒家思想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271年大蒙古国改称大元,国号之渊源出自《易经》,“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朱熹注曰:“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资之以为始也。”忽必烈及其继承者采纳儒臣主张,大力推行“汉法”,设立学校、讲授“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宣扬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传播渐广,上至皇帝,中至官员,下至民间都程度不同的受到儒学的影响。元朝宫廷里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等蒙古文译本,现存的《孝经》蒙古文译本就是供宫廷当作教材用的。元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多种类型的学校,皇帝本人包括皇子在内的贵族都接受儒学教育;另外,设立蒙古国子监学、国子监学、回回国子监学、诸路蒙古字学等,讲授的教材主要有《四书》、《五经》、《大学衍义》、《世祖圣训》。元朝十分重视科举,忽必烈“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元代开科共16次,录取进士1136人。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遂派遣大将军徐达等进行北伐,攻占元大都城(今北京),元惠宗妥欢帖睦尔逃离大都,经居庸直奔上都,后在应昌继续执政,史称北元。北元时期,儒家思想仍在蒙古人中传播。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落向明朝进贡,明廷回赏物品中有一部“夷字《孝经》”;有的蒙古王公贵族还学习《忠经》、《孝经》(注:参见张帆等《蒙古民族通史》第2卷,页361;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委会编《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05751条。笔者查阅《元史》卷22,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辛亥,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2册654页载,元代刊刻的蒙古畏兀字与汉字对译的《孝经》,今藏北京故宫图书馆。笔者以为此书可能是《元史》所记之《孝经》。)。此外,明代还有汉译蒙的《五伦规范》、《五伦图说》等儒学资料在蒙古人中流传(注:参见张帆等《蒙古民族通史》第2卷,页361;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委会编《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05751条。笔者查阅《元史》卷22,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辛亥,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2册654页载,元代刊刻的蒙古畏兀字与汉字对译的《孝经》,今藏北京故宫图书馆。笔者以为此书可能是《元史》所记之《孝经》。)。儒学影响仍存在,但应是有限的,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有的学者提出“自元朝灭亡,除了留滞中原或归降明朝的蒙古人以外,塞外蒙古人对儒学的传承基本已经断绝”的论断是有一定见地的(黄丽生《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清代的台湾儒学与蒙古儒学》(未刊稿)学术研讨会计划简介)。
二、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
北京既是清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儒学教育和传播的中心,更是儒学向蒙古地区传播的大本营。清代,蒙古部落大体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内属蒙古,主要地区有呼伦贝尔八旗、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等地。外藩蒙古分内扎萨克蒙古和外扎萨克蒙古,内扎萨克蒙古是指科尔沁等蒙古24部落49旗,又称漠南蒙古,或称内蒙古;外扎萨克蒙古又分为喀尔喀蒙古4部86旗,或称漠北蒙古,或外蒙古,青海蒙古5部29旗,还有西套额鲁特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杜尔伯特蒙古、土尔扈特蒙古、和硕特蒙古等10部34旗,它们统称漠西蒙古。有清一代,清朝所辖蒙古地区东至东三省,西至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北至大漠,南至长城沿线。儒学在这些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
满、蒙两个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上居住区域相邻,衣食相类,语言上关系密切,生产和生活上有许多接近或相仿之处。以科尔沁为代表的蒙古诸部落,与满洲贵族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反抗到与之联合,再臣服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十分看重蒙古地区和蒙古民族。认为蒙古“风气刚劲,习于战斗,恒不肯服属于人”,若“威德不足以慑之,故不为用,反而为患也”,为了达到变“为患”为“为用”之目的,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包括法律)[2]。力图把蒙古部落作为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大清王朝的北疆“屏藩”,利用这个“屏藩”,“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3](卷22)。授以种种特权,封官赐爵,并以联姻巩固其政治上联合。可见满蒙关系特别是上层之间关系之重要,因此,蒙古要接受儒家文化和思想,离不开满洲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早在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依据蒙文创制满文,此举为满蒙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和环境。在清廷推动下,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
儒家思想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清王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但为了适应和联络汉民族信仰和感情,为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极力推崇儒学。将它作为大清王朝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思想。
早在后金时,满洲统治者就开始接受并在满蒙民族中推广儒学,并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这都为入关以后大规模的广演儒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尚存的《天聪朝臣工奏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对满洲蒙古贵族进行汉化或儒化教育的教科书。《天聪朝臣工奏议》分为上、中、下三卷,这是皇太极执政的天聪六年(1632)正月至九年三月间诸臣的奏疏,共97篇(注:辽宁大学历史系《天聪朝臣工奏议》(清初史料丛刊第四种,未刊本,1980年12月。)。《奏议》由范文程、宁完我、王文奎、杨方兴等50余人撰写而成,他们大多数是前明文人,充任后金国礼部侍郎、书房秀才、书房相公等,他们的奏疏内容广泛,涉及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风俗等,从治国安邦之策,到养狗、开当铺等,纷纷谏言献策,疏中充分体现出儒家思想。
关外时期儒学的传播,从时间上讲,不算长,从地域上看,也不宽广,接受儒学教育和影响的人数,远比不上入关以后,但它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从意义上评价,可谓不小。
从顺治帝入关至乾隆年间,在一个半世纪中,清廷大力传播和宣扬儒家文化思想,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1)在京城和蒙古地区及蒙古八旗驻防将军、都统所在地区设立学校。据《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一书不完全统计,有如下学校:蒙古义学、八旗学堂、蒙古清文学、八旗教场官学、绥远城蒙古官学、盛京蒙古官学、热河蒙古官学、吉林蒙古官学、八旗蒙古官学、国子监八旗官学蒙古馆、咸安宫蒙古官学、布特哈官学、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官学[4](292)。清制,凡学皆设学官,如山西归化厅总官七厅,又称口外七厅,它们是归化厅、丰镇厅、宁远厅、萨拉齐厅、和林格尔厅、托克托厅、清水河厅、还有多伦诺尔厅(隶赤城县),每厅设教谕一人[4](257-258)。
(2)科举考试,主要在京城蒙古人中和口外七厅举行,廪膳生:京师八旗满洲、蒙古60人,盛京满洲、蒙古6人;丰镇、宁远二厅为一学,每学2人,归化、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五厅为一学,亦2人。附生:京师八旗满洲、蒙古60人,盛京满洲、蒙古11人;丰、宁二厅为一学,归、萨、和、托、清五厅为一学,每学7人,七厅共14人。直隶热河围场、多伦诺尔、独石口、张家口四厅学,每学2人,共8人。岁贡:此乃贡生之一种,按年取府州县学中食廪年深的生员挨次升贡,送国子监学习,京师八旗满洲、蒙古一年二贡,盛京满洲、蒙古三年一贡;丰、宁二厅为一学,归、萨、和、托、清五厅为一学,皆五年一贡,各地儒学生员升贡有额[4]。
清朝众多士子参加乡试、会试、殿试,中进士者必定是少数,据有关资料显示有清一代举行开科总次数是112,中进士者26000人(注:《中华状元卷》第1册,第13页;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研究》:清代共取进士26391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其中蒙古人中一甲一名者,据已知资料只有崇绮一人。《清史稿·崇绮传》:“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子。”同治三年(1864)“是岁成一甲一名进士,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5](243)。
新近出版发行的《清代科举家族研究》一书,对清朝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从新的视角进行探索与研究,书中提出“科举家族”这个新概念颇有新意。该书以《清代朱卷集成》为基本史料,书中亦记述了蒙古族著名科举家族,他们是正白旗蒙古巴羽特·尚贤家族,正黄旗蒙古来秀家族,正红旗蒙古衡瑞家族(注:《清代朱卷集成》:尚贤(1845- -?)字亚珍,又号雅真,一字颂叔。盛京驻防正白旗蒙古人兼隶都京正白旗蒙古第七甲喇拴禄佐领下,由附生中式顺天庚午(同治九年,1870年)科二百六十三名文举人。后会试中式一百二十八名,殿试二甲第六十八名。来秀(1819- -?)乌齐格里氏,字实甫,号子俊,一号鉴吾。内务府正黄旗蒙古全义管领下监生。殿试三甲第十七名。来秀是乾隆进士法式善的外孙。衡瑞(1855- -?)正红旗蒙古文翰佐领下附贡生,殿式二甲第五十二名。业师为前文所述之崇绮。他是道光进士倭仁之孙,其父福成,道光拔贡,母何氏,台湾海防同知允恭之女。第37册,页127、140。)。尚贤等三人及其亲属被称为科举家族,足以说明他们是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一举成名而成为蒙古族文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继而成为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宣传者和捍卫者,衡瑞之祖父倭仁即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注:倭仁著、张凌霄校注《倭仁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拙文(署名宝日吉根,下同。)《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法式善》,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12月。)。考中进士和未中的士子以及芸芸儒生,他们学习或者应试的考题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默写《圣谕广训》及《五经》一段,科试卷分六等[4](269)。皇帝崇儒,举行科举,下至地方州县官员,在每月朔望之日集士民于文庙、关帝庙等处,宣读《圣谕广训》及律条、乡规民约[4](253)。
(3)清代儒家思想还贯彻在礼乐祭祀活动中,既要祭天地、太庙,还要祭孔子、颜子等四子。清朝对孔庙大修15次,中修31次,小修数百次,超过历代王朝[6]。在祭祀列祖、列后时,清太宗皇太极的福晋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顺治帝生母),清世祖福临的福晋孝惠章皇后,三位皇后位列其中,她们三人都姓博尔济吉忒,皆是蒙古科尔沁部落女子。顺治皇帝即位,尊孝庄文皇后为皇太后,顺治帝秉承皇太后之训,“撰《内则衍义》”,并亲自写序进太后[4](8902)。康熙即位,尊孝庄为太皇太后,遂“命儒臣译《大学衍义》进太后,太后称善”,孝庄勉励康熙帝:“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同时亲自“作书”告诫康熙帝如何“为君”的道理,明白治国之道,“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我们从孝庄皇后既能著书,又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首家思想教育和告诫康熙帝,可见其人儒学修养之高。孝庄病重,康熙帝亲自祝文,并步行至天坛祈祷康复,死后割辫服衰,以表孝心。三位皇后死后,朝廷以特有的“皇后丧仪”举行葬礼(注:详见《清史稿》第8902、223、2698、2699、2700页。《清史稿·后妃传》:孝庄“作书以诫曰:‘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只承祖考遗绪,俾予亦无疚于厥心。’”。)。
(4)清廷征服并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把蒙古各部纳入大清王朝的法律统治秩序之内,法律制定者因受汉儒礼法思想的影响,所定法律中明显的表现出来。略举几例:例1,《理藩院则例》和《蒙古律例》等一系列法律是清廷为统治蒙古的需要,继承、修改、增减蒙古原有的法律,重新制定并颁布的法律。其中仍有汉儒礼法的条款,“存留养亲”是儒家“亲亲”原则的具体表现,内扎萨克蒙古因偷窃四项牲畜拟死罪及发遣人犯,符合条件,俱准留养[7](卷50)。例2,清制,“凡孝义忠节者,察实以题而旌焉”。在京和各省驻防八旗包括蒙古八旗在内,符合规定者,均在旌表范围之内,并设忠义孝悌祠、节孝祠等,给予表彰(注:《清会典》第254页;另参见寥杨《论清代蒙古地区的民族立法》载《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3期。)。例3,伊犁所属蒙古部落守节之孀妇,理藩院按规定准其旌表[7](卷27)。例4,依服制论罪和保辜制等(注:《理藩院则例》卷35,载蒙古属下官员等擅用金刃等物伤人、杀人者,照刑例定拟,其有服制者,仍依服制论;“斗杀”:凡斗殴伤重,五十日内身死,殴之者绞监候,其共殴者,照刑例定拟。)。
(5)清廷统治者深知儒家文化思想的潜移默化之效应,因而大量编辑、刷印、颁布各种儒家经典作品。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统计孝经类104部,四书类562部,二者合计666部。经部共11类,有作品5408部。仅经部内小学类所属“译文所属”一项内有富俊3部著作(注: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经部:第132、137、188页。)。为了读经、解经和普及儒家思想,清廷编辑出版了许多普及性的读物,如《三字经》等,还有《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雍正十三年八月,无名氏作序,序文称:作者“陶公”云云,系陶姓之人所作。无名氏序文开宗明义指出:“三字经者,上自天时之五行四序,下及人事之三纲五常,以至历朝之统绪,经史之源流,与夫蒙养之方,上达之序,嘉言善行之可循而可法者,罔不备载。”[8]这里把“三字经”的功能效应说得很明白。这部书在道光十二年,有了新镌本,由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书坊(板藏)。八旗蒙古富俊有序,将陶氏所译满文,富俊偕二三友人,由满文译成蒙文。翻译目的是学满洲翻译者,有钦定的《四书》、《五经》诸书可为法程,“而蒙古翻译则缺焉。”“学者病之”;又考虑到《三字经》是“童蒙必读之书”,于是费时二三寒暑,方成此书[8]。乾隆间有一部《御制翻译四书》,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制序文。乾隆帝认为旧译满文《四书》,文义、意旨和语气有未能吻合者,于是“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考寻译,单词双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要求上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凡民之俊秀,皆要学习,要“穷理正心修己”,懂得“治人之道”;告诫“学者慎毋以浅尝自足”[9]。将此由汉译满的钦定《四书》,后有土默特人噶勒桑译成蒙文,在世间流传。至同治间土默特一位学者[按:无名氏]“偶得”此书,“欣喜之余,想若满汉蒙三体文合璧刊刻,雕板刷印,日后于吾旗众学子必有裨益”。于是无名氏向本旗富家、官人求得施舍,筹措资金,自同治八年(1869)始刊刻,至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历经二十余年,完成此书。无名氏并为此书撰写序言,赞赏乾隆帝亲自指授翻译诸臣,完成汉译满《四书》,同时又指出“虽然如此,只有通晓满汉文字之人,方能习读此书,我等蒙古人焉能理会”[9]。另有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御制劝善要言》(满蒙汉三体);汉译蒙《三圣训言》,道光二十五年由内扎萨克蒙古喀喇沁中旗参领僧东格等翻译,卓索图盟土默特人拉锡彭楚等人编辑而成;关于《三字经》及其注解,有蒙汉、满蒙和满蒙汉三体文字,《中国蒙文古籍总目》著录66种[10]。
三、儒学传播的影响
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逐渐传播开来,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影响:清军入关以后,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皇帝率先倡导儒家文化,因之儒学的传播在大清王朝统辖范围之内,从中原到边疆,由城镇至乡村,朝廷势力达到之处,无不有儒家文化的影响。简括之有以下几点:(1)皇帝倡导,国家推行,官民人等力求修身、齐家、治国安邦,使社会稳定,利于经济发展,最终达到巩固清廷对全国的统治目的;(2)学习儒家文化思想,在蒙古人上层中培养了一批文臣武将,文臣如富俊、崇绮等,武将如僧格林沁等。这些人忠君爱国,为清朝的巩固发展做出了贡献。下层民众通过学习蒙文、满文儒家经典,学文识字,知书达理;(3)教养内廷的蒙古王公子弟,受皇帝崇爱,学习儒学,环境优越,有人甚至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注: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290页。杜书引《啸亭杂录》:蒙古敖汉部额驸彭楚克林沁,因“习汉俗,不乐居本土,故典宿卫数十年,卒于京邸。”)。(4)儒学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双向或多向交流的过程,这其中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蒙古人接触、学习儒家文化思想,主要途径是通过学满文和蒙文实现的,这种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5)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和态度,至今还在蒙汉等各族人民中传颂和传承。(6)儒学创始人孔子“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某些精神形态(如“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着精神联系的作用”[11](136)。
儒学在蒙古地区和蒙古人中传播之后,其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其表现:(1)禁锢人们思想,不论是“三纲五常”还是“三从四德”,培养人要顺从、服从、遵从;君权(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这四种权代表了清朝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政治上有保守思想,有复古主义倾向,等等[11](135)。
需指出的是儒学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在京城和有文化的上层人士中传播较广,而在下层民众中影响较大的还是佛教,即学界所称藏传佛教。
蒙古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从她形成的那个时代始,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为中国和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接受、吸纳儒家文化,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后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文化。蒙古民族是个开放的民族,她会继续保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
标签:儒家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蒙古民族通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三字经论文; 四书论文; 五经论文; 国学论文; 孝经论文; 元史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远古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元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