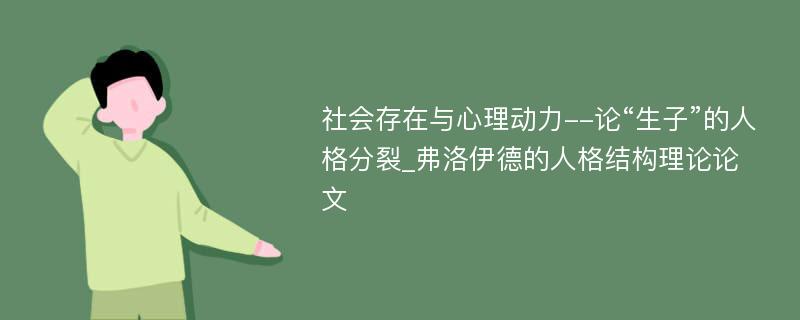
社会存在与心理动机——论《土生子》别格的人格裂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生论文,社会存在论文,动机论文,人格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查·赖特于1940年出版的《土生子》一书,被公认为是开创了美国黑人文学的新纪元,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然而遗憾的是,评论界多在“抗议小说”或“城市现实主义”上下功夫,结果有意无意贬低了这部伟大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反过来又影响了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对于这部小说的褒贬,均来自于对书中主人公别格的评价。因此,针对《土生子》的文本,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文艺美学角度出发,对书中主人公别格由社会存在所导致的心理动机及其人格的裂变进行分析,澄清这个典型人物在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土生子》一书中,作家有机把握了社会存在与心理动机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采用心理文艺学的方法,探讨了别格心理上无意识和意识之间的转化,分析了别格“仇恨—恐惧—压抑—报复”的犯罪心理过程,得出“别格的性格是美国文明产物”的结论,并使其人格升华,由本我达到自我,为现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开了先河。特别是在对人的心理机制方面,从社会存在入手,对主人公别格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尤其是在别格的变态心理描写上,赖特一方面跳出了弗洛伊德性本能压抑说的圈子,突出了来自社会的内心压抑因素;另一方面,又打破了萨特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由选择”理论的局限性,不仅使这部小说具有现代派艺术的特色,而且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结合与创新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存在决定意识。恶劣的社会条件使别格产生对生命力冲动的依附、对乖张异常的追求。从出生那天起,别格就被白人统治的社会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要求他按照规定的生存方式生活。在萨特存在主义看来,人生来本是无善恶之分的,只是在后来的自由选择中才变成了好人或坏人,赖特笔下的别格并无选择的权利,因此,个性遗传决定论与他的人格裂变无缘。要全面了解赖特笔下别格的人格裂变的产生根源,可以从系统结构理论上进行分析。在弗洛伊德看来:“不理解整体,个性中的任何一个单一元素都是不能被理解的;整个系统中的其它元素不发生变化,没有一个单一的元素能被改变,即便是很小程度的改变。”〔1 〕别格的初期心理结构模式(或人格结构模式)用弗洛伊德个性欲望说来分析,不难看出出身低微又未接受多少教育的别格,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中,多以本能欲望冲动的快乐原则行事,他只感到受压抑,并力图摆脱这种压抑感,然而他并不清楚产生这种压抑的真正原因在哪里,于是便形成了玩世不恭的处世哲学,他痛恨白人世界,也恨周围的黑人同胞,甚至对笃信上帝的母亲也时时产生反感。共产党员简力图教育别格走上革命道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欲望,别格则尽力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因为简也是白人。他的经历告诉他:白人永远是黑人的对立面,种族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所以,当简向他表现出友好态度的时候,他觉得当时自己的肉体已不复存在;他已成了某种他所痛恨的东西,成了耻辱的象征,这象征他知道是与他那黑皮肤有关的。在别格看来,这是阴暗区、无人区,是把白人世界与他所在的黑人世界隔离开来的世界。他觉得自己赤身裸体,通身透明;觉得这个白人在践踏他以后,现在又把他高高举起来欣赏玩弄。由此而产生的,不是爱和友好,而是他对玛丽和简怀有的一种无声的、冷酷的、不可名状的仇恨。在汽车里,简和玛丽分别坐在他的两侧,他仿佛是坐在两堵隐隐约约的白墙之间。种族歧视造成的隔阂使他在本我的误区越走越远,以致产生了恨不得用重物连他和这两个白人在内一道把汽车砸个粉粹的复仇心理。
白人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黑人进行压迫和剥削,而且还从宗教入手,对黑人实行愚弄政策,进而在精神压迫上形成一种新的、不可抗拒的精神存在。别格入狱后,说客哈蒙德牧师来到牢房,重弹圣经老调,要别格知恩知罪,在自己罪过的体验中单独与上帝对话,皈依基督教的真理,最后以殉教结束自己痛苦的一生,达到加深别格个体存在状态下恐惧和孤独感的目的。无奈别格在杀死玛丽之前,早已在自己的心中杀死了牧师所描绘的这幅令人念念不忘的生活“美景”,用别格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次谋杀”。但这并不意味别格一开始就是一名无神论者,这是社会现实这个大课堂教育的结果,他需要幸福,人世间一切应该有的,他都需要,但眼下他最需要的,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去对号入座,既不是第一层次生理的需要,也不是第五层次美的需要,而是第二层次安全的需要。〔2 〕此时,“活下去”是他的唯一目的。在此之前,为了“活下去”这个目的,他产生了杀人动机:他要杀死那些认为他不是人的人。正是为这了个缘故,他才杀了人。为了这个目的和动机,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也正是由于这个目的和动机,如今他却得死去。白人世界看不到,也不想看到别格的内心世界所在。在他们的标准看来,黑人所能遵循的,只能是超我原则,压抑个性,完全按白人统治阶级为他们规定好的道德法律原则等所谓理性原则行事。所以,如果别格想要获得体面和尊严的话,他就势必要冒犯这个社会;当他要反抗这个社会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对自己的敌人毫不留情,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剥夺了他做人的权利,用看不见的方式将他杀掉了。事实上,不仅别格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就连玛丽本人也是这个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悲剧的扮演者:是这个残酷的社会制度杀害了别格这个“杀人者”和玛丽这个“被害者”。
蓓西之死,州检官勃克利和法庭捞到了一棵保全体面的救命草,借机大造舆论,并把蓓西的尸体一丝不挂地展示在法庭,在煽动白人世界欲置别格于死地的同时,还企图煽动黑人同胞的情绪,因为蓓西也是黑人,同时又是别格的女朋友。别格杀死蓓西的动机,可以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焦虑说和弗洛伊德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冲突说来予以解释。海德格尔认为影响人对自己存在态度的最强烈的感情是焦虑。海德格尔强调的是通过焦虑来说明人自身存在的虚无性,因此,这里还需要加上弗洛伊德在哲学和文化影响上的伟大发现: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竭力寻找那些被压抑的种种冲动中的内容,这些冲动不仅仅是心理和生理的,很显然,他还寻找那些被压抑在社会中的内容。 ”〔3〕别格同蓓西的关系与其说是情爱,倒不如说是性爱。实际上,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而言。出于生理欲望冲动上的需要,蓓西需要酒和性欲满足,别格需要蓓西的肉体,于是两人走到了一起。当别格带她出逃时,她表现出犹豫、惧怕,这就更增加了别格的焦虑感。他感到走在他身边的有两个蓓西:一个是肉体的蓓西,他刚占有过,现在又非常想继续占有;另一个是存在于向他讨价还价、高价出售的蓓西脸上的蓓西。他恨不得把后者抹去、杀死、扫掉。由此可见,别格早已具备了杀死蓓西的客观基础,所以当新的危险来临时(害怕蓓西告密),他就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她。州检察官勃克利和法庭以蓓西之死大作文章,无非是只想要证明别格人格结构上的本我成分,是恶的象征,并以此扩展到黑人是“劣等民族”这一种族歧视的终极目的上。
在赖特之前,美国黑人文学所塑造的是多以汤姆叔叔为代表的黑人形象,俯首贴耳、逆来顺受,不是逃跑,就是甘愿接受奴役。赖特一反黑人文学的这种传统,在《土生子》中塑造了别格这样一名社会的“局外人”,社会的“弃儿”,为了生存而自卫和反抗的新黑人形象;在创作手法上,赖特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优秀成分,并使用了现代派艺术手法中的精华,从心理分析入手,向读者展示了别格的内心世界,从社会存在与心理动机之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挖掘了别格犯罪的社会根源,加强和提高了小说艺术表现力。
无疑,赖特笔下的别格是一幕人间悲剧:有价值的人毁灭了,但其价值却以某种形式和某种意义得到了确证、肯定、增值和光大。别格的悲剧是一幕社会悲剧。社会就是一个大系统,或曰一个大结构。美国黑人是美国社会的子结构,别格又是受奴役、受压迫的黑人群体中下一层次的一个子结构,人类社会是发展程度最高的自控、自调节系统。在阶级社会中,法律便是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自制机构。而在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人类社会群体系统中就同时出现了伦理调节机制,以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有利于人类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法律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伦理所调节的则是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行为,两者有别,又有互补共通之处,后者服务于前者。善和恶是伦理的主要内容。善和恶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其标准大不一样,但基本原则却都在于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人类一定群体系统的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即作为自控制系统的控制论目的。这样就把道德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了。别格在意识到危险来临之际,失手闷死了玛丽,无意间通过暴力行动保护了自己,但与此同时,却在道德伦理上扰乱了别人的正常秩序。别格的这种行为只能是出于生的本能欲望,是本我的表现,仅从这一点上分析,别格的悲剧是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可言的。其悲剧价值主要表现在杀人后,别格找回了自我这一关键议题。其人格裂变的过程产生于这桩杀人案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而非美国法律这种超我机制。而其人格自我的回归,主要体现在其道德良心的发现上,别格这种人格自我的回归同所有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一样,是在产生的剧烈振动之后,在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道德良知的初起阶段,别格只是隐隐约约意识到社会现实对黑人民族的不公,并力图采取行动,消除这种不公。但如何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式,他在内心中并不清楚,其人格结构还主要是建立在本我基础之上的,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坐在车上,眼望着人行道上的黑人,心里觉得,要消除恐惧和羞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使所有这些黑人采取一致行动,统治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做,并要他们去做。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方向,他和所有其他黑人都可以全心全意地朝这方向前进;应该有这么一个办法,可以把啮心的痛苦和不安的渴望交融在一起;应该有这么一个行动方式,可以使人们信心十足地投入整个身心,但他又觉得,这样的情况决不可能在他和他黑人民族身上发生,因此他恨他们,想要一挥手把他们消灭干净。然而他仍怀着模糊的希望。……他觉得有朝一日会出现一个黑人,能把黑人民族捏成紧紧一团,让他们共同行动,消除恐惧和羞耻。〔4〕这是别格杀死玛丽之后的一段内心描述。从中可以看出:别格在思想认识上已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是别格人格结构由本我向自我转化的第一个阶段。这种变化源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存在的现实,但在如何采取行动上,别格受到非理性意念的支配,在外界巨大的压力面前感到失望,从本我冲动出发,产生了一种破坏欲望和统治欲望。简和麦克斯的实际行动使别格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这是别格自我人格回归的第二个阶段。杀人前,别格从自我保护意识的“本我”出发,把简的一切友好行为都看作是一种危险信号,因为简也是一名白人,在别格的心目中,如同白人居住区和黑人居住区之间有条严格的界线一样,种族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也必然有着一条无形的、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在杀人之后,别格一度把危机转嫁给简,使简被捕入狱。当别格杀人真相大白后,简则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他摈弃前嫌,主动到监狱来看望身陷囹圄的别格。简的到来,使别格早已泯灭的人性开始复苏,为了拯救这个受害的“害人者”,简给别格领来了共产党的律师麦克斯。当这位白人律师甘冒白色仇恨来为别格辩护时,“字眼变成了血肉,在他这辈子里,一个白人第一次在他眼里变成了人;随着发现简的人性,他像刀割似的觉得悔恨:他杀害了这个人所爱的姑娘,使他受到痛苦。”〔5 〕第三个阶段是被关进监狱后,别格开始认真从这次事件中来总结他的人生旅途。一些过去茫然的东西逐渐清晰起来;危险和死亡离他这么近,超越已发生的一切之上,虽不可捉摸却是事实,这是一种流连在他心头奇特的权力感。他杀死了玛丽和蓓西,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杀人,他过去已经杀过许多人,只不过在过去的两天里,他的这种冲动才采取了真正杀人的形式。他仇恨他处的那个世界,是这个社会把他抛到了城市的一个角落里,让他去死亡、腐烂。他开始思考他追求的是什么,想得到的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开始感觉到有些东西是这个世界给他的,有些东西是他固有的,有些东西展开在他前面,有些东西展开在他后面,而在他整个一辈子中,由于他这身黑皮肤,思想和感情、意志和精神、愿望和满足这两个世界就从未联系在一起过,他从未有过整体感。此时,虽然死亡就明明白白地摆在他的面前,但他对死已不象先前那样惧怕,生存的欲望已被澄清杀人动机的欲望所取代,这是别格由无意识向意识转化的一个巨大转折点。第四个阶段是在他失手杀人被捕后重新认识了他与周围人们的人际关系。对于玛丽和蓓西之死,他已承担了道德上的罪责,这也就是说他更加看清楚了法律的虚伪性,因而使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自由感。他开始模糊认识到既然不能同他周围的男男女打成一片,那么也应该与其某个部分打成一片。他重又冒出杀机,但这一次不是向外针对别人,而是向内针对自己,干嘛不杀死他内心中那种刚愎自用的渴望,不正是这种渴望把自己引向这样的结局的吗?他曾向外扩展,杀了人,却没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为什么不向内扩展,杀死使他上当的东西?这种感觉就象一粒种子的外壳腐烂了,变成了泥土的一部分,但它自身却将在这泥土中重新生长出来。这桩人命案使别格从来自内心自省和客观外界作用两个方面的影响下重新审视了自己,使其心理上的无意识与意识达成一种调解,进而完成了自我的回归。别格这个非理性人物的象征终于回归了理性轨道。
赖特从心理分析入手,展示悲剧人物别格在社会存在与心理动机之间关系上所产生的人格裂变,使主人公由本我回归自我,由非理性回归理性,扩展了小说所要达到的社会效应,该书源于社会现实反之又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唤起包括白人社会在内的全社会的觉醒,改善黑人的悲惨生活境况和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取得人权的平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这部作品以独特新颖的现代派创作技巧加传统文学创作手法,来剖析社会现实与心理动机之间的关系,为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繁荣和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注释:
〔1〕〔3〕埃里希·弗洛姆著,申荷永译:《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0页。
〔2〕参见黄希庭著:《普通心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43页。
〔4〕〔5〕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134、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