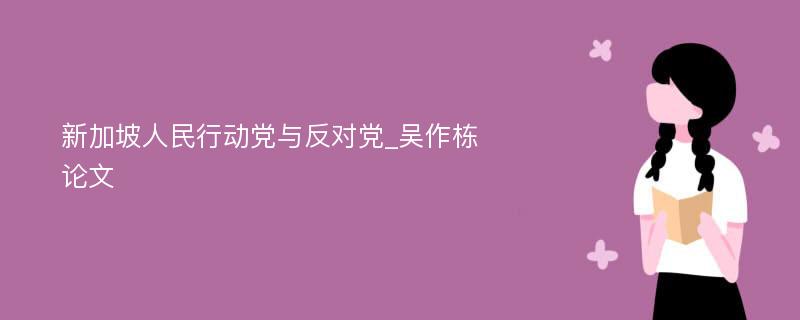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对党论文,新加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一直是通过大选来实现其执政地位的维持和延续的,但同时,“人民行动党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高度控制,控制了新加坡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虽然宪法允许反对党存在,但人民行动党给予反对党的生存空间十分有限,反对党难以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威胁,甚至不能影响其政策”。① 在其执政地位的维持进程中,如何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如何运用合乎法律的手段对反对党进行有效的控制至关重要。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表面上具备了西方代议制政党的一般特点,但在实质上,由于它对新加坡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施加重大影响,使人民行动党与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一起构成了有效控制新加坡社会的完整系统,因此又与西方政党的地位作用不尽相同。执政党要达到预期的执政目标并连续把持执政权力,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排除反对党的干扰,虽然反对党有建设性和对立性之分,但反对党的存在及活动对执政党来说无疑是干扰大于支持,所以如何处理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是研究一个政党执政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新加坡反对党角色认知的变化
在新加坡,反对党是一直存在的,且数量保持在20个左右。不管是人民行动党还是反对党自身,对反对党在新加坡政治系统中的角色认知都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逐渐形成了人民行动党不再把反对党看成洪水猛兽,而是作为民主政治的标志来容忍;对于反对党来说,他们也不再幻想取人民行动党而代之,只是想督促人民行动党照顾到他们所代表的特定阶层的利益而已。
在早期的人民行动党看来,国会中没有反对派对于新加坡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无疑是最理想的。因为反对党集团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不但提不出健全的计划,反而为了讨好选民,轻易施舍想像中的财富以争取选票,从而在人民中造成虚幻的希望。反对党的存在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延续和执行都是一种干扰力量。在客观上,“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的成功统治应归功于政治反对党的衰微”。② 针对年轻人认为新加坡需要反对党的观点,李光耀曾经指出:“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代还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痛苦。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相信,也许是诚恳的相信,新加坡需要反对党。1965年到1981年这几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历来最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也正好是在这些年里,我们政治稳定,在国会里没有顽强好斗、吹毛求疵的反对党,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李光耀语重心长地说,在今后几年里,这一代年轻人“很可能发觉到(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我们不幸的话,我们将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那样,反对党提出办不到的更大福利开支,引起更多的空想,造成好像英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的混乱。”③“那些认为有了反对党就能够改变政府政策的人,他将发觉这根本不正确。反对党无论是在伦敦、渥太华、坎贝拉、威灵顿、新德里或哥伦坡,都不能改变政府的政策。”④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逐渐意识到,反对党的适度存在对于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也就在对反对党的态度中多了些许容忍的成分。反对党的存在可以使新一代人民行动党议员在国会中受到锻炼,也减缓了西方民主思想在新加坡青年中的传播给人民行动党执政带来的压力。李光耀曾慨叹:“80年代新加坡人对于取缔反对党而由老一代领导人进行统治的方式已经不感兴趣了”,⑤ 新加坡前副总理拉贾拉南也说道:“这是由于年轻的选民希望议会中有反对党。”在新加坡民众看来,需要反对党的存在是因为“人民行动党过于强大了,需要监督”。⑥
对于反对党来说,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稳固前后经历了变化。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稳固以前,几个较大的反对党的目标就是在大选中战胜人民行动党而上台执政。到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态势形成以后,反对党意识到在新加坡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几乎不存在上台执政或几个反对党联合执政的可能性,也就重新自我定位。民主党惯以采取的“补选策略”就能说明问题:即在人民行动党稳操胜券的前提下唤取民众的支持,目的在于在国会中多占席位而不是上台执政。工人党新任秘书长林瑞莲在2002年10月加入工人党时强调,加入反对党并不表示是要与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对立。“我们不是要推翻政府,他们这几年的表现都很不错。”林瑞莲说,尽管如此,他们却还可以做得更好,而她加入反对党的原因就在于,她觉得政府需要更多不同的声音。“工人党向来都为工人阶层以及经济情况较差的人说话,对于这样的党纲,我相当认同”。⑦
二、人民行动党对不同类型反对党的不同态度
在人民行动党看来,以对其态度为标准,新加坡的反对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建设性的反对党”,其代表人物为詹时中、刘程强,他们态度平和,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是赞同的,其存在的目的在于向世人昭示新加坡的民主政体表象;另一类是“对立的反对党”,以惹耶勒南、邓亮洪和徐顺全为代表,他们锋芒毕露,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针多持批评态度。
“建设性的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来说自然构不成什么威胁,又可以向世人表明新加坡的民主政体,所以人民行动党近年来有意培养“建设性的反对党”议员。他们的活动在人民行动党宽容的范围内,人民行动党也需要这样的反对党人进入国会。詹时中自1984年起一直是波东巴西单选区的议员。2001年大选时,吴作栋在视察波东巴西选区时还同詹相互调侃,气氛甚为融洽。吴作栋声称:“詹时中这个人,他在国会内外都是一个君子。在国外,他的言行就是一个新加坡人该有的。这是我们在国会里需要的反对党人。可惜,他是站在另一边的。不过我们欢迎他,我们不介意。”⑧ 当詹时中向吴作栋问好时,吴作栋喜形于色:“这就是我所欢迎的反对党人。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会说总理,您好,而不是嚷嚷吴总理,过来,过来。这才对嘛。”⑨
对于那些“对立性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1997年的大选中,李光耀多次指控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是“中国沙文主义者”——持有偏见并反对基督教和英语教育的新加坡人,并刺激邓去法院诉讼。当邓亮洪说将会到法院告李时,李光耀就指控邓诽谤他撒谎而先告到法院,法院判决李光耀胜诉,邓亮洪必须赔偿李光耀“形象损害费”260万美元,逼得邓亮洪只得逃出新加坡。
200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把指责的目标定为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在政府为选举规定的9天竞选期中,人民行动党的核心目标是将徐顺全赶出国会。人民行动党攻击民主党提出的为被精简的工人设立20亿新加坡元福利计划是力不能及的建议。而徐顺全指责吴作栋在1997-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高潮时竭力为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170亿新加坡元贷款而奔走。后来吴作栋披露,这项提议从来没有被通过。尽管徐顺全对可能导致认为政府在提供这项贷款时有不良行为的误解公开表示道歉,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仍声称要对徐顺全提出诽谤起诉。2005年1月,新加坡高庭裁定,徐顺全须分别支付吴作栋国务资政和李光耀内阁资政30万新元,作为他在2001年大选竞选期间诽谤这两个领导人所造成的名誉损失赔偿。一年之后,即2006年2月,因徐顺全无力赔付,被高庭判洪破产。⑩
西方学者认为,使用诽谤罪名打击反对党是人民行动党的惯用手段。新加坡政府有时通过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从而使他们退出政坛。(11) 在选举中,执政党的要人往往会以威胁的口吻警告选民,如果反对党议员当选,政府将很难为这个选区拨款,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这种恐吓其实有悖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公平竞争精神。
三、反对党在新加坡社会生态中的客观作用
如果说反对党的存在及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昭示新加坡形式上的民主的话,那么,在客观上,反对党的活动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也产生了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是微小的且没有制度化保证。
第一,扮演执政党监督者的角色。新加坡贸工部部长杨荣文说:“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必须为下一次选举操心,这促使我们自我约束,并且在付出最少代价的情况下,努力实现长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必为选举操心,无论我们出发点有多好,都会使我们变得草率和傲慢。选举是使我们保持平衡和诚实的方式。”(12) 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的监督就成为对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一种制约。
第二,反对党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面目出现,督促人民行动党照顾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反对党每次大选都把贫富悬殊、弱势群体需要政府体贴作为赢取选民支持的砝码。而反对党为了在大选中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也祭出民众的大旗。2001年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抨击政府没有为下层平民办事。他们说:“新加坡执政者的薪金是全世界最高的,而老百姓工资是全世界最低的,这样的贫富不均,全世界只有新加坡才有。执政党口口声声说新加坡是一个大家庭,世界上哪有这样贫富不均的大家庭?”有的发言人认为“政府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导致新加坡工人沦为次等公民”;有的发言人则要求政府赶走跨国公司,以保护本地企业等等。(13) 工人党针对新加坡家庭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以纠正“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
第三,反对党议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绩效”,会在本辖区内为民众办实事。2001年大选中,作为阵容最为强大的反对党,民主联盟共派出13名候选人角逐三个单选区和两个由五人组成的集选区议席。在大选前,詹时中说,他所管理的波东巴西市镇会,虽然没有得到政府分文资助,但由于管理妥当,目前有累积资金将近800万元,而区内的每一座组屋,都经过了翻新、粉刷和修补。这次大选如果能够蝉联,他打算在接下来五年,更换波东巴西区内每座组屋的电梯,让电梯可以在每一层楼停留;他也计划要增建各种公共设施,以进一步改善区内的居住环境。但是,这种承诺相对于掌管新加坡经济大权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来说无疑太微不足道了。反对党的所得与付出是不成比例的,也彰显出新加坡民主之路的坎坷。
对于反对党议员,人民行动党尽力削弱其参政职能,如拖延给反对党议员提供办公室,惹耶勒南和詹时中分别在获选后8个月和11个月后才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不让反对党议员了解相关信息,使他们难以对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或因为失去了政策的基础而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经常报道对反对党不利的事件,而对他们的正常活动却不予报道。(14) 政府对反对党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措施,例如除大选的9天之外,不允许反对党举行公开的集会和发表反政府言论,议会中仅有的几名反对党议员虽然可以在议会中自由发表言论,但传媒对他们的正面活动的报道受到控制,因此其作用十分有限,这就使得反对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陪衬。
注释:
①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社会生态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Thomas J.Bellows,The People' 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Emergence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Monograph Series No.14/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1973,p.125.
③④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4页。
⑤Carolye Choo,The PAP &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Succession,Selangor:Pelanduk Publications ( M) Sdn Bhd,1998,p.39.
⑥李路曲:《新加坡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作用》,《现代国际关系》,1977年第3期。
⑦《单身女贵族林瑞莲:加入反对党我准备坐牢》,《联合晚报》,2002年10月29日。
⑧《在波东巴西相遇 吴总理跟詹时中互相调侃》,《联合时报》,2001年1月11日。
⑨2001年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路遇吴作栋,曾大叫:“吴总理,过来,过来。”并当面厉声质问吴作栋,要求他回答借给印尼苏哈托的170亿新元的下落。最后被吴作栋等以诽谤罪告上法庭。
⑩《没赔偿二资政诽谤金 徐顺全被判破产》,《南洋商报》2006年2月11日。
(11)吕元礼、邱全东:《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政党文化转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2)《好人才应该挺身而出》,《联合早报》1993年5月3日。
(13)萧功秦:《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兼论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14)Christopher Tremew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London:Macmillan Press,1994,pp.163-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