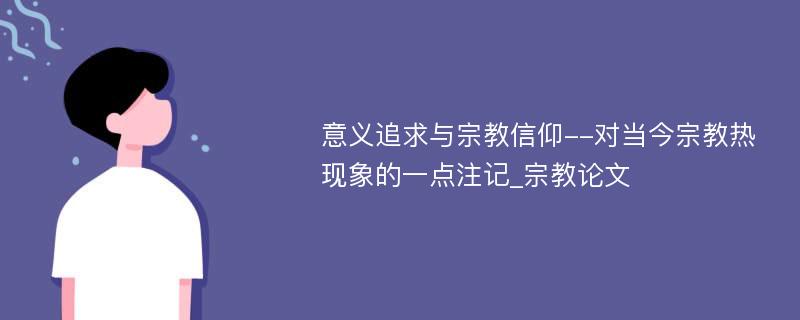
意义求索与宗教信仰——对当今宗教热现象的一种注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注解论文,宗教信仰论文,当今论文,宗教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B9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1999)03—0055—(7)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祛魅”(韦伯语)的时代,即一个“神灵”隐退的时代。然而,正是在理性昌明、科技发达的今天,宗教却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在西方,不仅出现了传统宗教(如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的复兴运动,而且还崛起了各种各样的“新宗教”(注:参见《当今世界的宗教热》一书,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在中国,自“文革”结束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热”,信仰人数大幅增加,宗教活动十分活跃(注:具体情况可参见1992年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本文不拟对这些原因作逐一的分析研讨,而只想从“意义论”(详后)的角度去打量宗教信仰在人生中的地位及功能,以此作为对上述“宗教热”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一、人生的两维:求生存与求意义
人生在世,总是从事着、烦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性质各异、种类繁多、不可胜数。但如果不断地加以概括和归纳,最后似可得到最基本的两类,也就是人生的两个维度:求生存与求生存的意义。
人须活着才能在世。活着既指个人的存活,也指种族的延续。人为此而从事的活动即是生存的活动。这又主要有两大内容:(1 )求食或以食为主而展开的活动;(2)求偶的活动。 这即是人们所谓的“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前者基础上所形成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在后者基础上所形成的则是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为保证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保证其利益的合理分配,遂又同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习俗、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等等。这些习俗、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反映性的和服务性的,即反映人的求生存活动的要求并为之服务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几方面都引起了巨大的变化:物质资料不仅易于生产,而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日趋繁多精美;婚姻及两性关系日益摆脱粗鄙落后的形式而变得更富人性;道德、法律、政治等等也相继走出中古形态而变得更加合理、完备。然而无论如何变化,这些活动的基本功能都不出求生存的范围,它们的改进,无非在于提高生活的质量,即求得一种更好的生存。
然而,除了求生存的需要外,人还有求生存的意义的需要。人对物质资料和异性的需求固然重要,无之,人便不能存活;但人对意义的需求也同样重要,甚至还更重要,无之,人即使活着,也倍感空虚无聊。人可死于冻馁,也可死于意义的缺失。动物只求生存,而人赖以存活的,还有意义。
这里所说的“意义”,不是语言学或语言哲学所说的“语义”即语词所指的无形的观念;也不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那种组建世界的“意蕴”即事物凭之得以展露和领会的因缘联络整体。这两种含义的“意义”与我们所说的“意义”虽不无联系,但却不是同一层次上的东西。我们所说的是一种“人生意义”,即人生在世特别有所依持(可靠、可安、可乐等)的那样一些存在状态。这一“意义”与前两种“意义”的区别可由下述情形见出:一个人说着语言(承诺着它的语义),也在由因缘联络整体所规定的世界中烦忙操持着(承诺着它的意蕴),可却仍感到他的生存是毫无意义的、空虚无聊的,仿佛还缺乏点什么。这个“什么”,多半就是可使一个人兴致高昂或兴味索然并因而可使他的生活充实生辉或空虚黯淡的“意义”。
现在进一步问:求生存与求意义这两者的关系如何?从时间上看,它们是同时的两维。这里没有先后之分。不是说先须求生存然后求意义,而是在求生存的同时就求着意义。以往的生存活动,无论多么原始、艰难,都有求意义的活动交织其中;将来的意义追求,无论何等广泛、深入,都须臾离不开求生存的活动。从模态上看,它们是并列的两维;不分仲伯,不相从属。因此,无论把何者看做决定性的(注: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在中,意义形态几乎全变成受经济基础制约的“意识形态”),弗洛伊德的“性欲决定论”(在中,意义形态如艺术、审美等等成为欲望的转移或升华),或可视为前者(生存为决定性的)的表现;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至上论”(重“义”轻“利”,以“内圣”开“外王”)或可视为后者(意义为决定性的)的表现。),都可能错失两者之间的真正关系。从方向上看,它们是逆向的两维:求生存的活动走在“出”的方向上,而求意义的活动则走在“归”的方向上。人若不从自身走出去,以认识和实践的方式去与世界打交道(注:人们一向高估认识与实践活动的意义,而对其负面作用却认识不足。事实上,“异化”就同时发生在这两种“对象化”的活动中:为了得以认识,人把自己限定为知性的“头脑”,把物揭示为抽象的“概念”;而为了得以实践,人则把自己限定为感性的“身体”,把物揭示为用的“资源”。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带来了人和物的实际分裂与失落。这种“异化”原则上不能在求生存的活动内加以解决(在此范围,最多只能做到后期马克思所说的“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只能靠“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意义活动来加以克服。这个“彼岸”并不遥远:只要我们从求生存的活动中抽身出来而进入专门的意义形态,我们就生活在“彼岸”。),人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但人若一味远出,则又可能迷失其中而成为飘无所归的“游子”,意义追求与体验就是引人归“家”的途径。虽说人有时有可能更多地行进在某一方向上,但相反的方向总是同时为人开放着。总之,尽管求生存与求意义的性质有别、功能相异,但它们都是“人”同时具有的两种基本需求,并且也共同服务和造就同一个“人”。
二、人求意义的基本方式
如果把“意义”理解为人生在世有所依凭的那样一些存在及处身状态,那么,很显然,凡能造成此种状态的东西都可视为“意义”之源。就此来看,人既可在求生存的范围内去求意义,也可在专门的意义形态中去求意义。人生中有此专门的意义形态吗?的确有。这些形态已随人的存在而被给与,并且一向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作用。仔细检视人的整个生活领域,就可发现:爱、友谊、游戏、审美(艺术)、道德(修养)、信仰(理想)等等,就是这样一些专门形态。它们的基本功能,主要不在求生存,而在为人生提供意义。因为它们的存在,人才与众不同,才有人生的幸福可言。否则,人就仍滞留在动物的阴黯中,人生就会变成一场西绪弗斯式的劬劳。当然,人也可在满足生存需要的那些活动或对象中去求意义。事实上,不少人就视财物、金钱、权力甚至劳作本身为有意义或最高意义而毕生追求之。始不论这样的东西能否成为形上需求的替代物,即使能,也远不能与上述专门的意义形态相提并论。茶杯在某些危急情况下可以用来御敌,但并不能由此说茶杯就是武器,因而可以像刀矛枪炮那样陈列到武库中去。同样,生产经营、赚钱牟利之类的活动可使一个人一时或长时感到有意义,但这些活动本身却不是意义形态而是谋生方式。所以,在这些活动或对象中获取的那种“意义”,尽管在当事人的体验中似乎也同样真实充盈,却无法与在专门形态中所求取的那种“意义”相比并。因为它们缺少超越性。而一旦获取较高的“意义”,它们往往就退居其次或变得微不足道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打赌》中有位律师,为了两百万元而甘愿忍受十五年的囚禁生活。就在得到这笔钱的头天晚上,他却逃走了。原因是他彻悟了人生的真谛(意义)。钱不再对他有意义了。在现实生活中,虽说类似的极端例子并不多见,但轻利重义的行为却比比皆是。进而言之,即使一个人把求生存的活动或满足生存需要的对象作为意义甚至最高意义来加以追求和领会,也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完全排斥那些求意义的专门形态。只要他在谋生之余还要交朋结友,还要娱乐消遣,还要阅读欣赏,那么,无论范围多窄,入迷的程度多浅,他都在这些形态中并通过这些形态求取着意义。
就专门的意义形态而言,似乎又可分为两类:(1 )在世内或向世内事物求取意义。爱、友谊、游戏、审美(艺术)、道德(修养)以及一般的(世俗的)信仰都属此类。(2 )在“世外”或向“世外”事物求取意义。宗教信仰即属此类。
由于深入分析爱、友谊、游戏、审美、道德以及一般理想这类意义形态的特点不是本文的任务,故略去不论。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作为求意义之极端形式的宗教信仰。
三、作为一种信仰的宗教
“宗教”一词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宗教,如印度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这些宗教各有其崇拜的对象、团体、经典、使徒、道德模式,各体现了不同的地域特征或民族文化传统,并且要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一是指与“神圣者”打交道的精神能力和倾向。我们称之为“信仰”。作为此种东西,它植根于人性的深邃维度,是一种人皆有之的形上需求。宗教的这两种含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能力和能力的展现是不同的:历史上的宗教是个复杂的现象,不是单纯的能力所能完全解释的。另一方面,两者又密不可分:无前者则后者无以从出,前者是后者的必然根据;无后者则前者抽象不实,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展现。本文所说的宗教,指的主要是人的内在信仰能力。但这种能力又总离不开它的某些外在表现。
但是,把宗教作为信仰,这不是又把我们带回到“相信”的领域吗?
人生在世,相信的东西很多。相信是对有关对象之存在、状态和价值的一种肯定态度。比如,相信太阳总是东升西落,相信脚下的大地不会骤然陷落,相信水可饮、粮可食;相信自我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相信亲属好友对我的爱意和照顾,相信社会规律和革命真理的存在;相信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相信万有引力的存在,相信火能灼人、水能溺人,相信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相信灵魂和神祗的存在, 相信除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永恒的超越世界,相信善恶报应和轮回;……总之,相信人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人生所形成的普遍有效看法。在这些相信中,有的是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得来的,有的则是从历史、书本得出的;有的是明晰的,有的则是暖昧的;有的是可以加以验证的,有的则是无法加以一般意义上的证实或证伪的。这些相信,是我们正常生活、正常行为的保证,甚至可说是人生在世的前提。没有这种相信,我们就无法正常有序地生活,就会时时陷入怀疑之中而一事无成。试想我们不相信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坚实的,而怀疑它随时都可能陷裂,试想我们怀疑包括至爱亲朋在内的所有人都会陷害我们,试想我们每天都担心明天的商品价格和交易方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试想我们一面进行数学计算一面又严重怀疑有关定理、公式的正当性……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就根本无法正常地生活、工作和学习!由此可见,人生在世,总有所相信,而且这种相信多半也确有根据。说到底,相信是有所依凭的生存状态。人是以有所信的方式在世的。这信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就包含在他的存在之中甚至作为他的存在的基础。
诚然,我们也可不信并且也常有不信的时候。然而,这种不信通常所意指的,尚只是某一具体对象的存在或它的某种不清楚的地方。一俟这“不信”所否定所怀疑的对象或方面得到证实、澄清,便可变不信为相信。有时,人们以坚决的口吻表达的不信,骨子里仍可能是一种信:“我不相信是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诗)其意思正好是说:我相信梦不是假的,我相信死有所报应。退一步说,即便是彻底的什么都不信,骨子里也仍然蛰伏着某种相信。当一个人说他什么都不信时,至少他还有这样的相信,即他的这种断言是可信的,至少对于他是这样。同时,能说出或想出这一断言,表明他凭借的语词和语法是可靠的,否则他就根本不能作此陈述。陈述就是相信。可见这种极端的“不信”或“无信”也依然是一种信,本质上和信者的信没有两样。作为生存根据的本源性的“信”,不是一声“不”所能勾消的。
上面所举的种种相信,其所处的层面并不相同。首需加以区分的是一般“相信”与“信仰”。就对象言,一般相信所涉及的乃是世内的事物和现象;就态度言,有可能是不明确、不清晰的。信仰也是一种相信,其对象也可以是世内的,但却是一种深入意识之中并形成“信念”因而是更明确、更强烈的相信,对信仰者的思想行为也更具自觉的指导作用。“信仰”可说是突显着的“相信”。能够从一般相信中突显出来,这里面就有意志的努力。信仰是建立起来的。能形成一种信仰,这表明人决心按自己建立起来的某种明确的观念来生存。
第二层区分可在信仰之内作出。可以把所有的信仰分为“世俗信仰”与“宗教信仰”两类。两者的区别既体现在所信的对象上,也体现在信仰者的态度上。从前者看,世俗信仰的对象是世内的存在者,而宗教信仰的对象则多为超自然的神灵或神力;世俗信仰的对象的存在状况一般可通过实验观测来加以确定,而宗教信仰的对象则根本不可能加以一般意义上的验证;世俗信仰若对其所信的对象发生怀疑、动摇乃至转移,通常不会严重影响信仰者的生存状况,而宗教信仰对象的动摇,却往往造成信仰者精神的紊乱和崩溃。从后者看,世俗信仰所表现出来的通常是一种“次级关怀”的态度,而宗教信仰则通常表现出一种“终极关怀”的态度,即一种义无反顾的坚决赞同和绝对依附;世俗信仰常常建立在经验和理解之上,主要服从于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对我们的意识具有某种强迫性的事实;而宗教信仰的获得则多半最终建立在违情悖理的“一跃”上,这一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因而是一种非强迫的、自由的应答方式。
上述区分中,能把世俗信仰与宗教信仰最终分开的,恐怕还是信仰的“对象”,尽管这种对象只能通过信仰行为来加以接近。宗教信仰的对象是超越的“神圣者”,而世俗信仰的对象则只是有限的尘世事物。有些世俗信仰,也声称其对象是“神圣的”,也要求信从者的绝对服从,并且在其信仰破灭后也能造成精神崩溃。其中尤为接近宗教信仰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它把本民族的强盛当作超越一切的终极关怀,以此为目的,它对外无视其他民族的存在和利益,对内则要求自己成员的无条件服从,什么经济利益、健康和生命、家庭和亲情、对美的爱好、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统统都得为之作牺牲。这种信仰,若从形式上看,已几近宗教(有人称为“准宗教信仰”)。但它毕竟不是。无论爱情、金钱、权力,还是领袖、主义、民族,都还是这个世内的有限之物。作为此种东西,它们必然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易变易朽的,换言之,不神圣的。它们对神圣、终极的声称虽说也能迎合不少人的需要从而得逞一时,但最终无不以原形毕露而收场。在这方面,本世纪德国纳粹主义的出现和覆灭即是一例。
通过逐层剥离,我们看到,所谓宗教信仰,乃是一种特别的相信,即笃信世内所无的“神圣者”并以此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
四、宗教信仰与其他意义形态的一般比较
“合一”是宗教信仰与其他专门意义形态的相同面。这一相同主要是在与求生存活动的总体比较中见出的。在求生存的活动方式中,如在认识与实践中,都有主客二分和对峙的特点。为了得以认识和实践,前提是有一从事认识或实践的“主体”,同时有一在主体之外的可被打量和操作的“客体”。即使是在认识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自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心理学和解剖学)。这一“主一客”二元对峙的格局贯穿于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求意义的活动则与此不同。虽说意义活动也离不开当事人和相应的体验对象,但它们却不是作为“主体”和“客体”而发生关系并在此关系中保持为“主体”和“客体”的。一方面,意义是在体验者的体验中生成的东西,离开了体验者的体验,意义没有独立自足的形态;另一方面,体验者就驻留在意义中,走出了意义体验,体验者的存在状态就会发生改变(回到日常状态)。这种合一的状态极难言说。中国古人用“物我不分”、“物我两忘”来加以描述,法国哲学家杜夫海纳则把这种状态中的当事人称为“亚主体”( quasi-subject),把进入体验之中的对象称为“亚客体”(quasi-object),意在说明意义体验乃是一种超主客的合一状态(注:参见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第一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无论在爱、友谊、游戏、审美中,还是在道德自律和信仰中,无一例外地都有这种主客消融与合一的性质。在爱与友谊中,是爱者与被爱对象的深深相契;在游戏中,是游戏者与游戏活动的融为一体;在审美中,是审美者对形式的沉醉;在道德关切状态中,是普遍原则对行为者的“绝对命令”;在信仰中,则是信仰者与信仰对象的完全合辙。可以这么说,意义追求和意义体验就是对人和世界分离和对峙的克服。如果说,求生存的“出家”活动是通过主客相分进行的,那么,求意义的“归家”活动则是对此种分裂的弥合。
宗教与其他专门求意义的方式不同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在关涉的对象上,其他方式所涉及的皆为世内之物(这与世俗信仰的情形相同)。爱与友谊涉及的是人,游戏涉及的是约定的规则与相关的物件,审美涉及的是对象的形式,艺术的材料和内容也取自我们的世界和生活,道德法则或源于我们的内在理性或源于人人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可说都不出人和人的世界。而宗教信仰的对象却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内的东西。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其实就是“无”。正因为此,故常被信仰者体验为“全然相异者”(the Wholly Other)。但这个“相异者”又并非与人无涉,而是与人生死攸关。因为它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这个世界的根据。正因为此,它又被信仰者视为“神圣者”(the Holy)。其次,在关涉的主体方面,宗教信仰涉及整个人格,是人的心灵之最为核心的行为。与之相比,其他方式一般都不具有这个特点。游戏、审美更多地涉及爱好和习惯;爱与友谊涉及人格,但一般不涉及整个人格,它们也能成为生活的核心行为,但却很难长久地成为最为核心的行为。这不仅因为除爱和友谊外,生活还有别的内容和旨趣,而且还因为爱和友谊在琐碎的生活中容易磨损和改变;道德要作选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结果,故以人格(自我)的形成和统一为前提。然而,正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人格尚不是整全人格,毋宁说还只是人格的一半:道德主体无限感兴趣的乃是他自己的真实,他还不能通过否弃这种真实而把另一可能纳入到自身之中。这一可能就是对“神圣者”的无限兴趣(注:参见克尔凯郭尔《人生道路诸阶段》一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换言之,道德只承认作为自我的“有”,不承认、不接纳作为“相异者”的“无”。而只有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同时接纳这二者,方能称得上整全的人格。从表面看,宗教信仰也只是人的一种行为,与其他行为包括求意义的诸方式杂然并存。然而,这种信仰却发生在个人生活的核心处并涵盖了它所有的方面。信仰是心灵的最为核心的行为。它不是人的整个存在之某一特殊部分或某一特殊功能的运作。所有这些部分和功能都在信仰的行为中结合起来了。信仰并不是这些部分和功能的影响的总和。它超越了每一特殊的影响,也超越了这些影响的总和,从而反过来对每一这样的因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注:参见蒂利希《信仰的动力》第1—2页,Haper & Row,Publishers,Inc,1957。)。一个人具有何种审美趣味,对游戏的选择和喜好如何,一般并不涉及他的信仰,更难对其信仰发生显著的影响。反之则不然。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必然要影响到他的整个生活:不仅要影响爱、友谊、道德修养这些与人格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而且还要影响到人生的其他方面,甚至还影响到求生存或与求生存相关的活动。正如斯特伦所说,宗教信仰会造成信仰者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既是根本转变, 当然会造成人生诸能力、诸方面的相应调整。可见,宗教信仰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人的一种行为,而是关涉到人的整个存在方式的一种最为核心的行为,对人格的培养和性情的锻炼有着潜移默化但又深刻持久的影响力。
宗教信仰的以上特点,还主要是从形式上见出的。下面再看它在求意义活动中的内容方面的特点。
五、宗教信仰求取意义的特点
宗教信仰的核心处包含着人所要取的两大意义。这两种意义并不一定而且多半不会向作为信仰者的当事人清晰地呈现出来。
1.对无限性的追求
“无限性”相对于“有限性”。在此,“有限性”包含两个方面:世界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性。世界不仅指自然,也指社会。世界的有限性也就是自然和社会的有限性。自然和社会的事物,不论是矿物、植物、动物(其中也包括人),还是器物、典章、制度等等,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其中,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永世长存。就连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以及其上我们称为“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在时间中形成的东西,并且肯定也有消亡解体的一天。这是时间的有限性。有限性还有另一含义,即性质的有限性。凡是世界中的事物,乃至这个世界本身,都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甚至是恶的。在此,对“无限性”的追求也就是渴望超越世界的“有限性”,即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完满世界的意义祈向。这个无限的世界至少有三个规定性:(1 )这个世界应是“永恒的”。“永恒的”是说这个世界以及存身其中的东西能摆脱生灭流变的限制。(2)这个世界应是“神圣的”。 “神圣的”是说这个世界以及存身其中的东西不再是有缺陷的、丑恶的,而是完善辉煌的。(3)这个世界应是“正义的”。“正义的”首先指秩序的存在, 即有一凡俗世界所无法相比的合理秩序。其次还指秩序的性质,即这一秩序是按下述原则来安排的:能准确无误地评判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并毫厘不爽地给以赏罚。另一方面,人的有限性也包括上述两方面:生命的有限性和人性的有限性。生命的有限性是说人是有生有死的。人的存在只在生—死之间。人一降生,就进入这个有限的世界并同时受这个有限世界的法则的支配:人有温饱饥寒的感觉,有从幼到壮的成长,有健康疾患的转变,有喜怒哀乐的体验,有衰老死亡的大限。生,不容选择,死,无法逃躲。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死亡最终把人的存在抹得干干净净,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似的。人性的有限性是说人总是有弱点的。自其轻者而言,虚伪、自私、偏执、骄傲、忌妒、贪婪、好色、怯懦、冷漠等等,是人经常不同程度陷于其中的。自其重者而言,人性甚至还有极为凶残的一面,若施于个人,则个人不幸,若施于社会,则往往酿成奴役、战争之类的深重灾难。对于这些弱点,最多只能加以限制、防范。道德修养和健全的法制就是这样的手段。但这些弱点却不是可以根除的,因为它们植根在人的有限性之中。是人,就必然有此弱点。社会和制度是由人组成和构建的,人的种种弱点必然进入其中并造成它们的种种不完善。在此,对“无限性”的追求亦是渴望超越人的“有限性”。这体现在“生命”方面,则是灵魂不朽和永生的信仰:人的肉身固然死灭了,“但灵魂”却出窍并以某种方式延续下来了。体现在“人性”方面,则是人性的完善与得救的信仰:人不仅因彻底摆脱了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羁绊而显得自由无碍,而且还因克服了人性的种种弱点达于尽善尽美。有限存在的事实一旦给出,无限性的境域也就同时敞开。“人是由他对无限性的觉知而被推向信仰的”(注:参见蒂利希《信仰的动力》第8页。),同时也在信仰中将此无限性加工为他生存的意义之域。
2.对神圣价值尺度的追寻
与上密切相关的是人对神圣价值尺度的寻求。这是宗教信仰求意义在内容方面的又一显著特点。人生在世,总离不开各种尺度(标准)。这些尺度的设立,是用来规范、评判和指导人们的思想行为的。但所有这些尺度都是有限的。其表现有三。一是缺乏“高于性”。“高于”指的是比“人”高。具有“高于性”的尺度能够量度人世间的事物,而不被它们所量度。在此,尺度与被量度事物分属全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人制订出来的各种尺度都缺乏此种“高于性”。它们是人制订出来且又用来量度人的。在此,尺度所由从出的领域与被量度事物属于同一领域。人制订的尺度能量度比人低的东西,但却无法真正成为他自身的尺度。只有一种本质上比人高的东西,才可能成为量度他的标准。二是指缺乏“绝对性”。这又首先指缺乏“普适性”。人制订的各种标准,无不受时空的限制。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其所制定的价值尺度也常常不同。这种不同有时竟至截然相反的地步。这就为量度的有效性带来了困难。其次,缺乏“绝对性”还特别指缺乏“公正性”。有不少的尺度,本身就不公正,而只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和兴趣而制定的。以它们为标准,难免就要导致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状况。三是指操作上缺乏“准确全面性”。即使是那些相对稳定、公正的尺度,一旦由具体的人或机构来加以施行,也必然会因个人或团体能力上的有限而出现下述偏差:对于那些如实表现出来的行为,完全准确(毫厘不差)的评判可说微乎其微,更多的是不及或过。对于那些未充分表现出来或伴有假象的行为,评判常常失当甚至错误。因此也才一直有把腐败者当廉洁者、把奸佞者当忠信者、把庸常者当佼佼者来表彰褒奖的众多事例。而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暴露的行为,则是任何尺度都探测不到的。不仅法律奈何他不得,就是道德谴责也休想近他分毫。以上几种偏差,固然可因各类监测手段和矫正措施的完善而有所减少,但却永远也无法消除。它们的存在,使历史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笔糊涂账。然而,谁有权这样说:颠倒错乱是可以容忍的,无辜受难的叹息和奸恶得逞的狞笑是可以充耳不闻和一仍其旧的?
人无法把自己的“账”算清楚,是因为他用来量度的标准是他自己订的且又是由他自己来执行的。由于人是有限的,故由人设立的尺度及其运用也必然是不完善的、易出差错的。然而,人又并不甘于此,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准确无误地量度、评判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决不让善良蒙辱,狡黠得逞,要使人的历史成为正义的历史。为此,人便把目光投向了神圣的价值尺度及其执行者。
这个神圣价值尺度及其执行者的统一就体现为宗教中的“神圣者”(神、上帝等等)。“神”、“上帝”高于人,故其立下的标准可以成为衡量人的普遍尺度。这同时也保证了它的“绝对性”。作为执行者,由于“神圣者”是全知、全善、全能的,故对每一发生的行为及其性质都能了若指掌;没有什么能够不进入或避开这种锱铢必较的“知”;同时又有能力对其所知的行为及其作出者进行处置。这种处置并不因当事人的隐瞒和死去而被取消:它穷追不舍直至彼岸来生。而且这种处置是绝对公正的。它因为“知”得准而处理得“当”,没有不及或过的偏差。换言之,人做不好的,神能做好;人办不到的,神能办到。通过“神圣者”的干预,通过神圣价值尺度的设定与比照,一种向上的提升力量出现了:人的得救有了希望。无论这一切在事实上究竟如何,在宗教关于“神圣者”及其性质的设立和谈论中,不就突显着这样一个意义祈向即它要通过最高尺度的设立来使人的历史成为正义的历史吗?在此,神的正义成为人的历史运动的目的和方向。
把上述两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对超越的渴望:人力图通过信仰创造出一个高于现实人生和世界的完满存在。这是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内在冲动。“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个“永恒本性”是什么?按我们的理解,其实也就是对以“无限性”和“神圣尺度”为基本内容的“超越”意义的寻求。
综上所述可知:意义求索是人生在世的一种基本活动;求意义有种种方式与形态,其中,作为信仰的宗教,乃是意义求索的特殊方式;就关切的“对象”看,宗教信仰的对象是超验的“神圣者”,就关切的“主体”看,宗教信仰的主体是人格“整全者”,两者在信仰行为与意义体验中实为同一个东西;与其他专门的意义形态相比,宗教信仰求意义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即它是通过对人和世界有限性的超越,通过对神圣价值尺度的设立来求取意义的;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追求,表明人要为他的整个生存觅得某种目的和方向,俾使他的历史有可能成为正义的历史;只要人还在世,就必定有求意义这回事,也必定有以宗教信仰这一特殊方式来求建构意义之源的需求;植根于有限性深处的这种宗教信仰,恐怕是不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理性和科技的昌达而趋于消亡的。这也许可为今天的宗教热现象提供某种注解。
收稿时间:1999—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