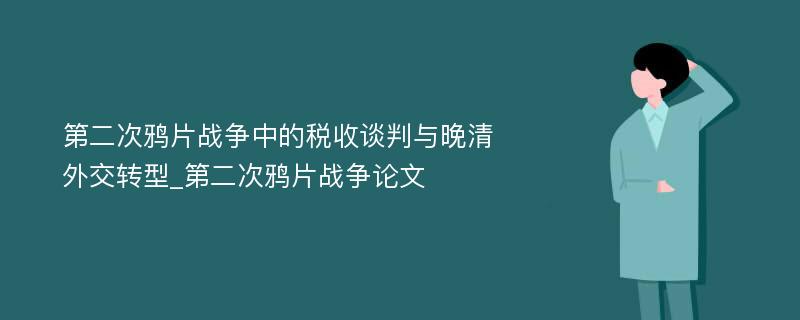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税则谈判与晚清外交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则论文,晚清论文,鸦片论文,外交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根据条约的要求,关于税则等具体的事项须到通商口岸上海才能议定。因此,英法美三国公使率兵船于1858年7月6日南驶,准备到上海与清政府就税则和贸易章程等问题进行进一步谈判。同时,清政府也于7月15日简派桂良、花沙纳、基溥、明善等携带钦差关防到江苏,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就通商税则等事宜与西方列强进行谈判。然而,综观通商税则谈判的整个过程,更为人所瞩目的则是清政府的谈判代表与清廷权力中枢之间关于税则和贸易章程的谈判原则的分歧和斗争。事实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关于通商税则谈判的整个经过,反映了清政府对于西方列强的认识一步步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清政府开始逐步适应西方列强的外交观念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目前学界关注较少,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税则谈判前清廷与谈判代表的意见分歧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上旬,英美法三国公使分别到达上海,等候钦差大臣桂良等与其进行税则谈判。但是这时,桂良尚未从北京启程,因此,上海的对外交涉主要由两江总督何桂清主持。
对于税则谈判,两江总督何桂清的总体目标与清政府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这是“夷务之一大转关”,(注:《筹办夷力始末》(咸丰朝)卷29,第1065页。)都想借通商税则谈判来补救《天津条约》的利权损失。但是,何桂清与清政府在具体如何挽回利权、应该挽救什么利权方面却有较大的分歧,体现了处理这一问题的不同视角,即是从当时的局势出发还是从固有的外交理念和模式出发。
何桂清奉旨后,积极地进行税则谈判的筹备工作。首先,分别照会英法美三国,告知清廷已派钦差大臣到上海准备与其谈判,请其静候,以免外国公使别有行动。其次,派定各熟悉外国事务的大臣,如苏松太道薛焕、候补知府吴熙等事先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钦差大臣桂良等到后即可调遣随往。同时,何桂清还就《天津条约》的祸害和如何进行税则谈判以挽救利权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天津所议条约,”其处心积虑,则在垄断专利,……侵夺内地商贩之利。一堕其术,则数年之后,我已民穷财尽,彼之富强更甚,……国计民生,大有关系。”因此,为了尽量减少危害,会商税则和通商章程时应坚持如下几点:一、“不准(其)将内地货物即在内地各口往来运销”,如此则“小民衣食有资,大局尚可维持。”二、“夷税以丝茶为大宗,而茶多于丝,故道光年间所定税则,茶税较重。”如果根据《天津条约》减茶税增丝税的原则,则税收方面必将“短征甚巨”;同时,允许外国人到内地贸易,原来征收的三关丝税外国人也有可能不纳,因此应“设法妥议,庶关税不致顿行短绌。”三、长江通商,其害尤巨,所以应等桂良到后再“和衷熟商”,以求“能补救一分,即少一分后患。”(注:《何桂清奏薛焕等据天津条约核议就税则补救之法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099-1101页。)“会议通商税则,本属羁縻之策,并非经久之图。该夷素假信义以通商,我即因势利导,示之以信,速与议定税则,收回利柄”。然后,“中外一心,卧薪尝胆,设法制之,未尝不可力挽狂澜。”(注:《何桂清奏已饬薛焕先与各国查议税则零星细款请敕桂良等迅速来苏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08页。)因此,当外国公使纷纷到达上海而北京的谈判代表还未出发时,何桂清多次上奏,请求钦差大臣速到上海,以期能“乘此驯顺之时,迅速筹办,或可挽回万一”,(注:《何桂清奏薛焕等据天津条约核议就税则补救之法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099-1101页。)同时不使外国公使借端滋事。
然而,清廷的希望却远非如此。事实上,清廷则希望通过通商税则谈判能够消弭《天津条约》中清政府认为有损国家利益的条款,即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长江通商、允许外国人内地游历、赔偿军费等条款。同时,清政府认为,中外冲突的根源在于外国人的嗜利,因此希望以全免关税为条件,让西方列强放弃公使常驻北京、赔偿军费、长江通商等条款,并且交还广州城,并认为如此可以一劳永逸。(注:请参看《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28页及其他相关的《廷寄》。事实上,清廷的政策向来是把外交事务看作纯粹商务性质的,因而也就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将外交事务的管理一并委之于既是对外贸易集中的海口、又是离政府所在地最远的海口广州的省当局。参见《远东国际关系史》,第201页。此外,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此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请参看该书下卷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第1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钦差大臣桂良还未到上海之前,清廷虽然委派何桂清协同办理谈判事务,但对何桂清的建议却不置可否,只是谕令何桂清等对外国公使“好言羁縻”,不使他们再北上滋事;同时先令薛焕等“与各夷清查历年夷税”,“等挂良到后再行核办”,其目的在于“大皇帝知尔等近年税银多有吃亏之处,是以清查明晰,将来不至尔等再有赔累。”(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9,第1084-1085页。)显然,清政府的目标与当时的历史现实相去甚远,只能是清政府的主观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传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模式仍是清政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八月上旬,英法美等国公使已在上海呆了一月有余,仍未见清朝钦差到来,颇有怨言。何桂清害怕夷务又多有波澜,一面上奏清廷,请求让桂良速来上海,一面让薛焕“事事处处,示之以信,设法驾驭”,同时,何桂清又一次阐述了自己对税则谈判的看法。他认为“皇上驭天下之大柄,惟信与财,而藏富于民,尤为理财之要诀。今在天津所议条款,任其周游天下,无论何货,互相贸易,则我内地货物,亦听其在内地兴贩矣,垄断罔利,莫此为甚。……胥见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而我藏富于民之术穷,民财既尽,即无恒心,其患有不忍言者。”只有钦差速来上海,议定税则,“以为暂时羁縻之计”,才能使得“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注:《何桂清奏各使因钦差未到即欲回国请敕桂良等兼程来苏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17-1119页。)无疑,此见是他在两江总督任上观察、处理中外事务的多年经验的总结,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清帝对此看法却不以为然。对于税则谈判,清帝一再要求何桂清等晓谕外国公使,令其静候钦差,会同商办;同时,清廷认为,等先期出发的明善、段承实到达江苏后,何桂清就会知道办理通商税则章程的“内定之法”,“自应遵照内定办法,未可擅出己见”,“倘于地方有窒碍之处,不妨与桂良等悉心筹议,稍加变通,大致不可更改。”“不得以现议办法,恐致军饱短绌为词”,(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16页。)“办成后,利权不至尽归夷人,可毋庸鳃鳃过虑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19页。)对清廷的策略显示出极大的信心。
八月十四日,先行从北京出发的武备院卿明善、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等到达常州,并于十六日由常州前往上海。一路上,通过调查上海中外交往情形,明善等认为,“其全免入口税课一节,亦不敢早为吐露”,应该“看开导之后,该夷光景若何,再为宣布皇仁俾知感激。”“若仅能消弭一二要件,或可不须免税,岂不计出万全。设夷性犬羊,坚执不允,再从税务作为转圜,又多一层办法。”(注:《明善等奏行抵常州与何桂清筹议全免入口税课不宜早为宣布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27页。)但是,清廷并不同意明善的看法,认为其“所筹尚未妥协。”一再指示,“此次桂良等前赴上海,应照原定办法,俾各夷感服。”如果“仅能消弭一二事,则该夷仍要赔偿兵费,广东省城即不即时退出。”“况待该夷坚执不允,然后再以免税为转圜,则该夷必以我为背约,愈多借日。”因此,“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无须再赴天津伸诉免抑,所许各项,全行罢议,此为一劳永逸之计。”“若如明善等所拟办法,即使该夷目前应允,日后必来饶舌,终无了局。”全免税课,外国侵略者的所有侵略借口都将不复存在,因此就可一劳永逸。于是,清廷一再强调,“如与地方情形有碍者,亦只可稍为变通,而大局不可更改。仍当遵办为要。”(注:《明善等奏行抵常州与河桂清筹议全免入口税课不宜早为宣布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廷寄》,第1128页。)
八月十九日,桂良等到达常州。通过了解沿海中外情形,以及薛焕、吴熙等与英使威玛妥、李泰国的当面交涉的具体情况,桂良等开始对清朝政府所面临的时局有较清楚的认识,也向清廷提出了关于通商税则谈判的意见。他认为,“清厘历年短收关课,本为笼络夷人之计,但犬羊之性何常,难保其不借此要求赔补。”“全免入口税课一层,亦为夷人惟利是图,给以便宜庶易令其就范。但设关抽税,借以稽查,若听其自便,则利柄尽属该夷,好宄且有不可胜道者。”因此,桂良等认为,通商税则的谈判应该:一、请将加惠该夷之恩旨暂缓宣布,因为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的条款,经过交涉,已有活动的余地。二、长江增开通商口岸,“若与之辩论,徒增口舌,惟有不准其将内地货物即在内地贸迁,则无利可图,或者其念可以渐息。”三、“兵费六百万,似不值与较”,因为如果关税不减少的话,两年就可以足给,同时还有欠税可抵,“以彼之税,偿彼之费,于我似无大损。”总之,当时的要务,“务以尊崇国体为先,尤以收回利权为要。”(注:《桂良等奏拟请将全免入口税课一节暂缓宣布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30-1131页。)此后,何桂清又上奏进一步指陈目前的形势,认为桂良、花沙纳“无将无兵,徒托空言,力阻其诣阙之请已属不易。……今事已如此,惟有就会议税则,为补偏求弊之计,似未可顿改前约,以致借口失信,另起波澜。”“臣维征收关税谓之稽征者,稽查其出入之货是否违禁,而征收其税也。若不征其出入口之货税,则无所稽考,竟可任听该夷将我内地货物,即在内地贸易,胥天下之利柄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因此,“利柄应该收回,税则不可轻免”。(注:《何桂清奏利柄必应收回税则不可轻免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32-1133页。)显然,桂良和何桂清的奏折,是根据其对时局的理解而作出的建议,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何桂清的意见,总结了多年上海与西方列强交往的经验,对关税的实质以及整个时局的理解更为深刻。
但是,清廷对桂良和何桂清所说“利柄”以及当前清政府所面临的实际情形还未能完全明了,因此坚持认为他们的意见不能使清政府“一劳永选”,因此应坚持“内定办法”,以免有妨大局。对于桂良等的意见,咸丰帝批示:“若逐款与较,何异授该夷以柄,哓哓不休。况抵偿兵费一节,全括于免税中,此时初入手,即作此下策,徒令该夷气骄意得,反似有所畏忌,勉强而然。何其见不能定,心总易摇,朕殊为过虑,恐其一浪未息,一浪又兴,后此作何了局?惟望卿等断不可于初定办法之外,另筹省事之法,破除情面,勿恤人言,方不致自干咎戾,无裨大局。”(注:《桂良等奏拟请将全免入口税课一节暂缓宣布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31页。)对于给何桂清的答复,咸丰帝似乎说得更加清楚。“(何的意见)所筹究为日[目]前起见,并非一劳永逸之计。……何桂清受朕厚恩,断不至别有他意,特恐属员虑及免税后,无可沾润,因而设词淆惑,亦事所必有。该督当力持定见,勿恤人言,至于地方情形,或有窒碍,……亦须将窒碍之处详细陈明,不可自出己见,致妨大局。”(注:《何桂清奏利柄必应收回税则不可轻免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廷寄》,第1134页。)
由此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通商税则的谈判中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政府中枢与谈判代表桂良、何桂清之间关于通商税则的意见分歧,事实上是双方对时局的不同理解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的分歧所造成的。以何桂清为代表的沿海地方官员,在长期的与西方列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利权”在国家生存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以此为努力争取的目标。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晚清中国政府的“军械兵通成法,皆不足以御夷”,只有“从新制造军械,拣士卒”,然后“中外同心,各口协力,方可制其死命”。因而目前只能“顺其性而驯之”才能相安无事。(注:《何桂清奏利柄必应收回税则不可轻免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32页。)但是,清朝政权中枢仍秉承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模式,试图用传统的羁縻手段,即通过对外国人施予恩惠,使得其对中国感恩戴德,从而“就我范围”。同时,在他们看来,商业利益仍是用以羁縻的重要工具,而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基础,因此还是一直坚持以全免关税来消弭外患,从而达到一劳永逸。
二、谈判代表的力争和清廷中枢认识的转变
面对清帝的多次严令,以及清政府权力中枢对时局的无知,在关于通商税则谈判中,中方代表桂良、何桂清等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一方面,如果秉承朝廷的旨意,则将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利权的流失,同时,谈判又将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根据自己对时局的判断而进行税则谈判,则又是抗旨不遵,又有身家性命之忧。他们的选择是两难的。
然而,为了挽救国家利权,桂良、何桂清等还是顶着压力,尽力向清廷解释清朝所面临的时局及其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以求得清帝对他们的意见的认同。九月初三,两江总督何桂清上奏,阐述外商和外国公使之间的不同,以及全免关税并无裨大局。他分析道:“各夷之往来贸迁者,谓之夷商;总理各口贸易事宜,取其盈余以供国用者,彼初称公使,今则僭称大臣,我则目之为夷酋;其领事等类,乃夷酋所属之人,是夷酋与夷商分而为二者也。”因此,“江海关征收夷税,向由夷商将货物清单报明领事,转报海关稽征,明立文案,中外皆有册籍可稽,并无浮收及征多报少之弊。若清查浮冒,则该夷并无赔累,夷酋夷商均不知所感也。”不可能起到令其心悦诚服而“就我范围”的功效。同时,“税出于商,与夷酋无涉,若免其出入口之税,夷商固属乐从,夷酋仍不知感也。”同样没有效果。此外,“鸦片烟我虽有禁,被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臣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者也。”事实上,外国人称兵犯顺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外商的利益,而是在于“夷酋不能进广东省城与钦差大臣会晤”,“故先窃据广州,而欲诣阙,皆系夷酋虚骄之气,与夷商无与也。”因此,何桂清指出,“驭夷之法,似应推求起衅之由,顺其性而驯之,方有把握。否则转以钦差大臣所定条约既不足凭,更坚其请觐之念,另起衅端,所关实非浅鲜。”(注:《何桂清奏免税开禁无裨大局现另筹挽回之法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53-1154页。)无疑,何桂清的意见,对于当时情势的认识实属洞若观火,这说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沿海通商口岸的清朝官员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愚昧无知了。遗憾的是,对于这种认识,清廷并未能认同,而是要求必须“仍遵内定办法,即使有所窒碍,亦应缕晰陈明。”(注:《何桂清奏免税开禁无裨大局现另筹挽回之法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54页。)
八月底,桂良、花沙纳、段承实、何桂清、王有龄等分别抵达上海,并且照会英国公使,准备与其进行谈判。但是,英国公使却以广东新安县团练与英国人的纷争为由,不与会谈。同时,桂良等又命薛焕对英国公使进行暗示,试图以全免关税换取“一劳永逸”,但英国似乎并不领情。桂良认为,“细阅该夷(英国)照会,所重不在利益,即以税课啖之,未必能动。”“此时遽行宣露(全免关税),恐该夷因贪利起见,佯为应允,再过一二年后,又执约中之事向我要求,何以应命?抑或另生枝节,均不可以不虑,彼时再欲收回利权,更从何处措手?”同时,桂良解释其虽屡奉严谕但仍坚持己见,是因为“体察夷情,参酌时势”后,“不敢顾此失彼贻误大局。”所以“再四斟酌,惟有因势利导,补偏救弊,和衷商办,总期不负委任。”(注:《桂良等奏徒言免税希冀各国罢弃全约势必不行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66页)但是,清帝仍然不为其所动,并且认为桂良等并未尽心。他严令桂良“自当激发天良,力图补救,若毫无把握,不过希图塞责,自问当得何罪?”“该条约(《天津条约》)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桂良等能将此四项一概消弭,朕亦尚可曲从,若只挽回一二件,其余不可行之事,仍然贻患无穷,断难允准。”同时,因为桂良上奏中何桂清没有会衔,清帝大为恼怒,指责其“奉旨会办而负气若是,真是无福之辈。”要求其“亦当与桂良等筹议,计出万全,岂可专听属吏之言,自贻罪戾。”(注:《桂良等奏徒言免税希冀各国罢弃全约势必不行折》,《廷寄答上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67页。)“即使照该督之意办结,向该督能以首领保之,是该督真有把握,朕亦无不欣允。”(注:《桂良等奏徒言免税希冀各国罢弃全约势必不行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朱批》。)口气十分强硬。
然而,何桂清等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九月十三日,何桂清仍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依然上奏详细阐明五口通商后的中外形势。他解释道:鸦片战争前,“其难发自夷商”,而五口通商后,“夷商与华商自行互相交易,已无洋行把持垄断之弊;其应完税课,由夷商报明领事,转报海关稽查抽收,亦无冒收中饱之弊;鸦片烟则公然贩运,无从禁遏,夷商亦无间言。所以复行称兵犯顺者,系夷酋虚骄之气,为不得进广东省城,与钦差大臣会晤起见。”“其欲更改税则章程者,因今昔物价不同也。其索赔商亏二百万两者,亦据声明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等因,……是现在之难,又发自夷酋,不涉夷商之事。”所以不能用“款夷商”的办法来对待。同时,“该夷虽具人性,而凶狡异常,恃其船坚炮利,结之以恩,转以为畏之,慑之以威,即行决裂。”如果全免关税,外国人将会看成是《天津条约》之外的新的恩赐,“而夷酋之所仰望者更奢。不独所许各项不能全行罢议,且将并一二事而不能消弭,从此借口要求,转生枝节。”“若不借征税为稽查,则华夷不分,更无约束,滋生事端,当不待崇朝。”“免其税课,即能俯首听命,亦不能决其必遵。”要真正解决问题,只有等到“兵精饷足”之时,目前只能“顺其性而驭之。”(注:《何桂清奏洋务皆由各使启衅宜藉征税为稽查以杜其渐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69-1170页。)
此后,钦差大臣桂良又两次上奏,进一步阐述不能全免关税的原因,“此时若照原定章程,无论该夷断不肯全行罢议,而利权一归外国,日后夷商往来,均属无可稽查。所谓‘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其弊不可胜言,且不税于夷而税于商,更有许多窒碍。”所以“非敢固执偏见,若稍可迁就,断无不遵照原定章程妥办之理。”(注:《桂良等奏英使覆照怀情词傲慢已照覆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72页。)只能“相机斟酌妥办,保全大局。”(注:《桂良等又奏税务不可全免各国坚请撤黄宗汉任削罗衍等权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72页。)但清帝仍未能相信,不仅对桂良等“办理不善”严加申斥,同时指出,只有将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偿兵费始还广东省城四项全行消弭,才能“曲从所请”,否则“断不能允”,桂良等也得“自问当得何罪”。(注:《廷寄答上三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73页。)最后,桂良等终于将不能全免关税“其中有万不忍言,亦万不敢言之苦衷”上奏清廷,即“盖英夷之雄长西洋,于其属国不完关税,已非一日,其志尚不全在利益,而在夜郎自大。故臣等欲留此遵奉天朝定制完纳关税之名,以崇国体,非敢惜此微末,致落下策也。”(注:《桂良等又奏税课末便宽免以崇国体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77页。)即关税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由此,清帝才焕然冰释,同意暂且不提出全免关税,另商挽救策略。
此后,桂良等又就全免关税对国家主权、经济利益、中外交往等各方面的危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注:桂良等认为,全免关税的危害其计有十条,详细请参见《桂良等奏免税有十可虑连日会议未敢轻举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80-1181页。)认为“其中可虑之处,实难枚举”,所以不敢仅为了顺承旨意,以求自身免戾而不顾全局之安危姑且迁就。全免关税可能带来的危害最终得到了清朝政府的认同。
由此,经过桂良、何桂清等与清政府之间的多方辩驳,“利权”在国家中的作用逐步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所认识。即通商和关税不仅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它不仅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关系。这与传统外交体制中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从而达到羁縻效果的基本策略相比,无疑具有历史性的进步。
三、税则谈判与“消弭四款”失利
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初一,桂良等照会英国公使,请求派员会商通商税则,但是,英国却送来照会强烈抗议,说广东黄宗汉、罗衍等乃在组织团练与英国对抗,这有违和好之意,英国准备再次北上天津。桂良等极力劝说,几经反复,英国公使同意派员进行税则谈判,但清政府必须“将总督黄离任,并将罗、龙、苏三绅士特奉之权撤去”(注:请分别参见《英使额尔金为请撤黄宗汉任削罗衍等权给桂良花沙纳覆照》和《英使额尔金为派员商议税则给桂良花沙纳覆照》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75、1176页。),桂良等答应上摺奏参。同时,桂良等向清廷汇报,尽改条约已不可能,只能设法将第一要事(即公使常驻北京)设法消弭,以及赔偿军费由关税抵偿二事。
九月初六,桂良等委派藩司王有龄、臬司署上海道薛焕,督同知府吴熙与英国公使共同商定税则,并且试图以全免关税来使其放弃驻京等四项要求,但遭到拒绝。九月十六日,桂良等又照会额尔金,“告以驻京一节,诸多未便,碍难照行”,“将来办理各国事务改由上海商办,……或由钦派之大员,有事随时代为陈请,往返甚速成,较之由京发出,查办更为便捷,即明年互换条约,亦可以无庸远涉”。(注:《桂良等奏连日与各国会议条约万不能动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第1184-1185页。)同时并请李泰国代为开导,但均没有结果。此后,桂良、王有龄、薛焕等一再与英使商议,“虽已精疲力竭,仍借税则故意延宕,与该夷早夜纠缠,总期能去一款,即少一款之患。”但是,“该夷持之甚坚,难以得手,即驻京一节,且以奉到朱批,业经奏明伊国君主,不能更动为词。”“即能不长驻京师,而随时往来四字,未肯改去,且必须择一与彼有益之处始可相抵。”(注:《桂良等奏洋务办理棘手各国不肯罢弃条约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2,第1189-1190页。)四款之中,没有一款可以消弭。同时,英法美三国公使还准备一同逆长江而上到汉口。对于这种局面,清帝十分愤怒,责备桂良、何桂清等深受重恩却无能改变局势,“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坚执己见,竟于国计无裨,……清夜扪心,亦当自愧”。(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2,第1191页。)
十月初,清廷提出的消弭四款所议均没有结果,何桂清因江苏军务紧急拟先回常州,同时对如何处理目前中外交涉向清廷提出了详细的意见,认为“欲罢其议,为一劳永逸之谋,断非口舌能争,亦非微利能动,必得用兵方可。”并且,果真要与外国人开战,必须“广求贤良,其经济学问,实已见诸施行著有成效者,置诸朝右,然后中外同心,协力维持,方能万全无弊。”(注:《何桂清奏缕陈洋务棘手情形折回常州再定进止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2,第1194-1195页。)同时,何桂清还指出,“中外交涉事件,有不能凭律例以决断者,全恃条约以为范围。若不收其关税,……真可任其为所欲为矣。……长驻京城一事,无论如何为难,总求挽回,以慰圣怀。至商民利柄,亦必当收回,庶江、浙、闽、广亿兆生灵衣食有资,不致另启乱萌。关税不增不减,聊以接济时艰。其各处游行,虽不能禁止,亦当严定章程,以资约束。粤东省城缴回有期,凡此皆所以崇国体,而藉条约以维系之也。”(注:《何桂清又奏美商船为华船碰损索赔无厌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2,第1198页。)但是,清廷仍坚持必须将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等各要件设法阻止,并且认为,“现议税则,该夷必有利益可沾,即可从此措手,不至即行决裂。”所以“该大臣等必当各矢忠诚,竭力挽回,为国计民生豫筹久远之策。”(注:《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2,第1196-1197页。)
经过多次磋商,虽然各国都表示愿永敦和好,但是,对于清政府要求的试图“消弭”的四项条款,各国均以“已定条约万难商改”为由加以拒绝。因此,在通商税则谈判中,为了尽量挽回利权,桂良等只好采取所谓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尽量减少损失。首先,对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一节,桂良等指出,天津条约事实上是“恃兵威要挟而成,举凡于英国有利而于中国大有损害之处,中国交涉人员均不容置辩”。同时,条约第三款规定,“或是留一代表驻京,或是派遣一二人随时往来”,因此请求从宽解释,不长行居住。(注:对于此,英国公使额尔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一面坚持所有条约权利的全部字句效力,但另一面却作了一项诺言,表示愿行文本国政府,并愿以“英国钦差于来年换约时倘能在北京受到适当接待,且天津所议条约的其他一切细节能获得充分实施,则允宜训令女王陛下驻中国代表在北京以外选择一驻扎地点,或按期访问京师,或仅视公务上的需要随时前往”之意,作为他本人的意见,敬请英国政府核夺。额尔金的方针经英国政府批推。参见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9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其次,长江贸易一节,桂良等认为,其目的是“欲攘我淮盐之利”,因淮盐“正课杂项及商民所得,每年计数千万,恃以养命者无数生灵”,所以“将食盐归人违禁货物款内,不准往来装载,将来设有逾禁,亦必随时严办,以杜外夷侵越之渐。即炮弹军火,一概不准进口。”其三,山东登州、牛庄两处口岸,“以豆石、豆饼为大宗,向来皆系江、浙、闽广商贩船户运销于东南各省,其利甚大。……其倚此为生活计者不下数千万人。”因此,税则规定,牛庄、登州两处不准英国商船装载豆石、豆饼出口,由此,“商船从此照旧贸易,不致遽绝衣食,海运漕粮亦可兑运,实于漕务民生,两有裨益。”其四,内地通商一节,“议明京师不准前往外,无论何处,必须体面人,方准该国领事官发给执照,由中国地方官查明盖印,以便随处呈验,既有稽考,可免夷匪混迹。”(注:《桂良等奏税则日内议定英人坚执入江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2,第1202-1203页。)根据这些原则,桂良等于十月初三和十月十九日分别和英美和法国公使商定通商税则章程,确定了值百抽五、行李免税、运往内地缴二点五子口税等原则,同时还详细规定了一些禁运物质,并附有常见货物的征税标准。(注:条约详细内容请参看《海关税则》,《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3,第1247-1253页;或者王铁崖编:《中外旧约汇编》第一册,第116-14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前者附有说明,表达了桂良议定这些条款时的考虑,后者分列英法美三国条款,并列有各常见商品税则。)而清廷所要求的“消弭四款”,桂良等建议以另立专条的形式和西方列强进行谈判。
显然,通商税则的商定,离清廷“消弭四款”的要求相去甚远。事实上,尽管桂良等多方努力,总是没法办到。此后,清廷又多次谕令桂良等设法再与英法美等谈判,并且以办理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移到上海由两江总督何桂清兼任等条件,希望外国公使能在上海换约,不必进京。但是,英国公使额尔金在与桂良等签订《海关税则》后,即率舰队到汉口,回沪后又以广东中外纷争为由南下,其后,英国又以普鲁士为公使,到中国行使换约。美法各国公使也纷纷回国,此后,两国政府又另外派遣公使到中国来。桂良等始终没能有机会就清廷要求的“消弭四款”与外国公使进行谈判。通商税则以桂良、何桂清等人的办法确定下来。
四、通商税则谈判与晚清外交转型
众所周知,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虽然经过鸦片战争的创痛,但是,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却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同时,也由于长期对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观察,清政府的地方官员的对外观念已经开始出现变化。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税则谈判,我们可以发现,桂良、何桂清等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已不再是从前的愚昧无知,他们的外交观念也开始突破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这主要体现在:
一、对于“利权”的认识。“重利轻义”、“重道德轻物质”是儒家文化的主导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也以此为价值指向。在宗藩关系体制中,商业利益只是宗主国换取藩属国的尊崇与服从,实现其“羁縻”政策的手段之一,因此在对外关系中,往往成为政治的附庸,不具有独立的地位。然而,在通商税则的谈判中,何桂清、桂良等谈判代表已经开始对其有所超越。首先,桂良、何桂清等已经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是维持清朝统治的重要手段,“皇上驭天下之大柄,惟信与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基础。因此,在通商税则谈判中,他们提出应以尽量设法挽救利权为目的,多次强调“利柄应该收回,税则不可轻免”。在他们眼中,物质利益已经不再是外交关系中可以随意牺牲的砝码,而是需要努力争取的重要内容。其次,在通商税则谈判中,桂良、何桂清等已经认识到,关税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物质利益,而且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它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且是一种政治关系。这在当时更是难能可贵。
二、对于西方列强的认识。在通商税则谈判中,谈判代表何桂清、桂良等人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和前人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中国大多将西方列强一概视为嗜利成性的“蛮夷”,因而利用商业利润对其进行“羁縻”是处理中外关系的重要手段。在通商税则谈判中,何桂清、桂良等人已经看到,西方列强有“夷商”和“夷酋”之分,二者之间的利益及其对中国的态度既有相同又有分歧,因此应分别对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商业利润,而且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模式的外交关系体制,以此来确保他们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并且,外交体制方面的要求还是西方列强的主要目的。因此,清政府应采取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对外措施,才能有效地抵御外国的侵略。这种认识,显然已经不是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所能包容的,既显得务实,也将更为有效。
三、在具体的税则谈判中也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在通商税则谈判中,面对着态度强硬、而且拥有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的西方列强,桂良、何桂清等谈判代表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即在具体分析西方列强所要求的条款将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后,采取所谓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尽量挽回利权。和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指导下的外交谈判相比较,有显著不同。首先,宗藩关系体制所强调的是对“天朝上国”的尊崇,而何桂清、桂良等在通商税则谈判中则以挽回“利权”为谈判的出发点,其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尽量避免危害人民的生计,因而更加重视实际的利益。这与宗藩关系体制重“义”的原则相悖,更加符合近代资本主义外交体制的原则。其次,在通商税则谈判中,对于西方列强提出的、与中国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全然相悖的具体条款,桂良、何桂清等谈判代表不是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修补、限制的办法来挽救利权,这种心态也与宗藩关系体制中的心态明显不同。我们知道,在宗藩关系体制中,宗主国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地位,因而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具有显然的文化优越感。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过武力较量,中西之间实力对比已较为明显的。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桂良、何桂清等在和西方列强的谈判中并不是在这种传统的虚妄的优越感的支配下进行的,而是以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尽力挽回利权。显然,这种外交态度和那种虚骄的、貌似爱国而实际上却不可行的主张相比,(注:事实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许多传统的士大夫本着固有的爱国热情和宗藩关系的情结,从传统的对外关系原则出发,纷纷提出了抗敌、退敌的策略和方针。特别是这一时期各地的御史最具代表性,他们提出的建议最多,情绪也最为激昂,但是,这些意见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渲泄,鲜具可行性。详情请参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的相关奏折。)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利益。
有论者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清政府虽然有‘抚夷局’并先后任命了交涉钦差,……但他们都是临时‘抓差’而来的,其外交知识、经验和手段仍是处理大清藩属间羁縻事务的老套,显然不能适应与列强打交道。”(注:参见姜良芹《总理衙门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一直占主导地位。)然而,事实上,何桂清、桂良等人对西方列强的认识已经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虽然他们的外交知识、外交经验等还很有限,但是,他们处理外交事务的方法已经不再全然是处理宗藩关系的老套,而是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从上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商税则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从上述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通商税则的谈判,谈判代表所面临的压力是十分沉重的。这一方面是来自于西方列强,为了维护主权与侵略者的斗争;而更为艰巨的,则是来自朝廷中枢的压力。如前所述,在通商税则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桂良、何桂清等谈判代表的每一步骤都必须得到清政府权力中枢的同意,清廷也不断地从传统的宗藩关系体制的外交原则出发对整个通商税则谈判发布指示,而且,清廷中枢的意见与谈判代表之间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桂良、何桂清等谈判代表处于两难的境地。若是顺从皇帝的旨意,则白白看着国家利权的损失;若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税则谈判,则又是抗旨不遵,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事实上,这种两难,也正体现了宗藩关系体制与近代资本主义外交体制的矛盾。桂良、何桂清等清朝谈判代表与清政府之间关于税则谈判原则的交涉过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转型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