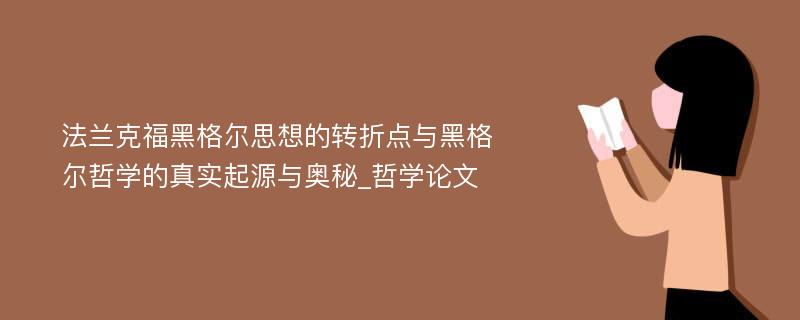
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思想的转折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法兰克福论文,起源论文,哲学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97年初,27岁的黑格尔离开伯尔尼来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801年初。法兰克福时期是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期间他开始摆脱康德主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辩证法的思想萌芽。这种转折一方面使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一度陷入了“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1〕; 另一方面也使他改变了对矛盾的消极态度,开始把矛盾看作思维与存在的共同基础和动力,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例如关于异化、扬弃、否定性、和解、对立统一等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内容。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黑格尔开始注意到“客观性”的重要意义,这客观性不仅构成了对矛盾进行积极理解的前提,而且也构成了和解思想的前提,这种态度与他在伯尔尼时期一味沉溺于主观性的情感和道德之中的倾向是截然不同的。正是这种提高使得黑格尔克服了康德的理想状态的道德主义,致力于寻求思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解和统一,从而使法兰克福时期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诞生地”。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在这部论著里,黑格尔一改他在伯尔尼时期的几篇文章(《民众宗教与基督教》、《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中对基督教的激烈批判态度。关于基督教的现实特征在这里很少直接论及,更多谈到的是宗教的精神本质(这种变化明显反映了黑格尔与现实生活的逐渐妥协)。理想对现实的单方面否定转变为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抽象的普遍概念作为精神或生活的一个环节在与具体的存在的和解中被扬弃了。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耶稣对摩西的批判或者道德主义对权威化的基督教的批判,而是裹藏在“爱”、“生命”等情感主义外衣下的刚刚萌芽的思辨神学对康德的道德神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青年黑格尔的自我清算,它标志着黑格尔从早期神学思想(即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的神学思想,其基调是希腊情感主义和康德道德主义)向思辨神学和思辨哲学的转化。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希腊情感主义和康德道德主义的瑰丽余辉,也可以看到《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思想的熹微晨光。
一、爱扬弃道德与“和解”思想
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反对犹太教的外在律法主义的主题转变为反对康德的内在道德律令的主题,耶稣与摩西的分歧变成了黑格尔与康德的分歧。与《耶稣传》中将道德与律法相比较的做法不同,在这里,出现了爱与道德命令的对立。在《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中,康德式的耶稣为了反对纯粹客观的律法,曾提出了某种与它针锋相对的东西,即“主观性一般”。这种主观性一般就是普遍的道德命令,它与律法的区别在于:律法是基于异己的权威的外在规定,道德命令则是基于主观的普遍概念的内在规定。然而,尽管有这种区别,道德命令仍然是片面的和抽象的,因为它缺乏具体的内容。道德命令表现了人的普遍的理性能力和主观理想,在它里面,外在性的权威律法被扬弃了;但是人摆脱了外在主子的奴役,却成为内在主子的奴隶,成为普遍的理性能力、概念、理想、“应当”状态的奴隶。“对特殊的东西:冲动、嗜好、病态的爱情、感性或其他种种说来,普遍的东西必然地而且永远地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客观的东西。那里面总残留着一种不可摧毁的权威性,足以激起人们的反感,因为普遍的义务命令所获得的内容、一种特定的义务,包含着同时既是有限制的又是普遍的这样一种矛盾,为了这种普遍性的形式,它提出片面的、极其顽固的自负的要求。〔2〕
外在性的异己力量(律法)被摈除了,然而人现在又陷入了内在的分离和对立之中:一边是普遍性的理性和合理意志,另一边是具体的嗜欲或任意;一边是“应当”,另一边是“存在”,而道德命令就是以这种内在的分离为前提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命令作为一种绝对的义务,要求具体的嗜欲或任意把普遍性的理性和合理意志接纳为行动的内在根据和准则,然而这种统一仍然是一种“应当”状态,它忽略乃至扼杀了“存在”本身。面对这种知性的分裂,《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的耶稣——这个耶稣已不同于《耶稣传》中那个以康德的口吻说话的耶稣——提出一种“较高的和解的天才”,即爱的意向。在爱的意向中,法规(包括外在的律法和内在的道德命令)失去了普遍性,嗜好则失去了特殊性,双方消除了对立而达到和解。关于爱与道德命令之间的根本性区别,黑格尔写道:“每一个命令只能表达一个‘应当’,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东西,从而立即表明了它的缺点,因为它没有说出存在。对于这样一种命令像:‘不要杀人’,耶稣提出了一种道德,人的爱的意向与它对立,这种爱的意向不仅使得那个命令就内容说来成为多余的,而且也打破它作为命令的形式,因为命令的形式意味着一个命令者与一个抗拒命令者之间的对立;爱的意向排除了任何关于牺牲、毁灭、压制情欲的思想,它同时比起理性的冷酷的命令是一个具有更丰富更有生命的充实内容。”〔3〕
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决裂是黑格尔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早在179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谢林就已经表现出对道德主义泛滥的强烈不满,他在写给黑格尔的信中多次表达了这种不满。谢林写道:“一旦在勿宁说是上帝把他们(指康德主义者们——引者注)带到的那个地方住定了,他们就制造出某种康德体系的肤浅杂拌来,从这里他们源源不断地把浓厚的哲学菜汤喂养着神学。于是,本来已经衰萎下去的神学,很快就以更加强壮的姿态出现了。一切可能的神学教条,都被贴上实践理性公设的标签,并且没完没了地做着上帝存在的神学历史证明。图宾根式的实践理性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4 〕谢林的这种态度不可能不对黑格尔产生影响。当然,黑格尔主要是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过程中达到反道德主义的结论的。在这里,希腊情感主义的形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批判武器,但是对康德道德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单纯地退回情感主义,而是出现了新的内容,即辩证思想的萌芽。邓晓芒先生指出:“事实上,在黑格尔摆脱康德的影响而实现其思想中的‘重大转折’的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首先就是以批判康德的伦理学、提出人的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和这种分裂的重新统一问题、提出‘生命’和‘爱’的概念为标志的。”〔5〕在这里,爱、 生命等等范畴虽然仍被黑格尔看作精神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它们已经开始向形式方面转化,而它们所包含的命运(生命的分裂与重新和解)、对立统一则成为精神的真正内容。
当黑格尔提出爱来扬弃道德时,他已经开始自觉地把矛盾、对立统一当作生活和思维的基本原则来对待,而不是像康德那样把矛盾仅仅看作理性的谬误。在爱中,法规与嗜好、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概念与具体存在之间的对立被扬弃了,从而实现了命运的和解。普遍的理性、道德命令、概念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或理想状态,是空洞的抽象,与这些抽象范围相对立的是特殊的和具体的存在、嗜好等等,而爱的和解作为一个辩证的结果,是对上述矛盾的扬弃,是对立面的统一。虽然爱仍然被限制在主观性之中,尚未提升到客观概念和精神的高度,而且爱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第三者,以一种外在性的方式把法规和嗜好统一在一起,但是在这里已经包含着明显的辩证思想。
爱的和解不仅超越了外在强制性的律法,而且也超越了内在强制性的道德命令。爱是比道德更高的层次,它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和原则,勿宁说,它就是一种真正的道德。黑格尔写道:“如果爱不是道德的唯一原则的话,那末每一种道德就同时是一种不道德。与完全奴役于一个异己的主子的法规相反对,耶稣所提出来代替的并不是一个部分地奴役于自己的规则、并不是康德式的自我强制的道德,而乃是没有统治、没有屈从的道德,即作为爱的特殊样态的道德。”〔6〕如果说(康德式的)道德曾经作为对律法的一种补充和扬弃,那么爱则是对道德的补充和扬弃。在爱中,道德的一切片面性和限制都被扬弃了。爱并非只是像道德命令或义务那样克服了敌对的一方,而是从根本上克服了敌对性本身。康德的道德命令以普遍性的思想(“应当”)与特殊性的现实(“存在”)之间的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制为前提和内容,黑格尔的爱则表现了精神的统一性,它扬弃了思想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对立,作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解的道德呈现出来。爱与(康德式的)道德的差异不再像道德与律法的差异那样,仅仅只是两种不同的片面性之间的差异,而是片面性与全体之间的差异、分离与分离之和解之间的差异。在这里,黑格尔决不仅仅只是用情感主义扬弃了康德的道德主义,而且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以思辨理性(虽然仍旧采取了情感和直观的形式而尚未达到概念思维的高度)扬弃了知性的反思,以辩证的统一扬弃了形而上学的对立。而这一点才是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神学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法兰克福时期的神秘性”——对于该时期的这种“神秘性”,狄尔泰和卢卡奇等人都曾强调过——的真正内容。
二、宗教扬弃爱与“苦恼意识”
在爱的和解中,精神超越了道德命令的片面性而达到了全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全体仍然是一种片面性,即主观的片面性,因为它始终局限于爱、局限于情感的范围之内。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已经意识到爱的片面性并且试图超越这种片面性,然而他却由于对康德的理性(普遍性的抽象理性或知性)的拒斥而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而且令他自己信服)的最高统一物。宋祖良先生指出:“康德在理性与嗜好、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主体与客体之间处处造成割裂。黑格尔认为,这些对立的概念被绝对地割裂开来。是单纯反思的产物,因此,他故意避免使用通用的一些概念,以求跟康德划清界限。”〔7〕虽然黑格尔试图把这个最高统一物说成是宗教, 并且提出了宗教是“反思和爱在思想中的统一、结合”这个公式,但是这宗教本身却由于缺乏概念的规定性而流入神秘,成为直观的对象;这种统一也由于缺乏体系而成为一种偶然性的“特殊心情”,仍然未能真正扬弃主观性。”〔8〕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苦恼意识”, 即由于不能在主观性的爱与客观性的反思之间实现真正统一而产生的苦恼。
被爱所扬弃的对立不过是一种主观范围内的对立,即普遍的主观性(理性的道德命令)与特殊的主观性(嗜好)之间的对立。当爱克服了道德的局限而达到了统一时,它并没有克服主观性的局限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因此它同样面临着被反思和客观性再度扬弃的可能性。黑格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克服爱的这种主观片面性,他提出了宗教作为更高的统一体。黑格尔说:“爱扬弃了道德范围的限制;不过爱本身仍然是不完善的本性。在幸福的爱各个瞬间里没有客观性存在的余地。但是每一个反思都扬弃了爱,又恢复了客观性,有了客观性又开始了有局限性的事物的领域。因此宗教就是爱的完成(它是反思和爱在思想中的统一、结合)。”〔9〕在另一部手稿中,他把道德、 爱和宗教作为三个不同的层次,认为“信念扬弃权威性、命令的客观性,爱扬弃信念的界限,宗教扬弃爱的界限。”〔10〕那么宗教这种更高的统一体在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那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事实上,由于拒绝从理性和概念本身来说明这种更高的统一,由于拒绝反思哲学而导致了拒绝哲学和思维本身〔11〕,黑格尔只能把宗教看作主观情感和想象力的对象化,只能把神说成爱的实体化或客观化——“爱为想象力加以实体化,就是神”(这个思想倒是与费尔巴哈的宗教观颇为接近)。因此神虽然被勉强地披上了一件客观性的外套,然而它却仍然缺乏本质的或客观的规定性,它的内容仍然只是主观的情感,是有限生命对于自己所设定的自身之外的无限生命的崇拜。“如果人把无限的生命设定为全体的精神,并同时设定为在他外面的有生命之物(因为他本人是有限制的),并且当他要提高其自身以达到这有生命之物并同它有最亲密结合时,同时又设定他自己自身为在他外面(即在他这有限制者外面),那么他就在崇拜上帝。”〔12〕
与后来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和宗教哲学的客观性路线相反,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完全是从主观性方面来定义宗教和神的。由于神只不过是爱的实体化,宗教只不过是“情感和情感对于对象的要求”的统一,所以对于神的认识就只能在纯粹主观性的方式即直观或信仰中进行。黑格尔说:“耶稣的本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关系只有从信仰着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能直观者与被直观者的对立,亦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在直观本身中消逝了。”〔13〕宗教是有限生命提高到无限生命时所达到的精神统一,这种最高形态的统一是超出思维的,因为思维是以对立为前提的,只有在直观和信仰中才能超越对立达到统一。因此,宗教就成为超哲学的,成为对思维本身的扬弃。在《1800年体系残篇》中,黑格尔写道:“有生命之物的这种部分(片面性)存在在宗教中得到扬弃,有局限的生命被提高到无限……正由于这样,哲学必须停止在宗教前面,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因而一方面以非思维为它的对立物,一方面又有能思维者与被思维者的对立。”〔14〕这种观点与成熟的黑格尔体系中关于宗教必须停止在哲学面前、直观和表象必须上升为思维和概念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它表明了神秘主义成分在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的优势地位。正是由于这种直观高于思维的观点,使得狄尔泰认为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陷入了神秘的泛神论,使得卢卡奇认为青年黑格尔的“生命”概念不仅在形式上“由于没有解释说明而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内容上也充满了神秘气息。”〔15〕
然而,也正是这种神秘主义的因素使黑格尔摆脱了康德的道德主义和一般知性反思的抽象对立原则,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胚芽。神秘主义固然仍是一种片面性,即直接知识的片面性,但是它却是克服知性片面性,即间接知识的片面性的最便利快捷的手段。在神秘主义的直观中,反思所造成的主客观对立消失在绝对的主观统一之中。如果说知性的反思造成了形而上学的分离,那么神秘的直观则孕育着辩证的统一。但是神秘主义只有当其扬弃了直观和直接知识的片面性而上升到概念、理念、思维和精神的高度才能成为思辨哲学,神秘主义的旺盛生机只有当其与逻辑的规定性相结合后才能发展为活生生的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就是那种神秘的“生命”、“爱”和“努斯”精神,然而它还必须为自己获得概念的体系和“逻各斯”的形式,否则它就是一种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本质,这种缺乏规定性的本质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和虚无。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尚未为“生命”和“爱”寻找到概念体系,精神、神还缺乏规定性。但是黑格尔并不像德国神秘主义者们那样陶醉于这种无规定性的精神本质中,而是孜孜不倦地试图建立体系,寻找规定性,从纯粹的主观性藩篱中摆脱出来,真正达到主客观的统一。他已经意识到客观性的重要意义,然而他却由于拒斥概念和思维而寻找不到实现主客观统一的中介。正是这种试图走出主观的“生命”和“爱”然而却又达不到客观理念和全体性的真理的迷惘、焦虑、困惑,正是这种“苦恼意识”〔16〕,导致了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在“精神上几乎陷于瘫痪”的思想危机,成为他的“本质上的一个昏暗的收缩点”。
三、辩证法的诞生地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
尽管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受到那种尚未被反思到的“苦恼意识”的困扰,只能把主客观的统一局限于神秘的直观,而未能提高到概念和思维的水平,但是,他却通过精神或生命的“原始合一”、“分离”和“发展了的重新合一”的三段式运动表达了精神的自否定特点,并且已经开始意识到真理就是过程和全体、就是被“理解了的生命”。他说:“无限与有限的结合当然是一种圣洁的神秘,因为这个结合就是生命本身。那分裂生命的反思作用可以把生命区别为无限的生命和有限的生命,并且只是就限制、有限事物本身来看,才得出与神相对立的人的概念;在反思作用之外,就真理本身来说,是没有那种限制的。”“精神的关系……把原始的合一、变形(分离)和发展了的重新合而为一在生命和精神里(不是在概念里)联系起来了。”〔17〕在这个时期的另一些手稿中他又写道:“生命必须从这种未经发展的合一出发,经过曲折的圆圈式的教养,以达到一种完满的合一。”“这个萌芽从原始的统一性分化出来,越来越走向对立,并开始发展。它的发展的每一阶段就是一种分离,其目的在于重新获得生命自身的全部财富。由此足见其发展过程是这样的:统一、分离、重新结合。”〔18〕在这里,对立统一已经不再是静态的和平面式的,即通过一个绝对的第三者从外面来调和矛盾,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精神或生命的自否定运动。对立和统一对于生产来说已不再是外在的东西,而上它自身发展的历程,是它自己的真理。在这里黑格尔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曲折的圆圈式的”运动的思想,并且确立了精神发展的三段式模式。生命的原始合一由于反思的分离作用而获得了规定性,而精神的活动则是对规定性的一种无限的扬弃。规定和规定的扬弃表现了精神或生命的自我否定特点,而这种无限的扬弃过程同时也就是精神向自身的无限的返回,唯有通过这种自我否定,精神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因此它同样也表现了精神或生命的自我肯定特点。在这种同时既是自我否定又是自我肯定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完成了对变形、分离、对立的重新合一,达到了全体和真理。
在法兰克福时期,这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尚未以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而是以表象的形式表现在刚刚萌芽的思辨三位一体的神学思想中。圣父被看作那原始的合一;圣子被看作圣父的“一种变形”,他“作为变形,作为一种有限制的东西,就能产生(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对立,并能够把普遍东西与特殊东西分离开。”〔19〕圣灵则是对圣子的否定,唯有通过圣子之死圣灵才能活。圣子渴望着死亡,渴望着对分离、对立的扬弃。在复活的耶稣里,生与死、神与人之间的对立最终被扬弃了,一切分离物都在精神(圣灵,Spirit)中实现了真正的统一,“精神(圣灵)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在这种以圣父、圣子、圣灵的表象形式所表述的辩证法中,已经包含着黑格尔后来在《宗教哲学讲座》中关于精神发展的思辨三位一体思想(即精神在“圣父的王国”、“圣子的王国”和“圣灵的王国”的表象形式中的辩证发展)的雏形。
关于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的思想转折,最后还须提及一笔的是他对启蒙思想的批判。黑格尔在1800年9月对伯尔尼时期的《基督教的权威性》一文所写的修改稿中,明显地突出了批判肤浅的启蒙理性这一主题。在修改稿中,黑格尔批判的重点已不再是权威性的基督教(天主教),而是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然宗教与权威宗教之间所设置的知性对立。针对启蒙思想家们把这种对立绝对化的做法,黑格尔认为,二者的对立只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一种看起来是权威性的宗教就其“符合它那个时代的自然状态”而言,同时也是“自然的”。判别自然宗教与权威宗教的标准不应该是抽象的人性,而应该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意识。任何一种宗教教义,对于不自觉的人性意识来说,是自然的;而对于被唤醒的理性来说,则是权威的,权威性不过是理性对教义的反思。因此问题不在于教义的内容,而在于这些内容所表现的具体形式。黑格尔明确地指出:“关于一个宗教是否权威的一问题,取决于它的教义和命令的内容较少,而较多取决于它证明它的教义的真理性和要求实践它的命令的形式。每一种教义、每一个命令都可以成为权威的,因为每一种教义或命令都可以压制自由的强迫方式表达出来;没有一个教义不是在一定情况下有其一定的真理性,没有一个命令不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成为义务,因为即使一般被当作最真纯的真理,为了它的普遍性,在应用于各特殊情况时,也需要有一定的限制,这就是说,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准的无条件的真理。”〔20〕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关于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说明,而且也可以看到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这一重要思想。
国内黑格尔学界一般都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把耶拿时期的《精神现象学》看作“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所谓“真正起源”是指“精神现象学已经包含着后来黑格尔全部哲学的雏形、萌芽和主要的观念,也就是说,黑格尔以后著作都是精神现象学某些思想的发挥、发展,都可以在精神现象学中找到它们的源头”,而所谓“秘密”则是“指其异化原理和否定性的辩证法”〔21〕。然而对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变化进行细致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哲学在《精神现象学》之前尚有其更为隐蔽的起源和秘密,这个更为隐蔽的起源和秘密只能从《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1800年体系残篇》等手稿中去发掘。当马克思把《精神现象学》说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时,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的神学手稿尚未被公诸于世,因此马克思就不可能提出进一步追溯其“真正起源和秘密”的任务了。然而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我认为,黑格尔哲学(包括他的辩证法)的真正诞生地应当是黑格尔神学(尽管它的成熟形态不是在神学中)。在黑格尔那里,宗教与哲学虽然存在着认识形式和表述方式上的差异,然而它们的内容却是同一的,即都是那个以辩证的方式发展运动和自我认识着的绝对理念或精神〔22〕。而这个内容最初是在法兰克福时期的神学手稿中崭露头角的,虽然它在那时还没有上升为概念,而是仅仅表现为意蕴朦胧的“生命”和“精神”。《精神现象学》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例如关于辩证的否定(自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异化、扬弃、对立统一、精神发展的圆圈式运动、真理是全体和过程、真理是具体的等等,都可以在法兰克福时期的神学手稿中找到思想原型。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的着眼点是要从黑格尔个人思想发展的全历程来研究其最终成熟的哲学思想的原始萌芽和秘密,那么就必须进一步追溯到法兰克福时期的神学思想;如果我们的着眼点仅仅是在哲学(概念的或思维的认识)的范围内来研究黑格尔最终成熟的哲学思想的起源和秘密,那就确实应到《精神现象学》中去寻找。然而,这两个着眼点并不是平行的,因为如果我们把《精神现象学》看作是一个发展的结果(辩证法要求我们这样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它的真正起源和秘密必须且只能进一步追溯到黑格尔的神学思想、追溯到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所表现的那些神秘主义范畴中。在人类思维发展的过程中,神话、宗教是先于哲学的,后者则来源于(当然是辩证地)前者。就此而论,黑格尔个人思想的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缩影”。
注释:
〔1〕关于这种痛苦的疑病状态和精神危机,黑格在1810 年的一封信中回忆道:“这种疑病状态,我遭受了好几年,以至精神上几乎陷于瘫痪。一般地可以说,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的本质上的一个昏暗的收缩点;他要通过这一关,才能达到安全境地,从而确信他自己,确信普通的日常生活,而如果他已经没有能力以日常生活来充实自己,则通过这一关才能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存。”类似的表白还有许多,参阅卢奇卡:《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3—96页。
〔2〕《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8页。
〔3 〕这一段具有显著的反道德主义色彩的语言后来被黑格尔本人从《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删除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对“理性的冷酷的命令”的犹豫态度。
〔4〕《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 —34页。
〔5〕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6〕《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1页。
〔7〕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8〕黑格尔后来在《小逻辑》中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 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9〕《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350 —351页。
〔10〕〔12〕〔13〕〔14〕〔17〕〔18〕〔19〕〔20〕参见《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附录,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6页,第403页,第362、366页,第404页,第358、370页,第443、446页,第359页,第169页。
〔11〕“当黑格尔在法兰克福从事新的理论探讨时,流行的哲学都渗透着反思的分离作用。为了跟反思哲学划清界限,他故意不提‘哲学’这个词。”(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15〕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8页。
〔16〕“苦恼的意识就是那意识到自身是二元化的、分裂的、仅仅是矛盾着的东西。”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0页。
〔2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 贺麟等译,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译者导言,第30页。
〔22〕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后来的许多著作(《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精神哲学》和《宗教哲学讲座》等等)中都反复强调。
标签:哲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精神现象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耶稣传论文; 小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