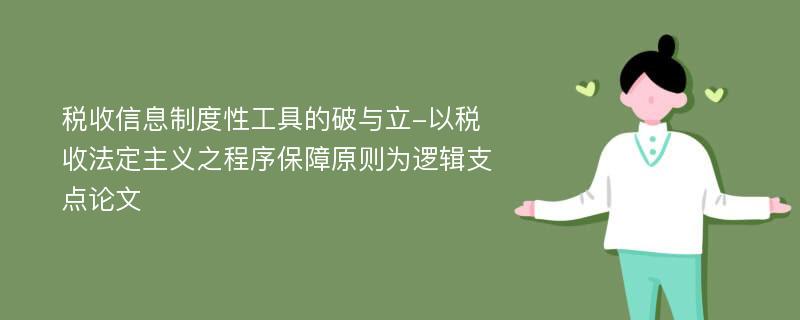
资政专栏
税收信息制度性工具的破与立
——以税收法定主义之程序保障原则为逻辑支点
张 怡,吕俊山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 要 :我国税务机关规定的税收筹划报告制度,因为缺少上位法依据且与《立法法》冲突而存在合法性瑕疵。不管税收筹划是否可能过于激进而容易出现避税、逃税的情形,税务机关都应当遵循税收法定主义之程序保障原则,不应当加重纳税人的程序性负担或者非法获得税收筹划信息,因此,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不能成为我国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的制度性工具。目前,发票是我国税务机关获取法定税收信息的主要法律工具,区块链发票为发票记载信息的增加提供了技术空间。如果通过立法改变发票的记载内容,信息博弈的格局将随之改变。事先裁定制度将为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提供不同于税务免费咨询的新路径,但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保障原则表明,事先裁定制度不应当成为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的制度性工具。
关键词 :税收筹划;程序保障原则;避税;区块链发票;事先裁定
作为获取税收信息的工具,我国税务机关要求税收筹划方定期报告和及时报告的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主要由《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3号,以下简称13号文)所确定并于2017年9月1日起实施。但是,该税收筹划报告制度因为缺乏上位法依据和为纳税人创设义务而存在合法性瑕疵,在实践中也面临识别困难、信息不真实等困境。新兴的区块链发票为发票增加信息量提供了技术空间,但是,受到税收法定主义之程序保障原则的限制,不论发票制度如何变迁,都不应当脱离纳税人意愿而成为满足税务机关单方意愿的税收信息博弈工具。尚未完成建构的事先裁定制度,不以满足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为目的,因此不能成为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的制度性工具。
一 、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立法困境
我国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雏形,是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在《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以下简称7号文)中有关税收筹划方提供材料的规定。7号文是现已全文废止的698号文的配套文件[注] 为了行文方便,《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在本文中简称698号文。 ,698号文是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杭州儿童投资主基金案”再审裁定实际依据的重要法律文件[注]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867号《行政裁定书》。 。7号文作为698号文的配套性文件,增加了税收筹划的报告义务[注] 在主文件698号文已经被废止的情况下,7号文没有被同时废止。 。13号文比7号文更进一步,将报告范围从所得税领域扩展到全部税收筹划领域,对税收筹划方规定了全面的信息报告义务而且规定了一系列罚则。
(一)法律依据和法律规定的不合法性
我国的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以7号文为雏形、以13号文为主体,但这两份法律文件都属于税收规范性文件,位阶较低,必须从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找到法律依据,不能突破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限制,否则即可能不具有合法性。7号文设定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法律依据”,据称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43条第2款、《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4条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7条[注] 7号文在首部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下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据此可以推断,其依据应当包括:(1)《企业所得税法》第43条第2款的规定,即“税务机关在进行关联业务调查时,企业及其关联方,以及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提供相关资料。”(2)《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4条对上述第43条中“相关资料”进行解释时采用的兜底条款,即“其他与关联业务往来有关的资料”。(3)《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7条的规定,即“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 。
如果把税收筹划方认定为《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关联方”,那么税务机关能且只能在“进行关联业务调查时”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料”[注] 参见:《企业所得税法》第43条第2款;《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4条。 。如果把税收筹划方认定为《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有关单位”,则税务机关同样能且只能在“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要求其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因此,7号文为离岸并购相关事务的税收筹划方提出的报告要求,依法只能在税务机关启动相关调查或者检查程序之后进行。换言之,税务机关不能要求税收筹划方提供材料以作为启动调查程序或者检查程序的前置程序。由此可见,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税务机关是否已经启动税务调查或者检查程序,是其要求税收筹划方报告信息合法性判断的界碑。既然税务机关无权要求税收筹划方在税务机关启动具体案件调查或者检查程序之前向税务机关提供税收筹划服务相关信息,当然更无权自行建立要求税收筹划方定期或者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税收筹划材料的制度。
13号文作为税收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依据方面更显不足:其法律依据据称包括《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务院有关决定”[注] 参见:13号文首部的规定。 。如上文所述,《税收征收管理法》并没有授权税务机关在“依法进行税务检查”这个特定时段之外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的规定;“国务院有关决定”语焉不详,无从查证[注]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于2017年5月发布了该公告的解读,说明是“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要求”,而没有提及其他“国务院有关决定”。《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有“依法治税”原则,涉及采集国土资源部门等第三方信息,但是没有关于涉税机构定期报送有关信息的规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确实存在“国务院有关决定”,那么这些决定不可能是行政法规,因为如果这些决定是行政法规,13号文在已经列举出《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情况下不至于不对此明确列举。因此,13号文规定的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不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没有上位法作为法律依据,可能不具有合法性。
除了缺乏上位法依据之外,13号文的具体规定也因为与《立法法》的规定相抵触而可能不具有合法性。具体而言,13号文要求税收筹划方“应当在完成业务的次月向税务机关单独报送相关业务信息”,将税收筹划业务和其他涉税服务绑定,采用暂停或者不予受理“所代理的涉税业务”等措施,都属于《立法法》第80条规定的“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降低信用等级或纳入信用记录”“纳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予以公告并向社会信用平台推送”等手段也都为《立法法》第80条关于“增加本部门的权力”的规范所禁止。根据《立法法》第80条的规定,即使作为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规章也不得在“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如此规定,更何况是低于税务规章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作为文件制定者,国家税务总局应当很明白该制度可能具有的非法性,因为其颁布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第4条就明确规定:“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的规定可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必须经过国家税务总局内部的专业“合法性审查”。税收筹划报告制度规定的出台,至少证明国家税务总局缺乏应有的谨慎。正如“在一个司机没有责任的法律制度中,司机几乎没有激励来保持谨慎。”[1]诚然,国家税务总局为自己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不谨慎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尚未出现。
对于非税务专业人士而言,我国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不合法性,尚未达到我国《电子商务法》中认定知识产权网络侵权责任所采用的“红旗标准”——不合法性如同“一面鲜亮的红色旗子”公然地飘扬[2]。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不合法性的隐蔽性,一方面源自普通纳税人对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源自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遵循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就可以免责的现实规则,这种规则导致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毫无动力去纠正上级文件的错误。
(二)违反程序保障原则的行政权扩张
避税和逃税的区别尽管有“一面监狱围墙之隔”[17],但是,在有些案件中,避税和逃税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如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广州德发案”[注] 参见:滕娟.专家: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设立专门税收法庭[N].财会信报,2017-07-03(A06). 。
我国税法中的“管理”理念,是我国税收程序法的核心理念。与法国《税收程序法》、日本《国税征收法》不同,我国规范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款征收程序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其名称突出“管理”一词[4]。相应地,管理的理念也完整贯彻到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乃至税款征收实践之中。虽然我国税务机关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系列部署,近年来专门发文强调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和优化纳税服务[注] 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税总发[2017]101号)。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为纳税人服务有时会被嘲笑为“幼稚”。例如,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问卷调查,在实践中被异化为“强制性”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过程演变为税务机关恶化征纳关系的过程,也蜕变成为13号文出台前的“吹风”和“通气”;更显得戏剧化的是,经过了被异化的“问卷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因为符合实证研究方法的形式要求,被理所当然地认为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与税收法定主义之程序保障原则的严重缺位相伴而生的是行政权力扩张。税收法定主义是现代各国普遍遵循的税法原则,是税法的“帝王原则”[5]。“现代法治中的依法行政、法律保留、法律优位等原则,莫不是源自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税收法定主义“是推动近代法治的先驱”[6]。基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分析可知,即使消除问卷调查的瑕疵,国家税务总局扩张行政权力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以防范税务行政机关扩张行政权力为宗旨的税收法定主义,必须对包括税收程序法在内的税法重要事项进行法律保留且严格限制对行政机关的授权。换言之,税收法定主义的宗旨决定着税法必须对行政权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并通过程序上的隔离实现限制行政权不受法律约束而任意扩张的目的。
虽然我们对抑郁症发生的机制不甚了解,但却发展出了一些有效的抑郁治疗方式,如第一代抗抑郁药物——三环类药物和单胺类氧化酶抑制剂,以氟西汀为代表的第二代抗抑郁药物,还有一些非典型抗抑郁药物。另外,氯胺酮快速抗抑郁效果的发现,也提供了具有潜力的研发方向。另一方面,非药物治疗,如心理疗法,电休克治疗,对抑郁症也有一定的疗效。
然而,我国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以及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政立法,已经在数量上和实践中成为我国税法体系的主体,诸如“增值税法”等本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常常徒有阵痛而迟迟不能诞生,或者如同最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一样,即使有重大修订也因为对行政机关的授权条款而成为“无腿的税法”[注] 2018年8月31日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法》第22条规定“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是“实施条例”不出台,多项扣除标准无法确定即属此例。 。我们或许可以接受的是,因为税法的复杂性和现实生活对税法的快速适应导致税法适用困难,税法的实施需要行政法规、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等下级法律文件对其进行充实以增强其适用性。但是值得正视的问题在于,过分依仗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痼疾正在瓦解立法机关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追求。一部税法必须由一部行政法规“配套”并由数量不加限制的税务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进一步配套的“1+1+n”模式或者在没有税法情况下直接制定行政法规的“0+1+n”模式应当改变,至少应当基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而限制行政法规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整体数量,以从源头上尽可能消除税法的不可预见性并减少下位法僭越上位法的概率。
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角度分析,集体失语是平庸之恶的表象,税收筹划报告制度可以认为是一种由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平庸之恶”造成的结果。历史上为平庸之恶的辩护核心是,该等行为只是职务行为,行为人只是整个恶行的一个“零件”,因此行为人本身不应当对职务行为承担个人责任。这里隐含的假设,是这些身处制度之中的人仍然应当对制度化的恶行有正常的判断[9]。平庸之恶是以自欺欺人为特征的“罪行”或者过错[注] 这里所说的国家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庸之恶”,一般是指这些工作人员不假思索地按照错误规定或者上级错误指示违反法律、侵犯纳税人利益的过错。 。因此可以看到,这些人处于“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状态,“能毫无困难地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规矩”[9]163。在税收筹划制度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中,看不到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为了保护纳税人权利而提出异议和为了保护纳税人权利而付出有效努力,反而可以看到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不假思索地推行税收筹划报告制度,因此可以说,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出台,离不开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作为一个个有能力选择却放任其侵犯纳税人权利的“平庸之恶”。反过来说,如果通过立法使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保障原则得以落实,这里的“平庸之恶”就将无所依附而成为无本之木。
限制行政权力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利,是税收法定主义产生的实践原因和历史起点,而税收法定主义中的税收构成要件法定原则、税收构成要件明确原则与合法性原则从三个方面强调行政权在实体领域不得扩张和滥用从而实现对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保障。相对于财产权利这种实体权利而言,纳税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也不容忽视,否则程序性负担也能成为纳税人不应承受和无法承受之重。程序保障原则要求对纳税人的程序性权利提供法定保障以免受行政权力侵害,在纳税程序和纳税人争议程序两个方面强调行政权在程序领域不得扩张和滥用。从一个角度看,税收法定主义从历史上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利的初衷出发[注] 从税收法定主义发轫到税收法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确立,再到之后税收法定主义在西方各国宪法中的确立,都关乎“最重要的事务——财产”。(参见:刘剑文,侯卓,耿颖,陈立诚.财税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0-92.) ,发展为从财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两大领域保障纳税人权利,并因此实现对纳税人作为整体的全方位权利保护,无疑实现了历史的上升。从另一个角度看,税收法定主义从保护纳税人权利、限制行政权力扩张的宗旨出发,通过四项细分的原则,从正面保护纳税人的财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并从反面限制行政机关侵害纳税人财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完整实现税收法定主义的宗旨,实现了逻辑的自洽。
然而,我国纳税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仍不到位,税务行政机关以保护国家税收利益为名随意增加纳税人程序性负担、侵害纳税人程序权利的情形时有发生,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出台即为典型例证。值得警惕的,还有国家税务总局扩张行政权力的过程中,税务机关内部审查程序“整体失灵”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集体失语”。
税收法定主义包括税收要件法定原则、税收要件明确原则、合法性原则以及程序保障原则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的程序保障原则,包括税收程序法定和纳税人权利救济程序法定两方面内容[7]。税收法定主义细化为四个原则,使税收法定主义理论实现了历史的上升,并形成了逻辑的自洽。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程序保障原则可知,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性义务,也表示其同时有权拒绝履行法定义务之外的程序性义务和以程序义务为借口的各种其他义务。从经济负担角度考察,程序性义务的加重必然增加纳税人的时间成本,或者剥夺本应属于纳税人的闲暇。闲暇则是一种“正常商品”,如填写各种纳税申报表格花费的时间和正常商品的消耗一样,是一种税收遵从成本[8]。对于纳税人而言,确定了法定程序性义务之后,面对行政权力的制度性扩张和非制度性滥用,纳税人就可以区分法定义务和非法定义务。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10]。假设存在可以接受政府通过税法提供的激励,“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没有完全利用这些唾手可得的机会,那他就是一个傻瓜。”[11]我国和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税收征管难题,但是发达国家税务机关早已认识到把纳税人看作“客户”的必要性,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瑞典、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税务机关早就开始重构管理措施,将纳税人视为“顾客”,满足其需求[12]。追本溯源,只有遵循税收法定主义之程序保障原则,为纳税人提供纳税程序保障,禁止增加纳税人程序性负担,税务机关才能把纳税人作为“客户”对待。
从税收筹划服务的市场属性分析,如果中介机构不能通过调整交易方案为委托人减轻税负,则客观上等于没有提供有效的税收筹划服务。
假设抛开上文所述及的违反税收法定主义之程序保障原则和行政权不当扩张以及相关的平庸之恶等问题,可以看到,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作为税务机关获得税收筹划信息的制度性工具或许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我国目前实施的税收筹划报告制度针对的是从事税收筹划的中介机构,而非不加区分地强制所有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报告税务筹划的内容;税收筹划报告制度没有限制纳税人通过合法改变交易架构而减轻税负的权利,也没有增加税收筹划方之外纳税人的制度性负担;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重点在于获得税收筹划信息以帮助税务机关尽早识别避税和逃税行为。不过,即便如此,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仍将面临实践的困境。
价格是影响进口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进口的价格上涨,进口量会相对应地减少;反之,进口的价格降低,进口量也会相对应地增加。对于婴幼儿配方乳粉而言,其进口价格体现为以美元表示的平均进口价格和汇率两个方面。尽管从以美元表示的进口平均价格来看,近年来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进口价格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是200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呈现的升值趋势,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价格竞争力。
二 、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实践困境
税收筹划费用被其他服务合同费用吸收,该费用没有减少,而且税率一般也不会改变,客观上不会减少纳税额。但是,将税收筹划合同与其他服务合同合并且不显示税收筹划服务内容,就掩盖了税收筹划服务与其费用的对应性,可能涉嫌违法,因为《发票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的虚开发票行为包括“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注] 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37条的规定,其法律责任是“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发票的法律规定对于“实际经营业务”尚未具体化,如果认为税收筹划也属于税务服务的一种,则不在发票上记载“税收筹划服务”而只记载“纳税服务”“税收咨询服务”“税务服务”“法律服务”也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如此,则合同与费用均不显示税收筹划的做法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
(一)节税、避税和逃税的识别困境
税收筹划无不以减轻税负或者规避纳税为目的[注] 13号文中的“税收策划”指的是“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经营和投资活动提供符合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纳税计划、纳税方案”。可见,其“税收策划”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税收筹划,即实践中税收筹划中的“节税”。果然如此,则税务机关根本不必掌握这些税收筹划信息,因为13号文创设的目的主要是尽早识别出避税和逃税的情形。 。从形式和实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角度,税收筹划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注] 实质标准和目的标准是区分避税与节税的两种标准,二者的关系争议颇多。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确立的标准是目的标准,但是在其他反避税法律文件中也有实质标准。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也是目的标准:“纳税义务人出于降低应纳税额之考量,恒常以各种经济上或法律上之方法,迂迴曲折地使特定交易关系不至于合致税捐构成要件,其中合乎税法立法之本旨者,乃税法秩序所容许之合法行为,谓之为节税,至若对于交易活动之内容未有隐瞒,仅系透过私法上所被赋予之选择权利或形成空间,做出不合税法目的之选择,以规避原本可能发生之税捐负担,此即学理上所称之租税规避,亦称避税,乃法外之投机行为,界乎于合法与违法之间。而纳税义务人故意隐藏其经济活动之利益或故意增加其交易成本之负担,以图达到减轻税捐负担目的之行为,则为逃漏税捐。”(参见:我国台湾地区2012年度台上字第5633号裁判书全文。) :第一种,形式和实质都符合法律规定,是为节税;第二种,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但是缺乏对应的经济实质,是为避税;第三种,形式和实质都不符合法律规定,是为逃税[注] 根据数学排列组合的规律,应当还有第四种形式:形式不合法而实质合法。但是,这种类型极其拙劣,已经不能被称为“税收筹划”了。 。
将税收筹划的性质划分为节税、避税和逃税并进行区分的意义,在于不同种类税收筹划的法律后果不同。逃税是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对应的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逃税罪的最高刑期是7年有期徒刑[注] 我国《刑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避税虽然不构成犯罪,也因其损害国家税收利益,“打击避税”在我国已成趋势[注] 参见:经合组织提交一揽子计划打击跨国企业避税行为[EB/OL].(2015-10-01)[2018-08-17].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510/20151001148286.shtml. 。税务机关重点关注的税收筹划也正是避税和逃税这两种激进的税收筹划。从《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一般反避税条款开始,我国已经建立比较系统的反避税法律体系。虽然我国构成反避税法律体系的法律文件具体位阶尚可争议,但是人民法院通过裁判表现出的支持税法和税收政策的鲜明态度弥补了反避税法律体系的不足。以“杭州儿童投资主基金案”为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支持税务机关依照我国反避税法律和政策作出的征税决定[注]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867号《行政裁定书》。 。
如图所示,在服务供应链领域,有72个国家/地区学者发表了相关成果,发文量超过100篇的国家为中国和美国,其中我国学者共发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207篇,2个国家累计发文量总占比56.58%,反映出该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区域的分布呈现典型的集中分散态势。其中,2008—2017年间,中国学者在SCI、SSCI与A&HCI三大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中发表的有关领域的文献数量为全球第一,表明了我国学者对服务供应链领域的关注程度与科研实力。
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审视,不论是逃税还是避税,都是让税法规定落空从而损害纳税人之间应有的公平,而税收公平主义是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7]83-92。税收筹划应当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基本要求,即把税收筹划的目标控制在“节税”范围之内,严格禁止进行“逃税”的税收筹划。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中介机构为纳税人提供“逃税”筹划方案,其行为涉嫌教唆犯罪[注] 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
税收筹划是否可以为法律所接受的界限很难划定[13]。例如,节税具有显著的合法性特征,将工资的一部分改为不征税的补贴发放,结果是工资总额减少、税负降低而职工实际利益增加,就是典型的节税方法[14]。但是,有些节税案例和避税有着相同的特征。在税收历史上,荷兰人减少甲板的宽度以减轻税负的做法,是足以被奉为经典的节税案例。在荷兰人的筹划中,税负减轻了,但是改造过的“大肚船”运载量并没有减少,因为“当时货船缴纳的税款取决于甲板的宽度”[15]。在“运载量”这种经济实质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甲板宽度”这种计税依据等法律形式而减轻税负,正是避税的精髓,但是本案例却因为技术局限而成为节税的经典。在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即排除“逃税”类型的前提下,如果通过税收筹划改变了经济实质从而减轻了税负,应当归类为节税;如果只改变形式就减轻了税负,则应当归类为避税。在“荷兰人甲板税收筹划案”中,当时的技术手段决定着税法无法不用甲板宽度去间接反映“运载量”这一经济实质,或者说,经济实质的改变与否因为技术原因导致税法无法通过甲板宽度以外的指标计量,因此除非改变税法的计税依据,否则“大肚船”一定会按照甲板宽度纳税。“荷兰人甲板税收筹划案”因此将税务机关置于尴尬的境地:虽然“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发生背离而导致国家税收利益遭受损失”,税务机关却无法“根据与经济事实相符的法律事实依法征税”[16]。这也正是本案的理论价值所在:若税收筹划方案达到了只有改变税法规定才能改变税收筹划结果的程度,即经济实质改变与否已经达到依照税法无法判别的地步[注]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甚至无法改变税法的规定,即无法通过弥补法律漏洞的方式解决问题,或者说该法律问题因为技术原因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 ,该税收筹划应当归类为节税。换言之,不同的经济实质没有不同的法律形式进行对应,导致“荷兰人甲板税收筹划案”中使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判断标准已经无法确定交易方案为避税。如果认定其为避税,则无法还原到未实施避税的状态,因此只能认定其为节税,判别节税和避税的困难由此案可见一斑。
美国存在对联邦所得税避税或者逃税投资交易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直接向美国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简称IRS)报告适格交易的制度[3]。但是,美国税法中的相关制度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的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缺乏法律依据且与上位法冲突,因此,我国的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与其说是我国仿效国外类似制度而制定的,毋宁说是税法体系内生的法律制度,是纳税人程序性权利弱化和税务机关管理理念强化而生成的制度。
对于需要可视化的学生数据,我们可以把可视化的类型分为数据关系的可视化和数据特征的可视化两种。而数据关系的可视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反映学生数据信息之间的关联性,比如说,每个学生每个月的支出的分类的占比情况;而所谓数据特征的可视化则是反映出一个数据的基本特征,比如说,一个学生每年绩点的变化情况。
立场不同是税务机关和涉税服务机构对同样的税收筹划安排的性质有着不同判断的重要原因:税务机关以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为己任,涉税服务机构以维护委托人合法利益为首要目标。本来就难以区分的节税、避税和逃税,在具体税收筹划安排中的定性因此变得更加富有争议。涉税服务机构不应当提供“逃税”的筹划,但是避税筹划以及对此进行保密和伪装很可能是涉税服务机构及其客户的积极追求,这种客观现实决定着税务机关不可能信赖涉税服务机构对税收筹划合法性的判断而应当进行独立判断。因此,税务机关希望获得税收筹划相关资料以进行独立判断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是如上文所述,其从税收筹划方获得税收筹划资料的做法因为不具有合法性而更容易强化税收筹划方的不合作态度。
(二)税收筹划假设信息的甄选困境
首先要允许内部控制人员对医院各经济业务环节进行调查了解,同时核实过后由其相关负责人进行尽快的问责,确保能够快速的找到问题所在并且解决问题;其次就是提升内部控制部门的权威性,要让医院了解到内部控制部门的重要性。
节税的交易方案,有些可能正好体现了税收政策的调整意图,比如在红筹上市过程中通过符合我国税收安全港规则的设计节税和适当增加科研投入获得税收优惠即属此类[注] 698号文明确规定离岸并购适用安全港规则,并为后来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所吸收。 。但是,经过税收筹划的交易,其形式更容易与经济实质相背离,因此,为客户提供避税方案乃至逃税方案的案例屡见不鲜。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税收筹划为例,有研究显示,德勤、毕马威和安永提供的税收筹划安排在法庭上获得支持的概率不超过50%,而普华永道的方案能够经得起法律考验的甚至只有25%,被认定为非法的可能性高达75%[18]。
纳税人很难对不能降低税负的税收筹划付费,因此,经过税收筹划的交易更值得税务机关关注,税务机关当然希望重点审查经过税收筹划的交易以提高筛选避税和逃税行为的效率。
MRS液体培养基,无菌条件下用浓度为1 mol/L的HCl来调整MRS培养基pH值,分别为3.0、3.2、3.4、3.6、3.8,然后将其分装于已灭菌的试管中,每个5 mL。其他步骤详见1.2.2。
对于税务机关而言,税收筹划合同与费用是发现和追踪税收筹划最直接的线索,因此我国税务机关根据13号文要求填报的国家税务总局监制的《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中包括“委托协议采集编号、协议金额、服务协议摘要”等信息[注]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没有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使用法律术语“合同”,而使用了“协议”,而且这里的“委托协议”和“服务协议”应当指的是同一法律文书。 。作为对策,为了不留下税收筹划的痕迹,税收筹划作为专项服务被其他服务吸收,就成为涉税服务机构对税收筹划服务进行更进一步筹划的内容。具体的做法是,在合同中提高另一项服务的价格而不显示税收筹划的相关服务内容。国外的研究表明,为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向企业提供税务服务和其他机构为企业提供税务服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各种机构为企业提供方案的作用也很难区分,税收筹划费用难以从通常的税务服务中区分出来。虽然可以假设稳定的税务服务费用之外的费用是税收筹划费用,相关证据却很难找到[19]。我国税收筹划方也有同样的做法。
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实践困境,首先是因为对税收筹划交易安排的合法性判断本身比较困难,其次是税收筹划作为服务类型可以被取代或者被掩盖,而且税务机关从税收筹划方获得的信息可能因为包含假设信息而丧失信息价值。
李离、袁安、上官星雨稍懂一点棋理。其时围棋风行天下,国手王积薪更是天下知闻。王积薪少年成名,集下名谱无数,其中最出名的,是为媪妇谱。据说王积薪青年时期云游天下,往来巴蜀道中,一夜投宿邮亭,清夜缘亭外小溪散步,上行十余里,听到溪上茅草屋里,婆媳两人联床夜话,下盲棋近百手,最后婆婆以九子胜出。王积薪只记下其中三十六手,怅然步月归,第二天早上再去沿溪找那间茅屋,溪流淙淙,朝暾洒满草林,茅屋却已不知所终。
实务中出现的上述对税收筹划费用和服务的再筹划,可能是实务界对13号文的应对措施。因为13号文关于税收筹划报告的规定突破上位法限制而可能不具有合法性,对于税收筹划方而言,不遵从其规定就很可能不会引起道德上的不安,对遵从还是不遵从的判断标准只剩下利益和法律风险。就法律风险而言,有人认为虚假申报的法律责任是法定的,所以没有人敢于虚假申报[3]46。但事实上,如上所述,税收筹划报告制度只是徒然强化了“警察与小偷”的对抗式博弈模式而减少了税法的“善法”色彩,从而可能使纳税人的实际不遵从成为常态和必然[注] “善税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不把纳税人当敌人、当仇人、当贼防。”(参见:李炜光.权力的边界:税、革命与改革[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53-54.) 。
美国通过立法规定对联邦所得税避税或者逃税的投资交易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应当直接向IRS报告这些适格交易[3]57。如果我们仿效美国的类似做法,使税收筹划报告制度合法化,那么税务机关基于税收筹划报告制度所获得的税收筹划材料,对于证明税收筹划方案涉及的纳税人可能存在的避税或者逃税行为而言,通常也不具有证据价值。因为在实践中,纳税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或者隐私,在向税收筹划方提供的资料中,经常掺杂假设的或者不真实的信息。税收筹划方的服务,只是根据客户提供的材料出具筹划方案,无权利也无义务辨别客户材料的真伪,因此税收筹划方根本不可能保证客户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这样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税务机关经由税收筹划报告制度获得的材料,仅仅具备有限的线索价值和参考价值[注] 即使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既为客户做审计业务又为客户进行税收筹划的情形中,通常也不能改变上述结论,因为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审计服务和税收筹划服务的团队通常并不相同。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团队同时做同一客户的审计和税收筹划两项业务,这两项业务对材料的要求不同,依据的材料也不相同,同样不能改变上述结论。 。
通过上述方法及太阳能系统的配置计算,得出常规安防系统、低功耗安防系统所需太阳能供电系统配置及耗电量对比情况,如表2所示。
清水砖:整体墙面砂灰抹面,涂料或者真石漆饰面,墙角采用灰色涂料或者真石漆做500高外饰面,墙脊挂灰色小青瓦;
退一步说,无论在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如何增加税务机关的信息量,对于税务机关而言,“应收尽收”和农业中的“颗粒归仓”一样,都是不可实现的目标,征税成本的增加和税款总量的增长之间客观上总有一个平衡点存在。就像没有必要凡事总要通过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来控制误差一样,立法机关和税务机关都必须现实地理解和接受税收误差水平。况且法律即使极度放任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程序性权利的侵犯,仍不能消除节税、避税和逃税之间难以定性的灰色地带,也不能通过税收筹划方获得交易的全部真实信息。税务机关反倒不如放弃“应收尽收”的税收追求,摒弃“警察与小偷”式的监管模式,依照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保障原则,把行政权力依法收缩到税法编织的“笼子”里,主动放弃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争取通过推动立法寻求获得税收信息的制度性工具。
三 、税收信息工具的法律建构
区块链发票的出现和事先裁定制度的设想,提供了在不实施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的条件下改变征纳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格局的法律空间[注]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税收信息报告制度、发票和事先裁定制度之外的其他税收信息工具进行评述。关于事先裁定制度,在2015年《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采用的名称是“预约裁定制度”。 。税收信息是征纳双方博弈的传统领域,税务机关对税收信息的获取是法定税收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信息工具一旦脱离法定税收程序,则可能失去合法存在的前提,沦为纯粹侵犯纳税人权利的工具,因此税收信息制度性工具的构建应当遵循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保障原则。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增加发票的信息范围提供可能性,但是无法改变发票的“法定”信息范围,相应的法律规则改变才是税收信息制度构建的根本。不言而喻,税收信息的范围正是发票制度、事先裁定制度等税收信息工具立法博弈的核心。
(一)区块链发票法定信息范围的博弈
2018年8月3日,我国第一张区块链发票诞生,标志着国家对发票的唯一性、不可篡改性和可追溯性等理想要求已经可能通过区块链技术得以在无纸化状态下实现[注] 参见:杜涛.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在深圳开出,区块链行业进入应用新时代[EB/OL].( 2018-08-12)[2018-08-16].http://tech.sina.com.cn/roll/2018-08-12/doc-ihhqtawx3399515.shtml. 。2018年11月8日起,深圳市宝安区的沃尔玛金海路分店“将为消费者提供区块链电子发票开具服务”,用户完成线上交易之后,“可以在线一键开具区块链电子发票”[注] 参见:腾讯科技.深圳区块链电子发票落地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线上线下同步打通[EB/OL].(2018-11-08)[2018-11-20].http://tech.qq.com/a/20181108/012186.htm. 。
凌薇有着所有大小姐的通病,盛气凌人却又同情心泛滥。安安的贫穷和谄媚极对凌薇的胃口,所以安安轻而易举地成为凌薇的闺蜜。
区块链发票记载的信息内容和目前的纸质发票、其他网络发票一样,具有证据价值。如果区块链发票中包含“税收筹划”等特殊涉税服务的具体类型或者有针对性的细节,则税收筹划报告制度会完全失去其仅有的线索价值和参考价值。区块链发票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容纳目前税收筹划报告制度所涉及信息几何倍数的信息,但是因为税收信息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甚至个人隐私,纳税人不可能同意对税务机关无条件开放税务机关希望获得的全部信息。
法律对发票信息类型和内容的规定受制于传统纸面介质上可以书写的文字数量,目前的网络发票和刚刚出现的区块链发票仅仅做到了无纸化而已,都没有突破原有纸质发票的信息量。突破原有纸质发票物理局限的无纸化发票的记载内容,则以无纸化发票相关法律的出台为先决条件,否则区块链发票仍然会停留在纸质版发票的无纸化阶段,无法实现发票信息承载量的质变。
区块链的应用层作为区块链最终呈现给用户的核心功能层,包括网络发票在内的存证类,是其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区块链技术放弃了传统的数据库“增加、删除、修改和查询”四个经典操作中的“删除”和“修改”两个选项,只留下“增加”和“查询”两个操作,通过区块和链表这样的“块链式”结构,加上相应的时间戳进行凭证固化,形成环环相扣、难以篡改的可信数据集合[20]2。所以,区块链发票和其他网络发票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了数据发票的唯一性、不可篡改性和可追溯性[注] 网络发票和电子发票,都是以无纸化为特征的数据发票。我国《发票管理办法》使用“网络发票”概念,不使用“电子发票”概念;《电子商务法》则使用“电子发票”概念而不使用“网络发票”概念。区块链发票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数据发票。区块链发票有可能是迄今为止最能契合发票特征和要求的数据发票类型,但不一定是数据发票的最高形式和最优类型。数据发票的特征决定着数据发票最好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但并不排斥其他技术的使用,比如目前的非区块链加密技术也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使用。因此,本文以区块链发票作为讨论对象,但是也可以将讨论结果应用于区块链发票之外依法得以开具的其他数据发票类型。 。这些特征也使区块链发票优于目前仍然广泛使用的纸质发票,因为即使在目前的“金税三期”条件下,仍然有假发票流转的空间;甚至在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办公场所附近,仍然经常有叫卖所谓“真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的人群存在[注] 根据本文第二作者长期观察,深圳市竹子林地铁站通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福田区税务局的路段,经常有多人在法定工作时间叫卖各种发票。 。
发票上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归入纳税人商业秘密的范畴,税务机关仅仅是基于法律规定才可以获得发票信息。通过立法增加发票必须记载的信息内容,税务机关自然期待能够通过发票信息发现税务疑点,纳税人不会同意区块链发票法定记载的信息无限制地增加。虽然税务机关本来就对获得的纳税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因此更多地获取纳税人信息并没有增加税务机关保密的法律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获得更多纳税人信息能增加税务机关获悉过多商业秘密的风险并增加税务机关滥用商业秘密和泄漏商业秘密的风险。税收信息不对称固然是税务管理低效和企业税收遵从度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但是,征纳双方信息的完全对称不可能实现也不应当实现,因为税务机关知悉商业秘密存在对纳税人潜在的损害,其知悉商业秘密的范围应当受行政的比例原则约束,税务机关对获取市场主体涉税信息量的渴望应当保持足够的克制。
综上可知,区块链发票的应用,使纸质发票对发票信息量的技术限制被突破,发票信息范围已经成为纯粹的法律博弈结果。区块链发票信息不但是发现避税和逃税的线索,而且是税务机关判断、行动和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的合法证据,区块链发票对于税务机关获取交易信息的功能已经远远高于对交易主体和交易本身的证明作用。未来的区块链发票将成为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的制度性工具;发票也将不再单纯是《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注] 参见:《发票管理办法》第3条。 。
正因为发票的功能早已脱离交易双方的需要而成为税务机关获取交易信息的工具,当区块链发票普及之时,其与纸质发票不可同日而语的可承载信息量将会使发票信息范围成为税务机关的着眼点和征纳双方法律博弈的核心,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保障原则将成为发票立法的直接约束。
(二)事先裁定的合理信息范围的限定
作为税收信息记载的法定工具,发票法定记载的信息范围只能随着立法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未来区块链发票的立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税务机关在税收信息中的劣势地位,因为成文法的稳定性和滞后性特征,税务机关仍然可能存在法律规定不足以应对新型交易或者复杂税收的筹划安排的税收信息需求问题。
(二)新课改下的小学科学课程有更强的趣味性,实用性与灵活性。为能更好激起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学习自动性,使他们在运用所学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过程中,锻炼探索创新的思维能力。新的小学科学课程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符合小学生需要和兴趣的科学内容。另外引导并提倡教师采用利于发展小学生研究能力的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在情感,知识,能力三方面全方位发展。
如何确定新型交易和复杂税收筹划本身存在的税务风险,对税收筹划方、交易方和作为中介的律师都是难题。例如,在“杭州儿童投资主基金案”中,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接到儿童投资主基金通过美国某国际律师事务所发来的律师函件,询问儿童投资主基金与Moscan公司收购儿童投资主基金所持有的CFC公司26.32%股权是否需要在中国境内完税[21]。“杭州儿童投资主基金案”中值得注意的情节,是美国律师向中国税务机关的咨询函件最终被中国税务机关审查后转变成为税务机关启动对该案件进行税务调查的线索。在目前可见的公开报道中,没有人对税务机关在税务咨询中发现税务案件线索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合理的解释或许是人们已经普遍将税务机关提供免费税收咨询服务和中介机构提供的税收咨询服务的性质区分开来:为客户保密,不能将服务中获得的信息用作对客户不利的目的,是包括税收咨询服务在内的中介机构的道德底线,也是服务合同中常常列明的保密条款;税务机关作为免费税收咨询服务的提供者,则因为其具有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特殊身份和职责而截然不同。税务机关的免费咨询,是可能否定目前交易合法性并进行行政处罚的“接警式服务”,如同警察对于咨询事项高度警惕,一旦发现犯罪线索就不应当放过一样。如此说来,对税务机关通过免费咨询发现案件线索的行为是否确有法律依据的疑问,反倒显得书生气十足。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税收信息的释放和加工基本处于咨询者可以控制的状态,咨询者不必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税务机关仅仅根据咨询者提供的信息提供服务。这些特征与中介机构提供税收咨询的性质相似,至于是否将咨询信息作为案件线索,是税务机关主动筛选信息、判断信息并进行调查的结果。税务机关在税收咨询中获得的客户信息本身就是“假设”的,税务机关并未从咨询中获得咨询者承诺为真实性负责的“真实”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税务机关对信息进行利用的辩解理由。不管上述分析是否理由充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的事实:税务机关提供税务咨询服务的过程,也是税务机关发现税务案件线索的过程。这样,税务机关的咨询服务,成为税务机关获取发票等法定信息之外税收信息的一条方便路径,税务机关可以通过提供咨询服务获得更多的税收信息,咨询者可以通过咨询获得主管税务机关对特殊交易的税法判断并以此指导交易,不过,咨询结果对双方并无法律约束力。
一般说来,特殊交易架构的背后,都有税收筹划的影子。如果税收筹划的结果能得到税务机关的事先确定,无论其属于避税、逃税还是节税,都可以让纳税人预知税务风险。如果纳税人按照税务机关事先确定税法适用结果的方案进行交易,征纳双方都将受到税务机关事先对涉税事项判断的法律约束,这就是事先裁定的真谛。事先裁定制度如果设计得当,应当能够成为纳税人税收筹划和税务争议之间的缓冲地带。据说我国不存在施行事先制度裁定的法律障碍[22],但是我国开展事先裁定服务的税务机关还为数不多,事先裁定在税收信息博弈中的合理信息边界仍需讨论。在我国的税务实践中,事先裁定仍然以“咨询”的形式出现,或者说,和上文所述“杭州儿童投资主基金案”中美国律师向中国税务主管机关的咨询一样,事先裁定是与一般税务咨询不加区分的。这种不加区分的结果,对于申请人而言,可以混入任何假设信息或者虚假信息;对于税务机关而言,可以随意利用纳税人提供的任何信息作为获得税务调查的线索;对于双方而言,咨询是低效率的,咨询的结果当然也缺少事先裁定应有的法律约束力。
采收前45天前后,即8月初至9月中旬,是保护梨果免受侵染的关键时期,一般年份应喷药3次,每隔半月1次。
事先裁定的信息边界,根本上取决于事先裁定结果的法律约束力:如果事先裁定结果没有法律约束力,则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可以是不确定信息,法律后果与普通税务咨询将毫无二致;如果裁定结论具有法律约束力,则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而且相当充分,足以反映未来交易的基本税收构成要件,否则裁定结论无法与申请事项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不会产生法律约束效力。在事先裁定中,税务机关对待未发生交易的法律适用,其实质和法院对待已发生事实的法律适用一样,是通过涵摄该事实的法律规定和申请事项对应的事实得出结论[23]。事先裁定的法律拘束力在于,申请人获得事先裁定结论后,如果按照事先裁定中提交的方案进行交易,则受到事先裁定结论的法律拘束;申请人如果改变方案,则不受裁定结论的法律拘束。
从事先裁定制度的目的出发,不难发现,事先裁定中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对税务机关的价值,应当在于确定未来交易的税法适用结果,不在于为税务机关窥视申请人未提供的商业秘密提供线索。尽管如此,如果法律未能作出相应的禁止性规定,事先裁定仍然可能成为税务机关获得新型交易信息和复杂交易信息的重要工具,因为税务机关在事先裁定信息的范围方面处于主动地位,而且,如果申请事先裁定的纳税人不再提供信息或者终止申请,反倒更容易引起税务机关的高度警惕,其后果和真正的报警并无二致。相应地,申请人对待是否申请事先裁定也会慎之又慎,因此,事先裁定事项的范围应当是不受限制的。
纳税人有权决定是否申请事先裁定,自然也希望有权决定在多大范围内向税务机关披露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涉税信息。相对而言,税务机关应当以能够作出符合申请人请求的事先裁定结果为限,确定获取信息的范围,但是客观上无法保证税务机关不会获得对申请人不利的涉税信息。如此,则申请人向税务机关披露的信息范围必然成为阻却纳税人申请事先裁定极其关键的因素,也将成为实践中事先裁定申请人和税务机关的博弈重点。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些专家认为,事先裁定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事项的全部信息”,“申请事先裁定等同于向税务机关明示其可能存在问题的涉税事项”[22]44。实际上,要求申请人提供超过本次事先裁定范围的涉税信息,可能会对申请人的权利造成损害。在进行事先裁定的过程中,税务机关不必考虑事先裁定的结果可以适用于多大范围的同类交易,但是,也不应当过分拘泥于“本次交易”而要求过于精确的细节。几乎所有的交易架构都可以复制,所以税务机关不应当要求获得本次交易安排的“全部信息”,而应当视其是否有专业人士代理的实际情况而决定是把申请人当作有基本税务知识的普通纳税人对待,还是当作有税务专业知识的纳税人对待,并由此决定需要获得的交易信息范围。如果税务机关借口事先裁定所必需而随意要求增加交易细节,则税务机关提供的事先裁定服务也将异化成为以获取税收信息为主要目的的法律工具,从而破坏纳税人通过事先裁定与税务机关进行合作的基础。事先裁定的信息范围,也正是在税收筹划报告制度所存在的“平庸之恶”可能再度以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为名损害纳税人程序性权利的关键领域,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不论事先裁定制度最终如何在我国落地,事先裁定和我国现有的免费税收咨询制度都是对“偶然”信息和“个案”信息的获得,而且都只能成为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服务提供者的另类收获而非目的。由此可知,事先裁定制度不能成为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的工具,更不能成为其获取税收信息的制度性工具。
这是到金江市区的唯独一条县级干道。看来今天是插翅难逃了。看到摩托车穷追不舍,胖子叫司机靠边停车,掏出电话向何泽说明了情况。何泽说,你们停下周旋一下,若能出点钱意思一下过去也行,不行就先拉到林业站,然后他来想办法。
四 、结语
我国税法体系中的税收筹划报告制度等税收信息制度性工具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且违反上位法的规定而可能不具有合法性,也因为实践中的困境而很难成为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的制度性工具。在区块链发票为代表的网络发票为发票信息扩容提供无限可能的背景下,如果通过发票的立法适当增加发票的法定记载内容而使发票成为税务机关获取税收信息更为重要的制度性工具,税务机关在税收信息博弈中的不利地位将得到改善。但是,税收筹划报告制度所折射的税收程序保障问题仍将存在,税收法定主义之程序保障原则在税法中的落实,仍然是构建税收信息制度性工具的关键一环。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保障原则,决定着税务机关不能随意构建税收信息制度性工具,不能变成法律的破坏者,而不论其真实目的是否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即使是在合法的范围内,税务机关在税收信息博弈工具的使用过程中,也必须遵守税收法定主义之程序保障原则,保障纳税人的程序权利。JS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G·拜耳,罗伯特·H·哥特纳,兰德尔·C·皮克.法律的博弈分析[M].严旭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
[2] 赵旭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释义与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287.
[3] Carmillae E. Watson. Tax Procedure and Tax Fraud in a Nutshell[M]. 4th ed. Minnesota: Thomson Watson, 2011: 57.
[4] 翁武耀.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制定[J].财经法学,2018(3):78.
[5] 刘剑文,侯卓,耿颖,陈立诚.财税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0.
[6] 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0.
[7] 金子宏.租税法[M].22版.东京:弘文堂株式会社,2017:83.
[8] 伯纳德·萨拉尼.税收经济学[M].陈新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2.
[9] 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M].陈联营,译.北京: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2014:17-18.
[10] 王宗涛.我国一般反避税条款:法律性质及其立法建构[J].税务研究,2014(8):66.
[11] B·盖伊·彼得斯.税收政治学[M].郭为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92.
[12] 埃里希·科齐勒.税收行为的经济心理学[M].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226-227.
[13] Richard Murphy. The Joy of Tax[M]. London: Bantam Press, 2015: 11.
[14] Sara Williams. Perfect Legal Ways to Pay Less Tax[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76.
[15] 金圣荣.贸易战:全球贸易进化史[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33.
[16] 张怡,吕俊山.税法中的法人格否认[J].河北法学,2019(1):64.
[17] 罗内·帕兰,理查德·墨菲,克里斯蒂安·肖瓦尼奥.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M].李芳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2.
[18] Prem Sikka. No Accounting for Tax Avoidance[J].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2015,86(3):427-429.
[19] Brian Hogan, Tracy Noga. Auditor-provided Tax Services and Long-term Tax Avoidance[J].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15,14(3):298.
[2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区块链白皮书(2018)[EB/OL]. (2018-09-05)[2018-09-23].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809/t20180905_184515.htm.
[21] 王开智,李国庆.从“儿童投资主基金”案看我国非居民企业间接股权转让所得税处理[J]. 税务研究,2017(11):105.
[22] 刘磊,熊晓青,周妍.事先裁定制度研究[J]. 税务研究,2012(9):47.
[23]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0-189.
The Break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Tax Information Institutional Tools :Taking the Procedural Guarantee Principle of Tax Legalism as the Logical Fulcrum
ZHANG Yi ,LV Jun -sh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tax planning reporting system stipulated by the tax authorities in China is possibly not legitimate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upport of the superior law and conflicting with the Legislative Law.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tax planning may be too radical and it will be easy to avoid or evade tax, tax authorities should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cedural guarantee principle of tax legalism and should not increase the procedural burden of taxpayers or illegally obtain tax planning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e tax planning reporting system cannot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tool for tax authorities to obtain tax information. Invoice is the main legal tool for tax authorities to obtain statutory tax information. Block chain invoice provides technical space for the increase of invoice record information. If the content of invoice record is changed by legislation, the information game pattern will change accordingly. Tax advance ruling will provide a new way for tax authorities to grab tax inform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free tax consultation. However, the procedural safeguard principle of tax legalism determines that tax advance ruling should not become an unrestricted institutional tool for tax authorities to obtain tax information.
Key Words : tax planning; procedural safeguard principle; tax avoidance; block chain invoices; tax advance ruling
中图分类号 :DF432
文献标志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1.08
文章编号 :1008-4355(2019)01-0088-15
收稿日期 :2018-12-01
作者简介 :张怡(1956),女,上海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税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博士;吕俊山(1967),男,郑州人,中国财税法治研究院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生。
本文责任编辑 :邵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