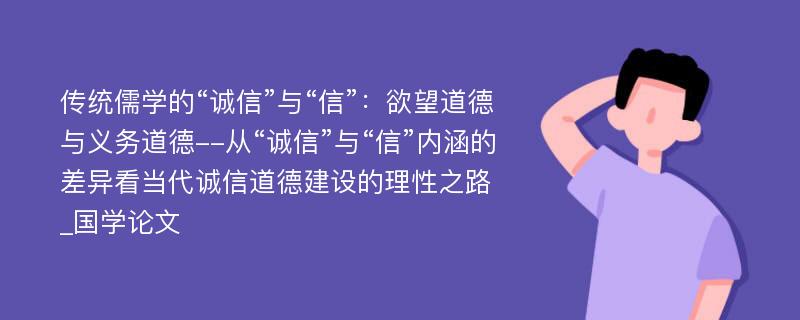
传统儒学的“诚”“信”: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兼由“诚”“信”意蕴差异看当代诚信道德建设的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道德论文,意蕴论文,儒学论文,道德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诚”、“信”二字连用始自战国,《孟子·万章上》说:舜的弟弟像“以爱兄之道来”,舜“故诚信而喜之,奚伪哉”?《管子·枢言》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荀子·不苟》说:“诚信生神,夸诞生惑。”现代汉语也承接“诚信”这一用语,并以之对应英文integrity。组成“诚信”一词的“诚”、“信”两字的内涵分别是怎样的呢?许慎《说文解字》云:“信,诚也。”“诚,信也。”许慎将“诚”、“信”互训,这使人们以为在表达古代思想的语境中“诚”、“信”可以相通,然而,如果我们细致考察和分析儒学史上所谈到的“诚”和“信”,可以发现,“诚”、“信”的内涵还是有所区别的。
1.传统儒学关于“诚”的内涵
儒家言“诚”始自《中庸》,《中庸》的核心观念就是“诚”。《中庸》是怎样论“诚”的呢?《中庸》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中庸》,31页)“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之,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1](《中庸》,34页)在这里,“诚”作为道德品质首先是被赋予“天”的,天“为物不贰”,亦即其自然运行时所显示出的真实无妄特点就是“诚”,“诚”是“天之道”。人未能有“诚”,故须求如天一般的“诚”,合于天道。《中庸》还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1](《中庸》,31页)此即是说,能合于天道的“诚者”具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这样一种圆融透彻、无所滞碍的心灵境界,而且,这样的“诚者”亦即圣人。《中庸》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诚”之于人的意义:“诚”提供了一条使人由凡入圣,成为拥有独特心灵境界的生命超越者的途径。故此,《中庸》还有这样的赞叹:“惟天下至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1](《中庸》,38-39页)
《中庸》之后的儒学家们也基本延续了对“诚”的这番理解。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孟子》,282页)荀子理论大异于孟子,但他也说:“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行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天地之大,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不诚则疏,君上为尊,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2](45-48页)孟子、荀子有关“诚”的这两段话与《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有相同的思想逻辑,都把“诚”看作是“天之道”,要求人们体悟天的“诚”,从而合于天道。孟子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孟子》,350页)他认为,个体生命获致“诚”,则心纳万有,“诚”被孟子看成是心体和道体合一的道德境界。荀子则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惟诚之能守,惟义之能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2](46页)这是说,致其“诚”,在仁义,实现“诚”,为“天德”。荀子以为,“诚”的获得使人不再拘执于一己之私,而是进入与天同德之境界。通过孟子的“反身而诚”说和荀子的“天德”说,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庸》一样,在孟子、荀子眼里,“诚”的意义在于它能使人摆脱身形的拘执,德与天同,予人以生命超越。
孟子、荀子之后的许多儒家人物,特别是那些着重阐释心性儒学的思想家,也确认形而上性质的“诚”的存在,以为这个“诚”下贯于人,人始有“诚”,而具备“诚”,人则获得生命超越。宋初的周敦颐曾言:“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3](15-16页)作为宇宙根本的万物资始之乾元就具有“诚”的本质,成为人真实无妄本性的“诚”乃源于此。周敦颐的“诚”既贯通天与人,又具有“纯粹至善”的性质,这样的“诚”对人而言,自然意味着一种彻底脱离私欲束缚从而合于天道的心灵境界。宋初的另一著名儒家思想家张载也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王夫之注:“……在天为道,命于人为性,知其合之谓明,体其合之谓诚。”[4](95页)人之“诚”可上溯于天道,了悟道与性的一体本质,则人达到“诚”,就此可见,张载的这个“诚”也意味着超越充满私欲之小我而臻至心灵天地。南宋大儒朱熹言:“诚是天理的实然,更无丝毫作为,圣人之生,其禀受浑然,气质清明纯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为而自然与天为一。如其余则须是博学审问谨思明辨笃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义礼智与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无非实礼,然后为诚,有一豪见得与天理不相同,便于诚有一豪未至。”[5](1563页)又注《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曰:“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1](《中庸》,33页)他认为,“诚”是“天理实然”,圣人生来已具,凡人后天习得,不过,无论何种情况下,在朱熹眼里,“诚”都意味着人从肉体的欲望中超拔出来,摆脱物欲之限,获得了合于天道的超越境界,达到彻底的道德自为。
2.传统儒学关于“信”的内涵
儒家创始人孔子未直接谈到“诚”,对“信”却言之甚多。孔子相当重视“信”,《论语·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论语》,99页)。“信”为孔子“四教”的科目之一。孔子又把“信”和“恭”、“宽”、“敏”、“惠”一起并列为“五德”[1](《论语》,177页)。孔子在如下一段和子贡的对话尤显示他对“信”的重视:“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论语》,134-135页)在这段对话里,孔子认为,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信”比“食”和“兵”更为重要。
为什么要讲“信”?孔子说得很平实。他认为,对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1](《论语》,59页)人若无信用,一如车无轴轮而不可运行;对于统治者来说,“信”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1](《论语》,49页),“信则民任焉”[1](《论语》,194页)。孔子没有直接把“信”同个体实现生命超越从而获得至高心灵境界联系在一切,在孔子眼里,之所以要讲“信”,在于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它的恪守能带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成员和谐交往的实际效用。
着眼于工具价值的角度谈论“信”,把“信”视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这不仅是孔子的思考方式,也同样是后来多数儒者谈说“信”所依循的思想路数。孟子说:“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1](《孟子》,282页)《礼记·大学》则言:“与国人交,止于信。”[1](《大学》,5页)《礼记·礼运》描画理想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6](331页)《荀子·王制》说:“……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2](461页)在这里,《大学》、《礼运》所谈到的“信”被看作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原则,孟子、荀子则是更进一步言明违背“信”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所带来的后果。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将“信”上溯于天,把“仁”、“义”、“礼”、“智”、“信”同五行联系在一起。在对“信”做了这番规定后,董仲舒仍把“信”看作是“五常”之一,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五者修饬,故受天佑而厢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7](1099页)还称:“伐丧无义,判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8](65页)认为统治者遵循“信”等五种规范,则受天之佑,惠及众生;反之,则处众之所恶。这些表明董仲舒依然把“信”看作是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原则,是包括从天子到庶人都应遵行的规范。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高峰,宋明理学家们常以天道言“性”,将“信”连同“仁”、“义”、“礼”、“智”作为“性”的内容,通过“性”把“信”与“仁”、“义”、“礼”、“智”同天道挂搭。如朱熹即称:“仁、义、礼、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9](2836页)然而在实际上,对于“信”,宋儒注意到的也还是它作为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原则这样的意义,注意到其工具价值的方面,如朱熹称:“若人无信,则语言无实,何处行得?处家则不可行家,处乡党则不可以行于乡党。”[4](595页)陆九渊说:“是故为人子而不主忠信,则无以事其亲;为人臣而不主于忠信,则无以事其君;兄弟不主于忠信则伤;夫妇不主于忠信则乖;朋友不主于忠信则离。”[10](374页)这里强调的是“信”在调整社会关系、理国治民中的作用。
二
在儒家思想里,意蕴不同的“诚”、“信”体现着两种不同的道德要求。
美国法理学家富勒(Fuller.L.L.)认为,道德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此即“义务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和“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前者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本条件,是对人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人应有的义务,如果我们的行为不符合义务的道德,则会受到指责,因此,履行义务的道德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不同于前者,后者即“愿望的道德不是人们所必须遵循的,它是许多普通人很难实现的道德要求,它“提供了应该作到尽善尽美的一个一般思想,而不是提供给我们作到尽善尽美的任何明确无误的指示”。“愿望的道德”体现为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精神层面的追求[11](54-56页)。
借助富勒对两种道德的分疏,我们来审视传统儒学的“诚”和“信”。
首先就“信”来看,上文言及,儒家更多的是从工具价值角度对它加以谈论,将它看成是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原则,是人们处世立身和统治者治理社会的必备之道,儒家的这番理解实际体现了这样的含义:人际的协调、社会的维系是离不开“信”的,只有借助社会上下层面、同一层面内部之间成员的互信,社会才能得以正常运转;换言之,恪守“信”是社会对人提出的道德义务。对照富勒对道德的分疏,儒家把“信”看成人们不得违反且必须履行的义务,我们可以认为,儒家的“信”给人们提出的是一种“义务的道德”。
再看儒家的“诚”。儒家认为人之“诚”作为德性有着存在于人之外的形而上源头,人应体悟这个形上世界,如此确立自我之“诚”,确立“诚”可以让人们实现生命超越。儒家学者在谈到这个“诚”时并不考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外在秩序的维持,而是要求人们通过对天道的体悟,去实现生命超越,获得理想境界,儒家这样的“诚”无疑相当于富勒的“愿望的道德”。
以“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要求理解传统儒学中的“信”和“诚”,对把握当前的诚信道德建设的理路不无意义,就此我们从“信”和“诚”分论之。
1.“信”——“义务的道德”提示以公共法规为诚信道德提供制度保证
就现实言,我国仍处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当前的诚信道德建设也正立足于此。按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社会属于乡土社会,这个社会以熟人为交往对象,是“‘熟悉’的社会”,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2](9页)。这样的社会里,其社会关系的处理离不开人情,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关系的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什么标准”[12](36页)。如果以“诚信”道德的视角看,乡土社会的“信”是也建基于亲缘、地缘关系上的,信用的范围局限于亲戚、朋友、熟人之间,因为超过亲戚、朋友、熟人间的交往并非经常,所以,在陌生人之间也谈不上人情,“信”不针对超于亲友、熟人范围外的生人。可以说,在传统社会背景下,是人情,更进一步说是人情背后的人们之间交往的经常性和无选择性保障着人际之间的“信”。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交往日前扩大,人际交流不完全局限于传统的亲朋邻里的小圈子,乡土社会具有的支撑“信”的基础不存在了,那么,如何发展出足以支持现代开放社会的诚信行为的一套机制呢?
富勒所谓“义务的道德”是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外在秩序的道德,它所面对的是社会公共领域,它基于公共领域的秩序维护向人们提出了起码不应该做什么的要求,这意味着“义务的道德”既具有人类都须遵守的普遍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和惩罚性,“义务的道德”具有迈向法律化的阶梯。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传统社会,“信”所面对的都是社会公共领域,它解决的是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不同的只是,两种社会下,人们经常面临的人际面是不同的。在传统社会下,人际的“信”依靠存在于人情背后的人们之间交往的经常性和无选择性加以保障,“信”没有被纳入法律化的形式中加以确定;在人际交往多维性、广泛化的今天,我们则可以利用“信”作为“义务的道德”所具有的类法律的性质,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缔结代替“人格担保”,以法律、法规的清晰厘定代替世故规矩,从而通过法律法规将人际之间的承诺、守诺置于法的约束之中,通过社会正式的法律制度,以法律义务的确立和法律责任的承担为材料浇注社会“信用”大厦的社会基石。要言之,“信”的意蕴指示我们通过将“义务的道德”法律化这样的方式为当代社会的“信”的确立提供保障。
2.“诚”——“愿望的道德”提示以私人信仰为诚信道德添加心理源泉
谈到“义务的道德”,富勒认为,这种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不同之处仅在于,法律在禁止这些行为时应区别行为本身的严重程度和危害大小。例如,道德和法律都禁止赌博,在道德方面,区别大赌和小赌意义不大;在法律方面,则区分小赌和大赌。这样一来,法律和道德似乎已经划上了等号,它们面对的问题在质的方面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量。
将信用施行于开放社会中的不特定人,对传统社会诚信道德做适于现代开放社会的转换,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法律道德化的方法,辅信用伦理以制度建设。不过,问题在于,正如富勒所察觉的那样,随着法制的发展和完善,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的重叠部分会愈益增多,它们两者之间的界限随之变得模糊。在这种情形之下,恪守信用作为显现出来的特定现象事实,就可能出自不同当事人的不同思想动机——既可能是源自对信用道德心诚悦服的遵守,也可能是出于慑于法律的他律,它们所引起的结果一致的,但一个是道德作为,一个守法行为。守法虽然也带来了对信用的维护,但问题在于,法律的完备性永远只是一种趋向,法律总有不能照顾之处,光靠法律的慑服,信用还是无法保证的。对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西方传统社会是基督教社会,宗教构成了人们道德生活的基础,进入现代,西方社会政教分离了,但是宗教依然发挥着很大的精神作用。即使在西方社会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宗教信仰依然构成了大多数西方人的重要生活内容,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使得他们有着对终极实在的敬畏和生命超越的祈求,这种对生命超越的祈求作为“愿望的道德”造就了西方多数人的道德境界,赋予他们道德履行的自觉性。在中国以往社会,作为大传统的儒道释思想都言道和心性,引导文化人体会心灵境界,实现生命超越。儒道释以性和天道提供的终极关怀未能成为民众的集体意识,但普通民众有对天的畏惧,他们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和“善恶有报”,有一种同样可以归之于“愿望的道德”的信仰。由此可见,以往中国的大小传统里都具有精英人物和普通民众都不乏为自觉进行道德践履的心理保证。
近代已降,伴随着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亘古未有的结构性变化,文化人告别了蕴涵着终极关怀这一内涵的传统文化中的性和天道思想,普通民众也趋向无神论。当代人受过科学教育,然而,科学教育并不必然使人具备对精神世界的向往,所以,我们看到,祈望生命超越的人士在今天社会里并不多见,有真诚精神信仰者也不为多。前文言及,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不能系于法律之约束,而无信仰者泛工具化地权衡利益,这当然使其无从获得足以支持自己道德践履的精神内力,诚信原则的自觉奉行对他们来说乃无从谈起。基于此,当前推进信用伦理的建设需要有一项基础性工作,这就是,珍视富含人文精神内涵的传统中外文化,倡导和引领人们在私人空间建立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体会心灵境界,使人们能有可守望的精神家园,获得终极关怀,进而为建立诚信提供精神之源。
标签: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道德论文; 论语论文; 孟子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法律论文; 荀子论文; 天道论文; 诚信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