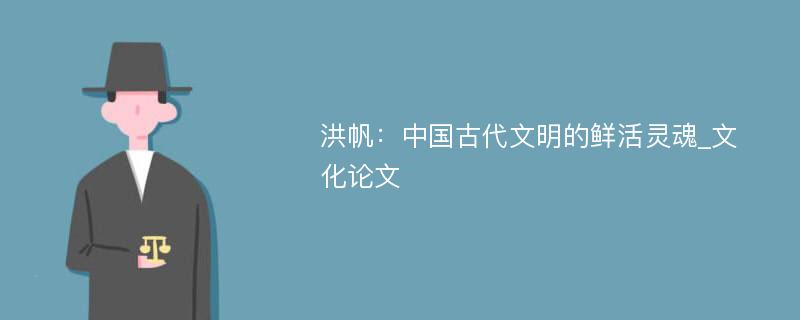
《洪范》——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灵魂论文,文明论文,洪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摘 要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本文旨在说明《洪范》就是这种真正的文化哲学。在批判了汉儒所建立的《洪范》学模式的错误取向(五行灾异论)后,探讨了《洪范》所蕴含的文化科学的意义:它把传统的宗教经验合理化为伦理文化;它指明了文化的五种物质要素和五种精神要素;它通过对殷代的宗教和政治的历史反思,创立了以“社会公正”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洪范》成为殷周之际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
关键词 文明时代 符号行为 洪范九畴 王道
一、导论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1〕本论文试图说明:《尚书·洪范》是中华文明形成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
根据本论文的旨趣,我们需要首先说明一下中国文化史上的文明时代形成于殷代,确认《洪范》是箕子的著作,以及评述一下中国“《洪范》学”的简史,以此作为导论。
1.殷代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洪范》是箕子的著作
“文化”与“文明”这两概念,在西方学术界一般不加区别地使用着,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所区别的。仅就本论文所涉及的一个方面,略述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人类学之父”泰勒(E.B.Tylor)第一次把人类社会进化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野蛮和文明。此后,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是城市化(意味着社会组织复杂化)和文字的使用。我国当代学者所熟悉的是摩尔根、恩格斯有关这三个时代划分的理论。他们把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作为史前的两大文化阶段,而在野蛮时代后期才开始向文明时代过渡。摩尔根把生产技术发展的一定水平(主要为铁器的使用,他是就古典古代的文明史而言,如果就古代东方而言,则应当是青铜的冶金术),并以文字的使用作为文明开始的标志。恩格斯进一步说明:“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劳动分工、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等等的发展改变了先前的社会,即以地域关系和阶级压迫为特征的国家机构代替了以血缘关系和公有制为特征的氏族公社制度。人类社会就由史前文化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社会则是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
我国的文明时代开始于什么历史时期?我国当代历史家一致同意开始于夏代。但是夏代的历史记载至今尚未发现考古学上的证据,历史研究者仅推测龙山文化可能是夏代文化遗址。但是遗址中没有任何铜器,没有记事的文字体系。传说历史中的夏代都城经常迁移,这种城市显然是部落社会的暂时定居点,而不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因此,我们认为夏代尚处在向文明时代的过渡阶段。我们同意历史家范文澜的论断,他说:“夏是国家机构逐渐形成的朝代,商是国家机构已形成的朝代。”〔2〕
断定商(即殷)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有关它的纸上遗文和地下实物与上述文明时代形成理论是一致的。据《尚书·多士》篇,周公向殷代遗民说:“惟尔殷先人,有册有典。”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的地下实物证明:甲骨文中已经有记载国之大事(“唯祭与戎”)的“书写的历史”;有了“京师”“大邑商”的称呼;至于殷代的铜器达到了世界青铜文化的高度水平;墓葬遗址表明“百姓”(贵族)与“民”的阶级划分,等等。
再就《洪范》篇的著作权言,自司马迁到清末,除个别人外(如南宋赵汝谈在其《南塘书说》中谓“《洪范》非箕子之作”),一般都认为是箕子之作。我国近代学者多认为《洪范》是战国时子思一派的儒家所作。但是历史家范文澜仍相信为箕子之作,他说:“《尚书·洪范》篇,据说是周史官记录箕子所说殷政治文化的纲要,大体可信。”〔3〕我们以《洪范》的本文为内证,完全有理由认定它是箕子的作品。第一,如果为战国作品,《洪范》在谈五行时必联系“阴阳”,但是《洪范》不谈阴阳,正如《周易》不谈五行一样,是有目共睹的。第二,战国儒者谈“王道”必谈“礼、乐、刑、政”四个“王道之端”,而《洪范》论“王道”完全不涉及礼乐。
2.《洪范》学简史评述
在经学史中,《洪范》的研究最为大观,称之为“《洪范》学”,当之无愧。但是它的主流,2000年来,走在误区中:它所建立的阴阳五行灾异论是幼稚神学和巫术的杂拌儿。
对《洪范》作专门研究开始于西汉初期。班固作过概述,他说:“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其传与刘向同。”(《汉书·五行志中》)又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师古注:错,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传》,……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汉书·五行志上》)夏侯始昌所作的《五行传》原名为《洪范五行传》(参看《汉书·夏侯胜传》),刘向所传《洪范》原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刘歆所作原名为《五行传说》。这类著作的不同,不在原理上,而在所举的事例上。这个原理,班固概述在刘向的著作中。他说:“向见《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纪,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汉书·刘向传》)这种天人感应的符瑞·灾异论的创立者是刘向之前的“始推阴阳”以曲解原始儒学的董仲舒。他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善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又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刘向、刘歆以及其他五经学者所建立的“五行阴阳休咎之应”的《洪范》学被班固总括在他的《五行志》中,成为支配中国正统史学的神学历史观。二十四史中从《汉书》到《清史稿》除了《新五代史》和《辽史》外,都有《五行志》。(《魏书》称《灵征志》,《清史稿》称《灾异志》)
隋唐的《洪范》学继承了汉代五行灾异论传统。不过,从北宋起,官方虽然宣传甚至发展了灾异感应之说(如宋仁宗撰《洪范政鉴》,明朱洪武撰《御注洪范》),而个别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则反对五行灾异论。我们于每个朝代仅举一人为例。例如北宋王安石著《洪范传》(已佚)指责伏生、董仲舒、刘向的五行灾异说为俗儒之一蔽,并主张虽有灾异,亦不足畏。南宋叶适在其《习学记言》中批判汉儒灾异感应论,并指责“洛书”为妄说。明代徐献忠在其《洪范或问》中明白认定五行是人类生活所需的“五物”,而后儒“谲其义”,妄解五行为吉凶主宰。清初,王夫之在其《尚书引义》中对《洪范》学作了方法论的批判,他认为把“五行”范畴和人事其他类型“强其似以求配”是诬妄之言。他说:“凡以形似配合而言天人之际者,未有非诬者”,这是“凿智以侮五行”;“比之,拟之,推其显者而隐之,舍其为功为效者而神之,略其真体实用而以形似者强配而合之。此小儒之破道,邪德之诬天,君子之所必黜也”。最后,我们借龚自珍的话作结论,他说:他“最恶刘向之《洪范传》,以为班氏之《五行志》不可作也”(《与陈博士笺》)。又说:“刘向有大功,有大罪,功在《七略》,罪在《五行传》”(《非五行传》)。
我们完全赞同王安石、王夫之等杰出思想家对汉儒《洪范》学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启示了我们:这种《洪范》学所以走进误区,主要由于它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是非科学的。
汉儒所建立的《洪范》学的理论前提,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学说中的坏的方面,即以阴阳五行相克相生的假说来说明天象的变化,再以这类变化巫术式地比似、象征、推断人间的政治得失和吉凶祸福,从而得出了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就是这样“始推阴阳”以“缘饰”儒学。
关于汉儒的方法方面,如王夫之所指出的“以形似配合而言天人之际”外,还可指出一点,即对《洪范》第八畴“庶征”所作的训诂学的曲解。其文为:“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庑。一极备(极备即过甚的意思),凶;一极无(长久不至),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旸若……。咎征: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旸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所谓“庶征”的基本意义为,五种天时(雨、晴、热、寒、风)对人类生产的影响,如果五者来得适时则众草繁盛,五谷以成。前者指畜牧业而言,后者指农业而言。从甲骨文看,殷代生产确以农业为主,畜牧为辅。如果五种中,一种来得过甚(如久晴不雨,或久雨不晴),当然是“凶”事,即旱灾或涝灾。至于所谓“休征”(美行之验)和“咎征”(恶行之验)是以天气变化的常态与异态比喻国君的性格或德行的善恶所引起的政治效应,就像时域久雨对人民所产生的结果一样。例如,所谓“狂,恒雨若”,就是说,君行狂妄,就像久雨成灾那样可能引起人民的政治动乱,当然是一种“咎征”。再如“肃,时雨若”,就是说国君在政治上肃敬慎行,当然是一种“休征”:使人民对国君像对时雨一样满意。在我们看来,关键问题为:在训诂学上怎样理解“若”这个词。我们认为应当解释为“好像”,如《尚书·盘庚》中的“若火之燎于原”一句中的“若”。但汉儒把“若”释为“顺”,仅就训诂学说,亦可通。如《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即命羲和敬顺上天)。但按古代语法,“若”放在所形容之词的后面,一般作“好像”解。汉儒从其天人感应论出发,把“若”勉强释为“顺”。例如,把“肃,时雨若”或“狂,恒雨若”解释为“君行敬,则时雨顺之”或“君行狂,则常雨顺之”,他们凭借这种不恰当的训诂而建立了天人感应论的阴阳五行灾异论。我们且举一例,看看汉代《洪范》学家所作的荒谬的解释。如《汉书》所记录:“《庶征》之恒雨……刘向以为大水。〔据《春秋》〕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刘向以为周〔历〕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是时隐公以弟桓幼,代而摄立。公子翚见隐居位已久,劝之遂立(师古注:“劝杀桓公,己求为太宰”)。隐既不许,翚惧而易其辞(注:反谓隐公欲杀桓),遂与桓共〔谋〕杀隐。天见其将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电。……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弟佞臣将作乱矣。’后八日大雨雪,阴见间隙而胜阳,篡杀之祸将成也。隐公不悟,后二年而〔被〕杀。”(《五行志上》)这真是一片妖妄的预言。
所以我们完全同意王夫之的看法,这一类的《洪范》学是“小儒之破道”、“君子之所必黜也”。于是,我们试图对《洪范》本文作出合于历史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全新的解释。附带声明一下,我们所引用的《洪范》本文,采用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的引文,至于有些必要的注释我们主要采用《十三经注疏》版本的《尚书正义》中的《汉孔安国传》(被视为魏晋人的托名之作)和孔颖达等人的《正义》。前者我们以下简称为“孔注”,后者简称为“孔疏”。
二、重新对《洪范》作出文化科学的理解和解释
当代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史潘格勒(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说过类似于马克思的话,他说:“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哲学,每种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天才的哲学家独具慧心,因而能对他的时代和时代的使命具有远见卓识”。箕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洪范》全文作出新的注疏,只挑出几个重大问题来谈谈。
1.把宗教经验合理化为“常伦所序”
在《洪范》的开篇,周武王访问箕子,提出如下的问题:“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的回答是:天所赐给禹的“洪范九畴”就是“常伦所序”。箕子所列举的九畴(即哲学上的九个范畴)为:“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武王提出的问题,依孔注和孔疏,就是问:“天默定下民使群生”并且“谐合其生”要凭借什么样的“常伦所序”呢?这几句话首先肯定了人天生是社会动物。所谓“常伦所序”,就是指维持社会秩序(谐合其生)的行为规范。箕子认为这个“常伦所序”是上天赐予的,这并无严格的宗教意义。从文化人类学去看,古代世界许多民族常常把社会伦常或法律规章假设为神所赐予的,以便加强它们的约束力。例如古代斯巴达的国家机制形成的时期, 赖库古(Lycurgus)的立法被认为是达尔斐(Delphi)的神谕(oracle)所提出的。赖库古并且被认为在成为立法者以前就是神。 古罗马人把一句谚语“天神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Iupiter omnibus aequus)”作为罗马法的来源。如果我们从《洪范》九畴全文去看,看不到上帝对人事的任何直接干涉(汉儒对“庶征”的曲解,我们在上文中已批判过了),也看不到对宗教的教义和信仰的任何规定。这样说来,所谓“天定下民群生”和“天赐九畴”不过像通常所说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一样。马克思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他并且解释说:“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4〕马克思所说的“古典古代”指古代希腊的“城市国家”(polis), 其特征为:天生是城市市民的希腊人,都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武王所说的“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和箕子所说的天赐“洪范九畴”也不过意味着:在王国领土内的一切居民天生是国王的下民(臣民)。这样看来,《洪范》中的对“天”的崇拜,至多相当于西方宗教学中的敬上帝而远之的“自然神论”(deism),如伟大科学家牛顿所信仰者。 牛顿认为上帝创造了自然界及其规律以后,不再作出任何干涉;他本人不过发现了这个自然规律而已。箕子和牛顿一样,认为天赐“洪范九畴”,不过由他发现而已。这不是证明上帝存在的“神正论”(theodicy),而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把宗教经验理性化(rationalized)为伦理·政治文化。而我们在上面已提到的,刘向等人则把历史经验(春秋时代以来的历史记载)神秘化为幼稚的神学。这是思想史上的倒行逆施。
2.文化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
我们再论述《洪范》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即“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原文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撇开了一切神秘主义的解释后,直接阅读本文,我们一眼就可看出:五行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基本要素,五事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基本要素。
我们先略释一下“文化”这个概念。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可以找到成百的“文化”的定义。我们仅就一般的用法说,文化包含有两大主要成分: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文化指在生产、生活和经营中所应用的器物、工具、武器以及其他一切人工的制品。精神文化指风俗习惯、语言、神话以及道德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价值体系。当代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的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社会组织(即人类活动的有组织的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谓“社会制度”)是精神文化的真正要素。当代人类学进化论学派大师摩尔根认为史前文化向文明时代过渡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标志为:由原始氏族社会演进为政治社会。
根据上述“文化”概念,试论“初一曰五行”的本义。“五行”从其名称及其属性看,显然指人类生活和生产所利用的五种物质要素。在战国时阴阳五行家出现以前,周代学者都是这样看的,如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昭公二十五年》、《国语·郑语》、《鲁语》等书中者。最有力的证明是《尚书大传》中所记录的这样一个故事:“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以达旦。前歌后舞,假于上下。咸曰:‘孜孜无息,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武王士卒所歌唱的一定是商郊流行的殷代的民歌。也许,“五行”这个术语出自殷代的民间。我们再从殷代的物质文化史看,就可看出五行的属性(“自然之常性”)的含义。如云“木曰曲直”(孔注:木可揉使曲直)显然指殷代的农业工具是用木揉制成的耒、耜、犁。“土曰稼穑”,如见于甲骨文者,指禾、麦、黍、稷、稻等农作物。至于“金曰从革”(马融注:金之性从人,而更可销铄),这个属性显然得自殷代高度发展的青铜冶金技术。至于“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更不用解释了。所以,我们“信而有征”地认定五行是殷代物质文化的五种基本原素。
我们再从精神文化要素的观点重新解释“二曰五事”。先从五事之“二曰言”说起。当代的语言学把“语言”(language)和“说话”(Speaking)分别开来。前者指语言本身,即语言的规范,它们是符号化了的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语言社会习用了的符号结构;“说话”指个人使用词和句的语言行为,而人们说话时不自觉地遵守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语言社会的语言习惯(这种习惯可以词典化和语法化”)。这就是“五事”中所说的“言曰从”。再说五事中的“一曰貌”(孔疏:“貌是容仪,举身之大名也),可以释为非符号的语言,即以身体的不同姿态表达自己的观念或情操,现代语言学称之为“身体语言”(bodylanguage or kinesics)。例如,俗语形容一个女人的灵活的眼睛为“会说话的眼睛”,就是以眼神作为体语。总之,貌与言都是语言(“貌曰恭”不过是就一种表情而言)。
自达尔文以来,西方学术界习惯于把人类说成是具有语言能力的高等动物,当代有些哲学家(如Wittgenstein、Derrida 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不再把语言看作是思维的表现,而是看成一种达到更高目的的符号行为。甚至认为没有符号行为,也就没有文化,人也就是动物而不成其为人类。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White)说:“人和类人猿以及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生物的区别就在于:唯有人具有符号行为能力。有了语词,人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观念和哲学的世界。人生活于观念的世界中,恰如他生活在他所感知的物理世界一样地真实。”〔5〕由此可见,语言的本质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最早的、最好的工具,而且是促进人类知识进步的工具,它导致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形成。这就是说:语言行为结构使人类首先促进了感知认识的发达,即“视曰明”和“听曰聪”;由此而进步到应用概念和抽象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思维,即“思曰睿”(孔注:“〔思〕必通于微”)。所以我们认为五事是精神文化的要素。
3.作为文化结构重要部分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仪式
我们再从政治制度是古代文化的真正要素来理解《洪范》九畴中的第四畴“八政”。这个范畴是箕子对殷代政治制度史的记实,也是国家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体系。
殷代王国政府分为八大部门,即“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就八政之第一、第二言,如《汉书·食货志》的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也。”就管理部门而言,如孔疏:“食,谓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货,掌金帛之官,若《周礼》司货贿是也。”“四曰司空”,孔疏为“掌居民之官”,用《食货志》的话说,“是以圣王域民,筑城廓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恩格斯指出:国家机构和旧的氏族社会组织的首要的不同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在殷代这样的专制王国中,政府不仅管理城市居民点的划分,如马融所注:“司空,掌营城郭,主空土以居民”;更重要的是农村居民点的划分,以便实行孟子所说的三代井田制下的土地再分配以及《食货志》中所描写的井田制下的“邻里”制度。至于“司寇”(“掌诘盗贼之官”)和“师”(“掌军旅之官”)则是国家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主要作用。“宾”是为天子“掌诸侯朝觐之官”。
再特别谈一下“三曰祀”。如《汉书·郊祀志》所释:“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这是殷(以及三代)的宗教仪式的两大类:祭祖以昭孝道,祭神以通神明。不过,殷代和周代一样“掌祭祀之官”所掌管的是国典,而不是民间的祭祖与祀神仪式,后者是家庭的私事。我们没有篇幅详论殷代的宗教文化,仅就其特点而言,第一,国家的礼典,指天子祭天(天神,即上帝)和祭社稷山川之神以及天子和诸侯的宗庙之祭。这表明宗教是服从于政治的。《国语·鲁语》中展禽答臧孙说:“夫祀,国之大节(注:制也)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由国家管理宗教仪式,是中国古代宗教的特点。战国时的儒家经典《中庸》中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这几句话揭示了三代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实质。第二,殷周以及整个中国古代的宗教仅重视仪式,而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神学,而且从仪式所表现的目的看,仅在于报答天地之神对于人类或祖先对于后代的功德。如《鲁语》所云:“〔所祀〕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注:质信也,以其有德于民而祭之,所以信之于民心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是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只有“此岸性”的目的,没有否定尘世而去憧憬“彼岸世界”(对天国生活的追求和灵魂的得救),没有“绝对的他在”(absolute the Other)。所以《洪范》中的“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者都是尘世的最大幸福。上述殷代宗教的两个特点,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过的,正是使宗教经验理性化为伦理·政治文化的表现。
4.作为政治哲学的“皇极”论
最后,我们解说一下《洪范》九畴中的最高范畴,即第五畴“皇极”。它涉及的方面很复杂,不过其主旨是指出了“正直”的“王道”。我们仅截引这一方面的本文:“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孔传注:“无有乱为、私好恶,动必循先王之道路”;孔疏云:“人有私好恶,则乱于正道,故《传》以‘乱’言”)。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皇极”论是箕子对殷代历史作了反思后而提出的他自己的政治哲学。虽然他把它说成是神的启示,实际上是“历史的启示”(apocalypse of history)。 箕子为什么要提出他的王道哲学?孔子指出过,殷代统治的特点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如我们在上节所述,殷人祭神、祭鬼(祖先)的国家祀典是从属于政治的。从甲骨文的卜辞和《洪范》第八畴“稽疑”所提到的龟筮决疑原则去看,“贞人”代表神鬼所作的指示似乎对王权有支配作用。但是从历史事实看,最圣明的国王和最暴虐的国王都不受卜筮的约束或不信天神决定其命运。就前者言,如《尚书·大禹谟》(虽认为后代伪作,但至少有相对的可信性)所说,舜已决定让位于禹,禹固辞,最后请舜以占卜来决定,舜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策协从。”就无道的君主言,如《史记·殷本纪》所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纣王的狂言是“我生不有命在天”。在古代专制王国的历史条件下,当宗教制约对暴君已失去效应的情况下,任何杰出的思想家不可能产生以民主制代替君主制的想法,唯一可能设想的是从精神上培养君主的道德意识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假托一些历史上的圣哲的君王(如尧舜)所实行过的“王道”让他遵循(即“遵王之义”、“遵王之道”和“遵王之路”)。于是箕子提出了他的“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南宋《尚书》学家蔡沈从《大禹谟》和《洪范》中看出这一“心法”。他说:“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书集传·自序》)。”
首先,我们略述一下聚讼千古的“皇极”这个词汇的训诂问题。汉儒郑康成、马融都释“皇”为“大”;释“极”为“中”。所以《孔传》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宋代大儒陆象山发挥了“大中之道”的政治哲学的意义:“皇,大也;极,中也。洪范九畴,五居其中,故谓之极。是极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万物以此而育。古先圣王,皇建其极,故能参天地,赞化育,凡民保之,以作懿行,息邪恶。”(《象山全集》第23卷)朱熹第一次不同意这种解释。因为“极”在古汉语中,从来没有“中”的含义。朱熹说:“‘中’不可解作‘极’,‘极’无‘中’义。”他按这二字的常用词义解释为:“皇,君也;极,标准也……‘皇极’二字,皇是指人君,极是指身为天下做个样子,使天下视之为标准。”(《朱子语类》)我们赞同朱熹的训诂,同时赞成陆象山所发挥的意蕴。我们认为“皇建其有极”,意味着国君要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在世袭君主制度下,要求国君实行“王道”,不失为一种最高理想。所谓实行“王道”,即上面所引的“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和遵王之义”。孔颖达称这三者为皇极之“体”,他解释说:“为人君者当无偏私,无陂曲,动循先王之正义;无有乱为私好,谬赏恶人,动循先王之正道;无有乱为乱恶,滥罚善人,动循先王之正路。无偏私,无阿党,王家所行之道,荡荡然开辟矣;无阿党,无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辩治矣;所行无反道,无偏侧,王家之道正直矣。”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皇极之体就是“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公正”一词就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道德上的公正,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即一个人所具有的美德不仅用来对待自己的事情,而且用来对待一切其他的人,在这种意义上,“公正是一切美德的总汇”。二指“政治的公正”,为了希腊城市国家的“自足的共同生活”,要求“或者以领导者身分,或者以随从者身分,造福于他人”。因此,“公正就是守法和均等”,不公正就是“不均”。〔6〕箕子所持的皇极之“体”(见上引文)正是这种“毋党毋偏”的在赏罚上和政治上的均等。这是对统治者而言,就一般人民而言,则如《皇极》中所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注:皇极所敷陈之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天子对臣民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仁爱,而臣民对实行王道的天子则“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箕子的“王道正直”观念蕴含着政治公正与道德公正的统一,所以九畴的第六畴“三德”中,以“正直”作为天子的首德,并且理解为“平康正直”(正直才能达到平康之治)。总之,“王道正直”意味着以“均”或公正为原则,造福于人民。
三、结论
箕子看到殷代宗教文化的衰微和殷王朝的灭亡,他以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王道正直”(社会公正)的文化哲学的概念,试图把衰微的宗教经验理性化为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同时希望建立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使世袭的君主制不再出现暴君虐政。借用西方政治学术语说,这是“开明君主制”。箕子的“皇极”论,古代就有些学者用《尚书·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来理解。所谓“惟和”即《洪范》中的“相和其居”;“正德”孔疏为:“正德者,〔天子〕自正其德”;“厚生”一般注释为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使人民家给而人足。箕子的这种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纲领,被周王朝的缔造者武王接受后,从而开拓出中国古代最光辉灿烂的周代文化,其特征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孔子对它表现出无限景仰的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本人的政治、道德最高原则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他对宗教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他的社会经济政策原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发现,在世袭君主制下,维持“国家以宁,庶民以生”的君民关系的辩证法则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孔子的这些观点显然是箕子的皇极论的继承和发展。箕子、孔子的政治文化哲学赋予了中国古代文明以非宗教的伦理·政治文化的特色,使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洪范》也就成为殷周之际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1页。
〔2〕〔3〕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53页,第5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
〔5〕怀特:《文化科学》,纽约1945年,第45页。
〔6〕均见《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2页引亚里士多德语。收稿日期:1995—12—05
标签: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文明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洪范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