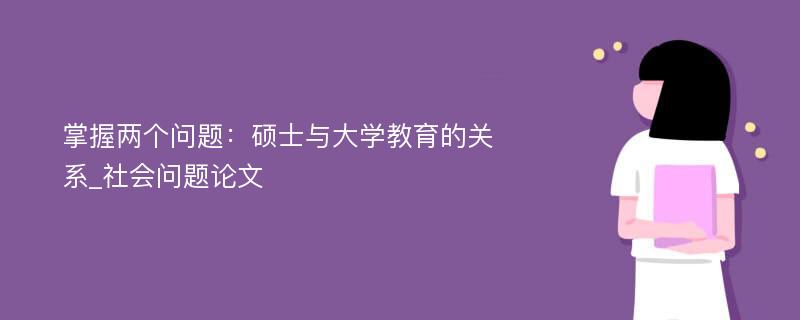
大师二题——大师与大学教育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师论文,关系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历年诺贝尔奖的颁布,更随着温家宝总理与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对谈如何在大学中培养大师话题的热播,培养大师的问题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无论人们怎样焦虑与不安、关注与期待、讨论与辩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大师仍可以说寥寥无几,对大师的渴求似乎成为大学挥之不去的梦魇,培养大师甚至成为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导向,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人们不禁要问,大师与大学教育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一、大师不是可以培养的,而是自然而然生成的
“大师”是相对概念,大众传媒中封某某为“大师”的不在少数,多年前的所谓“气功大师”之流早已成笑柄。就大学自身而言,大学的定位本身也影响着大师的标准。尽管给“大师”下个确切定义比较困难,但我们认为,从通常意义上理解,大师级人才,应指能够以独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开辟一个大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理论和研究方向并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发现的人才。有些人仅仅为了叙述的方便而把大师定为教授层次,①显然是不足取的。
对于大师的养成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问题,梅贻琦校长关于“大楼”与“大师”关系的定论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改革开放后高教界一再追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教育界没有培养出新的大师,针对此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鲁洁教授就提出教育要培养“帅才”、“大师”的问题。但为什么呼吁那么久仍然不见大师级人物出现,细细思考,我们发现,实质上大师是自然生成的,不可能通过大学教育培养出来。
首先,大师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他是多种因素际会、碰撞并达到最优化的结果。大师不是行政职务,它不能依级别的高低而定。一个人不会由于占据某个位子,拥有什么头衔,掌握多少资源就被人们称为大师。大师也不是技术职称,它不能通过量化的考核而成,不是学会多少种语言,写出多少篇论文或多少部著作就可以成为大师。大师还不是金钱可以堆积出来的,如果投资会产生大师,那么李嘉诚投向汕头大学的钱肯定早已产生出不同凡响的大师了。大师更不是自封的,不会因为自我玄虚或被自己的学生门人尊称为大师抑或通过媒体的炒作而就是大师。大师是公认的,是被学术共同体公认的。这个学术共同体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它不是自己私有的,而是属于全社会的。换句话说,真正的大师正是首先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才会被社会承认,进而被视为社会的财富。而且大师们注定要成为历史人物,他们不会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必将流芳百世,他们开创的基业必然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聪慧、坚韧、开创性、号召力、对事物未来发展的把握能力,诸如此类,都是构成大师的必备要素,但这些要素的堆积并不必然构成大师。换言之,大师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纯属偶然,是各种因素的际会、碰撞并达到结构最优化的产物,而且这种结果的出现并非刻意追求所能达到的。著名画家范曾当面问数学大师陈省身大师是如何产生的,陈省身回答说:“一半机遇,一半天赋。”范曾追问说:“努力其无用乎?”陈省身出人意料地回答:“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与成为大师关系不大的,成功和成为大师是两回事”,“大师是冒出来的”。②陈省身大师说得药中肯綮,成功与成为大师是两回事,成为大师需要许多条件,先天智能基础和学术潜质是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后天的社会条件与个人际遇是难以琢磨和把握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师是“冒”出来的。这一“冒”字颇值得玩味:它既意味着大师的出现不可能有一定之规,只要这些条件具备必然产生大师是不可想象的,也意味着大师的产生必然有很高的平台,众多高手共同追求某种理想过程中脱颖而出者才可能成为大师。
其次,大师也不是大学教育能培养出来的,不是凭借某种课程安排就可以训练出来的。无论人们怎样精心设计课程,怎样重金聘请名师执教,怎样在某个人身上重点投资,大师都不会因此必然出现。这是因为大师的养成有其更复杂的内在因素,并非外在条件具备便可成功造就。换言之,大师在“养”不在“培”。纵览大师的成长过程,似乎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人能知道如何做大师或培养大师,自古以来就有“只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的老师”的说法,没人知道自己的学生一定可以做状元,同样也没有哪个大学可以说能培养出大师。遥想当年杨振宁爬遍清华园里所有高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级人物。尽管目前人们对培养大师非常热衷,北京大学有“元培计划试验班”,清华大学有“诺贝尔班”(自称“基科班”),都是直奔“大师”而去的教学改革试验。这些试验还在试验中,断定其成功或者失败为时尚早。但常识告诉人们,大师不可能成批造就,北京大学把“元培计划”全面铺开的做法本质上仍然是一次教学改革而已,这种批量生产的模式与大师自身成长经验相差甚远。
第三,大师必须是聪明人专志于某领域长期耕耘的结果。大师必须是相当聪明的人才可为。人才成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师,都是在年轻时就成名于世的,不论世界级大师,如比尔·盖茨、牛顿、爱因斯坦,还是中国如数家珍的梁启超、郭沫若、鲁迅、胡适等诸多文化大师,他们成名都比较早,有“神童”之称的不在少数(爱因斯坦小时候愚笨的说法已被证实是错误的,相反他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而他26岁时的成果改变了世界物理学的面貌)。更有甚者,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汉代哲学家王弼,享年仅仅24岁,至今还有人在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开创时期著名教授刘师培享年36岁,仍被时人公认为国学大师。费尔兹奖被人们公认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明确限制获奖者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毫无疑问,聪慧、智力超群理应是大师的必备条件。但现实社会中,聪慧的人可以说海水斗量,如果按照心理学智力理论,人口中大约超过百分之一的人智力水平都可以算作天才,他们似乎都有成为大师的根基和希望,但真正能成为大师的可以说寥若晨星。这说明仅靠聪明还不足以成就大师,追溯大师成就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只有那些不辞劳苦在本专业领域内长期耕耘,做出过原创性贡献并为后人追捧,才能称得上大师。概言之,被称为大师者皆为某一领域的开创者或者里程碑似的核心人物,大师首先是专门领域的大师,甚至成为某领域的代名词,比如金岳霖乃至被称为“金逻辑”,显而易见,这是他本人在此领域长期耕耘并被人们广为认同的结果。
二、大师的特点及与大学教育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大师的成长过程恰恰是大师特点的形成过程。细考大师的特点,人们可以发现,先天遗传的聪慧仅仅是成为大师的潜在条件之一,大师的成长需要自身的勤奋努力,需要社会的呵护和支撑,更需要教育的正确引领与涵育。大师必须首先是某专门领域具有原创性的专家,敢于创新、勇于反思是他们的显著特点。他必须是在为了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崇高使命驱使下,基于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在反思与比较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人类的精神成果,原创性地开展某项工作并达到时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开创出相应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类知识宝库,引领了学术发展,成为人们自觉追随的目标与方向,从而成为人们公认的权威和大师。没有原创能力,没有学术上的重大发现和遥遥领先的创造成果,就不会被人们认同为大师。而这种原创性往往来自对传统的约定俗成的知识的挑战,来自敢为天下先的气度与胆识。在人们开始挑战权威的观点、挑战约定俗成的传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新知识的过程。与此相联系,大师们必须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仅仅学会了许多人情世故和为人为事的干练通达或者委曲求全,只能成为阿世之学的犬儒,不会成为大师。尽管奉行中庸之道和八面玲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不失为一种处世良策,但在学术研究中则很可能是平庸的同义语,相反,棱角突出、锋芒毕露和“不入俗流”则是从事原创性的学术研究的难得品质。正如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幼稚愚拙,在各种公众场合甚至连基本的礼仪都不懂并常常不修边幅的爱因斯坦,正是这种大智若愚成就了他作为科学奇才和伟人的品质。当然,大师还必须具备反思能力。任何一位学术大师都是具有这种反思精神的人,他们把反思人类自身及其精神成果看成是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反思是在独立、自由之思想支持下自由的思考,而且这种批判性反思的目的不是抛弃和中断既往学术,而是为了学术的继承、扬弃与发展。在他们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批判中,许多新思想、新理论不断被创造出来。大师们的这种原创意识和反思精神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而他们的努力与成功恰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他们开创的基业成为后人学习、模仿、领悟与再创造的基础,他们的薪火必须有人继承与发扬。
其次,大师还必须具备为学术而学术的献身精神。“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在中国学界似乎长期不受重视,相反“学以致用”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导观念,也是今天在学术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核心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首选。“如果你们的研究不能回答和解决时代的问题,那么时代要你们干什么?”这样的质疑在当今社会仍然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但是学术研究真的都能够对现实有用吗?学术研究真的都能够解决时代的问题吗?尤其是类如在课题申报过程中必须注明的解决那些所谓“具有前瞻性、重大性、迫切性”的问题吗?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律,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有自己独特的适用范围。如果人们不能遵循学术自身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反而受到非学术的干扰,纯粹围绕意识形态进行学术研究,自觉成为犬儒主义者,把学术仅仅用作敲门砖或“屠龙术”,那么再聪明的人也不会成为大师的。相反,如果把科学理解成只是为了人类天性中的那份好奇心,至于科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那只是副产品而已。那么,他与大师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进而言之,欲成为大师,必须把自己的志趣、爱好与自己的专业知识融为一体,真正成为以学术为生命的、至少是把学术放在首位的人。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说明了大师与学术的关系:在金岳霖身边待过的人都知道,在被问到为什么对逻辑感兴趣的时候,他说“好玩”。这个回答出乎常人意料之外,任谁都知道逻辑学是多么枯燥乏味,但通过金岳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把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看作“玩”,看作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所在,这不就是抛弃了一切功利思想的最直观表达吗?这里的“玩”表达了金岳霖的一种学术态度,也体现了他的一种学术观念。我们可以羡慕金岳霖没有专著就能当上教授,生活条件优越,不用申请项目,不为做课题所累,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每五年还可以有一次带薪休假。也许这促成了他那种“玩”的学术观念。但是谁都知道,他的《知识论》一书写了两遍。这是因为他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把刚刚写成的六七十万字的书稿丢失了。金岳霖的态度是“得重写”。既然是“玩”,就得继续,这是终其一生的事情。③学术是纯粹的,自然必须以纯粹的态度对待它。1952年以色列政府准备请爱因斯坦做总统,被他登报拒绝,他的名言就是:“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能在浮躁的社会中保持这一种纯粹的心态,也是大师成长的必备条件。反观中国社会及教育现实,人们无不赞同黄全愈博士在《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中国教育过于功利化,太缺乏对学生兴趣与好奇心的重视、欣赏与发扬了。中国大学教育的这种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功利至上的培养目标、空泛陈旧的教学内容、整齐划一的培养方式、僵化保守的评价体系都是扼杀大师成长的罪魁祸首。
第三,大师必须是具备着广博的知识,而且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师典型应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出将入相,博古通今,博闻强记,引经据典,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人物;他们的文章必须有文采,其作品应有广泛的读者群,他们开创的领域必须有人继续挖掘,甚至还要兼通中外——尽管时代的发展已经使这些要求难以企及——但文人就应该有文人的气度仍然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大师的形象,甚至成为社会的自发要求。“要像李白、杜甫,而不是萧何、曹参;要像苏东坡,至少也要像王安石。”④尽管按照马科斯·韦伯的社会分工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会分化得越来越细致,知识分子随之分化也成为必然,而只有更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才会对人类知识的创新与积累起根本性作用,他们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更大。但在当今中国社会,最容易获得激赏的实际上并不是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往往被称为专家而非大师。人们通常不会欣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比较纯粹的哲学家,而更欣赏的是罗素那样的有哲学家声望的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家。人们希望也需要大师们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发展乃至个人生活指点迷津。同样,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即是渴望经世济民、兼济天下。尽管他们似乎也接受个人自由主义,并强调独立的学术品格,但他们的自由之精神受制于他们的理想,他们骨子里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或多或少地都必须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姿态。换句冒昧的话说,大师往往是“学有专攻”的“杂家”,他们正是依据自身的学业专长对大众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批判与分析,从而引领人们能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此问题,或者能把自身研究的学术领域发展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从而把本研究、本学科带到一个新境界。所有这些都需要大师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此乃大师之为大,也是人们常说的“帅才”与“将才”的区别所在。
更深言之,目前关于培养大师的呼声似乎成为一种焦灼的社会心态,特别是在当今资讯发达、社会浮躁、而人们却普遍缺乏信仰的境况下,对大师的渴求显然是一种信仰的异动,并非社会良性运行的体现。因为从本质上说,社会的发展靠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而非零星大师的推动。就大学教育而言,尽管人们在大师问题上对大学寄予厚望,一方面想让大学教师成为大师,另一方面,想通过大学教育培养大师。但实际上,大学里更多的教师是没有可能成为大师的,对于绝大多数大学教师来说大学是他们谋取生存、发展的职场。大学的管理者如果把眼睛紧紧盯在有可能成为大师的少数人身上,而且集权式的官僚管理体制不作彻底改变的话,只能造成更多的学阀学霸而不会成就大师。当然,人们也承认,如果大学课堂不仅只是传授教科书里的内容,还能融入最新的学科成果,能激发学生对自己所教授知识、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引导学生掌握自己所教授内容的方法,诱导学生对所学知识内容进行反思、质疑,培养学生主动的科学探索精神,从而使本身不是大师的教师也可能培养出未来成为大师的学生。但这一切很难量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出优劣评价,相反把大师作为大学的培养目标本身就值得怀疑。因此,无论大学的管理者还是普通教师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更多的学生是永远成不了大师的,但他们也有权利在大学里学到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掌握更多将来生存与发展的技能,他们才是大学教育的主体。成就大师毕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而当下问题的解决才是众多学子关心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师的成长毕竟是一自发自为的过程,聪明的头脑,批判和创新精神、同行间深入的切磋交流、广泛的社会交往,诸如此类因素,与大学自身关系并不特别密切。而大学所能做的仅仅是提供知识资金储备和前人经验,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创造的社会软环境,克服社会的浮躁、管理的僵化、评价体系的扭曲及短视倾向等阻碍性因素。而至于大师何时何地及以何种方式出现,那不是大学所能或应当追求的!
注释:
①罗永忠:《大学之大:何以为大?》,《教育科学》,2005年第5期。
②范曾:《何期执手成长别》,《散文·海外版》,2006年第5期。
③王路:《大师的传统》,《博览群书》,2006年第8期。
④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构建》,《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