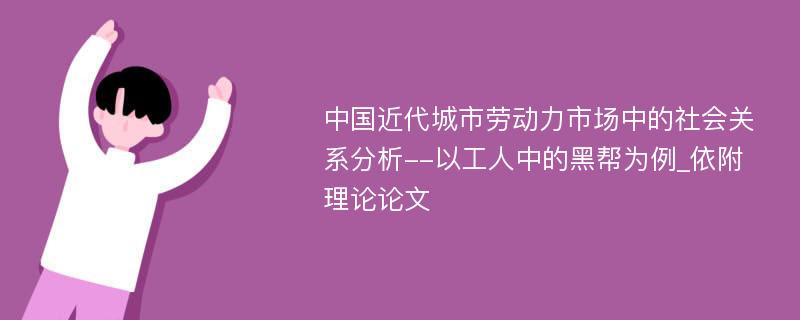
中国近代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辨析——以工人中的帮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帮派论文,为例论文,社会关系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城市工人中存在着严重的帮派问题,以往我们总是把这种现象归结于封建残余的影响。如果仅仅是这样,为什么越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城市(如上海),旧式帮派的活动反而越猖獗呢?越是在被认为革命性最坚决的下层工人阶级(如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工厂中的粗工等)中间,加入帮派的人数反而越多、互相械斗的频率越高呢?笔者不揣谫陋,从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这一角度对工人中的帮派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期方家指正。
(一)
在近代中国,人们大多认为:工商业、国际贸易和交通运输特别发达的通都大埠,各种帮派势力就特别容易获得发展(注:姚士馨:《解放前的天津“地道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15页。)。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都市,帮派问题也最为严重。曾在上海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认为:“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注: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20世纪30 年代初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的朱学范指出,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解放前,上海的在业工人最多,失业工人最多,入帮会的工人也最多(注: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据中共地下党员顾准等人在抗战爆发前后调查提供的上海工业工人资料,煤气工业中,工人主要有关帝会、同乡会、宁波帮、江北帮、无锡帮等团体(注: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 页。);英商公共电车业中,帮派势力较大的为苏北帮,在机务部则为宁波帮,而机务与车务两部工人的冲突和成见,始终难以消除,“这种成见之不能立即消除与帮派问题也不无相当关系。”(注: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页。)法商水电业中, 职员主要拜杜月笙等人为老头子(注: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邮电部门中,职员中有所谓的“十二弟兄”, 后扩大为“三十六弟兄”,再扩大到一百个,“局中人几有不入X门即入X门,否则不能存在之势。”(注: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页。)福新面粉厂中, 湖北帮与无锡帮势力最大,各帮工人彼此对立,互相轻视,湖北帮几乎全部加入了洪帮,拜码头工头为大哥,无锡人加入青帮最多,拜吕海山为师。阜丰面粉厂中,安徽人最多,其次为湖北人,许多人加入了青帮,拜中央捕房的一个包打听为师(注: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5页。)。在新关码头,工人有青口帮、太古帮、 天津帮之分,他们轮流在五号、六号码头作工(注: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页。)。 工部局工人大致分为4帮:本地帮、山东帮、江北帮、安徽帮, 他们普遍拜老头子、拜先生、拜把弟兄(注: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7页。)。
各地工人中,社会地位较高的职工加入帮会的比重远远低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人加入帮会的比重。在上海,地位较高的邮局职工中加入帮会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20%(注: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力车夫, 拜老头子的人数综计约占总人数的90%;上海棉纺工人中,“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拜有老头子。”(注:朱帮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7页。)在上海造船厂,“工人无团体的组织, 惟有所谓宁帮、广帮、无锡帮者;……据云,凡欲入各帮之同业者,必须经各帮之认可,方能从事经营;否则必受排挤,甚至工钱之多少,亦受各帮之规定。”(注: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 卷第6号,1920年5月1 日出版。)码头工人则几乎百分之百加入了帮会,上海所有码头都被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范回春的徒子徒孙控制着,成为码头上的包工头(大包头、二包头、三包头等),每人手里控制着成百上千的装卸工,形成浦东、山东、苏北等不同帮口。上海有句俗谚:“好人不吃码头饭,要吃码头饭,就得拜个老头子。”(注: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帮会在下层工人中的活动同样非常活跃。早期南京的帮会首领多来自漕运水手以及码头工人中的把头(注:姚士馨:《解放前的天津“地道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 219页。)。曾为江苏省会的镇江,是青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清末民初有所谓上中下“八洞神仙”、新老“十二属”的青帮人物,开始时,他们主要在江边码头、火车站吸收水手和工人入帮(注:姚士馨:《解放前的天津“地道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19—220页。)。在安徽芜湖,各码头统统被各帮各派的工人占据,“凡米粮之经过任何码头上下,皆必须经盘据该码头之工人搬运。……他人不得侵犯。因此,故常有争夺码头之事发生,即俗称所谓‘打码头’。”(注: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委托研究:《芜湖米市调查》,社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编,第45页。)
中国近代城市工人加入帮会的普遍性,说明这种现象绝不是某种势力的残余影响,而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反映了中国近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并从中折射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一般认为,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对工人阶级而言,地位越低下,革命性就越彻底。但为什么他们又与帮会联系在一起呢?
从表面上看,工人加入帮会基于下列原因:
第一,工人加入帮会是由于就业竞争所致。
20世纪初,中国人口过剩问题已十分严重。在华北,连当挖煤工也要托关系、走门路。据对开滦煤矿工人的调查,“煤夫分内工外工,内工为入坑从事作业的长工,……一般工人若无相当的牵引,不容易当内工。但有紧急情形,则非提供相当的运动费用与工头不可。”(注:宫协贤之介:《华北农村社会民隐裸记》, 《中国农工》(季刊)第1期,1935年10月出版,第139页。)1932年,上海邮局招考68名信差, 报名者达2400人之多;1936年,招收50名乙等邮务员,报名者达3000人(注: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无业工人的巨大压力,使每一个就业位置都显得极为珍贵,有力有势之人乘机垄断就业市场。在上海,福新各部门的工人都由工头分别统治,工头是哪里人,工人也是哪里人,形成帮派,工人要拜“老头子”才能做工(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5页。)。在上海邮局中,“ 信差中的劳逸程度相差很大,有些人为了在职务分工上能派到轻松的位置,或者在经济上盼求工资晋级快一些(……),需要有人支持说话,还有少数人想捞点外快,因而加入帮会。”(注: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 175页。)在上海码头,背包小工,每背一包,至多只有20文工钱,但却要捐出一文半,作为“公款”,“以备对待〔付〕外来野鸡工人,和抵抗外侮的〔费〕用哩。”(注:全汉:《中国苦力帮之史的考察》,《中国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出版。)
第二,工人加入帮会是社会治安不良所致。
工人为争抢生意,争夺就业位置而进行殊死拼斗的事例屡见不鲜。只要翻一翻当时具有社会感的报刊,这类报道就随处可见,如1924 年4月6日,黄包车夫戴双喜、戴月恩、左金芝等人, 在上海西门外斜桥因争夺生意而发生械斗(注:《黄包车夫争夺生意斗殴》,《申报》1924年4月7日第4张,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01册,第144页。)。1926年10月底,塌车车夫苏锦裕、张文发、胡华英等数人, 在上海杨树浦路,被同业数十人拦住殴打(注:《塌车夫被人殴打》,《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83册, 第11页。)。至于为争做工头发生械斗之事则更是司空见惯,如无业游民窦大麻子为与徐有才争夺上海泉安轮船公司工头一职,经常纠众上船骚扰,动辄将人打伤(注:《争充小工头目之冲突》,《申报》1924年4月2日第4 张,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01册,第35页。)。
上海纺织业中,更有青帮组成的“共进党”,“专门拿敲诈吓恐的手段,实行盗匪的行为”(注: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想在码头上立足,没有帮会作靠山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邮局工作的职工为了寻求靠山也加入帮会,外勤工人,如“投递信件和往码头运送邮袋的信差、差役等,还有个保障人身安全的问题,更需要有人撑腰。”(注: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恶劣的社会治安, 使工人们毫无安全感,那些孤身一人在城市工作的工人,有时真是寸步难行,动辄招灾,上海某纱厂的摇纱间,由于工头是宁波人,这个车间里的工人大部分也是宁波人,而其他地区的工人常常被宁波人欺负,“甚救〔至〕挥拳踢脚打得不死不活的;那少数的人,那里敌得过多数,自然忍辱受苦,哑口无言了。”(注: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这就迫使工人们不得不加入帮会,希望以此保障自己的利益。
第三,工人加入帮会系出于互助动机。
近代城市工人不但随时受人欺凌,随时有性命之忧,更随时有失业的危险。在上海,工人“新进厂学习工作,必须有奥援。……假使这位新进厂学习的候补工人,有他的亲戚,或者素来和好的邻伴在里面照应,这便没甚苦头吃。若是那么浑(通常译为‘拿摩温’——作者注)或宕管等,做他的奥援,那是更便宜了;虽然手脚粗笨做不来什么一样,却随着老熟手支付十足的工资。若是没有奥援的,进厂学习,那就苦了。往往听得有人进厂,学习了三四个月,依然没有半点儿酬劳,倒白白辛勤工作,帮助那么浑多添了如许进款。”(注: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某纱厂中,有位总管的女儿也到厂里做工,这位“奥援”自然很硬,“工人队里没有一个敢怠慢他〔她,下同〕,没有一个不恭维他,他的头寸,本来大了;他的脾气,也特别的了不得,别人家上工很早,都是六点钟到厂,这位老总管的千金小姐,每天要工人队里派人去,千呼万唤巴结他。他每天迟迟的到了八点钟敲过,方才到厂。”相反,另外一位没有奥援的工人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一位如皋籍工人,到上海一家纱厂做工,“别人都是贪吃懒做,偷闲来到寄宿舍去假生病,他独是一个勤勤学习。有一个机匠看见他这个样子,心中大大的妒忌,……有一天那机匠又来无端寻衅了。欺某志士是不能语上海话,有意和他攀谈,不问情由,就伸手来拿在某志士的脸上批了几下,下这毒手来羞辱他。”(注: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还有一种“存工”制度,就是工厂往往要把工人两个星期左右的工资存在厂中,作为押金,以防工人随意跳槽,但工人离厂时,这部分押金往往被工头或经管人克扣掉(注: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 日出版。)。可见,没有依附的工人, 在工厂中做工是多么的艰难。
几乎所有的帮会都带有原始的平等色彩,讲究互助互济,如青帮帮规“十不准”中规定“不准欺软凌弱”,“按祖师传道宗旨,应救济孤寡残疾、扶持弱小贫困,才是道义,凡在帮的人,绝对不准以威临人、以势欺人、以力压人,应抱有英雄豪杰之心扶持正义救济贫苦扶弱制强方是丈夫。”(注:陈国屏:《清门考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68页。)“十要”中则规定“济老怜贫”, 要求青帮徒众“帮丧、助婚、济老、怜贫、救困、扶危,……遇有三灾八难,必须竭力相助。”(注:陈国屏:《清门考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75—176页。)这些帮规对于渴望得到帮助和保护的工人,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朱学范所说的那样:工人“职业无保障,被中外资本家随意压迫、剥削的情况,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有的连人身安全也无保障,被人欺凌蹂躏,于是不得不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入帮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注: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1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如凡是到上海做修脚生意的人,都是捐10 块大洋给修脚业公所,作为入帮费,如果不交这笔钱,私自做工,被帮内的人发现,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一当工人加入公所, 便可享受到帮内的4项优惠:(一)享受帮内规定的统一修脚费;(二)生病时,由帮内供给医药;(三)如果失业,可以向帮内借贷,找到工作后,再分期偿还;(四)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帮内会餐一次(注: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 日出版。)。
工人加入帮会的普遍性,反映了中国近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以及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性格特征,说明即使在现代经济最发达的都市,真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形成,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并不成熟。
马克思认为,在真正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以中国近代城市劳动力市场与马克思的论述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要远远强于以法律表现的契约关系,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不完全符合商品交换规律,他们的劳动、自由、甚至生命都被别人所支配,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天赋人权的乐园”,这里还太多地保留了旧的制度。列宁指出:“陈旧的制度和充满等级性的土地制度无论在农业或工业中都会产生最有害的影响,都会保持着技术上落后的生产形式,这种形式是同奴役和人身依附的极为盛行相联系的,是同劳动人民最艰难最孤立无援的地位相联系的。”(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3页。)归根到底,工人普遍加入帮会的现象,说明中国近代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还没有确立。
(二)
马克思认为自由工人产生的前提,“既是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土地的主人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同样也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的解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4—505页。)。工人不得不加入帮会,反映了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形式的保护关系并没有完全解体。
一般说来,人身依附“是在缺乏发达的交换经济的条件下人的个性不成熟以及个人对狭隘群体的依附”(注: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造成的,但为什么越是现代经济发达的上海等地, 工人加入帮会的现象越普遍呢?
吴承明先生认为,社会发展并不总是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进行的,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可以超越的(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我们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是可以超越的,但人的社会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超越的。就上海而言,这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前提并不是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和保护关系的解体,因而当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后,反而从经济上为各种帮会提供了保障,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和保护关系以改变了的形式,从现代经济的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附着于现代经济的毒瘤。
过去我们多把人身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人身依附已被排除,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列宁写道:“资本主义排挤了人身依附的形式,这些人身依附的形式是以前经济制度的不可缺少的附属物。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尖锐,因为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在我国不仅曾经存在(一部分现在还继续存在)于农业中,并且还存在于加工工业(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采矿工业及渔业中等等。”(注:《列宁全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8—549页。)中国近代的人身依附更以变种的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并不以对财产的依附为前提。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既表现为工人对帮会的依附,也表现为资本家对帮会的依附,同时还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依附。在上海码头上的包工头,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他们,“如果得罪了,轻则受辱,重则送命。”近代经营过码头事业的刘念智回忆:“我父亲(即刘鸿生——笔者注)当时已经是十来个企业的老板,已经是千百万富翁的身价,已经是宁波同乡会的会长和公共租界的华董,而且是国营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在上海资本家中,他已经是数一数二的闻人。然而在十里洋场中,还得让杜月笙称王称霸。父亲和他称兄道弟,曲意奉迎,在我想来,这是难以理解的。”(注: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杜月笙称刘念智一声“四兄”,竟让刘鸿生深感得意,并使得刘念智在黑帮横行的码头上站住了脚跟(注: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9页。)。在芜湖,带有黑帮色彩的“闲荡阶级”,更多是向米业资本家进行“揩油敲诈”,“米商屡有倡言改革,惟因若辈积习已久,已成根深蒂固,势力极大,对倡言改革者,即不惜以死力对付,欲加纠正,实非易事。”(注: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委托研究:《芜湖米市调查》, 社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编,第48页。)
秦晖教授认为:“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人的不成熟,即个人必须依附于共同体。”(注: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我们认为, 这个看法符合中国的实际,并可以用来解释上海等地工人普遍加入帮会的现象。尽管上海等地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形式上已非常发达,但工人个人并不成熟,无法离开帮会等“共同体”的保护。可见,只要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以财产分化作为阶级形成前提的条件没有普遍建立、以权势分化作为阶级形成的社会基础并未真正地崩溃,人身依附就不可避免。那种认为不经过大机器工业的洗礼,只要是一无所有的工人就肯定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和无与伦比的进步性、肯定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工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于大机器工业为他们造就了“较高的识字程度,高得多的需求水平和生活水平,他们同那些‘愚昧的’‘乡下佬’的迥然不同”(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1页。)。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中国越是层次较高的工人参加帮会的比例越低,而越是下层的工人加入帮会比例越高的原因。
有人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最为深重。把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并列,这种看法有失公允。在中国近代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甚至是一种特权,而不是“边沁”。荣德生写道:“余以为创办工业,积德胜于善举。慈善机关周恤贫困,尚是消极救济,不如积极办厂兴业。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兴旺。”(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江南大学1990年打印本,“1944年纪事”、“1948年纪事”。)工人到了他的企业做工,就等于受到了救济。他说:“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经常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本人是以事业作为救济。”(注:《荣德生谈被绑真相》,无锡《人报》1946年6月 13日。)正因为工作是一种特权,工人们不是想方设法不进入资本主义企业工作、不受资本家“剥削”,而是不择手段地寻求工作的机遇,甚至强行“请求”资本家“剥削”。荣德生在抗战后写道:“茂一(即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笔者注)复业后,……复有一班无赖之辈依藉背景,要求入厂工作,不顾正理,一味胡搞,无法应付。”(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江南大学1990年打印本,“1944年纪事”、“1948年纪事”。)
由于中国近代的人身依附不是以对财产依附为前提,因而,用消灭有产者的方法来排除人身依附,只能是以油灭火。列宁在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快慢问题时指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的,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并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注:《列宁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0页。)近代中国与俄国相比,残存的旧制度更多, 中国工人阶级更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必然造成新的社会阶级,“这些阶级根据需要而竭力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并积极参加国家和全世界整个经济(而且不只是经济)生活。”(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1页。)
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工人需求水平的提高,随着中国与整个世界市场的接轨,中国近代工人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必然被缓慢地排挤掉。列宁指出:“大机器工业与以前各种工业形式不同的一些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为巨大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生产,在购买原料及辅助材料上同国内各区域及各个国家的密切的商业联系的发展,巨大的技术进步,庞大的企业所造成的生产与人口的集中,宗法式生活的陈腐传统的被破坏,人口流动的形成,工人的需要与发展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使国内生产日益社会化,同时也使生产参加者日益社会化的资本主义过程的因素。”(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2页。)
因此,用暴力手段来推翻一个阶级的统治、解除那种以对财产依附为前提的人身依附是可行的,但暴力并不能彻底解除那种以对权势依附为前提的人身依附,即使消灭了资产阶级,也无法真正打碎工人身上的人身依附的枷锁,因为暴力不可能使工人的需求水平、文明程度、生活状况以及劳动的社会化进程得以大幅度提高,只有现代大工业的不断发展才能做到这一点。
标签:依附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新青年论文; 列宁全集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