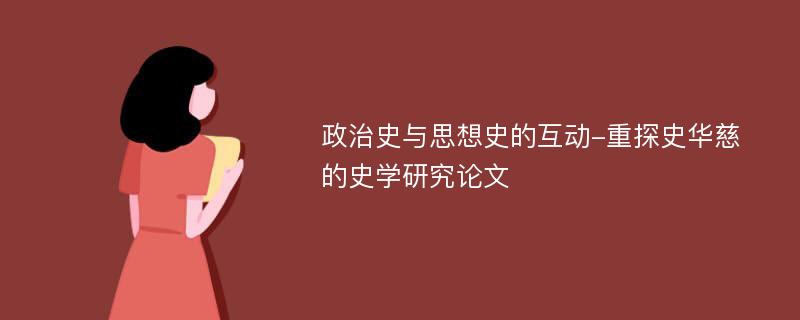
政治史与思想史的互动
——重探史华慈的史学研究
王 鸿
摘 要: 关于史华慈所从事的史学研究,一般认为有一个由政治史转向思想史的过程。但这种认识所带来的结果,是将其史学研究分为两橛,专就各自内在的研究理路进行探讨。事实上,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后来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路和叙述风格,而其思想史研究则进一步打开了政治史研究中提出的核心问题面向。史华慈这种打通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值得反思与借鉴。
关键词: 史华慈;政治史;思想史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是少有的成功横跨政治史与思想史,并在这两个领域均留下经典著作的学者。对史华慈史学思想钻研颇深的林同奇在《他给我们留下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一文中,便曾对史氏留下的著作作了这样的三类划分:“第一类属于中国现实政治研究,可称时论,多已收入两本自选论文集:《共产主义和中国:流动中的意识形态》(1968年)和《中国及其他问题》(1966年)。这类著作多半记录了他跟踪中国现实政治发展达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第二类属于中国政治史研究,即《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年),是由史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是他的成名之作。第三类属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包括《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年)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年)。”① 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载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55-256页。 林同奇的这个划分,大致反映了学界关于史华慈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认识,即除开那些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著作,他的史学研究便是发端于政治史研究,并在此后由政治史转向思想史。
基于史华慈的这种研究取向,诸多关于史氏史学思想的研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其政治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分为两橛,专就各自内在的研究理路进行探讨。② 由许纪霖等人编辑整理的两本海内外学者关于史华慈研究的主要文集来看,这种趋向是明显的。即使有学者注意到史华慈在探讨现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传统中国思想之间的联结(如萧延中的《史华慈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卢梭、孟子与毛泽东》、裴宜理的《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从孟子到毛泽东延至现在》),但是所处理的也仅仅是枝节性的内容,并未认识到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在总体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上的延续性。相关研究论文参见许纪霖、朱政惠编:《史华慈与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237-476页。 然而,史华慈的著作真的存在这种此疆彼界的严格划分吗?在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方法论层面的互动?进一步而言,我们能否在史华慈的研究转向背后,找到其史学研究理路上的延续性?
本文不免于冒险地认为开启了史华慈思想史研究特色的著作,并不在于被视为比较思想史典范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而在于被视为政治史经典著作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③ 史华慈的主要史学著作基本都已有中文版本,不过这些中文版本对于史华慈的独特表达方式,往往存在着误读的层面(如《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又或者是存在部分删节的情况(如《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因而本文对于史氏主要著作的探讨,以英文版为主,中文版为辅。 本文认为,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被提出的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构成了理解史华慈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关键所在:“一个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性运动,可以偏离原先的基本预设多远而仍保留其性质?”(另一种表达为:“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史华慈这一尚未被充分发掘的面向,为我们重新理解他的研究理路提供了新的视野,也对当前的思想史研究的“再出发”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启发。
一、作为“思想史著作”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在探讨史华慈在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转向时,林同奇指出:“驱使史氏在千门万户的中国文化中选择政治史和思想史作为终生研究内容,是出于他对‘人的有意识生活’的强烈兴趣和关注,是他探索‘人的全部复杂性’的志业无形之中所决定的。人的有意识生活在此可理解为由意识、处境和行动三者之间的‘三角互动’所交织而成的有血有肉的网的网络。它是政治史和思想史共同关注的领域。”而史华慈所从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区别在于:“如果说思想史侧重人的内心世界和真理宣称(truth claim),较多从思想层面入手,政治史则侧重政治决策、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较多从行动层面人手。”① 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第264页。
林同奇的上述论断,源自史华慈在《为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简单辩护》一文中对于其所从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反省。史华慈本人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这个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历史时,我发现我一直关注两个领域的研究——政治史和思想史。”② 史华慈:《为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简单辩护》,载王中江编:《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同时,史华慈也自省道:“当我反思隐藏在这两个领域背后究竟有什么公约数时,才发现它们都是涉及人的有意识活动的领域,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和他所遇到的处境之间,以及他和他在此处境中所采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③ 关于史华慈的这段话,此处采用的是林同奇的翻译。见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第264页。另有译为:“这两方面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思考构成这两个领域的共同基础时,我意识到它们都离不开人类自觉的意识活动,离不开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所做的有意识反应,离不开人类在特定环境中的自觉行为。”(史华慈:《为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简单辩护》,第108页) 从这个论述以及该篇文章整体来看,与其说史华慈强调的是对自身所从事的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严格区分,倒不如说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林同奇所归纳的“意识”“处境”和“行动”三者,不仅是史华慈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政治史研究的基座。因而,与其将《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定义为政治史著作,将《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视为思想史著作,更具刺激性的视角,倒不如从思想史视角看待前者,而从政治史视角看待后者。① 本文由于篇幅和关注点所限,只试着从思想史视角看待《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其实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不少内容是探讨思想家对于政治的看法。
当然,史华慈不是思想决定论或意识形态决定论者,他在该书中认为:“主义并非处于真空之中,而是受到活生生的人的形塑和扭曲,在具体情境中运作,并因各类动机而显得有生命力。”⑤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2.特别是在处理中共的历史中,除了主义的内部冲突外,党的领导人所处的情境也对于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党的领导人思想的关注,离不开对于他们个人的志向(ambitions)和抱负(aspirations)的探讨① 参见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4。,甚至某些时刻个人的性情也会影响思想的演变(比如书中提到瞿秋白的内向怯懦和李立三的野心勃勃)。
如果从史华慈所指出的此一恼人的问题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所处理的问题,固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毛泽东从中共权力边缘走向权力中心的历史,但是通观全书,更为深刻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想传统(书中主要提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托洛斯基的经典论述)如何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同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几位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等人)又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迎合、适应、抗拒这套思想传统,并从而产生出一套处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想传统中、但同时又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共产主义理念。[在该书中,具体表现为史华慈所谓的“毛主义”(Maoist)]可以说,在这个处理中,一个原本是政治史的命题被悄然转变成了从一个普遍问题出发的思想史命题。
初读史华慈的著作,我们往往既容易被他的旁征博引所吸引,也容易被他的“随意”联系所迷糊。在他的论述中,可能此处还在谈孔子,彼处便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毛泽东未谈完,卢梭便上场;一边比较着严复与朱熹、王阳明,另一边似乎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候场。孔飞力便坦言:“史华慈好像是在受到震惊的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组织整理他的讲演,他让他的思想在他心灵的超级链接之中自由地发展,于是他或许以毛泽东开头(在表述了很多从句之后),以迈蒙尼德(Maimonides)结束。这也许是一个夸张,但绝不过分。”① 孔飞力:《史华慈的历史贡献》,第551页。 问题在于,如果说史华慈如上节所言注重从思想体系中行文,注重那些“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理论不断诠释的历史,那么何以他会如此“不着调”地将处于不同历史情境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思想家放到同一个台面探讨呢?
此处勾勒《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关于工人阶级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的分析,并非是为了分析这一具体问题(其实有着远为复杂的面向),而是为了以此管中窥豹,指出史华慈这本“政治史”著作所蕴含的浓郁的思想史气息。如前文所指出的,史华慈眼中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实际上背后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关注点,即此前所指出的“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关注点促使他对中共早期历史的理解,并不是被客观历史环境决定了的社会科学式的理解,而是追问“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③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reface(to the 1958 printing),p.ix.。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是流俗理解的一套空洞价值宣称,而是充满内在张力。只有把握主义的细微之处(details of doctrine),才能促使我们看到主义的哪些部分已经消亡,哪些部分仍然充满活力。④ 参见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4。
他逃出保卫科,去大兴安岭前,不认识杨琳一家,他从大兴安岭回来,才知道欧阳橘红不在厂里了,才知道杨琳是欧阳橘红的救命恩人。他算了算时间,华安调回吉林的第二年,欧阳橘红就调到南京去了。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潜藏的思想史倾向,孔飞力有一个颇为敏锐的观察。他指出,这本著作虽然在当时是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著作,但是其中也“还隐藏着史华慈的信念,即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思想观念,而且把它们牢固地搁置于行动的语境之中加以思考;并且,在评价特殊的思想观念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们还有更为宽广的文化与思想的背景”② 孔飞力:《史华慈的历史贡献》,载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550页。 。孔飞力的观察显然并非无的放矢,史华慈本人在回应费理察的批评时便指出,在写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那时以及此后,他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③ 史华慈:《再谈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一个答复》,载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167页。 而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则是以下述的方式表达:“一个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性运动,可以偏离原先的基本预设多远而仍保留其性质?”④ 原文为:“How far can a historic movement,based on certain beliefs,drift from basic original premises and still maintain its identity?”(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201)对于这个问题,史华慈认为“是一个痛苦但是重要的问题,不管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儒教、基督教,还是任何其他信仰体系。一种理论或信仰的命运同下面这一问题有关:人怎样能够既追求真理又文过饰非?或者,一种思想怎样能同其他思想相混而仍继续发挥作用?在我看来,创始人的理论在后来的遭遇,可能不仅反映了后继者所作的曲篇,而且也反映了创始人自己的局限性和盲点”① 史华慈:《再谈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一个答复》,第167页。 。
因而,从《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到《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史华慈逆向溯源,持续关注着“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命题。在这种总体上相似的关注点下,我们可以看到史华慈在分析论述上呈现了诸多连贯的方法,这些方法论部分体现在他对一些词语别有用意的使用。
结果表明,研究2组与对照2组化疗性静脉炎治疗有效率差异有显著性,喜辽妥与湿润烧伤膏局部交替外敷治疗化疗性静脉炎效果显著。
不过,虽然对于思想的实际作用作了如此严格的限制,但是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史华慈此后的一些思想史分析手法已经形成。特别是考察中共历史背后的重要立足点,即“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命题,在此后的著作中不断地重复出现。
二、不断深化的研究
若是按当下的学科方向划分,史华慈的三本主要著作实则横跨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相当有意思的是,史华慈的研究不是正向递推,而是逆向溯源,研究对象从最初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到后来的清末民初的严复,再到先秦诸子。按照林同奇先生的理解,这种逆向溯源,一方面是“出于思想史家通常都有的追寻思想谱系的癖好”,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出于史所特有的对于问题意识的追问”。② 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第273页。 这种理解相当中肯。但若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史华慈的这种逆向溯源,是否也意味着这几部著作之间存在着某种延续性呢?
事实上,若是细致阅读史华慈的这三本主要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延续性,而这种方法论上的延续性与《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隐藏着的“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普遍性命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说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关注马克思、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等人开创和延续的共产主义理论传统在被中国共产党接受后出现的调整和创新的状况,那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则关注的是西方18—19世纪开创的启蒙思想与反启蒙思想,在被严复这位仍然带有中国传统视角的知识分子接受后的误读和创造性诠释的状况;至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则关注的是发源于新石器时期、在商周发展的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至汉代早期被孔子、墨子、老庄、孟荀、法家、阴阳家等思想家多元诠释的状况。① 林同奇指出:“在先秦诸子中,史氏似乎独钟孔孟。他对墨子之为功利主义,法家之为行为科学,老庄之为神秘主义,乃至荀子之徘徊于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之间皆有不满与批评。唯独对孔孟,特别是孔子,则几无微词。”(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第286页)但这种理解似乎与史华慈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的分析不相吻合,史华慈可能源于特定原因欣赏孔孟,花了最大篇幅论述孔子的思想,但是他在书中的分析基本上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倾向性,或者说他在此书中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褒扬儒家,而是为了整体分析先秦诸子基于共同的文化导向所提出的不同的理解。
这种在“意识”和“处境”“行动”之间此重彼轻的差别,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得到进一步深化。虽然史华慈在分析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等人的思想时,也时常提及他们各自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这种时代背景对于他们的思想产生的影响① 比如在分析孔子《论语》的思想时,史华慈会分析春秋时代周文明礼崩乐坏的情况对孔子可能存在的影响。在分析墨子对儒家的挑战时,会提及商人阶层的兴起、士阶层的分化、对周文明不再向往等时代背景。在提及道家中的分支“黄老之学”时,会提及争霸的时代氛围如何刺激了原本讲求“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的变化。参见Benjamin 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Belknap Press,1985,pp.56-61,134-138,237-254。,但是,总体上,这些分析言简意赅,对于思想人物的外在处境往往作简单处理。一方面,这当然是考虑到先秦诸子所处时代的模糊性,甚至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本身就存在诸多的学术争议,比如孔子在先、还是老子在前等问题。② 史华慈在书中采取的是孔子在前、老子在后的观点,这被他认为具有冒险性,但这种冒险又不可避免。参见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15。史华慈的这一简单做法受到朱维铮的批评。参见朱维铮:《史华慈的“思想世界”》,载许纪霖、朱政惠编:《史华慈与中国》,第36-61页。另一方面,这可能也与史华慈更着意于对思想内在魅力的考察有关系。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就缠绕史华慈的“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关注命题,仍然隐含在这部关于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只不过被改头换面式地置于对在商周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教义的分析上,具体则体现在对孔子、墨子、老庄、孟荀、法家、阴阳家等思想家的多元诠释中。总体上看,孔子的思想被视为提供了“人文主义”(humanism)的诠释方案,其中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面向提供了对孔子“人文主义”的别样诠释;墨子的思想被视为是对孔子思想的挑战,提供了“功利主义”(utilitarian)的诠释方案;道家分老子、庄子与黄老之学,总体上是“神秘主义”(mysticism)的诠释方案;法家则提供了一套“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诠释方案;阴阳家则提供的是一套“相关性宇宙”(correlative cosmology),被后来的董仲舒等人纳入儒家体系中。这些诠释方案,用史华慈的用语,是先秦诸子针对总体的中国文化导向(culture orientation)提供的不同的通见(version① 林同奇译为“理想远景”。参见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第276页。 )。这些通见在新石器到商周时期,主要体现为重视血缘与宗族、推崇祖先崇拜、强调圣王精神、重视礼仪、弱化萨满式的直通天意等。② 参见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p.16-55。在整体的文化导向与通见之间,史华慈显然更侧重于后者,强调文化导向被各家“误读”与创造性理解的面向。③ 史华慈在该书前言中便坦诚:“我们所处理的不仅是文化导向,而且是势必形塑了文化导向之演变的思想史。”(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10)
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的“原则宣言”一章,史华慈指出了严复早期在《原强》《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中出现的对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诠释,特别是所服膺的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个人德智体发展的斯宾塞主义。这些诠释构成了此后严复在翻译和解读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政治通诠》、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与《群己权界论》的理论基础,也构成了史华慈在此后的分析中反复援引的依据。在这些分析中,史华慈总体上试图探讨的是严复是否误读了斯宾塞的自由主义,是如何误读的,这种误读到底是仅仅源于严复自身的关切,还是本来潜藏于斯宾塞自身理论的张力中、只不过不为斯宾塞所强调而已。就此而言,这种分析路径与《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关于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系列理论的适应和创新的解读并无多大差别。如果说毛泽东从对列宁的“工农专政”理论的解读中,“片面性”地看到了农民阶级在共产党中的地位,那么严复则是从斯宾塞对于个人德智体的强调中,“片面性”地看到了西方现代性中与国家富强相伴的“浮普精神”。在毛泽东那里,他要面对的是马克思、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等人开创和延续的共产主义;而在严复那里,他要面对的是以斯宾塞为主,包括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甄克思、孟德斯鸠等人的启蒙教义。如果硬是要在这两本著作中看到不同的一面,可能在于原有的“意识、处境和行动”三位一体的研究法,政治处境和政治行动被转化为了个人处境和个人行动,“意识”凸显,而“处境”和“行动”稍微淡化。
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有上课前自主预习和下课后的自觉复习,“学案导学”的教学模式更重视从学生课前自学上对学生加以培养和提高,在教师提供的学案引导下,学生的自学过程变得有目标、有步骤,问题清楚明了,能一改过去自学时的盲目性。特别是那些不具备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有了学案的帮助指引,能够按照学案要求,带着问题阅读教材,可以简单掌握教师准备讲解的内容,可以在预习的时候对难点加以记录,并在课堂上向教师提出。使用“学案导读”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的同时逐渐学会好的方法、养成好的习惯,强化其自学水平。
有鉴于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城市知识分子,人称乡村建设派,曾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尝试乡村改造,推行诸如识字扫盲等社会改良举措,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收效甚微。1936年,吴景超就直言:
其一,是重视“文本”(text)与“文本诠释者”(interpreters)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体现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托洛斯基的经典文本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体现为以斯宾塞为首的启蒙思想家的文本与严复的关系;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体现为商周文化导向与先秦诸子的关系,也包括孟荀对孔子相关经典文本的解读。在这种“文本”与“文本诠释者”之间的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史华慈特别强调师徒(sage/master-disciple)的关系,如《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陈独秀、李大钊与五四学生辈④ 参见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8。;《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黄绍炎与严复的师生关系⑤ 参见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Belknap Press,1968,p.23。另外,斯宾塞与严复之间也被视为师生:西方老师与中国学生。;《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的孔子与诸弟子① 参见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p.130-134。。在这其中,史华慈似乎喜欢用“异端”(heresy)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剑走偏锋的“弟子”,这些人往往会开出不同的传统。
其二,强调思想的体系性与其本身的内在张力,以及所存在的多重诠释的可能性。如第一节所指出的,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史华慈强调共产主义“传统”(tradition)的重要性;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史华慈则强调斯宾塞总体思想(synthesis)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表现为对商周文化导向(orientation)与先秦诸子的通见的重要性。在史华慈的分析和诠释中,这些思想体系往往在内容上都涵盖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所不可缺少的成分: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家庭与宗族)、形而上学的基础(马列主义的历史观、斯宾塞的不可知论、先秦诸子的“超越突破”)。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华慈对于各思想体系既细腻又深入的把握,他的分析往往着意于思想体系内部各个部分的张力,对在思想体系受到冲击和批判时哪一部分弱化、哪一部分强化非常敏感,对它们是因何而弱化、强化的原因非常在意[如《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明显的语言媒介(language medium)上的误读与关切(preoccupation)上的误读② 参见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97。]。史华慈曾说思想像霉菌(enzyme)③ 参见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45。,体系内不同成分的组合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使是用了相同的观念,在不同的学派那里,往往也会由于侧重点和组合方式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④ 参见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174。在同刘梦溪、林毓生的对话中,史华慈便直言,“我心目中的文化形象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结构或模式。我觉得也许可以把文化比喻成一种化学上的复杂的化合物(a complex chemical compound)”,“正如一切化学化合物那样,其中各种成分都可以分离出来,可以从原有的结构中解脱出来和其他结构组合”。⑤ 刘梦溪:《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史华慈教授访谈录》,载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198-199页。
在这些方法论的细节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那个从《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便缠绕史华慈的核心命题——“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说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理论体系必然充满张力,那么,一部思想史就是对于这种张力的描述。而且,如果说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不同理论体系并无决然的对立,就像史华慈那样可以从毛泽东追溯到严复与先秦诸子,那么,中西古今的思想体系仍然处于不断的交融与碰撞中。正统不再,异端迭生。
三、思想体系中的问题意识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史华慈紧抓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想传统牢牢不放,即关于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就这一思想传统,史华慈认为,共产党与作为政党基础的工人阶级之间是否存在有机联系,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政党正当性的问题。在他的分析中,他用了“处于这一思想传统之外的人”(those who stand outside of the tradition)和“处于这一思想传统之内的人”(those who within the tradition)的二元对立来理解这一问题。②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119.对“处于这一思想传统之外的人”而言,工人阶级与共产党之间是否有联系,或者共产党是否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只是被视为一个关于信念上的主观看法或借口。但是,对“处于这一思想传统之内的人”来说,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乃是不容忽视的信念,脱离了这一基础而仍然以共产党自居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③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p.193-194.举例而言,即使在十月革命中,人们可以说农民和工人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但是首要的是,工人阶级确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个事实满足了主义(doctrine① “doctrine”既可译为“主义”,也可译为“教义”,这是史华慈经常使用的词汇。 )的内在要求,因而才具有影响力。② 参见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119。基于此,史华慈认为,处于国际共产主义思想传统中的中共(特别是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初使党中央从上海前往井冈山的革命实践)的重大特征之一,即不是以工人阶级,而实际上是以农民阶级作为政党的阶级基础。因而,如何诠释思想传统(意识形态)的要求与实际政治状况之间的裂缝,构成了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中不得不应对的问题。
近期,《中国矫形外科杂志》编辑部多次接到读作者的电话和Email,发现有多个网站利用《中国矫形外科杂志》名义非法征稿及骗取有关费用,要求作者将费用汇入指定账户等方式骗取作者钱财,侵害作者权益。《中国矫形外科杂志》编辑部提醒广大读作者,本刊编辑部从未委托任何代理机构为《中国矫形外科杂志》征稿。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将史华慈独特的对于“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的理解纳入到讨论中。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三本主要著作中,虽然不否认在不同思想体系之间存在不同的独特面向,但是他并不认为各个思想体系就完全不可沟通,而是主张不同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可资互相理解和辩论的问题。这一对不同思想体系的理解,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虽还没有明白提示,但是当他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托洛斯基放在一起探讨时,已经表明这些人之间虽然存在着文化上的隔阂,但仍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而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则在全书开头便反对那种将中西决然对立的研究倾向,认为非西方固然是一个不乏模糊的研究对象,但西方自身也并非自明。在严复与他所译介的那些西方“圣人”之间,明显地存在着共享的问题意识,只不过严复因为自身的关切点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读。到了《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史华慈进一步阐明了这种理解。他借助雅思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的看法,认为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宗教均出现了“后退一步,远眺彼岸”(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的趋势,一方面是反思和疑问,另一方面是出现了新的积极的视野和通见。① 参见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3。在史华慈看来:“从各个轴心文明中涌现出来的并不是众口同声的回应,而是一些共享的问题意识。只有当我们从总括的文化导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意识层面,跨文化的比较才变得最令人兴奋,也最具启发性。真理更多地存在于细腻的差别之中,而不存在于对甲文化或乙文化的总体性特征作出的粗糙的概括之中。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尽管更大的文化导向之间存在着更巨大的分歧,从而造成无可争辩的差距,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现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② 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14.此处参考了林同奇先生的翻译。因而,即使是那些横亘在不同文化导向和思想体系之间的思想家,在关于个人、共同体与形而上学等问题上,却往往存在着共同的疑惑和问题意识,这构成了将他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
从这种共享的问题意识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史华慈为何一方面强调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并不认为这些理论体系乃是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设想的那样是封闭的、无法沟通的。而且,史华慈似乎特别强调,正是在不同思想体系的碰撞之中,一些颇为有意思的面向得以生成。史华慈的三本系统性的主要著作,就是在处理不同思想体系碰撞后产生的思想的别样化合与重组,并在这种分析中形成了他的耐人寻味的洞见。比如中共领导人与国际共产主义理念的碰撞,让史华慈提炼出了关于“毛主义”的看法;严复与斯宾塞等18—19世纪思想家的碰撞,让史华慈提炼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存在的“寻求富强”的关切;在先秦诸子与“轴心时代”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史华慈得出了中国文化的主导倾向,并对先秦诸子均形成了独到的看法。史华慈特别擅长在看似封闭的思想体系中找到缺口,并由此看到与其他思想体系之间共享的问题意识,难怪余英时在评论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时指出:“这本著作的理念让我们想起了以塞亚·伯林的写作。像伯林一样,史华慈也是一位‘反潮流’的学者。在他那里,没有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他完全地将自己从所谓‘观念的奴役’中解放出来。”① 此评论见英文本1985年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勒口处。
但是,正如朱炳仁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并没有像前几代人那样继续传统的表达方式。从一位大师开始,继续他自己的创作。不,他心里有传统,并用这个巨大的来源创造了他自己的铜王国。他创造了自己的世界。他展现了他的个性。哪怕只看一眼,人们就会认出这是他的作品。不是细节,也不是他整体上的作品引导着对大师的认可,而是他的个性主宰了他的形象。他从中国的传统出发,把传统文化运用在了他的视觉故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创作了各种各样的作品。我称它们为中国艺术的象征。他用这些从中国古代艺术中提取出来的图像创作不同的收藏品。
其实,除了史华慈主要的体系性著作外,他的一些经典论文也有这个特征,总能在封闭的思想体系中找到突破口,把自己从“观念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其中一篇经典的文章是《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袖与党的组织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篇文章的前一部分是从共产党的理论传统中分析先锋队、党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后一部分则跳到18世纪的法国,探讨这一冲突问题背后所潜藏的卢梭式的“道德革命学说”。如果只有第一部分,那么史华慈仅是平庸的学者,就共产主义的理论传统谈中共;但正因为有了第二部分,在看似不搭界的法国启蒙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史华慈形成了独到的见识。史华慈并不认为这两个相隔近两百年的思想传统之间有着根本的隔阂,相反地,他试图去追问背后共享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探讨的是一种许多人都认为的疯狂现象,那么,这种疯狂是毛泽东所独有的呢,还是它通过什么途径与中、西思想史有某种更加广阔的联系呢?它究竟是西方的或是中国的,还是同时吸收了这两种文化传统呢?”① 史华慈:《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载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147页。
史华慈寻求从“观念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另一经典研究,可以参见《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标题显示的,在这篇文章中,史华慈探讨的是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但是他却用了几近一半的篇幅处理西方近代的保守主义问题。在他看来,近代西方的保守主义其实是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处于共同的观念框架中运作,能够用历史循环论、整体主义、唯社会论、有机发展观念和民族主义来论述保守主义,虽然这些论述也以别样的方式潜藏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中。在论述完这些特征后,史华慈转向了西方近代的保守主义与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他发现保守主义在中国的情境下被“改头换面”了:“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伯克式的全盘肯定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保守主义。所能发现的只是反映民族感情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与那种竭力维护现行政治程序的保守主义几乎无涉,尽管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也有后者的保守主义。人们还可以发现,虽然有一部分中国保守势力强调,中国过去的观念可为现代的目标服务,可是还有另一部分悲观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怀疑中国历史可以为当今服务,但他们却把他们的保守主义建立在对过去深刻的宿命论的理解上。”② 史华慈:《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载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83页。 如果没有打通中国保守主义与西方保守主义,并认识到二者内部存在的共享的问题意识,史华慈不可能提出这么细腻的比较性结论。
谈及史诗产生的时代,有一点须明确,即史诗作为民间文学中一种特殊门类,它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只是在口头流传,创制文字之后,才以各种手抄本辗转传播,流行于世,因此判断它们产生的具体时代,当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对某部史诗冠以“早期”、“晚期”这类界定语,务应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
当然,史华慈这种打破古今中西思想体系的做法很容易遭到攻击,特别是一些强调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更是可能质疑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没有文本依据的臆想。不过,正如史华慈颇为敏锐地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引用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提出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时指出的,将思想处处求证于史料也存在着缺陷:“一个观念(idea)的历史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于相应术语(term)的历史,尽管该观念最终要靠那个术语来辨认。”史华慈举“人性”这个概念为例,认为“人性的问题在上古时期的中国思想中就已经存在,与是否使用这个术语无关”。在《诗经》的“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事实上找不到“人性”这个术语,但是明显地,“人性”问题已经潜藏其中。① 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p.175-176.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史华慈那种突破不同思想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的依据,因为如果在毛泽东那里确实存在卢梭式的问题意识,那么,即使毛泽东没有直接援引卢梭,也不意味着就不能比较,而且这种比较研究往往还能够带来别样的洞见。当然,在很多时候,史华慈还是细致比对文本,他的问题意识式思想史研究法决不意味忽视史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一般的史料阅读还要来得细致。
讨论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回到那个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就出现的并一直影响着史华慈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的命题——“在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或许可以说,伟大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的观点和理论一旦被广泛接受之后,不是获得确定性的答案,而是获得永远无法确解,并随时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的问题意识。② 这也是林毓生对于史华慈“问题意识”的解读。参见林毓生:《史华慈思想史学的意义》,载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第237-246页。 只会有恼人的、可资讨论的问题意识,而不会有共同的答案。正如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史华慈引用格尔茨的话说:“问题由于是基本的,因而是普遍的;答案由于来自人类,因而是多样的。”③ 格尔茨的原文为:“The problems being existential are universal;their solutions being human are diverse.”(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p.8)那些由“伟大思想家”或“宗教创始人”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体系,仍然被不断地重新诠释,持续影响着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或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史华慈政治史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真正基座所在。
四、余论
任何关于某一思想家的重新诠释,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思想家本身的误读与发挥。特别是对于史华慈这样涉及的研究跨度极大、用词谨慎、行文异常细腻的思想史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不过,如果试图对史华慈的史学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们便有必要在细致阅读他的著作的情况下,作出相应的大胆的判断。
该意见强调,发展海水淡化产业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强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二是提高工程技术水平,三是培育海水淡化产业基地,四是组建海水淡化产业联盟,五是实施海水淡化示范工程,六是建设海水淡化示范城市,七是推动使用海水淡化水,八是完善海水淡化标准体系。
本文并没有就史华慈在某些具体议题上的研究而进行辩驳与质疑,而是从他的整体研究著作出发,探讨其政治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联系。通过上述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可以认为,那种对史华慈的史学研究进行一分为二的做法,显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偏颇。事实上,其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后来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路和叙述风格,而其思想史研究则进一步打开了政治史研究中提出的核心问题面向。在看似相隔甚远的研究主题之间,史华慈以其绝妙的史学论述能力,通过特有的问题意识,串联起草蛇灰线般的研究整体,实现了现代史、近代史与古代史的有效联结。即使在人才辈出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界,似也无人能出史氏其右。
当然,史华慈的研究自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一些具体的论证和判断也并非不易之定论。不过,就史氏研究的总体框架和规模而言,仍然有诸多值得进一步借鉴的方向,特别是他那种打破政治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壁垒,实现古今与中西之间的联通,以及深切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在当今史学界面临的日益碎片化的局面前,显然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研究进路,值得深长思之。
作者简介: 王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董成龙)
标签:史华慈论文; 政治史论文; 思想史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