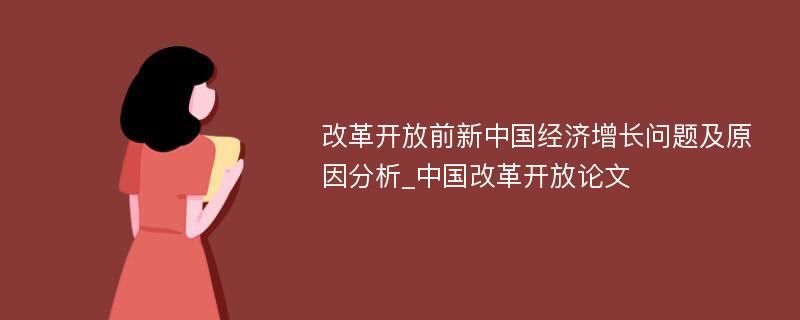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新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4-0196-04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统计资料表明,1953—1978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和6.0%。这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与经济发展较快的韩国、中国台湾相比也不算低。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24.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GDP从1952年的342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018.4亿元,第二产业GDP从1952年的141.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745.2亿元,第三产业GDP从1952年的194.3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860.5亿元[1](P3,4),增幅分别达到471.1%、170.1%、1525.2%和399.3%。
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后,美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多数学者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稳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但中国总是能从衰退中恢复过来,重新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在1952—1974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取得这样高的增长率的国家是不多的。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中国的战略和体制使中国脱离了落后的农业社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到工业化的中等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工业和技术变革。1949年,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异常贫穷、落后为特征,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已为人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衣服和住房,医疗卫生有了保障,人人有工作,并显示出改善的巨大能量[2](P10)。
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世界瞩目,但在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却依然是一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幅度,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同时,高速经济增长还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因为他们总是直观地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对比,而无需去考察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而历史研究者和党史理论工作者则必须力求再现历史的原貌,从当时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的诸多因素中捕捉这些问题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一个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判断,对这些问题作出历史的说明和合理的评价。
问题一: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人民生活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大大低于经济增长幅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虽然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由于效率相对较低,中国并没有脱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与经济增长同比例的提高。正如美国学者G.罗兹曼所言:“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配置更多的资源以增加工农业生产方面,是成功的。但中国政府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人民吃了很大的苦头,同时也造成惊人的资源浪费。”[3](P433)
为什么高速的经济增长没有直接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这与以下两个原因有直接关系。
第一,过高的人口增长率。
改革开放前,我国保持了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951—1973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都在20‰以上,其中1962—1970年间均高于25‰,峰值在1963年,高达33.33‰;1974—1979年间逐年回落,从17.48‰降到11.61‰[1](P1)。“中国急剧增加的国民收入当时没有变成劳动人民收入的相应增加”,“在毛泽东主义时代最后20年间,增加的国民收入许多用于赡养迅速增长的人口”[4](P488)。这种过高的人口增长率,有我们政策失当的原因,但更多却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
“富国变得愈来愈有钱,穷国变得愈来愈有孩子”,这是战后几十年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鲜明对照。和西方国家在经济“起飞”以前以及“起飞”期间所经历的人口缓慢增长的情况完全不同,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地遇到了过速的人口增长。人口因素日益成为拉大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日益增长和劳动力过剩的压力给现代化的后来者带来了特殊的阻力,单是人口一项因素就可能把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社会)自动淘汰出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影响了它们去取得本来也许能取得的进步,使人民失掉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5](P79)。过速的人口增长使中国和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难有大幅度的提高。
第二,过高的积累率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巩固国防,又要打下基业,这种形势使党中央和毛泽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有限的资金集聚起来投入重工业。除大量汲取农业剩余之外,就是实行高积累政策,勒紧裤带搞建设。统计资料显示,1952—1978年间平均积累率达29.5%,其中,1959年高达43.8%[6]。就一般规律而言,积累率与一国的收入水平成正比,但我国却在很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创造出大大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积累率,从而弥补了对外贸易和外援的不足,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维持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高积累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且有其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高积累,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到重工业部门,而在于这种积累是否全部、有效地投入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去了。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积累率,而且还取决于积累效果,如果积累效果不佳,高积累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如果忽视积累效果,盲目提高积累率,不仅无益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相反会引起经济运行紊乱,降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可见,高积累是表面、是枝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问题的根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注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经济增长几乎全部寄托在规模的扩充上,大量的资金被重复地投入某一行业,并且并不一定是最需要的行业上,投资效率低下,造成大量的浪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先后被苏联和中国理论界提出来,但直到苏联解体,直到中国制定“九五”计划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政策上更无实际举措。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或许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增长评价甚高的美国学者M.迈斯纳也认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工业经济同样面临着那些困扰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棘手的问题,如“浪费、低效率、官僚主义的人浮于事和懒惰现象、低生产率以及下级腐化现象;为投资于重工业而不断提高资金积累率以至于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忽视贸易、服务行业和消费品工业”[4](P485)。
为了积累(包括那些无效的、浪费的积累)的需要,增长的国民收入除了养活增加的人口之外,余额的大部分都进了国库,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剩余的部分仅仅能维持人民收入水平的少量提高。
问题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
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和部门不均衡问题,二是和国际上大多数后发国家一样,国际经济地位不升反降。
一方面,中国进行了50多年的建设,虽有高速增长,但时至今日,不仅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而且还要为实现工业化而努力,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差别明显的社会二元结构,即“双重二元结构”,时至今日,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仍要警惕跌入“拉美陷阱”。
毛泽东尽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试图探索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由于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加上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过分倚重重工业的弊端,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长期发展滞后,影响了包括工业在内的整个经济的综合发展,造成了发展的失衡,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比表明,到1975年,现代部门的比例使中国列入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农业部门的比例使中国列入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服务部门的比例则使中国低于任何一组国家的平均数。”[2](P43)
另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近30年虽然发展迅速,但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也大大落后于原先跟我们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当时中国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一样,在世界的相对地位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7]。从国际经济发展史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从1955年至198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按1980年美元计算,人均收入从7030美元增至11560美元。而同一时期,在印度,人均收入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但只从170美元增至260美元。1955年,美国和印度人均收入的差额为6860美元,到1980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达到11300美元。195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约为印度的41倍,而到1980年则变为44倍[5](P5—6)。自19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呈逐期下降趋势,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这种差距会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挫败感,甚至会使他们心灰意冷:付出如此大的努力,结果差距却在拉大,甚至越是拼命努力,差距反而越大。但是,如果放弃追赶的努力,那只有自甘落后。因为,如果他们不拼命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以一个超常规的方式加快建设步伐,他们就要继续被歧视,继续甚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必须树立一种长期的信心,埋头苦干,奋起直追,因为若不追赶,差距会更大,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问题三: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面对落后的压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领域急于求成。经济领域的“左”倾指导思想与政治领域的“左”倾相互影响,出现了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错误,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这样的代价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否不可避免?我们不妨把眼光放长放远一些。
放眼世界现代化进程,我们会发现,先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是逐步出现的,矛盾的解决也是因序而行的,社会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启动于政治(社会)革命而不是经济(工业)革命,并且是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同时进行,社会矛盾是以大爆发的形式出现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现代化的进程肯定不能够像先行者那样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因为历史给予它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并且,这种状况随着越晚近进入现代化而越明显,越往后,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就越突出,“一方面面临着更剧烈的冲突和不稳定;另一方面,面对先驱国家设定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而心急如焚。后发国家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进入现代化进程。……同社会各方面都平和地发展的地方相比,在喷气式飞机和牛车并驾齐驱的地方,现代化过程的张力大得难以衡量”[8]。这样,越往后,实现现代化的压力就越大,就越急于求成。在中国,除现代化的后来者必须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齐头并进的矛盾之外,人口众多、经济极端落后的大农业国的现实也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既要发展,又要驾驭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其难度可想而知。
毛泽东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想通过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进行改革的领导人,但直到最后,毛泽东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没有能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苏联模式的弊端,甚至某些方面还变本加厉。毛泽东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9]。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了追赶现代化,后进国家一方面不可能因袭先行国家的老路亦步亦趋,而必须要有超前的眼光和发展战略,紧跟当代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势,采取超常规的、跳跃式的发展,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否则便不能改变落后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国家长期以来处于落后状态,虽可利用自身优势加快社会发展,但却不会在短期之内发生质的变化,这就要求这些国家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切忌急躁冒进,否则将会欲速不达,反而造成所谓现代化的“断裂”。因而,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根据国情,该超前的超前发展,不该超前的则不可冒进,在一些领域里存在适当的滞后发展也是必需和合理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水平毕竟有重大的提高,构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并为以后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
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重工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