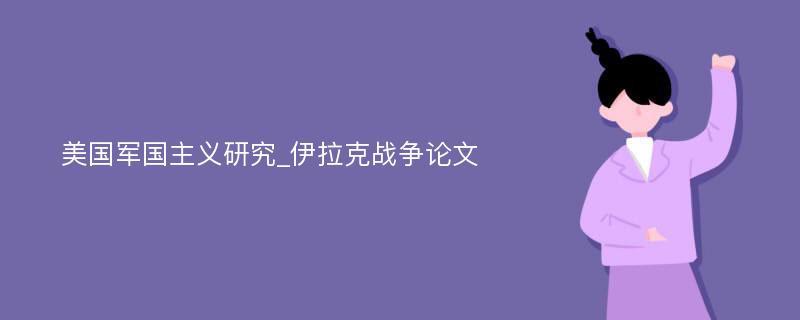
美国国家黩武主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主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美国而言,“伊拉克战争”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不过,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这场战争绝非值得称颂的正义之战,只不过是一场错误的侵略战争。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目的,不在于阻止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或者防止种族清洗乃至大规模屠杀。事实上,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美国决策者的真实意图是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尽管美国过去曾经支持过萨达姆政权,可是时过境迁,该政权已经妨碍了美国的利益,就必须用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权取而代之。简而言之,美国借助“伊拉克战争”再次向世人宣告,美国有能力颠覆全球任何一个损害美国利益的政权。即使是美国宣布“伊拉克战争”失败后,美国的外交精英似乎依然不改初衷,而美国的最高决策者对此则讳莫如深。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发动的最为失败的战争之一,事实已经验证了反战人士在战前的预见。与此同时,美国左翼的对外决策似乎也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动向。即便以捍卫自由著称的奥巴马当选了新一任的美国总统,今后美国对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政策走向依然存在诸多变数。
《异议》杂志一直关注伊拉克战争的残局,并在2009年春季号上刊载了一系列有关“撤离伊拉克”的文章。这些文章着重从道义和政治层面剖析了美国撤离伊拉克的无奈,美国历经艰险所取得的成果很可能随之付诸东流。至于文中提出的应对之策,则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初衷多有谋和之处。
例如,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撤离伊拉克”的系列文章中撰文批驳“美军应迅速撤离伊拉克”的观点。乔治·帕克认为,一旦美军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力量平衡就会被打破,战后重建也会因此而停滞。考虑到伊拉克战争的敏感性,乔治·帕克在文中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伊拉克战争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但是美国对于伊拉克应尽的义务,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都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数月,帕克便对当时的反战活动提出了异议。例如,他曾在2002年12月的《纽约时报》撰文指出,所谓的反战运动不过是由左翼操纵的。“鹰派”就是想借助战争消除欧洲人的疑惑,并且震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美国人。可是,他们却没有合理地解释“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之间的联系……
在“撤离伊拉克”的系列文章中,布伦登·奥利里(Brendan O'Leary)更为强调美国在伊拉克的责任。在是否借助军事力量重建伊拉克的原则问题上,奥利里赞同乔治·帕克的观点,认为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有助于稳定其国内政局。奥利里在文中指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对伊拉克复兴党实施种族灭绝显然是缺乏理性的。虽然小布什出兵伊拉克的决策是一个失误,但是他的初衷是想弥补老布什对伊政策的疏失。”与此同时,奥利里认为战后重建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政权更迭缺乏制度协调,军事占领缺乏必要性,美国的直接管治缺乏效力,决策及预测存在诸多谬误,这一切引发了一系列的恐怖暴力事件。”奥利里继而指出:“驻伊拉克美军时而缺乏明确的打击目标,时而缺乏足够的打击力度。假如美军过早地撤离伊拉克,这对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很可能会爆发内战。”美军唯有在伊拉克坚守下去,协调该国各派政治力量:维护联邦宪法,调解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武装对峙,保护库尔德人的区域自治。
对于部分反战人士而言,在伊拉克战争之后6年中的人员伤亡以及伊拉克遭受的打击,用“不负责任”一词是不足以加以搪塞的。
诚然,乔治·帕克与奥利里的部分论断是无可厚非的。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确有责任保护当地民众的安全,重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基础设施。伊拉克政府也应当尽可能地防止国内任何族群、民族在美军撤离后再度挑起事端。可是,从美国目前的处境着眼,要想实现上述目标绝非易事。
如果要推敲上述学者言论中隐含的深意,恐怕会令美国左翼为之齿寒:伊拉克战争的症结在于过于彰显美国的实力,应当更为务实地实现美国的利益。相比之下,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战前发表的言论似乎也有与之谋和之处:弗里德曼赞成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项大胆的计划,但是必须控制在美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国政府真能听取弗里德曼的上述建议,那么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原本是可行的。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坚信美国在全球打击邪恶、重建和平的使命始终是不容置疑的。假如某个国家威胁到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就有责任履行其维护正义的使命,采取类似于“伊拉克战争”的军事行动。
通常,人们会认为弗里德曼的上述理念出自于美国新保守派,因为新保派是伊拉克战争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回溯美国历史,这种理念应当追溯至美国的“天赋使命观”(Manifest Destiny)。“天赋使命观”在实质上是“美国例外论”的进攻主义表现。换而言之,命运、天意或者某种特定的“道德是非观”令美国确信自己肩负的义务,并将这种义务拓展至全球范围。
美国的思想家、外交决策精英、新保守派乃至新保守派的批评者都普遍受到“天赋使命观”的影响。这些精英总是将“天赋使命观”诠释为“维护全球稳定是美国特殊的使命”。恰如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所言:“如果我们不得不动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我们高瞻远瞩。我们更能预见未来……”奥尔布赖特的这番言论,就连“鹰派”也未必敢直言,着实为数年之后美军入侵伊拉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一旦接受这种“奥尔布赖特式”的美国观,便会将美国视为全球事务的最终仲裁者、世界霸权或者超级大国,可以使用武力对全球局势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对于美国民主党而言,其施政目标及方向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就连那些自命为左翼的思想家,不仅将美国视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也承认美国维持全球稳定的作用。
对于挑战这种美国观的人士来说,无论从政治还是道德角度来看,美军入侵伊拉克都是完全错误的。所谓错误不是谋略不善或者军力配备不足;也不是伊拉克军队被解散;更不是因为驻伊美军无能、腐败或者社会犯罪等因素。伊拉克战争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其侵略性、机会主义的本质,美国无权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而用武力改造其他国家。
不仅如此,这种错误的战争导致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扭曲。从全球范畴来看,许多国家正致力于改变霸权国家凭借武力解决国际冲突的传统格局,转而构建某种超国家的权力机构,依据多边协商决策来解决未来的国际冲突。可是,类似于“伊拉克战争”的错误抉择却在破坏这一进程。在美国国内,负面影响则更为凸显。美国为了确保其有能力影响全球任何国家或地区,加之“伊拉克战争”未能取得预期的目标,美国国民的生活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扭曲。
错误的战争令美国民众置身于一个黩武国家。
现状:黩武国家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军费开支已接近于全球军费开支的1/2,2008年这一比例已高达41.5%。同年,俄罗斯军费开支在全球军费开支中所占比例为4%。据预计,美国的军费开支位居全球之首,相当于其后12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军费开支,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英法两国(两国军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2.5%)。简而言之,美国在全球军事行动中所占的比重无疑是最高的。
与此同时,美国却无力保障其民众获得应有的医疗保障。例如,美国的婴儿死亡率与平均预期寿命在全球工业化国家中仅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某些领域甚至比不上古巴、希腊和约旦等发展中国家;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仅位居全球第十九位,在校学生的成绩表现也同样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美国拥有惊人的高犯罪率,其230万的监狱人口更是位居全球首位。正如英国犯罪学家维薇安·斯特恩(Vivien Stern)所言:“美国的犯罪控制已经偏离了西方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咎于美国对于发展军力的偏执。
不妨将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强制性投资进行比较,同时再将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进行比对。至于比较的结果,部分评论家会视为纯属偶然。对于这些评论家来说,也许美国对外面临巨大的军事威胁,对内则需要应对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或许,大多数美国人不仅对战争与犯罪司空见惯,而且早已习惯了那种缺乏医疗、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务的贫困生活。
如果美国知名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还在世的话,很可能会将上述评论家的观点归为“疯狂的经验主义”。显而易见,没有人能够预知美国政府在切实兑现那些有关社会福利的承诺之前,究竟还会在军费开支方面投入多少。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美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例如帮助美国民众获得更多的医疗保健、信息与教育资源,减少当前庞大的监狱人口,同时调整分配国家战略资源的比重,减少军费开支。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是惊人的。2009年秋,美国国内围绕健全全民医疗保险机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最终,美国的政治家们达成了一个有待实现的共识:在未来的10年之内,美国政府将投入1万亿美元用以完善医疗保险机制。
确切地讲,美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开支已经达到难以计数的程度。据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与琳达·比尔姆斯(Linda Bilmes)的研究显示:考虑到美国政府对退伍军人负有的长期义务,伊拉克战争的成本已高达3万亿美元。对于军费开支如此庞大的美国而言,所谓美国处于战略“防御”的论断是荒谬的,而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多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维持庞大的军费预算,已成为美国的战略传统之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新保守派的先驱成功地构建了这样一种理念: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受限制的。依据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美军退役陆军上校)的记述,这一历史性转折应当归功于为杜鲁门总统起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保罗·尼茨(Paul Nitze):
在二战结束后的5年里,美国的权力与影响力似乎已经达到了顶峰。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令美国再度意识到了潜在的巨大危机,所谓“美利坚合众国乃至人类文明均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出台之后,以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表的精英很快与之产生了共鸣,在他们的推动之下,美国最终确立了“永久黩武主义”的国策,并竭力将这一国策延续下去。原苏联解体之后,所谓的“邪恶帝国”不复存在,美国“永久黩武主义”也随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浮出水面,美国终于有了继续维持“永久黩武主义”的合理借口。
在美国国内,黩武主义者的野心似乎已不可抑制,甚至试图要挟主管军务的政府部门。这种情形就好比森林大火遭遇狂风,军费开支就如同燃烧的野草一般四处蔓延。奥巴马总统曾经成功否决了国会出资17.5亿美元生产F-22战斗机的议案。奥巴马政府认为,该项议案缺乏长远效益,毕竟目前全球现役的F-22战斗机尚不足100架。
时至2009年夏,奥巴马总统已无法阻止国会批准一系列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备合同。在这批军备合同的众多利益攸关方和支持者之中,立场最为坚定的莫过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约翰·默撒(John Murtha)。据《纽约时报》报道,约翰·默撒希望国会批准数额更高的军备合同,如此便可以为宾夕法尼亚州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默撒认为:“从美国国会目前批准的军备合同来看,美国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人数显然是不成比例的。”默撒的上述言辞,其逻辑令人不敢苟同。难道美国将成千上万的青年送上战场,就是为了换取相应数额的军备合同吗?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黩武主义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立法机构,甚至禁止公众或政府围绕黩武主义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早在竞选总统伊始,奥巴马参议员便猛烈抨击驻伊美军的人员伤亡是无谓的牺牲。可是,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其论调便转向了之前的对立面。例如,奥巴马总统并未继续有关伊拉克战争的公开辩论。美国原本可以借助公开辩论,减少驻伊美军的伤亡,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美国与部分国家的紧张关系。
与奥巴马相比,4年前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所面临的处境则要艰难得多。当时,霍华德·迪安曾经宣称:美国维护其国家安全应当遵循国际法,这是因为美国“不可能永远维持全球最强大的军力”。对此,霍华德·迪安的竞选对手约翰·克里的立即做出回应,不仅质疑迪安“作为美国总统指挥三军的能力”,还在非官方场合警告:“迪安对于任何削弱美国军事优势的举措,很可能会无原则地予以妥协和容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克里在竞选中着力宣扬自己曾在越战中身陷囹圄,然而这一经历在此后的选战中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
事实证明,霍华德·迪安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不可能永远在全球维持其军事优势。然而,霍华德·迪安作为一位颇具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却无法在竞选中充分阐述自己对于黩武主义的忧虑,这一事实恰恰反映出黩武主义对美国公共生活的扭曲程度。美国对于全球安全最大的贡献在于,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法治,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减少各国的军费负担,并缓减未来战争的潜在威胁。假如军力强大的美国不能担当这一重任,全球还有哪个国家可以胜任?
在21世纪,由于美国依靠战争支撑的黩武主义不可避免地损害了美国的公民自由,由此引发了美国公众的不满。
黩武主义摆脱了行政层面的重重限制,得以在伊拉克及其他热点地区无限制地推行“反恐”战略。从法理层面来看,总统在战时行使的特别权力是不受其他行政权力约束的。不仅如此,美军抓获的许多战俘实际上只是涉嫌参与反美的军事行动,却未经审判而入狱多年;美国政府曾竭力否认对嫌疑犯实施酷刑与非法监禁,在事实曝光的情形下才被迫予以承认;美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封闭,政府机构总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行政权力,其中包括对美国平民实施监控。从这一角度来看,奥巴马政府与其前任并无实质性的区别。美国的政治生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被黩武主义支配的时代。究竟何时才会出现转机呢?
对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来说,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现在,“不可或缺”一词已不适合形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美国已经变成一个缺乏自控的国家,不仅狂妄自大,而且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
要理性地面对这一事实着实不易,这就如同将美国等同于撒旦。回溯历史,美国总是倾向于钻牛角尖。美国一方面指责其他国家侵犯人权,另一方面却为了推行其外交政策而践踏人权。例如,美国出于利益需要,既可以支持民主国家(例如现在的韩国),也可以压制民主政体(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美国积极支持非洲各国防治艾滋病,却对部分领域的国际合作持有异议,例如气候变化问题、限制使用地雷以及在巴以冲突中偏向以色列等等;美国将剩余的食品出口到全球各地,同时也带去了金融危机与政治迫害的隐患。
并非只有美国在滥用手中的权力,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单方面地滥用权力。但是,只要美国还存在, “唯我独尊”的权力观与“美国例外论”就始终拥有滋生结合的土壤,类似“伊拉克战争”的黩武主义悲剧就势必会重演。
1993年,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经当面指责科林·鲍威尔:“如果美国不使用武力的话,您时常夸耀的强大军力的意义何在?”正是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之下,黩武主义不厌其烦地为美国的军事化政策进行辩护。事实上,美国强大的军力并未彻底摧毁那些所谓“倒行逆施”的政权。如果美国继续用怀疑的目光环视全球的话,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多年以来引以为豪的司法正义、民众福祉,以及国内法治都将因此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出路:普通国家
那么,美国的左翼是否能遏阻美国称霸世界黩武主义?笔者认为,左翼可以通过较为温和的方式将美国转变为一个普通国家。所谓“普通国家”是相对于全球其他发达的民主国家而言的。
对于左翼而言,当前的切实举措是将美国的军费开支减少1/2,减少至大约每年3000亿美元,或者约为美国年财政预算10%。减少的这部分军费开支,通常是用于雇佣军及其他不便公开的军事用途。尽管将军费开支减少1/2,美国依然是全球受黩武主义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但是此举有利于将大量的战略资源转向更具建设性意义的领域,例如医疗保险、再生能源投资、帮助全球最贫困的国家控制疾病蔓延等等。
对于上述温和的改革举措,黩武主义者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将来美国该如何应对那些威胁美国利益的罪恶、危机和阴谋?还有,美国该如何对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失败国家与核扩散的威胁?唯有美国才能引领各国共同抗击这些人类文明的敌人。削减军备就意味着放弃美国的盟友,放弃那些遭受苦难的国家和地区,这无异于孤立主义!
黩武主义者的回应,令笔者联想起一位绝望的肥胖症患者对节食建议发出的病态怒吼:“我不要节食!我会饿死的!”
适度地削减军费开支绝非摆脱美国现有的国际义务。美国即使将军费开支削减1/2,依然是全球性的军事强国。由此节省的大量战略资源,可以用于增进美国民众的福利。但是,在将军费开支削减1/2之前,相关的利益博弈与公开辩论恐怕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更为要紧的是,随着国家主权的普遍削弱,全球治理日益赢得各国的青睐促使美国重新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有利于美国及其民众尽快地融入当前国际格局转变的最新发展趋势之中。例如,构建监督战争罪行的国际权威机制,起诉并审判那些以主权豁免为借口的侵犯人权案件;增强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对于侵犯人权及其他暴行的监督力度。对此,美国的新保守派势力想必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认为这些改革并不足以改变现实政治规律。但事实上,这些新的发展趋势能够有效地防止黩武主义将美国推入毁灭的深渊。希望美国左翼能在21世纪率先进行有益的尝试。
诚然,有时国家不得不借助武力来解决问题。无论是应对国际事务,还是处理国内政务,部分极具破坏性的事件只能通过暴力加以应对。面对大规模的屠杀、单方面的军事侵略、国家领土面临直接威胁,或者种族清洗及其他可预防的灾害,任何国家均会联手加以应对,而美国则应恰如其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美国新保守派及其盟友是不值得民众信任的,因为他们总是崇尚武力干预。那么美国主导的波黑维和行动与伊拉克战争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笔者认为,这两个案例在目标和干预规模上均有很大的不同:波黑维和行动旨在制止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迫使波黑塞族签署和平协议;相比之下,伊拉克战争则试图彻底地改造伊拉克的传统政治体制与理念。
明智地判定是否启动军事干预,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准则。首先,自我防卫显然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具有侵略性的先发制人战略则不属于自我防卫;其次,应对人道主义紧急事件也属于正当理由,其中包括制止大规模屠杀,大规模种族清洗,减少饥饿和流行病等等;再次,美国必须放弃以功利主义或机会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军事干预,诸如“用战争结束战争”、“帮助某一地区构建新的政体”,或者将未来的恐怖分子“斩草除根”。
美国已经习惯于作为全球军事大国以及世界秩序的维护者,维持这一特殊地位的现实需要与道德上的优越感,将会长期伴随着美国。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切莫将自己视为维护正义的复仇天使,必须摧毁所有倒行逆施的暴政。这种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了。目前,全球与美国格格不入的政权和国家实在是太多了,美国根本无力逐一加以应对。即便如此,这种不合时宜的逻辑依然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系,以美国特有的方式来丑化任何妨碍美国利益的政权,并为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干预制造合理的借口。就目前的形势发展来看,仍有部分知识分子在推崇这种所谓高尚的理念。对于美国左翼而言,绝不可与之同流合污。
乔治·奥威尔的预言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一书中对国家透支权力的阐析述可谓无人能及。《1984》一书对极权主义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与此同时,奥威尔有关国际冲突的描述同样令人拍案叫绝:
1984年,大洋国(Oceania)已经与欧亚国(Eurasia)开战,并与东亚国(Eastasia)结盟。在任何公开或私人场合,这三大国均不承认上述事实。事实上,只有温斯顿(Winston,小说主人公)很清楚,这一切仅仅发生在4年之前。他之所以还记得这件事,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记忆力还没有被别人完全地控制。
虽然这部小说是虚构的,却与现实存在偶合之处。透过伊拉克战争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曾经刻意地控制信息,以便化解公众对战争的批评以及对“美国例外论”的质疑。等到人们都意识到这一点,恐怕为时已晚。
在奥威尔去世之后,他在《1984》一书中的许多预言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最为凸显的趋势之一便是“全球主义”——全球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口、思想、技术乃至武器的跨国流动越来越便利。与此同时,“全球主义”也滋生了恐怖主义,其负面影响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全球所能承载的限度。美国政府在处理情报方面的官僚主义倾向随之凸显,许多涉及军事问题的情报不仅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也禁止对公众披露。随着信息情报流动性的日益增强,美国亟须新增一批高素质的政务、军事专家,而这些精英的工作往往是不为人知的。长此以往,控制了大批精英的美国政府便无需就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展开公开辩论,例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威胁。
对此,奥威尔曾经提出过警告:虽然国家间的敌友关系总是在逐年变化,但是政府对于公众舆论及不同政见的约束却是大体相同的。数十年前,伊拉克曾是美国的盟友。十余年前,伊拉克又变成了美国眼中的所谓“邪恶轴心”;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中国时而是美国在21世纪最具实力的竞争对手,时而又是稳定亚洲和帮助美国经济复苏的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无疑是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或许终有一日该国也会被美国视为文明世界的威胁。即使是当前美国的盟友,有哪个国家敢担保以后不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标靶?又有哪个国家能确信黩武主义或者集权政治真的是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
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全球与美国格格不入的政权或行为体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如果美国因此而逐一加以讨伐并极力压制国内的异议,那么美国最终会沦为奥威尔《1984年》中预言中的极权国家。左翼有责任为美国找寻一条更好的出路。
在这个波谲云诡的世界,任何决策都要承担相应的风险。美国频繁的对外军事行动未必能够及时消除隐患;美国政府在国内实施的信息监控以及其他国家安全举措也未必能有效地阻止恐怖分子再度袭击美国本土。事实上,美国的上述这些决策很可能会令国内外局势变得更加糟糕。
政治决策的价值通常是由相应的风险来界定的,也可以由预期的利益来加以衡量。美国左翼一贯推崇在国内外实现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民主,呼吁政务公开以及公众广泛参与政治;与此同时,左翼为了防止上述构想误入歧途,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国家的机制来解决冲突,防止美国过度依赖于军事威慑;左翼认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绝不能以牺牲内政为代价,国内民众的健康、就业、环保和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现在美国对外深陷于国际冲突,对内则忽视国内福祉,由此带来的风险已经对美国的前途亮起了红灯,左翼必须尽快做出应对。
原文标题:The Military State of America and the Democratic Le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