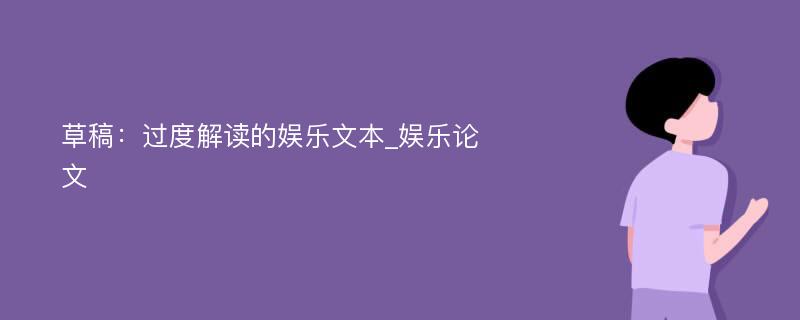
选秀:被过度诠释的娱乐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秀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秀,最初词义是为皇上选秀女。曾几何时,融合了“Show”这样的舶来意义之后,变成了大众传媒上甚嚣尘上的热门词语。这种学自英美、通过大众传媒直播的在民间选拔富于才艺或者具有特色的人物进入娱乐圈的做法,在前几年就崭露头角。但是,无疑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的大获全胜才使它风生水起,包括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电视台都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大量的收视率以及丰厚的利润回报,纷纷各显神通上马此类节目。“忽如一夜春风来”一般,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挑战主持人”、“娱乐篮球”、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安徽卫视的“真维斯新秀”以及与光线传媒合作的“猫人主持选秀”,深圳卫视的“功夫之星”,浙江卫视的“彩铃大赛”,山东卫视的“城市之星”……一时间成为2006年中国电视的最大景观。
事实上,如同一切风靡一时的大众传媒节目形式一样,选秀节目已经渐呈疲态,绝大部分的后来者都模拟了成功的先行者所设立的模式与框架,只是在细节上修修补补。湖南卫视、央视和上海东方卫视的三个选秀节目是这场竞争中的赢家。相对而言,挟余威的“超级女声”仍然是实力最雄厚的,尤其在情感和互动环节做得比较成功;但节目本身除了增加了“复活”的环节之外,没有太多推进。“梦想中国”在规则上有些改动。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代替了“我型我秀”的地位,在形式感上有一定创新,走的是“青春、时尚与综合”的路子,但是显然并没有超出前二者的定位。不过,一向随时而动,并无太长久打算是所有没有深厚人文底蕴和关怀的大众传媒的通病,选秀只要依然还有收视率的底线,就仍然阻挡不了后进者的步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电视台此类节目,包括种种方生方死、昙花一现,方兴未艾、前途未卜的,至少已经有一百多种。
如此宏大的景象,无法不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事实上也确实吸引了几乎全民性的目光,精英与大众不约而同地投入到这个集体事件中来,其中夹杂狂欢的喜悦、左派悲观的批判、宪政主义者乐观的民主发现,甚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广电总局都卷入这个原本发自民间的活动,出台了关于选秀节目的《通知》,规定选秀节目要审批,报名者年龄要满18岁,评委要有度等等。围绕着选秀这个无法回避的文化事件,也引发了形形色色的阐释、解读、转喻等话语的洪流,由之产生了诸如娱乐至死的快感、行为冲动的肇因与心理能量的释放、自由与压抑、娱民与愚民、商业逻辑与政治控制、民主机制的类比、阶层流动的解释,凸显出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伪知识分子、网络群氓、舆论领袖、试图成为舆论领袖的人们歧义横生的态度,而观察这种态度本身事实上比观看这些选秀节目要有意思得多。因为现实和文本在这里产生了互文,选秀节目在这里承载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在极度集中的视线和过度开掘的意义话语中被强行逼迫成一个意义集束的所在,成了一个挟裹了它本身所并不包含的意义与价值能量。
关于选秀节目的最常见的剖析在于它的商业层面,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成功策划,“超级女声”似乎给中国的传媒界树立了一个可堪效仿的榜样。分析其中所牵涉的利益诸方取胜的秘诀,其实是最无想象力也很乏味的,仅对试图从中再分一杯羹的商家和媒体有意义。那么,有关选秀产生的种种神话是否就是窥见了的事物的真相呢?我们一一来看。
娱乐无疑是选秀节目给人最直观也最切身的印象和体验。似乎巴赫金在论述狂欢节的时候讲到的广场狂欢在这里得到了现实的诠释,主次颠倒、脱冕与加冕、既定的秩序被混乱等等,在选秀这样集体性的嘉年华会中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确,节目中的选手们在选秀中一夜成名,貌似是个没有等级的草根民众崛起的过程,我们似乎有理由乐观地声称在这样的节目中显现了当代社会流动宽松的症候,并且这种流动所带来的快感副作用尤其强烈,媒体看上去是为了公众的愉悦不遗余力地在制造快乐的源泉。这种快乐的使用价值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以至于公众似乎忘了自己并不是在真正平等意义上参与的——你收看节目就要收看广告,你支持选手就要短信投票,没有免费的午餐。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都把“使用价值”作为核心概念,并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的快感”上,也就是说,文化产品是满足个人的欲望和快乐的需要而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时至今日,我们发现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意识到“需要”本身也是可以生产的。“不要以为那些需要是在不受影响地表达独立自主的消费者的随意、多变的愿望。需要是在社会中逐步形成的,并非不受其所在社会的主导生产模式的制约。它部分地由产品本身制造和诱发,因此只要一个小小的刺激,需要就会出现,满足这一需要的产品就会被制作出来”。①通过登台献艺而一夜成名的“需要”原本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是隐而不显,但是选秀机制给这个隐秘的欲望提供了空间。而这个欲望恰恰潜在地迎合了公众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需要,于是进一步勾起他们同情的投射。同时,原本籍籍无名的选手通过电视上个人才艺的展现、成长经历的回放、刻意煽情场面的安排,吁求起观众的支持需要。几方面综合的结果是,选手和公众的需要被放大,到了不得不满足的地步,媒体与其背后的商家满足了这种需要。于是,原本作为发泄渠道、释放压抑的娱乐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归根结底是满足了资本和利益的需要。有的论者认为,名目繁多的选秀节目带来了多元性,这是皮相之言,因为所有选秀就其本质而言并无二致,它们的哄然而上挤压了原本可供更多元节目展现的舞台。
由此看来,在这个生产、传播、消费的过程中,一开始公众就处于被动的局面,自由的、不受牵制的娱乐从来都是不切实际的迷思。因此,所谓高雅/通俗、精英/大众之间的区隔,以及区隔的弥合无从谈起。选秀并没有打破既定的社会流动脉络,在一场本身是被操纵的节目中,如何寻找真正的突破呢?大众传媒由资本与其他公共权力共同建构形成,在西方已经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这种势头已经逐渐波及中国。而选秀节目作为一个运作节点,它的种种动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挑战与突破,如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与帕迪·沃内尔 (Paddy Whannel)在《通俗艺术》中指出的,“所谓好的和有价值的与所谓次的和低劣的之间的斗争……是媒体内部的斗争”。②其实,所有的关于底层的上升的神话表象下面都是节目的表演场景,这种场景因为太过逼真,迷惑了天真的异想天开者。选秀节目因为服从于当代中国文化工业的生产程式,反而给我们一种消费主导的假象。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区分的工业生产文化和服务型经济的生产文化在这里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前者是由可预言性、完全监控和以终极产品为准的因素决定的,决定性的是产出;因此,工业生产编号可被描述为功能和批量导向的、现代的,亦即“阳性的”生产文化。而后者则指向过程化,它并不对产品生产进行全面监控,也不仅关心最终产品,还要关心产品形成的进程,它更强烈地体现为一种交往式的、情境式的、后现代的、“阴性的”生产文化的理想类型。服务型经济的“产品”比工业型经济的产品有更强的文化和象征性的特征。③当代中国文化工业可以说是两者的杂糅性的产物,选秀节目只是其中的一种,当然它更倾向性地表现为后者。今日显然已经进入一个马克·波斯特 (Mark Poster)所说的“第二媒介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很有可能促成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该系统将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分明。④
这似乎预言了一个美妙的场景:因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传播者之间互动性的加强,所以民主的曙光也就遥遥在望了。这也是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批判者所津津乐道的地方。更有自作聪明的批评者发现了选秀程序与权力分立制度之间潜在联系的奥秘,在他们的简单类比中,我们似乎明白了:专家评委相当于政治制度中的上议院,代表精英和权威;票选的观众相当于下议院,代表乡土和大众;发短信的观众相当于投票的公民,投票相当于普选。大众普选虽然具有最大的权威,但是也要受到精英的制约。如此一来,中国的大众在娱乐的选秀节目参与和观赏中,就免费获得了一次民主的操练和演习。这种师心自用的腔调、以严肃掩盖的轻浮充斥于我们的媒体,只是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我们需要谨记的民主的实质。民主是个双重过程,“一方面,它牵涉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新建构”。⑤而市民社会的重建最典型的标志是公共空间的扩大,在当下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媒介商业权威的合谋统摄下,所谓的公共空间并没有太明显的扩展,而在其内部去寻求民主的延伸无异于与虎谋皮。
选秀节目的特质如同克洛德·勒佛尔 (Claude Lefort)所说:“只有始终被观看,我才能存在。”文化批评家齐泽克分析这里的情形恰恰是“对边沁—奥威尔的圆形监狱社会观的悲喜剧倒置”。⑥在圆形监狱社会中,我们潜在地始终被观看,我们无处藏身,无法躲避权力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凝视。而到了这里,焦虑反而来自这样的担忧——担心没有始终暴露在凝视之下,以至于主体需要摄像机、照相机、摄影机的凝视,使之成为自己存在的本体论保证。这是种吊诡的局面——貌似民主的投票选举,先验的具有了失却民主根基的本质。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历次晋级赛之前和过后,总会产生种种关于电视台和评委黑箱操作、选手的流言蜚语。这里关涉的程序公正问题且先不考虑,我们知道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所有社会中,谣言和闲话容易形成交流的网络,想象力引发实际行动,实践行动再引发想象,这种反馈性循环可以制造话题,在当下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吸引公众的眼球——也就是说,负面新闻本身反倒进一步加深了控制的程度。
选秀的运作过程类似于我们在电影《楚门的世界(Trueman Show)》中看到的情形,通过连续性的海选、晋级、PK、幕后花絮、成长回放,我们可以持续不断地追踪整个事件和场景,仿佛看到选手真正的成长一样,尽管它们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但是正因如此反而获得了一种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真实”性——它们虽然是假的,但是却在刻意营造的虚拟情感共同体中更让人相信,真实的反而倒像是假的了。假作真时真亦假,过多的感情诉求,反而使得那些真正感人的细节变得更像是一场表演。一言以蔽之,整个选秀节目,“娱乐”的功能胜过“专业”的功能,“营销”的功能胜过“选拔”的功能,是资本运作中衍生的休闲工业的一种变体。
休闲式资本生产方式塑造出来的文化形式和基本的生活方式,屈从于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需要而获得自己的文化表达。“休闲的工业意味着:第一,它反对全面和谐的发展;第二,它降格为一种补偿;第三,由于屈从于心理异化,补偿直接表现为‘排解’肉体的寂寞这种方式。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休闲既是现代社会之自由的象征,也是现代人不自由的表现”。⑦比如,我们可以看到选手们由舆论支配的美丽标准、对自己身体资本化的理解、对个性的张扬都直接与资本的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那些都是吸引歌迷和观众的卖点。这里,我再次发现另一些论者的诞妄,他们在“超级女声”选拔出来的带有男性气质的女选手和“加油!好男儿”选出的带有女性气质的男选手身上发现了这个时代性别观念的转换,似乎女权主义有跃跃欲试的契机,而“雌雄同体”这样女性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也近在眼前了,或者至少已经在中性化气质的选手身上起到了表率大众的功用。而实质上,这种对于选手差异性的偏爱,恰恰正应了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追求差异的个性化表达方式只是消费方式的变体。⑧
当然,过分轻视观众/消费者的能动性显然是不客观的。法兰克福学派后期比如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积极意义已经有所发现,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著名的“编码—解码”分析中,也恰当地指出观众/消费者的能动作用。但这并非是对葛兰西(Antonio Cramsci)提出的霸权理论的抛弃。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的霸权理论认为在生产过程与消费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法。消费者总是把某一实际存在的作品与实践视为局限生产条件的结果。但消费者事实上在使用过程中生产了可能性含义的范围,这些含义不能只从作品或实践物质性的或生产手段与关系中领悟出来。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进而指出,“但这不是说通俗文化总是授权与反抗。否认消费的被动性不是否认有时消费是被动的;否认文化消费者不是文化笨蛋,不是否认文化工业谋求操纵。但它否认通俗文化只不过是一个商业与意识形态操纵的堕落的风景,是由统治阶级强加的,为了攫取利润和保证社会控制”。⑨因为事实上,只有在“使用过程中的生产”中,含义、快乐、意识形态的影响、融合或反抗问题才能依条件来决定,这是个一体两面的过程。
其实,对“大众”这样的复数名次发言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他们层次丰富,内涵与外延都不能简单地化约。我无意做出激进的姿态与面孔,只是对于现有的乐观论调保持必要的审慎。因为在铺天盖地的快餐文化中,选秀节目不过在其中增添了一个吃多了就有些腻的甜点,而大众的胃口被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往往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这个时候如果知识分子/伪知识分子再不明就里地跟着起哄,为臆想出来的种种“进步”与“开放”沾沾自喜,无异于火上浇油。
我在上面的文字中逐一破解有关选秀节目的诠释中快感释放、自由、民主、性别解放等诸多神话,是要说明选秀这种娱乐节目被过度地诠释了。且不说现实层面上,一些不太出名的选秀节目在形式和程序上存在着许多弊端,就是“青歌赛”这样有着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节目在专家评委与公众普选之间也存在前者强势的矛盾。就是对于选秀节目的过度诠释本身,其实有意思地透露出我们社会公共空间里所可以言说的话题的限制。排除一些假痴作癫哗众取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大话,也许那些诠释者本身并非不知道自己的曲解和放大,他们只是策略性的采取这种形式来言说自己的理路,或者表达自己的希望——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环境的尴尬,就不是本文所能展开的话题了。
最后,让我们回到节目本身,来看看它的钱景/前景。以我之见,就现在已有的情况来看,恐怕不容乐观。如同“正大综艺”、“快乐大本营”的热播曾经造成的众多综艺节目的粉墨登场,“实话实说”的成功带来众多谈心节目的如法炮制,林林总总、名目繁多的“××小姐”选美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样,选秀节目也存在后继不力的局面。尘埃尚未落定,但是已经显示了苗头。因为视觉媒介的特性规定,“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⑩滥情主义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受众群体并非无限扩大,在争抢有限的消费群体时,必然会给泥沙俱下的选秀节目以一个淘汰洗涮,生存下来的将是常变常新的少数。
换一个角度来说,选秀作为一档时尚节目,如果不走深度路线(事实上它的本质决定了它很难走),它必然会被新的时尚节目所取代。西美尔对于时尚的本质有着一针见血的剖析:时尚是阶层分野的产物。原因在于经济、文化上的较高阶层或自认为较高阶层的人们制造出时尚用以和其他阶层相区别;而低一阶层的人因为对较高阶层的羡慕和向往,就不断模仿那种时尚。这就带来时尚的两重性悖论,一方面要树异于人,另一方面要求同于人,其起因是为了特立独行,但最终却提供了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这又回到了我前面提到过的社会流动虚幻的放松的问题。
当时尚成为时髦的流行事物时,时尚原本所追求的独特性也就被抵消了。因而时尚逼着人去寻求更多的变化,以把自己和他人区别开来。时尚可以说是一场不懈而永无止境的追求,在技术和商业提供的便利条件下,这种更新换代的速度尤其被大大加快。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时尚的领导者,因为想做领导者,就被迫永不停息地追求、创造新的时尚,实际上是被后面的追随者赶着走。而时尚的魅力也正在于它具有开始与结束同时发生的魅力、新奇的同时也是刹那的魅惑,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带给我们更强烈的现在感。当时尚成为一个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时,主要的、永久的、无可怀疑的信念就会越来越失去其影响力,生活中短暂的、易变的、稍纵即逝的因素则愈来愈获得更多更自由的空间。(11)这是一场永不停息的追逐的宿命。我曾经在一篇评论“超级女声”的文章中说,铁打的fans,流水的偶像。Fans们总是喜新厌旧、朝三暮四,他们会在新一轮时尚浪潮中迅速地改弦易帜。最近《南都周刊》有报道说,许多“玉米”(李宇春歌迷)转化成“纳米”和“栗子”(历娜歌迷)的过程,正好印证了我当初的话。
抛开理论分析,从积极的角度看,如何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在具体的操作中,国外的类似节目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FOX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已到了第五季,收视率还在不断攀升,主办方扬言还要再做五季。这个案例的成功主要在于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节目的版权进行保护,其实美国不少好的节目也是从国外引进模式的,但他们成功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而且一旦版权在手,国内其他电视台就不能制作同类节目了。其他电视台想要在竞争中胜出,就不得不研发或购买其他电视节目模式,因而就能形成比较良性的竞争。国内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还达不到这一要求。另外,美国一些选秀节目也在做形式和内容上的更新,比如NBC新近推出的“美国能人” (America's Got Tadent)就不仅包括传统的歌手表演,动作表演、舞蹈、杂耍、脱口秀、魔术、口技以及更多的无法归类的神奇表演都被充实进来。这些变化已经可以在中国内地选秀节目中微见踪迹,至于在充满变量与定数的市场、媒体、国家、观众之间的博弈中,来日的中国选秀节目的命运会如何呢?还很难说。
注释:
①[英]特里·洛威尔(Terry Lovell):《文化生产》,载陆扬、王毅编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 128页。
②Stuart Hall & P.Whannel,The Popular Arts,London:Hutchinson,1964,15页。
③[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25页。
④[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9月,第2页~3页。
⑤[英]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第396页。
⑥[斯洛文尼亚]齐济克(Slavoj Zizek):《实在界的面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4月,第232页。
⑦胡大平:《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7页。
⑧参见[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⑨[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324页。
⑩[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9月,第157页。
(11)[德]西美尔(Georg Simmel):《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70页~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