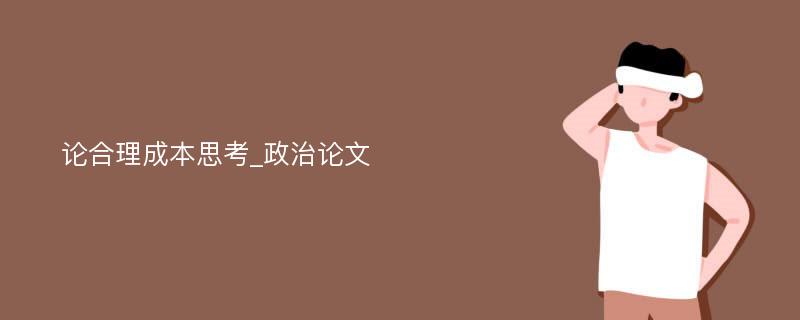
论合理的代价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价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负效应的日益突出,代价问题愈益引人关注。许多学者对代价的种类、本质、功能、成因及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为了实现代价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理化,我们不仅要有正确的代价认识,而且应具有合理的代价思维。本文拟对合理的代价思维的内涵、特点、功能及其建构作些探讨。
一、代价与合理的代价思维
在实践活动中,人们为了创造一定的价值,总要作出某种或某些放弃、付出或牺牲,这就是代价。笔者曾经提出,在实践过程中,代价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其一,主体在价值冲突或价值选择中,为了某一优先价值而不得不忍痛放弃另一部分合理有益的价值追求;其二,主体为了创价而必须或必然要作出的价值投入或付出,即成本;其三,主体在获取或享受某一价值成果的同时,不得不承担同一实践活动附带产生的不良因素或不良后果,即副产品;其四,由于人们主观的错误或失误所引发的,与创价并无必然联系的耗费、损失或消极后果等。”[①]代价的付出或承担具有经常性和普遍性,没有代价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践和价值创造,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当代代价问题的凸现说明,人们的代价决策和实践尚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而究其认识论根源,则不能不归因于代价思维的缺乏或代价思维的不合理性。换言之,当代实践向人们提出了代价思维合理化的要求。
所谓代价思维,是指人们对自身实践活动如何趋利避害、兴利除弊而进行的一种“应当与否”的判断推理,它是人的理性思维在价值观上的一种特殊运用。在现实生活中,代价思维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背理的代价思维和合理的代价思维。
背理代价思维是人们关于代价付出和承担的一种不科学、不合理的错误思维,它有多种表现形态,如有人认为,一切代价都是应该并且可以避免的,一切付出代价的实践都是不合理的实践,并由此企盼建立一个不存在任何代价现象的“乌托邦”、“理想国”;有人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宣称一切代价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它们或为进行实践和创价活动的必要前提,或为从事实践和创价活动的必然结果,因而都是必要代价或必然代价;更有甚者,有人强调创价与代价的付出成正比,代价付出越多,则创价越大,因而代价越大越好。所谓“(一切)代价不可避免论”、“学费(都是应该)论”在一定时期甚嚣尘上,除去蓄意诡辩、寻找借口等原因,不能说不是背理代价思维在作祟。代价思维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实践活动的成败得失,因而,当代实践呼唤着人们应以合理的代价思维代替背理的代价思维。
合理的代价思维,是指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具体实践中的代价的合理性进行的理性反思、评价、预测和规范,其核心、本质在于对代价的付出或承担“是否应当”、“如何应当”问题的评判与把握、分析与推理。合理的代价思维不是随意的或无根据的,因为它以实践为基础并以合真性和合义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即它既以业已获得的对客观规律正确认识的客观真理作为认识基础,以进一步求真合真;又以人类合理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价值指归,以进一步向善合义。合理代价思维具有下列特点:
(一)超前性。超前性是主体实现代价和实践合理性的前提条件,也是合理的代价思维的重要特点。首先,合理的代价思维对人们的各种价值目标和所能产生的代价的各种效应进行评估,告诫人们应注意代价取向的合理选择,以减少乃至避免不必要的代价投入;其次,合理代价思维对代价的付出、转化及分配的具体机制进行探究,启示人们应树立正确的代价投入意识,创造实现代价合理性的条件并竭力消除各种不利因素,以减轻各种必要代价,提高实践效率。此外,合理的代价思维还包含着“阵痛”意识,由于代价的投入和创价的获得有一定的时间差,人们在某些时候应该能够忍受“阵痛”,既然合理的代价是创价的源泉和方式,我们对代价应该具有远见卓识,不必为一时的代价气馁。
(二)整体推度性。代价包括在实践之中,为了促进代价的支付趋于有利、积极,避免有害消极,合理的代价思维强调对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作整体把握和精细推度。代价思维整体性推度的实质,就是系统思维与精确思维的统一。一方面,合理的代价思维认为,思维的零散性、片面性、枝节性必然导致实践活动的盲目性、被动性,从而误入歧途,导致不应有的损失。为了促进代价的合理付出,合理的代价思维注重从整体上对实践活动各环节作全面考察,而不是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细节、方面;另一方面,合理代价思维的整体推度性又包含着相对精确性,包含有定量分析。它认为,缺乏对代价的精确性思考,往往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使各种背理代价出乎意料地产生。因此,它主张尽可能精确地评估、预测各种代价的大小、范围,力图对代价作定量把握。
(三)中介——工具性。合理的代价思维是联系新旧实践的中介环节。一方面,它不断对人们过去实践的合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给人们提供“历史之镜”;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对人们的价值目标和代价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预测和评估,它虽不是却又不断构想着理想的未来,并成为未来理想的实践的催化剂或催生婆。合理的代价思维不以对代价的正确认识为最终目的,相反,它只是把自身作为新旧实践之间的中介和由现状达到理想的一种桥梁、手段、工具,合理的实践才是它真正追求的目标。
总之,合理的代价思维克服了背理代价思维的主观片面性和盲目性,第一次在实践的基础上使代价思维的合真性和合义性达到完美的统一,使人类的认识、实践与人性的合理发展联系起来,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企及的最高层次的代价思维。
二、合理的代价思维的功能
合理的代价思维是促进人们进行合理实践的认识论前提和重要工具,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它具有其他思维方法所不能替代的重要功能。
其一,描述功能,它主要回答代价“是什么”、“怎么样”。代价的本质是什么?代价在人类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代价和创价是什么样的关系?人能否或怎样实现代价的合理性?经济学等具体科学只是在具体的范围内从特定的角度对此进行描述,而合理的代价思维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间接描述,它提出不同于具体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实践模式,从而为人们提供一种特殊的关于代价的“知识”,这为人们的创价活动规定了一般的前提。
其二,解释功能,它主要回答代价“为什么”要付出或避免等问题。人在实践中为什么要付出或承担代价?不同的代价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社会效应?人类为什么应该防止和抑制不合理的代价?合理代价为什么说是人类实践的必要前提或必然结果?人类实践为什么应该和何以能够日趋合理化?等等。合理代价思维对代价的解释比对代价的描述更为深入,它对代价作何以如此这般的解释、说明,并为人们提供一整套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信念”,这些信念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人们在实践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制约和支配。
其三,预测功能,它主要回答将来的代价“是什么”或“怎么样”。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正确预测,“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②]合理的代价思维根据人类实践中代价和创价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综合考察各种现实和可能的因素,能对社会实践的未来前景作出相对准确的整体预测或预言。受社会认识系统中主体—客体相关律的影响,合理代价思维整体预测的功能表现在多种方面:(1)它可以阻止某些本来可能出现的背理代价的产生。背理代价对于创价不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有利性,代价预测可促使人们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从而防患于未然;(2)它可以促进合理代价发生量的变化。合理代价对于创价目标的实现尽管是必要的、可行的和有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代价量就绝对不可变。实际上,通过预测,人们可以创造和完善各种有利条件,减少不利因素,从而不仅可能防止背理代价,而且可以把合理代价控制在尽可能理想的范围之内。(3)它还可以促使主体自觉地投入某些合理代价,以实现创价目标。代价并非只是消极的,合理代价具有损失性和补益性双重效应,它是人们实现创价目标的必要前提或必然结果。有时,没有对代价的整体预测,人们就可能不采取某种行动,从而由此引发的合理代价也就不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合理代价的付出或承担是由合理代价思维的整体预测引起的,这就是社会预测中的所谓“俄狄浦斯效应”。
其四,规范功能,它主要回答代价“应如何”付出、承担、分配和补偿等有关问题。合理的代价思维不仅对代价进行现象描述,也不仅对人们的代价作出解释和预测,而且还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科学的规范,这突出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判定代价合理性的标准。笔者曾经提出,代价合理性的基本标准是代价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及促进社会进步的程度,这个标准可进一步量化为四个维度,即代价的必要性、可行性、有利性和公正性。人们在进行决策和实践时应据此标准作具体考察,“如果所付出或承担的代价对创价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并且创价与代价相比得大于失,代价的分配也是相对公平的,那么,这种代价就是合理代价;反之,所付出或承担的代价如果对于创价并不必要或不可行,即有失无得或失大于得,或者代价的分配具有不公正性,则这种代价就是背理(逆理)代价。”[③]合理代价思维提供的代价合理性的标准,使人们的决策和实践有了基本的依据。
合理代价思维的这些功能,不同于具体科学所作的描述、解释、预测和规范,它们更带有宏观整体性、综合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同时,我们强调合理代价思维的重要功能,但是,第一,我们并不否认实践对认识的基础地位。我们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包括代价思维,合理代价思维的各种功能之所以能够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结果,促进人类理想变为现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符合人类实践自身发展的逻辑,因此,合理代价思维的这些功能,体现了人类实践过程中不仅是自然历史过程,而且还是自觉意识过程和自主创造过程。第二,合理的代价思维对人类实践尽管举足轻重,但其作用终究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它的功能无限夸大,更不能把它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三、合理的代价思维的建构
合理的代价思维的建构,就是指主体应当如何进行代价思维、如何形成合理的代价思维。这里,我们在坚持以反映作为代价思维合理建构的基本方式的同时,着重探讨其特殊建构方式。
(一)反思。建构合理的代价思维,必须对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进行反思。不过,这种反思与旧哲学的所谓反思有原则的区别,因为后者是与实践相脱节的,如黑格尔认为:“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④]即反思既是对对象的反复思考,又是对思维自身的反身思考,因而,思维的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黑格尔所谓的反思具有辩证和唯心的双重性质,总体上并不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恰恰正是有一些反思的人,他们相信在反思中并借助反思之力,能够超越一切,然而实际上他们却从未能从反思中超脱出来。”[⑤]作为合理的代价思维建构方式的反思具有新的特点,它既不承认现有价值观念具有绝对权威性,也不承认现实实践是尽善尽美的,相反,它竭力对原有认识和实践分别进行反身思考和反复思考,并强调联系人的生存发展价值进一步反省具有价值观念和实践的理性根据及合理化机制。它是后思,即对“思”的“思”,同时又隐含一定的理性预测;它重视反思实践的本质规定性,却更强调反省实践的价值意义。因此,这种反思是后思性与前瞻性、反省性与为我性的统一,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科学的反思,它使人们得以正确地把握实践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及主体的认识能力和价值需求,从而建构合理的代价思维。
(二)批判。“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⑥]为了“改变世界”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语),人们必须先对现存世界的合理性进行审视和批判,由此确立作为现状否定形态的理想,进而通过合理的实践把理想转变为现实。作为合理的代价思维建构方式的批判,并不是消极的否定,它对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的审视和批判,是与未来的理想关系的构想和追求相联系的;它把分析与创造、破与立统一起来,把哲学的批判与人的生存发展联系起来,是建立在实践和全面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辩证的批判,是遵循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而作出的理性扬弃。这种批判不断地对人类代价决策的本体论前提、方法论前提和价值观前提进行审视、分析。由是,人们的代价思维才具有科学性、创造性、合理性。
(三)超越。对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的适度超越,是建构合理的代价思维的重要途径,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其一,对现实和时代的适度超越。诚然,代价思维是现实和时代的产物,它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并受到时代的限制和约束。但是,代价思维要具有独立性、科学性、合理性,又必须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惟其如此,它才能保证自己既不脱离现实又不为现实所淹没,更不至沦为现实的附庸。同时,尽管代价思维主体的视界及反思力、批判力、预测力都受制于一定的时代,但是,代价思维主体总是内蕴着超越旧时代的气质和力量,从而能够打破旧时代的束缚,并且如果代价思维对现状的反思、批判及对未来的构想是合理的,那么,这种被合理地构想的未来也终将变为现实。在这个意义,现实和时代孕育、创造着合理的代价思维,合理的代价思维则建构、催生着更为合理的时代和现实,从而促进着人类实践的自我超越。其二,对现存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的适度超越。主体的代价思维无疑要受到现有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的制约,但是,人们只有适度超越现有认识,才能对之进行反思、批判,从而促进人们代价认知、评价、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其三,对个人私利的适度超越。为了保证思维的合理性,代价思维主体必须打破名僵利锁,以免使其代价思维过于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和浸蚀。
在实践活动中,主体通过对现实的实践和认识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建构起合理的代价思维。一般说来,合理的代价思维的建构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代价认知,这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代价思维的起始阶段。人们要从事合理的实践,首先必须对其创造目标和代价有正确认知。实践向人们提出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代价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起因为何、表现怎样?代价在现实生活中又有那些具体表现?等等。代价的自觉认知,有利于人们保持清醒的代价意识,它促使人们进一步探寻代价的产生原因及代价与创价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而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进行代价评价和代价决策。在这个意义上,代价认知是人们建构合理代价思维和从事合理实践的认识论前提。
第二阶段:代价评价。在对代价有了正确认知之后,实践主体还应该自觉地对代价进行评价。代价评价主要是指主体对现实和可能的代价所作的预测、审视和评判。合理的代价评价对代价效应并不作机械的理解,它认为代价效应不仅是双重的,而且是动态的、可变的。一方面,代价的效应又具有时间性,这使它有着局部代价和整体代价之分,加上代价和价值主体具有多元性和社会历史性,主体的需求又是多维多向、异质异量的,因此,人们应坚持代价合理性的标准,对代价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评价。
第三阶段:代价决策。代价决策是实践主体围绕创价目标对代价的投入、转化、分配、补偿等问题进行的具体决策,它是代价思维和社会实践的中介和关键环节。主体在进行代价决策时,除了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还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其一,应优先选择、投入最有利于创价目标实现的合理代价。由于合理代价和背理代价有着截然不同的功能,为了促进创价目标的实现,实践主体应该趋利避害,在代价认知和代价评价的基础上,尽可能选择对创价目标既有必要又可行、高效的那种合理代价。其二,应在投入的代价和产出的创价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尽管人们一般都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投入换取最大的创价成果,但是,由于不同的创价、代价具有不可比和不易比性,对代价和创价大小的好坏都不能绝对化。这里,所谓代价的最小化只能是针对创价指标一定而言,创价的最大化也只能是针对一定的代价投入而言。由于具体条件的影响,有时,为了促进创价目标快速、高效地实现,主体需要自觉地增加投入以谋求规模效应;有时,为了抑制代价的恶性膨胀,主体则需要有意识地控制创价指标或减少成本以实现节约经营。因此,偏小的代价投入可能使主体不能获得充足满意的创价,而过大的代价则只意味着奢侈和浪费,合理的代价决策和合理的实践必然和只能是以合理的代价投入实现合理的创价目标。
第四阶段:适时检验。在实践中产生的代价思维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其证实部分将得到强化,其证伪部分将得到修正,从而,代价思维也日趋科学、合理。
从代价的认知、评价、决策到实践的检验,基本完成了一个代价思维周期。但是,人类价值需求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决定了人们对代价合理性的探讨也是没有止境的。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不断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并使其代价思维的合理度不断提高,从而也促使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不断趋于合理化。
注释:
[①][③]参见拙文:《论代价合理性的标准》,载《江汉论坛》1996年第8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④]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