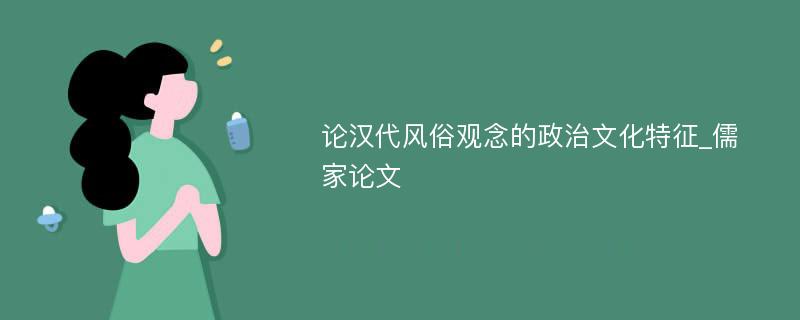
论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风俗论文,特性论文,观念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风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习的社会风尚①,是一定时代、一定群体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相对于法律、政令等强制性控制形式,风俗对社会统治的整合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软控制。正由于此,风俗往往为当时英明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特别关注。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关风俗的研究成果已很突出。然而有关两汉风俗研究的专著并不多,且多集中于对风俗史料的搜集上②;探讨两汉风俗观念的专题论文虽有一些③,但往往对政治文化和风俗观念的密切关系重视不够,从政治文化角度对两汉风俗观念进行考察分析者更难得一见。这种研究情形很难分析出古代风俗观念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古代风俗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做一初步探析,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变与不变的和谐:两汉风俗观念内涵与主题的统一
两汉时期,人们已比较注意探索风俗变化的规律,对风俗内涵的认识有着一个从整体到抽象最后再归于具体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随着两汉统治思想的变迁而变化发展。不过,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两汉风俗观念“广教化,美风俗”的主题却一直没有发生动摇。两汉诸子普遍重视风俗与政治的关系,主张通过礼乐教化来美化风俗;两汉统治者也深受其影响,在不同时期或主张顺应社会风俗,或倡导施行教化,采用各种方式移风易俗,以求化民成俗。
1.风俗内涵的正反合:从风到“风俗”再到风俗
风俗是一个在历史传承中不断更新的概念,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文化事项。古人在对风俗进行观察和表述时,往往又使用各种不同词汇,诸如风俗、风土、风尚、风教、流俗、民俗、世俗等。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人们出于各自的语境,对风俗进行的解释与评论也不完全相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决定了中国古代风俗的内涵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当中。
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并无“风”而有“凤”字,如卜辞中有“于帝史凤,二犬”。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一文从词源学考证“风”曰:“从隹从凡,即凤字,卜辞假凤为风。”关于以“凤”代“风”,郭沫若解释为:“是古人盖以凤为风神……盖风可以为利,可以为害也。此言‘于帝史凤’者,盖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二犬。”可见,“风”由“凤”假借而来,殷商时人看到“风可以为利,可以为害”的自然特性,就以凤为风神,把其神化为上天的使者④。
春秋时期,风在指自然现象的基础上,渐次出现风气、民间音乐等义项。在此基础上,先秦官方将先王之乐的教化作用与民众风俗文化直接相连,提出“天子省风以作乐”⑤的命题,使得风俗具备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品格。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演进也启发荀子将礼乐并举,使二者真正统一于教化风俗的目标之下,移风易俗作为儒家对先秦礼乐教化政策实质的概括而诞生,也为汉代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政策准备了充分的历史和理论资源⑥。
两汉时期,儒学昌盛,风的自然性更被广泛借用到社会文化方面。儒家士大夫倡导礼乐教化,他们普遍认为风有特殊的政治感染力,具备化导社会的作用。《汉书·律历志》载:“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⑦从凤鸣中分出十二音调,从而把凤、风与音乐、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这一认识前提下,两汉时人进一步形成了“诗教”理论⑧。他们普遍认为《诗经·国风》是天子派遣乐官到民间各地采集风谣整理而成的,以便通过风谣的内容来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为政府制定或调整统治政策提供相应的依据。为此,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倡导这种理论,并将之较成功地运用到政府日常议政、行政的实践活动当中。
“风俗”一词,较早见于《庄子》、《荀子》等书⑨,但关于其确切内涵,直至两汉时期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了比较明确的阐释与解读。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比较重视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对风俗概念的认识也有着一个随政治统治思想变迁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从而最终完成了对风俗概念内涵理解的正反合。
汉初,陆贾汲取秦以法为教、苛政而亡的教训,提倡采用无为教化的方式来美化风俗、“正风俗”⑩、“一风俗”(11)。随后,贾谊也在批判秦末汉初风俗败坏的基础上,认为“教训正俗,非礼不备”(12),主张“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13),通过兴建礼乐文化制度来移风易俗。他们虽从整体上对风俗已有所认识,但却显得有些空洞,只是意识到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至于风俗的内涵到底包括些什么并不清楚,而且似乎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淮南王刘安集其门客编写《淮南子》一书时,风俗的内涵开始得到初步探讨。他们意识到风俗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认为风俗“所受于外”(14),“时移则俗易”(15),在强调各地风俗互异,相互之间没有优劣标准的同时,主张采取“神化”的方式来“齐俗”(16)。随着汉武帝对儒学的提倡,董仲舒则开始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来审视风俗文化。他认为“教化行而习俗美”(17),主张兴建太学,大力发展教育,以道德和礼乐来教化风俗。
不过,直到西汉中期,两汉诸子仍大多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待风俗,也没有对风俗概念再做出进一步的阐释,至于有关专门探讨风俗具体内涵的篇章或书籍更是尚未出现。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具体风俗的理解有所偏颇,大都抛开下层民众在风俗中的主体性不谈,对风俗的论述也仅限于关注风俗与国家政治文化秩序之间的重要关系,片面强调上层社会的教化功能。
此后,随着对风俗政治教化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风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为发端,开始出现专门论述风俗的篇章。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划分了八个较大的风俗区域,而且对有关风俗概念的理论也有了一定的讨论,认识到风俗文化与地域以及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
及至东汉,随着儒家思想文化独尊地位的日益强化,人们对风俗概念的理解逐渐达成初步共识。他们对风俗概念的内涵加以界定,将与水土等自然因素有关的习尚称之为“风”,而与教化等社会因素有关的行为习惯则称之为“俗”,从而赋予了风俗自然和人文的二重内涵。在此基础上,人们也逐渐开始探讨具体风俗甚至下层民众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班固是第一个明确对风俗概念内涵加以界定的学者。他在《汉书·地理志》中对成帝时张禹属员朱赣所条理的各地风俗“辑而论之”,并且对“风俗”概念做出了明确阐释。他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8)认为风是因水土等地理条件而形成的民俗性格、言语歌谣等,俗则是因统治者的好恶而形成的社会趣味、情感、欲望与行为等,且随着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风与俗组合而成的“风俗”兼有自然性与社会性两重因素。班固对风俗内涵的定义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北齐刘昼仍认为“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已成性,谓之俗焉”(19),一脉相承地赋予了风俗自然和人文的双重含义。
而且,班固的风俗观还有更为重要的第三层内涵。他认为,“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20),试图将自然环境的不同形成的“风”和社会条件发展下形成的“俗”统一于王道教化这一“中和”的理想境界中,从而成就君主的德教,形成理想化的风俗。由于这一层内涵长期以来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以至于现代学者对班固的风俗观也没有给予相应的正确评价(21)。
东汉末年的应劭不仅写成了中国最早的风俗专著《风俗通义》,将风俗当做一学术门类进行探讨,而且还对风俗概念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他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22)应劭用列举的方式对风俗的内涵进行阐释,认为“风”是指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俗”是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趣味、情感与行为习惯等,使得风俗概念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风俗通义》虽然冠名“风俗”二字,但书中“俗”字比比皆是,却极少使用“风”字,也反映了风俗一体化和具体化的认识观念。并且,与班固对风俗的抽象理解不同,应劭把观察风俗的视角深入到了社会下层,试图探讨下层民众具体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而又将俗区分为本俗与正俗两种,以图“辩风正俗”。
到了汉末,曹操更是身体力行,直接从整顿具体风俗入手,禁断陋俗,“一之于法”(23),以期美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文化秩序。
可见,通过对风俗概念的不断探讨,两汉诸子对风俗的认识有着一个从整体到抽象最后再归于具体的过程,从而最终完成了对风俗概念内涵理解的正反合。
2.风俗主题的永恒:广教化,美风俗
由于风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两汉风俗观念一直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内涵,这在“广教化,美风俗”的风俗主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民只能在善良的风俗中过着谐和合理的生活;而政治的根基,必植基于善良风俗之中。所以政治的基本任务及最高目的,乃在于能移风易俗”,“这是战国中期以后发展出来的政治共同理想”(24)。两汉诸子和统治者大都认为风俗的美恶能够反映出政治的兴衰,政治上的败坏应归根于风俗的沦丧。因而,他们都十分重视风俗的教化作用,主张利用风俗的软控制功能,通过“广教化,美风俗”的途径来实现对民众的政治统治,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移风易俗,天下皆宁”(25),《汉书》中亦有贾山“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26)的言论。
由于风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27),这就存在一个为达到美化社会风俗目的而如何进行风俗融合的问题。是因袭、引导、齐整还是禁止,这对于风俗的转变影响巨大,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方式钳制思想,实施残暴苛刻的法治,“匡饬异俗”(28),结果不仅未能预防、改造“恶俗”,无法真正实现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反而终因不得民心而致使秦朝在经历短短十四年之后即告灭亡。
两汉时期,鉴于秦迅速覆亡的深刻教训,统治者和政治家们认识到,天下能在“马上得之”却万不可在“马上”治之(29),对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统,还须依靠教化才能真正实现和长久保持。但鉴于民生凋敝,汉初统治者采用的实为黄老思想,主张休养生息。直至武帝时代,在淮南王刘安、史学大家司马迁等人的思想中仍渗透着不少黄老理念。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0)等融合风俗的方式。
不过,随着汉王朝统治思想由崇黄老转向尊儒术,人们的风俗观念也逐渐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与黄老学派顺应自然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风俗融合主张不同,儒家学派则主张通过“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自上而下的教育感化方式来美化社会风俗(31)。
美化、齐整进而同一风俗是儒家建立社会文化新秩序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随着汉王朝国力的强盛,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大一统思想逐渐抬头。与此相适应,风俗同一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如武帝时期,终军就认为:“夫(人)[天]命初定,万事草创,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于无穷。”(32)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均热心于风俗的整合,力求将风俗纳入礼的规范。汉武帝曾下诏:“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33)在此,武帝广泛求取、任用精通礼乐的贤才,就是希望通过他们来推行礼乐以教化社会民众,其移风易俗的意图十分明显。由章帝钦定的《白虎通》也说:“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泆,节其侈靡也。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34)这里,礼乐用来防备、教化民众恶风陋俗的作用被清楚地写入官方法典,移风易俗作为统治者的政治文化政策被正式发布。
“‘移风俗’,要将社会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为良好的社会生活习惯;使人民生活在良好社会生活习惯之中,收‘徙恶迁善而不自知’的效果,亦即是成为道德与自由,得到谐和统一的效果。这两者是密切关联而不可分,应以此为朝廷政治的大方向。这是自贾山、贾谊、刘安及其宾客以逮董仲舒们所极力标举的政治原则”(35)。在百家逐罢而儒术渐尊的思想文化氛围中,经过贾谊、董仲舒、刘向、班固等大儒的持续发扬,由荀子所首倡的移风易俗命题作为儒家重要的文化主张,终于变成大一统文化政策的现实,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统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点。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提倡的力求通过圣王“移本易末”来使风俗齐一的“中和”风俗观逐渐变成了社会所宣扬的主流。
由此可见,虽然班固《汉书·地理志》在原材料上与《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风俗观念却有着很明显的差别。宋超曾指出,“不论在总体思想上,抑或在具体问题上,班固与司马迁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司马迁所热情歌颂的游侠和货殖者,正是班固所着力批判的”(36)。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也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7)。其实,这番评论正可看做两者风俗观念存在明显差异的一种佐证。而这种差异,实际上也正反映出两汉风俗观念的发展转变过程。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为维护其统治所提出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而两汉则是这一风俗教化理论的完善期。有学者就认为,美化社会风俗是汉王朝重视教化的原因之一(38)。换句话说,统治者重视教化的目的正是为了美化社会风俗。而且,风俗教化具有政治意蕴,是一种政治概念,它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汉王朝是为了巩固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而提出并实施风俗教化的。在这一时期,风俗教化被提升到巩固国家政权、关乎国家命运的高度,移风易俗逐渐成为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既是汉王朝对风俗教化地位作用的高度重视,也是汉王朝为风俗教化注入的新的政治文化内涵。
在日常各种政事措施和策略中,两汉统治者往往考虑到风俗教化的重要意义,极力引导人们避恶向善。在对民众进行教化时,两汉诸子及统治者既强调社会教育风化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行为对民众有着极强的感化作用。因为在儒家学者看来,教育和感化同样重要。如贾谊认为:“天下之命,县(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39)行教化重要的是教育太子,因为太子是储君,而君主的善恶又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乱,教育和感化同时集中在太子身上,成为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履行的义务。
不过,两汉诸子主张由上而下的整合方式,结果往往将风俗的改变完全寄希望于上层统治者身上。如董仲舒说:“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40)这种观念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对改变风俗的作用,而忽视了来自民间的力量,更没有考虑到民众在风俗变迁中的主体性,故而有其不合理性,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如史载,为了改变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奢侈风尚,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但最终却只落得一个“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的效果(41)。
二 独立与顺从的交融: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的互动
由于风俗的好坏逐渐成为一个代表国运盛衰的征兆,因此不能不引起两汉诸子和统治者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两汉诸子在不断加深对风俗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围绕风俗问题提出了各种移风易俗理论,试图化民成俗。他们或主张因循风俗,稳定社会文化秩序;或主张美化风俗,宣扬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或主张齐整风俗,实现六合同风的理想;或直接对风俗展开批判甚至整顿,以求匡正时俗,扭转社会不正之风,等等。
汉初,由于饱受秦朝暴政和战火的摧残,社会满目疮痍,经济萧条。摆在当时统治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统治秩序。至于移风易俗,显然不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同时,汉王朝是刘邦集团“反秦”之后继而又“承秦”的产物(42),若想避免重蹈秦亡覆辙,则既要反对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统治方式,又需在不触动秦朝各地旧俗的前提下塑造新的统治秩序。主张清静无为、因俗而治的黄老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直至文景时期,政府统治思想较之以前虽已发生些微变化,对儒学开始有所关注,但基本上仍趋向于道家、刑名之学,采用无为政治。
不过,无为而治对风俗的改变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而“以法为教”主要也是在去除恶俗,虽对齐整风俗有所促进,但与儒家主张的有意识地、大规模地移风易俗有着根本的差别。因此,随着对美化社会风俗的期望,人们在遵奉无为政治思想的同时,开始逐步意识到只有儒家教化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化民成俗。
在对秦朝恶风陋俗批判的基础上,陆贾首先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新理念。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化民,统治者只有奉行黄老无为思想,以身作则,施行教化,才能得民心,定大局,美化社会风俗。为此,陆贾总结了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着重阐释了以仁义为体、以刑罚为用的教化思想(43)。他希望统治者能够行礼乐教化,正风俗;修仁义道德,美风俗;同圣教好恶,齐风俗,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处于有序的统治之中,才能美风化俗。
陆贾是汉初群臣中立足现实,系统阐述秦亡原因的第一人,也是汉王朝建立后,重塑治国理念,明确提出统治者应身体力行,以礼乐教化和仁义道德治国,进而美化社会风俗的第一人。虽然陆贾美化风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统治者足够的重视,但在听到陆贾的治国新理念后,原本轻儒的高祖刘邦也逐渐意识到礼乐教化、仁义道德等有关风俗的软控制方式在政治统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徙儒者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过鲁,以大(太)牢祀孔子”(44)。
贾谊在论世议政时也非常重视风俗。在其政论文章中,贾谊不厌其烦地大谈风俗,把其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来加以重视和强调。通过对秦末汉初社会风俗的批判,贾谊得出天下治乱的关键在于风俗好坏的结论。
在贾谊看来,要想使淫侈的社会风俗得到根本的改善,教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为此,贾谊提出“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45)的教化主张,认为统治者应将教化视为政治的根本,若不务教化,就不能真正化民成俗。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广大民众,创建礼义制度,阐扬礼乐文化,以德教民,则是教化的重要内容。另外,贾谊还将教化的实行归结为统治阶层自身的修养和以身作则,“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46)。一句话,面对汉初风俗败坏的局面,贾谊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主张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基础,实行礼义教化,采取开明的“明君贤吏”政治路线,移风易俗,从而实现美化社会风俗的目的。
作为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和贾谊的思想深刻反映了汉兴三十多年来政治形势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显示出这一阶段政治统治理论从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向维护集权一统的有为政治过渡的趋势(47)。同时,他们都以得民、安民为治国之本,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以实现美风化俗的目的,而这正是风俗观念超越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鲜明体现。从无为政治向儒家礼治的发展,明显地体现了司马谈所谓的汉初儒家“以《六艺》为法”、“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思想倾向(48),也为汉武帝尊崇儒学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风俗文化也被正式提到汉王朝的议事日程上来,并受到时人的普遍关注。董仲舒认为,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仍是“习俗薄恶”,统治者“亡以化民”,不能给社会风气以有力的引导和影响(49)。因此,政府只有改弦更张,推行教化,才能实现“上下和睦,习俗美盛”(50)的理想境界。为此,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推行礼乐教化;兴办太学,培养教化风俗人才;选拔贤士,为民表率,移风易俗。
董仲舒以教化治国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思想方略,对于完善、巩固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做出了不可抹杀的功绩。自武帝起,关于风俗教化的主张被统治者所接受,开始实施设立五经博士、开办太学以及兴建地方官学等一系列和化民成俗有关的政府教化行为。
不过,诸子的风俗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除董仲舒等人提倡儒家风俗教化思想外,也有《淮南子》众作者以及司马迁等人对单纯采用儒学来齐整风俗表示不满。这种现象表明,风俗观念在受到统治思想影响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相对的独立性。
《淮南子》的风俗论综合反映了西汉前期的风俗观念,它对于风俗何以形成、因何变化、不同群体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风俗以及对不同风俗应如何评价等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51)。《淮南子》认为,风俗的形成是受外界影响的结果,其必然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此,它在《齐俗训》中提出“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的原则,要求统治者要根据当世的实际情况来移风易俗。又由于风俗因地而异,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在形式上虽有很大差异,但所表达的实质内容一致,“未必无礼也”,没有文明和野蛮之分。因此,统治者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应顺应各地、各族风俗,入乡随俗,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不可强为之一。
对于通过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淮南子》持不置可否的观点。能否运用法律来干预风俗,《淮南子》则表达了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氾论训》承认法律对风俗的制约作用,“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视法度为调节风俗的手段。《主术训》却认为“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对刑杀持否定性意见。这是因为,在《淮南子》看来,风俗问题最理想的效果是“道胜而理达”、“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憺然无欲而民自朴”,应该用诚心感化来移风易俗。《淮南子》还常提到“圣人”、“先王”的作用,肯定居于统治地位的权要人物对社会风俗的特殊作用,主张统治者“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简单来说,在移风易俗问题上,《淮南子》是以黄老道家思想为指导,它虽不排除教化和刑法所能起到的作用,但认为根本上还是“神化为贵”,其中统治者的以身作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淮南子》是刘安及其门客所编写而成,其成书的时日,黄老道家学说虽仍暂居优势,但自战国时起就被看做“显学”的儒家思想,正以其特殊优势,显示着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独尊地位的动向。《淮南子》努力维护黄老道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同时不得不应对儒家学说的挑战。因而,《淮南子》的风俗论在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和儒家教化思想的渗透下,同时保持着自身的特点,体现出风俗观念的独立性。
司马迁对风俗十分重视,他通过壮游全国的社会实践,对各地的风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并将其大量地叙述到《史记》的相关篇章中,反映出自己对风俗的新认识。司马迁主张“因民而作,追俗为制”(52),统治者应根据风俗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他还特别肯定音乐对教化的首要作用。在《乐书》中,司马迁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音乐对风俗人心的影响,认为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53),主张通过音乐来潜移默化民众,变革风俗民心。司马迁还重视采风入乐,明确提出采风俗而助政教的观点:“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54)更可贵的是,司马迁明确提出了风俗具有地域性的特征,重视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风俗加以记载和研究。他还发现地域风俗同经济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货殖列传》就集中记载了生产活动与地域风俗的关系。
另外,对影响风俗的部分特殊群体的关注也是司马迁风俗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司马迁首次为循吏立传。这些循吏虽因循风俗却能化民成俗,司马迁为其立传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只有官吏以身作则,才能真正美化社会风俗。与循吏相较而言,酷吏以杀伐立威,他们从没有把“化人心”作为自己治政的目标,因而不能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难以胜任治理大业。对于游侠给社会风俗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占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司马迁也持赞赏或重视的态度。
司马迁的风俗观念代表了西汉中前期儒学仍未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时的风俗思想。从武帝开始,儒家学说逐步成为政府的统治思想,但由于当时司马迁并没有受到儒学思想的太多浸染,因此,司马迁对风俗的评论,并不以儒学为唯一标准,且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他虽推崇儒学,但并不排斥百家,最终成为“子学时代”“具有独立人格、学风和文风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55)。
实际上,汉武帝也不过是把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招牌,借以宣化风俗,并没有赋予儒者管理国家的权力,采用的是阳儒阴法之术(56)。直至西汉中期,统治者对于各地风俗文化面貌的差异并不急于改变,也没有太多的闲暇去做改变。在这种统治政策的影响下,汉儒对风俗的齐整并不深入,各地风俗仍未发生太大的变化。
西汉中期以后,儒者士大夫逐渐构成了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元、成以后更是形成了帝室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情势(57)。因此,两汉统治者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必须充分接受和利用儒家学说,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随着儒学的普及,两汉政府对风俗的整饬、齐一也开始采取政教结合、以教为主的循序渐进方式。在齐整风俗的过程中,两汉政府特别注重以经易风,力图将一切风俗都纳入到儒家的礼义规范中去。
刘向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力主礼乐教化的大儒。他把礼乐教化当做治国的根本,特别重视音乐的社会政治作用。刘向还将礼乐与刑政相提并论,认为礼乐和刑政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同民心而立治道”(58)。不过,他也认识到“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59),刑法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如果舍教化重刑法只会带来风俗败坏的严重后果。可见,刘向对礼乐的提倡,是把礼乐教化当做治国安邦的政治工具,以图实现其理想伦理政治的目的。
针对当时矛盾重重、衰微破败的政治局面,刘向也提出了一些缓和社会危机、扭转社会政治风气的积极主张。他认为,君主只有正身修己,为政以德,崇俭抑奢,才能化及万民,美化社会风俗,稳定政治统治。修德是君主能够保有天下的最好办法,只要修德,不祥的征兆就会得到化解。
刘向生活在西汉元、成之际,当时儒家学说已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他编书言得失,以改善政风,其中许多论述都是对社会政治风气的关注,体现出刘向对风俗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
班固是第一位自觉认识并阐释风俗概念,进而确立传统风俗观的学者。如前所述,他认为风俗是地理环境和社会教化的共同产物,所阐释的风俗实有三层涵义。班固处于儒学正统化的正式确立阶段。受正统儒家文化的浸染,班固虽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地域经济风俗观念和风俗变革思想,但却进一步以儒家正统观念对其加以改造、完善,扭转了司马迁一味强调经济因素的倾向。班固综合各个方面,对风俗做了较为详细的界定,不但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司马迁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使对风俗的认识得到了理论的升华,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结论。
班固风俗观中最为重要的是其王道教化移风易俗思想。经过武帝独尊儒术,宣帝石渠阁会议再到章帝的白虎观会议,儒家正宗思想完全成为官方的支配思想,并进一步法典化、神学化。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正是儒家思想神学化的兴盛时期,班固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儒家政治理想是实行仁政,轻徭薄赋,使民以时,以教化化育百姓。班固的王道教化风俗观力求使风俗达到理想化状态正体现了这一点。班固强调风俗的等齐化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状态,但却常常是古人所要追求的目标。
对鬼神的信仰两汉一直盛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支持,谶纬神学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直接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社会上层流行谶纬神学,下层则盛行巫术迷信,而且上、下层之间的信仰也互相渗透和影响,谶纬迷信泛滥成灾。两汉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谶纬神学的这种社会危害,从而形成了一股反儒学谶纬化的思潮。王充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在《论衡》中,王充采取批判的方式,以理智的求实精神看待各种迷信风俗和虚妄之言,对各种风俗现象和迷信观念进行分析,以求“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60),“匡济薄俗”(61)。王充对儒学谶纬化的原因及其流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批评,认为经学的谶纬化与政治有关系,是衰乱时人为编造的。他解释说:“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遣告人言矣……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而谓之上天为之,斯盖所以疑也。”(62)对当时社会风俗中普遍存在的鬼神迷信,王充也展开了全面批判,其《订鬼》、《论死》、《死伪》、《纪妖》等篇详细批判了人死为鬼的陋说。基于对人死无知和死不为鬼的认识,王充又对当世的厚葬陋习和淫祀之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厚葬不仅造成物质上的损失,同时也是诱人为奸的原因之一。至于其他陋俗,王充亦有涉及,如《四讳》、《讥日》、《卜筮》、《辨祟》等篇批判了佞卜、讳忌等陋俗。最后,王充总结说:“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意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63)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程度加深,经学日趋衰落,社会上出现一股猛烈抨击当时腐朽社会风气,要求整顿社会风俗的批判思潮。王符、应劭、曹操等人,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代表。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上层奢侈腐化,吏治腐败,百姓流离失所,风俗极为败坏。为此,除了反对神学迷信外,他们把更大的气力用在了反对官场和社会中的恶风陋俗上。
通过批判骄奢淫靡之风、巫祝迷信之俗、以阀阅取仕之弊等,王符提出“移风易俗之本,乃在开其心而正其精”(64),“凡欲变风改俗者,其行赏罚也”(65),主张政府采用教化和法制的双重手段,力倡以民为基、富而教之,德法并用、知贤用贤的统治政策来加强对社会风俗的整顿,以期实现“变风易俗,以致太平”(66)的目标。同时,王符还高度强调了统治者在整顿风俗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认为“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67)。
应劭试图通过著书立说来“匡正时俗”,为政之助。因此,其著述多为礼仪风俗之作。特别是《风俗通义》对风俗专门研究,其中对风俗的相关论述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应劭将观察风俗的视野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通过丰富风俗概念内涵,使风俗观念具体化的特殊方式,提出了“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68)的主张。
应劭在阐释风俗概念中还提到风俗存在的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69)。对“本俗”的关注、对“圣人”于风俗的作用即“正俗”的重视成为应劭风俗概念的两大主旨。应劭之所以探讨风俗,其目的正在于“辩风正俗”,在“王室大坏”之际,将“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斑驳杂乱的“本俗”咸归于“正俗”(70)。
在应劭的理解里,风俗更大程度上是指民间浅俗,“虽云浮浅,然贤愚所共咨论”(71),是自己窥探现实社会,进而寻求解决现实危机方案以“匡正时俗”的一扇特殊窗口。应劭试图借风俗来佐治国家、教化人心,在乱世中“辩风正俗”,挽救社会危机。
曹操则直接从对具体风俗的整顿入手,主张禁断陋俗,“一之于法”;倡导良俗,以身作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可见,在崇尚使用法律手段禁止恶风陋俗的同时,曹操也时刻不忘强调道德和教化在整顿风俗中所承担的重要作用。
由于两汉诸子始终把风俗作为其议政论学的关注焦点,因而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研究过程;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命题,系统地论述了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72)。在这种移风易俗观念的持续影响下,两汉统治者也把对风俗的教化提升到了国家施政政策的高度上来。在平时议政中,他们注重对风俗问题的讨论;在日常行政中,他们更注意采取美化和齐整风俗的措施(73)。
两汉统治者认识到上层社会特别是皇帝本人对风俗的重要引导作用,他们宣扬以孝治天下,通过不断发布诏令和制定相关政策来禁止陋俗和提倡美俗。如汉武帝察举孝廉,目的在于“化元元,移风易俗”,还下诏说“广教化,美风俗”是公卿大夫的职责所在(74)。两汉政府还不时遣派风俗使到各地采集民众风谣,考察其风土人情变化,作为调整或改变统治政策的依据,后来除了解下情外,逐渐也成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整肃吏治的一种重要方式。另外,两汉政府还规定州牧刺史定期奏报各地风俗,或利用“上计吏”来了解郡国政风民情。而两汉循吏则在行政实践中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教化或整顿风俗,以求化民成俗。
可见,移风易俗作为教化政策不仅被提到了统治者的施政日程上来,并且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而移风易俗理论在影响统治者风俗政策的同时,也在统治者风俗政策的推动下不断得到扩充、深化和完善。两汉诸子移风易俗理论和统治者所实行的移风易俗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恰好体现了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一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关系。
综上言之,两汉时期,人们往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风俗,一般都比较偏重于探讨和处理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其一,风俗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与始终保持永恒的主题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自身在社会政治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和谐;其二,两汉诸子及统治者在对待风俗问题上,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采取的移风易俗方式多种多样,或因循、或宣化、或齐整、或批判甚至整顿等,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一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
①《辞海》对“风俗”的解释之一就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缩印本,第1726页),《辞源》的解释为“一地方长期形成的风尚、习惯”(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缩印本,第1854页)。但在中国古代,古人理解的“风俗”含义包容面更广,不仅包括我们今天常说的“风俗习惯”,还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风气”,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不过,两者之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往往相互渗透和转化。
②如瞿兑之的《两汉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韩养民的《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其中邓子琴的《中国风俗史》(巴蜀书社1988年版),直到1988年才以遗稿的形式最终问世,且第一编先秦及西汉部分已佚,无疑是学界的一大遗憾。彭卫、杨振红在其合著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中指出,风俗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于有关风俗的思想之中,这既是秦汉风俗观的中轴,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一条基本脉络。这是较为精辟的论述,然仅见于序言当中,在正文中未能加以详尽探讨。
③丁毅华对西汉时期人们的风俗观念曾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发表有《“习俗恶薄”之忧,“化成俗定”之求——西汉有识之士对社会风气问题的忧愤和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淮南子〉的风俗论》(《学术月刊》1991年第6期)等相关文章。前者重点讨论了西汉时期士人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批评和对策,是西汉士人整体上的风俗观。后者则以《淮南子》为研究对象,使《淮南子》中的风俗思想得到了初步系统的发掘和清理。萧放在《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古代学者的风俗观关注风俗发生的地域性与政治性,对风俗的教化功能有着特别的强调。拙文《论班固的风俗观》(《南都学坛》2004年第6期)认为,班固第一个对风俗做出阐释,其风俗观奠定了中国古代风俗理论研究的基础。陈新岗的《两汉诸子论风俗》(《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两汉诸子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风俗的形成、演进及其功能,对两汉社会及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该文相对比较简略,没有对两汉诸子的风俗观展开详述,更没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因而尚不能够确切反映出两汉时期风俗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无法深刻认识两汉风俗观念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④以上内容主要参考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考释·天象》,相关引文亦转引于此。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383、377~378页。
⑤《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杜注:“省风俗,作乐以移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24页。
⑥杨辉:《从“风”到风俗——论“风”的文化化历程与先秦音乐“移风易俗”政策之酝酿》,《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⑦《汉书·律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59页。
⑧韩经太:《“在事为诗”申论——对中国早期政治诗学现象的思想文化分析》,《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⑨庄子最先对“风俗”做出解释。《庄子·则阳》篇载:“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09页)在此,庄子主要揭示了风俗“合异以为同”的群体性特征,其对“风俗”的解释还远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风俗”。荀子在《荀子·强国》篇中说:“入境,观其风俗。”(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页)这里的“风俗”指的是秦国百姓的性情、对官方的态度以及其音乐、服饰等方面共同的文化特征,其内涵大致已与现代汉语中的“风俗”一词相当。《辞源》就是以此句作为“风俗”含义的典型例证。
⑩(11)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157页。
(12)(13)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4、204~205页。
(14)(15)(16)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75、796、614页。
(17)《汉书·董仲舒传》,第2504页。
(18)(20)《汉书·地理志》,第1640页。
(19)傅亚庶:《刘子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3页。
(21)详细讨论参见拙著《论班固的风俗观》。
(22)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23)《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页。
(2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1页。
(25)《史记·乐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11页。
(26)《汉书·贾山传》,第2336页。
(27)《汉书·王吉传》,第3063页。
(28)《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5页。
(29)《汉书·陆贾传》,第2113页。
(30)《史记·货殖列传》,第3253页。
(31)《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89页。
(32)《汉书·终军传》,第2816页。
(33)《汉书·武帝纪》,第171~172页。
(34)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3~94页。
(3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86页。
(36)宋超:《〈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学术月刊》1985年第10期。
(37)《汉书·司马迁传》,第2737~2738页。
(38)刘厚琴:《东汉道德教化传统及其历史效应》,《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
(39)《汉书·贾谊传》,第2251~2252页。
(40)《汉书·董仲舒传》,第2521页。
(41)《汉书·食货志》,第1160页。
(42)详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6页。
(43)朱海龙、黄明喜:《陆贾教化思想探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4)《汉书·高帝纪》,第76页。
(45)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保傅》,第186页。
(46)《汉书·贾谊传》,第2245页。又见《汉书·礼乐志》,第1030页。
(47)苏志宏:《秦汉礼乐教化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48)《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0页。
(49)(50)《汉书·董仲舒传》,第2504、2515,2520页。
(51)丁毅华:《〈淮南子〉的风俗论》。
(52)《史记·礼书》,第1161页。
(53)(54)《史记·乐书》,第1206、1211,1175页。
(55)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56)余杰:《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8期。
(57)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4页。
(58)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7页。
(59)《汉书·礼乐志》,第1034页。
(60)《后汉书·王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9页。
(61)(62)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7、784页。
(63)《论衡·解除》,第1046页。
(64)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1页。
(65)《潜夫论笺校正·三式》,第209页。
(66)《潜夫论笺校正·浮侈》,第140页。
(67)《潜夫论笺校正·德化》,第380页。
(68)(70)(71)《风俗通义·序》,第8、8、16页。
(69)王素珍:《〈风俗通义〉的风俗观研究——兼论〈风俗通义〉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价值》(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3年,第21页。
(72)孙家洲、邬文玲:《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
(73)拙著:《“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
(74)《汉书·武帝纪》,第166~167页。
标签:儒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风俗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司马迁论文; 董仲舒论文; 淮南子论文;
